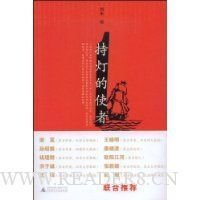持灯的使者读后感精选
《持灯的使者》是一本由刘禾(编)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持灯的使者》精选点评:
●徐晓有真情,马佳有隐情,舒婷只有矫情!
●可以和赵越胜的<<燃灯者>>一起读. 阿城的那篇特别有意思
●这本书也许会改变我
●M
●不喜欢这样的一种颇为粗糙的表述,尽管它是历史。
●大陆滞后九年……
●删节极端严重。以至于可能产生误导。不推荐阅读大陆版。
●看到作者走入地坛公园,遇见史铁生,突然觉得,这世上千千事,很多已经注定要发生,顺其自然就好,周末去杭州面试,带这本书送给德见兄,算是回赠于他,一个月前去杭州他送的《我与地坛》,来回奔波考试的路程中读完,内心充满着感激。
●THE BETTER YOUTH.
●今天以及关于今天的人,猴子,北岛。。。喜欢那个时代的这群人。
《持灯的使者》读后感(一):在时代的黑色画布上他们写诗
lt;文章来自个人公众号“小白楼来信”(tjletters),欢迎关注>
《持灯的使者》读后感(二):我们当下的生活是否真实
读到其中的文字,内心积聚不仅是力量,更多的还是感伤。纵使在网上无法查询到关于《今天》这份民间刊物的确切资料,纵使这样一群才子仅仅被扣在“朦胧诗派”的帽子之下,纵使他们如今已经各奔东西彼此相安无事,他们对至于那个年代,对至于现当代文学,对至于他们自己都已做到最好(姑且用“好”字来评说他们的努力)。正如安德烈巴赞之于法国新浪潮,郭路生给北岛、芒克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艺术道路的指引,更是生活上实实在在的关怀。幻想自己拥有这样的良师益友,还会去企图未来生活安逸稳定祥和吗?
羡慕他们曾经单纯、执着的奋斗。某种程度上讲,安逸近似虚无,正如黑色的眼睛陷于黑夜。
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不真实。。。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 ——欧阳江河
《持灯的使者》读后感(三):风中往事
买《持灯的使者》时略忽犹豫了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怀旧,所以才读回忆文字。上午与若海聊天,谈到青春逝去,一事无成,若海说我“老气模秋”,这倒是事实,十年多年我就自称“黔南老人”。“还没年轻就已老去。”我对若海说。在心智上我是没有青春期的,一开始就老,所以总也不成熟,像一只出生时就满脸皱纹长着胡子的山羊?这比喻是否恰当?
此书是海外版《今天》上怀人的文字,今天的老将们回忆《今天》岁月的文章,好些篇章我零散地读过,买此书,也是怀旧心态作祟。无论这帮人当年如何受苦受压迫,今天都算是出头了,成功地使自己钉入了“中国诗歌史”,至少是“中国诗歌运动史”。套用一句煽情的话,“足以安慰平生的沧桑”。
但在中国南方,并不晚于今天的贵州诗人们,至今仍然默然,不为人知。在今天前后,贵州的黄翔、哑默等早就开始了严格意义上的纯正诗歌写作,也办有《启蒙》等民刊,也曾上京去“轰动”……但历史走到今天,除了一些论文之外,很少有文章提到过中国诗歌在南方觉醒的这段历史。其原因,与贵州这批诗人没有主动的“写史”意识,没有宣传性的出版物有关系。如果将黄翔、哑默、路茫们的诗歌往事披露出来,后人将会看到,他们所做的贡献,他们的“惨烈”超过了海洋淀诗群或《今天》派。
贵州诗歌往事,也只有哑默收藏了,他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故事的亲人们》、《见证》等回忆性大著作,但至今因为种种原因也未能在大陆公开出版,甚为遗憾。今天派有赵一凡,贵州有哑默,哑默不仅收藏了那个时代,也是一位创作出重要作品的诗歌健将。
有些往事,渐渐在风中消失。
有些故人,渐渐在风中老去。
有些历史,却不是政治或时间所能压抑住它的良知与巨痛。
《持灯的使者》读后感(四):远去的,还在闪烁的灯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您看着眼熟吧,没错,这就是北岛《回答》的初稿,修改后首发《今天》的第一期。出身栏填着“地下文学刊物”的《今天》是中国当代诗歌不可绕过的重镇,她的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来自《持灯的使者》一书。此书对于读者,无疑具有文献意义和解密的诱惑;对于亲身参与的人,她是一次灵魂随之悸动的回望。
齐简展示了沾满铁狮子胡同旧称谓的记忆的诗句,如东四老房子改造,露出埋没的地基。田晓青耿耿于十三路公交沿线,他被沿线的站名撞了一下腰,那些凌晨的、朗诵的、贴在西单墙上的诗句,沉淀为小小的、顽强的、带着痛和快乐的结石,将伴随诗人一生。齐简回忆当初借着煤油灯读食指的诗,第二天“满脸的油烟和泪痕。”他们后悔过么?我边读边问自己。诗人们或死去或改行或继续写着,还有的困在精神病院里,今天,已不是他们的《今天》,诗歌还在,却绝无可能再现那个令外国人惊讶的,人们对文学近似狂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年我收拾旧物,发现自己的写满诗歌的笔记本,爱好文学的人,有几个不是从诗歌开始的呢?今天,诗歌仍在吟唱,但就像《今天》的诞生地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那样,委身于大片居民区中。真庆幸她在东四,她的墙上没有白色的拆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担心我配不上自己的苦难。《今天》那一代诗人,他们的苦难是双重的:历史赋予的和本身自觉的苦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冰雪尚未消尽,料峭春风给他们带来难以适应的温度。在《持灯的使者》、《八十年代访谈录》等书里,我们能够感到历史的寒意和善变的风向,然而,在所有可以看到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人,主动背负起苦难,朝着认定的方向前行,万死不辞。
林莽在一九九九年的第一期《芙蓉》发表《食指:一位迟到了三十年的诗人》。文中的诗人在精神病院里的生活似乎不错,还在写诗。我不关心诗人是否才情依旧,我在想,庄生和蝴蝶究竟哪一个真实,人们争论不休,其实重要的是他们的梦,只要以为梦是真的,敢于全力去做,那么梦想成真这个词语才有现实意义。他的后辈们,比如韩东朱文,改写小说;钟鸣,成了收藏家;一些诗人从事着与诗歌无关的工作。但是诗歌于他们,从来也不曾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比如我,会翻开笔记,去拜访那个激情的年代和激情的自己。
诗人也许是最不讨好的职业。从被尊重到被嘲笑,再到被忽视,还要忍受收入很低的现实。海子去世纪念日刚刚过去,关心房价的人绝对比关心海子的人多。人,诗意的栖居么?我只知道,生活恰恰是反诗意的。五十年内,不会再有顾城海子马骅。
我读《持灯的使者》,尽量避开那些怀念逝者的文字。你非得象一个诗人那样活着么?我无力回答。你非得象一个知识分子那样想问题么? “我努力让自己不那么偏激。” 许知远回答说,但他痛恨和痛心当下庸俗的中国社会心理状态。是的,比如我,唯有在阅读时,才觉得纯粹。我淹没在远离东四大杂院,却还在闪烁的灯光里,看不到星星,只看到一个当年订阅《星星诗刊》的青葱少年,和一本怀念《今天》的书。
《持灯的使者》读后感(五):谁在诗的梦里猎获青春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怀念总轻率地错落成文字,但我们其实都知道,记忆的困难才是写作真正的发端。一时之机,一地之宜,过了开口刹那的闪念,金句也便成了相顾无言里最后的几个烟圈。更何况许多话不是想说就能说出口。《今天》的过往就充斥着种种言不由衷。时至今日,《持灯的使者》这样断续的残片或者让我们重新趋近那段往事,看看飞扬的诗心曾经激起怎样的梦,又被怎样的现实割裂、粉碎。而在《持灯的使者》之外遮蔽依旧的故事里,我们同样也能嗅到荷尔蒙肆意的青春。
30年前是这样一个时代,凡是公安局看不懂的文艺作品都算是“影射”,而“影射”的罪名足以将个体生命完全卷入国家机器的缝隙,碾碎。于是诗作誊在硬抄本上传阅,绘画藏在房顶的棚里直到被雨水打湿粘成一块,出版民刊需要从单位“顺纸”、亲手刻蜡版,摇油印机,即便带着浆糊去西单墙张贴还需像就义般嘱咐后事。
3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时代,“冰川纪”刚刚过去,年轻而蒙昧的灵魂在未知的黑暗和光明之间蠢动;全国美展开幕前夕,被目作堡垒的中国美术馆的栏杆上挂遍了浓烈肆恣的民间画作,以“星星”之名;也是这个年代,长念“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的声音响起,不仅是在玉渊潭,也可能在某个宅院的某一间破旧小屋里,又有几盏心灯被点亮。
《持灯的使者》就站在这样的时代,围绕着一群追梦的人展开。如果你有心看完这300页的诉说,或者很难用单一的概括来归总这厚实的生命历程,糅合了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卑微,勇气与怯懦,信任与背叛,坚持与妥协,或者还有远不为我们所知的苦难。但我切实感慨这青春的美丽,并且时常怀疑,比起《今天》和诗人们的遭际,我们今日庸常的生活是否更真实?
“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这样生动的阅读体验怕是今日难再。也有“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这首诗流传出去,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这样的记述,你一定很难想到,这稚拙的笔力出自舒婷,而她竟在多年后的回忆里仍怀着不怯往事的赤诚。
至于各人的回忆里多次提及的芒克与彭刚的远行,既传奇,又真实。两个人身无长物,出走唯一的目的地是北京火车站以外,彭刚还撕掉了手上的绷带。后来提及这次远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彭刚:对我来讲,逃离就算解放,呼吸新鲜空气,背毛泽东的诗:‘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又流浪,又有美味,多棒。我想象的先锋派,到武汉,那边的人会热烈欢迎,这是一座有革命传统的大城市呀!哈哈。
问:结果如何?
彭刚:差点被饿死。
他们是以先锋派自居的,但先锋派并不常有他们的赤子之心。后来彭刚考上了北大化学系,去美国念了博士,成了硅谷的科技精英,然后,自杀了。
书里汇拢了各人的记忆,像北岛和阿城般长于文字的作者并不在多数,像多多般直切要害者更少,却很容易从各自的絮碎里寻得共通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借此扬名的北岛、芒克、多多、杨炼或者顾城、舒婷,也无论赵一凡、周郿英、徐晓、鄂复明这些诗刊的创造者,《今天》都是他们在诗歌的梦里猎获青春的证据。
有时候我不能忍受徐晓这样琐屑而悲苦的冗长文字,心想着如章诒和般的老境颓唐才会把往日苦难当作明日的出口,但这种凉薄也只是因为无法体会她们真正的苦楚罢了。作为女人,她们做得或者已足够多。至少她们和食指、和北岛、和其他诗人一样,没有成为感情的奴仆,也没有玩弄感情。这或许也是诗人和诗匠的差别所在。
纽曼说,大学应当激情年轻人诗心的荡漾。我们这代人怕是终究要和诗隔着一层了,于是毕业的情感都归于同一种言说,唱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道一声一路顺风,就草草收场。校园诗社耕耘的行行字据落在精美的册页里,雨水冲不化,却再少有人愿意去读上哪怕一行。不是诗歌的时代走到尽头,而是我们的青春和诗心早已作古。
我们应该读读这部书,应该记得这些持灯的使者和他们在诗的梦里猎获的青春。无他,只因为北岛在《诗人之死》里说的,诗人之死,并没有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永远青春,才有永远的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