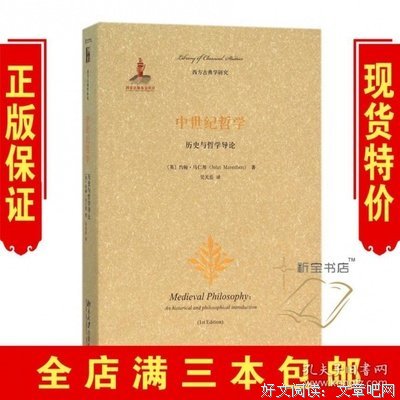中世纪哲学精神读后感摘抄
《中世纪哲学精神》是一本由吉尔松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哲学真是个神奇的学科啊,一旦发现过往的论述漏洞百出时,还能欣赏它的历史美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哲学在中世纪依旧在前进,将西哲直接追溯至古典时代是荒谬的。夏尔特的伯尔纳说过很动人的一句话,“我们就像矮子骑在巨人的肩上,我们比古人看得更多更远,但那并非由于我们的眼光锐利,亦非由于我们身材高大,而只是因为古人把他们的眼光与高度,借给了我们。”吉尔松将这句话引在了这部学术著作的最后,接着他告诉读者:“在今天,我们已经丧失这种尊贵的谦冲,我们当代人有许多宁愿停留在平地上,他们所感到骄傲的是自己凭本事看到的,至于自己身材矮小,只好用年龄老迈时的回忆来安慰自己。的确,丧失一切记忆的老年实在悲哀。假如像有些人所说的‘圣多玛斯只是个幼童,笛卡尔才是成年’的说法是对的,那我们这些人可都是老态龙钟了。然而,真理永远年轻,希望真理亦保持我们的心灵,永远青春新鲜,充满对未来的希望,以及迈进未来的勇气。”
●提纲挈领的介绍,以存在和创造问题为核心,贯穿至认识论、伦理学等,更侧重整体的“精神”而非各家分殊。向上与古希腊哲学对比,向下发掘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厘清信仰与哲学的关系,为“中世纪哲学”正名。译名有些影响可读性,书后有与通用人名译法的对照,但术语还是有些适应不来…努力克服吧…
●本书译者态度很认真,但是有太多名词需要与现在的习惯说法对应
●非常有收获!(妄言一句,是否作者行文当中预设了进步的思想在内?)
●磨磨蹭蹭了一年多,总算读完了。
●Contingent beings as being turns philosophy to the philosophizing of Being.
《中世纪哲学精神》读后感(一):很优美
有几个小问题吧
2.台湾那边的术语和大陆不太一样,比如be/ sein,这里译作存有,existence译作存在,只能脑补
3.注释中有很多拉丁引文,译者大概不会拉丁语,都没有翻译,序言里说这些引文的意思可以从上下文推出,总觉得这个理由是在为偷懒找借口...
瑕不掩瑜,现在能达到信达雅的翻译已然不多。
另外,似乎哪个领域的学者都是极为拥护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位作者也是如此,有时似乎过于抬高了,当然中世纪哲学家的智慧与功劳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作为学术讲座,这样的调调我不是很喜欢啊...
有机会看看英文本吧,中文的还是有点纠结
《中世纪哲学精神》读后感(二):传统的一环
思想的谱系上,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读过了,就也知道我们的前辈做过什么,想过什么了,于是,接下来就想着原著!
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
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豆瓣说,我的评论太短了!
《中世纪哲学精神》读后感(三):关于基督教哲学概念辨析的笔记
第一,我们是否能够形成"天主教哲学"这个概念。第二,中世哲学,即使它有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否确当地表达出历史实情。此所论的中世哲学,是穿透希腊传统,加以运用,并从其中掘发出真正特属天主教的世界(Weltanschauung) 。 前驱者及创造 检查中世纪思想的初生状态,从犹太和基督教传统接合到希腊文化传统的接枝点 反对“基督教哲学”的原因 理性之秩序就是哲学的秩序,所以哲学在本质上亦独立于除它以外的一切,尤其是独立于所谓启示这个非理性的玩意。 现在进行理性工作的我们,其中早已介入基督教信仰,每个人或多或少听过启示。 把启示当作吾人的向导,而且努力去了解其内容一寸主种对于启示内容的了解便是哲学本身。信仰寻求理解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这是一切中世思想的基本原则。 神学是奠基在神的启示之上,从这里获取原则,建立起一种从信仰出发的独立科学,只有为了引申信仰的内容或保护信仰免于错误,才会转向理性。 无疑地,哲学是附属于神学之下,但是,就其为哲学而言,哲学除了自己固有的方法以外,并无其他凭借,哲学既然奠基于人类理性,其全部的真实性都有赖于原理的自明和演绎的精确,以获致与信仰之间的自然和谐,而无须歧离自己固有的途径。哲学如果这样做,也是为了真理,而真理不会彼此矛盾。 伟大的宗教真理就其为启示而言都不是理性的,但它们既然已经被启示了,就可能成为合理性的。" 也许不是全部成为合理,至少有一些可以成为合理。 天主教哲学概念的澄清 因为哲学之整个内容,都已隐含在他的信仰之中,这种说法是不够的。故此,证明是需要的。 虽然证明"信仰无须哲学无疑会成为→种压抑哲学的方式,但这种证明却会在另一种意义下,成为进行哲学思索之最佳途径。 一个人仅凭理性的力量寻找真理,却失望了:信仰把真理送给他,他接受了 ,而他发觉他所接受的真理,竟然也满足他的理性。还同时以非哲学的方式获得哲学的真理。 启示将秩序带给杂乱的理性。 人所秉具对于真与善的认识,和福音所增加的启示认识之间有什么关系?外教人能因其本性启示而获得救恩。(圣儒斯定牛逼) 天主教义就承担了全部先前人类历史的责任,却也因此而获益。 虽然一切邪恶的过犯,都是违反道,但是反过来说,一切的善行皆是由于道的帮助。既然道即耶稣,所以按照定义,一切真理就是属于基督的。 启示之所以能取代哲学,正因为启示实现了哲学(伦理学的角度) 天主教义的伟大优点在于它不是真理的抽象知识,而是救恩的有效途径。哲学不仅是一种科学还是生活 天主教义用超性延长了本性,并且有恩宠可为依凭,作为理解真理、实现善行不尽不竭 的力量的泉源: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兼为实践,或者,更精确地说:天主教义是一种带有实践方法的理论。(天主教的恩宠观念) 真理是哲学家提出的片段,将片段组成可以形成全体真理。完整的真理,没有人能在各种哲学系统中分辨真与伪,若无天主借启示给予,也就是说,除非先借信仰接受了,没有人能预先认识完整真理。 建立在信德上的一种折中主义。 一方面有纯粹的哲学家,只依赖自己的理性,不依外力之助,发现真理一切的辛劳只能把握到一丁点真理的片断,而全体真理依旧潜藏在一堆矛盾错误之下,哲学家无力排乱解纷。 另一方面,则有天主教哲学家,信仰提供他一个准绳、判断的规范、分辨与选择的原则,使他能排除错误,拯救理性真理。唯有造物者能知之(Soluspotest scire qui fecit),这是拉克当秋之言,天主造一切,是以能知一切。 理性的犹疑和在信仰指导下的理性的确信 为理性若是完全合理,则理性将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因而人只有一条坦途,即检查信仰之合理性。 信仰就其为信仰而言,是自足的,但信仰也愿意明白自己的内容。 信仰并不依赖理性的证据,但在另一方面,信仰却产生理性证据。 寻求信仰,以便理解 信仰的真理,努力自行转换为理解的真理,这才真正是基督徒智慧的生命。 从这种努力所产生的理性真理体系,就是天主教哲学。 所以天主教哲学的内容,就是透过理性自启示那里所获得的帮助,所发现的理性真理之体系。 误区解释 唯有启示与理性之内在关系,才足以赋予天主教哲学以意义。信仰是知识的一种替代,但若用信仰代替知识是可能的,那也常是为了智性的一种积极利益。因为神学虽然是一种知识,但其目的并不在于转换其原理所在的信仰成为理解,这样做就等于毁灭了神学的适当对象。另一方面,天主教哲学也同神学一样,不会尝试把信仰转换为知识。天主教哲学家所自问者,是在他透过信仰相信为真理的命题中,是否有一些也可以由理性来认识为真理?如果一个人的这种新的哲学洞见是出自天主教的信仰,那他便成为天主教哲学家。"自然与理性皆向超性开放"一个向超性开放的哲学当然可以与天主教义相配合,但并不必然是一个天主教哲学。 假如这哲学堪当天主教哲学之名,则"超性"必须下降,成为建构哲学的建构性因素,但并非哲学组织上之建构因素(超性是啥玩意儿)
(上承三)我所谓的天主教哲学,是一方面保持理性与启示在形式上之差异,但另一方面,亦视基督徒的启示是"理性无可或缺的助力"的任何一种哲学。对于任何照这样理解的人,天主教哲学并不相应于任何单纯本质,可予以抽象定义,而是更相应于一种具体的历史真相,要求我们加以描述。它只是哲学类里面的一种哲学,其范围内所包括的哲学系统,都是因为有一天主教之存在,而且备受此一宗教之影响,才得以存在的哲学。 启示对于哲学的影响,乃在于简化哲学的建构工程。 信仰的坚定促进理性思考的坚定启示是理性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当我们跟随信仰之路之时,并不会失去理性所清楚要求,多少年来辛勤反省所得的各种必要的辨明。就哲学本身绝对言之,一个真正的哲学的真理只出于哲学的合理性,而且只出于合理性,不涉及其他。
《中世纪哲学精神》读后感(四):中世纪的自然观(《中世纪哲学精神》第十八章读书笔记)
自然的概念与必然性、命运、自由意志等概念密切相关。在二律背反中,往往是自然与自由的剧烈摆动,自然与自由的协调弥合是一个亘古扰人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里似乎是在自然层次上安放了一个超自然的层次,这也符合创世说。
在中世纪哲学里,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总是靠在一超自然秩序(supernatural order)上面,“它倚赖此超自然秩序,并以之为其根源和目的”(p291);“在中世纪哲学里,自然存有(natural being)即如古代哲学中的自然存有者一般,乃一活动的、带着种种出自其本质(essence)的运转的实体,而此自然存有者则必然为此本质所决定”(p292);而自然界(Nature)则是种种“自然本性”(natures)之总和,所以自然界同“自然(本性)”一样都具有丰富性(fecundity)和必然性(necessity)。
必然性:
每当我们认识到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或事物一再重复发生时,我们就肯定此常规性是具有一原因(cause)的——“一本质或自然本性之存在”(the presence of an essence or nature),而自然本性与必然性之间关系更密切:“凡为万物所共有者,即为真正自然的事物,因为自然经常以同一样式运转。”(p293),所以可以理解司各脱的归纳法仅为何看此一原则。
中世纪科学为何难以进步:
亚里士多德的“质的物理学”有碍于“量的物理学”、人们相信“宇宙决定论”,一种星象学类型的宇宙决定论。
必然性与机缘:
“圣托马斯认为较低级物体之运动是由天上物体的运动所引致的。而尘世的一切现象莫不由星辰之运动所统御”(p293);但星象学不是绝对必然地强加于地上的,圣托马斯认为“机缘”(chance)仍有相当大的活动余地,他考虑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逍遥学派(Peripateticism)中机缘所占的重要地位,在逍遥学派中,机缘绝不是一种纯粹的不决定,机缘论与普遍决定论并不相悖,在此【目的因】与【动力因】分开对待了:“自然里偶然的事物就是缺乏目的的事物”(p294),偶然的事物=缺乏目的的事物=(由于目的是原因)没有原因的事物。
值得留意的是,这种“相对的不决定”在中世纪的自然概念中也消失了,中世纪的自然概念驱逐了chance:“在日常谈话里,我们固然可以谈到机缘,但世界既是天主之作品,而世上万物更无一能脱离天主之摄理和眷顾,我们当然不可能将任何事物视作绝对偶然的”(p295);在神性的层面上再无机缘可言,“因为甚至两串不同的因果系列显然的偶然遇合,也是依靠在不变的秩序上面的,而这不变的秩序,正是‘由那睿智地安排万物在其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可敬的天主’所建立的”(p296),自然乃天主之作品,其中就不可能有任何错误,处理的方式是:“当这些自然的缺憾(defectus naturae)发生时,天主必定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如此安排的”(p296)。这样就把机缘放在了律则(law)之下,所以就将自然从【命运】中解放出来,因为万物皆具有【充足的理由】(充足理由律),不过这充足理由必须是“理性本身”(Reason Itself)。
宿命论与中世纪的命运观:
宿命论(古希腊)是说事情之发生乃由某些【盲目的必然性】所引致的,它【独立于人类和天主之意志以外】;而中世纪哲学认为“命是依乎天意之原则而产生的结果”(p296),“命”是处于天主的统摄之内的。并且,“愈接近中心则愈不受命运之浅系。任何事物一旦能紧贴于至尊的心灵之绝对不变性时,即可摆脱运动之束缚,超越于命运之必然性之上”(p297),命虽然在说明偶然性事件方面看似有用,但它仅是【天意之结果】而已。
偶然性与可预知性:
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机缘,也肯定了【未来的偶然事物】之存在,所以未来无从预测;而斯多亚学派认为未来是【可以预知的】——斯多亚学派对【占卜】极为重视——但他们把预知未来建立在“命”的理论上,这项理论之作用正是要从宇宙中【清除一切偶然的事件】。但天主教哲学克服了这两方面的困难,同时肯定【偶然性】与其【可预知性】。
在亚里士多德之体系里,机缘既属于【非理性】的层面,自然是不可预知的;但在天主教思想里,“机缘却成为合乎理性的和可以预见的”(p298-299);但天主知道原因之秩序,却不会引致失去意志自由,因为他早已知道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原因。
中世纪的“奇迹”(miracle):
中世纪是奇迹的时代,“任何出人意表的事物,都会被视为显示出天主之直接参与”(p299),中世纪的自然是【关联于天主的自然】,“中世纪的奇迹的确证实了,而非否定了自然之存在”(p299);“在天主所创造的宇宙里,虽然奇迹依然是超自然的,但在哲学上还是可能的”(p300),圣言已道成肉身。但是,奇迹仅是对人而言的,对于天主而言,则没有奇迹可言。
自然是天主意志所成就的“第二因”(second cause)之秩序,天主不受自然秩序之约束,因为他是第一因,“在贬损自然律则时,天主却依循一较高的律则,他的一切活动均不会违反此一律则,因为他自己正是与此律则相合一的”(p301)。
服从性力量(potentia obedientialis):
自然的可能性之层次被界定为所有能在被造的第二因之层次里发生的事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只依赖神圣睿智和意志的普遍层次,所谓服从性力量就是“内在于天主所创造的自然中,变成天主所能要它和确实要它成为的事物的可能性”(p302),这是一种【被动的可能性】。
两种恩宠(grace):
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是一种恩宠,但伯拉纠派忘了还有另外一种恩宠:【拯救自然的恩宠】,这个前提是罪,恩宠所预设的自然的概念直接与哲学及哲学史家有关。
超自然层次:
在自然之上添加奇迹的层次,就得考虑这种超自然层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确实一种必然性,但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而“天主教所创造的本质虽然被它们在自然层次中所能做者和所忍受者所包围和封闭,但它们这种必然性却在超自然的层次中,向天主所能施加和赋予这些本质的一切,【保持开放】”(p304),以服从取悦创造者,开展其命运,这是本质的实现而不是改变本质。
自然的界限:
自然被严格限制在自然层次上,不可僭越超自然层次,“在自然里面,没有任何引发超自然的能力,更无任何要求超自然的能力”(p305),服从性力量是绝对被动的,自然会自动地(ad nutum)服从天主之命令,天主教哲学中的自然之特性乃是【向它的创造者开放】。
《中世纪哲学精神》读后感(五):读书报告
挂读书报告求人品
理性不是信仰的敌人,哲学绝非希腊的专利:一神教信仰引领哲学登上了新高度
首先,在遇到这个论题时的首要困难是,希腊和中世界的哲学师承关系,以及信仰和理性的关系。
一方面,历史学家们坚持,所谓的中世纪存在的经院思想不过是纯粹的希腊-罗马哲学遗产,因为奥古斯丁是柏拉图忠实的弟子,而圣托玛斯的工作亦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翻译。所以整个中世纪的哲学原则,只是希腊哲学的延续,而中世纪所作的对天主教思想的诠释,也不过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者思想的中和。
然后是,哲学家特别是其中的纯理性主义者,他们指出,启示的宗教所具有的信仰属性,跟纯理性运作的哲学,这是永不调和的两者。信仰和启示所教导的那些观念,与以自然理性在专心地分析自己的内涵时,在本身内部发现的东西,是不谐和的。哲学像医学生物学一样,完全独立于宗教之外。
如果不先理清中世界的传统和希腊文化传统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不事先解决掉以上两个反题,这个问题的论证就无法展开。
于是紧接着吉尔松在第二章,通过论述启示对于理性哲学的益处,化解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解决了第二个反题。这里所思考的即是,朝向圣经和福音去寻找哲学灵感,可以获得什么学术上的益处。
在整个中世界的历史实践中都显示了,理性帮助理解神学,理性用来证明启示,即用哲学理性的方式,来证明神学《圣经》中所启示给人们的,使基督徒证明“神恩”,理解神恩。中世界所有的历史实践,都在通过证明人,然后证明神的荣光。然后神学大师,洁身自好的提高着信仰和启示的地位,将它们从世俗中脱身而出:他进一步论证,信仰并不依赖理性证据,信仰却产生理性证据,并不是为了寻求理解以便相信,而是为了寻求信仰,以便理解。启示并不依赖理性,哲学若不是为了证明神,本事不重要的。
通过哲学家皈依天主教,和到处渗透着天主教教义的17世纪以后古典哲学家们,吉尔松列举了充分的史实证明着:这些哲学家最后所运用理性证明了的东西,往往其实就是《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的结论。并且,更高层次的是,启示给理性以依托,给理性带来秩序。启示,又避免纯粹理性人类的骄傲自大所导致的错误。神学一方面是哲学般的理论,一方面又是一种实践,这是希腊哲学所止步的,哲学在中世纪这里接着天主教教义走到实践的层面,再由后世的康德们发展着。天主教教义不仅是哲学的真理所在,而且还能引导人们走向救恩。在天主教关心的领域里,即在有关人与天主的关系上,有关天主的存在及其性质,灵魂的源起、性质和命运上,一直是启示带领理性哲学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层面上,启示和理性保持着和谐。(而17世纪从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们,他们自己所定义的自然“理性”,当中却实际上是以天主教的创世说、神恩、原罪等教义为基本观点的。他们自己已为神学领域的信仰和启示,所渗透着。)
在理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后,吉尔松继续以列举史实方式,显示了,天主教教义中的启示对于形而上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这样,中世纪哲学和希腊哲学便清晰的显示出他们自己的样子,中世纪和希腊的师承关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与奥古斯汀派和圣托玛斯派的哲学继承,也就是中世界对于希腊哲学的继承和补充,也显得清晰起来。而对于一神教信仰,引领哲学登上新高度这个论点,也在吉尔松关于启示对形而上学发展影响的各个细小的论题中,在针对第一个反题的批判中展开并被证明了。
在方法论上:吉尔松更多的不是用哲学的逻辑上的辩证来证明,而是以历史学的方式,用中世纪主要思想家们的论点,经过解释以后作为证据,然后再分析希腊哲学的极限和存在问题,然后给我们看到,天主教启示,使希腊哲学,在哲学史上怎样实现了突破,走向17世纪古典哲学,为笛卡尔康德继续发展着。以此来完成证明天主教教义中的启示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
天主教教义是以“人与天主的关系”为中心的体系,所以首先在哲学基础,整个大的形而上的框架上希腊与中世纪的相似性(3.大有及其必然性。4.诸有及其适然性)不能忽视。
形而上的相似性在神的观念上。以神的观念为中心点,回到柏拉图自然神学和亚里士多德里,可以看到柏拉图《理想国》善的观念,以及《提美乌斯篇》中戴米乌吉神,亚里士多德不被动的主动者,第一因,超物理界的最高真实本质等等不胜枚举。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诠释家里,这些概念,无限接近于天主教的“神”,彼此难以区分。受到柏拉图影响的奥古斯丁和受到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圣托玛斯,他们对天主所作出的展望,于是被众多人认为不过是希腊传统的延续。
在形而上的实体论的构成上,即宇宙学说,世界的秩序。柏拉图的理念,黑洞,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运动,与天主教的世界观几乎完全一致。突破点在于天主教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即是建立在一种神性存在的观念上,本质=存在。只有天主才是完满的真实的存在,诸有之所以偶然的存在是因为分享了神的存在,诸有只有在通向神的道路上,才能找到自我,才能拥有自己的存在感。不同的即是巴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没有结论,只有形式。而奥古斯丁和圣托玛斯则走的更远,得出那个秩序的完整模样是如何在神性的光辉下存在的。这使得形而上学的发展前所未有的进步,才能有笛卡尔17以后的哲学家们。
这两章主要论述了希腊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及对天主教哲学深刻的影响,并开始将天主教创造的观念引入。后面,在模糊的形而上学之下的详细内容里,天主教教义的各个方面开始展开。对希腊哲学的发展也明细起来。
有了如此的大轮廓,在天主和人类的平衡,天主和人类宇宙关系的实体上(5.类比、因果关系、目的性。),吉尔松论证了天主教的类比构建了形式,用因果律解释了推动,而目的论是勾画了最后的界限。天主教世界的样子就显明了,像看得见的线条。古希腊模糊不清的杂乱的哲学,所没有的秩序,在天主教这里宇宙却是整齐而系统的。
第六章(6.乐观的人生)首先了破除了大部分对中世纪的主要误解,又树立了人,本性,原罪,天主的善等天主教的基本观念。然后第七章汇合为荣耀天主的主要路线上,即存在本身创造诸有,皆是为了他自己的光荣,存在本身创造万物皆是为了万物能披被荣光。
哲学最终是研究人是什么的学科。吉尔松在天主教创世说的基本教义阐述结束以后,人在其中的地位,人于天主创造的宇宙秩序中的地位就不能不考虑。通过三章(8.天意观。9.人类学。10.位格论。),阐述了神性眷顾如何照管人类以及人应该如何照顾自己。灵与肉,神恩,位格的观念。正是这些基督教教义使我们现在比起希腊来说在人是什么走的更远了。
然后是关于人的认识论(11.对自我的认识。12.对万物的认识。13.理智及其对象)和对人至关重要的伦理学(14.爱及其对象。15.自由意志与自由观。16.律则与道德。17.意向良心和义务)上,用同样的方法剖析其希腊哲学传统的源流,以及天主教教义的主张,和17世纪以后古典哲学的发展趋势,为我们显示,圣经的启示,并不是用来装饰的没有任何哲学意义,而是在各方面都是伴随着思想的必要的指针,提醒并保护思想,天主教哲学使启示带给理性以帮助。对每一类重要的哲学问题,都走出了希腊哲学的困境,并提出新鲜的结论和解答,使哲学登上新的高度。
甚至在历史哲学上,也因中世纪扬弃了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主导观念,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作为历史变化过程的基础的有关永恒实体的实质主义的观念。而得到重大的发展。
可见启示给理性带来的福祉是如此醇厚,启示给理性带来秩序,引导理性走在道路上不要迷失,启示又避免纯粹理性人类的骄傲自大所导致的错误。启示跟理性是彼此和谐的,启示引领哲学登上新高度。
所以莱布尼茨说:“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这些真理知道的很少,只有耶稣基督将它们表达的最为神妙,而且它用这样明白可亲的方式表达,使得最单纯的人亦能追随,它的福音整个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