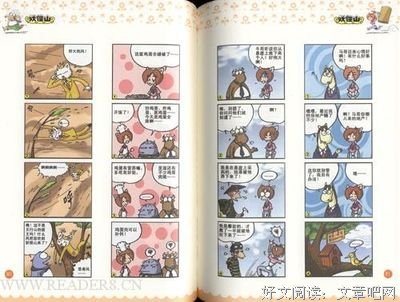妖怪山经典读后感有感
《妖怪山》是一本由彭懿 文 / 九儿 图著作,北京连环画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014-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妖怪山》精选点评:
●又一个“救朋友于险境”的寓言。至今遗憾我没有救成她,于是所有“救朋友脱离险境”的故事对我而言都有无法形容的意义。
●现实背景下的恐怖故事呀,四个小朋友去山里玩耍,一个小朋友失踪了,一年后,三个小朋友再次上山寻回失踪的小朋友。虽然说是在告诉我们跨越心中的大山,但是不科学呀。
●作为成年人,觉得这个故事有点恐怖~ 夏蝉失踪一年,这要是在现实中父母得多心碎呀
●2015.6night 彭懿《妖怪山》。 在彭懿看来: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 记得,这本书还是过年前就收到的,一直不敢翻开来看,也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情去看它。怕自己的理解不够格,读不懂作者直白语言里掺杂的深刻的含义。 直到那一晚,不知该带哪一个绘本去学校时,突然想起了它。从厚厚的书架里找出来,细细翻看,竟然被打动了。
●没看导读,单看内容还可以,图画很漂亮
●灵异
●图和文的内容设计很用心,文字不是“看图说话”,图不是照搬文字内容(目前看来这是很多原创绘本的诟病)。图文除了呼应和交叠的内容,还有各自向外延伸的部分,这是构成一本绘本“可读性”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妖怪山》在这一点上做的很好。 绘者九儿的画风有点像连环画。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参考:所谓旧气、但有着传统风味的画风如何在画面上进行突破。虚构的妖怪形象给了老画风一种新活力,画面边角藏满了不太容易发现的小妖怪眼睛,让这本书在故事之外多了一种游戏性,设计下功夫了。 导读设计也很用心。两篇文章很短,但是一下子把这个幻想故事的内容拉高到了道德和教育的层面。虽然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不得不说是一种很高明的做法。
●国内也出了这么让人刮目相看的绘本
●角色夏蝉被朋友抛弃,在妖怪山待了1年,父母、村民不着急?小伙伴找到她,夏蝉还像个正常人。不合常理,可能才是绘本吧
●怎么那三个孩子就变成妖怪了呢?读完觉得心里很感动,小女孩没有记恨自己的朋友,而是很理解朋友的做法;三个小朋友第二次没有退缩,齐心协力用智慧和勇气救出了小女孩。
《妖怪山》读后感(一):勇敢的孩子从哪里来?
儿童文学理论家 刘绪源
这本来是一个很悲剧性的故事:一群孩子兴高采烈出去玩,结果出事了,有一个孩子受伤或失踪了,甚至永远地离去了;其他孩子也许各有责任,却不能全怪他们,因他们毕竟都是孩子;从此,同伴的受害,成了他们永远的阴影。这样的事故过去有,今后还会有。
《妖怪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写事故本身,而写孩子们如何走出阴影;也不将事故按本来面目写(那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就太沉重了),而以幻想作品的形式,写成一场可以恢复的游戏,只要大家战胜自己就能赢得同伴的回归——这就使故事合于儿童的审美需求,让小读者的心灵在跌宕中得到充实和启迪。
我觉得,这故事中写得最好的一笔,恰恰是孩子们看到同伴被妖怪抓住,吓得转身就跑,一直逃到山下。我们看到过不少童话,在写孩子需要做出重大牺牲,需要把自己日夜不离的最心爱的东西永远送给别人,包括遇到从未见过的可怕场面时,常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各种壮举。这样的“壮举”往往并不感人。因为这不像孩子的行为,也不合乎孩子的心理。那类描写其实大都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并不是从孩子的实际生活出发的。本书中的孩子一直到事发之前都不相信真会有妖怪现身,他们毫无心理准备,事情陡然生变,他们的恐惧和逃跑正是本能的应急反弹,他们自己也没法解释。
大人并没有责怪他们,因为大人们不相信会有妖怪。但他们自己不可能摆脱这内心的沉重。我们也曾看过太多的儿童小说,写孩子们遇到麻烦后,如何在大人或组织的帮助下一点点走到正确的方向,这些小说有不少是图解概念的,其写作目的就在于强调“正确方向”,而不是写孩子的生活。
这本图画书的又一成功之笔,就是写孩子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难题,用的是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孩子特有的心理。细心的读者会从画面上发现,他们当初上山时,有的用狗尾巴草編小兔,有的用挖了孔的绿叶遮眼,有的用双手抛红果子玩。到他们再次上山,为救自己的同伴,竭力抵抗不断袭来的恐惧,说什么也要把游戏玩到底时,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急中生智,不约而同地重复当初上山时的动作,或抛果子,或编小兔,或举绿叶,从而暗示了真实的自己。这类微小的细节,恰恰是大人所难以把握的。画家为此设计了左右扩展的加长页,安排了分组进展的连环图画,可见是颇费了一番匠心的。
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有个哲学难题,即“道德的起源”。人的道德意识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童年最细小的地方开始的。所有的道德都意味着牺牲,不抢别人的饼干也意味着会少吃一块或许能抢到手的饼干。而牺牲就是与自己的动物性,与一些本能的需求作抗争。道德要承认这种本能,然后才会有抗争和战胜。孩子们第一次逃跑就是本能,以及在本能支配下的行动;经过一年的懊悔和痛苦,他们下决心再上山,勇敢地做完游戏,这就是他们的抗争了。勇敢的孩子不是天生的,道德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人不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成长的吗?
最后说几句本书的画风。九儿的笔墨有自己的特色,画树与景物相当工细;画人则用老连环画式的简要线条(中国古代版画的线描人物即此种风格),再略加淡彩。这种画法适合民间故事一类作品,因其有旧气。本书有淳朴的乡村气息,加上这种画风,还真有点民间故事的味道呢。
《妖怪山》读后感(二):如何跨越“妖怪山”?
《妖怪山》是一个颇有勇气的绘本故事,作者彭懿选择了在中国原创绘本故事中极其少见的失踪题材,表现了同样少见的救赎主题——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说,这里首先要给作者的勇气点赞,他像一个了不起的魔术师,表演了一出难度极高的魔术,令人惊讶地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我们经常这么说,这没有错,但我们没有说出的是:每个天使的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
中国的传统蒙学时常以“圣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儿童,大谈仁爱、孝道、自然之道而无视儿童有瑕疵的个性,贬损儿童不完善的自我,不能切近儿童的生活,无法引起真的兴趣,落不到现实和人生的层面,结果所谓的道德不是高高地被悬置,就是浅浅地浮于表面,造成如鲁迅所说的矛盾冲突的人。当下,在国内儿童教育领域盛行的“国学热”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而《妖怪山》则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它是孩子们游戏的场所、幻想的乐园,同时,它也是孩子们面对危险的怯懦、面对困难的沮丧、面对责任的逃避,它是每个孩子在成长中都曾经犯下的过错,它是每个孩子在生活里都曾经感受到的遗憾。它存在着,就像阳光、雨露、友谊、亲情这些美好的事物存在着一样。有时候,它还很严重,重得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每个孩子心上,就像《妖怪山》里描述的那样: “他们怎么会忘记夏蝉呢!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连一天也没有忘记过她。……尽管害怕被妖怪抓住,但他们不能不去。”
英国作家切斯特顿这样谈论童话:“童话其实最真实不过: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可以战胜的。”《妖怪山》正是这样“最真实不过”的童话,它不但告诉我们妖怪山是存在的,还告诉我们妖怪山是可以跨越的。孩子们不是因为完美才被称为天使的,而是因为他们可以战胜困难、弥补过错、获得救赎,因为他们可以和不完美的世界、不完美的自己和谐共处,我们才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天堂的样子。
《妖怪山》展示了孩子们如何跨越妖怪山:首先,孩子们要面对妖怪山存在的事实,要面对真实的自我,哪怕这个自我有那么一点胆怯、自私、无经验、少能力,总之不是那么闪亮耀眼,孩子们要学会接纳这个不完善但是真实的自我。其次,孩子们要有担负责任的勇气,获得勇气的方法不是速成的魔法,而需要漫长的时间,故事里孩子们获得勇气的契机是收到夏蝉的一封信,实际上则是时光老人馈赠的一整年,够他们每一个人懊悔、遗憾、怀念并从中逐渐成长,获得勇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孩子们不但要认识真实的自我——即使变成了妖怪也不失本心,还要有能力展现出真实的自我——向你的朋友、亲人和周围的世界展现出你独特的个性,表达出独一无二的你自己。细心的小读者在读到那幅超长跨页大图时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虎牙、野狐、笛妹要怎样才能让夏蝉认出自己呢?(答案就藏在之前的精美图画中。)如果是你的话,怎样来展现出一个独特的你,让爸爸、妈妈、同学或者朋友认出你呢?
《妖怪山》还告诉家长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跨越妖怪山,除了要给予孩子温暖的拥抱(如同故事结尾失而复得的拥抱)之外,还要做到基督山伯爵一直强调的两件事:等待和希望。等待孩子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慢慢成长,希望孩子们获得勇气、展现自我,让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美好——这世界上一切有关教育的秘密,都蕴含在这四个字之中,是的,“等待”和“希望”。(儿童文学作家、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 常立)
《妖怪山》读后感(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绕过它,还是跨越它?
小时候我怕鬼,也怕妖怪。
当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家里老人家对鬼怪绘声绘色的讲述足以让我毛骨悚然,同时也使我对现实发生的事情加以杯弓蛇影的想象,从而更加惧怕所谓鬼怪。
在童年的朋友圈,鬼怪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默默遵守着不知源自何处的约定。
例如,晚上不轻易出门,不然鬼会跟上你;有人在背后喊你名字不能立即回应,也不能让人在背后拍你的肩膀,不然鬼会勾走你的魂魄;床底下肯定是藏着鬼,晚上睡觉要小心千万别将手脚伸进床底,不然鬼会咬住你。
我更害怕的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
例如,离外婆家不远就是铁路,每天都有火车呼啸而过。大人们担心小孩子在铁路上玩发生意外,便编了故事说,那边铁路撞死了个疯女人,手脚血肉飞了一地,如果小孩去那边玩,可能会被疯女人的鬼魂抓去作伴。我听着心里发毛,每次路过铁路总是胆战心惊,害怕被撞死的疯女人阴魂不散大白天也跑出来抓替死鬼。
又如邻居家有个哺乳期的女人突然离世。后来大人们说送她去埋葬时,为了不让她回来寻找自己的孩子,在她的乳房上倒扣了两只大碗。这件事在我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我总觉得区区两只碗怎么可能扣得住母性?那个女人的鬼魂肯定会回来。所以后来的许多夜晚,我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生怕一不小心发现女人回来喂她的孩子。
这样的恐惧震摄着我幼小的心灵许多许多年,直至打开唯物辩证主义的大门,才慢慢克服这种心理。也就是说,我花了十几年才跨过心中的妖怪山。
所以,在协助建立小七的世界观时,我刻意打破对鬼怪的旧有观点,直接跟她说,夸父和女娲是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上帝是外国的神话,鬼怪是人类编造的故事,都是不存在的。
她接受了我的说法,整天把鬼怪挂在嘴边,害得外婆连声说“不能说这些不好的话,不吉利。”作为矛盾的制造者,我只笑笑不说话。
世界的真相孩子始终会知道,掩盖无益。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绘本《妖怪山》。
称作者彭懿为国内最了解小朋友的作家不为过。他对儿童图画书的研究较为深入,至今共翻译并推广了七百多本绘本及故事书。经他翻译的绘本大多深受孩子喜爱,如《爷爷变成了幽灵》、《我的爸爸叫焦尼》、《好饿的小蛇》、《小黄和小蓝》、《100万只猫》、林明子系列绘本、安房直子系列幻想故事书等。
《妖怪山》是他拟写的第一本绘本,讲述四个好朋友到妖怪山玩,其中一个不小掉进裂缝变成妖怪,其他三个丢下好朋友落荒而逃,最终他们克服困难,解决被困好朋友的故事。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读到好朋友变成妖怪从裂缝里飘出来,我心里还是有点发毛(童年阴影啊),但小七的反应比较镇定。她问了几个问题:
01 如果我的好朋友掉进裂缝了怎么办?
小七:如果我的好朋友掉进去了,我肯定会把她救出来。
我:可能有妖怪哦,你会害怕吗?
小七:怕。
我:那怎么办呢?
小七迟疑一下:我也拉不动她怎么办……我可以去找她的爸爸妈妈把她拉出来!
我:好办法。
02 如果我掉进裂缝了怎么办?
小七:如果我掉进去了呢?你会救我吗?
我:当然啊,我必须把你救出来。
小七:可是妈妈不害怕妖怪吗?
我:怕呀,但我更想把你救出来。
03 如果全部小朋友都掉进裂缝了怎么办?
小七:(三个小朋友回去找夏蝉的时候)如果又一个小朋友掉进去怎么办?
我:对呀,怎么办?
小七:如果全部小朋友都掉进去了怎么办?
我:对呀,怎么办?
她笑了:那就太好啦!全部小朋友都会变成可爱的小妖怪,开开心心一起玩!
第一个问题,她设身处地,想象掉进裂缝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她首先肯定自己会救好朋友,后来发现自己害怕妖怪而且力气不够,所以想到了解决方案B:找可靠的大人帮忙。
第二个问题,她换位思考,想象掉进裂缝的是自己。这个问题光是想象就令她惊恐,所以她必须确认妈妈会排除万难来救她。这个想象也是她对第一个问题的心理基础,她幻想到掉进裂缝的恐慌无助,所以确定自己要救出好朋友。
第三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对大人来说,掉进裂缝是坏事,变成妖怪也是坏事,但在她的想象中,只要和好朋友在一起,上述两件坏事就会负负得正,成为开心又有趣的好事。
这些问题,充分展现孩子的纯真、善良,以及孩子寻找解决方案的积极、向上,让这个我原本觉得立意欠佳(在困难面前丢下好朋友自己逃走)的故事变得温暖起来。
原来绘本可以这样理解。
于是,我又回过头仔细研究这本书,才发现它不简单。
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妖怪,而是遇到重大人生挫折时,怎样走出内心的恐惧及现实的困境。
如,书中第一次落荒而逃的小朋友,他们如何接纳丢下好朋友的懦弱的自己?
在收到好朋友的求助信后,他们如何鼓起勇气再次回到妖怪山?
亲眼见到好朋友变成了妖怪,他们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惧?
当自己也变成了妖怪,他们如何想办法自救?
当一切恢复如常,他们如何向好朋友表达愧疚?
这一系列问题巧妙地隐藏在故事里,读者在获悉小朋友们的方法时,也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作者在其中传达的思想是:懦弱、失败、愧疚、挫折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应该直面它并寻找到解决的办法。
书中问: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绕过它,还是跨越它?
小七的答案是:跨越它。如果绕过去,可能会掉进裂缝里,应该大步跨过去。
我觉得这个误打误撞的答案意外的好。
面对心中的妖怪山,跨越它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处理办法。
《妖怪山》读后感(四):无心之失与非理性成长:《妖怪山》、《失物之书》对比读
孩子是什么?当这个问题被明确意识到,且不断呼唤回答时,关于儿童的意识才终于在人类文明史上露出了浅浅的轮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多种多样,但其中很可能包含一种对照关系,由此引发的结论就是儿童不同于成人。这种差异在成人极力求同的霸道态度下就演变成了儿童有时甚至令人发狂,诚如我的一位学姐瞪着眼睛说她的小学生儿子“有时候就不是个人”。这种贬损性话语从根本上泄露出成人对儿童非理性存在状态的无奈态度,当然也是对此的变相谅解。
在今天的中国,成人家长中的一部分——我是指那些愿意了解儿童心理,关注他们成长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一方面希望孩子在宝贵的童年时代尽情尽兴尽性地享受作为儿童的乐趣,另一方面则祈求他们在全身心感受周围世界的同时获得完整的人格成长经历与经验。能将这两个层面的愿景结合起来的方式常常存在于游戏之中。除此之外,阅读也是两个层面容纳彼此的好手段。这种阅读应该是亲子阅读,而非孩子单独翻书。这种良好有趣的方式能够给成人提供一种观察儿童成长的有效参照。它既是指亲子共读绘本,也是指亲子共读大本的童话书,甚至包括黑童话的共读。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领悟,我为我年幼的女儿购置了许多绘本,同时也在自己阅读童话作品时开始留意、准备与慢慢成长的她共同要分享的快乐,以及可能遭遇的疑难。
在这条已经开始的漫漫阅读路上,我与《失物之书》不期而遇,我把它看作是写给成人看的黑童话,而且是一本负责任的好的黑童话,因而将来我一定会陪伴女儿重读这本书。《失物之书》来到我身边时,彭懿的《妖怪山》也来到了。一本黑童话,一册绘本。前者的暗黑气质,和后者的五色斑斓似乎不应相提并论。但作为一位关注孩子成长的母亲,作为一名热爱妖怪文学的读者,我又很容易将两者作比照,很自然地把它们结合起来阅读、思考。
我同女儿一起读《妖怪山》时,她最喜欢用她暖暖的小手抓住我的食指在每一页上指点暗藏的小妖怪的眼睛。这使我们的每一页阅读都充满笑声,全然冲淡了只要是成人读者就能从这绘本中捕捉到的悲剧气息。因为四个孩子结伴去妖怪山,只有三个回来了,另一个掉到了山里的裂缝里,她失踪了,甚至可能离开了人世。当悲剧发生时,三个孩子吓得转身就跑。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说,这是故事中写得最好的一笔。作为妖怪迷的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评价,但是我感激他有这样的敏锐和谅解。亲子阅读推广人粲然将这些转身逃逸看成是孩子的“恶”。可是,这是什么恶呢?一群毫无心理防备的孩子在发生意外时陷入恐惧,转身就跑,这完全是本能反应。人体安全预警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转身就跑,这和遇到狗熊抛下同伴的那个成人所做的事情几乎差不多。对后者,人们编出让狗熊提醒被迫装死的人——抛弃朋友的家伙不值得为友的警告,而安房直子在《熊之火》中则让必须装死才得生存的人有了一段神奇的山中他界之旅,把所谓道德评判完全抛诸脑后。即使要做出评判,当然这样可能违背日本文化的特点,那么其所指对象也一定应该是成人,而不是儿童。因此,《妖怪山》中那些孩子的逃跑并非是什么“恶”,充其量是无心之失。所谓的“无心”正是儿童无法全面揣测、预料事件后果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妖怪山》对此有如此本原的直陈,但我并不认为这种直陈是书中最好的一笔,最好的一笔对我而言是绘本开始就出现的那个画面,三个幸存的孩子在露台上写作业、玩纸飞机,但他们心不在焉,想着念着失踪的伙伴,露台下面有个小小的身影,看起来就像是那个失踪的孩子,或者它和那个孩子交叠在了一起,在楼下不时提醒着过往。三个幸存儿在转身就跑之后的一年从未忘记自己的好伙伴,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疼痛了一整年,在那里就像有一根刺,而且是共同的。无心之失,却可能是一年,甚至一世沉重。这就是生活本身,它在这三个孩子身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启动了非理性心理走向成长的序列,它和玩耍、游戏、快乐、失意,以及抑制住心跳的勇气紧紧交织成生命的罗网,一个让往昔与当下遭遇的时空体,既围困幼者的人生,又将它们打捞起来。那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画面,尽管它处于绘本之初,但最紧张的人生问题早已拉开了帷幕。帷幕下是孩子们走回妖怪山的自我重塑。
类似的成长危机在《失物之书》中比比皆是,甚至就连小说的整体构架也是疾病困厄与战争惨痛的交织。那个叫戴维的小男孩注定要在危机的洗礼中过早长成一名拥有骑士情怀与国王气度的少年。因此他拥有一个打败巨人哥利亚的少年英雄的名字,“戴维”的另一种译法正是“大卫”。但是戴维的成长危机看起来并不是无心之失,他的本能在抗拒接受母亲去世后被重组的家庭生活。癌症夺走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则另娶他人,继母很快给这个组合家庭添了一个小男婴。戴维认定这个小男婴会取代自己,继母罗斯则会让爸爸忘记妈妈。小男孩戴维还不知道,人生的边界正是我们永远无法代替别人生活和决定存在本身。他只是个孩子,而且还那么沮丧,陷入非理性的扭曲情绪是多么正常的事情。
《失物之书》的作者约翰•康诺利,这个比彭懿年轻十岁的男人,对孩子的成长同样充满期待,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孩子的自我充分觉知,他们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那常常接近美好。但是康诺利比彭懿要残酷许多,因为他的书写主题就是“失去”,那正是人生的另一重边界,如同余华在《活着》所造的丰饶与荒凉的并存之土。小男孩戴维追随逝去母亲的一声声呼唤,其实是随着自人类的负面情绪有始以来便被呼唤出的扭曲人,进入了一块神奇而暗黑的森林厚土。在那里,他饱受被狼群与狼人追猎所带来的恐惧,经历迷失、思念之苦。直到有一天一个喜欢制造合成兽的女猎手带给他新的生存态度。那残酷的女猎手随意砍下由她制造的鹿女的头颅,那是个甜美的小女孩的头颅。戴维感受过这头颅皮肤的温热,甚至他脸上还蹭上那头颅脖颈处喷溅的热血。我相信正是在那一刻,他开始与自己的异母弟弟和解了。生命怎么可以被随意诅咒和戕杀?他人生命的边界是不可以随意被践踏的,人没有权力决定他人的存在方式,包括被随意嫉妒和拒绝。此后,戴维在同性恋骑士罗兰身上真实地了解到,那些所谓的禁忌之爱其实有着作为爱的珍贵本质,而那个有着他母亲和继母两重表象的可憎女巫其实不是她们任何一个。在未进入那块暗黑森林之时,他恰恰把罗斯看成是在父亲心中取代母亲位置的可憎之人,但荆棘堡之战则表明,罗斯不是女巫,绝对绝对不是。在跨越了一重重存在困境的扭曲镜像之后,他来到暗黑森林统治者国王的城堡。他偷看那本他自认为会给他回家指引的《失物之书》,无意中却发现了国王正是罗斯的大伯、早年失踪的男孩乔纳森。戴维清楚,即使乔纳森的父母之后又有了孩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失踪的长子以及被他带走的养女安娜。那就是爱的另一重本质,人由于被纪念,因而存在。戴维不会再担心自己被遗忘,被忽略,因为爱不会允许父亲那样对待他,罗斯也因此无法抢走他的爸爸。正是这些坚信让他一步步看清扭曲人占领他人生命的罪恶,并拒绝与之交易,即便在狼群利齿的威胁之下。他的拒绝如同坚守,开启了生命回归爱的大门。
这就是那些等待内心复苏与自我承受的孩子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精神珍宝。成人在它们的光照下是否会看清自己的内心呢?期待一个肯定的答案吧。它只与单个的人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