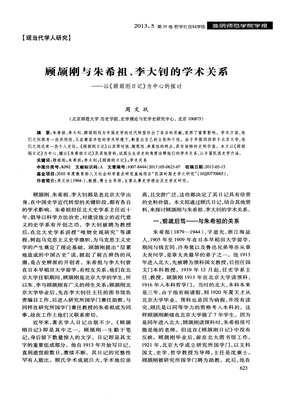《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读后感100字
《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是一本由顾颉刚著作,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2007年5月图书,本书定价:2612.50(人民币),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精选点评:
●真實的個人歷史記錄~
●98.算第二次翻阅吧,看得累人啊。
●学术写作时只能引用这版,大陆的是阉割版。
●电子版文献备查
●古史考人生。
●时断时续花了半年,才读完这套书,收获不如预想的大。
●台'版《顾颉刚日记》现货,需要联系我。价格优惠。
●补记
●顾颉刚日记已经算不错了,信息量很大,但还是改过的。
●图书馆貌似只有前五卷
《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读后感(一):不是评论,只是读后闲话(一)
这套十二册的“大书”,我断断续续花了半年的时间读完,抄录了最终不知能否用得上的十一万字的笔记,收获不如预想中的大。
由于第十二册是人名索引,实际上,我读完的只是前十一册。提到索引,这倒引起我一个不知道是否合理的想法,既然专门做了一册人名索引,何不干脆再做一册日记所涉的著述名索引?日记中涉及到大量著述,如有索引,在使用上,或许另有一番便利。举例说,顾颉刚一生都不曾忘怀胡适与钱穆的著作,不同的阶段,他都会翻阅两人的作品。如果只依人名索引,不容易看到这种现象。
这部日记不像豆瓣介绍所示那样——“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断记载外,自1921年起历60年基本未中断”,比如,实际上,1972—1974这三年的日记是空白的,1976年6月18日之后至1977年7月1日间的日记也中断了。
顾颉刚在日记所写内容多而杂,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事无巨细或者琐细。但是,有几条线索还是大体贯穿始终的。
其一,顾氏个人读书、写作(包括写作构想)、办刊、主持或参与各学术机构的过程。
其二,顾氏每天所见诸人,尤其是每次会议或宴会所见者,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有时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
其三,个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各方面给顾氏学术研究带来的困扰,顾氏身处诸种关系中引起的内心矛盾、焦灼、痛苦的精神状态。
其四,顾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几乎从日记一开始,顾颉刚就时时注意及自己的身体状况。
《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读后感(二):《一個歷史學家的微觀心態》
《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读后感(三):朱维铮:顾颉刚改日记
2009-2-1 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
久闻《顾颉刚日记》,已于2000年5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刊行,全帙凡十二卷,约六百万言。但直到去岁仲冬,始得《上海书评》鼎助,得窥全豹。
正因如此,这回拿到《顾颉刚日记》,便在非务不可的正业之外,即漏夜通读,断续耗时两个多月,虽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验。
它是“原始史料”吗?
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据整理者顾潮女士的“前言”,可知它的主体原名《颉刚日程》,有两个“基本”:
“《颉刚日程》自1921年1月始记”,“以后连续记载数十年而基本上不曾中断”。就是说,它记至1980年12月顾颉刚去世前,曾有中断。
引人注目的,是“前言”的另一点声明:“由于父亲将日记作为吐露心迹的场所,七情六欲,无所不谈,其中自有一些激愤之言,或许对他人会造成伤害,鉴于日记的史料价值,整理时基本未作删改。”那么,这类具有“史料价值”的涉及他人的言论,倘有“删改”,是否出于顾颉刚本人之手?
我生此疑,还因为顾潮有以下两点介绍。
第一,见于“前言”。“日记册的版式是父亲于1920年12月自己设计的,用毛边纸线装,约十六开大小, 每页竖向分为‘ 日期 ’、‘ 事类 ’…… ‘ 备注 ’、‘ 一周总记 ’九栏;横向栏目有‘ 号 ’、‘ 星期 ’及‘ 预计 ’、 ‘ 实作 ’二行,且排三列,即每页可记三天日记;页左端印有‘颉刚日程’四字及‘ 年 ’、‘ 月 ’‘ 号至号 ’及 ‘ 阴历月日至日 ’备填,以便检索。”(引注:空格均原有。)因知单是版式就很复杂。可惜联经版《顾颉刚日记》,虽有皇皇十二巨册,却没有一页书影,令我辈有幸一睹《颉刚日程》原稿面目,只能凭空想象那版式的“备注”、 “一周总计”和“预计”、“实作”等纵横栏列,必留不小空白“备填”。
第二,据“凡例”,可知《颉刚日程》原稿,“系表格式竖写”,由整理者改为横抄付刊。原稿正文每段“起始空二格,转行顶格”,“‘备注’及‘一周总计’中内容各另起段,起始空三格,转行空一格”。由于横排刊本,正文与“备注”等用同一号宋体字,读时如不留心每条起首及转行空格,便分不清孰为原记,孰为“备注”。
其实,如今所见《顾颉刚日记》,有多少可称“原始史料”?已很难辨别。因为根据顾氏自述,他的日记,多半先写在随身小册上,再誊入《颉刚日程》诸栏,也即在誊抄时做过修饰。他由草稿变成正文,又常隔数日乃至一周半月之后。这样他的日记,“基本”非逐日的记录,而是“日后补记”。据顾潮“前言”和“凡例”介绍,有些部分未经顾氏本人誊正,例如“文革”时,“写于小笔记本及台历之日记,内容系依《颉刚日程》分段,故抄写仍同表格式者”。不消说,经过如此处理,连小笔记本之类所存顾氏日记“原始”本色,在联经版刊本中也都消失。
既然如此,《顾颉刚日记》的“凡例”之二,就越发值得注意:“其中日后补记者,附于当日之后。若补记日期相距不远,则以较原记缩一格相区别;若补记日期在隔年之后,甚至相距数年或数十年,则更以楷体字相区别。”
章培恒先生看了关于《顾颉刚日记》的某篇介绍文章,已感到奇怪:“我才知道顾颉刚的日记是可以补充的,一九七几年补记他年轻时候的东西。”(《述学兼忆师友》,《书城》,2008年12月号)而我阅毕《日记》,回头再看上引“凡例”,不禁更感到奇怪,因为已刊《日记》本来大半属于顾氏本人“日后补记者”,岂知除此而外还有“补记”,而且后一类“补记”,又包含所谓补记日期“相隔不远”、“在隔年之后”,“甚至相隔数年或数十年”等情形。尤因刊本对“相隔不远”的“补记”,用同一宋体字排印,仅较“原记缩一格”,与当日的“补注”毫无区别,又没有《颉刚日程》原稿影本可资对勘,谁能分辨?
关于“更以楷体字相区别”的那些所谓补记,大约不会有人相信真是当年旧迹的实录。困难在于同“补注”无从分辨的所谓补记,可以信为真相记载吗?除了章培恒先生所疑的几则,如顾颉刚补记他年轻时对王国维的看法等。令我更生疑的,是顾氏有没有像他模仿的康有为那样,用倒填年月之类手法,以补记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或为自己作某种洗刷?
作为史学从业者,我相信马克思的一句话:“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看来,要清除对顾颉刚补记的疑问,一个简单做法,就是将他特别记述的时地人事,寻觅相应史料对勘。
《顾颉刚日记》的余序
早在1950年代,通过批胡适运动和众多师长谈论,我已知顾颉刚很难与人合作。他多疑成癖,好听窃窃私语,尤好信未必真实的传言。例如院系调整以后,他所在的上海学院部分系科并入复旦,而他本人也被复旦历史系聘为专任教授。他请假一年,分明由于当局已有规定,专任教授不可在外兼职,而他时任上海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经商收入远比复旦教授丰厚,但他却说不肯到复旦就职的理由,是因为周予同先生不欢迎他来复旦,所据便是某教授的私下传言。事实上,时任复旦主管文科的副教务长周予同先生,不仅与顾颉刚相交已二十多年,而且是决定聘任顾颉刚的复旦主要领导人。顾颉刚找借口继续经商发财,竟以传言为依据,忍心污蔑老友,还一本正经地写入《颉刚日程》(见《日记》1952年9月21日),此人所记可轻信么?
余序凡五节,第一节论顾氏的“事业心与傅斯年”,第二节论“顾颉刚与胡适”,第三节“顾颉刚与国民党”,第四节“1949年后的顾颉刚”,也都时时涉及顾、傅、胡的恩怨关系。我很佩服余先生对三造都取“了解的同情”的态度,却又感到余序或许调停过度,以致可能明知《顾颉刚日记》述及他与傅、胡关系,内有不实情节,却只含蓄带过。
一个显例,便是《顾颉刚日记》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
关于顾颉刚致胡适函
胡适于1949年仓猝离开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有大批私人文件未及带走,其中包括众多书信。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选编了胡适留下的部分书信及函电稿,题作《胡适来往书信选》,分上中下三册,由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发行。虽说发行限于内部,却很快传播海外。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刊行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所收函件便与中华版雷同。其中收有顾颉刚致胡适信多通,当然引人注目。
前揭《顾颉刚日记》余序引顾颉刚致胡适那通长信,序中明谓写信时间为“1929年8月20日”,出注谓引自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核以前揭中华版《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475号“顾颉刚致胡适”,引文及顾氏自署写信时间(“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完全相符。
余英时先生通读过联经版《顾颉刚日记》的全部未刊稿,不会不注意《日记》在1929年“八月二十号星期二(七月十六)”那天,所记内容为顾颉刚在苏州会友、游园、训女等,没有只字提及给胡适写信。尽管此前四天(八月十六号),他曾经“到苏州饭店访适之先生”。
然而,《日记》1928年“八月二十号星期一(七月初六)”,却赫然记道:“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同日“备注”又道:“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也在同日,又记“登日记七天”,显然此则乃属“日后补记者”。
于是我赶紧重读《胡适来往书信选》所载民国18年8月20日顾致胡信,核对字数,共四千八百余字,可称“约五千字”;内容呢?原信劈头便说:“接九日信,至感先生的好意。不过我两年来的环境和心情有非先生所知者,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详细一叙。”往下便由离北大到厦大说起,再详述到中山大学年余的遭际,中心就是述说与傅斯年(孟真)的关系日趋紧张,当然力陈错误全在傅斯年。信谓“先生信中劝我不要骄傲,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骄则未也”, 随即絮絮叨叨,自我辩解并指斥傅斯年,表示心中充满“烦闷,愤怒,希望,奋斗”云云。凡此,与《日记》1928年8月20日“写适之先生信”所记要点无不相合。
关键在于写信的时间。《胡适来往书信选》据顾颉刚原信手迹刊印,信末顾氏自署作期为“(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然而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却录于1928年即民国17年同月同日记载之内。二者相差整整一年,就是说两个年份必有一误,哪个记载可信?
《日记》既为顾潮编定,且看也由她编著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怎么说?该谱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戊辰)三十六岁”目内,在8月20日记“与胡适书”,夹注谓据“日记是日”,而后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所录原信的两段个人牢骚语,既略去信中对傅斯年的反复控诉,更不提信末顾颉刚自署的写信日期。更妙的是该谱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三十七岁”目下,连“八月二十日”也不记,甚至不提顾颉刚在此月19日在苏州造访胡适一事。对顾潮这一含糊记叙,只能说是她已发现其父日记与致胡适原信的时间悖论,却以一则夹注表示宁信日记,而对原信明署的作期,以不了了之。
恕我直言,余英时先生似有同病。他在序中特别说明顾颉刚致胡适的那封信,作于“1929年8月20日”,昭示他以为《胡适来往书信集》初次发表的原信所署日期是可信的。他将顾颉刚此信定性为“向师门诉冤”,也与原信内容主旨相符。但也因此,他围绕此信一再考察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恩怨,多处引用《日记》,却始终未提《日记》将此信作期提前了整整一年。个中缘由,甚盼余先生有以说明。
顾颉刚改日记后述
所谓日记,顾名思义,当为逐日之纪录。古往今来,日记作者多矣。就已刊布的日记来说,作者或为写给自己看,或为写给他人看。无论写给谁看,原记可以秘藏,可以销毁,可以在生前择要刊布,可以在死后全文公表,却很少有人在事后增补,更极少有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而篡改昔作。
《顾颉刚日记》却表明,作者不仅补日记,而且改日记。
本来,时隔经年乃至数年数十年,所补当年当月的日记,可信度已令人生疑。可是,顾颉刚竟然在晚年修改中年所写日记,乃至将他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也许他以为改得天衣无缝,谁能质疑他亲笔改定记载的可信性呢?
果然,从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到批判胡适,顾颉刚都能“过关”。他于是被召唤进京了,位居中科院一级研究员,月薪五百万,远过历史诸所首长;住房阔达十多间,较诸同所助研举家一室难求,有天壤之别。随即增补为政协委员,又名列民主促进会核心成员。因而他此后在日记中时时抱怨从政妨碍治学,是否真话?至少在京沪二地熟悉其人的学者中间,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表态出自肺腑。
2009年1月8日夜
《顾颉刚日記(全十二卷)》读后感(四):评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一文并驳斥改日记之谬说
http://www.gmw.cn/01ds/2009-03/04/content_893691.htm
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 ,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
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图一)顾先生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日记》说是因为“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信中所陈“两年中痛苦”,指从1926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到厦门大学说起,再到中山大学后一年多的际遇,主要是关于自己与傅斯年之间在学术研究、工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过程。但是这封信的落款时间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图二),即1929年8月20日。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此前曾引起学者注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根据原件整理,整理者将此信置于1929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5年)根据原件影印,编者已将此信置于1928年,可惜未说明理由。好在这封长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不难考究其确切的写作年份,因此三十年以来也并没有成为被大家特别提起的话题。 但是,随着《顾颉刚日记》的公布,细心的读者通过日记与书信的比对,发现了这个都是由当事人亲笔留下的在写作时间上的两歧纪录,于是产生了怀疑。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在读过《顾颉刚日记》之后,就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刊登在2009年2月1日《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版中。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日记在自己手上,而书信在收信人那里。―― 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年10月25日日记)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穆说:“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疑与信,皆需考。”所以说要确定顾颉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其最直接也最可信的方法,就是将信中涉及到的时、地、人、事,寻求相应的史料来比勘印证。 顾颉刚这封长信中,至少有八件事的确切时间可以考知,兹先引原文,再略述事由如下: 〔一〕前年出京时,负了二千元的债。 按“前年出京”指1926年8月顾颉刚离开北京受聘厦门大学事。顾颉刚1926年7月1日日记:“兼士先生送来厦门大学聘书二纸,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拟于八月中行。”遂于该年八月五日起程“出京”,二十一日抵厦门。所谓“负了二千元的债”,据顾颉刚1926年1月6日日记载欠债总数为“共一千六百五十二元六角零五厘”,同年5月16日致胡适信中,列“颉刚欠款”清单,共欠款“一千九百五十元”,同年9月12日日记载欠债数为“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元”。信写于1928年,与称1926年为“前年”正合。 〔二〕去年上半年,就为了别人的攻击,弄得心很乱,没有继续做研究的工作。 按“去年”指1927年。顾颉刚1927年6月28日致沈兼士信曰:“此半年中,一班无聊人为我造谣不少。”同年7月4日致王伯祥叶圣陶信曰:“这半年中,生活一乱,差不多没有读书。” 〔三〕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1月28日日记:“希白来信,谓燕京大学,司徒校长往美国捐款,得二百万元,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因招我去。此事我极愿就,在北京,一也。生活安定,二也。”同年2月23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研究中国学经费,年定十万元,予心颇动,欲往。盖(一)予尚未经过正式之研究生活,日夕盼望达到,(二)予书籍器物俱置京中,两年在外,总难宁定,(三)康媛不入北京聋哑校,无其安心立命之所也。”希白,容庚字,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所谓“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事,即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洪业、董纳姆等筹划,于1928年1月4日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基金”即由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所设立的“霍尔教育基金”。 〔四〕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 按“那时”指1928年3、4月间。顾颉刚1928年3月20日日记:“蔡先生(即蔡元培)有电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款照汇,筹备委员照派。此事可进行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民国十七年三月,本院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3月25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大学设立之研究院,其研究员仍须兼大学本科课,并须办事,闻此使我心冷。”次日日记:“写致希白书,详说近年所感痛苦,求去粤之意,并说不就燕大本科教授之故。”信中说:“兄来书中谓燕大中‘不教书、不办事是办不到’,这颇使我失望。燕大既办研究院,为什么不让人专在研究院而必兼大学本科的职务呢?兼了大学本科的职务,又要办研究院的事,那不过是使我复演厦门、广州的生活而已。我既决不会满意,而贡献于燕大的成绩也不会很多。……此事弟不愿就,幸恕之。”同年6月15日致胡适信:“今春燕京约我,我本想去,因怕伤孟真感情而辞去。好在我只想得一研究的环境,如中央研究院可办好,则与去燕京无殊,故下半年决在中央研究院矣。”又,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故十七年夏间燕大见招,弟已谢绝,谓下期到中央研究院,较燕大之必兼数小时功课者,尤为适于研究。”可为佐证。 〔五〕今年放暑假时,我是预备脱离广州的。经校长和学生作了十馀天的挽留,始应承再留半年。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7月11日致容庚信:“弟本拟于今夏返京,如无此间校长与学生日日来留,无法摆脱,只得再留半年。”同年7月15日致胡适信:“我本想本月底北行,因骝先先生及学生坚不放走,只得答应再留半年。”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不幸是年(即1928年)暑假时,朱骝先先生一再挽留,学生亦一再挽留,情不可却,只得再留半年。”故到1929年2月学校放寒假时,顾颉刚才携眷离开广州北上,临行时曾作《离粤时与诸同学书》、《顾颉刚启示》(分别刊于1929年2月间《中山大学日报》、《民俗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六〕举一个例罢:譬如这次中大招考新生,我为阅国文卷的主任,我见有些人批分太苛了,有些人的标准太不定了,使得考生吃亏许多,我便于阅毕之后重阅一过,改定分数。 按顾先生1928年8月17日日记:“阅国文试卷者六人,信甫、太玄、杭甫、莘田、泽宣(第二日请缉斋代)、予;予为主任。”19日日记:“到校,增加试卷分数。……阅卷诸人,缉斋太刻,太玄毫无标准,有可以六七十分而仅批八分十分者,虑学生吃亏,故为改批。” 〔七〕自从到了广州以后,《研究所周刊》出到四十二期了。 按“《研究所周刊》”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1927年11月1日日记:“[周刊一期(1―26页)。]”以后每周一期。1928年8月15日日记:“[第四十二期(发)。]”同年8月22日日记:“[第四十三期(发)。]”又,1929年7月5日致闻一多信:“《研究所周刊》已出至八十期。” 〔八〕今日览报,悉孑民先生已辞大学院长职,中央研究院不知要否受影响。 按“今日”指1928年8月20日。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谨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本职及代理司法部长兼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亦一并辞去。”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18日:“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东方杂志》时事日志1928年8月18日条:“蔡元培辞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携眷离南京。” 综上所考,顾颉刚日记将此信隶于1928年8月20日是不用再怀疑的。不过书信的落款写作“十八年”,确实有点令人费解――最可能的答案就只能是他一时的笔误。因为是年11月1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久不慊于我,今乃一发也。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矣。”傅斯年从胡适处见到的顾颉刚“致适之先生信”,即是此信。此信之曝光,似乎加速了顾、傅间的“交恶”。顾颉刚虽说“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实亦不曾断绝,从保留下来的1929年以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往还的十数封信中,我们犹可以读到两人间的互为帮助及真诚鼓励――或许这样的“私交”可能仅停留在文字客套的层面,所谓江湖浩浩,各行其道,但在学术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老辈风范,今之学人多不可及矣。
………………………………………………………………
读朱维铮先生2月22日发表于《上海书评》的《顾颉刚铭“九鼎”》(下简称“朱文”),对这桩我以前不甚了解的民国时期的公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收获颇多。朱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似素无好感(看《上海书评》2月1日发表之《顾颉刚改日记》),在此文中对顾先生自然亦颇多贬抑之辞。但文中有几处似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今写出来向朱先生请教,也请读者指正。 朱文说:“既然从1923年起,顾颉刚就坚持说大禹治水、禹作九鼎,均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由此建构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辨伪系统,怎么时过二十年,到1943年,他却自悖其论,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向蒋介石‘献九鼎’呢?”据我所知,顾颉刚先生从未发表过“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意见。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致钱玄同信中,写过下面这些话:“《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古史辨(一)》62页)顾先生在同一年发表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还提出“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的看法。总之,顾先生只疑禹本来并非人王;却并未讲过类似“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话。至于《史记·封禅书》等所说禹铸九鼎,大概是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语中“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说法演变而来的。顾先生对禹铸九鼎说法出现的时代本并无明确意见。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顾先生只说他在1923年给钱玄同的信中曾据《左传》此文相信九鼎是夏铸的,禹的出现与九鼎上所铸纹饰有关系;因顾先生又怀疑“贡金九牧”之语,所以放弃此说(《古史辨(一)》63、119-120页)。至于先秦无禹铸鼎之说,是顾先生和童书业在1937年合作发表的《鲧禹的传说》(《古史辨(七·下)》194页)中才明确提出来的意见,并非朱文所说的“1923年”。关于此问题,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指出先秦无禹铸九鼎之说,并非建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根据;第二,据童教英说,《鲧禹的传说》等文都是“由父亲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然后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49页,《鲧禹的传说》已被收入近年出版的《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将此意见归在顾先生一人身上,恐亦不妥当。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二)中“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一句,朱文解释说,“首句分明套用《周颂》‘於皇武王’,而‘於皇’据清人《诗》注乃表示赞叹的发语辞。但内有‘皇’字,便可能犯忌,……顾颉刚于是用生造的‘於维’代替了。次句‘允’作信解,也是《诗》《书》常用字,而‘允文允武’则语带双关,既赞总裁兼委员长乃唯一的文武领袖,又可据《尚书·冏命》释作总裁真是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至于《冏命》是‘伪古文’,就顾不得了。”其实“於维总裁”句即使是套用《周颂》“於皇武王”,“犯忌”之说亦不能成立。众所周知,《武》“於皇武王”之“皇”并非专制君主之“皇”,而是“大”的意思,顾先生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此句其实不但不是套用《周颂·武》,“於惟(‘维’与‘惟’古通用)某某”也并非顾先生生造。这类说法常见于汉代传世古书及碑铭,《汉书·叙传下》“於惟帝典”(颜师古注:“於,叹词也。”),《郎中郑固碑》“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金石萃编》卷十),《敦煌长史武斑碑》“於惟武君,允德允恭”(《金石萃编》卷八),《荆州刺史度尚碑》“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该,克忠克贞”(《隶释》卷七),是其比。伪古文《尚书·冏命》“昔在文武,聪明齐圣”中的“文武”自然指文王和武王,但是这跟顾先生所撰鼎铭又如何能够比附呢?从我们上举汉碑“允德允恭”、“允懿允明,文武是该”等话来比照,顾先生所作鼎铭“允文允武”中的“文武”则恐怕只宜作形容词理解,而决不好与“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等意义牵合。朱文以顾先生不顾《冏命》之伪以媚蒋,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一)原文“万邦协和,光华复旦”被马衡改作“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朱文解释说:“首句出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清代汉学家较通行的诠释,百姓指百官,协意为合,邦指封国。二语大意谓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这是未然语,表示一种期盼。但顾颉刚将‘协和’与‘万邦’二词对调,意思就变了,变成已然语,暗喻蒋介石已使万国实现和谐。”“协和万邦”是动宾结构,“万邦协和”是主谓结构,其差别并不一定在于“未然”和“已然”。从语法上讲,“协和万邦”自然可以根据语境表示“协和了万邦”或者“使万邦协和”的意思。从《尧典》上下文很容易看出,“协和万邦”实非“未然语”,而是对尧统治时盛况的描述。此句孔颖达《正义》说:“百姓蒙化皆有礼仪,昭然而明显矣,又使之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可以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理解。《东观汉记》“盖闻尧亲九族,万国协和,书典之所美也”(《后汉书·下邳惠王衍传》李贤注引和帝诏),正是汉人引《尧典》时把“协和万邦”理解成“万邦协和”的确证。朱文却将此句翻译作“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平白增添了“告诫”、“要”等词,并把“昭明”解释为“放明白些”,都与《尧典》原文意思不符,其症结是否都在于想把“协和万邦”解释成“未然语”,进而给顾先生贴上“寡亷鲜耻”的标签呢?最后说一句,《尧典》作“协和万邦”而不说“万邦和协”,是和下句“黎民于变时雍”趁韵(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邦”字条,“邦”、“雍”是古东部字);马衡将顾先生所写“万邦协和,光华复旦”改为“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最平实简单的解释恐亦当从押韵的角度考虑(“同”也是东部字)。所谓马衡对顾先生的“谀词”“难以忍受,非改不可”云云,大概也属求之过深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