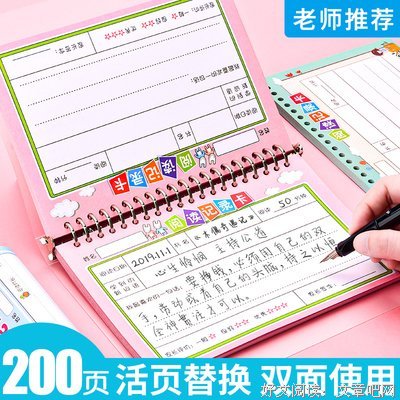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感摘抄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是一本由刘宁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1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精选点评:
●值得再读。
●一条脉络牵引下来,先秦至于民国之思想阐发与论述文体所以得以辩证交通,来往互动之间,遽然有所明白。
●没有想象中好。全书的想法源于韩愈的自白,更重要的或许是韩愈为何生出那样的作者意识,以及这一作者意识与古文运动的关联,与汉魏六朝作者意识的对照关系。论域收束于“论”文体的源流嬗变,可能反倒遮蔽了问题的本来面目,可能聚焦于“作者意识”的变动更为妥帖。
●这个题目满有发散性的。。。缺乏背景知识只能泛泛看了。。。事后想想真是功底深厚
●作者出于对韩柳古文的兴趣,以“论”为核心展开全书。第一章诸子论著算是“论”之前身,而自东汉以来有作者身份的“论”才是本作核心。尤其唐代以后的“论”,应是作者着力处。基于对大量文献的熟练运用,对“论”唐宋时段的转型颇有新意。可商榷处,是经、子与“论”的关系,此大题目似乎不易入手,以形式分析流于简单化。
●问题很重要 但写得没有想象的好 第四章宋代部分逻辑不能自洽
●言简意深
●新角度,切入经学、子学与文学的“夹缝”之中。但是感觉此书还可以更详而论之。
●干货
●翻完第一章,其他章节囿于知识水平不能继续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感(一):强行把书中大意梳理成了两条线索
两条线索相互对立:
子学论著与论体文-起于《荀子》-述圣-知言-辩名-博涉兼综-思辨性
语录、札记-起于思孟学派-拟圣-养气-悟道-高自树立-超越性
个人启发:
1.书中谈及《孟子》知言养气并重、玄学注经著论同兴,感觉是值得多做研究的部分,惜其未竟。
2.近代学术之论文、论著以史为重或许并非是中古述圣之论的回响,而可能是清代考据大盛的遗风。就此还可以发散出清代考据文章或许可称为汉语思想文体之再变的判断。书中只讨论了从“述圣”到“拟圣”的转变,而从宋明的儒学讲义到清代的经史考证或许又是一次转变。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感(二):在思想与文体之间 ——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
刘宁,女,1969年生, 江苏江阴人。1987至199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7至199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9至200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9年7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韩愈研究会理事。2001至2002年,任韩国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交换教授;2006至2007年,受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资助,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唐宋诗文研究,关注与此相关的思想史、经学史问题。
全书由五篇论文构成,分别为《汉唐子学论著》、《论体文的形成与演变》、《文体互动:经与子,注经与著论》、《宋代:拟圣:拟圣与理学文体》和《思想文体形式的近代转型》。这五篇论文构成了《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结构,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文本的承载形式,从而揭示中国思想的发展流变。任何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文体的表达形式,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把握中国思想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角度。
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整部书其实是中国”论“体文史,从首章”论“体文前史,次章论体文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注疏与论著的比较,第四章论体文的衰落,第五章论体文的现代转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先生这部书的主体已经从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变成了论体文发展史,这个转化将整篇文章的所探讨的主题进行了修正。
我们不妨设问,汉语思想的承载文体是什么?刘先生作为文学史家,从而并未对思想进行定义,径直将其定义为子学论著或者论体文。这样的界定,不免就将汉语思想限制在丙丁二部之中。这是否是汉语思想的历史事实?当然,这样的界定,使讨论刘先生避免了讨论甲乙二部的困境,毕竟讨论经学文体的转化,就不仅仅是这五篇论文就能讲清楚的,何况还有史部的体例调整问题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刘宁先生偏爱论体文的缘故,以至于其将宋明理学直接斥之为拟圣文体,并认为其导致了论体文的衰微。而在谈到论体文的现代转化的时候,虽然谈及严复、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超,却将白话文与西方学术文体的引入略之不讲。难道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化,不也是预示着汉语思想的巨大转变吗?
刘先生整部书给人的感觉是写作思路非常清晰,将论体文的发展和转变展现出来。但是,整部书给人的感觉却是文题不符,就如前述所言,是汉语思想决定了文体表达的形式,还是只有论体文才是汉语思想表达的方式?刘先生在整部书中并没有给与清晰的解答,而是含糊地将论体文径直当作汉语思想的表达形式了。但这就给人留有了反思的空间,难道只有论体文才能表达汉语思想吗,抑或是只有学院派的论文才能代表中国的思想表达吗?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感(三):读《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想到的
这篇不是评论。
去年秋天,十三哥和我夜宿陈老师家,侃到凌晨,席地而眠。在老陈书架上我发现了刘宁老师这本书。题目取的一点也不惊悚,乍一看还以为是那种搞文体分类流别的书。老陈说这本书“不错”,像他这种刻薄的潮汕人能有这般评价,实属不易,不久我就在西单图书大厦专门摆放汉语教学的架子上找到了这本小册子。书和众多汉语教材摆放在一起,很凄凉。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腰封已经丢了。
如今读者对书的评价很难一致,即使是品质稳定的学术书籍,也不见得人人都认为是好书。刘宁老师这本书我很喜欢,也主要是因为契合了自己读书和思考的一段经历。书只有150多页,说是篇论文也不为过。又据说刘宁老师为学术二代,温柔可人,著作果真是凝练准确、笔锋锐利,把观点解释的非常清楚。既然这本书写得又薄又不晦涩,所以有兴趣的读者直接去读。我这里只是因为读书会可能要讨论这本书,于是把一些想到的问题随手写下来备忘。
最主要的是“文道观”这一话题。
刘宁老师是中文系出身,凡是在中文系念过的同学都知道,自从经学被打倒,辗转苏联的西式学科建立后,“文与道”这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解经),在当代学界主要被锁在了中文系古代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史)这座幽暗的大牢里。自民国以来,近代教育兴起,学科建制逐渐成形,主要关注“道”的中国哲学学科对“文”关注的不多,因为“文”不属于“哲学”;而“文”天经地义地被过继给了中文系。近百年来,我们中文系关于“文道观”的种种论述虽然成就不少,但大致就做了两件事:其一,将其作为寿终正寝的“国故”,“阐述”和“辨析”(这两个词语在本书中有特定含义)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道观,譬如“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义理考据辞章”等等,区分其异同,阐明其意义,从而把“文道观”只能看作理解“古代文学”的理论工具之一;其二,不管论述的多么精彩,最后基本归于一种结论:古代的文道观念禁锢了文学的自由,把文学变为载道的工具。
说到底,文学学科对文道观的种种论述,是以现代观念的“文学”为立场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天经地义。但刘宁老师特别指出,被文学理论的锁链禁锢的文道观,只能看到“文学作品”的“文”,而对经学的历代注疏、论著、语录等以“载道”为旨归的“文”漠然视之,因为这些“文”太“质胜文则野”,压根算不得“文”了。
我最早在中文系接受的文学理论教育大抵如此,直到后来才彻底改变。近十年来,国内学风有些变化,重视经典解释尤其是经学解释是这些风气之一。不得不提刘小枫,虽然他从神学转向开始就毁誉参半,最近两年甚至颇招骂名,对他的新著,有人目之为神,有人目之为鬼,有人目之为神神鬼鬼。坦率的说,刘小枫对我的很多同龄人影响不小,当然这种影响既不在神也不在鬼。在本世纪初,我在中文系最初通过诗学、美学接触到他的著作,不久,加持文艺青年后又钟情《沉重的肉身》之类。所以,当他后来从神学转向经典,鼓吹读经更鼓吹读历代注疏,这一点也随之影响我与一些同龄人。当时,我和身边很多颇以读书自诩的同龄人都还在热衷各类理论概念,以能熟悉并使用西方最新的理论为荣。也沾了点古典文献学的仙气儿,但目的是背书名儿,更有些同学无条件反传统。但正是受刘小枫等的影响,大家开始认识到“读书”二字远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下大工夫读经典打基础的。所以突然有一天觉得曾经的自己就是文盲白痴(现在仍然是)。开始逐字逐句的读古书及其历代注疏,再也不敢把孔子和德里达都看做是地位“平等”的哲人了,再也不好意思念叨这个“后”那个“新”了。这就是刘小枫对我与一些朋友的影响,也仅止于此,至于小枫等人后来鼓吹的那些,反倒不怎么关心。
近年刘小枫组织翻译了不少西方经典的历代注疏,组织整理了中国经典的一些注疏(中国的这部分诟病较多,不是书不好,而是质量不够上乘,他一直找不到一流的人才帮他做这些事)。但是,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始终未能解决“文何以载道”的问题。所谓“文以载道”,就是“经典如何解释”的。我们不再怀疑经典的意义和力量,也相信经典对政治、社会、人心有着深刻作用,但更觉得唯有实现现代意义的“文以载道”,找出能适应“千年大变局”的“经典解释”的方式,才能对现代及未来中国产生影响。刘小枫阐释经典主要是模仿施特劳斯师徒,有些笔调都相似(近年,做中国经典解释的青年学者颇出自哲学系而且是外国哲学,西哲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敏锐的发现有趣的思想问题,但同时对传统文献的把握不够精深)。其他很多学者则受制于学科建制,受制于把经典史学化的“从古史辨、整理国故到史语所”的近现代学术传统,受制于西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西学各流派)的“先进性”压迫,长期以来,甚至连“经典如何解释”的问题都不曾措意。
所以,刘老师这本书把“文道观”作为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存在,且生命延续至今的“活”问题表述出来,而不再以整理国故的态度,将其作为“文学遗产”的“死问题”。于是在我看来,“文以载道”也总算挣脱了中文系文学理论学科“降龙伏虎”的枷锁,恢复了其“经典解释的文体形式”的本来面目,把“毒害文艺青年”的大帽子扔进了文学史;也比刘小枫等人更切近实际的谈到了: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解释有着相当丰富、多样、深刻、契合不同时代经学思想的解释方法与文体。(想到了M老师的《比经推例》)
去年,花溪廖兄来邮件,也在谈今日将用何种文体来解释经典的问题,目光敏锐。我想起甘阳曾经讲过一个很流行也备受取笑的段子,他说如果国防部长改称兵部尚书,就会自觉的去找历代兵部尚书的传记和著作来读,而不是只读外国的国防部长们的著作。对甘阳不做褒贬,但这个笑话倒是指出了这本书能够产生的一个影响:先要知道历朝历代对经学的解释(汉语思想)是通过哪些不同的方式(文体形式)表达出来的,才能对今后用何种方式、何种文体来解经有更新、更细致、更深刻的视域,而不必非要按照近代以来的范式写论文出专著,或非要学西方公羊家把隐微书写搞得人尽皆知。至于书中是如何具体梳理历代解经文体形式的,开卷有益,毋庸赘言。
另一个问题是这本小册子可以说从文体形式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一遍经学史,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部经学小史。简而言之:
《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有着独特的文体形式,表现为对儒家圣人的思想“述而不作”的“述圣”格局,语言呈现出“阐述”观点、“辨析”异见的特点,重在“正名”而轻于逻辑推理。这几个特点极大影响了汉代之后的解经文体及风格。(第一章)
在西汉,刘宁认为“今文章句”这一解经文体之所以篇幅越来越长,是因为受《荀子》影响,章句不断地“辨析”新出的“异见”并“阐述”家法(p93),她猜测今文章句可能和“子书”的风格近似(p85);到东汉,古文章句摆脱了这种影响,重在打通群经的基础上进行简明训诂,但是,《荀子》的影响转到了东汉诸子学、论体文(p65)的兴盛上,并持续到唐代。(p85)。
魏晋受玄学、佛学影响,论辩风气蔚然,东汉论体文又有了新发展,刘老师称之为“著论”,并认为,魏晋的注经仍然延续了东汉注经的方式,但“著论”更体现时代特色,更便于论辩。魏晋“著论”虽然内容多为玄学,但却影响了六朝经学“义疏”这一“文体形式”,刘老师认为义疏中包含的论辩内容,既是《荀子》及汉代论体文“辨析”特点的延续,也受“著论”的推进(p95)。
以上可以看做一个关节。刘老师从形式上梳理了汉唐经学思想解释的文体及其变化,基本上符合她提炼的“述圣”的格局。
自韩愈开始有了变化。刘老师首先仍然将韩愈置于受《荀子》影响的“论”的文体传统中,但她指出韩愈是一个“转型”(p70)。所以,宋明理学兴起,表达思想的文体则逐渐以语录、或问、札记等为主,刘老师概括为“拟圣”(她指出杨雄、王通等已有先例)。理学的兴起大家都很清楚,用语录等文体来直击宋明儒者对道德主体的追求、对圣人的模仿也的确便利。而汉唐经学的“述圣”格局崩坏下去,刘宁有一句话一语中的:“子学论著的核心精神是成一家之言,与圣人制作判然有别”(p106)。
有趣的是,这两个关节恰恰也与经学史上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不同特点有颇多相应之处。汉唐经学的内容确乎是以讲解儒家观点、与墨、释、老等展开论辩为主,而宋明理学无论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目的都指向个体道德主体的构建;汉唐的经师们大都以将儒家信条落实在政治制度、法律解释上为己任,没人敢说学孔子,而宋明儒则不介意学圣人,甚至鼓励学圣人;汉唐的名相贤臣们多是以事功为中心,而理学兴起后的名相贤臣则想集“道德文章功业”为一体。所以,刘宁老师关于“述圣”“拟圣”的文体形式,简直可以构成一个小小的经学史。
在最后一章,关于文体形式的现代转型,刘老师也有一些有趣的见解,她认为近代学科体制建立,民国开始以论文授学位了,但直到今天,汉语“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写作,其实仍然受《荀子》“述圣”风格的影响。(p152)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实则宣布了“文道观”一直存在,传统文体的影响也一直存在,经典解释的文体形式大有回溯揣摩的必要。
最后说点闲话,读完此书,越发觉得写短文真见功力,也真难。记得当年写毕业论文,我和十三哥约定,谁要是超过了十万字谁就是傻逼。结果没几天学院通知说不许少于十万字,我俩骂了一通规定,等到真正写的时候,却发现写短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写多了。刘老师这本书满打满算只有六万字,几无一句废话,值得学习。不足之处,一是对《孟子》的讨论极少,可能确乎不易处理;二是是对“论体文”的表述前后有些混乱,概念定义不清,当然这可能是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无论怎么下定义都会有例外,而思想史上过于漂亮的整齐划一不仅必不存在,而且可疑。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感(四):《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读后
一. 载道之体的历时演变
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一书,所关注的是“文”、“道”关系。此处“道”指的是思想;“文”指的是“文体”。但这里的“文体”很难用“体裁”、“体类”、“风格”来解释。看刘宁的论述,这里的“文体”更多指向一种文章写作方式,与历史文化语境有相当大的关联。
1、子学论著
“子学论著”(包括《荀子》以及诸多汉唐子学著作如《淮南子》《论衡》《潜夫论》《新论》《中论》《申鉴》《傅子》等),主要是一种经验式的,以“述圣”为特色,关注政治、伦理等现实问题,不注重抽象玄远之思,融合百家,“成一家言”,结构松散的文章写作方式。
小问题:
(1)七十子后学散文与《荀子》的异同:
同:①都带有“集义”特点;②都强调修养教化精神(都有“师”者气象,孔子是万世师,荀子是帝王师,这一点与其说是述圣,不如说拟圣更确切[1])
异:①《荀子》以儒为宗,但已杂入他家,如法家,有融汇百家的气象。
②在思辨性、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专论意识上,相对于七十子后学的“传记”传统有了改变。一个突出表现是,其专论之主旨更为集中了。P16
(2)《荀子》之正名论证与辨析群言
正名论证:多援引论证(即引《诗》《书》以为证),少历史论证(即引历史事实为证)
辨析群言:多直陈主观见解,很少展开辩论
荀子之文以“正名逻辑”为核心,与注重逻辑的“辩者派”不同,“正名派”以政治伦理为主,其目的是为政治和伦理服务。
(荀子这种充满教条化色彩的端庄之“辩”,并不能在逻辑上有深入的探索,其核心还是运用主观性的“正名”来树立己见,甚至对“正名”的运用也缺少复杂性。思辨手段的简单,使得荀子对抽象问题的讨论,比较质实,缺少玄远、抽象以及超越性的色彩。)[2]
(3)《荀子》与《韩非子》的异同
同:都是有内容丰富的专题论文构成。
异:《荀子》论辩极为平和;《韩非子》善于揣度人心,感染情绪,快捷犀利。
《荀子》并不涉及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更关注君主的“修养”,注重启发教诲;《韩非子》大都是“法术之论”,文体近于“策”,更关注现实具体问题
《荀子》采用“集义”格局,结构松散;《韩非子》的行文结构更有条理性,呈现为数字式的归总概括。
《荀子》的正名逻辑是,通过对“名”的各安其位来完成论证;《韩非子》则更注重对“名”之差异与矛盾的辨析,韩文之犀利老辣,也正来源于对“名”与“名”之间尖锐对立的揭示。
(4)《荀子》与汉唐子书论著的异同
汉唐子学论著的代表性著作:
西汉:贾谊《新书》、陆贾《新语》、刘安主编《淮南子》。
东汉:王符《潜夫论》、桓谭《新论》、王充《论衡》、荀悦《申鉴》。
魏晋:曹丕《典论》、徐干《中论》、傅玄《傅子》、葛洪《抱朴子》、刘昼(北齐)《刘子》、萧绎(梁元帝)《金楼子》
同:汉唐子学论著受到《荀子》深刻影响,表现在:
①侧重“治术”的讨论,“上穷王道,下掞人文”;
②经验化的表达特点,侧重经验教诲的“述论”格局,在逻辑与思辨上缺少深入的推进,折中群言成为重要方式,在表达上比较理性节制;
③结构上,以松散的体式为主,没有明确的体系;
④汉唐时期,尤其东汉魏晋时期的思想格局,与荀子接近,是一种“儒家统摄九流十家”的格局。[3]
异:汉唐子学论著中,包罗万有的格局逐渐消失,向专门化发展。
总结:P53
2、“论”体文
“论”体文的最主要特征是对抽象义理的关注,有一种超越品格。
具体而言,“先秦时代的‘论’体,是针对抽象义理从特定角度展开的反思性论述,其产生和反思群言的时代氛围有密切的关系,在形式上吸取了往复辩难的表现因素,其关注大义的超越性品格,和务实功利的策士说辞有明显区别”[4];
《荀子》和《公孙龙子》中以“论”名篇的篇章,基本上是对抽象的核心义理的阐发和说明[5]。《荀子》所讨论的“礼”、“乐”、“天”都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而《荀子》其他不以“论”名篇的作品,基本是关注具体问题。《公孙龙子》之五论所讨论的内容也是关乎名实关系的抽象逻辑命题,这说明“论”所着眼的,不是一事一议的具体功利问题,而是关乎大义的伦理命题、逻辑命题[6]。
问题讨论:如何理解“述经叙理曰论”?
作者说:“《荀子》之专论,‘传记’之文有密切的关联[7],《荀子》之《劝学》和《礼记》之《学记》就多有近似。但‘传记’之文的内容比较丰富驳杂,而《荀子》四论,则更加集中于抽象的核心义理的讨论。刘勰《文心雕龙》认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这就揭示了‘论’在体制上,既继承了‘传’‘记’说解经典的基本特点,又专注于抽象义理的独特侧重。”(P58-59)
又,结合前面所说:“《荀子》之文,是‘师道’教化之文,其说理格局,通过‘七十子后学散文’的中介继承了《尚书》的君臣训诫以及《国语》的贤人教诲传统,侧重的是教化之道的直接传达。这样的说理格局,表达意见的‘述’,是行文之重心,而思辨之‘论’,则要从属于‘述’,在这样的‘述论’格局中,逻辑与思辨的发展,要受制于‘述’的基本精神。”(P22)
大致可知,按刘宁之意,《荀子》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以“述”为中心,以“论”为从属,述论结合的写作形式。而《荀子》“四论”则更为侧重“论”,专注于抽象义理。
此处刘宁对刘勰之“述经叙理曰论”的论断,实际上是分开理解的。即,《荀子》的多数文章可看作是“述经”的,而“四论”是“叙理”[8]的。这种理解是否符合刘勰本意呢?可是按照这种理解,“四论”之纯抽象说理,与刘勰所说的“述经叙理”似乎并不一致。
又,“‘论’体文虽然在理论性和思辨性上超过了子学‘论著’,但由于其核心仍是以‘述’为本,在超越性层面的开拓,仍然受到制约。”
可见,在刘宁的理解中,“论”体文中的“述经”是无处不在的,“述经”是本。因此,在《荀子》中,乃至在东汉、六朝、中唐的“论”体文中,“述经”是其根本,“叙理”存在于“述经”的基础上,只是二者的成分多少有所不同:述经多而叙理少的,与七十子的传记更密切;述经少而叙理多的就可称为“论”了。
以《荀子》为例:
东汉至六朝之“论”体文兴盛。六朝“论”之主流是以哲理探讨为主的理论性文体。
(原因:新莽的失败,对西汉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思想带来沉重的打击,由此经学内部的经义论辩开始兴盛。)
主要论述了佛教之“论”对“论”体文的影响P70
刘勰所言“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突出了专业性与精深性。P70
中唐的转型:“论”从侧重理性转向更为注重实用和修辞。
韩愈不著“论”之原因:①“论”成为科举文体,而韩愈认为科场文字是“俳优之辞”,无个性化面目;②更注重发明建树,正面阐述内涵,而非反思群言;③思想性格上,更强调身体力行的主体承当与实践,而“论”是具有强烈反思性格的体裁,与韩愈性质不相容。
柳宗元、刘禹锡之“论”:更注重在辨析成说的基础上提出对儒道的理解。体现出清晰的论述层次。
柳、刘之论与六朝之论的差别:①六朝重玄理辨析,柳刘重现实政治、伦理问题;②六朝之论,学理色彩浓,情感传达弱,柳刘相反,学理色彩削弱而情感传达增强,有了文气和情绪的表达。
3、理学文体:语录、札记
传统:
②宋人的“论”体文,承续的是中唐柳、刘的思路,也不再注重抽象玄理之思,而注重现实问题。如政论关注具体政治问题,史论多是以史为鉴,关注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经论也是多通过阐发经义来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
③宋人的解经体,如经解、讲义、经说等,多以简约为尚,在形式上与札记相近。
④宋代的理学思考,主要采用的文体是语录和札记体。
原因:宋代理学继承的是思孟学派的思路,而先秦思孟学派的文献形式或为“语录”,或为篇制精练短小的“集义”,类似札记。宋代理学带来思孟学派的复兴,而理学文体也青睐“语录”和“札记”的形式。
为何思孟青睐语录与札记?——“从思想的内在格局上看,思孟一派,高自树立,立足内在的道德主体,对儒家精神做深度的探求,其重心在于超越性的发明与感悟,以及心灵间的直接感染与启发,因此语录与札记的简约、直接,就很好地适应了表达主体体认,实现心灵启发的需要。” (原因阐释略单薄)
示意图表
4、近代的思想文体
(1) 严复译《天演论》,内容虽为西学,但在文字表达上,则是以子学“论著”为基准,表现:①由原来之科学著作,转变为一种“陈述教义”的姿态;②与《荀子》详实透彻的“述说”基调相同,严复的翻译将原作中推测假定、引而不发之处,都尽量言明。
(2)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
①康有为的政治文化思考,内容极具新意,但形式是古老的。至死未变。
②章太炎的著作,以《訄书》(后易名《检论》)为例,其目录编排经历了一个从中古子书到现代意识的转变,与近代学术著作有了更多的接近。
③梁启超戊戌变法前的著作形式还带有宋学(如政论等)的特点,戊戌变法流亡日本之后,其著述格局全面“近代化”,有了非常明显的现代学术自觉。
(3)近代学术体制与思想文体形式的转型
①学术论文自1920年代就已定型,至今未有明显改变。
②中国的学术论文受中古时期“论著”与“论”体文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
中古时期的“论著”与“论”体文,是“述圣”思想格局的产物,长于“述说”和“分辨”。而现在文科学科中,“史”的地位也非常突出。其实,“史”的研究,是以“整理”与“重述”为核心,与长于“述”、长于“辨析”的中古论著及论体文是十分接近的。
(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现代学术研究中,只有“述圣”的传统,而没有“拟圣”的传统?刘宁此书不妨看做是对“拟圣”[一空依傍]传统的一种尝试)
二. 载道文体的演进动因
1、两汉:经学文体与子学论著的关系
具体来说,子学论著与今文经学是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反相关关系。
①今文经学的“大章句”[9],在牵引诸说与引申阐释中,容纳了经师的经典思考与现实思考,多少包容了经师“自我树立”的愿望。“大章句”充分体现了今文经学关注现实的特点,“家法”的建立,也表达了经师自我树立的愿望。在今文经学大兴的西汉中后期,几乎难以看到士人创作专论子书的行为。因为今文经学实际起了某种替代作用。
②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被排抑,古文经学兴起。古文经学避免了今文章句的繁琐、抑制了过多的引申阐发,但也压缩了现实思考和主观阐发的空间,使经学注疏不能表达丰富的现实反思。而以现实思考为其擅长的专论子书,在这一形势下,也就弥补了经学的不足,而为士人所青睐。
因此,正是今文章句学与专论子书在东汉的此消彼长,才使经学传注和子学著述,形成明显的区分。
2、魏晋:注经与著论
魏晋玄学家之玄学文体形态,包括经典注释与“论”体文两种。
(1)经典注释方面,以王弼、郭象为代表。
①王、郭之经注由于不采“论辩”入注,因此能发明经义,直探玄理,绕开了辨析“名理”的枝蔓,而直接着眼于玄理的体察与解悟。
②淡化“别异”思路,更注重“会通”,既有经学(古文经学)的会通,也有玄理的会通(贯通体用)[10]。
③经注写作的独立性更强,与清谈的互动不如“论”体文那样密切,经注也在经典阐释中讨论玄学义理,但并不直接由清谈话题所促发。
④经典注释是与经典本身以及所有前代与当代的阐释者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超由现实讨论所激发的思考。
(2)“论”体文方面,以阮籍、嵇康为主要代表。
①“论”体文十分注重论辩,强调“辨析群言”。
②魏晋“论”体文,在辨析群言时,接续了韩非之文的“别异”,辨析更趋精微,论证更为开阔。
③“论”体文与清谈的关系十分密切,“论”体文的内容往往就是清谈反复讨论的话题,思理深刻的“论”体文也往往成为清谈的依据和取资。 但由于与清谈关系过于密切,“论”体文也往往受到清谈论域的制约,其所辨析的“群言”许多就是清谈中谈敌所提出的意见,当然,可以从容构思的论文,对论题的内涵,可以思考得更丰富,涉及更多层面,但这仍然难以和经典注释时所涉及的丰富内容相比。
总结:对于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王弼与郭象都致力于结合与贯通,而阮籍、嵇康所追求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则突出了两者的矛盾。追求统一的王、郭,创作了重要的经典注释之作,而突出矛盾的阮、嵇,倾力于“论”体之文,而在经典注释上殊少建树。这正透露出注经与著论,在思想表达上的显著差异。
3、近代:旧瓶新酒与新酒新瓶
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在对待新的文体形式的态度上还是有别的,康有为显然更为难以接受,章太炎对现代教育形式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在文体形式上也并非完全排斥,《訄书》到《检论》的发展透露出这一点,相比之下,梁启超对新的文体形式接受得更快,也更娴熟。究其原因,不外两个:
①时代演进:三人虽属同时代人,但在年龄上还是有差异的,康有为最年长(1858),章太炎其次(1869),梁启超最年轻(1873) ,在接受新事物的程度上很可能不同。
②个人文化语境的迥异,康、章身上的传统文化积淀比梁启超要更为厚重,也更为难以跨出。
在接受新事物上,形式表达方面是否比思想内容方面要更滞后?待考。
三. 启发
1、宏观印象:虽述有拟,一空依傍
通过对载道之文体的历时性考察与反思,得出了极具原创性(“拟圣”)的见解。十分难能可贵。
2、缺陷:宏观性,整体性极强。但总感到,论证不十分密实,大多是从目录学、分类学的角度来发现并总结问题,缺乏更为细节的论证。对当前的学术成果,不加怀疑地引用,有时是大段引用。 思维广度与深度令人叹服,但材料方面过度借用,有些讨巧。
3、文体学反思
文体与思想的关系
思想对文体有何影响?文体又对思想有何影响?
(1)整体性 “文体”是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外壳。
在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表达方式,但随着新的表达方式的形成,这一方式也就与思想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宋人对思孟学派的回归,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文体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思想与文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由于文体是思想的一部分,其本身也体现着思想内涵,因此,当用一种旧文体表达新思想时,就不再是旧文体与新思想之间的摩擦,而是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近代康有为、章太炎之文章就表现了这种冲突。在旧文体与新思想的摩擦中,随着隐藏在背后的两种新旧思想之争的平息,会逐渐找到一种适应新思想的心的文体形式,而与此同时,这种冲突之后的思想也不再是之前的新思想了,而是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被“旧文体”磨合过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文体虽然内在里有思想的影子,但其本身也仍然是文体的,有文体特有的力量,在与新思想磨合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了两种模式:一是文体形式之隐含思想与新思想的磨合;一是文体形式本身与新思想的磨合。前一种磨合产生一种更具适应性的思想;后一种磨合则产生一种更适合“改造后”思想的文体形式。
(2)动态性
正如上述论述,新的文体,是在与思想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形成之后会相对稳固,形成一个整体,但在遇到新的思想时,又开始新一轮的互动与成型。
(3)特征性
文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整体,尤其从写作或表达层面来看,它是一个具有丰富特征的整体。以刘宁所列举的“汉唐子书论著”这一文体为例,就包含诸种规定,如——主要是一种经验式的,以“述圣”为特色,关注政治、伦理等现实问题,不注重抽象玄远之思,融合百家,“成一家言”,结构松散的文章写作方式。这里的诸多限定词,其实正是这一特定文体的丰富特征。
注释:
[1] 解疑:“《荀子》之文,是‘师道’教化之文,其说理格局,通过‘七十子后学散文’的中介继承了《尚书》的君臣训诫以及《国语》的贤人教诲传统,侧重的是教化之道的直接传达。这样的说理格局,表达意见的‘述’,是行文之重心,而思辨之‘论’,则要从属于‘述’,在这样的‘述论’格局中,逻辑与思辨的发展,要受制于‘述’的基本精神。”P22 这里的“述”,应有“重述”的含义。
[2] P31
[3] 荀子在战国晚期,以礼法为核心,融会百家之说,注重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的思考;汉唐子学论著融会百家、关注“治术”、缺少玄远之思。P53
[4] P63
[5] “论”是不是“论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呢?前文所说的“集义”,也是体现在各单篇文章中,对论著的整体性结构有所忽视。对“论”的单独拿出,也是一例。
[6] 疑问:伦理问题与逻辑问题,有一致性吗?都是基础命题?都是抽象义理?
[7] P12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共同主题是阐述礼学,在后代被视为礼学的“传记”。 P13“七十子后学散文”作为“传记”,在内容上注重阐发礼义。
[8] 刘宁又专门总结:《荀子》四论的特点:第一,“论”的主题十分集中;第二,在辨析群言“方面更为突出,吸收了往复辩难的形式。
[9] 章句不是,或不仅是零星的词和字的解释,而是整段逐句的文义解释。P82 林庆彰区分了大章句和小章句,小章句就是就词解词,不作延伸;大章句则增加大量的引申阐述,并和政治结合,随势附会。
[10] P99 余敦康:“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结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頠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思潮的合题,……在更高的水平上把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