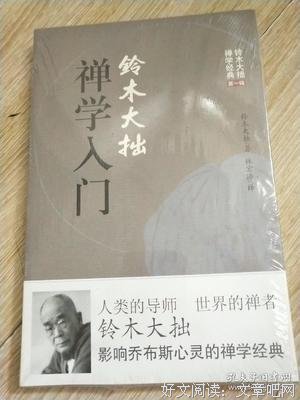铃木大拙禅学入门读后感摘抄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是一本由铃木大拙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精选点评:
●知见
●打破二元对立,达到生命的本真
●仔细想想,如果把中国的佛教分成净土、藏传、天台、华严和禅宗,我看的最多的,还是禅宗的书吧。破空,慈悲,然后,远离颠倒梦想。
●入不了门
●古文的禅宗公案看不大懂,也没个翻译,不知道这书有没有英文版,英文版中这些公案是怎么写的。
●看了一禅堂介绍部分,还不错。继续看。
●禅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还没摸着门框就跌了一跤
●顿悟后,就能见到二元论限制下无法见到的全新世界,你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 体力劳动是调节因久坐不起而心智昏沉的最好方法。人的身体和心,总不太能协调在一起。可人在体力劳作时候,为了让自己少出些力气,一定会去动脑筋,想方法把活儿快些做完,身心就有效结合在一起了
●没有开悟的人肯定不明白作者在讲什么,所以这书其实真不是入门级读物。个人体会,禅就是一种心法,使人看到世界的真相。禅的理念是要得到更高的肯定,而不是肯定与否定的逻辑对立命题。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读后感(一):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戒之警之
讀的是海南出版社2012年的版本。書不厚,加上榮格的一篇文章也才十五萬字左右。譯筆典雅、註釋精當。但是鈴木本人的文字總是給人感覺說的不透,缺少直擊人心的力量。倒是鈴木引用的語錄、公案中有不少經典的,極其精彩者亦不下十來條。本次讀到很覺衝擊和啟發的: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給書打分的話,3.5分吧。相當於百分制的七十分。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读后感(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禅”最早诞生在印度,后传入中国,结合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禅宗”,在唐朝时,又传入日本。禅宗最早在日本并不发达,直到宋代时,一位日本和尚两次来中国学禅,将禅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的临济宗带回日本。临济宗以单刀直入、使人顿悟为特色,恰好当时掌握日本国家实权的北条氏对禅宗热情信奉,甚至皈依了禅宗,于是禅宗越来越兴盛,逐渐融入并植根在日本文化和精神的方方面面中。
铃木大拙生逢其时,在西方产生了持续影响,西方许多重要的人物,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心理学家荣格,甚至是乔布斯,都受铃木大拙影响,西方重要的思潮运动,如嬉皮士运动都将铃木大拙的思想奉为经典。
禅,是一种神秘主义,它无法用逻辑去分析,坚持的是一个人的心自在无碍,禅是依赖于个人体验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的,禅倡导的是,当人们在打破二元对立的逻辑后,就能抵达世界和生命的本真,而那一切无法用言语去描绘,无法用固有的概念和逻辑去分析,只能用心去感受去印证。
了解了一些禅学的方法,比如公案,一种场景制造机,把人瞬间丢到两难的场景中,逼迫人走出超越逻辑,而抵达悟。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读后感(三):《禅修的意义》
这几天在看铃木大拙的禅的入门,静下心来,受益良多,以下是两条修禅的箴言,融入生活,予以铭记。
1.听从自己的内心。——解决偏离自己内心实需所带给自身的痛苦。
按照你内心所想去做,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之于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坏之分,只要是你认为是你该做的事情,就去做,现代人则容易忽视这一点,为了利益或者社会普世价值观总是舍去自己内心所追寻的东西,或者仅仅是因为安全感,我们总是在等待,认为牺牲一下自己,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们忘却了生活的本质,发现生活的实相,每一刻都活在真实的生活里,并遵循我们内心所想并能够所及的事情,才是生活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内心才能回归宁静。所以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让心回归平静。
2.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解决拖沓行事所带给自己的焦虑感。
拖延症是一种,时间管理的无能会让大多数人陷入焦虑,这是现代人的通病,我们总是选择在对的时间做错的事情,而另外一件则是我们总是忽略一些小事,按照铃木大拙的禅语来说,我们应该生活在此时,去感悟身边每一件小事,去遵循你内心的想法然后做好每一件小事,比如说关注眼前花叶的飘动,早晨起来刷牙,这一件件小事,都是禅,禅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活在眼下,去感受去行动就是修禅了,因此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避免拖沓后内心所带给自己的焦虑感,在遵循内心保持行动力的基础之上,让自身回到充实且平静的状态。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读后感(四):最好的禅学入门书籍,没有之一
书名:禅学入门
作者:铃木大拙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R=Reading 阅读时摘抄或拍照原文片段
公案数目的确无关紧要,信心和用功才是必要条件,无此则禅只是泡影。把禅当作思辨和抽象思考的人,永远也无法入道,只有发长远心才能够探测到它。只要能如如平等、谛观生生不息的宇宙万象,公案就完成其使命了。
如果开悟的时节到了,则触处皆真,习禅者到哪里都会开悟的。一个非语言的声音、一段难以理解的话、一朵盛开的花或是一段小插曲,例如跌一跤,都会是豁然开朗的契机。
当心灵准备好了,鸟飞、钟响,你会立即回到原来的家;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当下真正的自我。自始一切皆即洞然明白,纤尘无翳,只是你把眼睛遮起来,而看不到实相。因此,在禅里头不需要解释什么,也没什么可教的,那些只会徒增知见。除非是自己的省悟,否则都不是真正属于你的认识,而只是借来的羽翼。
禅自己也不想不合逻辑,它只是想让人们明白,逻辑的一致性并非究竟,而单纯的知见是无法得到某些超越性的语句的。当一切都上轨道时,是与非的知性窠臼(kē jiù)还蛮管用的,但是一旦临到终极的生命问题,知性就捉襟见肘了。
排斥和限制,他们毕竟是同一回事,都是在戕害灵魂。灵魂的生命不是应该完全自由且和谐的吗?在排斥和限制里,是不会有自由或和谐的。禅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基于我们内在生命的需求,禅带领我们到一个没有任何对立的绝对领域。
在逻辑里处处有斧凿的痕迹,逻辑是有自我意识的。生活是一种艺术,就像完美的艺术一样,它必须是忘我的;其中不能有任何斧凿痕迹。禅认为生命应该如“空中飞鸟,不知空是家乡。水里游鱼,忘却水为性命”。只要有一点人为造作味道,一个人就被命定了,他就再也不是自由的存在者。禅意欲保存你的生命力,你本有的自由,尤其是你存在的完整性。换言之,禅要从内在去生活。不要被规则限制住,而是要创造自己的规则,那就是禅要我们过的生活。
挣脱名相和逻辑的暴力,同时也就是灵性的解放,因为灵魂不再对自己起分别心。
从前我们始终看到万物的对立面和差别面,在态度上和它们多少有点对立。但是现在它被推翻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世界的内在。于是,“铁树开花”“雨打不湿”。由此,灵魂得以整全、完美且充满幸福。
我们一般认为“A是A”是绝对的,而“A是非A”或“A是B”这样的命题是绝不可能的。我们从未突破这些理解的条件限制。但是现在禅宣称,语词只是语词而已。当语词不再与事实对应时,我们就应该抛开语词,回到事实去。不落名相更能开显诸法实相。
知性、想象和其他心识作用,以及我们周遭的事物,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要用来开展并增长我们自身拥有的最高贵的能力,而不只是满足个人的冲动和欲望。
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阴德”。但是当他继续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佛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深沉差异。无论心里想着任何人,管它是上帝或魔鬼,知道我们的行为而且会报答我们,这时候禅就会说“汝非我辈,不与我同类”。由这种念头产生的行为,会留下“踪迹”和“影子”。如果有鬼神追踪你的行为,他随时会抓住你,要你解释它,禅则不会如此,犹如天衣,里外皆无缝,那是完美的作品,没有人知道哪里是线头。
如是,毕竟净也就是绝对的肯定,因为它超越了净与不净,且在更高的综合形式当中统一了它们。其中没有否定,也没有任何矛盾。禅的目标就是在行住坐卧中去体会这种统一的形式。
禅是什么?禅不是什么。
在着手详细阐释禅学以前,让我先回答批评者经常提出几个关于禅的本质的问题。
禅像大部分的佛教教法一样,是一种高度知性和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吗?
我曾说我们在禅里头看到所有东方哲学的具体化,然而那并不意味着禅是一般意义下的哲学。禅绝对不是一个以逻辑和分析为基础的体系。它甚至是逻辑的对立面,我所谓的逻辑是指二元论的思考模式。禅里头或许有个知性元素,因为禅是整体的心灵,在里头可以看到森罗万象;但是心灵并不是一个可以分割为许多机能而解剖以后一无所剩的组合物。禅并不以知性分析对我们开示任何东西;它也没有任何规定弟子们要接受的教义。
就此而论,你也可以说禅并无定法。习禅者或许有些禅法,但那是基于自身的考虑,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他们不认为那是因为禅的缘故。因此,在禅里头并没有什么圣典或经教,也没有任何可以直指禅的根本意义的咒语。如果有人问我说禅有什么教法,我会说禅并无任何教法。即使禅有什么教法,也是出自自家心里。我们以自己为师,禅只是指路而已。除非指路本身就是教法,否则禅并不刻意规定什么东西作为其教旨或基本哲学。
禅宣称是佛教,但是经论里提出的一切教法都被禅视为只是浪费纸张,其作用也只在于拂去知识的尘埃,如此而已。但是我们不应就此以为禅是虚无主义。所有虚无主义都是自我破坏的,不知乡关何处。否定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并无不妥,但是最高的真理是一种肯定。当我们说禅没有哲学,说它呵佛骂祖,否认所有教法权威,将一切经论弃若敝屣,我们不要忘记,禅就在否定的同时举示了某种相当正面且永恒肯定的东西。我们在后面会阐明这点。
禅是一种宗教吗?它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宗教;因为禅并不敬拜神,也没有什么仪轨;亡者也没有什么归宿。更重要的是,禅不需要他者去照顾灵魂的幸福,也不很在乎灵魂不灭的问题。禅没有任何信理或“宗教”的累赘。
当我说禅里头没有神,虔信的读者或许会很吃惊,但这并不意味着禅否定神的存在;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禅所关心的。当一个东西被否定时,否定本身就蕴含着某个没有被否定的东西。肯定亦复如是。这在逻辑里是难免的事。禅想要超越逻辑,禅想要寻求一个没有反命题的更高的肯定。因此在禅里头既不否认也不坚持神的存在;只是在禅里面没有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所理解的那种神。禅既不是一种哲学,同理,禅也不是一种宗教。
禅是一个人的精神,禅相信人的清净自性和善
至于在禅寺里可以看到的佛、菩萨和天人诸众的雕像,他们只是木头、石头或金属而已;和我家花园里的山茶花、杜鹃花或石灯没什么两样。禅会说,那么干脆就膜拜盛开的山茶花好了。相较于顶礼诸佛菩萨、洒圣水或领圣餐,膜拜山茶花一样也很有宗教意义。
大部分有所谓宗教信仰的人认为有福报或神圣的敬拜行为,在禅的眼里都只是人为造作而已。它甚至大胆地说:“持戒比丘不升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狱。”对于凡夫而言,此番话无异于否认了道德生活的习惯法则,但是其中却蕴藏着禅的真理和生命。禅是一个人的精神。禅相信人的清净自性和善。任何增减损益都会断丧精神的完整性。因此,禅特别反对一切宗教习俗。
然而它的反宗教只是个表象而已。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赫然发现,在禅的粗野宣言里竟然也有如此深刻的宗教蕴义。但是说禅是如基督教一般的宗教,那也是一个误解。我举一个故事解释一下。传说释迦牟尼佛初生下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创立云门宗的云门文偃禅师却说:“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
一般人看到如此狂妄的评语,会对禅师作何感想呢?但是其后的禅师却赞叹云门是“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即名为报佛恩”。
禅要一个人的心自在无碍
禅不能和印度的遁世者或某些佛教徒的默观形式混为一谈。禅认为“禅那”并不等于禅修。一个人或许会在禅的训练里沉思一个哲学或宗教的主题,但那只是附带的事。禅是要觉照心灵的真正本性,据以训练心灵本身,做自心的主人。直指自心或即灵魂的实相,是禅宗的基本目标。因此,禅不只是一般所谓的默观或禅那。禅的训练在于开启心眼,以澈照存在的理由。
空中鸟默观什么?水中鱼默观什么?它们只是飞翔,只是优游。这还不够吗?
我们可以说基督宗教是一神论,吠陀宗教是泛神论,但是我们无法以类似的主张去谈论禅。禅既不是一神论也不是泛神论,禅并不适用这些名称。在禅里面并没有什么执持的对象。禅是虚空中飘荡的云。没有螺丝锁住它,也没有绳索系住它;它任运自在。任何默观都无法将禅系于一处。默观不是禅。无论是泛神论或是一神论,都不是禅所专注的主题。如果禅是一神论,它会要弟子们默观那以遍照世界的圣光泯除一切差别分殊的万物一体性。如果禅是泛神论,它会告诉我们说,即使是田野里最平凡的花朵,也映现着神的荣光。但是禅会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禅要一个人的心自在无碍,即使是一或全体的概念,也都是绊脚石和葛藤,只会戕害精神本来的自由。
因此,禅不会要我们去沉思狗子是不是神,或者三斤麻有无神性。如果禅这么做,那么它就落入某个哲学体系,也就再也不是禅了。禅只是去感觉火的温暖,冰的冷冽。因为天寒时我们会冷得发抖而去烤火。正如《浮士德》所说的,“感觉便是一切”。但是此处所指的“感觉”必须就其最深层且纯粹的形式去理解它。即使只是说“就是这个感觉”,也意味着禅已经不在了。禅是无法概念化的。此即为什么禅难以捉摸。
如果说禅主张任何默观,那也会是如实观照雪的白,乌鸦的黑。
禅有时候被认为是“杀心逐妄”。《日本的宗教》的著名作者格里菲斯如是说。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杀心”究竟指的是什么,他是说禅以心一境性或入眠去“杀死”诸心行吗?
看到对于禅无批判能力的评论者如此的浅薄鄙陋,让我着实惊讶。其实,禅并无“心”可杀,因此在禅里头也就没有什么“杀心”可言。禅也没有我们可以归依的“自我”,因此禅也没有我们可以陶醉的“自我”。
禅的外在面向捉摸不定
其实,禅的外在面向是极为捉摸不定的;当你认为窥见它时,它早已鸟飞无迹;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因此,除非以数年时间穷究其基本原理,否则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禅是无底深渊。禅会以另一种方式说:“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璇玑不动,寂尔无言。觌面相呈,更无余事。珍重。”须臾犹豫,禅便一去不返。三世诸佛都要你再一次拟举,却已经是“三千里外”。“杀心”、“自我陶醉”,诚然!禅没时间去和这些评论瞎搅和。
评论者或许会说,禅把心智催眠成无意识状态,好去体悟佛教所谓的“空”,主体在其中无法意识到客观世界或自我,落入广袤的空里头。这个诠释同样误解了禅。的确,禅的某些语词或许暗示着这样解释,但是如果要了解,我们必须做个跳跃。我们必须横越那个“广袤的空”。如果主体不想被活埋的话,它必须从一个意识状态里醒来。唯有抛弃“自我陶醉”,而且“醉汉”也要真正醒觉到他的深层自我,才可能体悟到禅。
如果有所谓“杀”心,那就交给禅吧,因为禅会让被杀者和无生命者重获永生。禅会说:“重生吧,从梦里醒来吧,从死里复活吧,你这醉汉。”因此,不要蒙着眼去看禅,你的手抖得太厉害了,也无法抓得着禅,而且不要忘记,我不是喜欢耍嘴皮的人。
这类批评不胜枚举,我希望以上举隅足以让读者接受对于禅的正面描述。禅的基本理念是要探索我们存在的内在结构,而且是尽可能以直接的方式而不假外求。因此,禅呵斥一切类似外在权威的东西。绝对的信仰只在一个人的内在存在里。如果禅里头有任何权威,那也是来自内心。这是在最严格意义下的真理。
即使是论理能力,也不被认为是究竟或绝对的。相反,它会障碍心和自身最直接的沟通。知性的任务只是一个媒介,而禅则无关乎媒介,除非它想要和他人沟通。因此,一切经教都只是方便假设,其中并无任何究竟。禅要如实把握生命的核心事实,而且是以最直接且生动的方式。禅自称是佛教的精神所在,其实它也是一切哲学和宗教的精神。当人们完全体会到禅,他就会得到心的绝对平安,也可以正其性命。除此之外,我们夫复何求?
或谓,既然禅的确是一种神秘主义,那么它在宗教史里就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或许是吧,但是禅是自成一格的神秘主义。它所谓的神秘主义,无非日照花开,或是我现在听到有人在街上打鼓的声音。如果这些都是神秘主义的东西,那么禅有一箩筐。有人问禅师什么是禅,他回答说:“平常心。”这不是很平凡直接吗?它和什么教派精神一点关系也没有。
基督徒和佛教徒都可以习禅,正如大鱼小鱼都可以在海里悠游。禅是海洋,禅是空气,禅是山,禅是雷鸣闪电,是春天的花,是夏天的暑热,是冬天的雪,不,不只如此,禅更是人。尽管禅宗史里积累了许多形式、习惯和附会,但是它的核心事实却始终生机盎然。此即禅的殊胜之处: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观照究竟实相。
如前所述,禅在佛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系统的修心法门。一般的神秘主义总是过于奇诡谲怪而脱离常轨,禅则对此有着重大的革命。禅把那高亢入云的东西拉回到地上来。随着禅的开展,神秘主义也就不再神秘莫测;它不再是精神异常者的突发性症状。因为禅就开显于市井小民最平凡无奇的生活当中,在行住坐卧当中体会生命的实相。禅以有系统的修心去观照它;禅打开人的心眼而得见那周行不息的伟大奥秘;它打开人的心量,在一弹指间领受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它让俗世生活犹如在伊甸园里漫步一般;而一切灵性的造就皆不假任何教义,而是直指那蕴藏在我们自性里的真理。
无论禅是什么,它总是实证的、平凡的,同时又是最有生命力的。古代有一位禅师,在说明禅是什么的时候竖起一指,有一位禅师则是踢球示之,更有一禅师掌掴问道者。如果那深藏于我们自性的内在真理如是开示,那么禅岂不是一切宗教当中最实证且直接的灵修方法吗?这个实修方法不也是最原创的吗?的确,禅总是原创性的,因为它不和概念打交道,而只关心生活的实相。若从概念去理解,那么竖一指也只是日常生活里的一件琐事;但是在禅的眼里,它却回荡着神性的意义和创造性的生命力。只要禅能在我们陈腐而拘于概念的生活里指出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有其存在的理由。
I=Interpretation 用自己的语言重述知识
译者谢思炜乃北京师范大学的知名学者,此君的专长是唐代诗歌,尤其在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身上著述甚丰。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了这部作品,虽然仅薄薄一部,但真趣闪烁,就像书中所言:房顶之上,繁星满天。
铃木大拙试图想从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入手,从知见和二元对立的逻辑世界中跳出来,直接到达心与自然相统一的内在体验的真境界。对那些执着于世的人而言,这一点不啻于当头棒喝,我读过许多人述说了这本书对于他们艺术创作的影响,至今记忆犹深。而铃木大拙能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上来谈禅学,更值得佩服。他说到了中国的禅,也提到了印度。唯一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说到中国的儒家对禅的影响。
书中云:何是净心!
禅师答:以毕竟净为净。
僧问:何是毕竟净为净?
答:无净,无无净,即是毕竟净。
问:何是无净无无净?
答:一切处无心,是净,得净之时,不得做净想,即名无净也。得无净时,亦不得作无净想,即是无无净也。
--------------------------------------------------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
德山为受教就来到龙潭处,一日,他侍立座下,龙潭问:“更深何不下去!”德山便往外走,却又回来说:“外面黑。”龙潭点蜡烛递给德山,德山刚想接过来,龙潭又把它吹灭了,德山于此大悟。
--------------------------------------------------
禅在生活当中,你离它近了,它却远离了你;你远远的看不到它,它却在你身边。乌鸦是黑的,A是A。
在文中,作者强调的是经验,以这种经验作为禅学入门的途径和基础。作者笔下的禅是非概念化的,即,即使有概念能够表述,但若无个人经验,是难以有效地被掌握的。
其次,禅是非逻辑化的,超越了知的范围的逻辑二元主义的界限,心中不再有“彼”“此”的区别。
再次,唯一能够取得个人经验和进行入门的途径则是借助作者所言的“公案”。这是禅学师傅通过某些言语、动作组合而成的作为启示弟子顿悟的方法和手段。如作者言,公案非谜语,也非机制的语言。具有明确的目的,唤起概念,并尽量把它推向极端。从而顺遂思想的自然流向。在面对壁垒之时,冲破它,从而达到洞察物的真相的内在意识的觉醒。
这几天在看铃木大拙的禅的入门,静下心来,受益良多,以下是两条修禅的箴言,融入生活,予以铭记。
1.听从自己的内心。——解决偏离自己内心实需所带给自身的痛苦。
按照你内心所想去做,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之于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坏之分,只要是你认为是你该做的事情,就去做,现代人则容易忽视这一点,为了利益或者社会普世价值观总是舍去自己内心所追寻的东西,或者仅仅是因为安全感,我们总是在等待,认为牺牲一下自己,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们忘却了生活的本质,发现生活的实相,每一刻都活在真实的生活里,并遵循我们内心所想并能够所及的事情,才是生活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内心才能回归宁静。所以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让心回归平静。
2.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解决拖沓行事所带给自己的焦虑感。
拖延症是一种,时间管理的无能会让大多数人陷入焦虑,这是现代人的通病,我们总是选择在对的时间做错的事情,而另外一件则是我们总是忽略一些小事,按照铃木大拙的禅语来说,我们应该生活在此时,去感悟身边每一件小事,去遵循你内心的想法然后做好每一件小事,比如说关注眼前花叶的飘动,早晨起来刷牙,这一件件小事,都是禅,禅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活在眼下,去感受去行动就是修禅了,因此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避免拖沓后内心所带给自己的焦虑感,在遵循内心保持行动力的基础之上,让自身回到充实且平静的状态。
A1=Appropriation 描述自己的相关经验
关于禅与道
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禅而非道;而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是道而非禅。
行到水穷处”大概就是指的这种人的思维被逼迫到绝境的境界,而"坐看云起时"则是开悟后的境界。而道家的深意,是天人合一,力图放开心胸达到一种相互包容或融合的境界。
禅的追求是开悟,开发智慧,最后进入另世界的境界,是反对世间的法。
道家立足现世、超越现世也是为了开发智慧,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生,是世间法。
应该说,禅走得更远一些。不过,它们都要求彻底认识人生,这个愿望是共同的。
武汉大学的一个哲学博导认为禅与道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 即看破虚象达成入圣之境。但是在各自的探索中却有着极大的区别, 如禅之开悟和道之入世。
皆言“禅”与“道”不可说。妙不可言,不可思议。那么,越是如此神秘,就越使人好奇啊。
老子的道德经,效天地之道以为人之德,短短“五千文”,费古今多少思量。道法自然,不言美善而至真;事处无为,孕生万物而不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胸怀真犹如母亲啊。从无生有,静中存动。那么,致虚、守静,以生妙有、容万物。天地之间因中空而动静相生,万物皆活。中空可容物。做人亦当虚怀若谷,有容乃大。用道,犹如水之入渊,冲而不盈,来不拒,去不留,留存无碍而不住。那么做人应淡泊明志,宠辱不惊,不患得失。上善若水,甘居下游,且能纳浊。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人效此道,于尘嚣中沉潜静定,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天地不能久。人应学会不希求永恒,不好高骛远。大智若愚,在拙朴的平凡里包孕着怎样的智慧玄思。处世犹豫,在不露的深藏里其实已洞穿了先机。
观天地之道,是那样自然而然,笃定超然。与释家的禅,其实哪里有丝毫相悖呢?禅之定、净,与道之安、静,可谓异曲同工。释家佛,因为中国的道,而生出了空灵的禅之意境。禅,只有与中国的道相结合才真正生出无限意趣。无相、无住、无念,三位一体。我,受着人世时间空间寿命的限制,一颗活心,犹如泉源,汩汩生念;而以我有限之尘心所生尘念,为生死为病痛为爱欲故生忧喜生惊怖。倘若冲破我的有限,冲破爱的无常,使我的一颗心不与尘埃相染,我有何忧,我有何怖?
禅意,亦从天地可得。一粒沙、一朵花,一枚月、一片石,皆有禅意。人之心,若与天地之心相慰藉,生生念念,何曾有挂碍呢。我,不过活在呼吸之间,前不悔,后无嗔。生生世世之我,如月、如石,以禅心入世,自摈弃无谓的烦恼而生万千般若。
道家云“静”,听觉的透明。佛家云“净”,视觉的透明。其实都是欲表述知觉的透明啊。表述一颗慧心,用心体会“净”“静”,内外空明,与己不相染,皆得自在。道家说“无为”。其实是,以虚空容生生不息之妙有,正是效天地无为而无所不为之道。哪里是真的无为呢? 佛家说“空”。但是,大乘中乘小乘浩浩之佛典,却是海一样的大慈悲。菩萨,生生世世甘为尘世牺牲,又怎么能真的是空呢?而禅和道,在中国的文人手里,又演绎成了千变万化的审美意趣。
我看《菜根谭》即是看道骨禅心。《菜根谭》正是禅道境界(当然也不乏儒家之儒风、墨家之侠气)。
“操存涵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的景象;风狂雨骤处,有波恬浪静的风光,才见处一化齐之妙。”动中沉潜静定,静里自有乾坤,何等的气象!自是道家仙骨。
“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地网天罗。”正一点禅心,兼取自然之道。
“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你自拈花,我自微笑。会心处何必多言。但解禅心道意,便不难了解古人为何有这般意趣啊。
袁宏道的《叙陈正甫会心集》,关于意趣,也写得极好。“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确实,除了《菜根谭》,古人深得意趣之诗、画极多。禅与道,正是美之凭据。古云“会心不在远”,说得极是。
梁武帝时候有善慧和尚,一日,善慧道帽僧衣儒鞋见武帝,武帝问:你是和尚么?善慧一指帽子。又问:你是道士么?善慧一指鞋子。再问:你是方内之人咯?善慧一指衣服。武帝乃问:你究竟是什么?善慧唱道:道冠儒履佛袈裟,会成三家作一家。这就是禅的境界,没有何种何家的区别,融合杂糅儒道佛,成为禅宗。
善慧有诗: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在水中流。意为,万事不要拘泥於成见,多多换些角度观察。
纪晓岚说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结果流传到现在变成“支离破碎,怪诞杂乱”,悲催啊悲催。
道家虽然有一段时间误入了炼丹的歧途,但是天地气息,关于人生气脉方面的一些理论我觉得还是颇有意思,也是蛮值得关注的,譬如说,他们认为人的气机,在一呼一吸之间,脉自运行六寸(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个人在一天一夜之间,共计有一万三千五百次呼吸,叫做一息,气脉运行经过五十度而周遍一身,用汉代的时计标准,是铜壶滴漏,经过一百刻的时间。提出人的十二经脉包括心、肝、脾、胃、肾、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胞络,刚好和天干地支对应起来。把养生、医药、生理学说结合到一起。真的很牛叉。
常常听说打通任督二脉,任督二脉是什么。督脉,是脊髓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任脉,是自律神经系统。好多东西都打医学理论和思想的萌芽。很是博大精深。
A2=Appropriation 以后我怎么应用
公案数目的确无关紧要,信心和用功才是必要条件,无此则禅只是泡影。读书也是如此,一味的一本又一本读书,不细细咀嚼,只是为了满足内心的不安,但内心依然是不安,拘泥于数量而非内心本身,并不能解决内心的问题,数量依旧是外在的表象,并未触及内心的本质。听从自己的内心。——解决偏离自己内心实需所带给自身的痛苦。
因此,在禅里头不需要解释什么,也没什么可教的,那些只会徒增知见。除非是自己的省悟,否则都不是真正属于你的认识,而只是借来的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