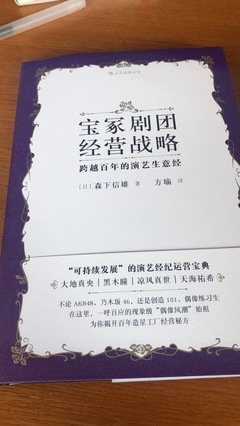我带你去那儿读后感摘抄
《我带你去那儿》是一本由乔伊斯·欧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页数:2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带你去那儿》精选点评:
●比较畸形的情感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欧茨虽然有很好的地方,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太话唠了。。。
●怎么她的作品读起来都很扭捏
●其实……这本写得很流行小说
●大片的自我独白,也就是发现自己吧,结局总归是好的,但总有些自我放逐的感觉
●畸形的情感。挺好看的。
●内向直觉
●个人历史与整个社会发展史的相互渗透,变态的人讲不出正常的故事....哲学不像是摆脱痛苦的良方
●当你穿过并不存在的房间走进屋子时,我看见的是你,而不是我自己
●小熊买给我的第一本书
《我带你去那儿》读后感(一):重生
" 一个内向直觉型女大学生的精神探索过程,"这句介绍很吸引人.看过觉得确实如实所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什么决定性格呢?据我的经验,童年生活对人来说很重要的阶段,父母的性格和关爱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书中女主人公,没有父母,在无人关心的氛围中艰辛成长.于是性格内向,孤僻.长大后寻求亲情把陌生人假想成自己的亲人,想从对方那里摄取关爱,但周围得人都是一群没有思想的利己主义者,而真正的同伴又在寻找自我,追求自由.
有时觉得不可置信,为什么正常的人都能活的那么心安理得,为什么能不更多的顾计别人.有人战战兢兢想得到一点关心,但别人只能关心自己.还好,作者给主人公一个光明的结局,父亲的遗产,可能是多年的愧疚,也可能是爱,,,至少得到了一丝回报.
看过这本和 中年 和 妈妈走了,可能因为是一个时期的作品,主题上也不尽相同,都是主人公出走最后获得新生,所以每次看完自己也对生活充满希望!但是不是真正如书里写的那样光明,还只是作者的希望,不过至少知道也有人和有你一样的希望!~
《我带你去那儿》读后感(二):我带你去那儿
《我带你去那儿》(I'll Take You There),第二次读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小说。很早很早曾经读过她的另一部作品,《他们》(Them),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情节,女人因为生活潦倒,去街头卖笑,没想到第一次就遇见了便衣警察而被捕。那时有种很奇怪的难受,小小的心脏不堪重负,只知道世界上有彩色和黑白两种颜色。警察捉小偷天经地义,可是人家又是生活所迫,所以难受得很无端。现在才知道,无常的命运唤起了心底下近乎本能的同情。命运,或曰生活之路本来就是这样,无常,无法规划,只有小心翼翼才能降低这根芦苇被折断的几率,但这种危险却从来不会消失。
那时语文读本里有另外一个故事,萨特的短篇,被捕的抵抗者为了掩护战友,对敌人扯谎。没想到谎言成真,战友阴错阳差地跑了谎言当中的那个隐蔽所。由善意到摧毁,命运的巧合就这样令人嗟伤。
《我带你去那儿》里面的主人公是个模糊得几乎不存在的女大学生。在她脑海中流动的记忆已经残破不堪,根本无法连缀得像个样子。她的身世像个谜团,好像呵气玻璃外面的世界;可以确定的,只有那个世界当中爱的缺失。最为重要的,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掌握。随便那个名字都可以用在她的身上,或者你的,或者我的。她仿佛并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自己的意识当中。
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名字的人,被强行卷入生活当中。她被拉进姐妹会,被逐出华丽的宿舍,与哲学研究生恋爱,又无望的结束……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因为她没有任何主动的努力,没有自我。她能做的只是努力维持自己惨淡单调的真实生活,而心不在焉地依附在五颜六色的生活上面。当她做出选择,要改变自己,即将寻找到自我的时候,收获的却是挫折。又是命运!如此蹊跷,又如此真实。
作者带来了充盈着哲学式迷离与美丽的意识流,在静默与深沉中感染正在生活着的读者。当无名的“阿尼利亚”见到垂死的父亲,一场奇遇,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在慢慢的回忆中,她追溯往昔,才找到了自我。一场奇遇,是回归自我的钥匙,就是这样。
欧茨是极多产的作家,现在在美国文坛地位颇高,也有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她的作品类型广泛,充满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准确。对心灵的捕捉和优美的文字都是她作品的出众之处。她曾写过梦露的传记(《浮生如梦》,已经有中文译本),印象里看到被我们很有名的一位翻译家,老先生,形容成猎奇还是什么的,总之愤愤不平。
《我带你去那儿》读后感(三):沉舟侧畔,不见千帆已过
阿尼利亚,“令人困惑的虚幻”。
当一个女人活在内向型空间里时,她是会这样的。思绪粘稠有如被冻过的蜂蜜,以至于找不到任何一个用于排解的出口。纵使找到了,她也会踌躇不前,只兴高采烈地取回一些碎片,修补自己不断破裂又不断重生的内心世界,仿佛普罗米修斯的心脏。
阿尼利亚——权且这样称呼她吧——并非外表那般特立独行。她比一般人更恐惧独行的苦楚,因为那样就没有人可以证明她的存在。所以,一开始她会卑微地跪倒在爱的面前(像许多绝望的女性一样),期待个体对个体的接纳。敬畏之心令她忘记了由此带来的疼痛,当一而再再而三的屈辱和妥协将她推至深渊边缘,她只用伪装起来的快感安抚灵魂里清醒的那部分抵抗。阿尼利亚始终无法正视她对沃诺·马休斯那种紧张的爱恋。她小心翼翼,用敏感的神经试探着马休斯对她的回应。我怀疑,现在还有多少女人将身体的付出当作一种付出,而阿尼利亚不是。但她早已忽略了自己的权利,只绝望地双手奉上她最后的资本。在男人眼里,性是令一切女人平等的条件。于是,一个聪明的姑娘以性感却胆战心惊的形象出现在她的情人面前。她苍白扁平的胸部下面,心脏几乎停跳。做爱让她在被亵渎的同时得到了忧伤的感动——他们终于以某种方式在一起了。
读到阿尼利亚对马休斯说:“我一个人的爱对我们俩而言足够了。”我的悲伤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疯狂而仓惶地四下逃窜。
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阿尼利亚“见到”了消失许久的父亲。年少时对于亲情的强烈饥渴如幽灵般与她的成长形影相吊。在母亲的早逝、父亲的不辞而别、哥哥的冷漠、祖父母的疏离中,阿尼利亚模糊地成长起来。家庭痕迹淡得如同一幅写意画,却戏剧性地留下了几笔浓墨重彩,比如阿尼利亚的高中毕业典礼上,父亲的拥抱和那句“别让那些混蛋看扁了你”。所以,当阿尼利亚在四年后独自穿越了大半个美国来面对奄奄一息的父亲时,她的人生仿佛一段圆弧终于被接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她在那里陪伴着“死亡”,感受到西部足以吞没一切的荒凉与无限。过往的种种穿越时空,排列出另一种生命的景象。当阿尼利亚透过父亲的眼睛再次凝视这副景象时,就像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净化,如她自己所说“我就自由了”。
最令我意外的是作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结尾方式。“我带你去那儿”可以是一句承诺也可以是一种指引,将故事说回从头,想起那个女孩最初的模样。
《我带你去那儿》读后感(四):【读品•仿事套环】罗小亦:你要带我去哪里——关于一本书的小说
欧茨的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狂燥沸乱,写尽爱欲生死的人生热病。但我能体会到其后的静默,因为take这个词本身就带着祈求救赎与指引的绝望。就故事本身而言,它通俗到没有任何难以解读的部分,尽管每个章节前的导语很明显表达了作者想要挂靠某种文化现存的意图。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种拙劣的拔苗助长,因为通俗小说根本无须顾虑它所传达的文化语境,会缺乏读者们可资理解的共同视阈。直到我试着模仿她来写一个近似主题的故事,才明白之前是如何庸俗地简化了作品的厚度。
写一个仿事体书评并不容易,断断续续涂涂改改,写到中段的时候网络出了故障,空白的屏幕宣布这一天存在的遗失,连时间的灰烬都没有剩下。我告诉自己这只是笔墨游戏,但还是觉得万分沮丧。我对打捞小说的本义不抱希望,只是想体验一下作者曾经历过怎样的哀伤。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小说《I’ll Take You There》,印象最深刻的那段是阿尼利亚站在污浊的地板上唱黑人歌曲,百叶窗的光打在苍白的身体上,沃诺拉起她,眼中的神色“几乎”是温柔的。他要她唱下流的黑人小调,他引用尼采的话并有所发挥,对任何事物的爱都是野蛮人的行为,欲望更加可耻。然而,比欲望还要可耻的是习惯于欲望,嗜欲成性——究竟我们的肉体臣服于什么?
2006年3月1日下午14点,我去北京万泉庄看阔别多年的老情人杜晓。等他的时候买了这本书,然后坐在图书大楼的台阶上看。翻到第二章的时候,短信和斯宾诺莎一起蹦出来。老斯说人的头脑中没有绝对或自由的意志,短信说我到了,你在哪里?我站起身来四下张望,低血压使我眼前一阵发黑。几秒钟后看见杜晓从一辆大卡车后闪身出来,脖颈缩在立起的领子里,衣着单薄脸煞白。我平时喜欢穿黑衣,方便下小馆子扒火车藏污纳垢,这天却圣洁地纯白着,白得亮晃晃,白得有点二。帽子上还有一圈毛,像高原上的雪羽。我指的是山巅上的积雪被朔风吹落时出现的那种,状似火山爆发的东西。杜晓摸了摸帽子说,很好看吖。我以为他会顺手怀念一下四年前一起去西藏旅行的事,却没有提。看来当年在山上摔的那一跤实在太惨痛,以至于连其余的记忆都消受不起,维系不住。
跟着杜晓穿过街,两下三拐就进了一栋楼,根本没看清楼门在哪里已经上了三层。楼道逼仄日光不肥,各处是杂物,落脚之处扬尘高过人,张牙舞爪扑上来。他回头看着我衣服一笑,我气闷,干脆脱下来挽在臂上。里面是低领黑毛衣,低到肩胛骨都露出了一半。身后的杜晓伸手握住我的脖子:你不冷吗?我昂首凛然答:你要掐死我?他笑起来,用手肘圈住我,一直拖进屋里。这亲密而熟悉的情状让我们回到了以前,青春真是央视黄金时段,普通的事件只要在那时发生就身价百倍,记忆几经选择,还是丢不掉。
杜晓穿薄汗衫的样子很奇怪,服贴而瘦削的整体简直有一种羸弱的病态,他的躯干并不如我长,但是肌腱鼓起。力让我想起死亡的恐惧,我们谁都不是强者,在昏黄的灯光下说起邱妙津和朱天心,对这个世界水蛭般的情欲让她们写出了尖锐的女性文本,对于生命完全可以自足的个体,向内封闭根本就是种常态,谁都不敢恃宠而娇。这些是我们年轻时常讨论的话题,现在呢,不卖脑髓了,贫贱的精神劳作者肉食者鄙。我清楚自己是个志大才疏没天赋的蠢东西,你清不清楚?我用挑衅的眼神看他。他张了张嘴,然后习惯性地抿紧。
关了灯,写字台上的电脑正好装完自动更新程序,轻轻喀哧一声,光线都寂灭了。我们在暗中拥抱并叹息。隔绝,窒息,互不相通,残光中我见他看着床头的现象学通论发呆,大概是在愁论文。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离我已经很远,现在除了三餐饭食四季衣裳很少为别的问题操心。我忽然意识到之所以要维护这种虚幻的自大,实际是在维护一种生计,面对他我还是一如往昔地心虚。之前的二十多年都浪费掉了,该因为年幼时的荒疏怠学后悔么?既无法安慰又如何慰藉。杜晓抽烟,我紧紧抱着他不松手。如果张牙舞爪一番,被他骂做无知也就罢了,但我深知他只会沉默着抵抗或客套地附和,视心情好坏而定。时间左顾右盼还是过去,劈头盖脑的绝望砸中了我。现在这样的对峙究竟是为什么。
感到口渴,终于记起自己还活着。地上有桶装的农夫山泉,于是倒了在玻璃杯里一饮而尽。那冰水却像活物,死而不僵的蛇,让我在床上翻滚了半日。问杜晓为什么不烧热水,含糊答了一句,也没听清。我告诉去年冬天一直在喝冰水,因为寝室里饮水机坏掉了,加温器不会自动跳停。烧水的时候得趴在水桶上听机子里的声音,咕咙叫了就是烧好了。后来我嫌那巨响太像深海里的声音,受不了这份虚拟的寂寞,就不喝热水了。
你从生满毒藻的海底逆着某种流向涉水而来,以光速介质的覆盖了我,请带我去那儿……这是一首歌词,配上Christopher Schmid应该不错,毁灭一切的绝望到了他的声音里就淡化成了永恒的失落,一种从内心噬咬你的身体的虚无。杜晓给我听他新写的歌,gothic doom,以死腔为主音,背后附和着高亢辽源的女声唱挽,钢琴与提琴的齐奏让悲哀更加直接地撞击心灵。我说:如果你要毁灭我那么就来吧,知耻近勇,我是活得太卑劣违心没质量了。此言一出,杜晓吓得赶紧关掉音响开始告解:许迭迭我对不起你,当年不该为求取功名抛下你一个人进京。我哈哈大笑:秀才,现象学描述的是对直接体验的认知,人对音乐的反馈并不值得把握。胡塞尔说任何一种反思都具有意识变样的特性,你这样的台词储备未免也太廉价。杜晓噎了一下,摇头说我们还是出去吃饭吧。
左岸大厦楼体纯黑,有种前苏联的肃穆。地底两层的韩式粥道馆,室温在5摄氏度上下,没开暖气。服务员穿着花花绿绿高丽孕妇装,端上来的皮蛋瘦肉粥和葱油饼、牛肉煎饺,倒全是道地的国产风味。折腾过大学几年,两人的胃都彻底毁了,象征性地举箸数下。当年别人都说我们俩吃饭的样子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心不在焉,眼睛直勾勾望着前下方45度角出神。现在仍是这样。食物很油腻,愈发倒胃口。陋店知味,那大概是江湖气氛的烘托而移情的缘故。然而此地虽是地下室,白炽灯亮堂堂直来直去,半点暧昧的余地也没有。饭毕沿着坑洼不平的夜路去找公车站,灯光昏暗市井喧闹,各自怀了很多鬼胎,连步伐都沉重了。若是生下来肯定像哪吒一样见风就长,十足的妖孽。
杜晓频频问我要在北京呆多久,住在哪里会去哪里玩,又言道中关村一带的房子房租很贵。我困惑良久忽然福至心灵,悟出他是有了女伴。故此希望我活动半径增大,人就散而难见。心里一阵冷笑,思忖北京城之大我何必非削尖脑袋与你同挤在一个村子里,就算万不得已要住,这两万多顷的地方又不是当年的中文系教学楼抬头不见低头见,能撞上那也是体彩头奖的概率。正要答话走过一长身男子来与杜晓打招呼,一面狐疑地朝我看。我赶紧掏出手机客串路人甲,默默赞叹自己世故通达知趣,也咒骂自己犯贱谨小慎微。当年他考上研究生毅然决然弃我而去,但那之前我亦有亏于,谁欠了谁都是一笔烂帐。重点是情债已过了时效,不可追索。算旧账也不合现代知识女性豁达气质,只能让人气短肾虚,一腔羞耻。
半天功夫,手机里倒是存了一箩筐短信,朋友们问我可安抵首都,内容大同小异,上言小别数日长相思,下言我爱北京天安门。消息灵通人士还通知我说毛主席纪念堂近日闭馆,不必去碰灰,因为老人家身体发霉在修补。还有几个北京的旧友约我一起去拔故宫门上的铜钉卖废铁,顺便一起吃顿饭。我噗哧笑出声来,杜晓和那人寒暄完了,拍拍我肩说走吧。
还是一前一后走,沉默是金卖呆有理。杜晓好像忘了之前的问题,我也就懒得提醒他。朋友阿婧忽然发短信说今天是农历二月二,她去形象设计室剪发了。要大修大改换造型,所以估计回家会很晚。这意味着我晚上将不能寄宿在她家,因为那小区是十一点关楼门的管理模式,而楼门的钥匙我没有。正月剃头死舅舅,我母亲没有兄弟,然而此前也已经很长一段没理发。刘海很长,接吻的时候扎进眼睛里,泪水直流。二月二也算个节日啊,我倒是忘了。节是硬性的停顿,用以捡拾平素的遗失。要挑着日子剪头发,可见她在异乡的生活也是贫乏荒疏,无滋无味。
到车站,我装模作样看了车牌,然后说想一个人静会儿打发杜晓回去。他恍惚地笑了笑,抬手想抚我脸庞却又放下,慢慢转身走进了夜色里。烟火沉实万户飘摇中,我终于看清这街道的本来面目。站在路灯下看完了那本小说,阿尼利亚终于结束了她无望的爱情。她隐居写作,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第一次坐飞机,恍惚、疲惫、悲伤,如释重负。这四个词让我有遇知音的欣喜。正如我许迭迭,请假坐飞机飞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坐了二十多站公交车,花去了近三千块人民币来到首都看旧情人,为的就是让事情有个明白的结局。也许在旁人眼里我是一个闲逸的花痴,千里迢迢投怀送抱,最后却流落街头。究竟是谁带我来到了这里?毫无疑问是自由意志。
我阖上书本,夏加尔和他美丽的妻子蓓拉仍在封面上用一种逃逸的姿态接吻。杜晓曾经和我商量说,如果将来我们要布置自己的家,就在屋子里挂满夏加尔的画。多么美好,他笔下的鱼是长着双翅的,他的母鸡凌空飞行,他的牛会拉小提琴。只要打开他的窗户,就可以看见,树林,绿草,月亮挂在林间,马留在农田里,猪留在圈里,一切都在它该安居的所在,蓓拉带着蓝色的夏夜空气,鲜花,和田野的气味,朝他款款行来。他们并不说很多的情话……夏加尔的衣扣再也扣不上了,而她穿着白衣服,或是黑衣服,在他的画里,飞来飞去,日益轻盈。
[美]乔伊斯•欧茨著:《我带你去那儿》,顾韶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