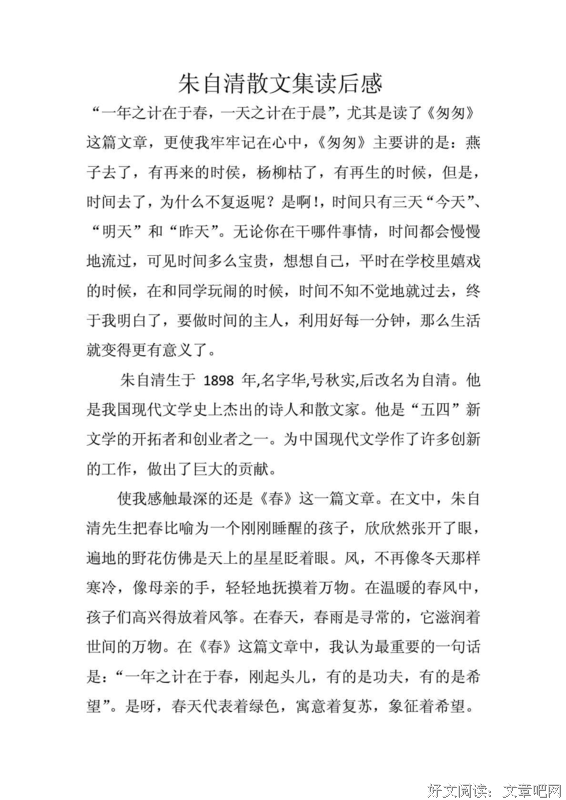散文的理念经典读后感有感
《散文的理念》是一本由[意]吉奥乔·阿甘本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元,页数: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散文的理念》读后感(一):阿甘本的美学迷宫
散文的理念评价人数不足[意]吉奥乔·阿甘本 / 2020 /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散文的理念》读后感(二):幼儿期的理念
在墨西哥的淡水湖里生活着一种白化蝾螈,有一阵子,这个物种吸引了动物学家和研究动物演化的学者的注意。那些有机会在水族馆中观察过这种蝾螈的人,会为它的幼儿的、几近于胎儿的外表而感到震惊。它相对巨大的脑袋,没入了它的身体,它的皮肤是乳白色的,在口鼻上和持续活动的鳃周围隐约有灰色的和鲜艳的蓝色、粉色的花纹;它的细足前端是花瓣形的肉掌。
白化螈(发生变态后的钝口螈有点丑,就不上图了hhh)起初墨西哥钝口螈被分类为一个终生维持一些两栖动物的幼体阶段特有的典型特征(比如用鳃呼吸和水生环境)的独特物种。尽管有着幼体的外表,但它完全具有繁殖能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它是一个自主的物种。直到后来,一系列的实验才表明,在这个小蝾螈身上施用甲状腺激素,就能引发两栖动物的正常的变态。于是,它失去了它的鳃,并且,在发展肺呼吸的同时,它也结束了它的水生生活,并发展成虎纹钝口螈(Ambystoma tigrinum)的成年实例。这些环境可能诱使人们把墨西哥钝口螈分类为演化的退化的一个案例,分类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一次失败,这个失败使蝾螈放弃了它的存在的陆生部分,并无限地延长了它的幼体状态。但近来,恰恰是这种执拗的幼体主义(幼体性熟或幼态持续),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解人类演化的钥匙。
现在,人们认为,人不是从个体的成年体,而是从灵长类动物的幼体(就像墨西哥钝口螈那样,这个幼体早熟地获得了生殖能力)演化而来的。这将解释人那些形态学上的特征,从枕骨腔的位置到耳郭的形状,从无毛发的皮肤到手脚的结构,这些特征与成年的类人猿不一致,却符合类人猿胎儿的特征。在灵长类动物身上是暂时性的特征,在人身上变成了最终的结果,这因此而以某种方式,在血与骨中,形成了一个永恒的孩童。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设还支持一种新的、理解语言和体外传统的整个领域[后者比任何基因印记都更称得上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特征,但直到现在,科学看起来都还在本质上缺乏理解它的能力]的进路。
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个幼儿,和墨西哥钝口螈不一样,它不仅维持了它的幼体环境,保留了它不成熟的形式,而且,可以说,它还如此彻底地被抛给了它自己的幼儿状态,它的细胞的特化程度是如此之低而全能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为了坚持它的不成熟和无助,而拒绝一切特定的命运和一切确定的环境。动物不关心它们不被铭写在其生殖腺中的体细胞的可能性;与人们可能的想法相反,它们才一点儿也不关注这个必死的东西(体细胞是每个个体身上无论如何注定要死的东西)呢,它们只发展固定在基因代码中的那些无限可重复的可能性。它们只注意规律——只注意被写(在基因里)的东西。
另一方面,幼态持续的幼儿,则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况:他有能力注意未被写下的东西、任意的和不被编码的体细胞的可能性;在他的幼儿的全能性中,他会狂喜地被压倒,被抛出自己——不像其他生物那样被抛入一个特定的冒险或缓解,而是第一次,被抛入一个世界。他会真的聆听存在。他的声音依然不受一切基因的成规的束缚,并且他绝对无物可说或表达,作为自成一类的动物,他可以像亚当一样,用他的语言命名万物。在命名中,人与幼儿期联系起来了,他永远与一种超越一切特定的命运和一切基因的召命的开放关联。
但这个开放,这个在存在中的呆若木鸡的停留,不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和他有关的事件。事实上,它甚至不是一个事件,某种可以在体内记录,并在基因的记忆中习得的东西;相反,它是某种必须保持绝对外在的东西,是和他有关的“无”,和因为这样而只能被交给遗忘——也就是说,只能被交给一种体外的记忆和一个传统——的东西。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准确地想起“无”:在他身上发生或自我显现的“无”。但这个“无”,作为“无”,也先于一切在场和一切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递任何知识或传统之前,人必然得先传递这个无思(svagatezza)本身、这个不定的开放本身——在这个无思、这个开放中,像具体的历史传统那样的东西才变得可能。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种看起来琐碎的论证来表达这点:在亲自传递某物之前,人必须首先传递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不可能再去学习说话;第一次进入语言的是孩童,而不是成人,而尽管智人有四万年的历史,他最属人的特征——习得语言——也依然与一种幼儿境况和一种外在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谁,只要他相信特定的命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说话。)
真正的灵性和文化不会忘记人的语言这个原初的、幼儿的召命;而那种为传递不朽的、编码的价值(在这样的价值中,幼体持续的开放,在一个特定的传统中,再次关闭了)而模仿自然的生殖腺的尝试,恰恰是堕落的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把人的传统和基因代码的传统区分开的话,那么,区分二者的确切来说正是这个事实,即,人的传统想要拯救的,不只是可拯救的东西(物种的本质特征),还有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拯救的东西,那反而已经丢失的东西;或者这么说更好,那被当作一个特定的属性来占有,却恰恰因此而不可遗忘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幼儿的体细胞的开放——只有世界,只有语言,才配得上它。理念和本质想拯救的是现象,那曾经存在的不可重复的东西;而最符合逻各斯的目的的,不是保存物种,而是复活肉体。
在我们内部的某个地方,那个漫不经心的幼态持续的孩童,还在继续着他的王的游戏。正是他的游戏,给了我们时间,使那永不落幕的开放对我们保持微开的状态。而大地上各色的人和语言,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保存和抑制——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就在多大程度上推迟——而看守着那个开放。各种各样的民族和那许许多多的历史的语言都是虚假的召命,在它们的召唤下,人试图对他不可容忍的声音的缺失做出回应;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它们(人的这些尝试)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试图把握不可把握的东西,变成——这个永恒的孩童——大人的尝试。只有在那一天,当原初的幼儿的开放真正地、令人眩晕地如是地被把握的时候,当时间终于完成的时候,人才最终有能力建构一种普世的、不再延迟的历史和语言,并停止他们在各种传统中的徘徊。这个人类对幼儿体细胞的真正回忆被称为思想——也就是,政治。
《散文的理念》读后感(三):试读丨羞耻的理念
《散文的理念》是阿甘本1985年出版的美学著作,也是阿甘本美学三部曲(《语言与死亡》《诗节》《散文的理念》)之终章。
书影1. 古人既无卑劣感的经验,亦无偶然感的经验(在我们看来,说到底,偶然夺走了人的不幸所有的伟大)。当然,对古人来说,欢乐,像(傲慢)一样可能在任何时刻,颠倒为它的反面,变成最苦的幻灭;但确切来说,就在这个时刻,悲剧,通过它的英雄封锁卑劣的一切可能性的拒绝介入了。在他的命运面前,船难是悲剧的,而绝不是悲惨的;他的不幸和幸福都不会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卑鄙。同样真实的是,在喜剧中,悲剧展示出它荒谬的一面;不过,这个被众神和英雄抛弃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卑劣的世界,相反,公正地说,这个世界是得体的:“在人真的是人的时候”,米南德的一个角色说,“他是多么地得体啊。”
在古人的世界里,人是在哲学中,而不是在喜剧中,遭遇到那种我们可以不强行引申地拿来和羞耻(那种让斯塔夫罗金的信仰瘫痪,或让我们觉得与神话的乱交,或卡夫卡的宫廷和城堡的神话般的污秽相似的羞耻)比较的感觉最初和唯一的踪迹的。(在古代世界,污秽永远不可能是神话的:百折不挠的赫拉克勒斯清洗了奥革阿斯的牛厩,使自然之力服从于他的意志。不过,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彻知我们的污秽,它在根源上总有一种神话学的残余。)奇怪的是,它(与羞耻相似的那种感觉)在巴门尼德的一段话中出现了,在那里,年轻的苏格拉底对伊利亚学派哲学家阐述他的理念理论。面对巴门尼德提出的这个问题——“头发、污物、泥巴和其他一切性质最恶劣、最令人不快的东西”的理念存不存在呢?——的时候,苏格拉底坦承,他觉得陷入了一阵眩晕:“我一想到这可以普世地延伸下去就感到痛苦不已。但一旦我心存这个想法,我就会立刻出于对因为堕入愚蠢的深渊而迷失的恐惧而逃避它……”但这只持续了片刻。“那是因为你还年轻,”巴门尼德回答说,“哲学还没有抓住你,我预言,有一天,它会的,那时你就不会再在任何这样的事物面前战栗了。”
内文书影丨在译者立秋老师的强烈要求下,用插图做了一个小书签:D在这里,重要的是,为思想(哪怕是片刻地)揭示卑劣带来的眩晕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说到底,是神学的)问题。上帝本身——天外的理念世界,巨匠造物主创造可感世界所依据的模型——呈现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的那个令人厌恶的面容,在它面前,异教之人移开了他的目光,并感受到傲慢,这个傲慢以如此伟力标志着古人的虔诚。上帝无需辩护:神是有理的,《理想国》中处女拉赫西斯的神谕就是这么说的。
不过,对现代人来说,神正论是必要的,但类似地,他也必然遭遇最悲惨的那种失败。上帝指控自己,并可以说是在他自己的神学粪便上打滚,单是这个,就给了我们的不安其确定无疑的品质。现在,我们的理性脚下的深渊,不是必然性的深渊,而是恶的偶然性和平庸的深渊。我们不可能因为偶然而负罪或清白:我们只能感到尴尬或羞耻,就像我们在街上踩到香蕉皮那样。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面带羞耻的上帝。但就像一切战栗都透露出一种与恶心的对象的隐秘团结那样,羞耻,也是一种人与自己闻所未闻、令人害怕的接近的索引。卑劣感是人在面对自己时最后的谦逊,就像偶然是那个隐藏(独属于人的原因对人的命运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面具那样,现在,看起来,人的整个存在都是在偶然的符号下缓缓展开的。
2.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只看到一个有罪的人,在一个变得疏远、遥远的上帝难以理解的权力面前的痛苦的总和,这是一种对卡夫卡作品的糟糕解读。相反,在这里,需要被拯救的,是上帝自己,而对卡夫卡的小说来说,我们可以想象的唯一幸福结局,是克拉姆、伯爵、匿名者,和被不加区分地全部塞进满是灰尘的走廊,或弯腰走在逼人的天花板下的那个由法官、律师和守卫组成的神学群众得到救赎。
内外封书影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把上帝放进了柜子——使碗碟间和阁楼成了典范的神学场所。但他的伟大之处——只在罕见的情况下,他的伟大才在他的角色的姿势中闪现——则在于,在某个点上,他决定放弃神正论,并忘记关于罪与无辜、自由与命运的老问题,以达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羞耻上的目的。
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人——世界范围的中产阶级——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经验,除了他们的羞耻,即人在内心最深处对自我的认识的纯粹的、空的形式。对这种人来说,唯一一种还可能的无辜将是,在冷漠中感到羞耻。害羞对古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感觉;相反,面对羞耻,他就像赫拉克勒斯在赫卡柏赤裸的乳房面前那样,恢复了他的勇敢和虔诚。卡夫卡力图教人使用这个留给他们的唯一一个好东西:不是把自己从羞耻中解放出来,而是解放羞耻本身。这就是约瑟夫·K在他的整个审判期间努力要实现的,而在结尾他执拗地低头看行刑者的刀,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羞耻,而不是他的无辜。“他的意思好像是,”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刻读道,“他的羞耻会比他活得更久。”
只有通过这个任务,只有通过至少为人类拯救其羞耻,卡夫卡才恢复了某种类似于古代的极乐的东西。
生活不易,狗子卖艺 友情出镜:立秋老师家的阿柴更多阿甘本之《语言与死亡》
更多阿甘本之《敞开》
《散文的理念》读后感(四):评阿甘本《散文的理念》:思想只有承担“诗的遗产”,才能朝向“散文的理念”
文丨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译丨王立秋
I
吉奥乔·阿甘本的《散文的理念》通过它的散文的间断性,或简省特征,来复活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形成的理念的星丛,是一种诗的使命的产物呢,还是一种致力于把真理从它的语言的具化中解放出来的思想的产物?这个问题,即哲学与诗之间、意指与melos(诗的声调)之间、一种散文(它隐含的哲学倾向管制着它的意指功能的效果)与一种诗(它的纯粹的声调的、和韵律的维度,看起来抵抗一切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中与书同题的那个片段或格言,即《散文的理念》,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甘本不想把意义、与诗的声调和韵律分开。相反,对他来说,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问题,变成了这样的散文或语言的问题,这种散文或语言不再任由自己为铭写在这个关系中的差异所支配:“既非诗亦非散文——il loro medio”。我们该怎样翻译阿甘本用来给这个题为《散文的理念》的片段或格言作结的“medio”这个词?如果存在一个超越意指与声调韵律之间、内容与形式之间、句法与格律之间的对立的理念或散文的理念的话,那么,这些(对立的)项,就都是被它们共享的东西即“il loro media”分开的。一方面,散文的理念既不与要么(哲学的)散文、要么(诗的)声调融合;另一方面,它又是那个被划分的场所、那个中间、那个环境、那个基质:特异的(诗的)声调和(哲学的)散文就是在这里被构造出来的。因此,散文与诗向彼此暴露自己,它们永远不会成功地构成一个统一体或一种稳定的同一性。
转向散文的理念(但这个理念并不属于一个超感官的世界)就是要理解这点,即,虽说散文与诗都不自成一体,但它们也不会合为一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思想必须面对的、被诗当作遗产留在身后的,既非诗亦非散文。思想必须要么与“诗的遗产”对抗、要么与之和解,而这个“诗的遗产”,确切来说就在于,你不可能给诗一种绝对独特的、可识别的同一性。阿甘本写道,“思想必须与这个诗的遗产——这个意义与声调之间的崇高的踌躇——和解”。如果思想不必标记一种非-同一性的、一种无灵魂论的踌躇的传统的话,那么,它可以像它比不和某个东西对抗、或不必与那个东西和解一样运作吗?这个双重的否定——“既非诗,亦非散文”——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它是一个双重命令,既指向过去,又指向未来。思想,为达到“medio”,必须使自己面向“散文的理念”,或面向诗的理念,但它只能通过承担“诗的遗产”来做到这点。
这个“medio”——在(哲学的)散文与(诗的)声调各自肯定其不稳定的同一性的那个时刻,它就已经把二者分开了;并且,思想通过遵从双重命令力图达到的,也正是这个“medio”——肯定不是一个位于两极之间的、在诗和散文的基础上增加的第三项。《散文的理念》的美国译者出于对亚里士多德文本典故的尊重,并根据从空间参照(这个参照使诗的起落、和散文的连续看起来是两种对立的运动)得出的线索,把“medio”翻译为“中项”。然而,倘若第三项存在,则又会出现关系问题,或者说三项间的关系问题,而思想也将陷入无限的后退。而且,这个“medio”也不可能是诗的元素和散文的、哲学的元素的混合物,一门半诗半哲学的语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门语言的诗的元素和哲学的元素可以被区分开,然后,就又会出现关系的问题;要么,二者会变得不可区分,这样如此,思想就必须任由“既非……亦非……”的激进来指导自己,而不是满足于“半……半……”的妥协了。
“Medio”有这本书的德国译者使用那个词即“Mitte”的双重意义。比如说,在黑格尔指出希腊人生活在由道德的实体和一个自由的、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形成的“幸福之中(glückliche Mitte)”的时候,他指的是在中间发生的事情,是不让位给极端、依然被环境包围的那个东西(而这正是这样一种中间状态的特征)。诗与散文的“medio”指的,也许就是这个“之间(between)”的中间和环境,而没有这个中间或环境的话,(哲学的)散文和诗之间就不会有联系了。但这个中间是一个原始的环境,而不是一个由已经构成的或已经被预设的两个极端创造出来的环境。这个环境(诗和[哲学的]散文都取决于它)和这个“之间”(它超出了那个同时切分和接合两个极端的界线),就是语言,就是分与共的、既非诗亦非散文的语言本身。散文的理念就是作为中间和环境的语言。它是在本雅明那里,把语言的存在指定为交流的“基质”的“可交流性”。如果存在语言,如果存在交流,那么,就必然存在散文的理念,即,一个永远不能被简化为哲学或诗的特殊性的基质,一种永远只交流自己的可交流性。每一次,在诗的个别性和哲学的普遍性把彼此分开,并以这样的方式来辨明对方的时候,它们已经在抹除自己了。
交流只可能是一种交流可交流性的交流,因为交流不可交流的东西和不属于语言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在存在交流的时候,被交流的,也是可交流性,即存在交流这个事实本身。但交流可能也的确隐含一个外部性,这个外部性把交流变成了交流某物的交流。语言在这个变化的基础上,引出了诗的个别性和哲学的普遍性,或者说任由差异存在。因此,直面“诗的遗产”,构想散文的理念意味着——至少,在你同意这里提出的诠释的情况下——达到作为中间、环境、基质的可交流性和语言。
不过,我们会好奇,达到可交流性是关乎触及“崇高的踌躇”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交流的外部性消失,并持续表明自身)呢,还是关乎建立语言的完整的现实性(一种无踌躇的现实性,它不再暴露潜能与行动之间的,可能性与实在之间的,本质与实存之间的,可交流性与交流之间的,中间、环境、基质、“之间”本身和哲学与诗所在的中间、环境、基质、“之间”之间的区分)。
II
思想如何面对看起来被诗当作遗产留下的那个东西?海德格尔用一个双重运动,来描述诗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个双重运动通过持续的分裂,持续地供应自己缺乏的东西。这个缺乏又把它构造成一个运动,使它停不下来。作为两条除在无-限中的一个不能确定的点上,除非在一个永远先于它们、且不预设任何进一步追溯的点上否则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诗与思想不停地呼唤彼此,并且永远不会在对方的呼唤中重返沉默。这样,诗与思想也就把自己铭写在实存(existence)上,而实存则标记着语言的差异:因为实存缺乏的,从实存的无根的底部呼唤诗与思想的,是说出了词的本质的词,即大写的存在(Being)的词或言说。
如果说,词的本质不在于使物变得可用;如果说,词为让物出现、通过让物自己显示自己来显示物而命名物;如果说词——首先,是诗人的词,或诗人给物的名——让物作为物而存在,就像海德格尔在他关于斯特方·格奥尔格的一首诗,《词》(“Das Wort”)的讲座中论证的那样的话,那么,贯穿每个词、把词和词自身分开的差异,就不可能被言说或说出了,否则,它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存在,就会反过来切分自己。因此,大写的存在的词、词的本质,不是词。它不过是纯粹的可交流性而已。海德格尔把这个可交流性称作“Sage”,即大写的说(Saying),他坚持,大写的说与大写的存在、词与物、开放与差异(开放把语言献给秘密,而差异则把每个存在和大写的存在联系起来),是分不开的:
最古老的[……]表示说的词是logos。Logos意味着大写的说,后者通过展示,让众存在在它们之“所是”中现身。不过,(在古人那里)表示说的同一个词,也被用来表示大写的存在,也即,众存在之在场。大写的说与大写的存在、词与物,以一种被遮蔽的方式,一种几乎没有被思考过的方式[……]属于彼此”。语言和说的“不可说”——这个秘密并不保守任何你可以识别、或使之出现的东西,这个绝对的秘密本身就是自己的秘密,结果,它也就只是一个秘密——根本没有隐藏或不可见之物的特征与连贯性。用本雅明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说,可交流性交流的永远是它本身,如果可交流性使自己与交流保持分离的话,那么,物就不会让自己被命名,也就不会有能力出现了。但同时,可交流性又不可能被交流,因为如果它可以被交流,那么,它就会具备物的形式,而交流,也会通过把自己简化为单纯的对某物的交流,而直接把自己抹除了。可交流性使交流的内在对踌躇、震动、不定、对外部性的肯定和悬置开放。
内在于交流的“客观”矛盾,即可交流性的交流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使可交流性和交流超出了它们的客体化——维持着那个使诗和思想出现的缺乏。因为这个缺乏不可能被填充,所以,我们必须如是地(as such)把握它。但如果,“如-是”定义的是被命名的物的出现/表象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如是地把握一个缺乏呢?这个问题也许表达了诗和思想不停遭遇的那个困难。如果呼唤思想的是诗说却没有成功说出的那个东西的话,那么,思想也必须反过来呼唤诗来面对诗的任务,即思考物中非物的那个东西、和语言中的无名的那个东西。不可思的与不可说的,物与词的联盟引起、挑起、和激起了诗与思想,因为交流永远是对可交流性的交流。对一切诗的词来说,对一切力图达到可交流性、medio、大写的说的思想来说,当务之急,是在自身内和自身外,把握一种与自身的交流重合的可交流性,把握既非诗人的词亦非思想家的散文、穷尽了大写的存在的词的词与物。散文的理念指的,不正是这个重合的完整的现实性吗?
III
在关于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论文中,阿多诺试图描述他在一些诗的不定中发现的安慰的姿势。安慰是否意味着肯定看起来失去的东西的在场,和否定它的失去?不,因为这样一种肯定,不过就是一种否定,一种试图让不被安慰的人放心的徒劳的努力。毋宁说,安慰的姿势——也就是说,诗本身的姿势,而不是诗人再现的姿势——在于经受那种让一切界限震动的不定。为了安慰,知道如何使划分缺失与在场的界限变得不确定,如何定位像无法被测定的震动一样遍布此界限的不确定性,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关乎特定的知识,考虑到使在场与缺失之间的界限变得不确定也可能导致疯狂。如果这个踌躇、这个不定、这个“既非……亦非……”(既非散文亦非诗,既非哲学亦非艺术,既非在场亦非缺失)的省略号指的事实上是一种完整的现实性,那会怎样?安慰的姿势的真正目标,不正是寻求一种完整的现实性,而非恢复某个特殊的在场吗?
由一种基本的不定、由一种对不再属于计算秩序的“不可决定”的体验产生的踌躇,看起来,是不可被简化为可能性、实在、潜能、或现实性的。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踌躇,只要我们让自己进入建立在两种或更多的可能性之间的摇摆运动,那么,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开始动摇,并因此而不再是自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踌躇把可能性暴露在一种虚拟的、或者说延迟的实现面前。如果我们可以坚持纯粹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踌躇的空间了。也许,踌躇也指示终结潜能的忧郁的哀悼工作。
在《散文的理念》中的一个文本,《学习的理念》中,阿甘本提到了投身于无止境的学习的人的忧郁倾向。的确,没有什么比太久地居住在纯粹潜能的领域,无限地延迟向行动的过渡更苦的了。可忧郁难道不是已经发出了潜能被污染的信号了么?踌躇并没有把自身遗弃在它的领域。不过,它也不排除潜能。即便在各种可能性之间徘徊并因此而看起来保持着多种外部的“可能”(这些“可能”已经把踌躇暴露在实在面前了),踌躇还是开始对可能性与实在、行动与潜能、实存与本质之间的对立构成阻力了。它触及了这样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对立的或者说不同的项不再肯定它们(各自)的同一性、它们的对立、它们的差异。踌躇使各项对这样一种经验开放或者说把它们与这样一种经验联系起来,即,对一种完整的现实性、对一种穷尽了潜能的行动、对一种如是地实现的潜能的经验。在潜能触及这个界限的时刻,它也就使自己停了下来,它不再是它所是的那个东西,同时也没有变成它所不是的那个东西。
不过,坚持踌躇,也就是放弃完整的现实性。因为就像踌躇即对“不可决定”的经验只有在最终导致一个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暂时的和狼狈的、还是不可撤销的和最终的)的情况下才成其为踌躇那样,对完整的现实性的经验,也只有在它包含为一切决定所固有的排除之力的情况下,才成其为这样的经验。散文的理念的政治维度,形成固定的东西的界限的中间、环境、基质的政治意义,或者说达到可交流性的界限的交流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此。散文的理念与权力不兼容。它如此激进地违抗权力,以至于作为排除之力、作为分化隔离之力的权力不能生效:“权力是对潜能的孤立,它使潜能与其行动分开,权力是对潜能的组织”。但如果现实性不可能排除那分化隔离之力(否则它就会立刻失去它的完整性,重新把自己和潜能对立起来并因此而生产出权力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对完整的现实性的领域或状态中的排除来说,又会发生什么?
在关于抄写员巴特比这个文学形象的论文中,阿甘本构想了交给记忆的救赎任务。从这篇论文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无论何时,只要你试图思考《散文的理念》的“既非……亦非……”就必需回答的关于排除的问题。“可能性的restitutio in integrum(恢复原状)”(它把发生与非-发生、成为的能力和不成为的能力维持在一个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结果,它必然是一种关于“不曾有过”的东西的记忆或回忆)和那个使可能性变得不完全、使记忆变得排他,超越一切悬置和一切踌躇的东西是什么关系?它和那个除通过实在来排除可能,否则便一无所是的东西是什么关系?它和永远是盲目而不妥协的排除之力又是什么关系?
IV
如果你不属于一个整体,不属于某种可被识别和命名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排除了。当我们意在通过占有归属本身(就像阿甘本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中指出的那样)来克服排除的时候,完整的现实性的决定性的困难,也即,这样一种整合和这样一种完整性——它本应只在排除的基础上恢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和发生过的事情——的困难又再次变得明显了。为在这样(那样)的存在的(像)这样的存在中把握这个存在,为在实存的发生在其理念中把握实存——这不就是要在不排除物或个体的任何属性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抵抗同一化的无-差异(状态)么?也许,最终,同一化会把每一个属性都构造为排他的属性。通过在不放弃自身、把自身交付给同一性的缺失或缺乏的情况下抵抗同一化,通过在归属中超越归属,来临中的共同体在一种可被称为完整的现实性中团结在一起。
在其他地方,在一个关于人民概念的文本中,阿甘本认为,就像我们不应该从黑话和俚语出发来建构语法,而应该让语言的“多”恢复的东西,即“语言的factum(事实)”出现那样;我们也不应该给人民一个受国家控制的同一性,而应该让人民掩盖、指向的那个factum,即“共同体的factum”出现。于是,我们从人民走向共同体;从对帮、伙的归属走向对这个归属本身的暴露。在阿甘本看来,人民总是“对factum pluralitatis(‘多’的事实)大体上成功的掩饰”。在向作为factum pluralitatis的共同体过渡的时候,对人民的归属不但被解除了。它还揭露了自己:它是一个拟像。实际上,你永远不可能属于人民,因为人民作为对“多”的掩饰,绝不可能是它声称自己是的实质的或精神的独立存在。
不过,当这样(那样)的存在在它(像)这样的存在中被把握的时候,它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还不大明确。一方面,个别性(就它是无论是什么的个别性而言)的无-差异,并不是缺乏归属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个无-差异又表明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对于一个占有了它自己的归属的实存来说,要和标记差异的东西、不可能与被标记的差异分开的东西产生联系,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这个无-差异不就排除了排除他者的归属吗?它不就也排除了归属的拟像——至少,就拟像因为其诡计的效力才成其为拟像而言——吗?它不就有了放弃自己、把自己交给分化之力,委身于排除的辩证的风险吗?一旦——为了构成无排除就不可能构成或存在的东西——排除是必要的,就像在卡夫卡的《地洞》中那样,被排除的东西就会变得比排除之力更强大。结果,排除也就得到了无限的延续。
V
“散文的理念”这个表达也可见于本雅明论历史概念的一个片段。但我们不能忘记,本雅明在写作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对散文感兴趣了。作为“诗的理念”,作为艺术的本质,散文在德国浪漫派那里,有着绝对的特权。如果说,在浪漫派的文类等级中,小说以某种双重的、矛盾的潜能,以自限、和向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就好像反思的自我限制仅仅是因为无限的自我延伸才是可能的那样)而著称的话,那么,批评就必须呈现艺术作品的“散文的核”。在这样做的时候,批评才会脱离单纯的评价,或者说,脱离与融合意见的判断。对德国浪漫派来说,散文是“不可破坏的”。它以冷静,而非狂喜或mania(狂热)为标志。
也许,浪漫派归给散文的这个不可破坏的特点,也是语言的理念的特征。而在关于历史概念的笔记中,语言的理念又与“普遍历史的弥赛亚理念”重合。本雅明把这个语言理念称作“散文的理念”,并且他明确地指出,它与“普遍历史的弥赛亚理念”的重合,标志着语言之“多”的终结和历史之“多”的终结。在普遍历史的和散文的理念的世界中,在“弥赛亚的世界”中,翻译走到了终点,语言也最终触及“完整的现实性”。本雅明是这样表达自己,是这样谈论“integraleAktualitàt”的:
弥赛亚的世界是普遍的和完整的现实性的世界。只有在弥赛亚的领域,普遍的历史才存在。普遍的历史不是书写下来的历史,而是被当作节日来过的历史。这个节日被清除了所有的庆祝。没有节日歌曲。它的语言是得到解放的散文——打破了抄或写的束缚的散文。如果我们想要参照阿甘本在《散文的理念》中说的关于引号的功能的话来改写本雅明的评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坚持,在“弥赛亚的世界”中,思想将完成它的任务,并将通过打破书写的束缚,和破坏长期缠扰语言、再现我们的“语言之囚”的无声的符号,与它的“诗的遗产”和解。救赎的散文是自由的,因为它不再依赖于书写,依赖于语言所受的限制(只要事实证明,交流与可交流性之间或者说翻译与可翻译性之间的差异对言说来说是决定性的,语言就会一直受限制)。本雅明声称,每个人都会理解这种散文,而不必非得把它写下来。作为无成规、无固定、无修辞、无感伤、无拜物教的散文,它既不传达任何意义,也不传递任何信息,我们也不必诠释、破译或解构它,因此,我们可以直接理解它。如果从这种直接性,从中间、环境、基质(这个中间、环境、基质不会再引出哲学与散文之间的差异)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散文的理念的确是不可破坏的。
本雅明用“散文的理念”这个表达来指语言、世界和历史之间的这种不再根据预设的逻辑来思考的关系。完整的现实性不预设任何东西,因为它就是完成了的或者说达到目的的翻译的语言,因此也就是对语言本身的暴露。但该如何思考这个关系呢?可以根据阿甘本的《散文的理念》来思考它吗?
吉奥乔·阿甘本,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曾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维罗纳大学、威尼斯高等建筑学院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欧洲研究生院等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对文学理论、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包括《神圣人》《王国与荣耀》《例外状态》《奥斯维辛的残余》《空心人》《幼年与历史》《身体之用》《敞开》《语言与死亡》等。
在这本书初版一年前写的关于“物自体”的讲稿中,阿甘本以一种让人想起本雅明的可交流性概念和海德格尔的诗中语言概念的方式分析了柏拉图的理念:
因此,关于理念,柏拉图的警告是,在被说出的东西、和在被说到的东西中,可说性依然没有被说出;在被认识的东西、和在被认识到的东西中,可知性丢失了[……]哲学呈现的任务是用言语来帮助言语,这样,在言语中,言语本身才会不再被预设,才会开始言说。只要语言还在预设语言,只要知识还在预设知识,只要交流还在预设可交流性,只要说还在预设大写的说或可说性,简言之,只要被差异分化的物还不是物自体、还隐藏在自体之中,可以说,理念就依然带有某种预设。因此,可以说,哲学家必须把这片混乱弄清楚,把理念恢复为理念。这里提到的任务,也就是《散文的理念》末尾指示思想家去与语言的“诗的遗产”对抗、和解的那个任务。通过阅读《表象的理念》可以验证这点。在那个片段或格言中,理念看起来是对可感物的暴露,因此也就是对物自体的呈现。在被暴露和被呈现的情况下,物不再预设它自己,也不再是“某个被语言和知识预设的可感物”。它不再停留在为可感的和可知的之间的对立所确立的那个领域,因为“不再与其可知性分离、而在其可知性中的物,就是理念,就是物自体”。
从这种对理念的构想(它把语言和知识在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五个推论:
谈论理念的理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理念就是“物自体”。强推预设的逻辑,不就是在把理念拆分为理念的理念吗?而理念与其自身的分离,又会危及到物。 散文的理念不是诸多理念中的一个理念,而是理念本身。理念永远是散文的理念。 记忆(散文的)理念是不可能的,因为理念不会发出它预设了一个过去的信号。相反,理念是不可记忆的和不可忘记的物,或者说,它是先于当下和记忆并且在被转变为预设时只会变成某个物、变成某个存在或某个实体的无。《不可记忆者的理念》里的一段话是这么写的:“从记忆跳向记忆,自身却不会被想起的不可记忆者,严格地说,也是不可忘记者。这个不可忘记的忘记就是语言,即人的词。”《幼儿期的理念》里的另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对[幼态持续的幼儿]来说问题确切地说是记忆无:对他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显现。然而,如是,这个无也预见了一切在场和一切记忆。” 作为物自体,(散文的)理念不会带来新的思想或新的艺术-形式,正如它不会开启另一个时代那样:“我们不想要新的艺术或思想作品;我们不想要另一个文化和社会时代:我们想要的是把时代和社会从它们在传统中的徘徊中拯救出来,把握时代和社会中包含的好的,即不可延迟的和非-时代的东西。” 理念不会上升到现象之上,理念会拯救或救赎现象。只有不可记忆者,只有绝对的忘记,才能拯救永远已经被忘记的东西,即物的可感表现或现象表象。反过来说,现象守卫着不可记忆者,即有转变为(语言和知识的)预设的危险的理念。如果说拯救现象和把思想与诗从预设的逻辑或结构中解放出来是必要的,那么,在我们确定这点——理念不过是可感物在其可知性中的暴露和呈现;语言不过是“无预设的非-潜伏物,而人总是已经居住其中了”——的那一刻,我们也必须说明把世界和语言关联到一起的历史纽带。但一切拯救某物的努力,都必须面对一个根本的绝境。
一方面,我们只能拯救不是其所是的东西。拯救意味着通过暴露和呈现物自体,恢复或构造物的完整的现实性。因此本雅明才会认为翻译是一个恢复活动,并在翻译中感知到一个“根本上服务于表达语言之间的最私密关系这个目的”的语言运动。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永远不可能拯救不是其所是的东西。没有非-存在,没有差异和忘记,没有排除,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现实性。可非-存在又会延迟现实性并最终使它被忘记。那么,从这个绝境的双重视点来看,我们该如何一般地、历史地思考完整的现实性的建立呢?
我们不能认为完整的现实性是逐渐接近的结果,是历史进步的目标或终点,无论这个目标或终点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因为接近和进步预设了一个方向,即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因为理念永远不可能被预设(否则它就会分裂),所以,我们必须这样思考完整的现实性的建立,即,认为完整的现实性是一种纯粹的中断,也就是说,一种无剩余的中断。
显然,从一开始,铭写在语言和思想中的预设,就使一切此类断言成为问题。不过,承认纯粹的中断的可能性,还不足以思考完整的现实性的建立或出现。当然,纯粹的中断会逃避它中断的东西。它不会准备什么,先于它的只有无。但展示完整的现实性分给这个无的位置不也是必不可少的吗?散文的理念这个问题,关乎一种不可能的整合的问题,因为它关乎怎样不排除根本的中断,而完整的现实性的建立就取决于这个根本的中断。如果我们认为,完整的现实性不取决于任何中断,并且事实证明它就是那个中断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解释不连续的时刻,而没有这样的时刻,中断是不可设想的。
VI
散文的理念给我们带来的语言和思想的难题,不是一个美学的或形而上学的难题,而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难题。因此,阿甘本对政治的话题、对政治哲学的话题的兴趣,绝不是一位不满足于哲学的抽象与思辨、也想成为一名在政治上介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家的兴趣。试图澄清建立(散文的)理念的完整的现实性的条件的思想反对这样的历史与政治观——指引这种历史与政治观的,是对某种无限的进步,或某种无限的理念,比如说建立在自由的、理性的和透明的交流行动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体的理念的再现。
这种思想证明了,通过不可能性来从根本上中断一切预设的进步逻辑,以不同的方式(即不是通过再生产自己想要摆脱的历史、政治和实践条件,而是通过别的方式来)操作是必要的。把自己逃无可逃地封入“就是那样”(that which is the case),属于预设的逻辑,属于理念与语言的具化——无限任务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
完整的现实性即中断的思想,提醒我们注意本雅明强调的那个事实:灾难绝不是内在的,事实证明,一切事物继续在同一条路上、向同一个方向运动,才是灾难。因为,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包含革命的时机,因为历史不过是对革命的延迟罢了,所以,本雅明不但强调中断与完整的现实性之间的本质联系,也通过对政治情景的特性的关注,认出了革命的思想家。
VII
我们发现,阿多诺在一个题为《论形而上学》的片段中,也直觉地把握到散文的理念的思想。他的表达极其强烈,又简单得令人不安。下面这段话从思辨辩证法的角度提出了完整的现实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有条件的,绝对的就不可能存在的话,那么,有条件的就必然属于绝对的,但同时,它依然是有条件的。这与这样的生命感完全一致:此生中的一切既绝对无意义,又无限有意义。作者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系柏林艺术大学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教授。原标题为“完整的现实性:论吉奥乔·阿甘本的《散文的理念》”。
<燕京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