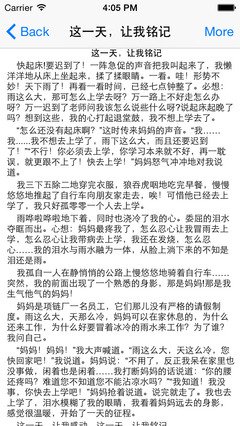迟疑·电视·自画像读后感精选
《迟疑·电视·自画像》是一本由(比)图森著作,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迟疑·电视·自画像》精选点评:
●各种感人
●从这本书之后,又看了他的另外两个
●一生只一次
●迟疑,很迟疑
●受不了的无意义磨叽文。 琐屑得让人全然没有哲思。
●空间代替时间
●学院图书馆借的
●黄龙时代汉庭酒店的前厅,看了《迟疑》。《电视》最好,崇拜。看《自画像》时偶遇了一场火灾。最近真是太热了。
●很喜欢图森的小说
●刻意学口吃就会变成口吃。
《迟疑·电视·自画像》读后感(一):内心独白
最近看了的几本法国作家的作品,都是节奏缓慢,描写精细的,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这可能就是法国风格了。
“我儿子在我前面坐着,在车里把头伸得比值,好象我赋予了他某种在船首了望的特殊使命,并且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状态在执行任务,风帽下的眼睛警惕着~”
“他又说了几句话,最后挂了电话,他走出电话亭,让玻璃门自己关闭。”
“……伸出胳膊,压在按扭上,图象破碎并从屏幕上消失了。”
他还来到蓬皮社图书馆查找缪塞的作品,并仔细描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里的交涉写了有五页,但是看来那个时代图书馆的服务也够局限的。法国机构一贯给人不积极的感觉,至少我这么认为。
《迟疑·电视·自画像》读后感(二):《迟疑》:故事,抑或一种讲述方法
陈侗在《迟疑 电视 自画像》的“编后记”里面说“我们知道,进入图森的世界并不需要掌握什么密码,只要稍稍调整一下姿势就可以了。”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说法。我们总算从各种各样的故事中逃离出来,只是讲一个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仅仅是“迟疑”而已。我去拜访一位老朋友,然而在到达了他所在的村子之后,事情却变得微妙了:大概没有比图森更饶舌的小说家了,这时候他开始让他的主人公“迟疑”起来,要不要去拜访老朋友呢?仅仅如此,他给我们讲了88页,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将要不耐烦了,但最终竟然读完了,读完之后,竟然,还想,如果有空,应该再读一遍的。
图森的风格被称为“极少主义”,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很能够代表他这种风格。故事的情节被压缩,同样的场景反复被描述,人物,事件都被减少到了极至。“我”带着儿子,住在离朋友家不远的旅馆里,常常半夜出去散步,偷偷窥视朋友家。反复考虑海里的死猫的事,在要不要去拜访朋友这件事上游移不绝,几乎是神经质的推测各种可能。
这样一个故事,其魅力何在呢?
它为我们讲述了人的神经质,更重要的是由此体现的事物的不稳定性,存在的不稳定性。事物需要被反复把握,这大概是他的小说的核心之一。在这种反复之中,聪明的图森把握住了某种类似禅意的东西(当然完全不是东方的那种)。正是这种核心使本是异常简单的东西变得繁复起来,一个小小的“迟疑”也值得大书特书。这是他的小说的内在的魅力。
而我们在把握事物的过程中,如何在反复之中把握到事物的各个细节呢?
图森在写作《迟疑》的过程中使用了照片。大概是这些照片使得他变得不厌其烦起来。他还拍摄电影。他始终在固定的事物上兜圈子,反复的摹写。每次只是改变小小的细节。这种方式很吸引我。 它是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不是每个作家都能驾驭这种饶舌的方式,并且使他们变得饶有趣味。 想象手头有一叠照片,然后把他们反复的摹写,并从中制作出故事来,更重要的是,制作出故事的韵味来,这实在是很迷人的事,这大概也是图森的乐趣图森的姿态所在。
而这种姿态,与慵懒有关,与某些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关,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潇洒在里面。显然图森并不洒脱,他也是不停的沉迷于客观事物之中,并且看起来并不想从里面抽身。
《迟疑·电视·自画像》读后感(三):越渡菲利普·图森(1)之迟疑
在写完一组图森的诠释文本五年之后,我写了一组新的《越渡叙述》,结果发现了这种文体的源头,包括这样的黑压压一片无分段的风格源头,里头就有图森(当然还有塞林格的宗教式谈话体文本,今天刚好是塞林格一周年,不得不缅怀下他那个弗兰妮和祖伊的朝圣者之路式谈话)。而图森的《迟疑》,作为一种新的符合表象秩序的文体形式出现(摒弃意义的深度,去描述事物的平面和外部,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的阅读方式显然要求改变,应该用照片式阅读方法,图森自己的小说往往也是开始于一张照片或一组图片,比如这个迟疑就是来源于左图的照片,这种写作就会要求不要把自己意识灌入照片去寻求解释,而是应该让照片射出一种刺,或箭,直接射中我们),整个小说就像一只猫被杀的侦探型小说,那只死猫的超细致描写和想像,还有图森孩子的道具式出场,我不知道为什么图森选择了一个孩子,或者多了一个孩子,他完全可以一个人,就是“我”,但是这个孩子的出现,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不说话,他只是起到了一个闹钟的功能,比如什么时候孩子醒了,必须会去照顾他。其余时间,图森都在做一件事情,观察这个岛,岛上的朋友家,以及那辆奔驰车,旅馆的其他房间,并且几次潜入别人的居室,进行搜查,包括他朋友家,因为他知道钥匙的位置,看别人的卧室,用具,听电话留言。这一切,都只是他的迟疑。他所谓的怀疑他朋友早就知道他来到岛上,但是不想见他,所以躲到宾馆里,故意不看图森写给他的信,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图森也故意没有直接找他朋友,而是通过对岛上的观察,和那只死猫的联想。图森的每个段落基本上就是一个照片,在照片内的物很细致,之外的,全然不知(但是还不是静态的照片,它在时间中行进,在空间中波形扩散,最快速诱骗一个客体逃离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它必须行进,因为盯住一张人的照片比一张风景照恐怖一些。你无法判断是我们在看它们,还是它们在看我们。它们又不依照观看者的角度变化。似乎它们都躲在里面把临终的一个惊讶抛给我们。好像另外一个陌生人。才发现我们被一种过去时间里的人给陌生化了一把。而且图森的文本还是有一种画外音的照片,这个画外音如鬼魅般统摄着这些在时间中运动的静止图片,图片里的内容本身是不动的,静止的,并不是无声,无声就是死亡的象征,这仿佛就是图森随身携带的一堆照片,他要开始叙述的时候,就把照片摊开,以一种可以叙述的形式摆放起来,对象就在那些照片的分布上,图森的画外音就像鬼魅一样飘渺,而且对图森来说,文字、电影、照片三者的界限没那么泾渭分明,他可以把它们协调得很好)。没有其他手段的叙述,很安静,简单,整洁的一段段。仿佛这是一个经典的几何体。描述一个数学的几何体所需要的叙述。那么简单,干净,几乎把繁复的叙述抽象出来。并且不解释其中的链接,那些地方都不动声色地存在。他抛给你一堆关于一个事件的尽量多的照片和细节。其他都是你自己要做的。整个小说,基本没有对话,只有很少的一句,也都是很简单结束。他在煞有介事地把一些虚假的想像叙述成真实(越渡叙述的法则,读者需要关心的是一种叙述本身而不是叙述中构成的论述主题或者小说中的情节推进,也不是叙述之中的词语和概念的意义,它一直在表面滑行,而不是潜行),而格里耶是相反的,是把很真实的物体描写后,让人感到距离,模糊,意外。这方面,也许图森走得离杜拉斯更近。他整个小说都在围绕一个气场写。这个气场就是封闭的岛。里面的所有人和物都处在场中,场有一种磁一样的性质力量,如果理解全篇都氤氲着那么一种图森特殊的气韵的话,大抵就能明白他的迟疑的写作目的了。比如一开始的死猫,“我”去朋友家拿的信,信采用了复现手法,在不同时间,地点,状态下出现,还有“我”的孩子从沙滩边拣到的一个塑料鞋,宾馆的钥匙,朋友家的电话留言,甚至那海水的波浪,这些东西原来拿出来,放在别处观察,会是很平常的一件物,我意思从原来的文本里单独拿出来,而不放在这个小岛上,小岛封闭的,图森显然别有用心。这些单独存放的情况下,几乎有点类似格里耶的写物。但是在这个岛上,在图森说明本来来这个岛的目的是为了来探望一个朋友,因为突然出现的一个死猫,或者是别的什么,图森产生了一丝迟疑,他决定在不通知朋友的情况下去窥视,我用窥视,因为他的确用了做贼的方法,比如取别人家的信,放在坛子里隐秘的钥匙,进入房间,探巡别人的客厅卧室。并几次试图用他朋友的角度和目光,“反”窥视这个房间外,他觉得他朋友没有离开这个岛,他存在某个隐秘的地方,正在窥视自己,或者躲避。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哪怕一模一样字句的描述物的语句,拿到别处就是很客体的,但是在这,被无形加上了一个气场。这种笼罩的气韵。无疑让每件物都带上了特殊的气氛和力量。这个气氛就是题目迟疑。物带上了犹豫不决。哪怕它描述得再客观,科学说明文一样描述,都无法避免得带上了怀疑和不确定色彩。那辆奔驰车,在村子里,停留,在远处仿佛形影不离得跟踪,监视自己。小说直到最后,才把猫的死因,汽车上的人,讲清道明。自始自终,他的朋友也没有出现。但是他作出了最后决定去正式拜访的举动,正是迟疑的结束。这也是所谓越渡的法则,制造了一个没有框限的自我,不在既定规则内既定文本内的自我,这个自我属于一个未被虚构出来的世界(那个图森制造的迟疑的世界),它只是标识了自身为一种不存在,因为旁观者本身也是一种存在,标识为能在它提供自己的观察作为”实在“的时候越渡(图森先制造一个怀疑朋友在岛上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做着一些事情,而自己又是跳脱在这个视角之外的观察者,直到他准备去正式拜访朋友,即要剖开自己制造的朋友可能早就在岛上观察自己的怀疑世界时,他才成为真实的施行主体出现),并取消它自己的观察地位,并在此结束文本。
《迟疑·电视·自画像》读后感(四):读《迟疑》
Ⅰ)
我想这比较类似某群人都写过的那种即景散文。女人式的,抒情式的,并且不逃避不诋毁为景生情。好比,我也写过一天清早从一条偏僻小径绕道去图书馆,路遇红舌头的狗,口水在它脚下滴成一滩,被太阳镀着光,池塘边的排水管突突的吐水,把浮萍冲做聚散状,远处荒野上一颗孤零的树,塔科夫斯基的味道。其实,真实中,那颗树并不存在,也不存在这么个早上。只有彼时想从现实中逃逸的我,虚构了一个塔科夫斯基味的早上。同样的,不存在一个迟疑的阴郁的村子,猫,奔驰,别墅,只有一个迟疑的阴郁的图森。从品格上说,这已是在创造世界。我们不应对图森的迟疑感到疑惑,就像电影《致命ID》中那个出色到可比最高超的小说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幻想呈现给我们一道凶杀的盛宴。那么图森在轻度的妄想症中游弋就近乎恬适了。何况他还不断的喂给我们轻微疼痛的叙述颗粒,被割肉的章鱼掉在地上,啪嗒一声,雨后的水洼,反射着不见本人的图景,还有蘑菇,一闪而过,像酸水滑过舌尖。从昨晚到今早,昏沉的开夜车般的阅读后,我想我停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32页,图森第一次在比亚基的别墅中游荡。之前出现过猫和奔驰的提示,猫(被幻想)是被比亚基的陷阱谋杀,奔驰曾跟随我进入村子而今被发现在比亚基的院子中。他将继续发现(幻想)吗?被关上的旅馆的门,甚至坐在车里,而后又在餐馆遇见的男人,都将一一被赋予叙述的功用吗?我在这里遇到的是侦探小说和散文小说的迟疑。这种轻盈的迷惑和叙述氛围一起构成了我对图森的期待。我发现我原本想说一说有关意义的消解,说说他让我想到的另一个极端,海明威,和与他似乎有着某种亲缘的杜拉斯,说说这种情绪式的叙述语气对一个读者的影响和戕害。然而一旦进入图森的叙述气氛,这些理论的箭簇则纷纷被阻挡在外。这时,除了迟疑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也许意义在叙述延拓的尾巴上自己跳着舞,或者散了架。从表面上看,图森是很容易被模仿的,一如杜拉斯式文体在国内的泛滥。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直觉到他俩在叙述之前的那种隐痛,那种在每一个细节中植入自我的冲动,甚至有时不惜为了花而制造花盆。它很容易教给我们一种观察方法,一种叙述语调,同时使我们忽略支撑这种方法的精神体系。它支持并鼓励嫁接。这是它的危险之处。这是我第一次读图森,如果我可以假定他和杜拉斯的亲缘,则我需对他警惕。我知道杜拉斯的纯然的女性世界是很难进入的,我舍弃了对很多男性经典的同情以进入杜拉斯,换来的就是对她的语气和精神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更深的迷惑。这种迷惑会发生在图森身上吗,他将使我丧失更多,或者将我体内存储的碎片拼贴?不管怎样,谋害已经开始。方向在逃跑之前被抹杀。你可以读一页图森或杜拉斯,就抬头在周围寻找相类的细节,建构你自己的图森式或杜拉斯式世界。杜拉斯不必说了,就图森的《迟疑》来说,他为什么会对一个朋友怀有这种迟疑,这种迟疑怎样造成了他的思维分裂,以及这种分裂怎样投影在叙述中,才是图森要在小说中解决的隐痛。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忽视就像杜拉斯成了可以随口拿来引述的作家而不必追问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这正是所谓某种“现实主义”和图森们的不同。也许他不再相信小说和意义的二元对立,他的细节就是意义,或者消解意义。但读者不能被动的被消解掉,不能为一道美肴败坏了味蕾。在我们肆意使用着图森式杜拉斯式的叙述语气时,必然要为这种对事物的不尊重付出代价。最糟的情况下,它将迫使我们无意识的一路欢歌着远离自我。
Ⅱ)
阅读停在第二部分倒数第三段。为什么留下两小段不读完,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先说说这部小说是如何生发的。当然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部内心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了。这很重要,这决定了你怎样看它,进而,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看到多少。图森是否有意把它往侦探小说的误读之路上写呢。我不确定。因为我不确定图森的邪恶指数。《迟疑》可以很善良,可以是一次忧伤的调情,也可以很邪恶,邪恶到对忧伤来一场冷嘲的诀别。我想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经验,你对很在意的某个人,或者干脆,你爱的某个人,会有神经质式的妄想,你会强迫症似的持续守候在他常出现的地方,当他跟某人讲话,你会疑心他在谈论你,他的书忘在桌子上,你会妄想这是他在给你的暗示,好让你把书送给他借以亲近你,他微笑着向你走来你会以为他要给你来个拥抱实际上他只是想到了昨晚做的那个滑稽梦。好了,不必再罗列了,我只是想说,如果你把对这类人的一堆情感,或者对一堆人的这类情感,包括怀疑,嫉妒,热望,忌恨,等等,揉进一个人,编进一部小说,它就是属于你的《迟疑》。这种妄想的特征在于,一,无逻辑,二,偏执。既然要见比亚基,既然去了他的房子,为什么不等到他回来?既然比亚基躲着你,为什么又处处留线索?这是无逻辑(有意思的是起初我一度把比亚基误读成了戈多),“我”为何有信心对比亚基做这一通乌有的编排,不顾有时对一个细节的妄想会前后矛盾,这是偏执。以上,我假定图森怀有和我们一样单纯的意图。《迟疑》只是还一个梦。但图森写《迟疑》时已经三十三岁了,他真的愿意忍受这华丽到腻味的冒险吗?还是这只是他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读者的一次玩笑式的邀请?“我嘛,既然也这样经历了三十三年,我不会再幻想我的什么本性,因为我刚满三十三岁,是的,这是告别青年的年龄。”这是第二部分倒数第三段的结尾。它显得突兀,和之前为内心吐丝结茧的努力似乎相冲突,它突然中止了我的阅读。它在直呈内心吗?“我”的本性是哪个?是每次窥探都恰好不被打断(除了孩子,这一点下面再说)的妄想狂?是从他者——旅馆老板,儿子,汽车里的男人,甚至从死猫,信,奔驰,如果它们有感觉的话——看来实际上只是一个神色怪异的路人?“我”在小说中是分裂的,一半和乌有的比亚基周旋,怕他甚至想在幻想中杀死他(这种经验我们也有,你梦到过杀死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吗?),另一半扮演一个远道而来看望老友的旅馆房客,就像你在旅馆见到的任何一个中年男人。有趣的是,图森竟然能使这两个世界并行不悖。他的内心不期望与外部相对应,这是他和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的距离。他仅仅就是妄想,妄想之上,老老实实的活着。不去干扰别人,别人也不能打扰这妄想。小说至此几乎成了图森的逃遁之地。而就叙述来说,他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因为假使像福克纳的那样,内心是外部的起讫点,则必须忍受不可避免的打断。就像昆汀坐在车上,听到声音就想起和班吉凯蒂的对话,然后,钟进入他的视线,意识马上转向父亲关于时间的一番哲论。图森在此设计了一个现实的挡箭牌,孩子。当“我”站在十六号房门口望着长焦镜头,随时可能被他人打断时,孩子的哭救了场。你能忍受被一声“你是谁,在我的房门口干什么!”打断吗?那样,“我”的妄想也许将丧失在我们心中的同情。(当然,除此之外,孩子还有个更重要作用是缓和叙述,像潜久了水要浮出水面喘口气。)这一场内心潜游,谁都不想中途退场,尽管有时闷得慌。
Ⅲ)
图森在结尾给了他自己内心的幽魅一枪,借比亚基的管家射出。然后,他怕幽魅还没死,又补上一枪,正中脑门,死猫的阴影消散。其实子弹已在第一次看见渔夫时就上好了吧?但幽魅彻底死了吗?不一定。它仍在籍着未被曝光的细节分裂,期待去找另一个附体,进行下一场狂欢。
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