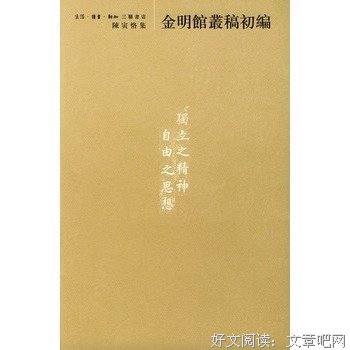《金明馆丛稿二编》读后感100字
《金明馆丛稿二编》是一本由陈寅恪 著 / 陈美延 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3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明馆丛稿二编》精选点评: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多短篇,亦精品。
●陈寅恪的中古史著作我这个门外汉也能看,而且还挺喜欢看的,真是有点意外。据陆扬(美国)的观察,我这种情况还挺多见的,这是因为陈的论文常给出非常截断的观点,很能吸引人。就我个人来说,似乎有这方面的因素,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陈的不少论文题目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比如李白的出生地、桃花源、齐地神仙传奇等等。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承认内亚对中原的殖民史,承认蛮族之优,中原之劣,他老是第一人。
●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
●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师
●经典著作,学习
●大学初入时候,因为对陈先生高山仰止的感情读了一系列之一。。。看来我还是天生的文博学生,专门做历史没有长性。
《金明馆丛稿二编》读后感(一):录文|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
按,本篇刊于《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1932年第2卷第4期,第404-405頁。又載王靜如:《西夏研究》第1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單刊甲種第八,1932年。又編入自印講義《敦煌小說選讀》,後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此篇题目作“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研究》本作“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研究》本之广告作“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考釋序”。以 《集刊》之標點錄文;「洵」《研究》本作「詢」;
《金明馆丛稿二编》读后感(二):含金量極高的論文
陳先生的書很難讀,很難懂,但就我能理解和讀懂的那部分而言已經是超值了,買這套書很值得!最近讀他的論文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這也是一本含金量極高的論文集。幾乎都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考證文章,但是每篇短的文章、考證,背後都是為了更大的思想主題服務的,所以跟乾嘉考據學為了考證而考證不同,是有思想的考據。更不用說那些紀念王國維先生而寫的文章展示了陳先生的自由思想學說,那些為別人而寫的書序也大多富於學術思想,可給後人許多學術思想方面的啟發,我不禁感嘆:真是含金量太高了!今天著作等身的教授很多,可是大部分著作還不如陳先生一兩篇嚴謹的論文,可歎學風至此,陳先生若在生當如何為今日大陸之史學感到痛心疾首乎?
《金明馆丛稿二编》读后感(三):金明馆丛稿二编
读一编时,觉不甚了了。今初参二编,始窥其一斑,蓋若负鼠汲海。方悟大家深邃,非平凡人可以遽量。
104,105,汉人八种,代指北方。南方有专名,谓“囊家歹”(Nangiad-ulus)者是。 146,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合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蓋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徵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167,蓋武曌政治上特殊之地位,既不能于儒家经典中得一合理之证明,自不得不转求之于佛教经典。而此佛教经典若为新译或伪造,则必假托译主,或别撰(音赚)经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书更难取信于人。仍不如即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为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为事半而功倍。由此观之,进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篡改者,其说殆不尽然。
182,“道”之一字,取诸老、庄。蓋佛经初译,字意未甚磨合,后以“末伽”(marga)易“道”,而“菩提”易“觉”。玄奘法师以为“佛陀”天音,唐言“觉者”。“菩提”天语,人言为“觉”。若以“菩提”言“道”,则人法两异,声采全乖。更进强调:“菩提”言“觉”,“末伽”言“道”,唐梵音义,确尔难乖,岂得浪翻,冒罔天听!…《大智度论》:佛常居中道。
238,《高僧传贰鸠摩罗什传》: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管锥编》:嚼饭与人、点金成铁、驴蒙狮子皮、以此种乐器演奏当由别种乐器所谱之曲调。)什公为照顾读者认知,不得不割舍原文精确词义,替换为秦人通可表达。譬如:犹如蚊子翅。扇于须弥山,虽尽其势力,不能令动摇。此处所译“须弥”梵本一作mandara,一作vindhya,蓋此二名皆秦人所不知,故易以习知之“须弥”,使读者易解。陈寅恪:凡此诸端,若非获茲贝多残阙之本,而读之者兼通仓颉(音结)大梵之文,则千载而下,转译之余,何以知哲匠之用心,见译者之能事。斯什公所以平居淒怆,兴叹于折翮。临终愤慨,发誓于焦舌欤?
301,安禄山,侯景,郭药师。302,无赖,赖:善。
《金明馆丛稿二编》读后感(四):【读品•考辨】郑幸: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札记
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有《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由陈寅恪先生整理收入《明清史料》首本第一册,涉及明清鼎革之际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议和秘史。按此“残本”原题“高鸿中奏本”,后其下半段为近人发现,一并收入《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
据陈先生分析,此本当奏于明清松锦战役之后,即崇祯十五年(1642)。先生随手勾辑《明史》、《清史稿》相关纪传文字,得此结论甚妥。我等后学,惟步武前贤,广征先生所无暇征之旧籍,聊作一二补充旁证。
先生所引《清史稿•太宗本纪》叙此事甚简,兹引《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九相印证:
崇德七年三月癸酉,围杏山。郡王阿济格奏报:“明国订于三月初四日遣人讲和,迄今未至。”……乙酉……奏云:“明国差总兵二员、锦衣卫官一员、职方司官一员至王贝勒前,欲求讲和。赍来明主敕谕一道,云:‘据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上览毕,亦降敕一道,谕诸王贝勒曰:“阅尔等所奏明之笔札,多有不实。若谓与我国之书,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况札内竟无实欲讲和之语,乃云‘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等语,此皆藐视我国,实无讲和之真心。”
又关于敕书,谈迁《国榷》卷九十八所记略异,兹一并相引,以为佐证:
崇祯十五年正月……丁丑……得敕曰:朕闻沈阳有罢兵息民美意,向来沿边督抚,未经奏闻。又云:朕不难开诚怀远,如我祖宗朝恩义联络之旧约。抚赏减旧额四十七万。建虏喝竿见之,谓历朝敕书,在属国皆龙边笺黄色。而此笺色采,中横一龙。且往时玺方,其篆敕命之宝,而今皇帝之宝;稍长,右角微挟一线。遂具书谓边吏伪作,并怒敕中语。马绍愉以闻。
又《崇祯实录》卷十五于此事所记虽略简,但亦有所补充:
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绍愉偕参将李御兰、周维墉至宁远,闻于清,请敕为信。乃复请于朝,敕曰:“朕闻沈阳有罢兵息民之意,向来沿边督抚未经奏闻。既承讲款,朕不难开诚怀远,如我祖宗朝旧约,恩义联络,永为和好。”清得之,以为边吏伪作,并怒敕中语。绍愉闻之。
三段文字所记,略有出入。首先是出使的时间。《清史稿》与《清太宗实录》均记为“三月乙酉”,即三月十六日,《国榷》、《崇祯实录》则均作“正月丁丑”,即正月初七。然而作为受书方的清人既云三月初四仍未至,则此处所谓“正月初七”便极为可疑,或为明使出发之日而非到达之日。
以上为明官员第一次出使,因清疑有伪而作罢。使臣马绍愉旋即返回,又于同年五月再度入清和议。《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六十一记崇德七年议和事云:
五月己巳朔……奏言:“明国遣兵部职方司员外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鲁宗孔,游击、都司、守备八员,僧一名,从役九十九名,在宁远城,欲来见皇上,以求和好。”是日上遣兵部启心郎詹霸、内院笔帖式叶成格、石图等前往谕之曰:“闻明国差官已至宁远。尔等至彼处,令每翼章京一员、每旗护军十名偕之来。……若至我境,按人给以羊只。将至京时,尔等先来报闻。”
六月己亥朔辛丑,赐明国议和使臣兵部职方司员外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鲁宗孔,并天宁寺僧性容,游击王应宗,都司朱龙,守备乔国栋、张祚、赵荣祖、李国登、王有功、黄有才等貂皮银两有差,役使九十九人亦各赐貂皮遣还。上命大臣送至十五里外,设宴饯之,仍以书报明国。……至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交相庆吊。每岁贵国馈兼金万两、白金百万,我国馈人参千斛、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愿如书中所言,以成和好……尔速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来,予亦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往。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
两段文字,明确记载了马绍愉一行第二次议和的行程,即于崇德七年五月初一到达清境,又于次月初一返回,恰好相隔一月。其间清廷对马绍愉一行盛情款待,大大出乎明人意料。事实上,在明人想象中,议和之臣必遭冷落甚至辱骂。这一点可以从相关的明人记载中略知一二,例如《国榷》卷九十八记曰:
或云:绍愉至塔山高台堡,宴建虏使者,议不及开市。问之,曰,待老憨命也。喝竿至义州,责诸臣私通,欲杀使者。绍愉走免。盖我旧将孔有德沮之,俟粮刍至仍进兵。
这种说法与前及史料记载可谓截然不同,然而并无确切根据,当为时人对于议和之事一种想当然的推测,相反,盛待之说则有不少史料作为旁证。最为可信的,当属马绍愉两年后致吴三桂之书信一封(收入《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
前年不肖到沈阳,极承大清先主宏仁,今闻仙逝令不肖涕泣感伤。又诸王盛情每日款礼之隆.三十里外迎送之厚,又三位老先生朝夕高雅,真是异国一家,如同兄弟。
信中所述,或有阿谀夸大之嫌,然而基本情形当不差。此外,尚可以朝鲜人所作《沈馆录》卷三所载作为旁证:
五月二十三日状启……和使方为留在,接待之事极其优厚,是如为白乎旀。和使四人,内一人则宗室而职兵部郎中,二人总兵,一人则副总兵,且僧一人亦为偕来,此则前往来议之人也。使臣等出来时载持米太四十余车,盖虑此国若不许待供馈,则以此为粮资之计。
可见,在出使清国之前,连明使自己也作好了受到恶待的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与前及《国榷》所载是比较符合的,应该也大致代表了当时明人包括明朝廷的想法。这种略带惶恐的揣测,当源于对此次议和的极度不自信。毕竟此时明清战局已今非昔比,明人此去实为求和,而非议和。然而皇太极还是对议和倾注了极大的诚意,甚至不惜力排众议促成和议,其《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云:
后来复命会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绝非虚语。朕初以彼之请和,不过巧诈诳诱,欲免锦州四城之难,亦未深信。今复遣官至,朕思四城已破,十三万援兵已尽,加以饥馑洊臻、寇盗蜂起、流贼转炽,盖迫于不得已不和耳。……彼既请和欲共享太平之福,亦朕之夙愿也。据诸王贝勒等,咸谓明之国运将亡,正宜乘此机会攻取燕京,安用和焉。但念战争不已,伤民必众,朕心实有所不忍。
事实上,此次和议对于明朝而言是有利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分析,以连山一带为界,相对于高鸿中奏议及祖可法、张存仁所说的以黄河为界而言,还是比较合理的。明朝若能好好利用这次议和机会,或许尚得苟延残喘,以待重整旗鼓。
然而此次议和终因明人陈新甲泄密导致崇祯颜面无光而告失败。对此,除陈文所引《明史》陈新甲、杨嗣昌传外,尚有不少资料涉及,互为印证,亦颇为有趣。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再一一展开,有兴趣的可参考《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崇祯实录》卷十五、《明史•徐石麒传》等相关记载,均记录议和一事由崇祯授意,然而为陈新甲泄漏;崇祯恼羞成怒之下,将其治罪,此事遂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此事,民间则另有说法,与史书记载可谓截然不同。李逊之《三朝野纪》卷七“崇祯朝”就将崇祯嫁祸陈新甲一事说成陈新甲自作主张引起圣怒。从这一点来看,崇祯对外显然一直竭力遮掩其议和意图,并且颇为成功。至此,在和与战的政治漩涡中,陈新甲便并不无辜地作了其间的牺牲品。优柔寡断的崇祯帝也终于丧失了最后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