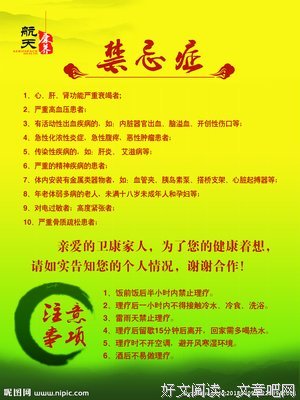《禁忌》影评精选
《禁忌》是一部由米古尔·戈麦斯执导,Laura Soveral / Ana Moreira / Teresa Madruga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禁忌》影评(一):《禁忌》
一个主人公,两段故事,三分结构。
开始以为是关于非洲神秘主义,中间演变成关于孤寂的艺术闷片,最后被拉回到最“俗”的虐恋故事。
影片一改我对画外音的偏见,只要有真正恰当的视觉风格,画外音未必喧宾夺主。
“失乐园”“乐园”两部分“日月”时间结构的不同以及叙事风格的两极化,使得整个影片具有非常强烈的落差感。
《禁忌》影评(二):黑白的复古情调,淡淡的讲述。
黑白的复古情调,淡淡的讲述。导演太文艺,太自我。
导演通过倒置的结构和结尾的延伸,加入了更厚重的历史和人文内涵,影片也蒙上了类似史诗的成色!他真正想指涉的是那段不应被忘怀的殖民史。影片的形式很有意思,尤其是后半部分对“回忆”的讲述:文学式的旁白、默片一般的表演、调度和配乐,都充满了怀旧的意味!但是拜托能不能多点对白?和观众的交流太少了。
《禁忌》影评(三):失乐园
开始以为是关于非洲神秘主义,中间演变成关于孤寂的艺术闷片,最后被拉回到最“俗”的虐恋故事。 影片一改我对画外音的偏见,只要有真正恰当的视觉风格,画外音未必喧宾夺主。 “失乐园”“乐园”两部分“日月”时间结构的不同以及叙事风格的两极化开始以为是关于非洲神秘主义,中间演变成关于孤寂的艺术闷片,最后被拉回到最“俗”的虐恋故事。 影片一改我对画外音的偏见,只要有真正恰当的视觉风格,画外音未必喧宾夺主。 “失乐园”“乐园”两部分“日月”时间结构的不同以及叙事风格的两极化
《禁忌》影评(四):这并不是法国女导演Claire Denis镜头下的非洲
这部电影拥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开场:摄影构图、古典配乐、诗意旁白和虚构方式,做得相当别致。当然,如果能坚持住前一个小时三个中老年妇女的冗长对白和蹩脚情节的话,后面的第二个故事保证让你精神百倍,惊喜连连。
这并不是法国女导演Claire Denis镜头下的非洲,尽管不免仍存在着种族问题和政治暗示,但所有这些“谑头”都完全让位于一个疯狂而禁忌的爱情故事。听起来相当俗气和老套,然而导演Miguel Gomez处理的手法却让我大开眼界:对白声音完全隐去,只看见演员的嘴巴讲话,却留下自然环境和角色动作及歌唱的声响。这种近乎默片的处理却始终贯穿着诗意的旁白,令整个叙事层面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尽管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黑白电影。
《禁忌》影评(五):《禁恋》Tabu_爱有徒劳
《禁恋》Tabu,又一2012年佳片(2012年真是极品影片多产的年份)。
本片前半(part 1)像反映当代南欧社会阶层、(殖民)历史的暮年日志(没有爱的失乐园,我们真空的当代生活);后半变成白人噤声的白人罗曼史。实验片、旁白与黑白默片对位;老歌、配乐和略带蓝绿色的黑白胶腃都有惊人的质感。
我们的长辈中(上个世纪台海两岸的分隔),有多少人渡过了没有爱的二十世纪,困在虚无中遥想往日的天堂乐园。
然而在这部影片中我看到的是,二十世纪初的浪荡不代表当时的世界更像天堂乐园般美好,让人们欲罢不能的爱上、让宿命论有机可趁。 通过一场男女间的禁恋,“记忆变得有限,世界却更加永恒”。
在任何一个人(出生、迁徙、流离、失魂、沉沦)之前,都有一段受框限
(好比大银幕的景框)的历史/记忆,影响着他们无限的未来。
《禁忌》影评(六):禁忌
按照影片的时间轴,这个故事基本是这三部分构成: 开始是文图拉为了逃脱自己,踏上远征,去冒险以期远离皮拉,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正如精神上“死亡”的奥罗拉所说“世界再大,你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心”,最终他义无返顾的跳进了有鳄鱼的水塘,他知道他逃避不了,而鳄鱼正式二人最初相识的见证,当然鳄鱼是高明的猎手,会将多情的人拉入欲望的池塘,淹死。 接着,镜头拉回到现实,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电影中的电影,之后不久出现了标题“失乐园”。《失乐园》本是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首叙事长诗,描写撒旦如何引诱夏娃偷食善恶果而被驱逐,失去乐园的故事。这里采用这样的标题,也是应和了现实的生活,皮拉离开了非洲,永远的失去了乐土。并且这种失乐有很强的的精神性倾向,并非因为现实的物质性贫乏,而是精神的驱逐,这种驱逐是我们与土地失去联系,就如从母体剪下脐带一样,享乐不再。而且这种失乐不仅仅是奥罗拉,她的好邻居皮拉,女仆人桑塔以及她的昔日情人都生活在这片废土上,直到奥罗拉的死亡,文图拉的谈话引出了回忆——那段昔日的禁恋。 除过一些背景介绍以外,故事很简单,文图拉爱上了已婚并怀孕的奥罗拉,而且奥罗拉也深爱他,而两人明白这段恋情是不该发生的,却也是越陷越深。直到奥罗拉失手打死了文的好友,被丈夫追回,两人分开了。两人很默契地约定彼此不见,终老一生。 在一般眼光里,这份爱是禁忌。这种婚外恋是要上道德的绞刑架的,人们似乎习惯性的举起伦理的大枪将全部的子弹倾泻而出,尽管通常他们不知道到底在打什么。我倒是觉得这种禁忌的爱是触到了爱的底线的,爱的底线是婚姻,或者说是婚姻带来的禁锢性力量。婚姻可能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但绝对是爱的禁忌。那个老宅男康德给婚姻下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定义:婚姻是男女双方合法使用对方性器官的工具的契约。爱通常在签约的时候到场了,后来常常是一生的缺席。当婚姻被定义为契约时,就从一种吸引的爱的聚合力量沦为了为了达成目的的约定。而且因为是契约,就可能存在各种违约,因此道德和法律很多就是为了为这份契约提供某种保障,真可悲! 触碰到婚姻的爱显然让当事人违约了,所以就会付出代价,并以此惩戒后人要遵守约定。这是禁忌,你要记住!不,算了吧,我宁愿嫖妓,也不会结婚!老康德如是说。
《禁忌》影评(七):电影的迷人性(三):作为机制的“若即若离”
导致《战场来信》和《横风之中》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都将画面与声音放置在同一重要的地位。当这两种殊异的感知方式以同等强度作用了观众的感官,困惑与错乱便发生了。像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电影作出的典范中,画面的空与声音的实形成了一种不对等关系,这便形成为距离。我们可以说,电影的迷人性正是来自于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即产生于有距离的两者然而又未彻底分离的情况。表现在电影中,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及的声音与画面的分离,还有另外两种“电影迷人性”的创造机制:人物情感间的疏离、摄影机与物像的间离。
孤独意味着无法融于群体,与他人产生距离;这种情感上的疏离在沟通过程中加剧。由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开创的现代电影中,集中展现的一个现象是人的情感在现代化工业社会环境中变得茫然无所适从,为了从外部世界抽身而出,只能退隐回自己的天地。这种内在选取的距离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而对于摄影机和物像间的间离,则是一种观察视角,是镜头获得的一种无意识。它既没有冰冷如一台机器记录着物像的运动,也没有试图创造一种代入感引观众身临其境。比如在阿彼察的电影中,摄影机与物像间产生了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从而让影像获得觉知的迷人体验感。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画面与声音间的分离获知的影像迷人感。这不仅可以在玛格丽特·杜拉斯所创作的大多数电影中看到:《卡车》中发生于室内的剧本朗读与室外卡车行进场景的潜在影像处于断裂而又维系着的状态,对影像的欣赏是在想象中完成,在《印度之歌》《夜船》《阿伽达或无限阅读》等这几部作品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方式;在另一位比利时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早期作品如《家乡的消息》《安娜的旅程》中,我们也能寻见产生电影迷人性的相同的制作方式。
这三种情形,现在可以在一部作品中悉数看到:这便是米古尔·戈麦斯的《一千零一夜》中。虽然在前作《禁忌》中,疏离的情形显得更加明显又有效,这些影像因为这个爱情故事的疏离散发迷人气质;而在《一千零一夜第二部:凄凉之人》中,《迪克西的故事》实践了第二种机制,摄影机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间离视角;到《一千零一夜第三部:迷醉之人》中,通过字幕条的加入,声音与画面间产生出三重距离:字幕条与画面、画面与画外音、画外音与字幕条,更进一步加重了影像的迷人气息。
《禁忌》影评(八):为何禁忌?
按照影片的时间轴,这个故事基本是这三部分构成:
开始是文图拉为了逃脱自己,踏上远征,去冒险以期远离皮拉,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正如精神上“死亡”的奥罗拉所说“世界再大,你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心”,最终他义无返顾的跳进了有鳄鱼的水塘,他知道他逃避不了,而鳄鱼正式二人最初相识的见证,当然鳄鱼是高明的猎手,会将多情的人拉入欲望的池塘,淹死。
接着,镜头拉回到现实,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电影中的电影,之后不久出现了标题“失乐园”。《失乐园》本是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首叙事长诗,描写撒旦如何引诱夏娃偷食善恶果而被驱逐,失去乐园的故事。这里采用这样的标题,也是应和了现实的生活,皮拉离开了非洲,永远的失去了乐土。并且这种失乐有很强的的精神性倾向,并非因为现实的物质性贫乏,而是精神的驱逐,这种驱逐是我们与土地失去联系,就如从母体剪下脐带一样,享乐不再。而且这种失乐不仅仅是奥罗拉,她的好邻居皮拉,女仆人桑塔以及她的昔日情人都生活在这片废土上,直到奥罗拉的死亡,文图拉的谈话引出了回忆——那段昔日的禁恋。
除过一些背景介绍以外,故事很简单,文图拉爱上了已婚并怀孕的奥罗拉,而且奥罗拉也深爱他,而两人明白这段恋情是不该发生的,却也是越陷越深。直到奥罗拉失手打死了文的好友,被丈夫追回,两人分开了。两人很默契地约定彼此不见,终老一生。
在一般眼光里,这份爱是禁忌。这种婚外恋是要上道德的绞刑架的,人们似乎习惯性的举起伦理的大枪将全部的子弹倾泻而出,尽管通常他们不知道到底在打什么。我倒是觉得这种禁忌的爱是触到了爱的底线的,爱的底线是婚姻,或者说是婚姻带来的禁锢性力量。婚姻可能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但绝对是爱的禁忌。那个老宅男康德给婚姻下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定义:婚姻是男女双方合法使用对方性器官的工具的契约。爱通常在签约的时候到场了,后来常常是一生的缺席。当婚姻被定义为契约时,就从一种吸引的爱的聚合力量沦为了为了达成目的的约定。而且因为是契约,就可能存在各种违约,因此道德和法律很多就是为了为这份契约提供某种保障,真可悲!
触碰到婚姻的爱显然让当事人违约了,所以就会付出代价,并以此惩戒后人要遵守约定。这是禁忌,你要记住!不,算了吧,我宁愿嫖妓,也不会结婚!老康德如是说。
《禁忌》影评(九):不浪漫的虚无现实
(观后感)
也许是因为最近考试多沉下心来了,拿到碟后便塞进电脑里播放,全程大屏幕没有别的小动作。但让我专心的更大原因是它一开始就吸引了我。当配乐钢琴曲响起,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就开始大赞“天啊这配得太棒了”。
序言部分十分有趣,死去的妻子突然出现在探险家的面前,告诉他他的灵魂没救了。他也觉得自己没救了,就慢慢走入有鳄鱼潜伏的池里。镜头没有让我们看见他被吃的样子,也没有让我们听见任何惨叫的声音,只是对准了岸上的非洲土著们。土著们有老有少,排成队伍看着池子的位置,而后突然跳起风俗舞来。
当以为整部电影都是这种荒诞意识流风格时,突然切换到Part One.一个女人孤零零地坐在电影院里哭。而后讲一个好心的孤独的女人和她好像疯掉的孤独的女邻居的故事。
有人说Part One是不必要的,或者说是沉闷的。但在我个人认为,令我决定认真看下去的、拍手称绝的就是Part One. 先不说导演如何用黑白把那种至深的无奈和孤独拍得淋漓尽致,如若没有Part One, Part Two 给人的感觉不会那么强烈。
当一个女人老了,老成满脸皱巴巴、会说‘疯话’了,不是总有个男人跳出来说“我就是喜欢你岁月沧桑的样子”的。甚至连个至亲的人都没有陪伴在身了。如果不是那好心的女邻居,可能这个故事就会随着另一个被视作疯了的老人的逝去埋在那疗养院的地底里了。那些最后的胡话说什么鳄鱼呀,猴子呀,非洲黑奴呀全是曾经存在的东西,是记忆里的东西。可谁会相信呢,一个会变卖自己的大衣跑去赌场的老女人?她曾经是那么英姿飒爽的女猎人?她曾经拥有非洲农场?她居然有过那么浪漫那么痛苦的恋情史?她曾经那样美?
老男人还会给人一种年老的独特美感,老女人也许就只给人一种神经质和絮叨的形象了(至少电影里是如此)。再怎么浪漫的恋情,在现实里过着日子也就消磨了,消磨成一个看上去仅留存着表层皮肤的人了。就算你以为时间会留下些什么,但那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只不过是脸上的沟沟壑壑。
女邻居好心得不行,好心得会为了并不多熟悉的邻居担心得心神不宁,日日为她的邻居祈祷。好心得明知道那个从波兰来的Mary不想在她家住,虽然她准备了胡萝卜蛋糕和满心期待,但她还满不生气的给了她礼物。她好心得会去找那不相识的邻居死前想见的男人。换来几句话——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善良的人。而她情感丰富,看电影常会落泪。但她最终也是自己孤零零一个的,只是她在意着他人,似乎丝毫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她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而现在的她已经会把手机忘在冰箱里了。她拒绝了那个不知所谓的画家,但看上去她似乎已经不想再忍受孤独了。但她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都不知道。
于是现实的问题就净剩下一些生活费、恶习、别人的画要不要挂在客厅里的琐碎小事。现实里没有非洲,没有农场,没有一堆堆的娱乐活动,没有奢侈的消遣。浪漫在过去真实地发生过,但放在现在来看那样虚无。
对比于那个爱情故事,我觉得这种对比更让人觉得揪心。
art Two 有几部分让我看得昏昏欲睡。但让我扭转态度觉得Part Two也非常精彩的一段是,女猎人看着扭结在地上的另一个人和情人,拿出手枪射杀了那男人的时刻。可以看见她的表情。我连呼吸都不敢了。这一段真是太棒。其余的也就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触犯禁忌的。浪漫的东西看得太多了,明明两者都能在现实发生,但不浪漫的东西反而能死死地让我觉得难过。
也许是因为我活在不浪漫的虚无现实里?
对啊,而且年轻的我那全部的甜蜜或苦难,看起来都像蒙着一层薄雾一般,模糊不清了。
《禁忌》影评(十):易逝的云
葡萄牙名导米古斯·戈麦斯执导的《禁忌》(又译《忌讳》2012年),与默片大师茂瑙电影同名。片名撞车不重要,关键是有否新意。这部《禁忌》所透出的黑白沉静风格,颇耐人寻味。该片被《电影手册》评为2012年十大佳片,还被英国《视与听》评为2012年十佳。葡萄牙电影中的寻思与安详,简约与沉稳,都是其所独有的。如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歌那样经得起岁月的磨砺,且愈久愈闪发光芒。
奥罗拉是居住在里斯本高级公寓的一个风烛老人,她疯疯癫癫,一会要黑人女佣盛塔帮她找邻居皮拉,一会向皮拉投诉盛塔给她施巫术,让她痛不欲生。久而久之,奥罗拉只信任皮拉。作为中年女人的皮拉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日子过得也不顺心。后来奥罗拉不行了。弥留之际,让皮拉叫来一位名叫吉安·卢卡·文图拉的老头。
老头一来,女老人就走了。安葬了奥罗拉后,皮拉邀老头一起喝咖啡。老头这才讲起他与奥罗拉的一段禁忌之恋。奥罗拉本是里斯本旺族,年轻时随父母到非洲开发,有一农场。父母去世后,她打点这一切。还喜欢上狩猎,枪法神准。不久,就爱上一个从德国来的小伙子,结了婚。她还投资拍过《乞力马扎罗雪山不再下雪》的纪录片。后来,文图拉作为一乐团成员来非洲采风游历,就住在她附近。奥罗拉有一小鳄鱼,跑到文图拉那。二人认识后,渐生情愫。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毕竟这种爱是遭人忌讳的事,纵然在非洲荒原。
二人甜蜜地躺在草丛,对着蓝天中的鳄鱼云,尽情比划着。鳄鱼云只是一种想象,看似美妙却极易逝,还隐匿着凶机。这也预示着他们的爱情。事实也是,愈爱愈让文图拉生活在恐惧中。后经好友马里奥相劝,遂随乐团回到欧洲。如此一来,二人只有鸿雁传书。奥罗拉说你是我唯一爱的人。而文图拉说你带给我的美梦,却让我无法面对现实。爱是难以忍受的,越抗拒越不可违。他们还是难以割舍。谁也放不下谁。影片的对话极少,大都是老头的画外音,如同黑白默片。
待再相见时,奥罗拉已是挺着肚子的女人。怀着老公的孩子,却跟文图拉爱得死去活来。难以置信又无法安稳,遂二人私奔,途中误杀了好友马里奥,奥罗拉还产下女儿。最终二人彻底分开。之后,奥罗拉老公去世,她回到里斯本。她依然爱着文图拉,但没能再见面。值得玩味的是,面对当年这一禁忌之恋,半个世纪后,老头平静地讲述这一切,犹如在述说别人的故事。这或许就是面对时间的无奈吧。
2013、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