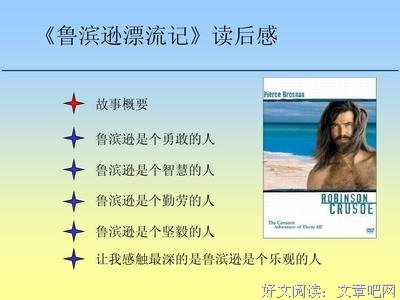勇敢的人死于伤心读后感1000字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是一本由云也退著作,理想国·九洲出版社出版的376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202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读后感(一):读后感集
正经的说,仅以部分书籍作为参考而言,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多数都挺不错的。这当中也包含这本书。
书名就挺有吸引力的,再加上那句围绕“文学”的赘述,挺有阅读感的。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不光涉及到文学方面,有不少章节还涉及了到了哲学与人性的思考。总体这本书其实更像是各类作品的读后感。而每篇读后感的开头第一段往往浓缩了更多的精华。让我很期待每一篇文章开头的那段读感。基于此,书中值得记录和学习的地方就显得甚多。不过有个问题还真得琢磨琢磨。为何纪德就比波拉尼奥矫情呢?通过文章了解到纪德这都如此没心没肺了,哪还有功夫去矫情那些有的没得呢?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读后感(二):一事无成之中,人变得高贵起来。
我甚至可以读出作者写作的节奏,读出哪些是一气呵成,哪些是拼凑,哪些是应景,哪些是一段落。这是一本太自我的书,是把自己袒露出来,又想隐藏在感受中的作品。作者特别像旁观者,既像加缪作品中那个,也想现实中的,始终以旁观者的角度在写。作者对海明威的态度,对待卡夫卡的态度,对待加缪康德拉的态度,截然的不同,看出对人生的冷旁观无意义且不愿附以意义,从我的观感,是厌世但又有些看不出来的留存的理由。作者上本书我也看了,起码在我的阅读范围,这种疏离感是我能跟随且对自我部分内心安抚的。但是整本书实在表现出太强烈的个人,特别的主观,有点不适感,但这种通过书评的表现形式,写出本小说和自传的写法,我是喜欢的。
我买的是签名版,从书名到签名,能感到作者对世界的看法,有人说作者对文学的诚挚,说实话,我认为不是真诚不真诚的问题,而是作者作为他自己是何人以及他想的表达的问题,与书无关,只和他自己有关。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读后感(三):编最不乐观的瞎话
当人幸免于彻底的胆怯 看了目录才知道,“勇敢的人死于伤心”这个名字其实是其中一个小章节的名字。顾名思义,在感慨我们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而勇敢面对之际,这个世界是由最后我们还是活下来的人构成的。活下来的人以谦虚的态度证明,无论有什么疏漏,我们依旧要把生活的中心无条件交付给一颗勇敢的心,并且乐于体验这份勇敢的存在。就像是不可分割的器官烙在人们身体中的功能与风格,组建成一个健全的自己。维系着做出承诺之后的恣睢,我们理想中不顾后果的勇敢可能是失心疯的来源,也可能使得我们有遭不完的罪。但它帮助我们在沿途风景不可胜数的路上所呈现出的决绝与毅力,回头一眼可见。我们没有故作深沉,可是勇敢就是那么从身体中冒出来,随后变成我们疲劳,匮乏的时候桀骜的面具。赶走了心理上蔑视阴霾,但也不再留挽任何宝贵纪念的戾气。 在作者讨论众多没有像聂鲁达那样风风光光的流亡者时他说,“流亡是内心的事情,一个吞下去的动作,是面对千丈深渊时喉头的一声哽咽,可以不提但不可伪饰。流亡者对缺席比对在场更敏感,他们总是在观察,寻找倾听和倾吐的合适对象。”流亡所对等的严峻对我来讲必然是匮乏,就像北漂那种朝夕不保的失重感,无法在谋生和确保未来无忧之间做出选择与平衡。一点点偏狭就会妨碍我们的理解,导致我们在迷惘间变得堕怠。贴切于流亡者身份的不是某个具体历史事件,而是睁开眼就需要解决的事实存在,在匮乏中忘记多年以后慵懒的午后,病恹恹的过去寄出去的信件,一头钻进去知道生活给我们回馈了见识与理解。坦然接纳流亡者自身的命运,就像是保护自己免受弱点所拖累那样,真正有意义的保护是尊重我们所在的恻隐状态。我们依旧能够接触到值得我们哀伤叹息的事物,这些事物的无常不会给我们的现实造成冲击,但它会真真切切的影响我们对于自我的判断,对即将到来之势的揣摩。 流亡意味着我们痛失掉整个生命能够回归的路,曾经它是那么明确的指向未来,那么短暂的指向死亡。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眼下的书籍,以及电脑屏幕上人们正因此担忧的事物。人类的童年发生在正要结束的路途中,而我们也渐渐发现我们的声音成熟起来,成熟而标准,像是媒体上偶尔喃喃自语的复刻。但是我们总是绕不来孕育着我们所有思想的故土,眼下它不仅不衰老、贫乏、苍白,但试图将我和它的现状维系在一起。我想是人都不会反感这种联结,它相当的抚慰人心,像是生命中最好的旅伴,知无不言的将另一个世界的姿态以非常平静的方式带给我。这不是重生的可能,是平行于我们感慨的另一种延续,一种双重的个人状态。我们保存好对惦念的试探最后划分给一种双重的叹息,为了我们曾向往的逃离后的事情。尽管那些试探都对我们怀疑无力而松散。 藏在隐秘的自我规劝中 大多数人的生命都会终结于诚实,人们在弥留之际无法说出一个弥天大谎而博得好感,体面的方式就是与自我以最真实的方式和解。但所有人是以痛泣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狡黠的眼泪从我们的脸颊上滑落,没有任何语言表达出我们不怎么情愿来到这个世界,分担这个世界人类局促的时刻,空虚的时刻,恐惧的时刻,最后才是满足的时刻。起初的人类心满意得正是钻进安稳的怀抱,而现在人们都要在人类的童年里找到自我价值的蛛丝马迹。那正是微妙而浓烈的时代气息,人们以委婉的方式避开了传统与整体性的混淆,坦诚与暴露的分歧,最后我们对自身的境况越待越明。可能我们会因错失一刻的命运而惋惜,但我们会以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所有的混淆与分歧都会流动,而且和解。 我们还会勇敢的捕捉到时代明媚阳光下的侧影吗?那种在现实中基于逃避的方式而被我们忽视的过程就隐藏在我们记忆的死角处。人们短暂的停歇是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漂泊者,流亡者,逃离者,被遗弃者,最后是不是只是小撮人,我们不乐于把这种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人们会辜负整个社会的动荡,它没有在自己那里发生关系。大家也都不曾给别人说明自己在某个时代的冷清与荒凉处所感受到的那种深刻的迷惘。直到人们认定时代幸存下来的事物才是我们匮乏的补充,或者是担当生活所需的必要时,我们才会怀念起我们曾经在丰沛中忙乱了手脚。我们在期盼中最后做出妥协,忘记了承诺过的和解,以及归来的时候温柔的声音。 世界上多的是不可解释的东西,我们在凭吊故去的旧日时会渐渐遗忘我们对它根源的好奇。无知并不是对一切确认的反叛。怀念后来变成一种琐碎的情趣,当我们无所倾诉的时候,印刻在我们记忆里再熟悉不过的事物就会变得僵硬,硬生生的变成我们想法的克服。但它不是麻木,我们依旧用心灵的柔软接受它,继续铭记它。无知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需要不断处理的考验,它变成捆绑我们的枷锁,但最后依旧不失为图腾的存在。这种体验恐怕是内心潜在的自我矛盾,极可能变成心灵上难以取走的老茧,让心灵变成坚实厚重的存在。但我们也就不再接受漂泊者的自居,变成一个自律、体面的人,不再轻信耐人寻味的他言。可能我们会有老去之时,在自我规劝里度过的一生是荒凉的,但那又何妨。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读后感(四):把生命交给动荡的漫游者
把生命交给动荡的漫游者
赵松
拿到云也退的这部新书之前,我看过目录,还以为是书评集。等书到手之后,发现我错了。这是一部“作品”,是一部可以跟普鲁斯特的《一天上午的回忆》归为同类的,将个人精神成长史与阅读深度缠绕在一起的“作品”——它不仅意味着云也退在文体探索上的最新成果,还会为他自己勾勒出一个全新的自画像。
认识云也退十几年,感觉很熟悉,细想又觉得并不算了解。很早就知道他是职业作家,常写书评类专栏,但我读得不多。反倒是他曾主编过的监狱杂志,还有对相声的热爱,这些信息更让我感兴趣。我们偶尔碰到,随便闲聊一会儿,也就散了。我没有他那么好的记忆力,多数聊天内容都忘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特别喜欢约瑟夫·康拉德、艾·巴·辛格、索尔·贝娄,还有写《国王的人马》的那个罗伯特·佩恩·沃伦。
当然,要是我真的仔细搜索那些有限的印象,也还是能得出一些判断的。比如说,我认为他当然不是讷于言的人,但也不能算是健谈之人。我发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活动上,当他拿着话筒,开始说话时,他的眼神似乎总是仿佛越过了听众们的头顶,注视着无处的某个地方,好像那里有个隐身人,他的话,只是说给那人听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倾听他的言语并仔细观察其神情与肢体语言之后,我就想,跟说话比起来,他似乎更不于沉默。甚至,他正在进行的那种自顾自的言说,在本质上,就是某种沉默。
真正让我认识云也退的,是他的那部《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它让我觉得“非虚构”的说法实在没什么意义,而只有“作品”才有可能提醒读者,还有这样一种文体,能把小说、文论、随笔的因素融而为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没觉得此书是云也退所说的“反游记”,这概括不了其文体特征。我甚至更愿意把它看作某种“漫游小说”,尽管他只是在以色列短暂生活过,但其自我意识对环境本身的不断渗透与漫溢,却让他在有限的空间里经历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并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自我认识。
我得承认,直到读完这部《勇敢的人死于伤心》,我才觉得终于了解了云也退这个人。尽管笔法上一脉相承,但这本书显然是对《自由与爱之地》的超越。因为它的焦点,是他自己。确切的说,是他的精神世界如何在他与书、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逐渐生成。当然这也决定了它的难度。把个人精神成长史与阅读经验放在一起,难度不在于如何把表达人生感悟与阅读的密切关系,而是在于如何同时彻底打开自我、打开那些书,使二者发生深度共鸣,并在文字风格和整体结构上真正融而为一、血肉相连。
对于云也退来说,日常世界就是汪洋大海,他热爱的那些书,则是散落海中的岛屿。他的每次抵达,其实都像海难的幸存者那样,不仅重获生机,还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奇异之境。他不是个只知活在白日梦里与世隔绝的读书人,每天他都需要考虑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写作是他唯一可依赖的谋生手段。这意味着,不管他愿意与否,都必须大量阅读和写作,就像落入汪洋里的人,必须不停地划动手臂,才不会被海浪吞没……已有太多的职业作家和专栏作者的文字被深深的厌倦与疲惫所充斥了。但是,在云也退的文字里却很难看到这种气息。他有自己的“岛屿”,可以让他怡悦心性、探索想象和思考,还能让他一次次重新满怀热情地投身生活之海,而他的精神世界也正是以此方式不断生成扩张着,在“与文学为伴的生活冒险”里。
正如没有想到云也退会以迪斯尼动画片《猫和老鼠》为开篇来写这本书的序,我也没想到他会以卜劳恩的《父与子》和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作为头两章的主要内容来开启这部作品。最适合解释其中意味的,或许就是《在公鹅的脊背上》末尾那段话:“这是一张真人的脸,一种真人的笑,嘴巴和眼睛受到的制约,反映了心灵在体验过一个真实世界之后所呈现的样子,带着收敛的动作,带着预期中的悲哀。”尼尔斯在经历了奇幻之旅后,也完成了他的成人礼,在悲哀的底色上。而悲哀,我猜也就是云也退为此书定下的隐秘基调,就像燃放焰火需要黑暗的夜色作为背景。
尽管云也退没有像卡夫卡那样以全然拆掉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去构建作品的世界,但他确实做到了让个人精神生活与他喜欢的书水乳交融。当然他并没有试图把个人与书中的故事刻意杂合出某种似乎有所呼应的效果,而是更着意于通过凝视与反思磨掉个人生活与那些书的外壳,让那些在凝视中浮现的场景、在反思中达成的自我认知,跟深入打开某本书的过程交织生成类复调般的“前后呼应、此起彼伏”的结构。于是,他的视野回应书中视界,他的反思回应书中的思想,他的感觉与联想回应着那些作者的感觉与联想……而整个过程里,他就像在以自己的低回歌声应和着作者们的自在吟唱。当他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世界跟书中世界重叠交融在一起时,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漫游者的形象。
尽管在书中这种精神漫游的状态时常呈现为对城市、山川的细微观察,但从本质上说,经由云也退的文字所生成的视界,无一不是内化的,是在其内心沉淀后重构而成的。他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置于恰当的位置,与那些被他深入打开的作品声息相通,只有这样,他的漫游才可以永远止境。此外,也正是声息相通的需要,使得他的文字会跟某部跟他心神相契的作品风格产生微妙的呼应。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写到康拉德时会在冷峻笔触里隐含激情,会写出“在那个让我宁可忘却自己的冷夜,我大声朗读康拉德,我愿说出这冷,说出那些让人欲言而词穷的景象,说出所有不可说的东西,例如黑暗。”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写作本身的领悟:“可是我在康拉德的写作状态里看到一种一个人的仪式感:一个人,要求自己写下的字如同期待诞生的孩子一样完美。文字出现了,组成的世界反过来将他围绕,以至于一封致友人的信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都能恰如其分地再现真实人生的戏剧面貌,有布景,有质地,有你我难以逃脱的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在写到帕斯捷尔纳克时,他会在传达对其文字之美的惊叹与恍惚时写道:“文字像巨蟒一样,对现实发起缠绕攻击,它用销魂的动作在消化客观事物的同时将它升华。北方的春天之所以是黑的而不是绿的,是因为俄国国土多在高纬诬地区,低于零摄氏度,因此土内含冰,春季白天气温略高时融化,入夜又复凝结,反复冻融不断,闰时,这些冻土就被马蹄、车轮和皮靴来回践踏、碾轧,土水相混成为凛冽的黑色。它们可能是脏的,很难讨人喜欢,我在东北的街头就见过头天的皑皑白雪,第二天就变成了遍地煤渣一般……”
如果说从他对前面这两位作家的激情体悟中能看出其文学自觉所来何自,那么,从他对纪德、加缪的作品及精神世界的深度解析中,则足以发现其精神启迪的根源。当他在纪德那章末尾写下:“在他开辟的迷雾重重的方向上,人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自我,它是唯一的导航仪,得到它之后,还要为它的存在而奋战,奋战,对了,那是我们的名字。”当他在加缪那章的最后写下:“存在主义在我头脑中加设了一个‘世界’的概念,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与世界的矛盾,与起源、与‘人之初’的矛盾,心里就会明白,这是我降临此世的结果之一。唯有如此,才能不一味转向他人,才能不计算得失,才能放下自己。放下,也许我永远入不了人海,但我可以放下。”这种时候,他的精神所向,已坦露无遗。
不管他骨子里有多么的骄傲,对待文字有多么的苛刻,但在这部书里呈现最多的,其实还是内心的坦诚。他在揭示那些他所喜爱的作家们的矛盾时,也会坦承自己的矛盾;在展现他们的迷茫与痛苦时,也会描述自己的迷茫与痛苦;他在分析他们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时,也会表露自己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而在苛刻的另一面,他其实还保留着重新理解与宽容的可能。比如,在面对他向来不喜欢的海明威时。而在写他厌恶的杜拉斯时,他更多的还是为了承认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困境与焦虑,在嘲讽杜拉斯成功地解决这类问题的同时,他也顺便嘲讽了自己的无力。
在书中,他还写了米歇尔·图尼埃、伊凡·克里玛、埃利亚斯·卡内蒂、特朗斯特罗姆、安部公房、波德莱尔、普里莫·莱维、雷蒙德·卡佛、凯尔泰斯·伊姆雷、马克斯·弗里施、索尔·贝娄、毛姆、波拉尼奥、巴勃罗·聂鲁达、乔治·奥威尔、约翰·斯坦贝克、梅厄·沙莱夫、罗杰·格勒尼埃、帕特里克·怀特等作家。中国作家他只写了两位,一位是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另一位是他的前辈好友、英年早逝的刘苇。在这些水准质量非常平均的篇章里,他的行文无论是冷静、犀利、婉转还是戏谑调侃,都显得游刃有余,精辟之处与亮点时有闪现。
但是,最能触动人心的,无疑当属《回不去的拜占庭——怀念刘苇》。它堪称全书的核心地带,是所有篇章中最为柔软深沉的,也是写他的内心世界里发生的缓慢但又至关重要的变化过程最完整的。在这里你看不到激情澎湃、冷峻犀利,也看不到讽刺调侃,其中有的,只是极为克制的笔触所生成的朴素风格与深情。作为全书份量最重的篇章,云也退只用了不到四千字,就写下了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对刘苇的深刻观察、理解与怀念,尤其是还含蓄地记录了在那个仍有天真、梦想与激情的年代里,对文学的热爱与自我精神的最初觉醒。
在这部精神自传式的作品里,云也退几乎写出了多年来他对文学与生活的所有体会与感悟,同时也表露出对自己所选道路的坚定不移。尽管理性告诉他,“坚持活在梦里的人必然会遭到惩罚”、“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他也仍然会“敢于把自己下放到真实里”,任性地把生命交给动荡。因为在他看来,“对作家来说,任性是必需的,相对于是非,他们更看好本能的力量。”既然写作已让他明白自己该干什么,那么最根本的信念就是不言自明的:
“那不是为了永垂不朽,那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倘若说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是因为不愿向充满利益纠葛、现世纷争的人间投降而选择向未知投降。”
2020年4月12日
(刊于《新京报》2020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