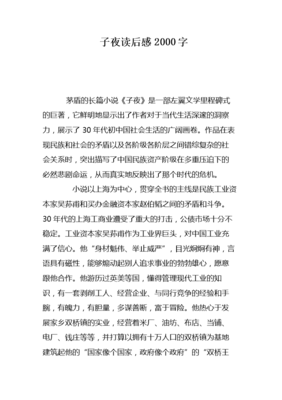有声的左翼读后感1000字
《有声的左翼》是一本由康凌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20-7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声的左翼》读后感(一):重返能指的一种方式
近年来的人文学术领域,似乎有一个转向:重视对符号自身的探寻,而非将其视为承载概念与信息的透明物。于美术史学者而言,是对器物形式的整体把握(而非抽离局部的片面元素,再直接纳入泛化的象征体系中)、对图像形式、构图、色彩的描述、对细节的辨析(Y老师语:“超级观看”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去历史性的、“纯形式”的研究,而是超越物与语境、内容的简单对立,新的问题及理解内在生成于对这些视觉材料的细读当中。
所以当看到作者对本书方法论的概括时——诸如“关注语言的物理的、声学的特点,而非将其简化、收编为对意义和主旨的复述”、“打开一个为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对立所遮蔽的、更广阔与复杂的论述空间”等等,新奇之余又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新奇是由于第一次接触“声音研究”,而似曾相识则是因为,它其实与前述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声音也是符号能指的一部分。
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概念之一,但凡对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左翼文学”的几个关键词:普罗大众、意识形态、政治动员。在这样一种看似已成定论的研究现状中,作者通过对诗歌语言的节奏、格律等声音面向的关注,揭示了左翼诗人的另一面:他们其实有在悉心经营着诗歌文本与音响形式。至于为何要选择听觉经验作为衡量诗歌创作的标准?其理论来源自何处?在此过程中又遭遇哪些困境?具体的讨论散见于本书的各个章节,涉及以感官愉悦构造身体性的团结感、知识的跨文化转译与挪用、听觉秩序与语义讯息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关系等多个有趣话题。
而在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作者又具备足够宏观的视野去反思整个20世纪文学史:左翼诗学对歌谣形式的反复辩证,与日后“民族形式”论辩的某种隐秘关联;在文学与身体之关系研究中,超脱个人情感爱欲、更为丰富的“身体”概念。既有理论与作品的自然衔接、个案分析之精深,又有大问题意识的格局,不得不惊叹作者的功力。
另外,有一个关于论文写作技巧的小小收获(其实也不小):作者在尾声的自我批评一节中提到,本书对听众反馈部分欠缺讨论,其实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对此,作者坦言自己试图以两种方式回应——或者更多的是绕开——这一内在要求:其一是援引了“可供性”的概念,将对“形式做了什么”的追问,转化成了对“形式有能力做什么”的探索;另一方面是通过对诗人写作方向调整过程的辨析,倒推文本在实践中遭遇的困难。这一做法或许会被读者诟病为从一手材料到推论的“危险一跃”,但个人觉得如果实在是没有机缘巧合找到更多合适的材料,这样的方法也不失为退而求其次的机智策略。
《有声的左翼》读后感(二):《有声的左翼》读书短札
本书的主体部分可看作一篇长论文。一章导论,二三章文献综述,四五章进入具体文本的分析,六章做小结。作者的切口极小——只选择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部分诗作进行研究,但旨归却大——希望展现出1930年代左翼朗诵诗的独特性,并尝试以声音为视角,形成理解左翼文艺的方法论。左翼朗诵诗是一种借助音响组合实现身体动员与情感动员的文学表现形式,诗人们对诗歌节奏的设计被看成一种“身体技术”,召唤着大众的身体经验与情感认同。但另一方面,诗人虽然想极力摆脱语言中介但终究受限于语言固有的物质性,因此时时感到某种“纠缠”。陈述此段的第四章第三节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段落。本文的最大贡献是把海外方兴未艾的声音研究视野成功地桥接到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中。作者对外国相关研究的把握相当准确,借用的几个概念如Speech Act, Affordance,Iterability等都有效地推进了自己的论断,而二三章所梳理的知识谱系清晰扼要,将“节奏学”的种族主义起源、阶级论改造及中国诗人的介入面向铺陈甚明,成功连接起节奏与身体两大理论话题,非常精彩。
若是谈到问题的话,可能四五章的文本分析未能全部信服,大概只有象声词部分是完全接受的。归根到底是这批文本打开的难度问题吧。虽然作者说自己始终分析的是一种诗歌形式的“理想型”,但作者也提到对理想型的分析并不能取代对效果的分析。但设若离开效果,理想型的分析又如何能避免失去分寸感呢?至少我觉得一些论断只是用学术黑话最为理想化地翻译了一些诗歌的表达效果。导论中有一句话非常引人关注:“对左翼的政治的批判必须同时是对左翼的诗学与技艺的批判”。但如果只看四五章,我们很难设想作者如何做出“政治批判”,因为这种身体召唤的情动视野,被他们“理想”诗艺充分满足了。而作者又借助“Affordance”可提供性这个概念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另一处觉得有局限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切口吧。作者“一个社团、一种诗歌实践方式、一次文学运动、一个知识谱系、一批诗歌文本”的自我概括非常精准,因此他自己也在结语中提到,其实需要考察左翼外部其他派别的作者群体。但我其实觉得左翼内部的其他群体就首先需要考察。我们都知道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一点儿都不弱于左翼与非左翼之间的论争,那么,中国诗歌会如何能代表左翼诗歌呢?左联、北平左联、中国诗歌会,至少是三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组织。作者这里的写法是在一点深挖,动用富赡的理论工具进行深描,但视野中缺少了这些相对参照系,精彩之余也难免会有力度偏颇吧。要是大陆方面现代文学的学科训练,大概会要求作者把各个群体都做一遍。但海外汉学的学科训练就会要求作者把这里获得的视野再投向完全不同的领域了。也是各有所长。很期待作者博论的其他章节也能这么精彩详实。
《有声的左翼》读后感(三):读后
对“声音”研究路径感兴趣的可以读读第三章和第五章,是条理清晰的理论梳理和文本分析案例。
以下是我还在思考的几点:
1.“声音”的本质是“兴”,也就是动员机制。这个传统是很古老的,尤其在西方文化从记忆术到辩论、演讲甚至史诗,都是orality的传统;与此同时在中国,这种传统渐化为民间娱乐(从诗经到说书到戏曲),精英层面则几乎绝对地被literacy的传统(诗文,尤其是作为精神枷锁的八股文)所占据,因此晚清到“五四”的知识精英才会有“声不振”的苦恼。于是“现代文学”本身便具有倡新“声”的目标(例如鲁迅召唤摩罗诗人),也因而与民俗(民间)有了契合点(歌谣研究会与平民主义),这个根底基本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基于人种生物学+环境的浪漫主义。三十年代左翼诗人也是延续了这一谱系,只不过他们所想象的民众主体已经变了,与此同时非左翼的文化人也在搞这一套,国统区的诗朗诵和戏剧更如火如荼。
2.声音作为动员机制,因此可以为任何意识形态所用。或者说,“形式”的意义其实是还没弄清的。在理论源头上,生物学的(人种、生理起源)和唯物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劳动起源)两说并存,即便三十年代左翼诗人有选择性地认可后者,建构起一套自洽的逻辑——现存的民间歌谣(谣曲、儿歌、小调、鼓词、弹词、竹枝词等)有着“劳动大众”的身体感官所继承的一套遗传密码式的音响节奏,于是在左翼的新歌谣创作中召唤这种音响节奏,配合以革命的进步的内容,就可以在意义和感官上同时动员大众了——其中也存在很多裂痕。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形式是原始的“劳动节奏”,具有天然的进步性,那又为什么是“旧瓶”,为什么(在形式上)也有封建因素的污染?这中间跳过的可能就是绵长的历史,与“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创伤必然也将体现在民间歌谣的形式而不单纯是内容上(比如书中举例的祷告求神的“天皇皇地皇皇”)。我认为三十年代左翼诗人在声音和形式上的理论建设还是想得比较简单或者说目的论的,拥有“劳动的自然节奏”基因遗传的“大众”只是他们理想中的虚构主体,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动员寻找一个逻辑闭环,最终在结果上把自己绕进去了,反而变成为了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改造自己了(eg.劳改),搞得很难受。很多民谣形式,是封闭的,循环的,消极的,好逸恶劳的,求来世富贵的,当然这不妨碍我们从中听到人们真实的需求和悲哀,但并不表示能激起身体快感唤起感官记忆的就是好形式,也可能是巴普洛夫训练的狗子。艺术上真正的革命一定是形式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胡风,同意鲁迅、周作人的文体革命(在声音上反对“载飞载鸣”的快感),我也同意在形式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朗西埃的“感性分配”。
3.声音的阶层性,这也是orality和literacy的分野遗留下来的吧。有一个现象,据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依赖于文字(视觉)。就个人而言,我喜欢读邮件而不是打电话,看中文剧也需要字幕,受不了抖音的听觉轰炸,不喜欢收发微信语音等等。估计豆瓣用户大多数如此,但可能这不是“大众”(或许又在臆测了)的喜好。我猜三十年代左翼诗人想必也是如此,又要动员大众但精神上可能又很“文”,蛮分裂的。
不过另一方面我又很能get空耳和鬼畜,如果声音研究可以讨论一下空耳和鬼畜的话,我大概会非常有兴趣!
《有声的左翼》读后感(四):“声音”作为文学研究的维度
“声音”作为文学研究的维度
在《有声的左翼》中,作者把“声音”作为观照文学的一个维度,展开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空间。实际上,作为一种携带着声音策略的左翼文学(诗歌),它与沉默的视觉的文学(用书里的话说:“背离大众的‘哑巴文学’”)构成了鲜明对照:“视觉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人民的“盲区”,它因其传播方式和受众,而一定程度上成为拥有视觉阅读权利和偏好的阶层或群体的意识形态载体。“听觉的文学”作为与前者不尽相同的文学样式,有着另外的传播路径和受众群体,因此也一定程度成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载体,承担不同的功能。
作者从这样的角度展开研究,让我更加确信一些想法:那些有开拓性的文学研究往往需要向外部拓展疆界,它需要勇敢地从既定的安全范围里走出来,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方法论、话语方式,然后将其嫁接到文学研究上。对于这本书来说,它移借了生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讨论声音的诸多范畴(节奏、韵律等)与身体的关系,认为“节奏”从根本上是“一种内在的身体机能与外部的感官世界之间的关系性机制”,节奏为诗歌文本“赋予感官秩序”,通过一些复杂的机制唤醒人和强化受众的情感反应。
作者也触及到这样的话题:声音的策略及其身体动员功能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与特定的和意识形态方向与宣传教育功能绑定起来,因而产生了其社会影响。在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中,声音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在力求凝聚人心,达到宣传、教化、动员效果的要求下,作为感官路径的“声音”则似乎注定被转化成技术和策略。
推而广之,声音这个维度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应该被点亮的话题,而并非仅属于左翼文学。比如抗战背景下的诗朗诵与当今文学沙龙式的诗朗诵都是通过声音来传递信息,却蕴含着全然不同的文学趣味、审美情调,承担不同的功能——而后者何尝不也是一种声音的策略呢?而这,又能展开一些具体的话题空间:什么人在传递声音,在传递什么声音,如何传递,什么人在听,他们听到了什么,他们受到了什么影响,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它成功了么?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声音”本身很难够成独立论述并大书特书的对象,因为“声音”本身很难成为一种本体性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形式,一种媒介,一种载体,以及一种强化效果的工具性的存在。我们在讨论“声音”的时候,往往也在讨论这些范畴:语义、结构、节奏、内容、叙事、听众。在讨论声音的时候,也不得不将声音的节奏、韵律等技巧与作者的诗歌写作策略、理论倡导、朗诵者的朗诵技术以及更大范畴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等纠缠在一起。在这里,声音的作用(如果一定要通过“节奏学”理论才能言明朗诵形式与身体的关系),其实还是作为策略和方法起到配合和加强效果的作用。所以,在讨论声音的时候,究竟在讨论什么?很多范畴早已模糊。如果说,对“声音”的研究是在“工具”和“策略”的层面上展开,那么,“声音”并不具备作为独立“主体”而被研究的条件——但很明显,作者似乎不满足,他还是想把“声音”作为一个某种意义上具有独立性的研究对象加以论述,最后却面临被诸多与“声音”密切相关却又不是“声音”的范畴纠缠在一起,甚至不断地把话题向周边相近的范畴扩展,从而让人感到有些混乱。
举个例子来说,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提到了他一个想做而未来得及做的事情,即讨论“声音与空间”的关系,左翼诗、集体歌咏、游行示威、口号呐喊、飞行集会等“围绕声音展开的激进文化实践”中的声音与空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但实际上,“声音”只是某种策略,以及这些策略作用下的效果。更为重要的范畴恐怕是空间本身的意义属性,是占据这些空间的人,是他们的思想、话语、实践,以及在这片空间中可能发生与已经发生的事,而“声音”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恐怕不是独立自足的。如果把“声音”作为一种被赋予主体地位的研究对象展开,即便写出来,可说的话实在有限。而即便再次讨论节奏、韵律,则也有新瓶久酒、老生常谈之嫌。
也是因此,相比于其他章节,我更喜欢这本书的第五章“诗的蒙太奇:作为音响的语言”,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分析。凭借丰沛的感受力和精深的文本分析能力,作者结合具体诗作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解读。在分析中他提到听觉上的重复感、规律化,以此生成的感官节奏,声音与语义结合所生成的叙事和抒情脉络,以及激发的听众的情感反应等;声音秩序和语义秩序的相互干扰;象声词在朗诵诗中的运用等。这些都非常精彩——从声音的维度切入的文学研究的魅力,似乎主要体现在具体文本分析上。
如果说一定要指出“声音”研究的主体性问题的根源,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与声音有关的理论本身的不自足,以及这些理论嫁接到文学研究的难度——这些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恐怕是很困难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一定要规避这些难度来写文章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关注历史现场的情境,朗诵者的身份、气质、嗓音、情绪,朗诵的场所,听众的状态、反应、效果等范畴,以及此类实践和广阔时代图景之间的错综关系——把这样的研究历史化,总是我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