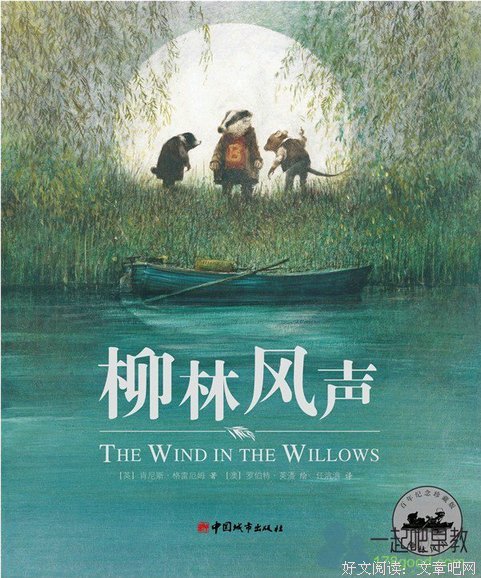《利他之心》读后感锦集
《利他之心》是一本由戴维·斯隆·威尔逊 (David Sloan Wilson)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00,页数:1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利他之心》精选点评:
●前半部分写得挺好,后半部分,可能是篇幅问题,没说透,加了太多似是而非的例证,让书有些散了。
●“得到”听书
●这本小册子虽短,却极富深度。不仅把演化领域的两种争论融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车轱辘话转……
●作者用演化理论作为工具,分析了生物界中广泛存在的利他主义得以演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利他主义带来了群体的整体竞争优势,而群体之间的自然选择才是生物演化的主要力量。同时,本书也分析了人类演化过程中,文化和道德的重要作用,以及利他主义对人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自私者在群体之内能获得更大收益,利他者在群体之间更多得益,利他特征得到保留
●不错,有点启发
●利他组战胜利己组
●总而言之就是利他有利他的好处和存在的作用。。(得)
●群体之内自私胜过利他。群体之间利他胜过自私。余下的全是评论。
《利他之心》读后感(一):得到解读
虽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说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样的进化模式下,生物是不应该存在利他这种特性的。但是从演化论的角度来说,自然选择不只针对个体还可以,是全族。利他特征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就是因为在群体之间利他胜过了自私。而让人类和动物变得不一样的原因,要得益于人类演化过程中,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规则的制定,让人类有效的限制了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恶性竞争。
《利他之心》读后感(二):实际是在说群体选择理论
马丁·诺瓦克把利他的成因归纳为五点: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结构和群体选择。受惠于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其中(至少对大众)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亲缘选择理论。本书关注的则是群体选择理论,或者按书中的说法为多层演化(选择)理论。因此本书的名字与其实质相比稍有点大而无当。另外,本书对群体选择理论的肇始和复兴基本上没有什么介绍,给人的感觉颇有以作者一人之力扛起群体选择大旗的意思,但实际上马丁·诺瓦克和爱德华·威尔逊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得不提的,为此道金斯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 《爱德华·威尔逊的堕落》 来反对群体选择理论。
《利他之心》读后感(三):社会需要利他主义
《利他之心》作者用演化理论作为工具,分析了生物界中广泛存在的利他主义得以演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利他主义带来了群体的整体竞争优势,而群体之间的自然选择才是生物演化的主要力量。同时,本书也分析了人类演化过程中,文化和道德的重要作用,以及利他主义对人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作者戴维·斯隆·威尔逊,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宾厄姆顿大学生物学与人类学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生物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进化论与生活》和《达尔文大教堂》也是全球畅销书。
1.如果现在或者未来的某个人类社会功能化的程度极高,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心一意地为了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努力,这个社会就可以称得上有机体,如同人类被称为有机体一样。
2.一个物种从非洲走出,只用了数万年的时间,就在全世界繁衍生息,适应了所有的气候环境,占据了数以百万计的生态位。
3.人类的演化受到文化和社会演进的影响,多亏了社会规范和规则的制定,人类可以有效地限制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恶性竞争。
4.在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利他主义者环绕在我们的身边,正是他们让我们更容易地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
一、自然界的利他主义是如何被演化?
1.什么是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1851年被法国哲学家奥古斯图·孔德首次提出来的。它是指一种无私地为他人谋福利、舍己为人的行为。利他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帮别人开门、搀扶起摔倒的老人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到为民族和国家而付出自己生命的大爱,都是利他行为的表现。
2.利他主义的两个层面
第一层:心理和感受层面的利他。
第二层:行为上的利他。
有的利他行为是出于一己私利,有的则是纯粹出于帮助别人。比如有的明星做慈善是为了出名,而有的明星做慈善则真的是想帮助别人,作者认为这种心理层面的真正动机很难区分。但我们真正所关心的是这个人是否真的在行为上帮助了别人。
3.利他主义三种解释
第一种:内含适应性理论,又称之为亲缘选择理论。
第二种:自私基因理论。比亲缘选择理论更近一步,认为基因演化的所有结果都是某种形式的自私。
第三种:演化博弈论。认为帮助别人只是为了让别人也帮助自己。
上面的三种理论,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基因是自私的这一结果而已,它们都可以归为同一种思维范式,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利他主义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这一现象。
4.功能型组织
是指一些个体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相互协同工作,以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比如一艘航母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大的功能型组织,航母上的每个人、每个零部件都有其功能作用,它们以一个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完成一系列既定的目标,比如向某个方向航行或者完成战斗机起降等任务。一个功能型组织要实现一个目标,就需要团队合作,因此必须表现出利他行为。利他主义不仅在个体中存在,而且在任何一个功能型组织中也都存在。
5.生物演化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自然选择是基于相对适应度。意思是自然选择关注的是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值。
第二:利他主义者在群体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三:功能型组织演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群体之间的自然选择。
案例:比如一只狮子费尽体力去捕获了一只羚羊,而其他没有参与捕食的狮子有更充沛的体力。它们在分享食物的竞争中会更有优势。但如果草原上有很多个狮群,有的狮群中利他的狮子多,有的狮群中利他的狮子少,显然有更多利他狮子的狮群,会因为有更加充足的食物,变得更强壮,在草原上各个狮群中的更具竞争优势。按照自然演化法则,那些只有少量利他狮子的狮群将被淘汰。
自然选择就像是在拔河:在组内,自私者胜过利他者,在组间,利他组胜过了自私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两个方向相反的自然选择的平衡点。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平衡机制演化的结果是抑制群体内的自然选择向破坏性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群体之间的自然选择成为整体演化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利他主义得以被演化。
二、人类怎么一步步成为地球的主宰者?
1.人类演化的两个方面
人类的演化分为:基因演化和文化演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好地解释了基因的演化过程,但是并没有解释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演化过程。
2.人类演化的特殊性
人类的崛起其实是演化史上非常偶然的事件。其他灵长类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合作,比如狼和狮子都是以团队合作见长的物种,而且在它们捕食猎物时也会表现出高度的合作性,但为什么这些物种没有得到重大演化的机会呢? 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这些物种的群体内部恶性竞争,仍然在它们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争夺配偶和领地等;另外一方面,虽然它们有合作,但并没有建立规则,没有抑制群体内恶性竞争。
3.道德与文化的作用
首先,达尔文在《人类的演化》中指出:较高的道德标准会使个人及其后代在部落内部只有很少的演化优势,但是较高的道德标准和更多秉性善良的人,会使这个部落相对于其他部落具有更大的优势。他们热爱、忠诚、服从、勇气和随时愿意牺牲的精神及同情心等道德品质会让部落发展壮大。
其次,一个功能型组织有体力活动和精神活动两方面。体力活动比如照顾长幼、获取食物、防卫掠食者等。精神活动包括符号语言、知识技能、认知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等等。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比如信任、认同的社会文化。这些精神活动使得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度大大提升,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让人类拥有了语言、文字,推动了技术和工具的出现,带来了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道德与文化带来的规则意识激励我们做出利他的行为,抑制了群内恶性竞争,使得利他主义在社会普遍存在。所以人类演化过程有别于其他生物,这也让人类最终成为了地球的主宰者。
三、利他主义对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1.经济活动中的利他主义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假定人都是理性、自私和贪婪的。那么,利他主义是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呢?作者提出,运行良好的社会只是社会层面选择的产物,而并不是个人自私自利的结果。
人类社会被一种更高层面的选择机制所推动,跟演化论中的群体间的选择类似,它并不在乎群体内部个体是利他的或者自私的。比如,我们可以将社会看成一个功能型组织或者有机体,基因和细胞是没有意识的,它们只是对周围环境做出简单的反应,从而影响到了有机体的生存和繁衍。而且这些反应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一大部分反应是不利的。这些细胞或者基因就像社会中的每个人一样,在我们所设计的社会规则中(如法律和宪法等),让利他主义得以在社会整体层面提高整个社会的利益。比如,社会中一开始出现了很多经济体系,但是在社会演化的过程中,那些不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经济体系,被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所淘汰,留下了当今主流的,并且是在群体层面利他的经济体系。
2.日常生活中的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也影响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列举了自己家乡宾汉姆顿市的例子。研究者对全市范围内的公立学校学生进行了亲社会性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学生很均匀地分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而且亲社会性高的学生往往会居住在一起。个人的亲社会程度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呈正相关性,也就是那些亲社会性的利他主义者,获得了很多的利他行为的回报,形成了正向循环。
同时,作者还发现。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或者说利他行为具有环境可塑性,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在一个亲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会事务中更加积极主动,在积极家庭教育的环境下 成长的小孩也有更高的亲社会性。
3.社会管理的意义
最后,作者指出不管在经济活动还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让社会能一直良好运转下去,社会管理非常重要,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鼓励社会在群体层面的利他主义,让人类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演化。
笔记来自有书共读
《利他之心》读后感(四):群体选择理论中的堂吉诃德
读完戴维·斯隆·威尔逊的《利他之心》,本不打算写些什么的。因为最近读了不少从演化、博弈论角度讨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书,有理查德·乔伊斯的《道德的演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的进化》以及马丁·诺瓦克与罗杰·海菲尔德 合著的《超级合作者》等等。
当然,加上之前读到过的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罗伯特·赖特的《道德动物》以及爱德华·O ·威尔逊的几本著作。已经足够让我对这个领域里关于道德、利他主义和正义的演化起源与生成有了了解。
然而,看到这本内容简短但深刻的《利他之心》,在豆瓣上39人阅读仅仅给出6.9分的评价,实在让人有些寒心。我不知道这些给予中等评价的读者到底是否真的了解相关领域,就把它说成是作者的“意淫”。这样一部深入浅出地介绍群体选择理论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作者也多次强调读者自行阅读参考文献,却被人误解,或说证据不足,或说阐述不清,真是可惜。
群体选择论的堂吉诃德或许是他们不太了解作者的缘故,戴维·斯隆·威尔逊 (David Sloan Wilson) ,与同姓的爱德华·威尔逊一样知名,至少在群体的多层次选择理论上,尤其如此。
戴维·斯隆·威尔逊
马丁·诺瓦克等人所著的《超级合作者》一书中,如此评价到: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科学家接过了群体选择理论的火炬。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宾汉姆顿大学的教授大卫·斯隆·威尔逊。威尔逊坚信,进化生物学在20世纪60年代走上了歧途。他在群体选择领域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研究。这位独行侠在他那被众人视为堂吉诃德式的探寻之路上,遇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科学哲学家埃利奥特·索伯,以及哈佛大学伟大的自然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这两个人选择与他一路同行。这样的评价颇为中肯,在《利他之心》书中,作者也介绍了他和哲学家索伯的相遇与碰撞,以及其他学界人物的合作,如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共同研究。他也创建了演化学研究项目(EvoS)和演化研究所,从演化学的角度规划公共政策的智库。
当然,戴维·斯隆·威尔逊的著作也颇丰,有《达尔文的大教堂》(Darwin's Cathedral,2002,无中译本)、《每个人的进化论》(Evolution for Everyone,2007,中译本名为《进化论与生活》)、《致其他人》(Unto Others,1998,与索伯合著,无中译本)。他也与爱德华·威尔逊合著过《社会生物学理论之基础的重新思考》(Rethink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ociobiology,2006,无中译本)
这本《利他之心》提出了好些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话题,都是在作者其他书和论文里有更深入的阐述。此书的原著为2015年出版的《利他主义存在吗?:文化、基因和他人的福利》(Does Altruism Exist?: Culture, Genes, and the Welfare of Others)的译本。
这个小册子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与坦普尔顿出版社(Templeton Press)共同推出的丛书“大题小做”中的第一本(作者前言)。因此,算是一个简短的科普作品,原著总计才不到200页的内容,所以作者“内容力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就像通往知识殿堂的快车道,使广大读者免于陷入烦冗细节的泥淖”(同上)。
我在这里根据上面提到的书籍加上个人的见解,总结了本书三个方面值得重视的理论。
一、消解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之争演化论自达尔文创立至今,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自然选择是作用在个人层面上还是群体层面上。我在前文已经简单叙述过理查德·道金斯与爱德华·威尔逊的争论(见《在宇宙中孤独并自由着》一文)。
简而言之,群体选择,或者称为多层次选择的核心就是自然选择即在个体层面发挥作用,也在群体之间发挥作用。爱德华·威尔逊过多地强调群体选择,是因为他看到了自然选择作用在群体层面上,能够增加我们的道德,而不至于让我们陷入到人人自私自利的社会中。
其实对于理查德·道金斯与爱德华·威尔逊两人,我都难以割舍与抉择,理查德·道金斯从基因自私到群体福利的说法很有说服力,爱德华·威尔逊则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然而,是戴维·斯隆·威尔逊却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让我不必在两者之间必须二选一地去相信。
戴维·斯隆·威尔逊调和群体与个体之争所用的方法,就是他所说的等效性。不同于库恩所谓的“范式革命”,等效性并不要求一个必定去舍弃一个而存在。在《利他之心》中,等效性是如此表达的:
等效性的概念与范式提出的标准过程有两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与标准的范式出现过程相同的是会有不同的思想结构存在,但是它们是可以共存的,而非必须互相取代。第二,不同的思想结构之间可以没有可比性,也不需要有。个人或者是整个社区的人都可以掌握不止一种思想结构。就拿演化领域里的群体和个体选择来说,各自只是看到了不同层面的作用。就像是你买东西,无论是刷卡、付现,亦或是支付宝、微信一样,只是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
群体选择看重的是多个群体之间的竞争,所以相对合作的群体会比自私者组成的群体有更好的适应性,而在群体内部,无疑自私者更具有适应性。两个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理论之基础的重新思考》一书中如此总结道:
“群体之内自私胜过利他。群体之间利他胜过自私。余下的全是评论。”(转引自《利他之心》)因此,我们每个人的道德观念都是在自私与利他两种观念之间纠结,视不同情况而定。一个自私者在群体需要时也能够挺身而出,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可能斤斤计较。这也可以解释一个群体在面对外部入侵时,常常能团结一致,而在和平时期却相互内斗。
二、用演化生物学去反思经济学我从不讲道德的经济学逃离,希望在哲学领域里寻找伦理时,却发现伦理学已经变成老学究式的形而上学,陷入到抽象层面的争论。
自亚当·斯密开始的经济学,越来越把理性人、也就是自私算计的个人当作假设前提,之后这种经济学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第一个思想者就在十字路口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追随着他的脚步的很多现代思想家也会走在错误的路上。(引自《利他之心》)阅读演化生物学的个体选择理论,尤其是道金斯等人的学术路向就会发现,其思路与经济学竟然如此的相近似,从“蜜蜂的预言”到“看不见的手”,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人人自私算计,就能带来全社会福利的增长。
这种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也是学术研究的主流思路。不单单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就有过这样的反思:
个人主义方法论支配着经济学中与社会学相近的部分、社会学的大部分,以及心理学中偏向组织理论的全部。这个原则是指所有的人类社会群体过程都要用个体行为的法则来解释,群体和社会组织没有实体性,按照这个原则,组织之类的存在不过是个人行为的一个便易的合集。(转引自《利他之心》)政治学中也有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前者有迈克尔·桑德尔,后者代表是约翰·罗尔斯。这种个人主义的传统占据了各个方面,并影响了欧美至今的政策。戴维·斯隆·威尔逊说道:
如果社会的运行以个人利益驱动的市场力量为基础比以善意为基础更好,那又何须善意呢?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做出了这样的声明,随后这个主张在传统基金会、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各国智库和政治家的推动下成为公共政策。这让我想到了早年学经济学时,一些国内的“知名经济学家”不加反思地为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观摇旗呐喊,《蜜蜂的预言》一度成为畅销书,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被这些人奉为楷模。而提到社群主义,就被等价于集体主义、斯大林社会或奥威尔的1984。这些舶来的个人主义让我们的改革变得渐渐不再与福利社会沾边,让全社会所有东西都标上了价钱,让我们的道德水平也直线下降……
从演化生物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重构经济学、甚至是社会学基础的可能性。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在《助推》一书中,就提出一种“自由家长主义”的助推方案,这是一种思路,若从群体组织层次来规避自私自利者对“公地”的蚕食,也是一种思路。
三、利他主义不必有高尚的动机戴维·斯隆·威尔逊是演化生物学家,但其理论底色却浸染了浓厚的制度经济学色彩。对其理论影响最大的一位,就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与奥利弗·威廉姆森共同获得那样诺贝尔奖的。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有中译本)、《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1993,与人合著,有中译本)。
公共治理方面,最有名的问题是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简单来说就是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财产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如空气、公地、河流等污染和滥用,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难题所在。
可以说,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提倡或是私有化或是自上而下监管的解决方案,“私有化”的口号一度在国内也是主流声音。然而,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另一种新颖的解决方法,只要设定原则,社群可以自主管理好公共资源。
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八项原则,对于任何组织的设立和管理都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具体可以参见《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在此简单列举如下:
社群及其目标界定明确;收益与付出相对等;集体决策;监管;赏罚分明、有人性;公平正义的冲突解决之道;群体内部有主权;与上级群体协调妥当。在奥斯特罗姆原则下的群体,是能很好地解决“公地悲剧”,也有一个独特的价值,就是利他主义可以从这样的功能性组织中产生。
人类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组织方式,最成功的往往是与奥斯特罗姆八项原则最为接近的群体。这样的群体机制运转良好,就不需要另一个东西的介入:圣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利他主义者一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若只是在行为上的利他者,他做好事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博得名声、或是怕被惩罚,或是表演给别人看,就不算个道德高尚的人,不能被称为利他主义者。
但戴维·斯隆·威尔逊认为,利他主义者不需要很高尚的心理动机,只需要在行为上是个利他主义者就可以了,不必在乎其心理动机是否真心实意。这种把利他主义看作是组织的一种功能性产物,实际上秉承的是实用主义传统。
如此而来,戴维·斯隆·威尔逊的利他主义,就将心理上的近因与演化角度的远因区分开来,“这不同于康德、边沁和密尔这些哲学家所做的系统化努力,也不同于现代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剖析表现出相同行为的思维感受之间的微妙不同的努力。它与改善现实世界中人类福祉的利他主义目标密切相关。”(引自《利他之心》)
总结这本书虽是一个小册子,但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之门,让我从经济学逃离后再次回归到经济学,重新以演化生物学的角度审视,就看到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书的最后提到的《星球级利他主义》虽然看起来遥远,但也是一种理论面向和未来展望。这样的展望在爱德华·威尔逊的《人类存在的意义》、《生命的未来》中反复提到,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著作《人类的终极命运》、《人工智能的未来》中反复吟诵,《超级合作者》一书的作者诺瓦克在最终章节中追问:“人类下一步该怎么办?”
如果没有这样的广度和胸怀,我们只能在“在宇宙中孤独着”。
《利他之心》读后感(五):如何利他
这本书中译本少了一章,Altruism and Religion。劳伦斯曾说:人的灵魂需要的实际的美,永远胜于需要面包。在《理性之谜》中,Mercier and Sperber说,一些研究者把自己的特点推而广之,以为人类都是自己这样子(的心理体验或思维方式)。在这里,劳伦斯就是这种自我代入者。阿诺德看得很清楚,他说,在人类的各个时代和各个群体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异类”(aliens),指的就是DH劳伦斯这种。有时候,这些人就像Ellis所说的,像兰花一样,对环境要求苛刻,很容易就枯萎了;而其他人更像蒲公英,随便丢在犄角旮旯里就能长得很好。有时候,这些人,如果没有凋零,有机会像Adam Grant所说,他们作为non-conformists“非随波逐流者”推动了世界。保罗·巴恩说:只有死鱼才随波逐流。哈。所以当Samuel Johnson说,穷困和困难压不倒天才,莎士比亚们总会破土而出,他实际上错了,Taleb已经以黑天鹅谈到过这种survivorship bias;他应该是在读到Henry Fielding出身贵族世家说富贵给了自己求知的便利时,因为他自己在贫困中长大,有点自怜的意思。
这看起来有点精英主义的意思,我记得帕累托谈过历史的“精英主义”,意思是历史是精英来书写的。但是,此处提到的outliers,这些异类、异形、外星人,并非这种意义上的精英。谁会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足不出城的康德和足不出户的斯宾诺莎是政治上的精英?伯里克利、哈德良、奥勒留是,亚历山大、凯撒、屋大维是,拿破仑、毛、川普是。同样,落魄潦倒的梵高、一生默默无闻的卡夫卡、死后才获得注意的王小波,相比那些当世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甚至能呼风唤雨一部电影票房几十亿、一句话调动上千万粉丝的文化红人,又怎算是艺术精英?参与历史,必然需要有资本,无论是权力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经济资本。在《今日简史》中,Harari Yuval说,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握在这些资源拥有者手中,他们的意志虽然不能让公鸡下蛋,但是在可能的选择范围内,他们实际上能够掌握社会的摇摆方向。就像领袖一句话,一个想法,比如垃圾分类,就能让历史(至少暂时)走向巨大的垃圾堆。马克·扎克伯格的想法,甚至也能引导某些政治或经济的走向,比如干扰美国大选,或引导虚拟货币市场的起落。在权力场、经济场和文化场中心的那些个体,才是通常所谓的“精英”。像苏格拉底、梵高,仅仅是在超越时间和空间在起作用,或者说,不是他们在起作用,是他们身上产生出来的抽象的“文化碎片(memes)”在起作用。柏林在《自由论》中谈到这一点,他说,不要以为某个书斋里的书呆子(“教授”)是个死瘦宅废物,任何小看思想力量的人,都会在历史中吃到教训。在这里问题中,我认为应该分开两种东西:死瘦宅和思想。死瘦宅还是废物,但是思想却是另一回事。瘦宅就瘦宅,为啥非要加一个“死”字?大概因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我并不喜欢过这种生活。但是胖瘦和哲学家什么关系?我猜想哲学家瘦子多,就像哲学家自杀率低于艺术家一样。虽然有时候会出现某种重叠,就像麦迪逊参与面过建国,是美国宪法之父;但是即使如此,如刘易斯在Make No Law中所述,麦迪逊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显然远超时代,要美国的最高法院实现部分他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还需要等到在他之后将近200年的纽约诉沙利文案。房龙说,人类精神的拓荒者远远走在人类的前面,往往在拓荒中孤独地死去,说的才是这类人,他们并非引领历史潮流的精英,才轮不到他们来“指点江山”,因为他们一旦“指点江山”,那些手握权力的真正精英就要请他们“包吃住”请君进去。苏格拉底什么时候指点过江山?他只是发表了一种不同的看法而已,被判为亵渎神、腐化青年的罪名。就像我在此仅仅谈谈我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解,谈谈个体发展和群体组织,如果不符合执政者的看法(实际是利益),就会被当作是煽动、颠覆、造谣、境外势力支持罪,聪明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哪儿都不少傻子。
实际上我才仅仅是想弄清楚怎么回事而已,我想知道人的存在是怎么回事,社会和历史是怎么回事,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就如粒子、黑洞和宇宙边缘,宇宙的过去和人类的未来)。我自己不过是“尘世间一个迷途小书童”,什么煽动什么颠覆,您抬举我。话说回来,人人都应该肩负起责任,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人人都搅和在一个“社会”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我们人人都有关系。就像DS Wilson所说,我们现在更想是“社会超级有机体”中一个小小的细胞。我们日常的吃穿住行,都是一种和别人编织的分工合作之网中获得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之一,即我们的生活绝大部分卷入在“公共领域”,问题在哪里呢?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即私人的归私人,公共的归公共,在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之外,充分、完全尊重个人的自由,甚至,为了保护之中自由,Mill说,就像一个人”酗酒“,这种行为间接涉及公共利益,因为可能会妨碍公共秩序,但是,出于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我们依然不能为了防止扰乱公共秩序的可能,而禁止人们酗酒。我们宁愿承担公共利益可能受损这种麻烦,也要尽量给个人自由提供便利。David Miller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提出过一个异议,我认为他弄错了,从他办公室挂裸女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以为挂裸女图是个人自由,但是这不是私有空间,就像自己房子外墙上一样,这涉及公共空间和他人利益。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卷入在整个社会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卷入在公共领域之中,使得我们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小,而我们的自由越来越难以恰当界定,给了公共权力越来越多的可能侵犯个人自由和其他利益。所以,实际上,我们现代人甚至应该更多介入到政治之中。有些人说“不关心政治”,所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无知的;当然,有些人是有些“犬儒主义”的心理,觉得政治肮脏,自己也变得自私而要明哲保身,这些行为和思想既不明智,也不高尚。至少,我跟这些人不是朋友。
DS Wilson和Haidt一样,都想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品。他们俩都是做descriptive研究的现实倾向者。你可能知道我不是,我喜欢predictive研究的理想主义者。差别在于,我们的理想不切实际。就像Taleb在谈黑天鹅时所说,他的理想国,都是由“认知者”组成。类似,我的道德理想国,都是由homo moralis组成,是完全的道德者。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索》中曾提到,所有美德能够集中在一个身上,因为它们是品质的不同方面。类似地,柏林在《自由论》中曾问:像平等和自由这样的美德,能否在一个社会中和谐共存?就像如果我们让人们充分的经商自由,那么必然有人发达有人破产,结果就导致不平等;如果我们要求平等,那么就得限制个人自由。由此引出关于开局自由、结果平等的各种观点,对于这些争执,Haidt在the Righteous Mind中提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关注点不同,有人关注是否存在伤害,有人关注是否存在公平,这种差异,有天生的因素,也有后天(性格养成)环境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基本上内嵌在你的气质之中。王小波在《万寿寺》中,说他自己是个自由派,和学院派势不两立,其实就是他的“大大的”自由派、浪漫派的气质所导致,针对的正是倾向于维持现状、反对变化的保守派。Jonathan Haidt和DS Wilson,和Mercier and Sperber看上去就是现实派、保守派;我和Dawkins、Stanovich、Dennett、王小波这些人就是臭味相投。但是任何这种内在盲目的动力,都是要经过审查和警惕的。你听起来中听的话语,尤其要严加提防。甚至,不仅要不相信那些和你意见一致的人,你或许想问:那相信谁?再听我下一句话:连自己也不要信。就像那个苏联笑话所说:是,我是有意见,但是我不同意我自己的意见。Mercier和Sperber在《理性的迷思》(我不知不觉更改了书名)中说:人们本来要用理性来破解思维的迷雾,但是理性带来了更多的迷雾。我的看法是,按照我的办法,就能破解这种迷雾。Tetlock在《超预测》中说,历史上那些医生,多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有一种“上帝心理”。就像盖伦的说法:如果病人好了,是我治好的;如果死了,说明得了不治之症。波普尔在提出能证伪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时说,阿德勒对于自己的个体心理学就是采用一种证实偏见,找到一个又一个符合的例子。但是不符合的就被选择性失明排除在外了。解毒剂,Telock说,“就是一大勺怀疑”。这也是去掉理性迷雾的清风。那么类似平衡和自由能不能和谐共存?在我的道德理想国中可以,这些都是美德的不同方面而已。你可能还不信,那是因为我解释的不够详细。
我在谈道德问题的时候,总是以苏格拉底为例子,或康德,或斯宾诺莎。但是,这些人都是“异类”。Haidt在the Righteous Mind中说,研究显示,那些伦理学教授、哲学家,道德水准和普通人并无区别,甚至更低。DS Wilson,和Mercier与Sperber一样,研究的对象都是当前的人类大众。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岔路。人类智能的运作,通常是自动的。Kahneman在To Think, Fast and Slow中说,我们大部分都是靠system 1这个自动系统处理日常事情,即靠欲望、直觉、感受、情绪来做事,并不会坐下来,详细分析、反思各种信息,来推论出一个结果。一方面,如Kahneman所说,详细分析这种过程太耗脑力了,只有在system 1出现困难的时候,比如让你计算两位数乘法的时候,你才调动system 2出来;甚至,当让你选择党派、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时候(when?),你都不用动用system 2,你凭直觉就能做出选择。就像研究显示,人们看面相(身高)就把喜好定好了选谁。这有点像玩笑,但是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在《态度转变和社会影响》上,我们经受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来自《可预测的非理性》,往往我们的《Gut Feelings》就把决定给做了。很多人,包括Harari、Gazzaniga和前面提到的几本书的作者,都注意到,市场广告和政治宣传,都在尝试诉诸我们的这些直觉的感受,来诱发我们的某种态度和行为。我记得有一段有新闻说,政府宣传要“接地气”,甚至也采用一些“网络流行语”,这就是一种套近乎的方式。就像一只美洲豹,想要用你当作午餐,但是显然你对你的身体另有打算,不同意它的想法。那么它就可以“喵~、喵~”,像你的家里喵一样让蹭你,让你给它抓抓痒,让你抵抗不住这只大喵的温柔陷阱,然后你就给人家当午餐。但是,理性如何?Mercier和Sperber提出,甚至理性也是一个自动模块,是一种对表征的表征性直觉模块。这就意味着,你的理性不仅有缺陷和偏见,而且“很不理性”。我等谈及这本书时,详细解释其中存在的问题。
DS Wilson和Haidt自然也有理想,务实派的理想往往不明晰。我们理想很明晰,但是不现实。智能的自动化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存在homo moralis。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只能靠一种大脑的生化改造。如何改造?我猜想,应该涉及对incentives相关(如纹状体相关的快乐中枢)的神经回路进行某种修正。具体的做法,容我再慢慢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我要考虑的理性的“心力”有关。在苏格拉底身上,你知道的,理性获得了控制。但是,除了康德和斯宾诺莎,在别人身上似乎更接近Ovid笔下人物所谓的理性选了一条路,但是心却走了另一条。也就是说,常人身上的欲望和直觉更可能获胜。就连Sophocles也说,等我到了老年,我才从爱情的奴役之下解脱出来。那么,如何达到苏格拉底、康德和斯宾诺莎的理性获得对欲望的胜利的程度?这个问题我上次走在街角的时候开始考虑,现在有一些想法,但是等以后再说。
DS Wilson和Haidt的看法一样,他们都是做descriptive研究,发现自然情况下,人们的利他行为,是在“集体利益”层面作出的,所以二人的提议、理想都是,把社会改变为引发人们为集体利益努力的环境。坦白讲,我认同这二位的看法。不,我没有叛变。这里,存在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区分。正如前面提到,人类的智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的。DS Wilson和Haidt,因此就对应人类的这种特点,把人当作一种自动机来进行处理。DS Wilson坚持(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的),群和群之间的自然选择,导致了群内个体的利他行为。确实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即群体之间存在竞争、斗争的时候,群内的团结程度会提高,人们会趋向于抑制自私、增加利他(集体)的感受和行为。Haidt说,911之后,他很激动,想在汽车上贴上美国国旗。他自己意识到,他的“爱国”集体自动模块被触发了。但是他意识到这是不好的,这是一种egocentric自利反应。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时候,政府采用的一种方式当国内出现了什么不良事件、矛盾,就加大某种来自国外威胁的宣传如贸易战,来转移国内视线。实际上这一招应该很灵,因为这正是能刺激“集体利益”模块,能够让人们更仅仅团结在中央某某同志周围,团结一心共斗外来威胁,有维稳、巩固统治的效果。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川普是否能够再次当选?看他现在搞了这么多国外威胁,我预计他大概率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关于群选择的问题,我还不能多谈,但是我认为DS Wilson的群选择理论存在缺陷。我在谈及赖特的Nonzero的时候,已经谈过,蜜蜂的群,和细胞集群类似,但是和人类的群不同。所以DS Wilson的类比,应该也是错误的。在本书中,DS Wilson在计算群间选择导致利他者A-Type在后代中所占比例增大,且适应度超过自私者S-Type的例子,我认为他的计算是错的。如果你恰好读了这个本书或要读这本书,不妨来审查一下我的这个看法。就如DS Wilson和J Haidt所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动机,因此通过改变环境,就能改变人的一些行为。就像DS Wilson所说,人们在一个亲社会环境中,会变得更亲社会,因为这样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反之依然。也就是说,在一个大家都相互合作的环境中,你也合作,你就有好处。就你不合作,你就不利。而在一个大家都相互出卖的环境中过,就你不出卖,那么就你最惨。这就是当年文化上的大革命中为什么学生出卖老师、孩子出卖父母。不是说,这一代人多么没人性,而是环境使得人没人性。DS Wilson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他说,乌龟看到危险,会把头缩到壳中;危险过去,再伸出来。人类也有这种伸缩性,人们进入一个亲社会环境中,亲社会度立马提高;反之亦然。但是,这种灵活性并非完美的。人的先天基因、后天环境养成(从娘胎里就开始),还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就是表观遗传,都会影响到你的亲社会性基础。所谓表观遗传,意思是,如果你父母,甚至你的祖父母,如果亲社会性高,你的亲社会性也可能对应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不平等。当然,环境也影响亲社会性,最富有的孩子不是最亲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富有或有地位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并不就最合作。你知道原因吗?是那些只有部分(经济或社会)资源的孩子合作度最高。我猜想,这就是来自working class甚至poor family的孩子的特征,就像Laureu在Unequal Childhood里所描写的那样。这是我关注的匮乏环境成长出来的孩子的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回头仔细读一读。但是,还有,就是那些最匮乏的孩子,他们亲社会度最低。我猜想这些孩子是那些生活在poor families之中,并且不受父母待见的孩子所发展出来的一种人格适应性。我好像是要说另一点,即不是站在一种“集体”的角度,看社会如何组织,而是站在个体的视角,看如何提高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道德。我相信这就是历史上一些伦理学家的理论视角,就像关于“理性”的历史上的理论,往往也是这种个人视角一样。当然,这就回到了如何升级你的脑力,如果对付自己的自动系统,如果打造一个新的“mindset”,代替原生智能,来获得对本能的超越,给自己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