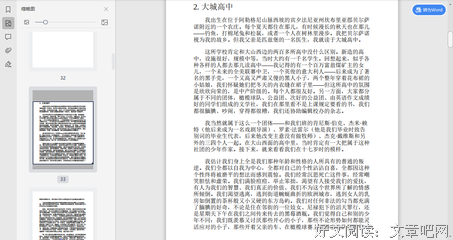流放者归来经典读后感有感
《流放者归来》是一本由[美] 马尔科姆·考利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一):马尔科姆·考利与《流放者归来》
译自Poetry Foundation
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出版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学史《流放者归来》,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重要作家的地位。三十年后,也就是1965年,Literary Times的编辑写道:“在今日美国,马尔科姆·考利是仅次于埃德蒙·威尔逊的最杰出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
1934年初版20世纪30年代早期,考利的名字经常与政治左派联系在一起,但也有评论经常指出,他作为评论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处理。Literary Times的这位编辑写道:“可能没有一个人比考利做得更好……他以其对《袖珍本福克纳选集》出色的介绍,在1946年牢固地确立了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重要作家的地位。”
考利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史家之一,他的《流放的归来》,如果不是20世纪20年代最权威的编年史,也肯定是最受广泛阅读的作品之一。1934年,本书首次出版时,J.D.亚当斯在《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是我们时代一个作家的真诚尝试,他阐述了他自己和他那一代人,追踪了他们观念的流变,以及他在成长岁月中受到的其他影响。考利先生的书是极具价值的文献。未来的文学史家会对本书感兴趣,就像考利先生的同时代人对这本书感兴趣一样……”1951年,《流放者归来》修订版出版,引来了更多的好评。劳埃德·莫里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中称赞“在对传奇般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生活的所有描述中,本书是最为动人的”,并说本书“为美国小说和诗歌复兴的时代提供了一幅亲密而真实的写照”。J.W.克鲁奇在《周六文学评论》中说:“考利先生对包括乔伊斯、T.S.艾略特、普鲁斯特等老一辈最为成功的作家的评论非常酷,而且总体上远远超出了偶像崇拜的范畴。但这些评论看起来又极为公正,而他对巴黎左岸和格林威治村的描述色彩斑澜,又丝毫没有夸张之处。”
考利另外一部大获好评的文学史著作是《第二朵花:迷惘的一代的作品和岁月》。本书涉及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E.E.卡明斯、桑顿·怀尔德、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哈特·克莱恩的作品。《纽约时报》评论道:“这证明了考利作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天赋,他的视角是新颖的;也就是说,他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洞察,和他对这些作家本人的刻画,同样引人瞩目。”
刘易斯·P.辛普森在《西瓦尼评论》中写道,考利把自己职业生涯的一部分献给了“将美国作家从疏离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根据辛普森的说法,疏离的主题贯穿了考利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诗歌。“作为‘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创造者和诠释者,”这位评论家继续说道,“考利对这一代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定义了一种名为‘流放诗学’的创造力神话或传奇。”他先是理解了美国作家童年时期的流放状态,接着理解了他对社会的流放,最后是对自我完整性的流放。在《流放者归来》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前两个“阶段”;而在他的诗集《蓝色的朱尼亚塔》中,第三个阶段——自我流放——是显而易见的。
在接受艾伦·盖勒的采访时,考利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与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我认为现在有一群非常有趣的作家。”他提到了索尔·贝娄和约翰·契弗,认为他们是这一群作家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品味)变得更加成熟了。它是否变得更好,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它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参考点。”他还说:“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没有人再相信他有责任或能力以任何程度或方式重塑或改变环境。”
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考利对《南方评论》的采访者黛安·U.艾森伯格说:“我并没有强迫自己去写一些别人真正期望我写的大作品。我也有机会,但我没有强迫自己去完成。事实上,我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把自己逼得够狠,这是我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都在文学领域度过感到满意。他对艾森伯格说:“作家的职业是把文字转换成模式,这是一项费力、乏味但可爱的工作。我热爱这个行业。而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
考利的大部分著作是在他70岁生日之后出版的。1983年,他停止了写作,从此一直在从事文学研究这一副业。他的文件存放在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和耶鲁大学。“太多该死的论文了,” 他在去世前四年,也就是1989年说,“剩下的时间不够了。”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二):流放者尚未归来,我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初版于1934年。
193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美国经历了股市大崩盘、经济萧条,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社会刚刚有所起色。
很多作品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关键节点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社会思潮的形成。
《流放者归来》完成了对整整一代人思考总结之大成。这一代人被叫作“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坦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用作了《太阳照样升起》(1926)的题词。对于经历杀戮和死亡场景的海明威来说,“迷惘的一代”这个称谓有一种特殊的权威,它传递了一种观念,在那些一战幸存的年轻人的心灵里,残酷的战争和战后放荡奢靡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收藏家,花园街27号沙龙主人。在当时巴黎艺术圈有非凡影响力,是最早扶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家之一,艺术青年、作家对她的沙龙趋之若鹜。马尔科姆·考利的概括:“他们是迷惘的一代,首先因为他们被连根拔除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几乎切断了他们和任何传统或地域之间的纽带。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另一种生活准备的,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在战后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也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找乐子的生活)。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想要生活在流放中。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过去的那套行为规范,也因为他们对社会及作家在其中的地位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一代作家属于已经固定下来的旧价值观和尚待确立的新价值观之间的一个过渡期。”这段话很重要,特摘录。
这段话出现在《流放者归来》的序言,这个序言并非写于1934年,而是1951年该书重版时的产物。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在本书导读中指出,在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想要表达的是在发展中的的美国文学传统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到了1951年,公众已经对这种传统以及考利和他的同辈人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有了认识。福克纳认为1951年是重版该书的绝佳时机,考利也说50年代已经不是“喜欢认真思考的一小撮酒鬼”的时代,而是“美国文艺的关键时期”。《流放者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后在美重印了三十次。
莎士比亚书店,诞生于一战之后, 主要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当时在巴黎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都是书店主人西尔维亚·毕奇的座上客。1951年版对1934年版的正文没有大的修改。1934年,与在此之前,当考利提笔之时,并不是1951年序言所表现的外部审视态度,他不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文献式的综述,《流放者归来》是一部自我代入感强烈的文学作品,它采用了“我们”的叙事角度和抒情笔调,用不断呼唤的“我们”作为一种缔造传统和召集令的方式——“我们”是同时代人。
这部作品是从马尔科姆·考利的成长经历与学校生涯说起的,一旦回望青春,我们的心中想必也会泛起类似的记忆与情绪。这是《流放者归来》越出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年轻作家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从家庭背景上看,“迷惘的一代”大部分作家,海明威、帕索斯、菲茨杰拉德、E.E.卡明斯等人,都是像考利那样,出身于医生、律师、农场主或商人等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多半在公立学校就读,在学业过程里逐步改变了乡土气,成为放眼世界特别是被巴黎气息、被欧洲文化吸引的年轻人。他们极少受美国的历史束缚,他们割断了地域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可是,1919年之后,世纪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让他们感到愤怒,而诸如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技术的革新,又让他们着迷,他们在分歧中、怀疑中、疏离中做了一些自己从前不以为然的事情,过度的自怜和夸大的自我意识让他们隐现灵魂危机,陷入迷惘。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泽尔达、女儿司各特。实际上,“迷惘的一代”作家要比他们前一代的作家,比如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等人幸运得多,其中的许多人没到三十岁就成了有国际声望的小说家。“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是当时流行的选择。他们试图避开美国压抑的清教徒氛围,避开商业社会的粗俗、单调、沉闷和道德上的因循守旧,他们想在欧洲的自由空气里寻找自我的生活模式。然而,这个松散的共同体的瓦解是非常快的。欧洲在一战后的经济危机急遽地改变了“迷惘的一代”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那些原来居住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那些饱经达达主义、立体主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熏陶的年轻人,忽然发现美国和美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现在却要由边缘重新进入中心,必须快速调整他们对于文学的社会意义,对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
对于马尔科姆·考利来说,那些无法再把年轻人和外界事物联系起来,甚至无法使年轻人彼此联系起来的道路似乎仍旧指引着他和他的同代人。1934年的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像是刚刚经历一战、在废墟里挣扎重建的欧洲。马尔科姆·考利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怀旧的情感,渴望回到一些失落的、依旧残留在记忆中的地方或一些依稀仿佛的所在,但也伴随着对未来的兴奋乃至恐惧。失去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刺激考利不断翻阅“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理想的破灭保留着一种美感,年轻人注定要情愿或不情愿地从他们的文化困境中突围,《流放者归来》以“一本描述思想的书”的尝试来力求表现这个过程。
流放与归来,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写作者的宿命。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文化赋权之间的张力,促使作家主动理解自己在创作与世界的关联上的深刻投入。那种切断了传统或地域纽带的感受,迫使作家们或者所有飘离的人们从被留在身后之地和实际的此时此地两个角度来分析事物、看待自身,1951年的马尔科姆·考利、1934年的马尔科姆·考利,更早时的马尔科姆·考利,与他的伙伴是同时代人。“我们”与“他们”,也是同时代人。
北京日报 “迷惘的一代”,创作与世界的关联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三):《归来》by 许知远——转载自《单读06》
哈罗德·斯特恩斯归来了。在巴黎游荡了12年后,他回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切——声誉、才华、女人、公寓……
这是充满反讽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国的青年逃离自己的国家,前往巴黎寻找传统、自由与创造力。
不过31岁时,他就主编出文集《美国的文明》,他和同代的作家与学者在其中诅咒自己的国家,认定它无根、偏狭、市侩,倘若你想保持自由灵魂、体会文化的丰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欧洲。
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群美国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他们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不到三十岁,他们中最有才华、最幸运的就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因为远离,他们重新发现了美国,而借助欧洲的现代主义视角,他们描绘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机勃勃的幻灭感、一种自怜的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轻时,我迷恋这个故事。倘若“迷惘一代”为美国社会的迅速、戏剧性转变感到无根之痛,在巨大的商业与技术变革前陷入边缘,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的我同样如此。我反复阅读着迈克·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寻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流放异乡的浪漫感与归来时的荣耀。
哈罗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着探索与荣耀,而是对雄心与创造力的摧毁。他成了自己引领的潮流的牺牲品。在巴黎时,他常没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睡觉,海明威讥笑说“躺在那里的是‘美国文明’”。回到纽约后,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编辑了一本文集,却再也不能找回他失去的影响力。社会情绪早已转变,美国对欧洲的焦虑迅速的减弱,大萧条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入更极端的情绪,让他们憧憬的是苏联的试验、是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式的独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点了一杯old fashion,再度翻阅起《流放者归来》。这酒店名与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无关系。在20世纪初,这片凌乱区域曾是反叛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那是一个J.P.摩根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唯有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来对抗这强大的外在秩序。他们彼此谩骂与安慰,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倘若这仍让人窒息,他们就逃离。迈克·考利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往返。
而如今,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顿昂贵的时髦的象征之一。在昏暗的灯光下,Art Deco的设计过分精致,一楼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们都有一种刻意的随意。杯中的黑麦威士忌过分爽口,毫不苦涩。我的意外不无矫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亚的味道。自消费主义诞生以来,昨日的异端总是轻易地化作今日的流行。
还是说,我的这感慨本就过分矫情。反叛从不是这么浪漫,贫穷艺术家并不总占据道德与审美上的制高点,总是逆潮流。
一个世纪前的格林威治的艺术家们不仅被粗鄙的物质时代压抑,他们也受惠于一个蓬勃的商业文明。这个商业时代催生出人们消费热情,现代大众媒体与娱乐就此诞生。印刷业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写作者——不管是小说家、杂志编辑、广告文案、还是编剧——都成为一种新时尚。而当他们逃往欧洲时,他们不仅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那样糟糕,更发现美国蓬勃经济、坚挺的汇率,能让他们以更放纵的方式享受这个老欧洲。而当他们中的杰出者获得世界性承认时,你很难说它与美国日渐重要的国际地位无关,世界开始关心美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930年把文学奖授予辛克莱·刘易斯时这样声称“他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溶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中。伟大的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
这评语也像是对爱默生一个世纪前的感叹的回应。这位美国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国文化能摆脱对英国的附庸地位,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品位。在几代人之后,它在“迷惘一代”身上实现了。在这漫长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遗忘。很有可能,他们并非不够杰出,而仅仅是运气不佳。比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更年长一代的作家们,成长于1890年代,从未迎来他们的绽放时刻,他们被时代的转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许更具普遍性。如今想来,是《流放者归来》记录的荣耀、而不是挫败,才是击中了我的原因,没有日后的荣耀,这挫败会显得过分窒息。但历史中的基调却是挫败。
挫败却却激起另一种回想。在“迷惘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说家们,世界开始兴奋于美国人怎么感受,却还没准备严肃对待他们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涌来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被这个国家的浅薄所震惊。直到1960年代,这个状况才因“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而改变——美国人也能为时代提供崭新的分析。哈罗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遗忘的先驱者。
二
对于纽约,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个城市自然迷人,自从1930年代以来,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与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别的国家与文化的流放者们的梦幻之地——你逃避家乡的逼仄,赢得新的荣光。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放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或是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他们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八十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驱使他们获这成功的除去个人的创造力,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灾难、然后戏剧性崛起,把他们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合作。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艺术与世界性的财富从来就结为一体,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正代表财富的新潮流。
但他们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小部分。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是另一种命运,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性的。他们与这群中央的艺术家是同代人,他们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戏剧性地逆转。但他们从事的事业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空洞口号中。他们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它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的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 Arias曾写道,他目睹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他们就必须自我流放。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经常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地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过分功利性。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恐惧本身的价值。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四):马尔科姆·考利:美国文学史的亲历、书写与旁观者
对于爱书人而言,一次性批量收入某个心仪作家或主题的系列作品,无疑是最幸运的书事之一。更何况这批书籍被大洋彼岸的藏家颇为精细地保存了数十年之久,且本本都有原作者亲笔签名或题词。因此,当我从漂洋过海而来的书箱中逐册拆开这些珍贵的签赠本时,那种满满的幸福感是可想而知的。
马尔科姆·考利的九本签赠本和《流放者归来》2021年最新中文精装版这批藏书一共九本,得自纽约一家旧书商,作者是我自大学时代起就颇为喜爱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
考利在每一本书上的亲笔题赠据书商所言,其中八本的前主人约翰·佩里(John Perry)是考利的生前好友,因此这八本书也基本上囊括了考利自《流放者归来》(Exile's Return,1934年)以来五十年创作生涯的所有代表作。另外一本考利晚年作品《八十岁的展望》(The View from 80,1981年),则来自考利的晚辈同行——同为文学评论家的唐纳德·福克纳(Donald Faulkner,1952-2018)。
马尔科姆·考利的九本签赠本和《流放者归来》2021年最新中文精装版更为有趣的是,在我拆开这册书的塑封时,还自书中掉落一封考利写给福克纳的亲笔信,泛黄的考利专用信纸,正文由打字机打出,落款亲签,实乃意外之喜。从信中内容来看,语带诙谐的寒暄之后仍是学术往来,大意是考利告知对方在得到出版方Viking授权后即可正常引用书中观点,还很贴心地写明了有关内容在书中的具体位置,其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可见一斑。这一点在日后以诺奖得主威廉·福克纳为首的同辈及后备作家的回忆文字中也多有反映。
马尔科姆·考利1982年写给唐纳德·福克纳的亲笔信考利生前一直被称作美国文学史的活化石,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他生前的近一百年里,几乎亲历和见证了美国每一次文学潮流的兴衰,又与每一个潮起潮落的知名作家都有交情或交集,同时也能以参与者的狂热心态和旁观者冷静视角将每一段潮流以文字方式记录和书写下来,最终让自己也成为了文学史本身。
考利1898年8月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尔萨诺(Belsano),成长于匹兹堡(Pittsburgh),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不过,与整整一代美国文艺青年类似,他在哈佛的教育因一战爆发而中断。1917年,考利以救护车司机身份加入美国野战部队,奔赴法国前线。一年后战争结束,考利返回哈佛,两年后顺利毕业,并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以为杂志撰写书评谋生。
1921年,考利获得美国野战部队奖学金一万两千法郎(大致相当于一千美元),携妻赴法国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留学,1923年返美。在法期间,考利一边研究法国古典文学,一遍为杂志撰稿试笔,同时还结识了很多当时自我放逐至法国的伟大作家、艺术家如庞德、斯坦因、艾略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普鲁斯特、瓦雷里等,受其影响同时也吸收了阿拉贡所推崇的达达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和历史观。
回国后,考利在1929年大萧条伊始接棒前辈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担任《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长达十五年之久,就此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中坚力量。日后成为考利最著名作品(同时也是美国文学史旗帜性著作的)《流放者归来》一书最初的章节,便是这一时期撰写并陆续发表于《新共和》的。
《流放者归来》中文版英文版合影《流放者归来》1934年初版时的副题写作“思想的记述”(A Narrative of Ideas),1951年考利亲自修订时改为“1920年代的文学浪游史”(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 1920‘s),此后便以这一修订版行世。因此,考利的视角,不是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为整整一代人树碑立传(这代人日后被称作“迷惘的一代”,包括考利自己),考利所追记的,不是文学史单纯的文献式记录或总结,而是思想的源流与变迁。
在考利笔下,这代人先后经历过多次流放与归来。先是世纪之交与故乡小城的分离,流放于大城市的校园;接着是学业被一战中断奔赴欧洲,流放于战火之中;之后是硝烟散尽后肉体的流放结束,但精神家园无尽空虚,于是再次自我放逐至巴黎游学;最后是不论各自是否能找回自我,也都渐次返回美国,哪怕继续着精神放逐。好在无论是精神还是地理上的流放,这代人最终都通过写作实现了回归。也正是从这一代人起,美国文学正式从欧洲文学、英国文学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旗手;而考利和他的《流放者归来》等作品,正是实至名归的摇旗呐喊者和推波助澜人。
我是在上世纪末的人民大学图书馆里无意中读到《流放者归来》中文版的,只是当时既不了解考利本人,也不知道那本1986年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精装本正是本书的中文首版。但读完后就大为激赏,留下了极深印象。所以2006年华章同人再版列入“重现经典”丛书时,我也朝花夕拾般买了一本回家,重温那个伟大年代的同时,其实也重拾了自己的阅读记忆。再之后就是去年这批来自考利故乡的签赠本,基本上涵盖了美国近百年文学史的方方面面,蔚为大观。其中那本《流放者归来》蝴蝶页上赫然被考利自豪地写着“五十年后(1984年)仍在重印”的题赠,而事实证明,又过了三十多年,本书依旧在全世界范围内重印。这不,最新的中文精装版上个月由浦睿文化再版,到手后我翻开起首一篇长长的导读,发现竟是我那封信的主人、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所写,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考利亲笔题赠:五十年后仍在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