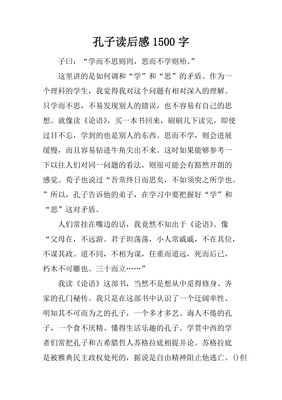孔子读后感精选
《孔子》是一本由[日] 和辻哲郎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孔子》读后感(一):跟着友邻读书
也许是因为友邻翻译的书,认认真真读了好几个午后,可是想写短评的时候却迟迟下不了笔。凭感觉读书,读完情绪复杂地不得了,却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是从硕士开始就有的坏毛病,想要改过来就很困难。
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非常喜欢孔子,平时讲教育史,每每都会拿孔子做例子,可是很多时候我体会不到那种亲切感,常常不能感同身受。现在想来,应该是我分不清孔子、汉儒和宋学的区别,层层叠加的文化传统,混淆在一起造成的错位。正是基于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视,和辻哲郎的《孔子》在开篇并没有介绍孔子的生平事迹而是谈到了对历史的理解。
序言和译后记都说到作者把孔子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下,与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一起被称之为“人类的教师”。虽然孔子早就教导过“性相近”“习相远”,但从不同文化的特异之处找到它们的共性,而不是光顾了偏向于各自的习俗,在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它不仅有宏阔的视野,也包含着一种宽厚的胸襟。当然,小而精深的研究不仅耗费精力,多少也限制了某些具体理解的可能性。
有些地方,作者常常给出出乎意料却又合情合理的解释。比如孔子在知天命的年纪从政,作者解释说“孔子能够脱离出四十来岁时的理想主义下的焦躁感,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介入了势必要有所妥协的现实政治之中。这种体验,才让孔子做好了进入耳顺心境的准备。”这样的结论虽然值得商榷,但是考证和论证的过程看得很过瘾!傅老师的序言当然赛高,译后记也很感人,感谢译者把这样的“小书”介绍给我们,也想问问译者,为啥觉得自己有义务翻译这本书呢?
最后,把这段话送给这位我非常尊敬又喜欢孔子的老师,“学者,则应当超越贫富,唯乐于道,唯好于礼而已。这种道,便是无限的修养。所谓‘切磋琢磨’,则是用来形容这样一种没有止境的、无限的道。”
《孔子》读后感(二):哲学研究视角下的孔子
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把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这“世界四圣”拉出来做对比,并提出了他们都是“人类的教师”的观点。这几位人类的教师不同于英雄与稻草人,他们之所以是“人类的教师”,不取决于少数者的洞察,也不在于是否获得了同时代大众的承认,而在于他们人格与思想贯穿世代的感化与影响,与孕育他们的文化作为契机。作者认为这些古代文化,在孕育出来以上思维伟大教师后也就达到了巅峰,并暂时走向了完结。文字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各朝文化的统一,作者尽管认可汉字的独特机能,却并不认为先秦文化或汉文化被完全一贯地继承了下来。基于此,他视孔子为先秦文化的结晶,并指出了各朝各代对于孔子的理解存在差异,至此“人类教师的普遍性”论证完成。
第二章题为人类教师的传记,这种传记有别于传统人物传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在长时间的过程中由无数人所怀抱的理想所凝结而成的“理想人”的形象,更接近于一种文化史上的发展。而当真正追溯他们真实的形象时,可信的信息与真实的记叙显得尤为稀少。作者在本章中对于部分文本内容的阐述似乎有很大程度上的偏离原意,解读上也带有非常明显的日本文化视角。
第三章主要是对《论语》的原典批判,作者贡献出了一些颇为有趣的观点。如对于“吾十有五志于学”一句,他想到的是圣人也并非在幼年时就醉心学习,倒不失为一种众人可以采纳的一种乐观的看法。人人均可以效仿的“人生历程”也将孔子对于自己一生的概况推及了人类的高度,视野开阔。
第四章关于人类教师的死亡的探讨非常惊艳。作者指出,其他三圣之死都被赋予了极为重大的意义,他们生前的教诲借着死亡的机缘展现出更为强大的效果——死亡本身便是对自由的觉悟。而只有孔子之死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孔子传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将死设定为中心的祖师传。“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说教没有神秘色彩。比起其他三位革新家,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将孔子归为原初型的思想家。孔子的语录比起其他三圣戏曲结构式的故事也显得尤为简明。
整本书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国内传统的研究视角,对于四圣的对比探讨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展现了孔子作为人类教师的普遍性与独特性。
《孔子》读后感(三):《孔子》:日本学者和辻哲郎从文本中批判性的解读孔子生平和理论
孔子在中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们了解孔子,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民间传说、正史记载,当然还有他人的论著。如果还是不行,我们可以到孔子的家乡去拜访、去探寻、去寻找孔子曾经的足迹。 但今天我拿到的这一本关于《孔子》的著作,是极为另类的一部,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由日本人所著,更是它内容的另辟蹊径。他引用的资料也仅仅是《论语》和《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他所看的这些资料就还不是中文原本,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译注,但他却写出了非常另类,但有言之成理的学术见解。 这位日本学者就是和辻哲郎 ,他被我们中国学者所认识是因为他的著作《风土》,而这本小书《孔子》,是他1938年出版的“大教育家文库”中的一本,是向日本介绍古今中外的著名教育家的科普书籍。因此,在这本书中把孔子叫作教师也就顺理成章了。
和辻哲郎在这本中,开篇就把孔子和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并称为四圣,分别代表了世界闻名的四个地区教师的代表。他们作为教师,必然有着优秀的徒弟,他们的理论就这样传递给徒弟,传递到了后世,深远的影响了曾经当地的民众。释迦牟尼之于印度,苏格拉底之于希腊,耶稣之于犹太地区,孔子之于中华文明,之于中国黄河领域,都有的深邃的影响。 他们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他们的生平考察,和辻哲郎提出了他的质疑。毕竟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都是在他们死后上百或几百年之后,才确认并记录在案。这就一定有着非常大的出入。对于孔子,和辻哲郎指出,他的生平大多来自于《史记》,而《史记》的成书年代,已经是在孔子去世三百多年之后了,其中有错误,那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和辻哲郎对于其中的异议之处,逐条进行分析批判,指出了很多更加不确定的结论。
我们不去评论和辻哲郎的这些结论对还是不对。毕竟我们无法穿越到孔子生活的年代,对于他的事情,我们和和辻哲郎一样要根据现有记录的去研究,但现存的记录,有很多是根据当时现实的需要而做的修改或者创造。文本的东西本来就有相应的目的性,这样理解也是可以成立的。比如,作者认为老子和孔子的会面是汉代儒学家为了让两大正统的儒教和道教在最开始之初就有在相应的碰撞而创造,既可以提高相应的地位又可以得出孔子虚心请教的形象。这种理解也是说得通的,这样解释孔子生平的内容,书中还有很多。同时,作者对于《论语》也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 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和辻哲郎解读出来的观点,但批判性解读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的。历史上的这些文字,包括《论语》,写出来之后,就已经不再属于作者,而怎样解读的权利,已然在后世的读者。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丰富填充这些内容,特别像《论语》这种语录体,截取生活中一两个片段,没有前后的语境,本身就有着非常大的歧义。我们通过思考,去揣摩、去恢复当时的情境,凭自己的想法还原当时孔子的和他的弟子们要传达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读书并思考的重要意义所在。
和辻哲郎写了一本《孔子》,给我们了一种批判意识,阅读这本书让我们以另外一种眼光来审视孔子,审视他的《论语》。阅读这本书,也许能够给我们理解儒家文化另外的启迪,这也就不失阅读此书的意义所在了。
《孔子》读后感(四):理想主义者的焦虑 | 夏目漱石门生这样解读孔子的一生
市面上研究孔子的书不可胜数,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发现不一样的孔子?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本哲学视角的孔子普及读物,作者是日本“哲学泰斗”和辻哲郎。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与伦理学家,他研究孔子的专著《孔子》一书八十多年前出版,曾在日本风行。近日,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次在中国面世。该书受到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论语》的李零教授与曾在复旦大学讲授《论语》的傅杰教授一致推荐。现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的傅杰应邀为中译本作序,以下序文经授权发布。
跟众多日本的孔子研究者不同,本书作者和辻哲郎(1889—1960)不是汉学家,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与伦理学家。他生在村医之家,中学时代因困扰于信仰与人生意义的问题而沉迷文学,二十岁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决定以学术为志业,二十四岁出版《尼采研究》,二十六岁出版《克尔凯郭尔》,一生著作等身,全集逾二十卷,曾任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也是日本伦理学会多届会长,代表作有《伦理学》《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人格与人性》《日本伦理学史》《日本精神史研究》等,其伦理学说被称为“和辻伦理学”。
和辻哲郎
以日本所受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身为研究日本精神文化的巨擘,和辻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当然不会陌生,在著作中多有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讨论,也写过不止一篇的专门文章,以至于他的弟子径称读和辻的著作,可以深感他是以受过儒家熏陶之眼来看西方传统的,也是从儒家道德的视角来界定伦理学的。所以在已名满天下、诸务缠身之际,收到撰著《孔子》的邀约,虽然他自谦无研究、无学养、无准备,却还是欣然命笔。从本书在日本的风行,到今天有了中译本,历史证明他八十多年前的心血没有白费。
正如在本书中和辻自己提及的,他著有《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与《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他没有提及的是他还与人合译过《希腊天才之诸相》(后重译改题为《希腊精神的存在形式》),可知他对佛教、基督教、古希腊哲学都有着非同泛泛的理解与把握。
在本书前两章,他把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作为不同文化的人类教师的代表进行了比较。和辻肯定了把他们合称为“四圣”的说法,因为这包含了一种“不是只偏向于西方,而是能够广阔地纵观世界的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将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以及征服了欧洲文化的犹太文化,“平等地予以极高的评价”。这自然是通达的认识,不仅比西方文化中心论者理性,也可能比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视释迦牟尼与耶稣为“偏至型的圣贤”而孔子为“圆满型的圣贤”的论断更易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
和辻复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的事迹作参照,通过对《史记·孔子世家》的讨论,指出这些人类的教师往往都有很好的弟子,他们坚信自己的老师乃是真正的“道”的体悟者,他们宣扬老师的道,也实践老师的道。亲受过感化的弟子们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教师最卓越、最值得感悟的地方;而对无缘亲炙者而言,只能从前辈所传递下来的局部印象来认识他们。
随着时间推移,经过层累式的叠加,遂使“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认为,人之为人、最深的智慧与人格,都可以在这些教师身上窥见。这便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形象的凝结过程。如果这么看的话,人类的教师,只能说是在长时间的过程中,因为无数人所怀抱的理想而被创造出来的‘理想人’的形象”。
如果人类的教师确属这样的“理想人”:那么,有关他们的真正的传记,就必须被理解为上面所说的这种凝结的过程。这应当被视为一种文化史上的发展,而不是一种个人的生涯。然而一直以来,这些人类教师的传记都往往只是被理解成一个个人的生涯记录而已。因此,当我们追问这些传记中有多少真实性的时候,就常常不免有一些强烈的疑惑之感涌现出来。
这样的人类教师的传记,都是记叙非常含糊的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性“非常难讲”。而孔子正是作为“先秦文化的结晶”出现、在后来的文化中得到传承延续的,“汉代的儒学是基于其所理解的孔子,创造了汉代文化,宋学也是基于其所理解的独特的孔子,创造了宋代文化。正是随着这一历史的发展,作为鲁国一夫子,孔子获得了作为人类教师的普遍性。在这一点上,孔子和其他人类的教师并无不同之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洞见,这样的文化比较,也才是既融通透彻又足以给人以启迪的文化比较。
如前所述,和辻不是专业的汉学家,他对《论语》的认识与理解主要依傍的是日本以实证见长的中国哲学名家武内义雄的著述。他引据的《论语》文本是武内义雄译注的岩波文库本,他对《论语》全书结构的把握也以武内的考辨为基础,作了推衍发挥。
武内1929年在《支那学》上发表的《论语原始》,他的相关演讲让和辻深为折服。1939年武内的《论语之研究》出版,和辻又撰写推荐专文(见本书附录),誉称将来的《论语》研究“必将以此为出发点”。因为武内融会古来中日学者关于《论语》的辨证成果,条分缕析,将《论语》二十章厘为四个部分,即所谓河间七篇本、齐人所传七篇、齐鲁二篇本和另外的《子罕》《季氏》《阳货》《微子》等篇,企图以此明断《论语》各篇形成的先后,甚至进一步考定儒家不同学派的思想演进,通过这种对《论语》原典的批判来究明早期儒家思想的变迁过程。
他坚持研究经典必须“弄清书籍的来历,进行严密的原典批判”,这种努力是可贵的。然而《论语》成书既早,史籍中未见明确的编纂情况记录,编排既不易看出严密的系统,又语多片断且往往缺乏可相照应的语境,面对这样的古代文本,其实到现在我们也不具备彻底弄清其来历的条件。所以尽管武内功力湛深,作的推论乍看令人惊艳,细审之下必然仍多疑窦。
年辈稍晚重译过《论语》的日本史学大家宫崎市定曾自述:
武内博士的考证极其细致慎重,一步一步地推进,可以说一点隙缝都没有。同时代的和辻哲郎著有《孔子》一书,基本上就采纳了武内博士的说法,并且极口称赞。我自己最初读到武内博士的这一新说时,感觉从考证学的奥义来看,简直不可能超出其右,几乎让人惊叹这已经就是最后的铁案了。然而,今天我自己来研究《论语》,为了把武内博士的学说介绍给读者而重读此书时,却产生了各种各样新的疑惑。(《论语研究史》,童岭译)
宫崎重审史料,以为“与其从武内博士的新说,不如从以往传统的通说”,这应该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数学者的共识。如日本的古文字学大家白川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著的《孔子传》中就明确表示:“同《圣经》一样,《论语》也是需要严密的批判的一本书。不过说起这种严密的批判研究,尽管前辈学者已经做了诸多出色的工作,但仍然没有显示出充分的成果。”
由于是同类性质的著作,又特别言及了原典批判,白川静的话也许就是针对武内与和辻说的——毕竟和辻是武内最坚定、最著名的拥护者,宫崎也才会在涉及武内的观点时特别提到他。武内的学说既然不能成立,和辻某些立论也就失去了根基,这是显而易见、毋庸讳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章“《论语》原典批判”就失去了价值。
首先,我们仍然可以借此了解武内与和辻在《论语》文本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其次更重要的是,尽管和辻对《论语》文本构成的分析时见意必之辞,但他终究是一位有着通透人生观与敏锐洞察力的大哲,而且还是一位对文学有深切爱好与很高素养的大哲——他从青年时代就跟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等文豪有往来,向往成为如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诗人哲学家,所以他对《论语》的阐说往往具有不同于他人的光芒。
例如他对众所熟知的《论语》第一章《学而》第一节孔子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论述:
这很明显是孔子学徒们的一种学究生活的座右铭。这三句话,并不是孔子在特定的什么时候,向特定的某个人说的话,而是要从孔子的话中,选出几句作为学园生活的座右铭时,被挑选、并列于一处的三句话。
也即是说,第一是学问之喜,第二是因为学问而结成的友爱的共同体之喜,第三是在共同体中的所得,只是为了自己人格及生命价值的提升,其目的只在自己身上,并不关涉名利,这里是标举出来学问生活的目标所在。这反映了当时学者未必为世所用的时势,抑或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不过,提出这样主张的人,肯定是一个理解上述学问精神的人。这种精神不仅在柏拉图的学园、释迦牟尼的僧伽、基督的教会中所共通,而且即便到现在,也不失其共通性。以上三句中所呈现出来的学问的精神倘若失去了,那么一种活生生的学问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这里有宏阔的视野,有入微的体会,有精彩的引申,其境界不是一般讲《论语》的学者所易达到的。又比如《为政》篇里孔子那节著名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明儒顾宪成称这是“吾夫子一生年谱,亦便是千古作圣妙诀”,出语甚简,陈义甚高。后人则每在孔子所志何学、立个什么等等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上作过深而无谓的凿求。和辻则把孔子六十以前的所历全视为普通人的普通境遇,以之为“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阶段”,从这里正“彰显了孔子作为人类教师的意义”。这个看去卑之无甚高论的体会,或反而是能使广大读者更觉亲切、更能从中得到启示的。
就这样和辻把《论语》中尤其是跟孔子生平事迹相关的章节做了诠释,多有常人所不能道的可圈可点之处,读者不难覆按,自无需在这里多加引录,但我依然不避累赘,忍不住要在这里再引述一下和辻对《论语》阅读方法的提示。
在序言中,他开宗明义表示他的“志向在于让那些至今还从未接触过孔子的人,也会有一种想要将《论语》熟读玩味一番的兴致”;在第四章“孔子的传记及语录特征”中,他苦劝想要接近孔子思想的读者“反反复复熟读《论语》”,因为“《论语》中藏有无数的珍宝,而且是不能用其他的语言来重新讲述一遍的。而且,这些孔子的话都凝结成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句子,唯其如此,原初型的思想家孔子才会成为一位永远的思想家”,而孔子语录的样式乃是独具特点的:
毫无疑问,《论语》中孔子的话,都是为了传递孔子的思想,然而,这并不是单纯地将一些具备客观意思的内容,以一种逻辑的方式讲述出来。孔子本人,在向弟子说教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将他的思考建立在一种缜密的秩序之上加以论述,但就《论语》而言,书中所收录的均是那种短小的、格言式的命题。这当中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记录的是孔子和弟子之间的问答,还有一种则是完全独立的命题。问答,是和孔子的言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问答,不是用语言将一种定义确切、毫无歧义的思想表现出来,而是以孔子和弟子从人格层面的交流为背景,展现一种活生生的对话关系。由此,在对话之中,孔门弟子们的人物和性格,其问答进行时的境遇等等,均可以被掌握到。这就成为这些对话的一个背景,并为这些对话的命题带来了更多意蕴和话外之音。然而,孔子的对话,并不像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对问题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展开,而是以弟子问、老师答这样的形式就能完结的对话。也即是说,这些对话都是一个回合即决定胜负。因此,这些对话只针对关键之处展开。孔子的回答,以一种非常简洁、锐利甚或是一种立意新奇的形式被刻画了下来。
因此,“我们在阅读、玩味这类问答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思想运动,而是能感觉到,我们和那些孕育了这些思想的人,有了活生生的接触”。因此在对《论语》进行文本梳理、语句分析的同时,他还这样以诗人的眼光来欣赏《论语》,以哲人的心灵来体悟《论语》,而这样的眼光与心灵,在诗人哲学家和辻哲郎的身上获得了有机的统一,也在他的这本不同凡响的《孔子》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
《孔子》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和辻哲郎研究孔子的专著,作者精通东西方哲学,被誉为“日本比较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书中提出了“人类的教师”的概念,将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等先哲做比较,并分析了“世界四圣”为什么会成为圣人;梳理了四位先哲的传记,重点对与孔子相关的史料,如《孔子世家》《孟子》等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中的不可信性;此外,作者从《论语》 原典出发,对这本书的成书早晚、编排次序、语录体特征进行了分析,重新考察了有子、颜渊、子路等重要人物。
总之,这是一本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经典小书,有宏观的世界文化比较,有敏锐的深刻洞察,也有充满哲思的人生感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形象。
北京大学李零:“中国古礼最重“天地君亲师”,孔子是其中的“师”。作者从《论语》研究这位“老师”,有四个切入点:一是与世界级的其他“老师”做比较,二是把《论语》当这位“老师”的传记读,三是分析《论语》的“地层叠压”,四是从语录体把握其形式特点。这四点,除第三点存在很大难度,方法可商,其他都是阅读《论语》的不二法门。”
浙江大学傅杰:“在对《论语》进行文本梳理、语句分析的同时,作者还以诗人的眼光来欣赏《论语》,以哲人的心灵来体悟《论语》,而这样的眼光与心灵,在诗人哲学家和辻哲郎的身上获得了有机的统一,也在他的这本不同凡响的《孔子》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