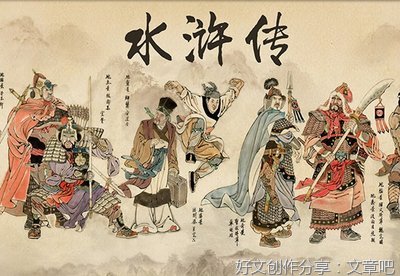竟然是真的读后感锦集
《竟然是真的》是一本由刘天昭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52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02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竟然是真的》读后感(一):人生的勇气来自独处 和持续供给的虚荣
刘昭天的书《毫无必要的热情》被朋友推荐了多次可仍未拿起来看完,今日在书店偶遇新书《竟然是真的》,还是本诗集,凭着“遇到了就是种缘分”的心态看了起来,似乎更能理解“毫无必要的热情”的这个状态了。 生活中总会有偶尔的灵光一闪,似乎周身都变轻了,眼睛模糊了,声音遥远了,光反而清晰了,那种持续的瞬间好像脱离了现实的生活而飘荡到了另一层状态。而这本诗集读下来很多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来自于那些偶然的灵光,轻飘透明,又不易靠近。 这本书里似乎提到的最多的是生活、扔垃圾和无意义,又或者这真是生活的常态,接受了那些无意义反而能更坦然的的去面对生活,像个安静的观察者,而内心偶尔的喜悦却更想自己保留。 生来的孤独感怎样都没法消灭,从脱离母体后,每个人便都是独立的存在,群居的喜悦是假象,而长久的孤独才是人生常态。就像手术室里侧身独自等待麻药的患者,“在没有眼睛的地方,人的孤独是多么的自然”。 感动于对血亲的想念,那些传递下去的血肉之躯好像时间的车轮,来不及好好认识一番,便一代又一代的推进而去。“我在人生的中途想起我奶奶,也许不同的命运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东西,也许我们,我和奶奶,可以在对自由的理解中相遇”。 小小的一本书里对于“丧”和“热爱”都会有体现,是一本很诚实的书,诚实的面对作者自己,直面自己的每一份感触,分享自己的每一丝波动。书的末尾,后记里,作者说这是35岁到43岁之间的诗,这些诗也是突然间跳跃着出现,被作者抓住而出现在了眼前,又或许正是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时刻波动了那瞬间的心弦。 这本诗集中可以找到很多生活中的影子,好像对着阳光发呆的那个人也是我,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到光的温度,照在眼皮上的色彩似乎都是相通的。 看完这本书,吹着初秋的晚风,耳机里突然传来低苦艾的《红与黑》,似乎和这样一个读完诗的夜晚特别相称。“可现在我只想紧握你的双手,和你的苦难在一起。” “不再有虚度的压力,也就是不再有野心,不再自以为值得精打细算,不再有一个虚拟的目标隔阂,不再有一个世界挡在我和生命之间,挡在我和死亡之间,也许那时候的沉默里才有最勇敢的文学,最浩荡的诗。”
《竟然是真的》读后感(二):唯有明亮与柔软,才能穿过这茫茫人生
诗,现代诗,我一向是畏惧的。毋宁说,对于人的思想之繁复、符号构筑的独异世界,我是畏惧的。那更像是故意横亘在理解之外、经久不衰的漩涡、难题、只关乎自我的语言迷宫,一面展示着神秘,一面引你坠入无解。
刘天昭的诗,是个例外。
不是评论家,不是诗人,对诗歌唯有敬畏、不敢造次,照理没有资格评述,因而权且当做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读者,和书页另一端的那人说说话。
翻开诗集,卷首的《主妇》,是北方才能生出的诗。没有炫技,没有遣词造句的痕迹,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词句,副词也不惹人厌烦。神奇的是,温度、光、影、感受、气息,通通都对了。
从上大学离开家到今天,已十年有余。自那以后,每一次返乡,故乡只有秋冬,没有春夏。以至于快要忘记,北方春日下午那清冷掺杂着暖意的阳光——仿佛是从高远无界的天地间洒下来的,质地像揉碎的一颗颗金子,比黎明和正午都要明亮、清畅。少年的我会踮起脚,打开半米见方的木制气窗,让青草味、泥土香和春风一道注满整个房间。院子里荡起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靠在窗台边的旧床头读几本闲书,想象未来自己会去向更远的远方。
加州的阳光和北方最像,尤其是春秋。金灿灿的,没有攻击力,密度恰好,又不吝惜,晒在身上是暖的,风则是清凉,每个毛孔都舒爽。这十年间,足迹从江浙遍布东南沿海,而今又到华北平原定居下来,没有哪里的阳光比北方春日傍晚降临前的阳光更让我怀念。
离乡后再也没能成功复制的记忆,还有凛冬的清晨。
我经历过很多地点、很多国家的冬。也曾尝试在不同语言的诗句里找寻体感的贴切。譬如德国作家马蒂亚斯·波利蒂基写德国的冬:“屋里如此静谧,如此静谧。窗外一棵树,在雪花飞落中/变得苍白而沉寂——它的耳语热烈无声,在冬日最后的享受后窸窸窣窣/这将要燃尽的火焰……”(《四月,四月!》)德国的冬日大概和英国的冬日一样低沉多变。在曼彻斯特,从教学楼走回宿舍就要经历一场雨雪,有时要靠雨伞才不会浑身淋湿。波利蒂基所写的苍白沉寂、热烈无声、火焰燃尽是独属于欧洲的诗。
“清冷的月亮,高悬在清冷的田野之上!冬原的上空——是何等的寂静!噢,晦暗的月亮,眨着不祥的眼睛……周围是广袤无边的寂静。光秃、干燥、瘦骨伶仃的芦苇/向大地俯首默哀……”(《冬天的夜晚》)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冬更孤绝,生命绝迹,万物俱寂,酝酿自决心杀死一切的极寒之地。
“在淡雪中浮现的/三千大千世界/而在那之中/又有细雪降落”(良宽)日本的雪,好像非要细细淡淡,浩渺中有禅意才好,才值得入诗入画。
在东北,冬日的清晨是深蓝色的,确如天昭所写:“那黑暗非常蓝,可能有点像海”。学生时代,从温暖的被窝里艰难爬起去上学,天将亮未亮,路灯比睡眼朦胧,又像是刺进苍穹的遥远之物,怎么都看不分明。“风又沉又硬”,身躯受着自然力的挤压,而羽绒服是风和雪的缓冲。走路需要技巧,尤其当积雪结了冰,上下坡时需绷紧小腿和脚趾,碎步前进。偶尔也会被刀子般的劲风恐吓,只好背过身站一会儿,等这阵风过去再继续走路。
那时,所有人都用身体的经验谙熟在冬季走路的技巧,只承受寒冷,不多谈论。以为寒冷不过如此,是天经地义的事。直到去南方读大学,十几度的室温,门窗漏风,没有暖气,寒冷入骨,无力驱散,终日怏怏不乐地抱怨,除了瑟缩毫无办法。所以若干年后,在选择定居地时,直接将长江以南刨除在外。而今在北京,冬天的冷是干涩而温吞的,不比钱塘一带阴冷,也不及东北凛冽。只是再回乡,那刺骨的寒意反而是陌生的,无论如何也唤不醒与之对抗的本能。
读到这里我几乎惊叫起来,再没有比这一行诗更符合我童年和少年的心境了!日复一日一个人走进未知的寒冬清晨,抵抗着困顿和寒冷,不断和自己说话、打气。羽绒服底下、蒙上白霜的围巾后面,藏着的滚烫的小小身体,曾天真地渴望过一个不灭的灵魂、一种无限远的将来。
天昭的诗是开阔的,不仅在于她的书写几近完美地传达了某种共同性的经验,敞开时空的维度,把若干个体的生命体验包容进来、连接起来;还在于她尤其擅长跳脱出此时此地的局限,将目光放远,去整体性地感受和永恒相关的事物,譬如时间,譬如美善。
《绿萝》就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读了直叫人想掉眼泪:
有多少个瞬间,人会不自觉地想到老,想到死。那瞬间的降临毫无征兆,也没有预警,也许是在替一盆花浇水,也许只是把坏掉的剩菜倒掉,也许是春天极致灿烂的午后、人声鼎沸的公园,就那么不经意地,想到死。想到肉身泯灭后一切如常,是多么残忍又正常的事。一闪念过后,返回生活,依旧做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不仅不记得曾经的犹疑,连之后重整旗鼓的热切也一并忘却。
而《绿萝》告诉我们要记得,在年岁荒芜时记得,在欲求淡漠时记得,在哀哀戚戚找路问路时记得,记得那份毫无必要的热情。记得代表着了不起的复原力,不是为了延续热情,而是为了浇灭失望。这境界像极了辛波斯卡的那句:“‘我将不会全然地死去’——过早的忧虑。但我是不是全然活着,而且这样够吗?过去不够,现在更是不够……”(《巨大的数目》)
真是奇妙啊,人偏偏会记得某个无足轻重的时刻。天昭的诗就是这些时刻在时间里结成的果。她会记下一只九十年代的发卡,记下那把母亲嫁人时就有的小菜刀,记下父母房间抽屉里的一对按扣,一块香皂,一枚戒指,记下自己悬挂一盆绿萝。她似乎尤其痴迷穿越时间的静物、生活角落里不被人察觉的物件。
物件之上,流淌着时间。人和这些物件一样,均在时间之流中相处。不同人的时间有时刚好重叠,有时碰巧错开,有时交错,略过的部分也许将永远略过,比如看上去有点粗俗的爸爸,实则有过旁人无可想象的人生:
人难道不孤独吗?不理解的,将永无可能理解了。可是人会怀念啊,承担且只承担有限度的怀念。我们不间断地遇见一个个人,不间断地道别,怀抱着还会再见的期待。可分开只是分开。分开的人和你的缘分,仅仅停留在你们分开的那一刻: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恰如临睡前关灯过后的静夜,“翻一个身/像是翻进荒野”(《约会》)。是不是在你我存在的局促时空之外,还静候着另一个时空,像无尽的海,空旷的荒野,自我的反面,未知的,混沌的,召唤着我们潜入,探索。
除了追溯时间的绵延,天昭还贪恋于让时间悬置的游戏。
《多余的镜头》里,韩剧中的爸爸下班回家,家中无人,抬头之前,开口之前,有两秒的寂静,“像是跳针了/像是弄错了/忽然就是真的/忽然就是我对文学的期待——在没有眼睛的地方/人的孤单是多么自然”。《花火》则表达了对时间悬置的渴念,这种渴念即不必迎合,不必屈就,只将身心安置在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不想结识一个陌生人/不想体会他的用心/惊叹他的美好/暂时还不想/暂时我只想待在/好不容易整理好/可以持续一段的/干净房间里”。《10秒》更是将这悬置的游戏进行到顽皮的地步,早餐包用微波炉加热10秒刚好,“这10秒做什么都不够/只够一个清楚的念头”。10秒,那样短暂,又那样确实,够得上一场盛大的自我欢庆,却又如微风拂走灰尘般轻巧。
工作的这些年,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一件容器,不停灌注、不停填满。上下班走在城市的街道,身边的人也是满的,世界是满的,不留任何一点缝隙,透不过一丝风。人们恨不能将自己肢解,三头六臂,所向披靡。生活被忘却了,时间再也不能静止。春日的阳光、凛冬的清晨、少年的心境通通不可企及。
Jim Holland作品
而阅读天昭的这些小诗,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起Jim Holland的画,午后的阳光印在墙角,无人的房间摊开一本未读完的书,光影交错于小镇蜿蜒的小径,平静的海面停泊着桅船。它们会将你吸入时间的流动与静止,让你不自觉地忽略现代诗的技巧,语言的诡辩,难解的词义,干干净净地摘除缠绕在你身上的谜团。此刻,你和写下它们的人一样,安静,幸福,明亮,柔软。
天昭在后记里写:“这些诗太细小、太清楚、太偶然,只是它们跳脱出来的瞬间,是昏昏中的恍然,又像是醒来又像是迷幻,我觉得是宝贵的幸福。”是啊,如果不是这稀缺的安静的幸福,不是这昏昏中的恍然时分,不是这反复睡去又醒来的意志,不是这份明亮和柔软,我们怎么才能赤手空拳、徒步穿行晦涩坚硬的茫茫人生呢?
(原载于《单读》,原标题为“人偏偏会记得某个无足轻重的时刻”)
《竟然是真的》读后感(三):“长久浑浊中,奇迹的一瞬”——关于这本诗集的私人回忆
写完《无中生有》之后,刘天昭开始在豆瓣和微博断断续续贴上一些书评和诗歌,看时便觉得在阅读她的生活。那是一个会跟装修工人吵架、分五次下单买股票的三娜从小说尾声时开始的生活,是在25楼的家中看鸟群飞过黄昏、煮饭、午后随着人群去打疫苗的生活,渐渐能感到,“她很高兴自己在如此具体的境遇中显性,拥有细细一丝但是无比结实的命运”。
书评时断时续,但诗歌却源源不绝,时而也会看到编辑罗丹妮的转发和赞叹,便觉得即将会有一本书出现了。但真把这本142页的小书拿在手上时,却发现它集合的竟是纯然的欢喜,那是一种“不论做什么都能轻而易举(简直像是自欺)地确认”的生活,是“是啊我行走在大地上、观看与表演合而为一、那强烈的坚定感明显不可靠、但是在这一片时光的涟漪中就是真实”,最终,是“意识透彻的那一下非常幸福”。
“竟然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的感叹,那种幸福抛却了“从前挣扎难受的荒废之感”,毕竟那种荒废早已经化为一本80万字的厚书降生于世,同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刘天昭竟然也同时选择了生一个孩子,其实,在《无中生有》的结尾也提到了这件事,但当时似乎还没有确定。
刘天昭像是自出生起就带着一层透明薄膜存活在世间,而这本诗集,则是她发现自己竟然打破了薄膜,“好像刚刚投胎”,又如同“带着复活的喜悦”,重新降生在这个世界,能够亲身接触它,真正生活于其间,她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特别是那些格外有真实感的瞬间,从第一首《主妇》开始就是这样,她望着世界沐浴在金色的永生中,但她并不想进入那金光,而宁可站在人世的宁静里洗碗、烧饭,时不时望一望它就好,“你不能拥有……但是你也不会失去/它永远在那儿/就在窗外”,这是另一首《窗外》,以及“玻璃这边总是/只能,止步于知道/并不能真的进入那感召”(《喜鹊》)。她对生活所有似乎最乏味的瞬间兴致勃勃,像喜欢《金瓶梅》里那些日常,她不想去海滩趴着,看雪,而宁愿到银行和医院、社保所和冲印店办事,去买面包,去踏入最庸常的生活,“要感谢这些给定的东西,坚固的东西,不会在意识的照耀下动摇的东西;要感谢这些让人不自由的东西,让自由变得有意义的东西”。许多首诗,都带着对“活着”本身实体感的验证,也有回忆,回忆也能被刘天昭写成实体,比如一只90年代的发卡,就是一段时代与个人史,因为“我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偶尔触着褪去的旧壳,也仍有过去三娜排山倒海般思辨的来临,有着《寡人》中拔剑四顾的茫然,然而,“怀疑来了,我不怕”,因为她已经“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她不再“在门厅永久地徘徊,空守着舍不得用的人生,自己过期了”,“不再有一个虚拟的目标隔阂,不再有一个世界/挡在我和生命之间,挡在我和死亡之间”。
幸福时刻,为什么要写诗呢?《摇晃》提出:“也可以不写诗,也可以放弃必然性的保障/依然写诗。在狭小的自由的缝隙里”,《终于》回答:“可做可不做的事还是做吧。”《多余的镜头》也给了个说法,就是韩剧里的父亲下班回家时,在玄关台阶上甩掉鞋子,剧情开始之前,爸爸说话之前,有两秒钟的寂静,刘天昭写,“忽然就是我对文学的期待——在没有眼睛的地方 人的孤独是多么自然”,我想把《红星美凯龙的孤独》放在这里,变成一个脚注,“孤独多么好啊/孤独的时候拥有各种各样的孤独”,《从外面回来不想进屋》则是另一则脚注:“又茫然 也就只能看着这茫然 看一会儿。这正是我想要复习的答案。”对写作和语言的反思,时而出现的词语则是含蓄、狡诈、自欺,在《不可能厌倦秋风》中,真实的风吹打破了经验的垃圾、语言的诡计,然而最终捕获这一切的还是语言。在《智慧生物》中,一切颠倒过来:“读书中的世界/给情绪命名/并且信以为真/逻辑如树木/诗歌如飞鸟/而大自然依然在/在人体内/密林深海/照之不透”。回到全书的《竟然是真的》这个题目,有点像马格里特的“这不是一只烟斗”,画上确是一只烟斗。刘天昭则是反过来的,她说这竟然是真的是一只烟斗,画上也是一只烟斗,这“只能是真的,又……不像是真的,仿佛总有更真的”,而且她还问,“现在写诗的这个人又是谁?”
画面是凝固的,但诗歌是流动的,正像现实一样,用诗歌去描写真实,真实似乎在其中平行地发展。“我看见这一切都恰好/对了、但是不停留/坐在黄金的缝隙中/用意志的玻璃,挡住贪婪”,这里的天昭像是拒绝说出“你真美啊”的浮士德。但我不可能比刘天昭聪明,去说出什么她使用的典故,她要的是化繁冗智识为纯真之眼:“但是啊,在生活的现场总有/总应该有,确实会有,一种生动。/一种生动宛如永新的四季之光/独立于平庸的自我创作者”,“真实,越逼真越流动 而想象越逼真越狭窄 在一个针尖上 结束了”,“等真的到来了 还是新的 还是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就是真的”。
这本书不是我买的,而是单读送给我的,仅仅是因为之前写过《无中生有》的书评。我还没有买这本书,恰恰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好阅读它的准备。我能感受到刘天昭的狂喜,她甚至已经说,“人生是多么好啊”,但同样面对生活的细节,我们的位置并不相同,她拥有与之恰当的距离,玻璃、两秒的寂静或者空白,我却深陷其中,并正因此,而感到与她相反的痛苦与烦扰。虽然并不觉得自己准备好,但读完后,我却更深刻地理解了能写出《无中生有》的天昭,理解了她写作的方式,那是极端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境遇,事无不可对人说的袒露,因而一道道堆积如山的思考与意识,是极度的勇气。这勇气富有感染力,我只愿终有一天,也能如此真切面对自己的内心。
最后,其实在打开诗集前,似乎已看到贴出来了,然而还是不敢仔细看,只有在收到书时,才认认真真读了,是在109页,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这首诗有个确凿的题目,叫《母爱》,那一刻像是谜底被揭开,我当时竟浑然不觉。尽管诗的最后几行写得清清楚楚:“我对那个遥远的/更清晰的人/涌起母爱/如大雪”,但我最初读它时,看到的题目叫《冬天》,我并不了解那时的刘天昭竟然是真的竟孕育着一个孩子,更不敢将小说的结尾和她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毕竟,我和她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无中生有》,才成为了一个被给予丰富营养的读者。
那是在2020年的2月,因为疫情,我在沈阳家中过了一个很长的年,长期的滞留里,我擦干净一块早就买来,但一直空白,导致长期积尘的画布,画下了杭州一次大雪时我租的房子楼前的场景。顺着那条道路,两旁长满了高高的鹅掌楸,春天它们会绽开金黄杯状如郁金香的花朵,正好在我的窗前,秋天,它们落下马褂形的黄叶,冬天,成为修长的骨骼。杭州的大雪饱含水汽,在枝干上显得更为蓬松。画到百分之八十时,我把它发在了豆瓣上。
后来,刘天昭看到了这幅未完成的画,问我画完啥样,我豆邮发去,她遂发来这首诗,共有三稿。今日重读,发现纸上落下的精炼诗句,确是在微妙的修改间,才成了最终的模样。
“心思闪光一跃/长久浑浊中/奇迹的一瞬”,在第一稿中,是“猝不及防/心思闪光一跃,几乎/从长久的浑浊中/脱身而出”,在第二稿中,是“猝不及防/心思闪光一跃/在长久的浑浊中/只有一瞬”,最终删去了“猝不及防”,变为“心思闪光一跃/长久浑浊中/奇迹的一瞬”,像是把这个时刻点亮了。
“回到放学路上/无自觉的孤独中/大声成长”在前两稿中,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放学路上的成长”,与下文“泥土中的黑暗/冰雪中的晴朗”,三个同样的句型放在一起,在终稿中则发生了变化,增添了内容,也改换了节奏。“泥土”原作“土壤”,而最末一句,原作“如大雪降临”,现在的改动读起来更有力而美了。
在和刘天昭豆邮往来时,我并不欲多言,只怕打扰了她写诗。
然而,那个隐而未显的时刻竟在此时显明。在无边大雪之下,这首诗中竟蕴含着那样温暖的意念。
谢谢天昭,作为小说家,也作为诗人的给予。
最后,附上这幅画未完成和完成后的样子。第一张拍摄于夜晚,光线偏暖,第二张拍摄于白天,光线偏冷。自觉粗拙,而天昭说她“只是喜欢冬天”。
《楼下的冬》,2020年2月
《竟然是真的》读后感(四):人偏偏会记得某个无足轻重的时刻
刘天昭在后记中写了一句话:“也许有缘的朋友可以感应到那种幸福。”《竟然是真的》出版近一个月以来,单读陆陆续续收到了“有缘的朋友”的反馈,他们通过天昭的诗,重新体会了日常生活中忽然明亮的惊奇瞬间,捡拾起那些被忙碌的工作压抑了的感受。
张畅也是其中之一。在下面这篇评论中,她分享了经天昭“没有遣词造句的痕迹”的诗句唤起的深藏记忆中的感受,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竟被恰到好处地写了出来。天昭的诗不只善于描写共同性的经验,张畅还透过眼前看似普普通通的句子,读到了诗人对与永恒相关事物的洞悉。这本书让她“感应到那种幸福”:“不是这份明亮和柔软,我们怎么才能赤手空拳、徒步穿行晦涩坚硬的茫茫人生呢?”
诗,现代诗,我一向是畏惧的。毋宁说,对于人的思想之繁复、符号构筑的独异世界,我是畏惧的。那更像是故意横亘在理解之外、经久不衰的漩涡、难题、只关乎自我的语言迷宫,一面展示着神秘,一面引你坠入无解。
刘天昭的诗,是个例外。
不是评论家,不是诗人,对诗歌唯有敬畏、不敢造次,照理没有资格评述,因而权且当做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读者,和书页另一端的那人说说话。
“北方才会这样。春天的下午/和傍晚之间/有一会儿工夫/也许有半个钟头/外面会异常明亮/简直比正午还要明亮。空气里有金子/的光,没有芒。光失去速度,可能也就/是这样。”(《主妇》)
翻开诗集,卷首的《主妇》,是北方才能生出的诗。没有炫技,没有遣词造句的痕迹,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词句,副词也不惹人厌烦。神奇的是,温度、光、影、感受、气息,通通都对了。
从上大学离开家到今天,已十年有余。自那以后,每一次返乡,故乡只有秋冬,没有春夏。以至于快要忘记,北方春日下午那清冷掺杂着暖意的阳光——仿佛是从高远无界的天地间洒下来的,质地像揉碎的一颗颗金子,比黎明和正午都要明亮、清畅。少年的我会踮起脚,打开半米见方的木制气窗,让青草味、泥土香和春风一道注满整个房间。院子里荡起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靠在窗台边的旧床头读几本闲书,想象未来自己会去向更远的远方。
加州的阳光和北方最像,尤其是春秋。金灿灿的,没有攻击力,密度恰好,又不吝惜,晒在身上是暖的,风则是清凉,每个毛孔都舒爽。这十年间,足迹从江浙遍布东南沿海,而今又到华北平原定居下来,没有哪里的阳光比北方春日傍晚降临前的阳光更让我怀念。
离乡后再也没能成功复制的记忆,还有凛冬的清晨。
《逃走的女人》剧照
“……天还没有亮,当然/在操场中间路灯都非常遥远/那黑暗非常蓝,可能有点像海/空气冷厉,风又硬又沉/有时候要转过身来等一会儿/双肩书包贴到背上变轻了/好的时候也要缩着脖子/让围巾挡住更多的脸/围巾上都是霜……”(《操场上》)
我经历过很多地点、很多国家的冬。也曾尝试在不同语言的诗句里找寻体感的贴切。譬如德国作家马蒂亚斯·波利蒂基写德国的冬:“屋里如此静谧,如此静谧。窗外一棵树,在雪花飞落中/变得苍白而沉寂——它的耳语热烈无声,在冬日最后的享受后窸窸窣窣/这将要燃尽的火焰……”(《四月,四月!》)德国的冬日大概和英国的冬日一样低沉多变。在曼彻斯特,从教学楼走回宿舍就要经历一场雨雪,有时要靠雨伞才不会浑身淋湿。波利蒂基所写的苍白沉寂、热烈无声、火焰燃尽是独属于欧洲的诗。
“清冷的月亮,高悬在清冷的田野之上!冬原的上空——是何等的寂静!噢,晦暗的月亮,眨着不祥的眼睛……周围是广袤无边的寂静。光秃、干燥、瘦骨伶仃的芦苇/向大地俯首默哀……”(《冬天的夜晚》)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冬更孤绝,生命绝迹,万物俱寂,酝酿自决心杀死一切的极寒之地。
“在淡雪中浮现的/三千大千世界/而在那之中/又有细雪降落”(良宽)日本的雪,好像非要细细淡淡,浩渺中有禅意才好,才值得入诗入画。
电影《白日焰火》中的东北
在东北,冬日的清晨是深蓝色的,确如天昭所写:“那黑暗非常蓝,可能有点像海”。学生时代,从温暖的被窝里艰难爬起去上学,天将亮未亮,路灯比睡眼朦胧,又像是刺进苍穹的遥远之物,怎么都看不分明。“风又沉又硬”,身躯受着自然力的挤压,而羽绒服是风和雪的缓冲。走路需要技巧,尤其当积雪结了冰,上下坡时需绷紧小腿和脚趾,碎步前进。偶尔也会被刀子般的劲风恐吓,只好背过身站一会儿,等这阵风过去再继续走路。
那时,所有人都用身体的经验谙熟在冬季走路的技巧,只承受寒冷,不多谈论。以为寒冷不过如此,是天经地义的事。直到去南方读大学,十几度的室温,门窗漏风,没有暖气,寒冷入骨,无力驱散,终日怏怏不乐地抱怨,除了瑟缩毫无办法。所以若干年后,在选择定居地时,直接将长江以南刨除在外。而今在北京,冬天的冷是干涩而温吞的,不比钱塘一带阴冷,也不及东北凛冽。只是再回乡,那刺骨的寒意反而是陌生的,无论如何也唤不醒与之对抗的本能。
“这几天北京寒冷,说起来那时候/真好啊,独自赶路的小孩/是完整的一个意志/又完全融于大地”。(《操场上》)读到这里我几乎惊叫起来,再没有比这一行诗更符合我童年和少年的心境了!日复一日一个人走进未知的寒冬清晨,抵抗着困顿和寒冷,不断和自己说话、打气。羽绒服底下、蒙上白霜的围巾后面,藏着的滚烫的小小身体,曾天真地渴望过一个不灭的灵魂、一种无限远的将来。
《逃走的女人》剧照
天昭的诗是开阔的,不仅在于她的书写几近完美地传达了某种共同性的经验,敞开时空的维度,把若干个体的生命体验包容进来、连接起来;还在于她尤其擅长跳脱出此时此地的局限,将目光放远,去整体性地感受和永恒相关的事物,譬如时间,譬如美善。
《绿萝》就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读了直叫人想掉眼泪:“等妈妈老了/更像个老人/我也老了/微波炉坏了都不修/也不扔掉/到处堆叠着无用的旧物/碰一碰就要起灰/碰一碰就要碎掉/等这屋子住老了/等生活老了/我要记得此刻/念念挂一盆绿萝的心情/毫无必要的热情/生活过”。
有多少个瞬间,人会不自觉地想到老,想到死。那瞬间的降临毫无征兆,也没有预警,也许是在替一盆花浇水,也许只是把坏掉的剩菜倒掉,也许是春天极致灿烂的午后、人声鼎沸的公园,就那么不经意地,想到死。想到肉身泯灭后一切如常,是多么残忍又正常的事。一闪念过后,返回生活,依旧做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不仅不记得曾经的犹疑,连之后重整旗鼓的热切也一并忘却。
而《绿萝》告诉我们要记得,在年岁荒芜时记得,在欲求淡漠时记得,在哀哀戚戚找路问路时记得,记得那份毫无必要的热情。记得代表着了不起的复原力,不是为了延续热情,而是为了浇灭失望。这境界像极了辛波斯卡的那句:“‘我将不会全然地死去’——过早的忧虑。但我是不是全然活着,而且这样够吗?过去不够,现在更是不够……”(《巨大的数目》)
《海街日记》剧照
真是奇妙啊,人偏偏会记得某个无足轻重的时刻。天昭的诗就是这些时刻在时间里结成的果。她会记下一只九十年代的发卡,记下那把母亲嫁人时就有的小菜刀,记下父母房间抽屉里的一对按扣,一块香皂,一枚戒指,记下自己悬挂一盆绿萝。她似乎尤其痴迷穿越时间的静物、生活角落里不被人察觉的物件。
物件之上,流淌着时间。人和这些物件一样,均在时间之流中相处。不同人的时间有时刚好重叠,有时碰巧错开,有时交错,略过的部分也许将永远略过,比如看上去有点粗俗的爸爸,实则有过旁人无可想象的人生:“但是他的胖儿子以后长大了/可能以为他始终就是这样/他们也不可能跟他讲/根本也讲不清楚/讲清楚了也不可能听明白/能听明白就更不应该去讲/那是人生最隐秘的剧情/是人生本身,属于他自己”(《老头子》)。
人难道不孤独吗?不理解的,将永无可能理解了。可是人会怀念啊,承担且只承担有限度的怀念。我们不间断地遇见一个个人,不间断地道别,怀抱着还会再见的期待。可分开只是分开。分开的人和你的缘分,仅仅停留在你们分开的那一刻:“我差不多是真的有点伤心了/可能很久都不会再来/好像也不会为了这个特意来/好像真的去告别就像是假的/啊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酒店两则》)。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恰如临睡前关灯过后的静夜,“翻一个身/像是翻进荒野”(《约会》)。是不是在你我存在的局促时空之外,还静候着另一个时空,像无尽的海,空旷的荒野,自我的反面,未知的,混沌的,召唤着我们潜入,探索。
《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剧照
除了追溯时间的绵延,天昭还贪恋于让时间悬置的游戏。
《多余的镜头》里,韩剧中的爸爸下班回家,家中无人,抬头之前,开口之前,有两秒的寂静,“像是跳针了/像是弄错了/忽然就是真的/忽然就是我对文学的期待——在没有眼睛的地方/人的孤单是多么自然”。《花火》则表达了对时间悬置的渴念,这种渴念即不必迎合,不必屈就,只将身心安置在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不想结识一个陌生人/不想体会他的用心/惊叹他的美好/暂时还不想/暂时我只想待在/好不容易整理好/可以持续一段的/干净房间里”。《10 秒》更是将这悬置的游戏进行到顽皮的地步,早餐包用微波炉加热 10 秒刚好,“这 10 秒做什么都不够/只够一个清楚的念头”。10 秒,那样短暂,又那样确实,够得上一场盛大的自我欢庆,却又如微风拂走灰尘般轻巧。
工作的这些年,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一件容器,不停灌注、不停填满。上下班走在城市的街道,身边的人也是满的,世界是满的,不留任何一点缝隙,透不过一丝风。人们恨不能将自己肢解,三头六臂,所向披靡。生活被忘却了,时间再也不能静止。春日的阳光、凛冬的清晨、少年的心境通通不可企及。
而阅读天昭的这些小诗,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起 Jim Holland 的画,午后的阳光印在墙角,无人的房间摊开一本未读完的书,光影交错于小镇蜿蜒的小径,平静的海面停泊着桅船。它们会将你吸入时间的流动与静止,让你不自觉地忽略现代诗的技巧,语言的诡辩,难解的词义,干干净净地摘除缠绕在你身上的谜团。此刻,你和写下它们的人一样,安静,幸福,明亮,柔软。
Jim Holland 画作
天昭在后记里写:“这些诗太细小、太清楚、太偶然,只是它们跳脱出来的瞬间,是昏昏中的恍然,又像是醒来又像是迷幻,我觉得是宝贵的幸福。”是啊,如果不是这稀缺的安静的幸福,不是这昏昏中的恍然时分,不是这反复睡去又醒来的意志,不是这份明亮和柔软,我们怎么才能赤手空拳、徒步穿行晦涩坚硬的茫茫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