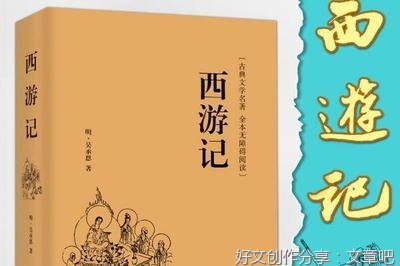论生命之短暂读后感摘抄
《论生命之短暂》是一本由[古罗马]塞涅卡著作,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19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生命之短暂》读后感(一):读后笔记
非常喜欢这本书中那篇《论心灵之安宁》,虽然一下想不起来那里到底让我学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当时读这一篇时,心灵仿佛在炙热的荒漠中忽然被山顶的清泉淌过 在面对挫折与苦难,塞涅卡的态度和我了解的尼采很相似——他认为正是挫折与苦难证明了伟人之所以伟大。是的,一帆风顺的人生并不会造就多传奇的人物,只有在风浪颠簸过的船长和水手,才能称得上勇敢、经验丰富。在我今后的日常生活、学习、事业上,必然会遇到很多坎坷、挫折,那时我应该庆幸,因为这些坎坷挫折,终将亲手引我通向离梦想、离伟大更接近的地方塞涅卡在面对他人指责自己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他自己的生活有时与他所传述的信念不统一时,塞涅卡大方的承认——:我又不是智者,我能比那些坏人好一点就足够了。我能做的就是吾日三省吾身,每天改变自己的一些恶习,我就很满足了
《论生命之短暂》读后感(二):《论生命之短暂》导读
在苏格拉底逝世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西提乌姆的芝诺(Zeno of Citium)在雅典城邦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最初,他的追随者们被称为“芝诺学派”(Zenonians),但由于芝诺经常在雅典公民广场西北角的“画廊”(Stoa Poikile)散步、讲学,他们后来就被称为“画廊处的人”(men from Stoa),学派也因此被称作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斯多亚派”或“廊下派”(Stoics)。
该学派历史悠久,至少长达三个世纪。通常认为,该学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早期,主要指学派创立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代表人物有芝诺、克莱安塞斯(Cleanthes)与克吕西波(Chrysippus);(2)中期,主要指希腊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内修斯(Panaetius)与他的学生波西多纽斯(Posidonius)。在这段时期,学派的研究中心逐渐从雅典转移到其他城市,如罗马;(3)晚期,主要指罗马帝国时期,代表人物有元老院议员塞涅卡、奴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与皇帝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但实际上,斯多亚派的理论影响要更加久远,我们在中世纪经院哲学、苏格兰情感主义、斯宾诺莎、蒙田、帕斯卡尔、康德等人的理论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斯多亚思想的遗产。时至今日,在美国著名古典学家、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等人那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斯多亚派宝贵的思想财富。
就这三个阶段而言,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们之间的融贯性与相似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鲜明的。早期斯多亚主义者依然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很深,尤其受到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犬儒主义影响很深,他们的主要论敌是伊壁鸠鲁主义。因而,他们讨论问题的概念、方式与关切点依然与整个古希腊哲学十分密切。而中期的斯多亚主义则体现出了一种折中主义,他们主要通过吸纳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学派的哲学内容,以应对怀疑论的威胁。最后,晚期斯多亚主义的最大特色则是他们逐渐抛弃了希腊哲学式的研究方式,而是倾向于直接利用早期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术语进行道德劝诫。换言之,按照今天的视角来看,他们更像是劝人向善的道德家,而非从事理论研究的哲学家。
正是由于晚期斯多亚派的这个特点,他们的作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几乎所有人,在不需要任何哲学背景的前提下,都能从他们的作品那里体味什么是人生,以及我们该如何生活。此外,晚期斯多亚主义相对更加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文献问题。由于早期斯多亚学派的原著留存下来的很少,而且大多是一些残篇。我们便只能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西塞罗等人的转引或论述去了解他们,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难与不确定性。相较而言,晚期斯多亚主义者的著作则相对完整的保存下来。
其中,本书的作者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前1年—公元65年)就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是斯多亚学派中最多产的一位。他留下了许多作品,尤为著名的便是他的《道德书简》(Epistles),也就是本书的母体。他本人曾被称为小塞涅卡,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享有很高的声誉。小塞涅卡是尼禄年轻时候的导师与顾问,但他却没有得到尼禄的青睐。最终,他为了逃避尼禄的愤怒而选择了自杀。显然,这种失败的辅佐经历却并不影响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之一。
本书则选择了塞涅卡在今天依然非常流行的五篇信笺或文章,分别是:《论生命之短暂》《论心灵之安宁》《论天意》《论闲暇》和《论幸福生活》。她们经常出现在各种摘编本里,并且每篇都有多个译本。
《论生命之短暂》(De Brevitate Vitae)想要告诉我们,与其抱怨生命太短,不如学会珍惜时间。因为只有庸人们才会放纵欲望,才会为了财富、权力等外在善一生处心竭虑。他们浪费时间且不自知,到头来却还要抱怨时间不够。相反,只有热爱智慧的人,“只有潜心钻研哲学的人,才是真正悠闲自在、真正活过的人”。
有学者认为,《论心灵之安宁》(De Tranquilitate Animi)在塞涅卡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只有它真实地体现了塞涅卡与塞雷努斯两人之间的交流。这篇文章同样说明了心灵之困扰主要源于我们对外在事物的执着。于是,他建议我们要实现静心,要在履行自己政治义务的同时,热衷于智慧与沉思。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心灵之安宁”或“静心”其实是古希腊伦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εὐθυμία/euthumia。该术语最早得到了德谟克利特的重视,主要指灵魂处于好的状态之中,或各部分达到了均衡,没有斗争与纷扰。因而,euthumia便是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一个善/好,或一个目的。普鲁塔克亦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这个概念。
《论天意》(De Providentia)在早期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叫《为何有些不幸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尽管天意存在》,也就是该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塞涅卡表达了斯多亚派常见的一个伦理观点,即:那些看似不幸的事情,其实对我们而言都是有益的。或者说,现实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通过智慧,我们都能从中获益。直到今天,我们对这种想法似乎也不陌生。但我们朴素的想法,其实和斯多亚派的观点还是有些背景性与框架性的差异。我也曾撰文区分过斯多亚派的观点与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等类似现象有何不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另外,这个问题还与斯多亚学派的自然观或宇宙观有关。简言之,他们认为自然或宇宙体现了一种完美的理性与智慧(这种观点的继承者则是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等),并且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必然性(这与他们的论敌——强调偶然性的伊壁鸠鲁学派针锋相对),因而“以恶报善”似乎违背了这种宇宙观。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是要安慰那些遭遇厄运的人,而且还有助于他们维系其自然学理论的正确性。
《论闲暇》(De Otio)是古希腊常见的一个话题,它涉及到古希腊哲人长久以来所争论的“政治/实践生活”与“哲学/理论生活”之间的张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明确区分了闲暇(σχολη/scholē)与消遣、放松、娱乐等之间的不同。简言之,闲暇不以快乐为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必需,而是为了高尚和自由,它是因其自身故的。于是,只有智慧之人,才能真正享有闲暇。而在该文中,塞涅卡则通过讨论闲暇,再次回应了人们在一生中应该如何应对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投入到公民生活之中与享受闲暇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
最后,《论幸福生活》(De Vita Beata)则讨论了古希腊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幸福(εὐδαιμονία/eudaimonia)。除了昔勒尼派(Cyrenaics)之外,几乎所有的古希腊伦理学派都把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或最高目的,只是他们对“幸福”的解释不尽相同。就此而言,包括塞涅卡在内的斯多亚派则认为,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理性或美德。换言之,只要我们拥有了理性或美德,我们就获取了幸福。同时,也只有理性或美德是获取幸福的手段,而所有的财富、权力等外在善都无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的。
囿于篇幅所限,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由衷地希望每一个读者,无论是否赞同,都能从阅读塞涅卡这里找到智慧、幸福与静心。
陶 涛
南京·关岳斋
2021.08.28
陶涛,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论生命之短暂》读后感(三):《论生命之短暂》导读:与其抱怨生命太短,不如学会珍惜时间
在苏格拉底逝世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西提乌姆的芝诺(Zeno of Citium)在雅典城邦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最初,他的追随者们被称为“芝诺学派”(Zenonians),但由于芝诺经常在雅典公民广场西北角的“画廊”(Stoa Poikile)散步、讲学,他们后来就被称为“画廊处的人”(men from Stoa),学派也因此被称作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斯多亚派”或“廊下派”(Stoics)。
芝诺悖论
该学派历史悠久,至少长达三个世纪。通常认为,该学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早期,主要指学派创立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代表人物有芝诺、克莱安塞斯(Cleanthes)与克吕西波(Chrysippus);
(2)中期,主要指希腊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内修斯(Panaetius)与他的学生波西多纽斯(Posidonius)。在这段时期,学派的研究中心逐渐从雅典转移到其他城市,如罗马;
(3)晚期,主要指罗马帝国时期,代表人物有元老院议员塞涅卡、奴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与皇帝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但实际上,斯多亚派的理论影响要更加久远,我们在中世纪经院哲学、苏格兰情感主义、斯宾诺莎、蒙田、帕斯卡尔、康德等人的理论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斯多亚思想的遗产。时至今日,在美国著名古典学家、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等人那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斯多亚派宝贵的思想财富。
马克·奥勒留与斯多亚派
就这三个阶段而言,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们之间的融贯性与相似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鲜明的。早期斯多亚主义者依然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很深,尤其受到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犬儒主义影响很深,他们的主要论敌是伊壁鸠鲁主义。因而,他们讨论问题的概念、方式与关切点依然与整个古希腊哲学十分密切。而中期的斯多亚主义则体现出了一种折中主义,他们主要通过吸纳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学派的哲学内容,以应对怀疑论的威胁。最后,晚期斯多亚主义的最大特色则是他们逐渐抛弃了希腊哲学式的研究方式,而是倾向于直接利用早期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术语进行道德劝诫。换言之,按照今天的视角来看,他们更像是劝人向善的道德家,而非从事理论研究的哲学家。
正是由于晚期斯多亚派的这个特点,他们的作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几乎所有人,在不需要任何哲学背景的前提下,都能从他们的作品那里体味什么是人生,以及我们该如何生活。此外,晚期斯多亚主义相对更加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文献问题。由于早期斯多亚学派的原著留存下来的很少,而且大多是一些残篇。我们便只能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西塞罗等人的转引或论述去了解他们,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难与不确定性。相较而言,晚期斯多亚主义者的著作则相对完整的保存下来。
其中,本书的作者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前1年—公元65年)就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是斯多亚学派中最多产的一位。他留下了许多作品,尤为著名的便是他的《道德书简》(Epistles),也就是本书的母体。他本人曾被称为小塞涅卡,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享有很高的声誉。小塞涅卡是尼禄年轻时候的导师与顾问,但他却没有得到尼禄的青睐。最终,他为了逃避尼禄的愤怒而选择了自杀。显然,这种失败的辅佐经历却并不影响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之一。
塞涅卡在科尔多瓦的雕像
本书则选择了塞涅卡在今天依然非常流行的五篇信笺或文章,分别是:《论生命之短暂》《论心灵之安宁》《论天意》《论闲暇》和《论幸福生活》。她们经常出现在各种摘编本里,并且每篇都有多个译本。
《论生命之短暂》(De Brevitate Vitae)想要告诉我们,与其抱怨生命太短,不如学会珍惜时间。因为只有庸人们才会放纵欲望,才会为了财富、权力等外在善一生处心竭虑。他们浪费时间且不自知,到头来却还要抱怨时间不够。相反,只有热爱智慧的人,“只有潜心钻研哲学的人,才是真正悠闲自在、真正活过的人”。
有学者认为,《论心灵之安宁》(De Tranquilitate Animi)在塞涅卡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只有它真实地体现了塞涅卡与塞雷努斯两人之间的交流。这篇文章同样说明了心灵之困扰主要源于我们对外在事物的执着。于是,他建议我们要实现静心,要在履行自己政治义务的同时,热衷于智慧与沉思。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心灵之安宁”或“静心”其实是古希腊伦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εὐθυμία/euthumia。该术语最早得到了德谟克利特的重视,主要指灵魂处于好的状态之中,或各部分达到了均衡,没有斗争与纷扰。因而,euthumia便是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一个善/好,或一个目的。普鲁塔克亦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这个概念。
《论天意》(De Providentia)在早期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叫《为何有些不幸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尽管天意存在》,也就是该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塞涅卡表达了斯多亚派常见的一个伦理观点,即:那些看似不幸的事情,其实对我们而言都是有益的。或者说,现实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通过智慧,我们都能从中获益。直到今天,我们对这种想法似乎也不陌生。但我们朴素的想法,其实和斯多亚派的观点还是有些背景性与框架性的差异。我也曾撰文区分过斯多亚派的观点与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等类似现象有何不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另外,这个问题还与斯多亚学派的自然观或宇宙观有关。简言之,他们认为自然或宇宙体现了一种完美的理性与智慧(这种观点的继承者则是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等),并且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必然性(这与他们的论敌——强调偶然性的伊壁鸠鲁学派针锋相对),因而“以恶报善”似乎违背了这种宇宙观。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是要安慰那些遭遇厄运的人,而且还有助于他们维系其自然学理论的正确性。
《论闲暇》(De Otio)是古希腊常见的一个话题,它涉及到古希腊哲人长久以来所争论的“政治/实践生活”与“哲学/理论生活”之间的张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明确区分了闲暇(σχολη/scholē)与消遣、放松、娱乐等之间的不同。简言之,闲暇不以快乐为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必需,而是为了高尚和自由,它是因其自身故的。于是,只有智慧之人,才能真正享有闲暇。而在该文中,塞涅卡则通过讨论闲暇,再次回应了人们在一生中应该如何应对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投入到公民生活之中与享受闲暇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
最后,《论幸福生活》(De Vita Beata)则讨论了古希腊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幸福(εὐδαιμονία/eudaimonia)。除了昔勒尼派(Cyrenaics)之外,几乎所有的古希腊伦理学派都把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或最高目的,只是他们对“幸福”的解释不尽相同。就此而言,包括塞涅卡在内的斯多亚派则认为,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理性或美德。换言之,只要我们拥有了理性或美德,我们就获取了幸福。同时,也只有理性或美德是获取幸福的手段,而所有的财富、权力等外在善都无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的。
囿于篇幅所限,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由衷地希望每一个读者,无论是否赞同,都能从阅读塞涅卡这里找到智慧、幸福与静心。
陶 涛
南京·关岳斋
2021.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