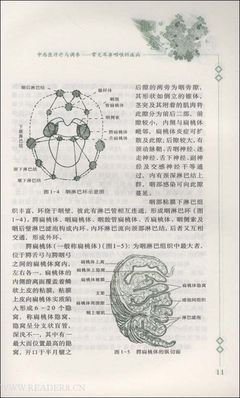《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读后感精选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是一本由皮国立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医应对西医的细菌学(传染病学)的历程是中学碰撞西学的一个缩影,这一案例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作者通过详实的资料、客观的论述、理性的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中国医者、患者观念的曲折转变,政府与社会态度的起伏更易。值得借鉴学习的研究范本。
●在书展做志愿者时偶遇,就翻了起来,说是中西医博弈,但主要是以现代医学中传染病——传统中医对应的温病这一块切入,不客气的说,失之细碎,几无全貌,不过这似乎也是很多专门史写作的特点……不过在启发下给大象写了篇文,后来赠给故人,也不枉在书展上的相遇。
●前面读起来尚可,后来感觉内容越来越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的电子书的原因。算是接触过现代中医理论的学生,依然对这些东西保持一种怀疑,更多的感觉是中医的现代化停滞了,仍然在那西学东渐的矛盾中。个人理解。
●中医用了西医的病名,器具,却仍旧埋头故纸堆中寻找治病救人的法子。几千年来,一代代医家,从未超越老祖宗。
●余云岫该是爱中医爱得深沉,以至粉转黑。不过他说的有趣:文化低的信鬼神,有文化的就只顾辩义理了。这话嘲得很,几乎能解释中国迄今所有所谓知识分子为啥只能嘴炮却不能打。就中医,我的理解,温病和伤寒派天天斗法,争论孰是孰非,治病实践却抱古守残,和西医实践出真知,怎么打?本书作者选取几个断面来诉说中西医博弈(中医输了)倒也有趣,但是没解决一个问题:虽然中医不乏看世界的人,为何依然没有现代化?作者只说恐怕有社会文化问题,大抵如是。
●“重层医史”结合内外史的尝试、对近代史史料的把握以及对史学和治史本身的思考都非常值得借鉴,诚如作者所说,“中医史可以给读者带来很多新的思考”,仅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与“公共”就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了。
●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地黑(现代化之前形成的落后的)中医理论,与西医的博弈也像是近代中国与所有现代科技文明拉锯的缩影,仿佛先秦军队问美国大兵:你为啥不会使秦弩啊?
●收获很多新知识,由历史来看面对西方科学冲击时的中医困境和努力。温寒之争,中医内部的难于统一,面对西医冲击时的寻古解释,个人式卫生,中西汇通之可能。有些论述过于重复
●看不懂看不懂。各行如隔山。看了前三分之一。在细菌病毒没有被发现以前,中西医对个人的治疗还不相上下,甚至还能展开对话。可是,分界发生在细菌病毒被发现以后。现代医学不再只重视个体治疗,而把很多经历花在流行病的预防和处理上,所面对的对象变成了群体。中医还在讲因人分症之类的。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读后感(一):重层医疗史的一次尝试
绪论中,作者皮国立交待了什么是重层医疗史:融合专业医学和社会生活两个维度的历史书写,也叫内史和外史的融合。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样的初衷是好的,但最后呈现出来的样貌却不好看。为何?一方面,书中大量对中医术语的援引非内行看不懂,书中间杂的对当时社会风俗、制度的描写又零零散散,细碎的跳来跳去,让读者不能一次看过瘾。
本书主要以传染病为载体探讨了中医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转变。转变即意味着传统认识的抵抗,也意味着新名词的加入。为此,就有了中医古籍的再正典化,意为对经典古籍重新解读,以便适应新形势。打个比方,要创作中医的白话文让今日有西学背景的学生看懂古文。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线,即伤寒派和温病派的争论。这当然不是民国才有的事情,从明末温病学派的发轫此类争论就开始了,只是到了民国,在细菌论的传入后尤盛。尽管定义五花八门,但温病的重点一直是热病,又尤重“湿温”,可以说是由急性传染病在伤寒辩证无用后的发展,药性偏凉而非温,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之所以争论,又是因为其易学易用,宗旨是用药轻灵,所以很多人学会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被很多伤寒大家诟病,非学派之罪也。
总的说来,尽管字句严谨,小标题清晰,但全书的结构零零散散,有时候偏向毫无意义的考证,不时说些有的没有,趣味就冲淡了好些。两条线夹杂起来,引用甚多,但是夹杂的中医术语让门外人望而生畏,只以为是玄学集解,实在可惜。但是里面间杂有不少民国的名人轶事,其对中医态度鲜明,如有真人立在眼前,当作消遣看倒也不错。对中医学子来说又是一部大家学术脉络指引,对中西医论争可以一窥。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读后感(二):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与名 — 从民国医学史看中西医之短长
近期的COVID-19对于国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医的兴衰有哪些深远的推动,相信历史会给出它的答案。
但是,这一切不妨碍可以借助100多年前的民国医学史,来聊聊中西医之短长。
首先,先来看治疗。从清末鼠疫,到民初世纪大流感,到10余年前之非典,直至今岁之新冠,无人可以否定中医治疗之优势。当细菌之抗药性越来越甚,当病毒之变异性越来越快,中医之优势则越来越大。《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之作中的方剂,仍有深入研究之必要,无它,黄师曰:西医治人之病,中医治病之人也。人体之变异,远远落后于细菌与病毒之变异速度,而细菌与病毒作用于人体之反应,与两千年前,并无大的变化。
但是,中医在“正名”当面,确实受到了现代医学很大的冲击。阴虚、湿温等描述,相对肺结核、肠伤寒等病名,确实有点含混不清,如果再遇上不同的医生,病名就更混乱了。本体研究的不同,现代医学的宣传,造就了与民国现代医学刚刚进入中国时完全不同的情况,现代中医,不了解点现代医学的病名,检查报告,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窃以为,借助病程发展的了解,尊重检查报告,借助检查报告,正可以凸现中医的优势。在免疫系统与病毒性疾病,如过敏性紫癜和肝炎等的治疗上,中医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断根,不仅仅是临床症状的消失,更是检查指标的正常。
而中医的优势,更加凸现在预后的调理上,这也是治疗非常重要的一环。以最近的新冠为例,连续核酸检验阴性就好了?舌苔厚腻吗?舌下仍红吗?脉象平和吗?怎么处理“食复”与“劳复”?翻看民国医史,你可能会明白的更多。
凡事一分为二,中医相比较现代医学最大的劣势,是没有系统的防疫与卫生。翻看所谓的预防方,绝大部分仍是治疗方。而所谓的“芳香逐秽”,更多的也是在治疗上的作用,不可过分强调在预防上的应用。看看当初中国是如何消灭血吸虫病的,我这代人从小吃的“糖丸”,以及这次中国的“封城与口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还是非常清楚的。
不妄自菲薄,宜乘胜追击,这是我对于放下中医的态度。
另,本书内容繁杂,不推荐非专业人士阅读。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读后感(三):写了不少中医缺点
古文太难,民国挺中医章太炎,恽铁樵说,中医自己99%不看《黄帝内经》。《伤寒论》看的人也少,明清两代温病学兴盛,一般也就看些清代人写的医书,还说很多老中医看了一辈子,对五脏四时什么都说不清。
后来在西医非常强烈压力下,再从源头经典找回自信,也就是书里写的”再正典化“,不过也是力推实用的《伤寒论》而不是挺玄乎的《内经》,ps:当时日本皇汉医学也只尊《伤寒论》。
--------------------------------------------
当时西医没有抗生素,对细菌感染病也没啥特别好方法,也就对白喉少数几个有特效。中医对外感热病相当自信,双方临床治愈率其实都不算高,也没拉开,加上传染性,我估计是民国第一死亡率高的病。
------------------------------------
中西医对病的命名权很重要,代表对病原判断及时性和准确性,代表根据谁分类就和谁的体系思路来,另外一系统只能翻译对应。基本后来新发现都是细菌名命名病名。
-------------------
西医细菌学进入后,中医基本分了3种。
1.否认,用显微镜能看到细菌,否认不了,只能否认细菌会招致生病,不过太牵强,当时会被人抨击没有科学常识。
2.认为细菌就是气化而生,中药一样是杀菌,日本皇汉医学就这么认为,不过细菌太多,难以和中医理念一一对应,而且当时中医买不起显微镜,没有实验室,都是二手知识,这套融合起来困难。
3.说中西医两套系统,西医体系杀菌,中医体系气化,用增强人体自身正气,驱除邪气,属于两套系统。
----------------------------------
中医对防疫经验缺失,只有治疫,防疫没有专著,对隔离,灭鼠,灭菌消毒,烧尸,都没有概念,当然和中国传统政府不管防疫,都是本地乡绅出面自我救助有关。当晚清政府想管这事时候,能提出方案也就是西医,在1910鼠疫,西医防疫胜利后,中医受到质疑,后来民国几次大疫情中医都没有起到作用,结果导致1929年废医案。
----------------------------------
都说中医不科学,中医都说自己是哲(xuan)学,其实中医里派别内斗也是一样。科学之争么,大家拿证据,只要一方证据够硬,另外外一方基本也认,书里民国伤寒派和温病派从头斗到尾,有种文无第一感觉,各说各理,各说各的个案,谁也不考虑怎么拿出过硬证据。当然也和中医基本都是临床,没有专职搞研究的有关。
---------------------------------
十人十方是有,不过没有现在网上说的十人十方都能看好这么理想,伤寒派温病派两派内部还互相说对方害了病人,书里没有明确说十人十方,但是有写民国生病治疗周期要拖很久,要换好几个医生,所以十人十方可能意思你要看十个医生吃十副药才有效。
-------------------------------
另外,中医护理学也没有,一般都是靠家人照顾。
--------------------------------------------
最后书也没有写,到时别人的序言写了,民国晚年40年代末,青霉素开始民用后,细菌传染这块,开始全年领先中医,中医现在基本也退出外感热病。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读后感(四):范瑞:中医抗菌史的启示
无论2003年的“非典”还是现下的“新冠”, 当西医对新型传染病束手无策时,人们自然会想到从中医中寻求另一种对抗病菌的方法。与此同时,围绕中医防疫是正道抑或伪科学的争论也会甚嚣尘上,以致有人戏称,如果要让一个微信群起内讧,最好的话题就是中医防疫。到底该如何认识中医防疫,皮国立教授《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一书提供了几个有价值的思考方向。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被认为是细菌学的年代。细菌学的问世给人类带来了对抗传染病的前所未有的希望,西医在世界范围内的正统地位随之确立,相反,中医则被定位为“不懂细菌学”,被排斥在卫生体制之外。对细菌学的信仰导致以往的研究几乎是将中医“不懂细菌学”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判定,而未加以必要的反思。该书从多个层面呈现出近代中医抗菌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指出与细菌学的对话是中医发展至今的精髓所在。
中医史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立足于中医自身的“内史”研究,研究者往往是中医从业者;一是立足于中医所处社会的“外史”研究,研究者往往是历史学者。作者主张打通二者之间的界限。一方面,与一般的“内史”研究不同,作者并未将中医看作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是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之。他指出,不断阅读、诠释经典是中医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表面会固化思维,但实际却是动态的,即对经典的再诠释会随着所处时代及相应问题与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近代中医在对经典的阅读、诠释中会不自觉地与细菌学对话,从而形成抗菌的知识与方法。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外史”研究不同,作者认为中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内在知识体系上,或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变是以传统中医为基础与根据的。中医两大传统流派“伤寒论”与“温病学说”在发轫之初均针对“外感热病”,即广义的传染病。这一传统如果缺失,那么抗菌的知识与方法就不会形成。
从该书的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关于近代中医发展史的认识夸大了中西医之间基于科学与否的对立或存在“中西医冲突”的刻板印象。西医传入中国之初,中西医之间颇能交汇、融合。尽管细菌学的权威建立后,中西医呈论争之势,但论争的形式更多仍体现中西医之间的交融,而非对立。一般上认为,中医的核心理论——“气论”与细菌学是相悖的。然而,近代中医在坚持“气论”的同时并不排斥细菌学,而是强调“菌在气中”,简单讲,即细菌、病毒无法脱离空气、季节、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而单独导致疾病发生,从而促成中医气论与西医细菌学之间的汇通。
作为与现代西医同台竞技过的传统医学,中医为反思科技“进步”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这一点在该书的论述中有充分体现。近代中医对细菌学的质疑主要在于其将关注点全然放在由实验认定之病菌上,忽略了由症状反映出来的病人本身的身体变化,舍本逐末,甚至,将人体视为“器物(试验管)”。而且,科学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如1918年全球大流感中,由于实验仪器不够精密,当时得出唯一病原体是“普淮斐氏菌”的结论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对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细菌学兴起的“进步”背后实际是医疗对象由病人变成病菌,也即病人主体性消失及医病关系不对等的反思,近代中医对细菌学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前意义。
该书的一大亮点是探讨了知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结,即中医抗菌的理论与技术如何赢得病人或融入日常生活。作者指出,以细菌学为主导的公共卫生机制其实就是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将在实验室生产的知识推广到日常生活中。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发生了“异化”:其一,由于国家效能低下,公共卫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对个人卫生的强调,或更多靠个人的力量来对抗传染病;其二,由于缺乏实验室医学的支撑,在日常生活中,细菌学基本停留在杀菌、消毒与阻断传染等笼统的概念上,与分辨细菌种类及其传统途径的专业知识相去甚远。这两个“异化”为中医实用性的持续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在理论层面,对个人而言,细菌学并无实际的指导意义。相反,中医“气论”将疫病的发生定义为个人行为与空气、季节等环境因素之间的因果对应,也即“气”是身体对空气、季节等的感知,是可以被观察与推测的,从而给出个人对抗传染病的基本思路。在技术层面,传统中医知识体系不乏杀菌、消毒与阻断传染等概念,以此为基础与根据,近代中医整理出诸如雄黄、苍术、贯众、藿香、蒜、硃砂等防疫药物,但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经验来看,由国家主导对中医防疫药物进行科学实验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总之,用该书序言作者余新忠教授的话来讲,所谓中医“不懂细菌学”、“反科学”更多是一种“想象”,而非“真实”。同时,皮国立教授在《自序》中写道:“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了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尽管占据着知识甚至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但在“造福全人类”的目的下,科学终究只是手段,以科学与否来评判中医,否认其“治病济世”的价值,显然是不可取的。
(2020年4月29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读后感(五):困境与再造:细菌学之下民国中医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
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原本信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被抛进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西学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学术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学为体,中学不能为用”的挣扎,几乎所有业已习惯旧道德、旧学问的人,都不得不如吴宓所说的那样,脚踏两匹分道而驰的马背,在新世界和旧理想的拉扯中承受心灵的车裂之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也是如此。近代中西海禁重开以后,西医来势汹汹,一路攻城略地。清末,面对西医由解剖学发展而来的生理知识,中医尚且可以应付,甚至有汇通中西的努力。但20世纪,尤其是民国肇始以后,细菌学的传入和确立却直接动摇了中医生存的基础。在学理层面,“一病有一病之病原菌”直接挑战了中医疾病学的基础,不能知菌、杀菌成为中医“落后”、“不科学”的象征;在政策层面,中医对以细菌学为基础的国家防疫体系的建设无所贡献,也为甚嚣尘上的废止中医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说,细菌学是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生死存亡的挑战。
中医如何应对来自西医细菌学的挑战?如何在传统正典的基础上吸纳、汇通西医的疾病学理论?在此过程中,他们有怎样具体的改变,又有哪些坚守的底线,以致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中医?以及,中西医思想的混杂交织如何下渗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正是皮国立的新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所要解决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本书取民国时期的外感热病为对象,对中西医学在整体细菌学上的争议做了详尽的讨论。除第一章绪论与最后一章结论外,共八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两章为第一部分,介绍细菌学理论传入前中西医学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解,两者如何从似曾相识逐步走向貌合神离;以及清末民初以来,西方医学和日本汉方医学热病书籍的传入对中医的潜在影响。第三、四、五章为第二部分,从医学理论层面,探讨在面对细菌学挑战时,中医内部如何调和既存的寒温之争,重新定义西医的病名;如何以传统的中医理论认知、回应和汇通西医细菌学;并以恽铁樵的例子来看新中医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与困境。第六、七、八章为第三部分,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出发,检视西医的卫生论述如何被中医所吸收,形成近代中医独特的防疫技术和抗菌思想;同时,这类知识如何下渗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大众日常的防疫、保健,以及病后的调理与饮食。
通过这样的章节编排,作者皮国立希望能够实现他所提出的“重层医史”(multi-gradation of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的研究目标,即立足“上层”,以文献梳理医学“内史”脉络,梳理医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同时,亦能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兼及“下层”,呈现医学知识变迁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具体而微的影响。
细菌学的挑战与中医的因应之道
所谓外感热病,是指那些由外感六淫(风、湿、寒、暑、燥、火)造成的病邪传变以及脏腑血气受损的疾病,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相当于西医的传染性疾病与感染性疾病。从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出现开始,中医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疾病,并有相应的理论与疗法。明清之际,伴随战乱、对外交通以及南方人口的快速增长,温病学派在江南地区兴起,中医内部出现了寒、温并举的局面。伤寒派和温病派成为中医热病理论的两大流派。
19世纪中叶,西医逐步传入中国。虽然在热病的命名和分类上,中西医有所不同,但就其成因及症状描述,两者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晚清在华行医数十年的合信就曾以气、季节、风土、秽毒、天行、热感等解释热病,与中医传统的气论及风土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热病知识的归纳上,双方均着眼于以“症状”来命名疾病,且实际治疗效果而言相近。因此。清末中西医热病学说的初次相遇,并未给中医带来真正的挑战,甚至因彼此的“似曾相识”而使两者之间有了更多“汇通”的可能。
不过,当民国初年,西医细菌学理论支撑起的传染病论述,及其背后附带的身体观、疾病定义、防病观念,尤其是国家卫生行政体制在民国初年逐步站稳脚跟后,这样的汇通便不再可能,中医的挑战正式来临。
如今我们一般将“辨证论治”视为中医的根本特征,虽然这是1949年以后中医因应“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影响才确立的概念,但以症状而非病菌作为疾病划分的依据,确是中西医之间的重要分别。民国初年,当细菌学及其所主张的“一病有一病之原”观念被掌握国家卫生行政主导权的西医精英接受后,传统中医以症状来统称一类疾病的做法便不再适应“现代医学”的要求。但如果放弃旧有的疾病解释权,全然采用细菌学定义,则又会使中医陷入不能自立的境地。
面对这一困境,民国中医采取的策略,是将细菌学及其定义下的“伤寒”容纳进中医原有的疾病分类和知识体系之中。总体而言,民国中医并不排斥细菌学,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学术更新问题,无人能够否定细菌的存在,而且西医以发热症状作为热病的诊断依据,也与中医伤寒理论一致,两者并非不可汇通。因此,从一开始,中医基本上就对细菌学保持吸收的姿态,许多中医专门学校还开设了相关课程,吸收部分西医学说的新定义,再套入古典学的相关理论。而深谙旧学章太炎甚至“据古释菌”,将微菌与中医常说的“虫”相联系,并从古籍中考证出“厉风”、“贼风”、“瘴气”与微菌的关系。这种“西学源出中国说”虽然不无比附嫌疑,但强调细菌古已有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医接受细菌学的难度。民国初年,当Typhoid作为“伤寒”的中文译名籍由赴日留学的中国人输入国内时,寒温两派都表示接受。不过,“伤寒”派中有人主张将中医伤寒与西医Typhoid相对应,有人也认为中医伤寒涵盖更广,Typhoid仅为其中一端。“温病”派则以“湿温”来加以解释,认为湿与细菌实有相似之处。通过这样的策略,寒、温两派成功将西医细菌学的理论纳入中医原有的疾病解释框架之中,以实现应对西医挑战,保存古典医学的初衷。
中西医病名的对译只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在医学知识转型的宏观层面,中医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民国初年,应对细菌学的挑战,中医回归正典,提出了“菌在气中”的主张,将细菌纳入传统中医“六淫”气论的范畴中加以解释。气论者认为,西医坚持以细菌作为疾病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细菌并非主因,它的滋生深受客观环境制约,不仅与空气、湿度、温度、季节变化等外在环境息息相关,还跟个体的身体状况,如气血、经脉密不可分。西医单讲细菌而忽略人体内外环境,无疑是偏面的。除此之外,被抓住把柄的还有西医的实验室验菌方法。中医强调说,人体是一整套玄之又玄的系统,一个人健康与否,视各种气的消长与症状的关系,如果仅凭实验室观察到的病菌就来确定疾病,无异于将“试验管视同人体,以动物试验为金科玉律”。何况细菌种类繁多,变化多端,远非当时诊断技术所能完全确定。因此,西医将大把精力耗费在病菌的分辨上,不啻胶柱鼓瑟,缘木求鱼。
虽然不能验菌,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医自信其所坚守的气论和辨证施治,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比西医更为可靠。名医恽铁樵就认为西医对细菌的重视是着眼于外因,但一个人感染病菌与罹患疾病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生病与否,关键在于个人精气是否充足,亦即西医所说的“抵抗力”和“免疫”,而精气又跟五志、饮食、男女性事等因素相关。因此,验菌只是对中医理论的验证和补充,并不能撼动其基础。有些急性病发展迅速,病症变动不居,杀一菌又变一病,如果拘泥于病菌本身而忽视病症变化,不仅对于诊断毫无帮助,甚至有可能因此错失治疗先机。中医从大处着手,依据外在症状施加治疗,自然比西医单纯的杀菌更为可靠。更让中医倍感信心的是,民国时期,西医虽然有办法验菌,但有效的杀菌药物一直要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才被发明出来,因此,长期以来,西医所倡导的应对之法也只有隔离、消毒等消极预防措施。在恽铁樵看来,这些做法很多生活困难的病人根本无法实施,平添负担,远不如中医以调摄之法增强病人的气血和抵抗力来的高明。
以经典理论因应细菌学的挑战,几乎是民国中医界的共识。但中医作为一种技术,如何在临床治疗中展示其实效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是此时中医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民国时期,在西医尚未发明抗生素的年代,中医反倒有许多对付“细菌”的观念和药方。在当时的中医内部,有一种思路认为,细菌并非热病的主因,因此药物的使用应当着眼于驱逐导致菌毒的“外气”,即寒和热,菌毒既除,菌也就不足为惧。另一种思路则认为中医传统“解热拔毒”或“杀虫”的方剂事实上也有除菌功能,用汗、吐、下等法将病人体内的毒排出,病人自然能够痊愈。还有医者相信“微生菌既由气候而来,参气候之变”,因此,不用汲汲于微菌和杀菌本身,立足传统,调整外在之气与个人身体的关系,才是治本之要。
通过对民国中医热病知识的细致梳理,皮国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本土知识体系在面对近代西学冲击时的困境与努力。在中西医学交汇的时代,面对细菌学的挑战,民国中医虽然处境艰难,但最终却没有走上西医实验室验菌、杀菌的路子,也没有抱残守缺,避免了像日本汉医一样被废的命运。而是一方面籍由经典,选择性地吸纳细菌学的部分知识,另一方面,固守“五运六气”、“虚实寒热”等“正典”的支柱地位,并在与细菌学的交错互动中实现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更新,重建了一套中西医汇通的历史模式。他们努力、坚持和改变,使中医一步步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
中西医学交织下的日常防疫与个人生活
20世纪初,细菌学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一套新的卫生学知识,强调病菌对人体的危害,研制药物杀菌,要求个人卫生对自我卫生行为加以约束,以医院作为疾病管理的主要空间。不过,这套西医的标准化的操作在民国并不适用。中国人日常处理热病时,事实上很少去思考细菌、实验或科学用药,仍然沿用传统的应对方式和养生之道。而中医在面对西医冲击时,虽然不断对话,甚或受其影响,但根基还是传统经典。这种中西交织、混杂的局面,不仅塑造了民国时期中医新的防疫技术和抗菌思想,还由知识层面下渗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图景。对这部分历史的描述,是本书的另一大亮点。
皮国立认为,中医在日常防疫和个人生活中,与知识层面的状况一样,对于细菌学也没有过多的排斥。19世纪中西医相遇时,中医还曾不断吸收西医原始的瘴气学说,阐述空气、日光、水、土壤等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密切关系。这跟一般人所想象的近代中西医论争,两者势不两立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细菌学进入中国后,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异化”趋势。第一,在西方以细菌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公共卫生和大规模的传染病防疫是最重要的举措,但在近代中国,“个人”的防病和卫生被摆在了第一位,压过公共的视角;第二,虽然细菌学的权威无法撼动,但在日常生活的抗病和防疫时间中,分辨细菌种类,阻隔和消灭病菌却不是特别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消毒、清洁和隔离知识。这是当时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不健全所致,也是近代西医科学与中国社会文化交错融合的结果。
日常生活领域为中医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于热病的成因,中医始终将气论放在最核心的位置,认为气远比细菌重要,感染季节之气会罹患“时病”,感染杂气、寒气或非时之气,后果则更加严重。因此,中医时时告诫民众在日常生活和病后调养中必须因时而动,配合外在寒暑和温度,感受、顺应四时之气,以最适宜的方式来生活和疗养。病人病后的饮食和调养也是如此。虽说中西医都重饮食调理,但两者的理论基础截然不同,西医着眼于饮食的营养、生熟和卫生与否,但中医却认为食物与气密切相关,有寒、热之分,饮食不当会导致“食伤”。因此,传统中医在热病患者的饮食上有诸多禁忌。例如不能吃肉食,因为会使体内产生过多的热气;不能过食,因为胃气还未完全恢复,不利病后调理。民国时期,虽说“食禁”原则有所松动,但多数中医依然强调病人病后不能妄进食物,饮食应以清淡素食为主,“补虚”,但切忌荤腥,吃的太饱也不行。同样,中医传统的“虚”与“补”观念,在民国时期依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中医也强调病人在调养期应保持静养、休息,不可劳动、多语,饮食起居慎之又慎,同时注意身体与外界之气的调和,唯此才能够匡扶正气,恢复健康。这与西医从细菌学入手,阻止菌毒生长和传播的做法大相径庭。
不过,西医知识的传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和健康原则,上述看似复归传统的观念,事实上已经是中西医学知识杂糅交织后新的抗菌思想和防病原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风。传统中医认为风对外感热病来说是极为危险,生病后的病人应当闭门不出,以免再次感染风寒。但民国以后,接受细菌学的中医开始强调病室的空气流通,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关注的是人与物质、环境共生的议题。此外,有中医倡导平日在住所中应多焚降香、大黄、仓术等物,这样的做法固然古已有之,但他们的解释也是“细菌学”式的,出于破坏细菌滋生的潮湿空气,达到杀菌目的。许多传统药物,如雄黄、藿香、大蒜、朱砂等,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再次“发现”,并被赋予了防疫的功效。在饮食部分,民国中医吸收了大量有关营养、抵抗力的知识,将其转化为解释食疗或食禁的依据,中医传统的气、血、精等观念,也在此时用新的科学概念被包装起来,成了一种既现代又有延续性的论述。这种中西新旧观念的混杂,最终都成为新中医的组成部分,作为“活着的传统”,我们今天的中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变迁中不断演进而来。
余论:作为中国史研究的医疗史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是一本医疗史著作,但熟悉20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读者应该不难看出,该书所描述的近代中医的困境以及其努力,事实上是此时所有中国传统学术共同面临的问题。用李零教授的话说,近代所有以“国”命名的学科,如国学、国医、国剧、国术等,几乎都是“国将不国”之学。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至上和价值观念,每一种传统学术都必须在坚守经典和回应西学挑战中寻求平衡,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中证明自己的实用价值。
中医最终得以在细菌学的冲击下自存,一方面在于它在坚守传统理论的同时,吸收西医知识来排除旧有理论中的某些部分,并在其中融入新的解释,成功走了“再正典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于它能够为民众日常的防疫、治疗和调养提供指导,弥补西医重“公共”轻“个人”的空缺,换言之,是它“有用”。而这两方面的努力了最终为中医构建起了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使其能够存续至今。这段中医的历史折射的是近代中国传统知识的转型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又不是单纯的医疗史著作,它适合所有关心20世纪中国学术走向以及中国史研究的读者。
【七月份应朋友之请帮责任编辑写的一篇书评,其实也不能算是书评,读书心得吧。压缩到 1800 字今天发在了《光明日报》第 15 版上,因为大庆稿子被延后了。因为已发,这篇长稿子终于可以上网了。自觉写得一般,作者的书其实更复杂一些,各方的博弈、对话、协商,没办法完全写出来,自己学力有限。有兴趣的读者还是自己去读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