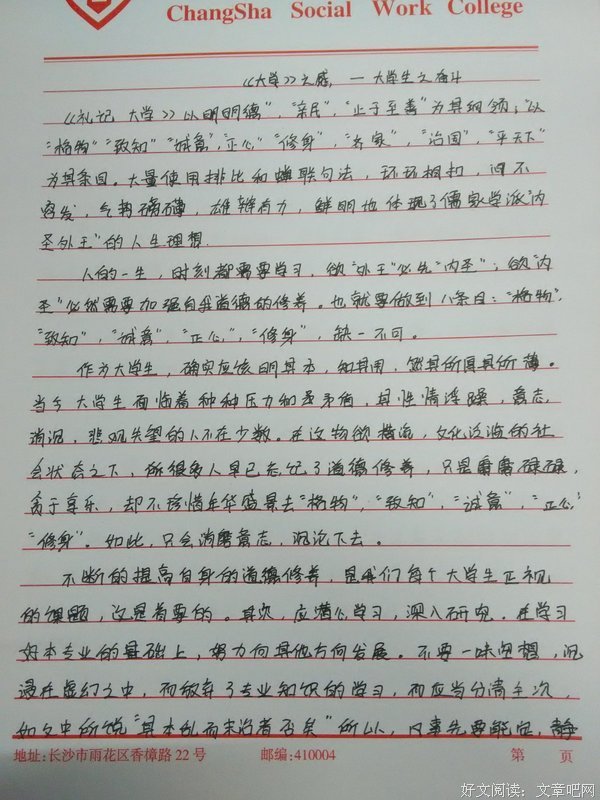《《诗术》译笺与通绎》读后感1000字
《《诗术》译笺与通绎》是一本由陈明珠 撰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术》译笺与通绎》读后感(一):【转】陈明珠:《诗学》的文本特征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微术
【作者简介】陈明珠,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法国马赛一大古典研究中心中法博士生院联合培养。现为浙江省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西古典诗学研究,专注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和中国《诗经》经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研究”,成果结项优秀。“玛高琉斯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评注研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内传风格与哲学探究”获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已发表二十多篇中西古典诗学方面的论文。出版译著《哲学之诗》(2012)、《双重束缚》(合译)(2006)、《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合译)(2014)《探究希腊人的灵魂》(合译)(2016)等。
《《诗术》译笺与通绎》读后感(二):【转】刘小枫:诗术与编故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题解绎读
【作者简介】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2003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诗术》译笺与通绎》读后感(三):【转】刘小枫:诗术与人性
【作者简介】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2003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诗术》译笺与通绎》读后感(四):【转】刘小枫:何为诗术?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要探究的绝非仅仅是“故事”的构成,很可能也包括人这类动物的自然构成本身,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不用说,凡故事都不可能没有人物,有人的行为才可能有故事。不探究人的本性及其各种行为,不可能搞清楚故事的性质及其构成。从而,探究故事的构成与探究人的本性及其行为是一回事。这样看来,《诗术》所要探讨的制作知识,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的确有直接关联。
本文选自刘小枫《巫阳招魂》现在开始阅读《诗术》,由于前述种种原因,我们必须读得极为缓慢。
第1 章起头的一段话显得是个引言,概述了要探讨的基本论题,不妨视为题解。亚里士多德以提出一系列探究对象开头:
[1447a8]关于诗术本身及其诸样式本身,以及每一[样式]具有何种特别的作用,倘若想要诗作得美好,[10]故事应如何编织,恰切的各部分该多少和什么性质,以及关于这些的其他东西,这里都要探究, 我们不妨依自然首先从首要的东西讲起。一连串的抽象术语让我们有些头晕,似乎要考验我们是否真的热爱抽象思考。首先是“诗术本身”及其“样式”这两个并列的术词,然后是“潜能”“故事”“部分”“性质”。这些语词并非平行关系,而是显出某种有层次的递进关系。“诸样式”明显是对“诗术本身”的进一步分解,随后的“作用”则是“诸样式”的进一步分解。从而,诗术—样式—作用这三个语词显得属于同一个范畴。
“倘若想要诗作得美[好]”之后出现了“故事”这个术词,与“诗术”对应,随后的“各部分”和“性质”与前面的“诸样式”和“作用”对应。最后说到“探究”方式,又出现了“自然”和“首要的东西”这两个带形而上学意味的术语。
看来,开篇第一句有三组词群,需要我们分别理解。前两组词群指涉探究对象,六个主词与第6 章具体分析肃剧时提到的六大要素在数目上相合,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第三组词群指涉探究方式,这句开场定题陈述的第一个语词是“术”,最后是“探究方式”,与《伦理学》开头第一句的“每种技艺和方法”一样。
探究对象显得有两个:第一,诗术本身,即作诗的性质、样式及其作用;第二,故事,即诗作的具体性质及其构成。两者之间有一个连接语:“倘若想要诗作得美[好]。”看来,即便懂得了作诗的性质,不等于能作诗作得好。“美”的原文是副词καλῶς,包含“好”的意思,但究竟指作诗的技艺“好”,还是故事本身“好”,并不清楚。显然,要说清楚何谓“诗作得美”(καλῶς ἕξειν ἡ ποίησις),需要大费周章。在第25 章我们会看到,所谓作诗作得“好”,不能等同于政治术或其他什么术意义上的 “好”。
什么是“诗术本身”
关于“诗术”这个语词,我们已经有了初步了解,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加了着重词“本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所谓“本身”(αὐτό)就是一个东西的“是其所是”,就是logos,但不是所有的“自身”都是logos(《形而上学》1029b19)。这里的logos 若译作“本质”(the essence),未见得达意。
我们已经知道,“诗术”这个语词有两个含义:制作和作诗,亚里士多德可能与自己老师笔下的第俄提玛一样,会玩两个含义的差异,但毕竟是在说“作诗”。我们的确不应忘记poiēsis 的源初含义是“制作”,但也不能仅仅强调这一含义。亚里士多德加了着重的“本身”,似乎在强调值得探究“诗术”的含义:有一种叫作“诗术”的技艺吗,就像我们说造船术(凭此打造出船)、御马术(凭此能御所有马)、战术(凭此能对付所有战斗)那样?获得“诗术”就能作诗,或者就能掌握作无论什么形式的诗作的能力?
“样式”的原文为eidos,在柏拉图那里,这个语词极为重要,通常也译作“相”“理式”。关于这个语词的用法,施特劳斯在《会饮讲疏》中有过简洁明了的解说,比我们从辞典里看到的释义更容易理解。他说,在柏拉图那里,eidos 这个语词首先指一个东西的形,但这种形仅有心智的眼睛(the mind’s eye)才能看见。其次,这个语词被用来指称本质性的东西(the essence)。但必须注意,当说到本质性的东西时,意思是它被理解为可能的东西,与现实的或实存的东西判然有别,而柏拉图的确认为,有某种比可感物更为真实的东西。
第三,eidos 也用来指事物的种类。在柏拉图那里, genos 与eidos 被用作同义词,所谓“种类”指起源、家庭、族类,从而先于逻辑的区分。狗的eidos 指所有狗,而非具体、个别的狗,比如说这个黑的而非白的狗。个别的东西不完整,eidos 则意味着完整,从而,eidos 这个语词带有激发性目的(the goal of aspiration),即激发对整全的关注。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自己恰恰习惯于关注个别的不完整的东西,而非关注整全。
按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的说法:下定义就是把正在讨论的东西放进它所应该归属的“种类”(genos)里面去(108b22)。这里看起来就是在下定义,下定义就得划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通过划分而来的定义,首先得到的是“种类”(γένος)和“属差”(διαφοραί,1037b29)。工具论中的说法更清楚:
最初的词项是个种,这个词项与他的属差的结合也是一个种,属差是全部被包含在内的,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不可再划分出属差之点。(《后分析篇》97b3)在《诗术》的开首句中,“诗术本身”显然是种类,而eidos 是属差(复数)。〔1〕由此看来,似乎eidos 可以理解为诗作的“文类”。可是,亚里士多德明明说“诗术本身”的诸eidos,而非诗作的诸eidos。接下来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叙事诗、肃剧诗、谐剧诗等等,这些可以说是诗作的属差,却不能说是“诗术本身”的属差。毕竟,诗作的属类与诗术的属类不是一回事,因为诗作与诗术不是一回事。
必须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两次用到“本身”这个语词。肃剧诗人作肃剧、叙事诗诗人作叙事诗,因而有诗的具体属类,但“诗术”本身的“属类”就令人费解。造船术得掌握木材(作为材料),诗术得掌握言辞,可以说,诗术关涉立言行为。但立言的属差很多:作诗与论说或演说肯定有差别。难道“诗术的eidos 本身”要讲这个差别?倘若如此,“诗术本身”就是单一的东西,何以谈得上“诸eidos”,甚至“每一eidos 具有何种特别的作用”?
总之,“诗术本身”与“诗术的诸eidos 本身”有差异。不仅如此,前者不可见,后者则是具体可见的形态,而这种形态似乎又不等于各种诗作的属类。由于我们不知道这里的“诗术的诸eidos 本身”指什么,我们也无法知道“每一eidos 具有何种特别的作用”指什么。
还剩下一种可能性,即把“诗术的诸eidos 本身”试着理解为仅有心智的眼睛才能看见的形。这意味着,我们看诗术的各种具体的样式,不能仅仅看可见的“样式”,比如论说或演说,诗歌或戏剧,音乐或绘画,还应该看到种种无形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诗术”的诸无形的样式又是什么呢?凡此现在我们都还无法确定,需要留心亚里士多德随后怎么说。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表面上看来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探究对象,实际上,他仅仅是在抛出一个谜团或戏剧性线团,随后才来解开这个线团。
“诗术”及其“诸样式”
仅“诗术”及其“诸样式”用了“本身”,起码表明诗术与“诸样式”同样重要。既然两次用“本身”来强化实词,那么,“诗术”和它的“诸样式”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为分析性的递进关系。诗术的“诸样式本身”不同于“诗术”本身,但毕竟是“诗术本身”的“诸样式”,从而使得没法直接呈现的“诗术本身”转换到可以直接呈现的“诸样式本身”。反过来说,唯有通过诗术的“诸样式本身”,我们才可能搞清楚“诗术本身”。
接下来提到诸样式的“作用”(δύναμιν / dunamis),显然是对诗术的“诸样式本身”的进一步分析性解析。如果“诸样式本身”是种类(genos),那么,诸样式的“作用”就是其属差(species)。亚里士多德说过,只有从量和属差来分解一个实体,才知道它由什么组成。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亚里士多德解析诗术,很可能基于他的Logos 观或他的静观知识。如果我们不清楚他对 “术”“自身”“样式”“作用”的解释,那么,就没法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
不仅如此,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如何使用“作用”这个原义为“能力、潜能”的语词。他说:要搞清楚好人的德性与好公民的德性(τὴν ἀρετὴν ἀνδρὸς ἀγαθοῦ καὶ πολίτου)有何不同,首先得搞清楚好公民的德性是什么(《政治学》1276b17)。这意味着, “好人”与“好公民”不是一回事。
为了说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打比方说,正如水手是一个共同体,但每个水手的具体作用(或能力)却不同,划桨的、掌舵的、瞭望的,这表明每个水手的具体德性有所不同。同样,公民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虽然各有各的作用(德性),但共同体总有共同归宿,这就是政体——公民的德性与他们所属的政体有关。我们不难理解,美利坚公民的一些“德性”,对我们的政体来说,恐怕得算劣性。
这段说法给我们的提示在于:“作用(能力)”与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词。就“德性”(τὴν ἀρετὴν)这个语词本身的含义来看,也如此,它首先指特殊的能力,比如马有自己的“德性”,狗有自己的“德性”……人的 “德性”则被区分为伦理的德性和政体的德性(好人和好公民)。
从这段说法中,我们看到静观知识与实践知识实际上没法分开。如果与这里说到的“诗术的诸样式”的 “作用”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静观知识与制作知识如何贯通。比如,如果“诸样式”相当于种种政治共同体,会意味着什么呢。尤其应当注意,接下来一句“倘若想要诗作得美”的副词“美”有“高尚、高贵”的含义,而且修饰动词,也就是说,这个词语界定的是行为,而非界定作为作品的诗作,那么,这里强调的就是某种行为(作诗是一种制作行为)的政治德性品质。
可以看到,第一个词群呈现为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程式。诗术本身—诗术的诸样式本身—诸样式的 “作用[德性]”。但是,诸样式的“作用”虽然已经很具体,“每一样式”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清楚,其“作用[德性]”当然也不清楚。诗术本身得通过具体的诗术样式(不等于诗作的样式)才能见出,因为,抽象的东西隐藏在具体的样式之中。由于“每一样式”究竟是什么不清楚,如此解析等于没有让我们明白,抽象的诗术何以能得到具体解析。
“诗术”与编织“故事”
接下来第二个词群以“故事应如何编织”为导引,我们拿不准,这里的“故事”究竟对应“诗术”还是 “诗术的样式”,抑或样式的“作用”。从分析性的角度来看,对应于诗术样式的“作用”可能性最大,我们可以说:诗术诸样式的“德性”就是“故事”。
但是,每一种诗术的样式都以“故事”为特征吗?如果“故事”是“要想作诗作得好”的关键,那岂不是说,“故事如何编织”就是“诗术本身”?换言之,关于“诗术”本身的性质,要靠具体的“作诗”来回答。以“故事如何编织”来规定作诗“本身”,让我们感到费解,除非我们可以设想:作诗等于“编织”(συνίστασθαι)故事。
无论如何,以“诗术本身”为主词引出的第一词群与以“故事”为主词引出的第二词群,无异于“诗术”与“作诗”对举。换言之,“诗术”无论如何得通过“故事如何编织”呈现出来。倘若如此,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第一个词群是涉及性质本身的认知性(eidetic)说法,第二个词群是涉及具体能力[德性]的发生性(genetic)说法。两者结合在一起,相互说明,才能把何谓“诗术本身”讲清楚。
“诗术”这个复合语词本身具有双重含义,《诗术》开篇第一句通过两个词群同样呈现出双重含义:“诗术”与“故事”。这使得我们当注意整个《诗术》的说法可能具有双重含义,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很可能以双重说法的方式来阐述“诗术本身”。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既然“诗术本身”靠“故事应如何编织”才可能得到透彻说明,那么,整个《诗术》本身也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编织的一个故事。换言之,既然亚里士多德以编织故事的方式来阐述何谓“诗术本身”,那么,《诗术》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以诗术方式制作而成的故事。
倘若如此,我们就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我们必须以解读故事的方式来读《诗术》。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诗术》特别难读:《诗术》毕竟是论说文,但这个论说文却是用编故事的方式写成。说到底,亚里士多德在作诗。换言之,由于我们的脑筋断乎不会想到,理论性论说也可以采用编故事的方式,《诗术》乃至亚里士多德的其他传世讲稿才难以理解。
第二,对诗术的理解必然超逾我们习传的对诗的理解:诗术不仅涉及作有格律的诗,毋宁说,它涵盖所有立言方式,尤其论说的立言方式。由此可以理解,为何诗术的“诸样式本身”不能等同于诗作的样式(各类诗作的体裁)本身。
“倘若想要诗作得美”——我们可以问:热爱智慧[哲学]的论说之作不需要作得美吗?《会饮》中的第俄提玛曾“举诗为例”,借助制作与作诗的双重含义来说明热爱智慧[哲学]本身。第俄提玛从任何爱欲都追求美谈起,然后描述不同的爱欲追求生育不同的美,最后才用诗一般的言辞说明:热爱智慧本身与追求“既不生也不灭、既不增也不减”的“永在的”美,真正的热爱智慧者会“在无怨无悔的热爱智慧中孕育许多美好甚至伟大崇高的言辞和思想”(《会饮》210d5-211a1)。
通过以生育类比制作,第俄提玛让苏格拉底领会到:倘若谁有热爱智慧的爱欲,谁就会欲求善,但这欲求不可能充分,因为这种爱欲没有顾及美的样式。换言之,完整的热爱智慧必然欲求美,即欲求立言,从而欲求写作,或者说欲求特别的制作德性,即作诗。
倘若没有这种“作诗”的制作德性,热爱智慧的爱欲就缺乏生育能力。我们可以设想,《诗术》意在培育政治的热爱智慧者具有制作德性,通过学习“故事如何编织”,使得自己的论说之作也能“作得美”。
所以,第俄提玛把作诗、立法和学问三者相提并论。
“故事”(μύθους)这个语词的本来含义是“讲述”,引申为“故事/ 神话”,也可以代指“诗作”。尤其重要的是:“故事”都是编出来的,或者说,“神话”也好、 “诗作”也好,都是编出来的。在《王制》中,苏格拉底说到“制作故事的人”(τοῖς μυθοποιοῖς)时,指责赫西俄德、荷马等诗人“给世人编织虚假故事”(μύθους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ψευδεῖς συντιθέντες,377d5),这里的μύθους 译作 “神话”“故事”或“诗作”都可以,“诗人们”与“制作故事的人”是同义词。
在这段对话里, 苏格拉底提出了“ 制作美好故事”(καλὸν[μῦθον]ποιήσωσιν) 的问题(377c1)。初看起来,苏格拉底批评两位诗祖制作的故事不“美好”,理由是他们编虚假的故事。但随后我们看到,故事不“美好”,不是因为编织的故事虚假,而是“虚构得不美好”(τις μὴ καλῶς ψεύδηται,377d9)。目光锐利的尼采说得好:
苏格拉底不是就说谎指责荷马及赫西俄德,而是指责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说谎……说谎在特定情况下对世人有用,必须允许统治者为了其城邦公民的利益使用谎言。〔2〕因此,“美好的故事”不等于真实的事情,而在于虚构得“美好”。
在这段对话中,以“故事”为宾词,依次出现了三个动词:ποιήσωσιν[ 制作] —συντιθέντες[ 编织] —ψεύδηται[虚构],似乎可以互换。作形容词界定名词的 “美好”(καλὸν μῦθον[美好的故事]),变成了副词修饰制作行为本身(καλῶς ψεύδηται[虚构得美好])。
苏格拉底是政治的热爱智慧者,他对传统乃至现代诗人的批评暗含一个前提:政治的热爱智慧者也能够甚至应该作诗。作什么样的诗和怎样作诗呢?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多》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现身说法的答案。临终那天,苏格拉底在狱中对前来探访他的年轻的热爱智慧者说,自己一生总梦见神命令自己“作乐和演奏乐”(《斐多》60e7)。他觉得奇怪:自己一直就在作乐,因为在他看来,热爱智慧就是最高的“乐术”,而自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不就是作乐吗。〔3〕用我们的话说,热爱智慧就是在作乐,怎么自己还会不断梦见被命令去作乐呢?
苏格拉底说,直到被判刑之后,又遇到神圣的节日让他可以多活一些时日,他才想明白:原来,梦中命令他“作民人[喜闻乐见]的乐”(δημώδη μουσικὴν ποιεῖν,《斐多》61a8)。用我们的古话说,相当于“制礼作乐”。苏格拉底听从梦的命令,赶紧“制作诗篇”(ποιήσαντα ποιήματα,《斐多》61b1),作了一首供献祭时用的诗。
这时,苏格拉底又进一步反省到,如果要做真正的 “诗人”,就得“制作故事而非论说”(ποιεῖν μύθους ἀλλ᾿ οὐ λόγους,《斐多》61b5)。〔4〕由于自己天生不是μυθολογικός[说故事的人],苏格拉底只好把伊索的μύθους[故事]拿来“改编”(ἐνέτυχον),然后“作成诗”(ἐποίησα)。我们应该想起苏格拉底曾说过,隐晦地用民间的或诗歌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智见,乃古人的遗训(《泰阿泰德》180c7-d5)。
在《斐多》中,苏格拉底说到过自己的“再次起航”,非常著名,这指他离开自然哲人的静观方式:不再仅仅冥思天体,而是更多探究人世。如此转变再清楚不过地标识出,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意味着:苏格拉底从热爱智慧者转变为政治的热爱智慧者。
可是,苏格拉底关于“作诗”的夫子自道,不也可以看作他的“再次起航”?
苏格拉底的这段记梦无异于讲了一个故事,其中包含四个关键词:音乐、热爱智慧[哲学]、作乐、故事。起初,苏格拉底一直在践行热爱智慧,热爱智慧是最好的音乐,因此,践行热爱智慧就是作乐。被判刑后他才明白,梦要他制作贴近民人的乐。换言之,苏格拉底以前不明白,乐有两类:曲高和寡的乐与民人喜闻乐见的乐。于是,苏格拉底有了“再次起航”,作了祭祀性质的民人喜闻乐见的乐。可见,从热爱智慧者转变为政治的热爱智慧者还不够,苏格拉底进一步反省到,如果“应该做诗人”,那就必须会“制作故事而非论说”。
这里出现的转变是:诗人[制作者]取代了热爱智慧者。“故事”与“论说”的对举,无异于虚构与言说真实的对举:“制作故事而非论说”无异于说,也要做诗人而非仅仅做哲人。但自己天生不是“会说故事的人”,或者说自己的天性不会虚构,怎么办呢?苏格拉底想到的办法是:改编现有的民人喜闻乐见的故事(伊索虚构的故事)。这样,苏格拉底才觉得完成了使命,成了真正的诗人才心里踏实。
从古至今,天生“会说故事的人”多的是,每一时代都会涌现一大批,尤其是在民主时代。所以,雅典城邦设立戏剧文学节,让众多写手竞技。苏格拉底则看到,即便像荷马或赫西俄德或埃斯库罗斯这样的说故事高手,仍然有欠缺,即他们并不追究绝对的真实,而是逞才或挥洒自己的天赋。不仅如此,他们并不自觉地弥补自己的欠缺,相反,真正的热爱智慧者总是在不断找自己的欠缺,并切实致力于修补欠缺。苏格拉底在临终前对热爱智慧的青年讲述自己的“作诗”经历,无异于告诉他们:夕闻道而改之,亦为时不晚。热爱智慧的真正含义是修己,仅仅热爱说故事则是娱乐。修己者自有其乐,但这种“快乐”不是常人所理解的“娱乐”,而常人也不会把修己视为一种“快乐”。
由此看来,在“再次起航”以后,苏格拉底还面临过如何作诗或成为诗人的问题:作乐变成了作诗。在古希腊文中,作乐本来已经包含作带格律的诗,作乐变成了作诗的要害在于:把言辞从音乐中分离出来的。作诗的本质在于虚构的叙述(《伊索寓言》不是合乐的故事)。从而,由哲人转身为诗人,无异于从说理的论说转变为编织的叙述。
说到做到,苏格拉底的这段自叙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虚构性质。他说自己一生都在从事曲高和寡的作乐(热爱智慧之业),这应该是真实的。但他说自己在被判刑以后才明白应该制作民人喜闻乐见的乐,就未必真实,否则,他从事民人喜闻乐见的作乐时间很短,等到他发现自己“应该做诗人”并且必须会“制作故事而非论说”,为时已晚,根本没机会践行。实际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早就会改编民人喜闻乐见的故事。
可以说,苏格拉底的这段经验之谈不是论说,而是虚构的作诗。如此虚构的意图在于,借自己被判刑这一事件,突显热爱智慧者“应该做诗人”并且必须会“制作故事而非论说”,其理由究竟何在。
教热爱智慧者[哲人]如何作诗,背后暗含的问题是:哲人应该胜过诗人。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指责诗人,说他们没有制作出“美好的故事”是因为他们“虚构得不美好”。回头看亚里士多德说“倘若要想作诗作得好,故事应如何编织”,刚好接上苏格拉底对诗人们的批评。我们可以设想,《诗术》的讲授对象是那些已经知道而且明白苏格拉底为何“再次起航”的人——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挑选出来的人”。
倘若如此,《诗术》的意图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人如何作诗,而是特殊意义上的教热爱智慧者如何作诗,如何“制作故事而非论说”。由此来看,《诗术》中没有说到“在我们看来”应该说到的关于文艺理论甚至肃剧理论的方方面面,完全可以理解。反过来说,如今的戏剧学家或人类学路数的文化学家指责亚里士多德忽略了什么什么,甚至关于肃剧讲错了什么什么,不过是以自己的眼界来看亚里士多德的眼界。
我们值得进一步问,为什么诗人的制作会“虚构得不美好”?这个问题可以在第俄提玛对苏格拉底的教诲中得到解答。
第俄提玛的教诲从以诗为证开始,最后讲到何谓热爱智慧,她的说法本身就带有虚构性——或者说苏格拉底的忆述本身就是编的故事。但是,苏格拉底忆述自己的老师对他的教诲时,肃剧诗人和谐剧诗人的代表都在现场,而这个现场是肃剧诗人阿伽通因自己的剧作在戏剧节上得奖办宴。柏拉图让我们看到,当时阿伽通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行。虽然他心里清楚,“对于有脑筋的人来说,有头脑的少数人比没头脑的多数人更让人畏惧”,他仍然沉浸在雅典民众的赞美中不能自持(《会饮》194a5-c6)。这意味着,诗人缺乏对自我灵魂的专注,自我表达的欲求过于强烈,作诗被作为自我爱欲的最高实现,从而不可能触及“真实”。
因此,传统的自然哲人会攻击诗人制作“虚假故事”。热爱智慧者寻求“真实”——万事万物的真实。就言说“真实”而言,热爱智慧的论说高于诗人编造的故事。但如果热爱智慧者也应该关切城邦生活,从而应该考虑共同体的立法问题,那么,政治的热爱智慧者就应该也学会像诗人那样,制作民人喜闻乐见的故事。
因此,临终前的苏格拉底作了一首“大地之歌”。与诗人虚构的故事不同,苏格拉底的诗作中隐藏着真实,即人的灵魂的真实以及灵魂在人世中应该如何度过一生的真实。从而,苏格拉底所制作的故事,不是虚假的故事——“虚假的故事”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故事与人的自然
说过“故事该如何编织”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恰切的各部分该多少和什么性质”。这话看起来像是指构成“故事”的各部分,但背后已经隐含着热爱智慧的静观知识,因为“恰切部分”(μορίων)在这里不等于“部分”(μέρος)。
亚里士多德有一篇讲稿题为“论动物的恰切部分”(μορίων),这里的用法与亚里士多德这篇讲稿的篇名用词相同。人是动物中的一个属类:动物是一个“种类”(genos),人是其“属差”(eidos)。探究动物的“恰切部分”,意味着探究人这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与作为类的动物的属类关系。因此,亚里士多德一开始辨析了“种类”和“属”的逻辑区分(《论动物的恰切部分》639b4以下)。
如果我们听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门自然学课程,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到,《诗术》开篇所谓“恰切的各部分该多少和什么性质”,是否不仅指“故事”的各部分,也可能指人这类动物“恰切的各部分该多少和什么性质”?随后的“以及关于这些的其他东西”的所指,是否也如此?毕竟,亚里士多德在说到动物的“种类”和“属”的区分之后,随即谈到技艺的成品(《论动物的恰切部分》639b15 以下)。
无论如何,我们若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论动物的恰切部分”,理解《诗术》引题的最后一句“我们不妨依自然首先从首要的东西讲起”会比较容易。所谓“依自然”(κατὰ φύσιν)指依“人”这个自然动物,至于就这个自然动物而言,什么是“首要的东西”(ἀπὸ τῶν πρώτων),则要看亚里士多德随后怎么讲。
倘若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要探究的绝非仅仅是“故事”的构成,很可能也包括人这类动物的自然构成本身,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不用说,凡故事都不可能没有人物,有人的行为才可能有故事。不探究人的本性及其各种行为,不可能搞清楚故事的性质及其构成。从而,探究故事的构成与探究人的本性及其行为是一回事。这样看来,《诗术》所要探讨的制作知识,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的确有直接关联。
注释:
〔1〕戴维斯认为,亚里士多德把eidos 理解为“属差”(species)而非“种类”,因而译作kind,如果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用法,那就得译作idea。
〔2〕 尼采,《古修辞术描述》,前揭,页7。
〔3〕 柏拉图,《斐多》61a3,亦见《王制》548b,《斐德若》259b-d。
〔4〕 王太庆先生译作“语涉玄远,而非平铺直叙”,算优美的意译。
《《诗术》译笺与通绎》读后感(五):【转】刘小枫:《诗术》与内传诗学
来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3年3期
【内容提要】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是内传文本,因此,如果说《诗术》“开启了文学批评的范式”,就言过其实。因为,既然《诗术》是内传文本,即便在当时的雅典或后来的古代晚期,也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看到,从而也就无从开启文学批评之范式。事实上,读书人是否能够理解《诗术》的意图,迄今仍然是一大问题。我们如果要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首先就得尝试进入这个内传文本。本文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文本流传以及释读史来试探这个问题,借此探究《诗术》在西方思想史(文教史)上的实际含义。
【关 键 词】亚里士多德/《诗术》/诗学史/内传文本
【作者简介】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在西方文论典籍中,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又译《诗学》)显得具有无可争议的显要地位……但仅仅显得如此而已。如今的大学中,人文学科并没有立“诗学”科目,大学有文学系,并没有“诗学系”。“文学”等于“诗学”吗?作为一级学科的“语言文学”属内的二级学科“文艺理论”等于“诗学”吗?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现代大学文教的开科设教并不具有规定性,《诗术》的所谓显要地位形同虚设。
在西方古代教育中,也没有“诗学”这个科目。古希腊人的确有诗教,但不能说诗教是“诗学”。古希腊的所谓“高等”教育要么是哲学,要么是修辞学——在雅典民主政制时期,还出现过哲学与修辞学争夺教育领导权的著名争议。①在古罗马时代,教育的主体是修辞学而非哲学。无论哲学还是修辞学,都会涉及对古传诗作的理解或解释,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的教育中都没有独立的“诗学”门类。亚历山大时期出现了专门研究古传诗作的专家,他们被称为“语文学家”,而非“诗学家”。由此看来,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大约公元三百多年前(一说在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之年,周显王22年]之前,一说在公元前335年之前)讲授过“诗术”,实际上并没有由此确立起独立的“诗学”学科。
现代文教体制中有一个庞大的专业门类名之为“文学批评”。有的时候,文学“批评”显得与文学“研究”有所不同:文学批评指对同时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学研究则指对文学写作的理论性探讨。但在更多时候,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很难区分。比如说,古代文学研究也可以被称为“文学评论”;反过来说,研究文学史实际上也是在做“文学批评”。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诗术》中讨论了古希腊的三种诗作类型(叙事诗、肃剧诗、谐剧诗),现代西方学人通常把亚里士多德视为西方文学批评的始祖,这其实是误会。“批评”这一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包含对古代和当代诗作的研究或评论——用古代传统的说法叫做“解释”,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明显并非这类“文艺批评”。古希腊早就有对古传诗作或当代诗作的解释,但与现代人所理解的文学“批评”不是一回事,正如西方很早就有《圣经》解释,但与文艺复兴之后才有的“《圣经》批评[考据]”不是一回事。如果用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来衡量,就得说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还够不上文学“批评”的档次——今人理所当然会认为,《诗术》并没有重视文学批评应该重视的东西,比如命运或神对悲剧性结局的重要作用。②如果用现代的文学“研究”观念来衡量,就得说《诗术》也够不上文学“研究”的档次,因为,今人有理由认为,《诗术》“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剧的存在、兴盛和趋于衰落的社会原因”……何况,“《诗学》不是一篇完整的、经过作者认真整理润色的、面向公众的著作……《诗学》中的术语有的模棱两可,个别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文章的布局有些凌乱,某些部分的衔接显得比较突兀”(同上)。就此而言,我们实在很难说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对如今的文学研究有何典范意义。
如今的大学文科中还有庞大的“美学专业”,甚至有全球性的美学学会及其各国分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美学是否有典范意义呢?尽管《诗术》开篇第一句就出现了“美”这个词,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论所谓“美学”。如伽达默尔所说,“美学”这一学科完全是现代学术的产物,其奠基者是康德,而非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学界晚近出版的一部“权威”教科书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明确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美学这一领域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任何一本著作好像都没有专门涉及这一题材。”③的确,“美学”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甚至比作为学科的“文学批评”出现得还晚。19世纪初,德国大哲人黑格尔47岁那年在柏林大学开设美学课(从1817年至1829年,共讲了五个学期),虽然此前和之后都有西方学人讲美学,就全面、系统和理论深度而言,黑格尔的美学讲稿(经学生整理于1835年首次出版)无人能及,堪称“美学专业”的真正奠基者。④一百年后,同样是德国大哲的海德格尔多次尖锐攻击“美学”,矛头直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解释过好些古希腊诗人和现代诗人的作品,但很难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种“诗学”,或者说海德格尔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尽管海德格尔尖锐攻击“美学”,这个专业在现代文教中的地位并无丝毫动摇。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启发下写成的《真理与方法》甚至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学要著——凡此都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在西方文教中的典范地位不得不持怀疑态度。
亚里士多德不是如今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而是哲学大家,或者说西方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本身就是值得搞清楚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问题。由于黑格尔或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身份一样,都不是如今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而是哲学大家,他们为何以及如何论诗,同样是值得搞清楚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大问题。⑤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又遇到了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典范意义问题: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的诗论与亚里士多德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先搞清楚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我们恐怕也很难搞清楚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更不用说理解《真理与方法》的问题所在。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仅仅显得在西方“思想史”(更恰切的说法最好是“文教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追究。事情的起因其实源于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是内传文本——用有点儿耸人听闻的说法,则可以说是“秘传”文本(esoteric这个词既可译作“内传”也可译作“秘传”)。20世纪初的著名古典学家桑兹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为“诗学系统批评之最早典范”,并不为过,但他说《诗术》“开启了文学批评之范式”,就言过其实。⑥因为,既然是内传文本,即便在当时的雅典或后来的古代晚期,也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看到,从而也就无从开启文学批评之范式。事实上,读书人是否能够理解《诗术》的意图,仍然是一大问题——这样的问题迄今没有消弭。何况,大哲人并不搞“文学批评”——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的诗论也都不是“文学批评”。倘若如此,我们如果要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首先就得尝试进入这个内传文本。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将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文本流传以及释读史来试探这个问题,借此探究《诗术》在西方思想史(文教史)上究竟有何实际含义。
《诗术》讲稿下落不明
今本《诗术》源于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蜡板上写下的学园内部讲课稿,原本很可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肃剧(旧译“悲剧”),第二部分论谐剧(旧译“喜剧”)——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仅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很可能遗失了(也可能根本就没写)。除《雅典政制》之外,如今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传世文迹都是这位伟大的教师在自己学园内部开设哲学教育课程时用的内部讲稿,传统说法即“内传”讲稿。⑦亚里士多德在课堂上经常说,就同一个问题他在对外的通俗作品中也曾讲到云云……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谈论一个论题会有两种讲法,内外有别。比如,关于诗这个题目,亚里士多德还有通俗对话作品《论诗人》。可惜,这部作品很早就遗失了,我们没法对比亚里士多德内外有别的讲法究竟有何不同。⑧不过,为何哲人亚里士多德要写《论诗人》的通俗作品,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思考——黑格尔在十八岁时就写过《论古代诗人的某些特征》,当时他还没有从人文中学毕业;海德格尔则在自己的思想已经炉火纯青的时候写过著名的《诗人何为》一文。
由于《诗术》是给门内弟子的内部讲稿,对于我们这些亚里士多德学园的门外人来说,即便没有语文障碍,也不一定看得懂——对现代西方学人来说同样如此。既然“内传”讲稿是讲给有学问基础的人听的,即便对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来说,要具备这样的学问基础也很难。因为,这里的所谓“学问基础”,指的不是一般读书人或文士具备的知识——比如说,不是我们现代人所具备的人文科学知识,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哲学知识。如果我们要读懂《诗术》,至少必须先熟悉比如说《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等等。对如今从事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甚至美学研究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要求显然过高。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不久,雅典兴起了新的哲学学派(廊下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亚里士多德学园开始门庭冷落。他的内部讲稿尽管由弟子们保管、传承下来,具体流传情况却迄今不明。今人仅知道,这些讲稿被弟子们带到特洛亚(Troia)附近一个小城邦,直到两百年后的公元1世纪初,才由一个藏书家带回雅典。⑨因此,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重要哲人、文史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虽然曾留学雅典,也没见过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仅见过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外传”作品。
著名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8)也是文史家,年轻时(大约19岁)曾留学雅典习哲学和修辞术。但他进的是柏拉图后学主持的学园,同样没有证据显示,他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从名称上看,我们会以为,贺拉斯的《诗艺》(Arspoetica)是《诗术》的仿作。《诗艺》共四百七十六行,内在结构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行1—294)论“诗艺”的基本性质,第二部分(行295—476)论完美的诗人——看起来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内在结构大致一致。此外,与《诗术》一样,《诗艺》谈论的诗作主要是史诗[叙事诗]和戏剧诗(行136—294),并未论及所有的诗作类型——比如,没有涉及所谓的“正诗”(justum poema)亦即抒情诗。⑩然而,这些类似之处不足以证明《诗艺》是《诗术》的仿作。事实上,贺拉斯并没有写过一部名为《诗艺》的书,所谓Ars poetica是贺拉斯的诗体书信集《书札》(Epistulae)卷二中的一封致皮索(Piso)父子的诗体长函,《诗艺》这个题目是后来的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95年)题赠的。《书札》主题杂多,绝非以文学问题为主。卷一中有二十封信,在这些写给各种人的书信中,论题相当广泛,如果要说有一个大致的主题,只能归为如今所谓的道德—政治哲学。与西塞罗一样,在《书札》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贺拉斯对伊壁鸠鲁派和廊下派哲学的看法。(11)即便说到文学问题,贺拉斯也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谈的——比如,在致马克西姆(Lollius Maximus)的第二封信中谈到荷马的《奥德赛》时(行19—31),贺拉斯把荷马当做一位道德教师。(12)
《诗艺》为什么也主要谈论史诗[叙事诗]和戏剧诗呢?据说原因在于:
《诗艺》赋予戏剧以大量篇幅的做法,部分源于雅典人对戏剧的偏爱——雅典时期,戏剧拥有政治规模——及其在罗马的地位。由于文盲和半文盲数量巨大,戏剧是文人学士与广大群众进行全面交际的惟一手段。(13)这种解释值得稍加修正——应该说,《诗艺》主要谈论史诗和戏剧诗,原因在于古罗马最早的诗人以模仿古希腊史诗和戏剧诗为尚。在贺拉斯写作《诗艺》之前,古罗马已经出现了好几位模仿古希腊戏剧诗的拉丁语诗人。严格来讲,贺拉斯的《诗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一样,不是如今所谓的诗学(或文艺理论)论著,而是道德—政治哲学论著。“诗艺”问题在柏拉图那里是政治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承接了这一看待“诗艺”的方式(“诗术”与“诗艺”就字面含义而言是一个意思)。作为柏拉图后学的学生,贺拉斯的《诗艺》看起来与《诗术》有品格上的类似,并非不可思议。但这不足以证明,贺拉斯直接接触到《诗术》,更有可能的是直接接触过柏拉图的弟子赫拉克利德斯(Héraclide du Pont,约公元前388—约公元前312)的著述(参见贝西埃等编,《诗学史》,上册,前揭)。
公元86年(汉元和三年),罗马人苏拉挥军洗掠雅典,把雅典的好些藏书掠到罗马,其中就有亚里士多德的讲稿(Pragmatien)。罗得岛人安得洛尼科斯(Andronikos von Rhodos)据此编辑了第一个亚里士多德“全集”(Corpus aristotelicum),实为全部内传讲稿(《诗术》就在其中),但并不包含亚里士多德的通俗作品。(14)不过,尽管有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在罗马帝国时期,仍然未见有哪位学人提到过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讲稿。随后的北方蛮族入侵,把古罗马文明几乎一扫而空,西方文明从此中断,亚里士多德“全集”也从此不见踪影……
僧侣学人与《诗术》
在所谓西方蛮族化的“黑暗”时期,文明的光亮在东方的西安和巴格达却十分耀眼。大约公元900年间(唐乾宁年间),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有了今人能够知道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叙利亚文译本,译者是侯奈因(Ishaq ibn Hunain,逝于910或911年)。830年(唐大和四年),有个名叫马蒙(al-Mamun)的僧侣学人在巴格达创建了一个名为“智慧之家”的学园。学园中有个翻译学园,专事把古希腊文典翻译成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侯奈因的父亲是医师,当时负责主持这个翻译学园。侯奈因的译本采用直译方式迻译,很贴近几百年后的7世纪才发现的古希腊文抄本残段。不过,侯奈因的这个译本并未流传下来,仅见于几百年后的僧侣学者萨科(Jacob bar Sakko)所编的古哲语录《对话录》(Dialogues引用过第六章中界定肃剧的1449b24—50a9一段——萨科逝于公元1241年,可见,直到13世纪,学人还能见到这个译本的踪迹)。大约三十年后,一个名叫比沙尔(Abū Bishr Mattā,870-940)的僧侣学者把侯奈因的叙利亚文译本转译为阿拉伯文(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对其中的注疏采用了有选择的直译,这就是今人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诗术》译本。当时,比沙尔在巴格达学习哲学和医术,而且学有所成,在巴格达被人叫做“逻辑家”(这是很高的敬重之称)。侯奈因不仅翻译了《诗术》,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内传讲稿,比如《后分析篇》,比沙尔也把这部讲稿由古叙利亚文译成了阿拉伯文。
在随后的两百年间,接续出现了几个阿拉伯文的《诗术》译本,均出自伊斯兰教僧侣哲人手笔。951年,阿尔-法拉比的《诗术》译本问世。(15)法拉比谙熟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统绪,有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二大师之称。换言之,法拉比首先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哲人,而非如今所谓文艺理论家,他对《诗术》的理解,不会是一种门外人式的理解。仅仅几年之后,比沙尔的学生、也是法拉比的朋友阿迪(Yahya ibn Adi)又从叙利亚文译出了一个新的阿拉伯文译本(约在960年),这个译本没有流传下来。
几十年后(我国进入宋初之际),僧侣学者阿维森纳(980-1037)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第一个《诗术》义疏。阿维森纳有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三大师之称,算是阿尔-法拉比学问的继承者,他同样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学问家,而非所谓文艺学家——那个时候,仍然没有文艺学家这样的学人。阿维森纳的《诗术》义疏共八章,第一章是对“诗”的一般解释,依据法拉比对诗的看法阐述自己对诗艺的理解,与《诗术》文本的关系并不明显。随后分七章(第2-8章)较为宽泛地疏解《诗术》文本中的主题,并未疏解整个《诗术》文本。(16)一百多年后,阿威罗伊(1126-1198,宋靖康元年至宋庆元四年)完成了亚里士多德所有内传文本的翻译和义疏。对同一个文本,阿威罗伊作的注疏分短篇、中篇和长篇三种。《诗术》有短篇注疏(大约成于1160年之前)和中篇注疏(大约成于1175年)两种——中篇注疏(有两个抄件传世)明显基于比沙尔、法拉比的翻译和阿维森纳的注疏,对《诗术》文本的分章与阿维森纳大致相同。(17)
这些亚里士多德《诗术》的阿拉伯译者和注疏者都是哲人,他们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却不一定熟悉《诗术》所涉及的古希腊诗剧。因此,无论阿维森纳还是阿威罗伊的《诗术》义疏,都很难按一般意义上的“诗学”来看待和理解。按照亚里士多德门内弟子的传承,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统绪被分为两类:工具性的学问和有“实质内容”的学问。工具性的学问如今称为“工具论”,这类学问旨在培养学问人的思辨“能力”(faculties)。具有实质内容的学问分为三个学科:理论性学问(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实践性学问(政治学、家政学和伦理学)和制作性学问(包括大多数职业和手艺)。亚里士多德的门内弟子把《修辞学》和《诗术》归为“工具论”类的讲稿,与《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等视为同类讲稿。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按照亚里士多德门内弟子的传承来疏解《诗术》,阿维森纳把《诗术》分为七章(而非如今的二十六章),依据的就是“工具论”原则。(18)
可见,要理解《诗术》,先得掌握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统绪,或者说先进入亚里士多德学问的家门——有如我国古学所谓“家法”。如果仅仅从如今的文艺美学甚或古典学的视角来看《诗术》,恐怕就很难进入这个“内传”文本——直到20世纪,仍然有西方学者指责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把《诗术》归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部分,却没有努力去理解为何如此。古典学家桑兹说,《诗术》“题旨宏深,惜传至今世的本子未够良善,多有阙佚与窜衍”(《西方古典学术史》,卷一,前揭,第88页)——中古阿拉伯学人并没有这样认为。爱尔兰的阿拉伯学家马戈琉斯(D. S. Margoliouth)与桑兹是同时代人,他根据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的注疏传统提出,所谓阙佚或窜衍其实是“内传”文本的特征,并非真的是“阙佚与窜衍”。(19)
阿威罗伊注疏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主要讲稿,13世纪的基督教僧侣学者几乎将这些注疏全部译成了拉丁文(仅两部注疏未译)。(20)把阿威罗伊的《诗术注疏》译成拉丁语的是日耳曼修士阿勒曼努斯(Hermannus Alemannus),成于1256年(宋宝祐四年)——这个名为Poetria Aristotilis的拉丁语译本有24个抄本传世。阿勒曼努斯还翻译了阿威罗伊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修辞学》写的中篇注疏。他本打算从阿拉伯语译本翻译《诗术》正文,由于感到难度太大,最终不得不放弃。值得提到,阿勒曼努斯要求按照伊斯兰教僧侣学人的家法来理解《诗术》,他在为《修辞学》—《诗术》注疏拉丁语译本写的译者前言中说:
任何读过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阿威罗伊和诸多其他学者著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两部著作属于逻辑学的一部分。的确,从文本本身来看,这也显而易见。任何人也不可能从西塞罗的《修辞学》(Rhetoric)和贺拉斯的《诗艺》找理由。西塞罗把修辞学当做“通俗哲学”的一部分,并从这个角度仔细研究它,贺拉斯则把诗当做语法的一部分来研究。(21)这段说法让我们得知两个重要的文史背景:首先,在接受亚里士多德《诗术》之前,西方基督教僧侣学者已经熟悉西塞罗和贺拉斯的著作,在阿勒曼努斯看来,贺拉斯的《诗艺》乃是理解《诗术》的障碍,正如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这段说法无意间挑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与通俗作品的差异——西塞罗仅见过亚里士多德的通俗作品,在阿勒曼努斯看来,从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讲稿是不恰当的。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对话)的通俗作品,贺拉斯的《诗艺》显然属于通俗作品,从《诗艺》来理解《诗术》同样行不通。
阿勒曼努斯的阿威罗伊《诗术》注疏拉丁文本问世二十多年后,基督教僧侣学者莫尔贝克的威廉(Wilhelm von Moerbeke)直接从希腊文将《诗术》翻译成拉丁语(1278,宋祥兴元年),这的确让人惊异。遗憾的是,今人无法得知威廉所依据的希腊语原文是哪个年代的抄本。威廉也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他翻译了好些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包括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并未重视的《政治术》讲稿。由此可以推定,基督教僧侣学人并非没有获得古希腊文典抄本的直接来源——自3世纪以来,苏拉从雅典带回的亚里士多德讲稿,很可能一直在基督教僧侣学者中传衍。然而,令人同样感到奇怪的是,莫尔贝克的威廉的译本长期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古典学家发现。无论如何,至少直到14世纪,研读《诗术》仍然是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做的学问。两百多年后(1481,明成化十七年),威尼斯出版商泽里斯(L. de Zerlis)印制出版了阿勒曼努斯翻译的阿威罗伊《诗术中篇注疏》(Determinatio in poetria Aristotilis),这是《诗术》的第一个现代印刷本(Philipus Venetus版,与阿勒曼努斯翻译的阿威罗伊的《修辞学中篇注疏》合刊),而非莫尔贝克的威廉的译本。可见,即便在16世纪初,威廉的译本仍然不为人知。
重新发现和复原《诗术》的希腊文本
15至16世纪间,也就是已经有基督教僧侣学者据希腊文翻译出拉丁语译本一百多年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陆续从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发现了《诗术》的古希腊文抄件残段(最早的残段是大约7世纪的抄本),其中有一个较为完整的10世纪抄本(称为cod. Parisinus gr. 1741),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讲稿的抄本残段以及其他古希腊修辞学文献抄本在一起——比如德莫特瑞俄斯(Demetrios)的《论解释》(Peri hermemeias)和哈里卡尔纳斯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os von Halikarnass)的修辞学著作抄本。经古典学者释读,这些抄本出自四位抄写者,其中出自相同抄写者的抄件时间大致在924—988年间,也就是阿拉伯僧侣学人从希腊文把《诗术》翻译成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时期。十字军东征时,西方的基督教军队曾突然掉头攻打拜占庭,掠走不少文物,想必这些抄件来自拜占庭的收藏,因为这些抄本有君士坦丁堡图书馆的注录时间(13世纪中期)——到达意大利和法国的时间大致在15世纪中期(1427—1468)。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发现的《诗术》希腊文抄件还有一些,最重要的是三个抄件:Vaticanus 1388号抄件,Estensis 100号抄件和cod. Parisinus gr. 2038号抄件——这些抄件的年代都比1741号抄本晚。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依据这些抄件把《诗术》翻译成拉丁语。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瓦拉(Giorgio Valla)依据100号抄件翻译的拉丁文本在威尼斯出版——至1930年发现莫尔贝克的威廉的译本之前,这个译本一直被视为第一个译自希腊文的拉丁语译本。路德发起宗教改革那年(1517,明代正德十二年),Marcus Hieronymus Vida的拉丁语译本问世。在随后短短半个世纪里,意大利连续出现好几个拉丁语译本:Giovanni Giorgio Trissino译本(Venedig 1529/1562),Franziscus Utinensis Roborielli译本(Florentiae 1548),Madius[Maggi]译本(Venetiis 1550),Antonio Sebastiano Minturno译本(Venetiis 1559/1564)。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人开始着手复原《诗术》的古希腊文本——瓦拉的拉丁文译本问世(1498年)的十年后,威尼斯出版商Aldus Manutius出版了第一个《诗术》希腊文本——阿尔德(Alde)编订的《诗术》希腊文本,但这个编辑本凭据的并非是10世纪的1741号抄本。由于抄件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复原考订工作极为艰难,进展很慢可想而知。1794年的牛津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希腊文本已经是《诗术》的第七版,在当时算最好的本子。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Bekker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文考订校勘本全集问世,声望很高(即著名的柏林学院版,如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码即来自这个版本的页码),其中的《诗术》希腊文本仍很快受到挑战——1867年,瓦棱(Vahlen)才根据1741号抄本这一唯一的最早来源建立起《诗术》的希腊文原文,然而,这个抄本本身也并不完整。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者又发现了一个源于拜占庭的古希腊语抄本,但年代要晚得多,是14世纪的抄本(称为cod. Riccardianus gr. 46,现存佛罗伦萨图书馆)。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抄件,现代西方语文译本的译者在翻译时主要依赖这些古希腊语抄件(尤其1741号和46号这两个较为完整的古希腊语抄件)。(22)希腊文本抄件的发现,使得校勘家们完全撇开了中世纪的阿拉伯语译本,尽管西方学人获得《诗术》的希腊文本远远晚于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拉丁文本。然而,所有古希腊文抄件要么不完整,要么多有模糊不清的地方。20世纪的校勘家逐渐认识到,中世纪的阿拉伯语译本仍然理应作为非常重要的文本考订凭据,毕竟,这些译本的年代甚至与来自拜占庭的古希腊文本的年代差不多!此外,中世纪晚期的拉丁语译本也具有校勘学上的价值,因为,在帕兹(A. de' Pazzi)发表希腊语文本与拉丁语译本对照版之前(1536),依据阿威罗伊的阿拉伯语译本翻译的拉丁文本一直占支配地位——1548年,罗伯特罗(F. Robortello)的第一个拉丁语《诗术》注疏《亚里士多德诗术诠解》(In librum Aristotelis de arte poetica explicationes)在弗洛伦萨出版,马基(Maggi)和伦巴蒂(Lombardi)的拉丁语注疏也很有名(Venedig 1550)。著名的德国学者R. Ksssel的希腊文编本(1965)问世后一度被视为定本,但随后不久,这个复原本就受到严厉批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重视46号抄件和阿拉伯译本这两个来源(参见R. Janko, 1987前揭书)——实际上,晚近的新译本仍在吸纳最新的校勘成果——Fuhrmann的德译本(1976)据抄件订正Kassel本十多处,Schmitt的德译本(2008)订正Kassel本达三十多处,伯纳德特与戴维斯合作的英译本(2002)以及Sachs英译本(2006)亦有个别订正。可见,《诗术》的希腊文本的复原工作一直没有结束。最早的阿拉伯语译本本身对今人来说也已经是古本,同样需要考订校勘的复原工作才能使用,何况,能够同时兼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和中古阿拉伯语的学者又能有几个——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终于有两位学者合作(分别对付古希腊文—拉丁文本和叙利亚—阿拉伯译本),共同完成了依据希腊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拉丁文译本综合考订的希腊文复原本,并作了笺释。(23)
《诗术》的外传与失传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俗语学术写作的出现,也开始出现《诗术》的俗语译本。塞格尼(B. Segni)译本(1549)据说是第一个意大利语《诗术》译本,半个多世纪后又有Daniel Heinsius的意大利语译本(Lugduni Batavorum 1610),第一个法语译本(André Dacier, La Poétique d' Aristote)问世于17世纪末(Paris 1692)。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卡斯忒尔维特洛(Lodovico Castelvetro)用意大利语写的《亚里士多德〈诗术〉疏证》(Poetica d' Aristotele vulgarizzata et sposta, Basel 1570[明隆庆四年])——这个义疏堪称现代西方人理解《诗术》的开端,也是第一个译成中文的《诗术》义疏(节译)。(24)阿威罗伊的《诗术》注疏在16世纪虽然偶尔遭到攻击,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罗伯特罗(Robortello)、塞格尼(Segni)、马基(Maggi)和伦巴蒂(Lombardi)用拉丁语写的注疏无不追随阿威罗伊,把诗术视为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卡斯忒尔维特洛的注疏依据贺拉斯的《诗艺》把“诗术”视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而摆脱了阿威罗伊的注疏传统。
无论学术型的俗语写作还是翻译,起初都并非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而是出于捍卫俗语写作的需要。事实上,欧洲的俗语写作几乎与经院学的兴盛同步:一方面是基督教僧侣学人传承的拉丁语学术,另一方面是俗语文学的出现。在16世纪,意大利语和法语的文学写作已经有相当的积累,然而,人文学者仍然固守拉丁语的权威地位——著名的古今之争,可以说源于当时已经出现的俗语学术与用拉丁语表达的古学之间的紧张。(25)为俗语写作辩护,贺拉斯的《诗艺》比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显得更为有用。毕竟,相对于希腊语文典,拉丁语也曾是俗语。由此可以理解,在17世纪时,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已经有了俗语译本,并没有赶过贺拉斯的《诗艺》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布瓦洛的《诗艺》(L'art poétique)就是证明。
启蒙运动酝酿和形成之际,不断有《诗术》的俗语新译本问世:神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库尔提马斯(Michael Conrad Curtius, 1724—1802)的德译本(Aristoteles' Dichtung,带注释和专论,Hannover 1753[清乾隆十八年]),Charles Batteux的法译本(Paris 1771[清乾隆三十六年])和Thomas Twining的英译本(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牛津版1794),都是当时的著名译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这部内传讲稿在启蒙时代才开始真正外传,卢梭的《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1758)和莱辛的《汉堡剧评》(1769)都具有时论性质,其中都提到甚至深入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随着外传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理解《诗术》——莱辛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原则:“我们应该处处用亚里士多德来说明亚里士多德。”
然而,随着康德美学的出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重新开始失传——内传理解意义上的失传。换言之,不仅审美学[艺术感觉学]问题取代了“诗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诗术》的外传,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内传含义也随之失传。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堪称第一部“美学”的百科全书,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观念,而非“诗”的观念。当黑格尔开始讲“美学”时,他心里显然还没有忘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在“美学讲演录”一开始,黑格尔就说,Asthetik甚至Kallistik这个语词并不恰当,因为这门学科的对象范围是“美的艺术”。“艺术”这个语词的德文原文虽然不是来自希腊文,却是用俗语[德语]来表达希腊文的“技艺”或“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术》可以译作Staatkunst,“诗术”可以译作Dichtungskunst)。黑格尔说,“在当时德国,人们通常从艺术作品所应引起的愉快、惊赞、恐惧、哀怜之类情感去看艺术作品”(《美学》,卷一,第3页)——显然,“恐惧”和“哀怜”这两个语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而且在启蒙运动时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比较《美学》卷三[下册]第287-289页对亚里士多德的“肃剧”观的解释)。黑格尔在18岁时就写过《论古代诗人的某些特征》,他当然熟悉亚里士多德的《诗术》。然而,尽管黑格尔认为,“美学”的正确名称应该是“艺术哲学”,仍然依据德语[俗语]哲学的“美学”观念置换了“诗术”的目的:
诗的艺术作品只有一个目的:创造美和欣赏美;在诗里,目的和目的的实现都直接在于独立自足的完成的作品本身,艺术的活动不是为着达到艺术范围以外的某种结果的手段,而是一种随作品完成而马上就达到实现的目的。(27)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诗”成了“各门艺术”的一个种类,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重点讨论的戏剧诗在这个种类中处于最末位置(参见黑格尔《美学》卷三[下册],页240以下),尽管黑格尔还没有忘记“古代戏剧体诗与近代戏剧体诗的差别”(参见《美学》卷三[下册],第297-300页),这意味着没有忘记现代与古代的对峙——尽管如此,或者说,尽管在讨论戏剧诗时,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显得具有政治哲学的深度,如果我们对比基尔克果在《或此或彼》第一部中的“现代戏剧的肃剧因素中反映出来的古代戏剧的肃剧因素”对黑格尔的反驳,就可以看到,基尔克果对《诗术》的解释更靠近内传诗学(即便这种解释带有基督教信仰色彩)。(28)
为了恰当地理解希腊悲剧中深刻的悲痛,我必须体验希腊意识。因此,当那么多人赞美希腊肃剧时,无疑常有鹦鹉学舌一样的重复,因为,很明显,我们时代至少对真正的希腊悲痛没有伟大的同情。(同上,第168页)借用基尔克果的这一说法,我们兴许可以说,随着《诗术》希腊文本的校勘和译注的不断精进,我们的时代无论对《诗术》有多少赞美,至少对《诗术》没有“同情”(或内传)的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格尔“美学”虽然反康德“美学”,一旦他跟随康德的哲学范式,审美主义的自律论必然会打断《诗术》的内传传统——据说,诗的制作和欣赏属于审美经验独特且自主的领域,审美经验的愉悦与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无涉。20世纪中期著名的《诗术》研究者布切尔(Butcher)清楚知道,“美的艺术”(fine arts)是个现代观念,但他说,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诗术》,因为《诗术》提出了“一种与宗教和政治不相干、且自由而独立的心智活动,具有与教育或道德提升截然不同的目的”,“美的艺术无涉乎实践需求;它不寻求影响现实世界”。(29)布切尔固然是在赞美《诗术》,然而,这种赞美是康德美学式的赞美。(30)即便反对用康德式审美观念来阅读《诗术》的拜瓦特(Bywater)宣称,亚里士多德的肃剧论具有道德—政治意涵,其前提仍然是康德的美学观。(31)
内传《诗术》失传的最佳证明,见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类学式古典学的《诗术》解释——这个学派迄今仍然是西方古典学界中的显学。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与维达-纳克(Pierre Vidal-Naquet)合著的《古希腊的神话和肃剧》(1973)早已成为当今古典学“经典”,亚里士多德在其中受到这样的指责:由于把肃剧视为民主政体的公民教育手段,他看不到肃剧愉悦引发的崇高感,将人们在阅读或观看戏剧时体会到的深奥玄妙还原成一套平板乏味的公式。韦尔南的人类学式的古典学具有这样的抱负:撤销《诗术》解释古希腊肃剧的权威性。据说,古希腊的肃剧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与其说让我们能够理解古希腊肃剧,不如说让我们不能理解古希腊肃剧。因为,亚里士多德不能理解肃剧情景,不知道如何审视肃剧中的那些深刻的历史和人类难题,看不到肃剧所教导的善之脆弱。何况,《诗术》在最关键的地方背离了古希腊肃剧的特质,因为《诗术》仅仅关注的是成文的剧本,并由此引申出所谓文艺的普遍真理,完全忽略了戏剧的表演和剧场,忽略了当时的文化生态和观众的参与,忽略了肃剧诗要靠歌曲及抑扬顿挫的吟咏来展现——戏剧的特质在于演出,而非成文的剧本。跟随这样的显学,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探讨肃剧时,亚里士多德有着极严重的盲点,或者可以说是戏剧欣赏的智障,因为他着眼的只是剧本,只是参见理念与知性范畴的故事与性格发展,只是文化的展现。”(32)
无论康德美学式的赞美,还是人类学式古典学的贬抑,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不相干。毕竟,《诗术》在一开始就是内传的“诗学”——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具有内传性质,我国第一位与西方诗学照面的伟大诗学家王国维才与《诗术》失之交臂……不然的话,《人间词话》或《红楼梦评论》都会有别样一番景观。
注释:
①参见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八章“教育与修辞”。
②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1999年,引言,第7-8页。
③见福莱主编:《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冯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④黑格尔:《美学》,三卷本,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1981年。
⑤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在“浪漫型艺术”的分类题目下系统论述了“诗”,见黑格尔:《美学》,前揭,第三卷下册。海德格尔的“诗学”论著主要见于:《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荷尔德林诗的解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⑥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卷一,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⑦参见哈利维尔:“《诗学》的背景”,见《经典与解释15:诗学解诂》,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⑧《论诗人》残篇辑佚,见R. Janko编修,Aristotle, Poetics I with the Tractatus Coislinianus, a Hypoth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Poetics II, the Fragments of the On Poets, translated with notes, Indianapolis/Cambridge 1987. R. Janko雄心勃勃,不仅重订《诗术》文本,还试图重构据说失传了的《诗术》论及谐剧的部分,并辑佚《论诗人》。
⑨《诗术》文本的流传史,依据Thomas Busch, "Chronologische bersicht zur Textgeschichte"(“文本史编年概观”),见Arbogast Schmitt, Aristoteles Poetik, Berlin 2008, XVII—XXVI;哈迪森,《阿威罗伊〈诗术〉注疏在中世纪批评史上的地位》,见阿威罗伊:《论诗术中篇注疏》,刘舒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45-165页。
⑩参德拉·科尔特(Francesco della Corte)和库什纳(Eva Kushner):《古代诗学》,见让·贝西埃等编:《诗学史》,上册,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11)O. A. W. Dilke, Horace: Epistles Book I(《贺拉斯书札卷一笺注》),London, 1966, pp. 16-17. Horaz, Episteln (《书札》),Christoph Martin Wieland译注,Stuttgart 1963。亦参C. O. Brink, Horace on Poetry: Prolegomena to the Literary Epistles(《贺拉斯论诗:文学书简绪论》),Cambridge, 1963。
(12)有学者推断,贺拉斯也许从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著作中得知《诗术》的一些内容,或者通过亚里士多德弟子(如漫步派的尼俄普托勒摩斯[Néoptélème])的著作接触到《诗术》。
(13)贝西埃等编:《诗学史》,上册,前揭,第34页及下页。
(14)参见H. Flashar编:ltere Akademie—Aristoteles—Peripator(古学园—亚里士多德—漫步者),Basel 2004,第147页以下。
(15)A. J. Arberry编辑和翻译的文本(Canons of Poetry),见Rivista degli Studi Orintali 17[1938],第266-278页。阿尔-法拉比的亚里士多德内传讲稿注疏,参见参见阿尔-法拉比:《哲学的兴起》,程志敏编,中译本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6)1953年,开罗出版了阿拉伯语考订本。西方学者的研究和翻译,见I. M. Dahiyat, Avicenna's Commentary on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A Critical Study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Leyden, 1974。阿维森纳的哲学思想,参见阿维森纳:《论灵魂》(译自俄文),北京大学哲学系译,中译本前言,商务印书馆,1995年。
(17)1953年开罗出版阿拉伯语考订本,参见中译本阿威罗伊:《论诗术中篇注疏》,前揭。
(18)《诗术》的阿拉伯语译本和注疏的权威研究为J. Tkatsch, Die Arabische bersetzung der Poetik des Aristotlles und die Grundlage der Kritik des griechischen Textes(《亚里士多德〈诗术〉的阿拉伯译本及其希腊语文本考订的基础》),两卷,A. Gudeman/Th. Seif编,Wien/Leipzig, 1928/1932。
(19)参见马戈琉斯,The Poetics of Aristotle(London 1911,英译加笺注),导言,第21-123页。桑兹甚至没有提到《诗术》文本的“内传”性质,这对于理解《诗术》却是首要的常识。
(20)还有译自叙拉古文的希伯来语译本,尽管版本情况不明,我们应该注意中古中期的犹太教哲人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接受——我们中国学界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依循的是基督教僧侣学派的传统。基于儒家传统的我们,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必须考虑西方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大不同传统的差异。1337年,居住在法国阿尔附近的犹太哲人托德罗西(Todros Todrosi)将阿威罗伊的《诗术》注疏翻译成希伯来语,他还翻译了阿威罗伊为《辩谬篇》和《修辞学》所作的注疏。
(21)转引自哈迪森:《阿威罗伊〈诗术〉注疏在中世纪批评史上的地位》,前揭,第153页。
(22)著名的有意大利学者A. Rostagni的编本(Turin, 1928),法国学者J. Hardy的编本(Paris, 1932),德国学者A. Gudeman的编本(Berlin, 1934)。
(23)Leonardo Tarán/Dimitri Gutas编辑、笺注,Aristotle, Poetics, Editio Maior of the Greek Text with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and Philological Commentaries, Leiden, 2012.
(24)中译(吴兴华译)原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六辑,重刊于《经典与解释17:诗术解诂》,华夏出版社,2006年。
(25)参见贝西埃等:《诗学史》,上册,前揭,页225-229,尤其页374-380;彼得曼,《马基雅维利与但丁》,见《经典与解释10:马基雅维利的喜剧》,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42-195页。
(26)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3页。在解释“肃剧性恐惧”时,莱辛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谈到“净化”时引用《政治学》。在与友人讨论《诗术》时,莱辛断言:“我无法想象,一个人不读《修辞学》第二编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全书就能够理解这位哲人的《诗术》。”见莱辛:《关于悲剧的通信》,朱雁冰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1757年4月2日信。
(27)黑格尔:《美学》,前揭,第三卷[下册],第46页。毕竟,美学是德国启蒙哲学的产物,黑格尔的《美学》明确以康德-席勒的美学论述为前提,参见《美学》,卷一,第70-78页。
(28)基尔克果:《或此或彼》,阎嘉译,上册,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53-188页。
(29)参见Butcher,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New York 1951。
(30)其实,这样的观点早已经进入玛戈琉斯的《诗术》笺释,并在具有权威性的D.W.Lucas笺注(Clarendon 1968/2002)中得到延续。
(31)参见哈里维尔:《〈诗学〉的背景》,前揭,第44页及注释。
(32)郑培凯:《古希腊政治、文化与戏剧:兼论中国曲剧之文化生态前瞻的另类思考》,见《当代》第131期(台北,1998年),第71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