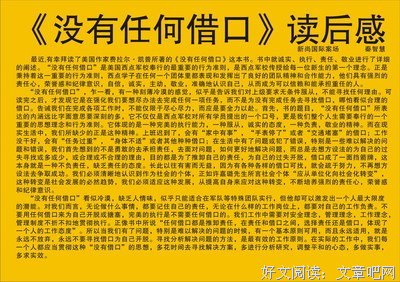风格与世变的读后感大全
《风格与世变》是一本由石守谦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多了一點點史學論述才明顯看到文學及藝術論者的缺陷,臆斷。但是史料稍詳實,邏輯合理,也不失為一種思維的樂趣,算是prediction...模式是A與B矛盾,以一個concept為線索,推出B也是正確的,進而推出當時論者認為B是錯的原因另一個方面在於文化氛圍和趨勢,即此類concept的沒落。又試圖推出此種con沒落的原因...士族以及文人失去權力后欲于entertainment領域建立嚴肅價值觀的ambition。
●逻辑清晰,行文干练。作者在第一篇提出一种可能连通变革内外结构来解释画史之变的视角,即观察创作者与其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第二至十篇则依时间顺序,在具体画史之变问题上落实其想法。
●嘛,这书,与其说是画论倒不如说是社会论,是一种思想的波动史,而非专注于画本身的传递。所以这样不行?那倒也不是的。只是难免有穿凿之举。
●幹惟画肉不画骨太好了。唯有艺术史家才能观察出的文本解读角度,特别服气。感神通灵观总让人联想起稷下学宫对圣人“能致物”的描述,近似于某种巫术的残留。此外觉得石涛那篇还挺有意思的,其他大多是从发展与变化着眼,纵向的问题横向的解答,年谱式研究,也很好看。
●不大好读!
●从唐到明中国绘画的发展,石守谦的理念在这十篇论文里,表现得相当充分。
6脚注④,《冯平山图画馆金禧纪念论文集》。应为冯平山图书馆。
7脚注①,《橋本コレクショソ・中国近现代绘画》。应为コレクション,即英文collection的片假名。
11脚注②,小川裕充〈唐宋山水畫史におけるイマジネ——シヨソ〉上、中、下。应为イマジネーション,即英文imagination的片假名。
147脚注②,Richard Barnhart, "Figures in Landseape,"。我相信这个也是不小心打错字了,不过校对在哪里?
154脚注⑤,《故宫藏书精选》。应该是《故宫藏画精选》吧。
《风格与世变》读后感(二):第一章
1“画史之变”为美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不同在于对“变”的推动人物,“变”的数量等具体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别,但共同点在于都肯定了“变”的历史意义。引用了张彦远(政治力与艺术发展存在真比关系),王世贞(变革本身自个自足),董其昌(画风之变是波浪式的产生),高居翰(外部影响力不容忽视,如何灵活的去探索外部结构与创作者内心),罗越(回到艺术家自身),卢辅圣(球体说)等。
作者认为艺术创作者与其文化环境的互动是其中重要的“变数”。以中唐为析,中唐文化界最重要的分子已由初,盛唐时有权势的世族弟子变为没落世族的弟子,他们反对富丽的宫廷画风,因此出现了水墨山水。相似现象见于宋,王安石新政后饱受艰辛的士大夫们追求自我性灵之抒发,他们反对像郭熙为代表的讲究技巧的画家,但其中士大夫们的艺术实践却各有特点,例如米芾“反技巧性”,李公麟“理性”等。元代则因为外族的统治者,文人士大夫的地位沦落至娼丐之留,赵孟頫,钱选等开始思考如何对传统文化继承,并开创抒情与书法写意新格局。明末,绘画以创作为第一要义,笔墨活动生生不息的新变。代表中国山水画最后风潮的文派山水受到王世贞,董其昌等的挑战,这些文人在传统的功业外进行文化创作从而寻找自我,例如吴昌硕“金石入画”,扬州八怪等。民国初,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推动者徐悲鸿强烈批判吴昌硕作为笔墨形式艺术,他追求“归本溯源”。
以上为作者从创作者与其文化环境互动中观察及后续发展的问题的研究。
《风格与世变》读后感(三):读后的一点小感,特别为最后一篇
这本书很有名,市面上都卖到缺货。无奈买了一本盗版印刷的,字迹淡的在灯光下看的都模糊。花了一个月时间断断续续看完了,乘现在还有点小想法,来写写看后的感受。
总体上来说不错,作者发现了很多细节问题,并深入研究,展现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在这里总体说说不足之处。
一,写法问题
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会看的比较“迷茫”,是因为作者有时候在一篇文章中引申的过于大,过于详细导致的。我们如果把一篇文章比作树枝,那么当中好几篇的树枝都太多了,有人或许会说这样说明作者的思维周密,我倒觉得是作者怕读者不了解有些历史,同时也有点小卖弄的意思。将很多背景或者作为类比的例子交代得过于详细,则会让人读起来觉得很累,往往弱化了中心问题。
二,细节问题
在读的过程中还是觉得问题比较多的,不过前面几篇都是几周前看的,大致上的都已遗忘。我就从刚刚看的,最后一篇讲石涛和王原祁合作“竹石图”这篇文章来说几个小点。
346页,作者用王原祁在《雨窗漫笔》中的一段话,就是那段批评当时扬州南京画风问题的话,来得出“也应该(批评)石涛才是”。而我认为这里的逻辑就很不周密了,在清初时候,南京的确有曾“流行”过一种浙派的风格,究其原因是因为南京还有明朝味十足的一个古城。周亮工当时在评出金陵八家时,我们发现八家中大多数是有点浙派的风格的。王原祁在这段话中所述其实严格来说,是对浙派这一风格的批评,我们知道王原祁师法董其昌,是反对所谓的北派的。所以用这段话来将石涛也包括进去,是不合理的。当时的南京一带画家遍地都是,龚贤曾经就说过南京画家达到百千人这样的话(原句不记得了~),出众者更是不少。王原祁虽然身居画家中的顶尖位置,他也不敢这么否认这些成堆的画家,同时其原句中开始便是“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其实王原祁是拿那些学浙派风格的说事,不包括石涛。
我们再看作者还有一个例子,也是346页,下方。作者一段王原祁推崇大痴的话,作者认为王原祁欣赏黄公望了,就是会不喜欢石涛,这个漏洞也一样很大。作者是要推崇黄的画法没错,但是一点都不代表他有瞧不起石涛这类画法的意思,至少从这段文字中看不出来。如果你师法张三,你当然会推崇张三的画法了,这段话只是很自然正常的话。
再回头看整篇文章,作者认为这个竹石图有问题,可能不是两人自愿合作的,他其实是从两点来入手,一点就是刚刚上面说的王原祁不喜欢石涛,甚至瞧不起,但我上面说了,这个不一定。另一点就是作者认为王原祁后来加的石头看起来使画不和谐,那我们来反过来说下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合作”的事实清宗室傅尔都提出来的,我以前看石涛传记的时候,记得这个傅尔都其实和石涛合作好久了,石涛也想借他进入皇家讲佛。这个傅尔都是有眼力的,他不会拿着一幅已经被石涛完成的竹石图再让王原祁去改改,改什么呢?加了两块石头而已,作者认为王原祁在改动的时候是有一种修补的心理。可是你就加了两块石头,根本没有改掉画的大的感觉,小小的一些修饰只是让画更加的丰富罢了(作者也在文中认为只是丰富了画作),这样的改动根本不叫修改。作者说加了石头后反而不好了,我相信傅尔都也是有眼力的人,他没有必要这样让王原祁加两石头而让整个画“更好看”。作者没有论述这点问题。用这个论点来证明王原祁“修改”了这幅画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作者的想法不错。发现的细节很多,值得学习。我在这里只提出自己的一点疑议。
《风格与世变》读后感(四):文人画和九个时代关键点
假期很长,北京也没有什么好的展览。于是就猫在家里看书了。看的也就基本集中在书画和明清这一段的艺术史了。石守谦的《风格与世变》就是我跨年看完的一本。什么是石守谦心目中书画发展轨迹?
盛唐的“白画”分为白描和凸凹画法。白描本是靠线描的粗细和密集程度呈现体积,是绘画的作色准备阶段,而凸凹画法则是有着浓淡墨晕染是呈现体积一种方法,凸凹画法从西方跟随佛教造像一起传进来的最后和白描结合成了白画,从而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力。这种变化和盛唐的文化(世变一)开放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非常不同明末清初或者清末民初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如果说白画取代白描是盛唐气象的变化的话。那么“感神通灵”这种汉代谶纬学术标准也在盛唐安史之乱(世变二)后随着职业画家的减少文人画家的出现而崛起。也是因此消失于杜甫盛唐题韩干的“干惟画肉不画骨”被后人理解为对韩干的批评在石守谦眼中也是具有隐喻意义的。
进入宋代以后,规劝绘画出现了新的形态。石守谦认为唐以前是人物规谏和象征物规谏两种风格,北宋则有了人像规谏(人物和象征物的结合),南宋则有了故实规谏。“故实”规谏的目的本不在表达臣子的勇敢,而在表达君主的从删入流。这和唐及北宋《历代帝王图》之类的规谏其着眼点略不同,而背后原因则是南宋政治气候的变化(世变三)。元代以后,北宋的李(成)郭(熙)风格曾有短暂的复兴(唐棣等人)。这种复兴主要因为中国华北最先归入蒙古统治,而蒙古统治者崇尚北方雄浑的风格。唐棣的李郭风格实际上是投元代贵族所好,为贵族所推动,为宫廷建筑所消费,并影响到南方文化。而1352年元末动乱(世变四)前后,文人重新夺回了为北方贵族所影响的南方文化权。在纷乱世道下,董巨风格则成为喜欢隐居题材文人的首选风格。
与石守谦而言,有明一代最重要的世变是嘉靖皇帝(正德皇帝的侄儿)在位期间试图将自己父亲的牌位纳入国家庙堂(正德之上),从而引起保守派林俊(文征明的提携者)与改革派张骢之间的争论(世变五)。这一世变引起了三个结果。一是明代初年由于江浙地主支持过元末农民起义张士诚,所以明初明朝对于此地一直打压(世变六)。这种打压的结果是南宋浙派成为贵族和宫廷装修风格。而嘉靖之间的政治争论导致文人和宫廷之间的忠奸质变,讲究礼仪的文人和文人风格取得对立,于是江浙一代吴门风格又取代了浙派。二是稍早于此,由于明朝早期打压苏浙地主,迁都后有所缓和(世变七),所以苏浙人去北京做官偏多,所以导致送别题材增多而且有所发展(文征明的雨余春树开启了非程式画的纪念送别风格)。三是嘉靖辩论之后,以文征明文人基本退缩出来,从而形成了受王蒙影响一种长时间描绘,堆山头饱满的“避居山水”。(这种风格后来成为董其昌批判的对象)。这种风格最终使得绘画成为私人化行为,也随着嘉靖年间苏州文人躲避倭寇入侵迁居南京(世变八)而最终消弭了浙派。及至清初,入京的四王风格成为主流,而江浙的四僧风格违背接收。无论四王、四僧都和贵族搞好关系(世变九),但又彼此不买帐,所以才出了石涛和王原祁那种你不情我不愿,博尔都穿针引线的合作以及讹传的王原祁的狠狠表扬石涛的画传。
石守谦的有两个惊人的能力,一个是他显示出作者对画论、笔记、诗文的惊人阅读能力,而且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找出被我们忽略的信息。这些在对杜甫的诗歌以及唐棣的生卒年考证都可看到且让人佩服。读书时看画论,处处是“某某擅什么,学什么”没有传世作品对照。觉得特别无聊,现在看石守谦分析浙派风格、李郭风格的衰落则知道这些都是线索。其二,石守谦是方闻的弟子。方闻则是试图在形式分析范畴内通过对空间结构的解读来取代原来的笔墨气韵读画系统。从具体作品上看,石守谦的分析方式无异是得到了方闻的真传,在对唐代白描与汉及魏晋的白描对比中,在对李郭风格与唐棣关系的研究中,在描述浙派对南宋院画的改变时都是值得学习和推崇的。
本书是9篇论文加上一个序言而成。作者试图证明具体风格的变换并非是艺术形式规律运动的结果,而是必然也首道具体政治、社会事件的影响。本书就试图呈现这种影响。而本书从盛唐对外吸收风格到中唐文人崛起,以及元明文人对李郭和浙派大山水的取代等角度描写,又可以被看作是文人画的政治史。其中最为精彩的时明代嘉靖的“大礼议”与浙派、吴门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事件的变化如何在人事、风格、交游、方法层面具体的影响到艺术家心态和风格创造是。相比之下,或许是由于资料缺乏的原因,在论及凸凹画进入中国风格时,或者中唐以后汉代谶纬学说标准退出批评舞台时,甚至李郭风格的崛起和消亡时,其风格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行文在尾部显得有些突兀。尽管如此,本书还是有些地方富有启发,比如对于元明两朝雅集(沙龙)对于风格的传播的研究,对于科举与落第或者放弃科举的分析(城市精英)都是我们切入明清现代性研究的地方。
作为一个补遗,在谈到避居山水的时候,石守谦在结尾引用了王世贞对于避居文人趣味的批评。“或谓余有所寄则不然,大丈夫好山水便当谢去朝市,安用役役寄此为然。人生有义命,要不当一端成出处也。譬如见佳画,辄云是真山水,见佳山水辄云一幅真画,究竟何所归?”王世贞对绘画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意思是绘画就是画无需附会(有些形式主义的含义),好画就是好画。这一引文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实际是朱熹和王守仁的学说之辩,后者无疑更改现代。而当时文人如文征明是在林俊保守派一边的。大礼议在后来因为辩论需要直接导致了考据和训诂(大百科全书派)的兴起。这也是现代主义的起源。只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框架中看文人画会很有意思。其二王世贞在当时文人和政治圈子权力都很大。他也是四王的理论后盾(王“辉”的爷爷)。王原祁曾说“广陵白下(扬州和南京)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需戒之”。王世贞、王原祁之间观点如何。他们乃至董其昌批判吴门的点在何处,是否在对于寄情与叙事的批判?最后,王世贞(金瓶梅的嫌疑作者)和王守仁(“现代儒学”)之间关系何在?如果我们建立其这个联系,或许对于四王的判断就会从保守主义变成中国形式和唯美“滥觞”。(当然这个角度对于东方的现代性而言有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
《风格与世变》读后感(五):《风格与世变》评述
本书是作者石守谦的论文集,它总体论述的是各个朝代的画风的流变情况以及其原因。如要分析本书的正文,那么必须先对导论进行阐述。
在导论中,作者主要就历来的对于画作风格流变的分析视角进行了一定分析。作者谈到,在对画派流变的分析过程中,往往会存在其他的因素干扰分析的过程,比如分析的时代的资料是否丰富、材料的代表性是否充足、材料的分散性。同时分析的整体视角大致不出唐朝的张彦远和明朝的王世贞与董其昌的分析框架。前者从外部结果的影响着手,(在发展成熟后)主要分析社会及经济环境、政治形势的变动以及当代思潮对于画风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后者则相信艺术内部结构之内生力量,力图从内部结构之内在规律,或者画家个人才华的层面去进分析。其后作者举了一些例子如潘天寿等人的分析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此处不再赘述。本质上这两种分析的视角都是想要再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中对问题进行因果的解释,但是这样的效果如何,后面再加以讨论。总之,“外部结构的形塑力量和内部结构的自生力量两种解释,这两种模式基本规范了后代学者对于中国画史、尤其是山水画史之变的解释途径”。
以下对正文的整体论述逻辑进行说明。在第二部分即第九篇的“失意文士的避居山水——论16世纪山水画中的文派风格”中作者的整个论述逻辑是先从文徵明即作画者的个人角度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画作,然后从苏州和南京文人的角度分析他们的整体的思想背景,并结合各地的经济发展、时人的家庭背景、不中举、对派系和官场斗争的不敏感、官场在“大礼议”之后情况进行分析,用以解释为什么文征明的画作会得到大家的承认,最后是对于多方的接合。从而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解决了最初的问题。之所以选择代表来分析,在作者看来是这样的:“一个绘画变局的出现,通常即直接牵涉到文化主流人物的性质的改变,则其对政治、社会及其他外部结构的变化考察之,各自有不同的比重,研究者于此便各依据其状况所需,进入到文化史的范畴之中”。
以下进行更加具体的论述:
作者首先谈到了16世纪的吴派和浙派的历史及演变,其中吴派在人才更换后的代表人物是文徵明,他作为“吴中四杰”之唯一超乎寻常地存活下来的人,成为了吴中仅有的大师和文化领袖。引出文徵明之画法革新,进而探究其革新为何能够引发众人之追捧。过去很多 学者采取的是以形式分析为主的观点,认为吴派晚期山水画风的确立缘起于文徵明个人对画面结构所发展出来的高度兴趣,同时当时众多的鉴赏家及文徵明的徒众对于其精彩的笔墨、秀雅的造型以及整体充满古意的气质所感染。这种分析的视角本质上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将画风的生成与繁荣放在艺术的技法发展的脉络中进行分析,但是对于个人背后的思想却并没有深入探究,也就是说缺少了一个视角。
从这里,作者引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文人的心境、背后的思想因素和其情感上的起源来进行分析。形式分析中,能够欣赏到其画作的对山水画革新的意义的人不是很多。(不过关于这一点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还是形式所承载的意涵境界,是和他们的心境所匹配的那些因素,他们对于隐逸山水画所现的情境呈现某种偏向态度(这部分作者后面会这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而选择南京和苏州来分析是因为它们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
接下来是对画作技法的具体分析,他谈到王蒙的山水画作品是产生文徵明清逸深秀风格的必要资源背景,他相对于沈周来说更加投入和持久地使用这种风格。之后考察了相关的证据证明其影响,即文徵明以往作品中呈现的类似笔法和主题。一个证据是他的《山水卷》中淡墨干笔、山石形状与质理的描绘都重在表达一种轻度扭转的动态而这来自于对王蒙风格的有意识学习。其他的画作也可作为例证,如约1530年所作的《山水》。而王蒙笔下的山水景观,如《夏山高隐》很可能是文徵明作此风格时参考的范本。似乎从1530年起,这种技法即较为繁复堆叠充塞下的山水画便逐渐成为了文徵明绘画创作中的主体。而这个时间比较特殊,有可能反映文徵明个人的某些心理状态,作者提到60岁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意味着的是富含警讯的人生关口,他们往往都会进行反思和回顾,而这会对他们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之后作者分析了他为他的好友王宠作的诗,分析道其表达了他内心上的对于平静的隐居生活的期待。之后作者对其《千岩竞秀》画作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同时说明他在八十高龄时作此画的情况,体现其严肃之心境,并且自称其“颇有思致”,同时结合它个人较为收敛的个性分析道他做出这样的感叹可能是这幅画确实在他认为是值得被高度肯定的,而被肯定的部分便是其中的“思致”。之后,作者再次对画作的构图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以往有着同样母题的画作以及题词(即“万叠高山供道眼,千寻飞瀑净尘心”)中体现的意涵,来表明这幅《千岩竞秀》中悠远而占比很大的深邃的山林其实寓意着对于淡薄生活的向往。在分析构图的下部时,作者谈到在以前作品《绝壑高闲》中作者采取了类似的构图,并通过对于作此图的目的即赠友祝贺他得以安于淡薄的生活来说明这样的构图其实表达的是对于“朝隐”、“隐居”的向往。总结即此幅画体现了他饱受挫折后力求内心平静之隐士的“避居山水”。
在对画法进行具体分析过后,作者对于苏州和南京的士人群体进行了一定分析。首先是苏州的群体。作者谈到在16世纪中叶左右,很多怀抱着“避居山水”思想的“失意文人”聚集在文徵明周围。作者对这个文人群体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当时苏州经济发展良好,产生了很多富有的商人家庭,所以很多这些士人的家庭背景往往是比较好的,他们都有入仕的情节,同时也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就在文艺学术上有了杰出的表现,如蔡羽、王鏊等人。但是他们中只有50分之一的人中了举人。即使中了举人的人也缺少对于官场规则的熟识,同时也无法很好地在妥协中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他们往往很早就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提早退休。这些文人便在文徵明周围形成了他作品的良好的受众,文徵明的作品恰好可以为他们所欣赏,于是流派逐渐发展壮大。南京的情况类似就不再赘述。而在这些失意文人在文化界地位不保后,“避居山水”也就失去了其凭借而陷入窘境,之后出现了新的流派和新的文人群体。一代潮流自此落幕。
总之,作者实际上是融合了两种讨论的视角,一方面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当时以文徵明为主导的后期吴派风格的形成与巩固消亡进行分析,这里具体体现为讨论苏州和南京文人在当时的官场环境、社会环境之下的普遍特质,如家庭的背景、中举的比例、苏州人向南京的迁徙的现象等等,一方面结合文徵明个人的曾经的作品、经历、文稿对其作品之典型即《千岩竞秀》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其思想的演进的脉络,从而揭示在其画作中潜藏的对于隐居生活的向往。两条分析的线路,一条较为宏观,属于作者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外部结构的形塑力量,即某某某倡导的分析画风之变的模式。而另一条较为微观,它是由内部结构的自生力量即个体追求风格新变的自我内在意识所决定的。而作者很好地将二者融合了起来。
接下来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艺术史分析方法和自然科学分析方法进行简单的议论,进而提出自己的意见。在阅读艺术史的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当研究者想要寻求某个现象的证据时,往往只能找到所谓的“代表性的”证据来对事件进行验证和说明。具体的例子如在说明文徵明的归隐行为的时候是通过对他的一个时期的代表作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但是在自然科学中的证据就要求普遍性而非代表性,要求完备性而非特殊性。另外,二者分析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前者可以通过对画作风格上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进而推断出模仿行为。如《夏山高隐》中有文徵明1535年山水轴上的那种居中由上往下不断地逐层泻下的流泉,从这之中就可以推断出文徵明有将王蒙的作品作为自己的灵感的来源。但是这里就存在问题,即相似是否就意味着联系,有没有可能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碰巧就采用了同样的构图和同样的母题,但是文徵明却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借鉴王蒙的作画方法?这种例子很常见,比如微积分可算是莱布尼茨和牛顿同时发明的,而进化论的思想也在华莱士和达尔文那里几乎同时出现。如果深究下去其实是无法得出结论的。而自然科学是通过比较严谨的定量研究与实验得出结论,其结果具有可验证性。
另外,笔者想要谈一下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作者似乎表明自己并不偏袒哪一方,而是持有对于普遍规律的较为坦然的态度。即“如果研究者接受“变”之不可预测性及其受社会认可的不确定性的话,那么观察创作者及其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能即可作为连通变革内外结构为一体的津梁”,这种预设其实是贯穿在作者的分析过程中的,即普遍规律之难以捉摸。所以我们往往不能直接套用各种公式。作者或许很认同高居翰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相信有任何的公式,可以在探讨一件作品的风格及其外在的因素之间,指明或暗示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任何一种思潮都不能简单地整体拿来对现象进行解释。但是在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的分析中,往往存在一种倾向即将一些时代的普遍现象作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因素,如作者在分析1530年文徵明绘画风格突然改变的时候,采用文人60岁普遍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顾这样的一个规律来进行解释。这是否有说服力?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作者并没有给我们解答,而只是凭借自己的个人理性和拿这些普遍的规律来对问题进行解释。不过即使这种推理的方式可以被批判,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无法再去访谈文徵明、无法获取其口述的资料,进而往往只能依靠有限的史实对结果进行猜测。
.S. 中国艺术史课程论文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