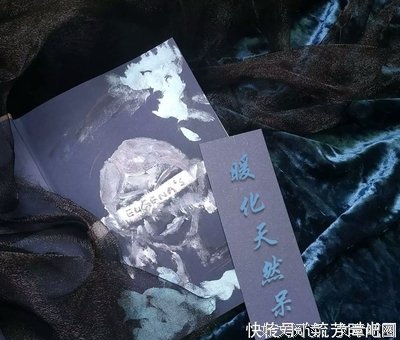沧桑看云(上下卷)读后感100字
《沧桑看云(上下卷)》是一本由李辉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的756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200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沧桑看云(上下卷)》精选点评:
●这种叙述方式和语言方式很喜欢,学习!偶尔就拿出来翻翻。
●马桶读物。
●当著名报刊的编辑真是美差
●文坛恩怨向来太多
●无意间购得,上午看了几篇,大呼过瘾。自序里说道自己喜欢和老人在一起,喜欢和老人聊天,喜欢写老人的故事,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是一段历史。上部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描述随笔,下部则以他人视角为线,对此次购置很满意。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关键看有没有人给你记忆
●历史不该掩饰不该淡忘,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是非功过,统统留待后人评说。
●李辉对一群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人物们的解读
●两本大厚书,收入的文章大多完成于九十年代,集中呈现了一批在二十世纪后半部分的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的文化人的际遇,只是主观抒情成分太足了。
●比李洁非类似题材的《典型文坛》抒情,但对于看书慢的我,更喜欢李洁非学者般的文笔,没有多余的煽情,却经常令人热泪盈眶。
《沧桑看云(上下卷)》读后感(一):胡风不告密
“告密”事件,热闹了一阵子,冷却了下来。人们对“告密者”冯亦代和黄苗子先生多半采取了宽容和谅解的态度。因为说到底,他们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我粗粗想,“告密”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的告密”,告密者往往被体制洗了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出自某个崇高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一个伟大的目标。既然目的是一切,那么什么手段就不重要了;另一类是“无耻的告密”,告密者出于卑劣的动机,向体制献媚取宠,于是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造谣加诬陷,残害无辜。当然,在一个充斥着“红色恐怖”、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氛围里,这两类情况总是交织在一起,由“无知”而“无耻”,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丑陋不已。
就在我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懦弱脸红的时候,我“看到”了胡风先生,虽然这尊雕像已经被风雨剥蚀,可是依然高高挺立,向我们昭示着什么。
胡风不告密!
他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主帅,打入大狱。文革中,那些昔日导致自己遭受厄运的人,如周扬等,也受到磨难。他完全有理由产生某种幸灾乐祸的满足。当一拨拨外调人员前来搜寻“黑材料”时,他原本可以毫不迟疑地揭发、批判。但是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随意栽赃,更不会诬陷;让外调人员不可理解,大失所望。再比如乔冠华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却在他落难之时,避之不及,很不仗义。可是文革后外调乔时,他仍然一如既往,如实地回忆自己与其交往,如实谈己对他的印象和看法。不仅如此,胡风先生还尽可能对他人的保护。比如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曾经是向胡风投稿的文学青年,外调者想从这儿找到打倒黄的突破口。胡风知道自己每句话的利害程度,便用非常明确、肯定的语气,证明其与自己的“罪行”毫无关连。他保护了别人,却又一次丧失了“将功赎罪”的机会!
说老实话,对胡先生的文学理论,我看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他这些轶事展示了一个文人的人格,是他人生最壮丽的诗篇。我们曾经真诚地相信,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之献身在所不辞;可是当“革命”成了神圣的谎言,告密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并泛滥成灾了。说假话、讲违心的话被视为正确,实事求是成了落后甚至反动,人之间最宝贵的信任感和真诚感也被砸得粉碎。就像那两句名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胡风先生因为“高尚”,悲剧一生,但他活得真实,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自己。黄树则先生说:做人应该像胡风这样。这比一切对胡风的褒词、颂词更加有分量。
昨天端午,我去听了一个教育讲座,那位特级老师在台上侃侃而谈着为孩子设计人生,什么“重点高中”,什么“名牌大学”。我忽然想到,现在的教育什么都不缺少,唯独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却要么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我们强调了许许多多,唯独“做人”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渐渐被人淡忘,被人忽略,于是我们看到了凶猛的狼、懦弱的羊,却看不到人。想当年,《舞台姐妹》里的那句台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是多么地激励我们呀!时间可以流逝,世事可以变迁,但做人的原则和标准是不应该改变的呀。不坚持“做人”的教育,或者用些大而不当、抽象的“XXXX教育”来替换,那么,我们社会的道德滑坡。远远没有到谷底!
胡风不告密。就因为这一点,我也要在他风雨中的雕像前,深深地鞠躬,奉上一瓣心香。
(《沧桑看云——不应忘记的人和事》随感之二)
《沧桑看云(上下卷)》读后感(二):剖析自己难上难
瞿秋白是烈士吗?当然是。他死得那么从容,走出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没有一点畏惧。记者这样描绘:“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是真快乐。”他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盘膝而坐,直到枪响。俗话说: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瞿秋白就是用这样动人的方式告别了世界。我想,尊其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绝对名副其实的。他将载入民族、国家的史册,流芳百世。
可是他偏偏在牺牲前,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自白《多余的话》。他写自己本是一介文人,由于历史的误会,却从了政,还成了共产党的领袖。虽然在风云变幻残酷险恶的日子里没有迟疑没有胆怯,可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回顾一生,他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对政治的厌倦。他的曾有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都以本来面目留在了文字中。
哎呀呀,一个政治家说自己“厌倦政治”,一个布尔什维克说自己是“历史的误会”,他不知道“人民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吗?果然,他被斥为“叛徒”,文革期间,连墓地都被捣毁了。我揣测过他这样写的动机,原来他不想“冒名顶替”!他写道:“以叛徒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大家是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你看,他对名声之类是多么淡漠,他只想给亲人、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宁静。至于谁“不高兴”,后果有多“严重”,那就由它吧!想想眼下那么多的沽名钓誉者,想想为争八宝山的排位、争悼词里的一个形容词而让一些人血压陡升,我对瞿秋白的坦诚深表敬意——剖析无人所知、“不光彩”的自己,毁坏自己的“光辉形象”,那同样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呀!
撇开政治。就我自己来说,有没有剖析自我的勇气呢?或者说,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敢不敢在围着我一圈的亲人面前一把摘掉那戴了一辈子的“面具”呢?
虽然平平凡凡草根一生,没有也没有条件做什么大恶之事,可是,还是没有那个勇气呀!“大恶”没有,“中恶”呢?“小恶”呢?一辈子,几十年,要干干净净、纯洁无瑕,还真不容易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这话并不完全应验,就像那句“好人好报,坏人恶报”一样。那个真实的自己是只有自己才清楚的。可是又有几个人敢于捅破自己的窗户纸呢?……按理说,活着的时候,掩饰一下、美化一下,还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可“死后原知万事空”,干什么还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呢?原来还是我们的东方文化里,形象、印象、评价之类,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赢得生前身后名”哟!瞿秋白的伟大更在于此呀!
瞿秋白说了,写了,他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从容地走了。不知那些戴着面具走的人,能不能心安理得?我想起了西方宗教世界的忏悔。你把一切告诉了神父,你的心宁静了,你的形象依然完好如故,这实在是个既神性又人性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呀!
不过,我想不一定指望神父。当社会的宽容度大大提高,当人性的多侧面被承认,当人们破除了对先辈和各种偶像的崇拜,那么,真实地“交代”自己的人生而求得良心的平静,也不是十分遥远的事。瞿秋白袒露了内心的软弱、动摇,不照样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吗?毕竟敢于解剖自己灵魂的政治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呀。
《沧桑看云(上下卷)》读后感(三):阅尽沧桑,坐看云起
一次阅读李辉的作品是在九十年代的《收获》杂志上。那时,他作品的栏目就是现在的书名《沧桑看云》,写的都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大师们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作品充满了一种苍凉之感。
李辉的文字沉着、冷静,带着深痛的思索。我没见过他本人,但他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一个和那些大师们不相上下的老者。可是,我错了。当我翻看这本厚厚的《沧桑看云》,在它的扉页,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李辉。照片中的他穿着褐色的鸡心领短袖体恤,背着一个公文包,留着卷发,面带微笑,显得风流倜傥。原来他是一个如此潇洒的中年人。然而,他的文字何以如此老成、苍茫,似乎已历尽了人世的沧桑?李辉在序言中坦诚他的妻子也是这样认识他的,他说他接触的都是经过了人生浮沉的老人,而且他喜欢和那些老人来往、交流。每一位老人,他们的故事都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这些文字虽然作者以自己的口吻在讲述,但不可避免地浸染了历史的沉重和人生的复杂。
这本《沧桑看云》该是那些发表在《收获》中的作品集了。一拿到书,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一口气读完了。以前是零星的、松散的,而这一次却是系统的、整体的阅读。书中那些文坛大师们再次栩栩如生地进入了我的脑海中。每一篇,每一个人都给我带来一种心灵的震撼。字里行间,我跟着作者感受着、经历着、思考着……
为什么我会如此迷恋这些作品呢?一方面,那些文坛大师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都是我崇敬和仰慕的。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的道路我曾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对他们的人生我始终怀着一种向往、追寻、探究的心态。另一方面,解放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浩劫使得他们的人生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那种政治的风云狂飚,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及生命的衰败都深深攫住了我的心。
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更不该让这一幕幕人间的惨剧重演。当一切尘埃落定,当人们的悲痛被如风的岁月抚慰平静,当批判、侮辱、武斗甚至杀戮离我们渐行渐远,是否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记取了历史的教训?显然不行。如今的现实我们依然能触摸到“盲目崇拜”、“大鸣大放”、“拉帮结派”等历史留迹。我很赞同巴金等几个老一辈文学家提出的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的建议,让那些在政治运动中被侮辱的、被扭曲的灵魂时时呈现在人们面前,让我们时刻铭记这一段民族的耻辱历史。
整本书,不同的章节都渗透着作者对人生、对历史的终结和深层次的思索。其实作者也在解剖自己。他告诉我们不必永远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之中,更无需让昨日的记忆来主宰我们的现实生活,“人生来就该拥抱现实,应该永远充满活力地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之中。”但是,当我们在回望历史时,“如果缺乏自我解剖自我忏悔的精神,那么对于历史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认识必然时有缺陷的,是不客观的。”。对于历史不仅仅是反思,更应该对我们现实人格的重构。“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种特别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赞赏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对于大师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沧桑。他们的人生给我一个启示:处绝境时不要失望,因为那真是希望的开始。抬头仰望天空,我们的心灵便拥有了自由辽阔的天地。
《沧桑看云(上下卷)》读后感(四):太平湖:轻波微澜依旧在
李辉的这篇《消失了的太平湖》不算太长,大概是2万字左右,写于1996年。我则是从一套新近出版的大厚书里读到的,《沧桑看云——不应忘记的人与事》。
(一)
“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马路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公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什么地方?文中告诉我们了,太平湖。对,太平湖,老舍的那个太平湖,那个早已被填平了的太平湖。李辉在《消失了的太平湖》中的一段描写。这段文字的基调,我感觉,也正是反复出现的那个字——"静"。
下面这段话还是呈现着一种"静":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
当然,那个年代一点都不平静。老舍沉沉地坐在湖边的那一天,一点都不平静。那片太平湖,因为老舍,尽管已经于物理上湮没无痕,也注定会在后人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漾起波澜。
投湖前的心境,决绝那一刻的所思所想,当我们上溯老舍的人生历程之后,其实无须再作具体的揣测。政治与文化的悲剧史诗进入高潮,无论什么样的抉择,今天看来,也都是深刻的哀与痛。
(二)
老舍与北京,北京与老舍。这对粘帖在一起的名词,早已浓浓地浸透了文化的韵致。
在李辉看来,太平湖、城墙,都是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 ,也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古都文化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扭曲的、粗糙的情感和举止。
提及龙须沟人文革中对老舍的"批判",李辉试图联系北京性格中的劣根性,诸如"可以批评一切,也可以接受一切"之类,认为这些劣根性在一个非常年代被空前地激发起来。
quot;空前地激发",这个语汇李辉还在另一处使用:" 文革,仅仅因为它把人的兽性空前地激发出来这一点,人们就永远不能淡忘,并且需要时时反思之。" 相关的叙述是:"在面对文革历史场面中的纷繁人事时,便不能不承认,人身上原本有动物的凶残的一面,有随时可以因环境的诱导而迸发的邪恶。"
我想到的问题是,兽性(动物凶残的一面)、北京性格中的劣根性与古都文化的支离破碎,其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古都文化的支离破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未曾支离破碎的"古都文化"是否有一个清晰的面貌,兽性和劣根性以怎样的形式潜藏其中?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提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如果问题可以基本成立,答案肯定都不会简单。如果问题不成立,那应该从什么角度去提问题?
不过,我坚持怀疑“兽性”的提法。文革所激发出来的,是“兽性”吗?人类的这一种凶残,是动物所能比拟的吗?或者换个问法,仅用“凶残”二字可足以形容、概括?用兽性来指斥,恐怕是一种过于便捷的解释。
(三)
书中提到的《骆驼祥子》的修改情况,以前不曾注意。如提及最初对《骆驼祥子》的修改,是1945年纽约出版英译本时,译者删改了有关祥子堕落的章节,杜撰出了个大团圆结局。而老舍在1955年自行修改的时候,则将结尾部分直接删去了一章多,内容也是祥子堕落的部分。而最初老舍谈及这部小说时曾说过,须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地刹住,囿于报刊连载的需求,才不得不匆匆结尾。增的初衷和删的结果,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
在文章中,李辉将老舍与茅盾、巴金、沈从文后期的创作道路做了个简单的比较,认为"成功地完成了一种调和,一种平衡 ,于调和与平衡中保持了文学生命的延续",他将这种情形,归因于老舍的文学创作乃是源于对老北京的魂和根的贴近和挖掘,以及老舍所浸淫的北京文化的调和性质。
据说,老舍离家而去的时候,携带了两样东西,一副手杖,和一篇亲笔抄写的《咏梅》——毛泽东的那首著名的卜算子。
(20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