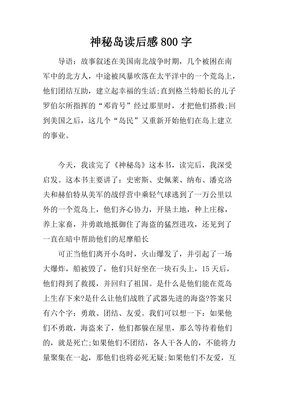《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读后感1000字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是一本由孙丹年著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58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1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精选点评:
●中美合作所为抗战立下的功勋都被隐藏了
●全书都在引用梅乐斯,也不知作者除了看这本书,还干了什么……
●还中美合作所抗战之本来面目。#20121104
●想法是好的,枯燥。
●给五星的都是矫枉过正, 和某帮伙的作派如出一辙。
●秒杀中流砥柱的游击战
●那段时间喜欢看战争
●作者可能读了一些历史档案,但似乎缺乏相关专业背景,全书组织不是很合理,主题不明确,史料考证不到位。书中几次提到战略情报局表述不尽一致,人名译法也不十分规范。有空还是要找原版资料看看。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读后感(一):为中美合作所说句公道话——读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
中美合作所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批准建立的情报合作机构,中美两国情报精英紧密合作,奋斗在一条隐蔽战线上。这本书是目前国内能找到的给中美合作所以客观公正评价的历史书。
那是中美两国一段亲密无间的岁月,就历史地位而言,中美合作所的地位应该和陈纳德的飞虎队,史迪威领导的中国远征军一样,在秘密战线上协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且很多无名英雄的牺牲都隐蔽在历史的深处。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非常感慨的,特别是上了歌乐山,看了中美合作所的旧址,梅乐斯住过的,如今空荡荡的,搞得不伦不类的书画展的梅园,总觉得很遗憾,像对司徒雷登一样,很多于中国有贡献的人都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没有给出公正的评价,读这本书算是一种对历史真实的了解和补充。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读后感(二):廓清一段被误会的历史
事实上,中美合作所是一家技术单位,负责情报搜集,成立于1943年4月,后因抗战胜利,1946年1月即宣布解散,同年10月,所有美方人员均已撤回。可以说,它对后来的解放战争没有造成值得一提的影响,也没有参与到对革命者的屠杀暴行中。
在抗战初期,美国基本持观望态度,一方面,美国人认为日本对自己没有威胁,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中国能抵抗很长时间。甚至蒋介石也对美国不抱幻想,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说服苏联人上面。
然而,偷袭珍珠港改变了“二战”格局,美国太平洋舰队遭遇了沉重打击,实力已不如日军,西海岸面临着空前的威胁,直到此时,美国人才看到,4年多来,无数中国人毁家纾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不肯屈服。中美不仅在利益上找到了交集,在道义上也找到了共同立场。
首先,美国人更重视欧洲战场,将亚洲战场看成是辅助性的、次要的,由于投入不足,限制了中美合作所发挥更大的作用,尤为麻烦的是,它卷入了军方内部的派系斗争中,梅乐斯小动作不断,和陈纳德联手,想扳倒武断的史迪威,结果自己被先干掉,这使中美合作所被边缘化。
其次,中美合作并不愉快,充满了摩擦与误会,其中许多情报甚至对中国人保密,这让蒋介石大感屈辱,所以国民党方面对美方在战争中的支持往往大而化之,笼统用感谢加以模糊处理,不愿意讨论细节,也不愿说明具体有什么贡献。
第三,中美合作所建立前,原办公地址白公馆本是监狱,后监狱搬到渣滓洞,中美合作所解散后,白公馆又与渣滓洞合并,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历史沿革关系,误以为中美合作所也参与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纠正误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这是追寻历史正义的必经之路,本书在此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值得尊重。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读后感(三):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王 川 平)
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王 川 平)
几年前,一些被扭曲的历史信息呈爆炸状态流行时,我对孙丹年女士说:会有一位勇于澄清历史的人在应该的历史时刻出现。当她把这本《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交到我手中时,那份惊喜可想而知。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作为中美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它到底干了些什么,它与后来发生血案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又是如何发生关系、产生如此巨大误解的,本书渐次展开论述,铺陈众多历史资料,从雾里海里把读者带回到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地方。作为读者,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智气,此二气合在一起,就叫实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学术良知。有良知多好啊!
时至今日,与美国的情报合作问题,仍令巴基斯坦等国受困,清理一下20世纪40年代中美合作所短短四年的情报合作,或许还有更大的价值吧。我是这样以为的。不信,试试。
2011年5月
王川平,中国作协会员、重庆作协副主席、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党委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读后感(四):孙丹年的自我救赎(赵 晓 铃)
孙丹年的自我救赎(赵 晓 铃)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那一片山麓下有一座人间魔窟。
那里没有阳光和花朵,只有满山荆棘,遍地虎狼。
那片山麓叫歌乐山,我们重庆长大的人很少想到那山原来的名字意味着快乐与歌唱。心里都有魔窟的浓浓的阴影,阴影下有清晰的“USA”的字样。
我们从记事起就被组织到那里参观,看阴森森的刑讯室,看沉重的铁镣手铐、带血的皮鞭和老虎凳、看灌进鼻腔的辣椒水,看钉进手指的竹签……回到学校还要开会谈感想,在课堂上还要写作文。
我们小小的心田就种下了仇恨,对于我来说,还有恐惧。
仇恨的对象不仅有国民党,还有美国人,我们亲眼看到,曾铐住烈士手腕的手铐上有“USA”字样。
与这片山麓有关的小说、电影、歌剧,写得真是好,演员也演得真是好。我特别喜欢那部具中西方音乐特色的歌剧的音乐。那些歌曲流行全国之前,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同学、江姐的儿子彭云拿到了歌单,得到了唱片,在学校里播放,在每一个班里教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诵读、歌唱,一次又一次地激动,流泪。仇恨和恐惧便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刻在我们的骨头里了。这样的血液铸造着我们的思想性格、气质教养、行为模式,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选择。
以后我做了老师,便复制自己受过的教育,领着学生去到那山下,把仇恨和恐惧的种子种进他们的心灵。回到学校,也指导学生写下仇恨的作文。
现在孙丹年写了一本书——《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说那座山下曾经有的那个机构是中国与美国合作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机关。虽说早些年我们已知道,杀人魔窟渣滓洞白公馆和中美合作所没有关系,与中国人杀害中国人的那些残酷和惨痛没有关系;但是,早年的教育毕竟进入了骨里血里。读了孙丹年的书才能比较彻底地知道,那个几乎影响我一生的传说不但是片面的,甚至是荒谬的。她的材料那样详尽,无可辩驳,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中美合作所对太平洋海战的巨大贡献,而是她讲述了梅乐斯和他带领的美国大兵在中国英勇卓绝的斗争和牺牲,他们的光荣与功勋一点不比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些战友差。而那个在我们的历史教育里臭名昭著的军统头子戴笠,也功不可没!
梅乐斯善于与中国人合作,在来华参加抗战的美国将军中,他最少对中国人的岐视。最令我惊讶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游击部队。
我们看过了那么多电影电视,从来没有看到过江南的敌后游击队由操着英语的美国小伙子带领着,拿着美式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只记得沙奶奶在《沙家浜》里骂“忠义救国军”是“不救中国救东洋,忠在哪里义在何方”!谁知那时候,竟有上千美国人活跃在江南的敌后游击战场!
梅乐斯和戴笠也去到那里,他们挨过日本人轰炸,还差点被汉奸暗杀。梅乐斯为保护中国翻译官受过伤,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极度的紧张劳累中,他病得很严重,同时,这个单纯的美国人还要对付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尽管他后来被美国人误会,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误会了很多很多年,以至于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梅乐斯的贡献。但是他在晚年仍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他说:
不能使用共通的语言,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在文化背景,在军事传统,在政治演变等各方面都有这样大的差别,而居然能够顺利草拟出一个有关联合情报机构的设置方案……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都具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亟待完成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打垮日本鬼子!
相信这本书会让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读者心绪难平。
因为我们是非常奇特的一代,我们对灾难与屈辱熟视无睹,见惯不惊,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是“母亲打孩子”,是误会,是大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光荣的代价。
仇恨让我们充满戾气,我们会把一点点错误或是差异上升为矛盾和冲突,为了“政治的正确”,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传承了千百年的优秀文明。“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们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对于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特别不了解。
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在能够思考的时代,我们的一生已过去了多半。
但是有一些人固执地要思考,要寻找真相。
孙丹年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
孙丹年的父亲孙铭勋是一位早年就追随革命,也追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家,在50年代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他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是错误。因此孙先生不但自己吃尽了苦头,也让妻子和女儿吃了苦头。
孙丹年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回到内地后就在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工作让她充满激情而又珍惜。然而,当她发现自已竞竞业业一字字写出的宣传材料并不真实时,她非常痛苦。为了生计,她不敢贸然放弃这份工作,但她终究是她父亲的固执的女儿,她最不可能放弃的是诚实。她做到副馆长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就要赶上评职称了,她说,高级职称,不评也罢。
歌乐山下的故事却选择了孙丹年。她不仅是不再撒谎,而且要寻找真相。
我和她是因为文学交往的,我读过她的小说,以我的专业眼光看,她的语言,她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对细节的捕捉,真的很有才华。
我问过她,怎么不写小说了?
她说:没有动力。
她别无选择地走向了历史。
孙丹年命中注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写这本书是她最好的自我救赎。
孙丹年认为,中美合作所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这或许不是一本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著作,但我知道,这是一本可靠可读的书。
这本书对于我的同代人来说,是珍贵的,对于受过与我相似的历史教育的上一代与下一代来说,是必须要读的。因为我们与孙丹年一样,需要再教育,需要一个自我的救赎。
2011-6-11
赵晓玲,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重庆 《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 作品主要有长篇儿童小说《独生女》、散文集《宋词有魂》、历史纪实《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卢作孚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