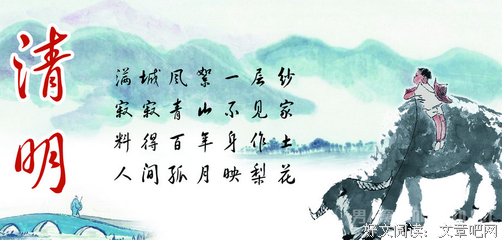《A Translucent Mirror》读后感100字
《A Translucent Mirror》是一本由Pamela Kyle Crossley著作,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33.95,页数:4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A Translucent Mirror》精选点评:
●might be a "landmark" in terms of her perspective and concentrations, but not in terms of a good contribution on methods and argument. A smart and accurate capture of many things, though, the power rarely lies in her expla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vidences. it is a fruit out of the breakthrough of literary theories, i would say.
●对于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三个时期满清统治的意识形态根据实际政治需求发生变化的考察。集中于针对“汉军八旗”的身份/历史的修改操作、皇帝针对不同统治地区(满、蒙、汉、藏)打造自己的不同形象等问题;认为乾隆时期帝国统治造成的满/蒙/汉身份区分稳定化为清末的汉族民族主义兴起埋下种子
●All talks abou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 pre-nationalism regime seem to be pretty vague. If, Crossley is correct in her arguments.
●非常难读,一不小心就理解错了意思,但写得很好,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诸多专门知识如此了解,实在太不容易了。装作自己读过吧
●清帝国意识形态研究。作者认为清帝国前期和后期(以乾隆朝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有一重大转折,清前期并不存在明晰的满汉区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满人”、“蒙古”等概念实际上是乾隆时期帝国建构的产物。问题意识应该算是站在魏斐德的延长线上?即女真怎样树立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外加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套
●新清史四书最理论的一本,其实就是套理论套的最多的(尽管柯娇燕不肯坦承自己和安德森的关系),也难怪被钟喷的那么起劲……
●O, poststructuralism! Identity is forever changing.
●No comment. A transparent mirror wanted....
●introduction,第四章
●四星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这种解构的approach...
《A Translucent Mirror》读后感(一):not so "translucent" for reading
omewhere between emperorship and ethnicity(identity) falls A Translucent Mirror. Running through Nurgaci, Huang Taiji and Qianlong, it explores the ideology of universal emperorship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he Manchu rule, together with its relation to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The Nurgaci rule is characterized by a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which defies a description with “loyalism.” Huang Taichi’s rule saw a transition from Khanship to empire, which process was finalized in the Qianlong reign. The postscript touches 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relating it to the previous issues of ethnicity.
The author chooses to use highly metaphorical and thus murky languages in both the chapter titles and the main text. For example, putting together the chapter titles, one finds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orm a general idea of the book’s discussion. Such difficulty remains in the reading of the main text. The author jumps from ideas, linking them together imprecisely, all of which forbid a quick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The introduction presents a theoretical background woven together with Hume, Said, Derrida etc., but readers might still ask how this background and the main chapters support each other. I believe I need to read it in more details to appreciate its values.
《A Translucent Mirror》读后感(二):导言第二部分译文
意识形态、统治权和历史 清皇权接收信息,予之联想形式(associative forms),再将其送返。没有代理机构从头开始表演这套艺术。理想情况下或许能把理念转换和散播的每个时刻孤立起来,但既然这不可能,读者必须记住,清统治的各个时期在这方面从来不是静止的,视作一个整体的清时代同样如此。朝廷不断对历史知识再加工的劲头只能由暗示得知。整体中的接收和发送动作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下面将探讨这个问题。此中之所发现必然只是一个旁证,因为宣布了它的在场和意图的意识形态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了。其主题不可见闻,不能被计算,也不能以任何满意的方式被核验,只能从语言、典礼、政治结构和教育程序的形塑中推断。我曾尖锐地怀疑过进入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但我相信,证据优势确认了清中后期系谱化的历史习惯用语可连接到18世纪皇权的普世化。现有理论坚信“历史”不外乎它的资料,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坚持——历史研究只能是意识形态研究的扩展。那些资料被制造,被赋予它们的概念轮廓,并成为进一步编制文档的基质,但这个过程常常留于抽象之中。[12] 这个研究可以弃绝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上的长久沉思,因为在帝国意识形态的例子里,那种关系非常清晰。 尽管还留了一点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考量要说,我想首先描述历史制作的创始人:统治者。统治者作为一个人很重要(有些情况下,比乍一想所认定的还要重要),但这里“统治权/位”(rulership)包括扩展统治者执政人格的全部工具——精神的、仪式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13] 统治权,就像我在别的地方写的,被看成执政程序中扮演(被归结为)动态角色的全套工具。精心谱写的曲子不止有统治者本人,还有他的血统圈;他的表演仪式;安排其教育、健康、性活动、衣物、财产和日常起居的官职;以情报搜集和奏议派送形式充作其听觉之延展的秘书;生成军事命令、民事布告,为重印或新委任的文学作品写帝国序文时充作其讲话之延展的编辑。我将涉及“朝廷”这一套班子最内部的行列,这是大多清史著者使用这个术语时所意谓的。[14] 将统治权视如这些谱曲的部分,它们协和与不协和的可能性都可以草拟出来。至于清帝国,统治权/位当然就是皇权/位:分部辖域之上的治理机制。[15] 清皇权在表达上就是我所说的“simultaneous”(漢语“合璧”,满语kamcime)。[16] 即,它的布告、日志,纪念碑有意设计成多种语言的帝国言辞(至少是满语、漢语;通常有满语、漢语、蒙古语;18世纪中叶以后频繁使用满语、漢语、蒙语、藏语,以及常称作“维吾尔”的中亚穆斯林用的阿拉伯字),作为多元文化框架中帝国意图的合璧表达。合璧不仅仅是实用的事。每门正式书写的语言代表一种独特的美感和族群代码。皇帝用每门语言宣称,既作为发声者又是那些感性和代码的对象。各自分开的文法,到头来拥有同样的意思——皇权之公义。或者,用18世纪常见诸皇权的车轮隐喻来说,辐辏于毂(the separate spokes must lead to a single hub)。一个美学的和族群的向量如果引离那个毂/中心,无异于导向革命的字面的和隐喻的载体。 清皇权的合璧,与很多更早的帝国所用的表达时尚类似,至少可追溯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但最有名的还是蒙古大汗。[18] 我不是说早期现代之前的陆地帝国是清帝国的前任,或者可与之互换。相反,清的运作在我看来是意味深长的早期现代——排除了早先政治权威的世俗神圣二分法,建立起文化之上的超越(transcendence),为新的普世主义奠基。清对更早的帝国的建构,特别是唐(618-907)、金(1121-1234)、元(1272-1368),成为17、18世纪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当然,合璧表达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在上古就有可能了,纵然使用的语境产生了与更早时期截然不同的效果,清也是继承、详述并采用如此做法的帝国之一。作为政治和文化机制,帝国合璧似乎精准抓住了“人物角色”(persona)一词,我用以表示此意——话音发出来所透过的面容(visage)。无视清帝的品质,将有误解语境的风险,而清史料就在那个语境中形成。 对清皇权表达模式有瑕疵的刻画,远不如这种假设有害——“种族”或“族群”状态可解释早期现代的变化。早先学者的这种想法仍在鼓励将清代政治文化解析成或更“中国”或更“满洲”的尝试。[19] 其中Franz Michael更具影响力,他在《满洲在中国统治的起源》一书中想击败认为满洲统治确定是“外来”的观点,这一观点经Karl Wittfogel[21]变得时兴起来。在Michael那一代(源自中国早期民族主义的时代)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清被看成“漢化”政权,其中和差异性有关的事务,无论清朝前期还是后期,往往被当作“好做作、妖艳贱货”而不予考虑。直到最近“漢化”概念才被中国史学家认为是有问题的,虽然我在别处[22]争论过这个概念缺少明确性,搅混了原因和结果,且抑制了对一系列已认可观念的疑问,比如为什么中国语言、习俗和社会结构扩散到了东亚各地,又是如何扩散的。“同化”和“涵化”不是向中国史学家否认的词语或概念。倘真如此,“漢化”再无别的目的,除了作为放置一组意识形态强加要求(ideological impositions)的容器,要求将同化和涵化描述为具有关系到(不知为何是特殊的)中国的原因和意义。作为在中国的心智史研究中的理念,“漢化”仍然有趣且重要;作为当代话语中的定理,它只代表了一团纠纷,属于为东亚的文化变迁做出的不可阐明而富于情感的解释。本书在雍正帝《大义觉迷录》(1730)中的转型主义理念上费了一段笔墨,但这里描写的那种转型论并非漢化话语的早期形式。雍正帝及其前任的意识形态关注的是,通过系统暴露于文明实现总体道德转化;相反,“漢化”有时可以由不如采用漢语言那么深远的事实引发。 对汉化假设之同义反复和历史薄弱性的不耐烦,之后导致了偏向“满洲”的解读。[24] 18世纪朝廷的政治一度从被嫁祸的种族效忠和紧张方面得到解译。按同样的脉络,一直都有把中国在鸦片战争(1839-42)中战败归咎于中国社会“种族”矛盾的尝试。[25] “种族的”现象是什么,为其设立一个门槛很重要。[26] 种族差异造成了一些事的发生这个命题,设想了这样的差异在清国家存在之前即已存在。一些群体通过历史区分自己与他人,群体间的敌对频繁发生。依我看,没什么现象是种族的,即便不同群体间体质差异的历史纪录上的议论也不够格。进一步说,体质差异被归因于宗谱附属关系(genealogical affiliations),或者在现时代归因于遗传力的某种机理,仍非种族的。但是,以祖先附属关系为基础,对固定道德文化品质确切的归因,并使个人或群体变得不可同化且不可转化,无疑满足我的“种族的”标准。真的,这么说来种族主义和种族的思考总得是属于未来的理论。不管怎样,本研究中“种族”不过就是社会史、文化史和心智史现象。 声称18世纪清帝国意识形态拥有“种族的”产物时,隐含了一种对比,就像关于“意识形态在清廷行为中呈现”这个命题的对比。此书所用到的“意识形态”只有基础的,也许是单纯的含义。我的指涉物是大卫·休谟对“印象”和“联想”的分水岭讨论。休谟有些讨论源自约翰·洛克,但在我看来休谟关于特定语言的怀疑论是现代意识形态议题讨论的直接祖先。一个有用补充:特拉西把术语“意识形态”指派给休谟定义过的联想进程(并把“感觉能力”指派给“印象”)。后继的学者,从康德到托多罗夫,探索了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人或社会的影响,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运作贡献了许多装饰音和具体的洞见,但都和休谟的基础的话语概念没有太大不同。无疑,休谟对于身份的议论充分覆盖了目前研究的理论场地,承其所是:“……所有关切人身份的美好而微妙的疑问,永远不可能断然已决,它要被视作语法困难而非哲学困难。”身份取决于诸理念的关系;这些关系以其所造成的那个简单过渡,产生了身份。经由帝国中央集权过程施加历史身份的早期现代现象,拥有一名早期现代作者为其持久的分析人。当然休谟的“身份”本质上是分殊问题,而不像很多关于身份的现代讨论所认为的,是与社会文化结构相关的任何自我定位。
《A Translucent Mirror》读后感(三):【转】葛以嘉:评柯娇燕《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
2001年第4期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张慧文 译
--------------------------------------------------------------------------------
柯娇燕柯娇燕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洞见深刻,标志着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巅峰。与美国历史学家Mark Elliott、Peter Perdue等人的出色合作,使柯娇燕将我们对于清帝国早期现代民族身份之形成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既包涵复杂性,又有理论清晰度。著者不仅就民族身份与帝国权威在清代的变动性“接合”(articulations)做出错综、详尽的阐述,还将清帝国与俄罗斯、奥德曼土耳其等其他庞大的早期现代帝国并置,试图建立起一种比较视角。如果说许多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工作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是清帝国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柯娇燕就在证明若想理解国家权力与民族形成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回答“可汗是怎样变成清帝的?”
除去《引言》和《后记》,本书共分三章,大致对应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的统治。然而这些章节不止是对三位统治者政治风格的描述;更确切地说,每一章都致力于阐明一种独特的统治范例(paradigm of rule)。这些范例并非取决于某位皇帝的个人品格,而是取决于整个国家作为结构实体的建筑需要——著者一再提醒我们:不同于个人,国家宣传和操纵种种观念却“不相信”它们(p.225)。官方意识形态的范例变化迫使满族统治者频频更新和修正皇朝历史的自我书写,柯娇燕的论著由此在本质上成为从历史编纂角度切入的清代文本分析:从皇太极、康熙对爱新觉罗氏起源神话的苦心经营,到清帝国对明遗民、清“贰臣”以及煽动反叛者(如曾静)或激或温的道德评判。
首章探讨的是努尔哈赤上台时辽东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形态。著者的目的之一是要超越那种认为17世纪辽东、吉林的身份是处于汉、满两种文化“夹缝间”的观点。她证明这种描述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将18世纪的类属(categories)投影为17世纪早期的现实。作为例证,著者向我们介绍了围绕童[佟]姓——一个来自抚顺的汉世系,在17世纪清廷占据了诸多职位——的民族身份与忠诚的论争。童家并非每个人都投向清一边;明官员童步年(音,Tong Bunian)在被当朝以煽动罪下狱并于1624年勒令自杀期间就始终辩称自己坚贞不渝,属于一个清白无玷的汉人传统。但仅仅60年后,也即康熙治下的1688年,童姓却在民族上被正式指认为满人并在军制上被吸纳入满旗;这一趋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与之伴随的是汉武装[汉军八旗](Chinese-martial)作为一个行政范畴的彻底解体。
从努尔哈赤可汗到乾隆皇帝,关于民族身份的政治纲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能解释像童家这样的急剧转向?由于著者描述的过程十分复杂且充满层层的修正、重述,我将砍削书中的观点以便概括它们。在第二章,柯娇燕主要讨论的是皇太极对官僚政治组织(bureaucratic apparati)的运用和扩充。这是一种努尔哈赤从总体上鄙视的毫无个性的政治控制机构;它们中的多数关乎识字、教育与历史书写(所以皇太极谥号“文皇帝”),皇太极借此重塑了大众与历史人物的身份:追封努尔哈赤可汗为“皇帝”;变称“金”朝为“清”;将“满”创型为一个先前只存在世系联盟的民族部落。这一描述和控制过程在第三章随乾隆皇帝的登场达到顶点:他扮演了一个大一统主宰的角色,超越了一切文化的界限。这种超越能力源自乾隆同时运用各族文化方式(cultural idioms)说话办事的才干,反过来这种统治模式又要求治下的各族文化(满、蒙古、汉、藏)相对独立。雍正声称曾是蛮夷的满族在经历了汲取儒文化的进程后可以当之无愧地一统“天下”;乾隆却拒绝用这种抬高儒家的策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对他而言,皇帝更是“变革者而非被变革者”(p.246)。这种观念引出一项巨大的改造工程并为乾隆赢得声誉:重组各种文字、图像材料,全面修正清朝的历史书写,以支配者视点汇编治下各民族的文化产品。著者在论及乾隆的上述自我建构——作为一个大一统主宰与“推动者帝王”[转轮王](wheel turning king)而超越并整合个别文化——时表现出动人的才华与说服力。尽管该书有许多基本观点可以在她此前的文章中找见,但在这里,著者还是向我们揭示出某种无法解决的“纠缠”,它发生在统治者身份的范型与民族划分和忠诚的观念,以及历史书写、神话营建和领土管理的制度之间。
由于将分析对准清代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顶点,柯娇燕必然要首先考察官方正统的文本材料。这样做的问题还不在于著者的视像会出现偏差,因为她非常清楚这些资料所潜含的“失真”陷阱;而在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著者可以用这些文本对清朝统治范例“怎样”变化作出有效阐释,但那些隐身变化后的历史动机、那些“为什么”却依然暧昧不明。有时柯娇燕给出一些简短而很难落实的暗示:存在某种可能发生作用的历史强力(historicalforces)——比如,在谈到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行政范例变化时,著者指出努尔哈赤征服辽东并统领空前庞大的人口的事实,使他无法再简单地强迫臣民迁居或对他们任意处置,而不得不采用更为官僚化的手段在他政治生涯的晚年实行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从“可汗”向“皇帝”的过渡。又比如,在第三章论及乾隆的意识形态与康熙、雍正的基本区别时,著者指出这些区别的起因缘于后两位的主要任务是“征服”而乾隆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但是,对于诸如此类的大量“文本外”(extra-textual)强力,柯娇燕也只走到了“暗示”这一步而已。
照亮本书的学术努力,特别是那种将清代的民族与帝国关系理论化的学术取向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劳动还引出如下问题:这部论著存在哪些薄弱点?是企图转变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的当下概念的目标?还是着重显示民族身份的建构与操控并非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明而是在早期现代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就已生根的意向?新近的清史研究已将这两方面都完成得很好;可一旦触及对“太平天国”后“汉民族主义”(Han nationalism)吁求的理解或对“汉民族主义”动因和范例的追溯,它们就往往走过了头——柯娇燕的《后记》即是一例。尽管在章炳麟与乾隆关于民族划分的范例间可能发现某种联系,也可能在很多方面发现梁启超与雍正的相通,这些汉民族主义者(Chinese nationalists)的历史语境仍大量充斥着其他发挥作用的文本强力与政治强力,以至于柯娇燕看起来仿佛是将激活未来的力量归结为历史之镜中的暗影。与此相似,著者所谓中华民国继承了乾隆的文本趣味(penchant for textuality)——只承认那些有手记(written scripts)的非汉族群体为独立民族的观点也高抬了清政府:它虽然创造和强征了各种手记,这些创造和强征却是在它并未控制的、特定的地域及文化语境中完成的。乾隆治下的鼎盛清朝曾一度被认为是相当儒化或汉化的国家,柯娇燕以她的学识出色地粉碎了这一神话;尽管如此,对于20世纪各民族紧张关系的体察还是要求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转换思路,将研究焦点从国家的意识形态迁移到更为切近的历史事件。
《A Translucent Mirror》读后感(四):前言部分译文
按:这不是我翻译的,我从国学数典上搬运过来的。
本书前言:
曾有一度,现代“民族”、“族群”身份的源头,看似存在于许多世纪以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在过去百余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式微、乃至印刷与数字传媒出现而得以重新提炼的共同体、团结和公益等观念中。尤其当我们考察19、20世纪之时——在这两个世纪,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说,许多人民确实将自身想象作共同体——这一表象多少总是真实的。上述解释,由于可以而且已经被施加于各式各样的民族历史,因而具有一种动人的灵活性。然而,无论这一范式在描述诸种公有社会观念(communitarian concepts)如何被宣传作民族身份这类过程上怎么有效,它仍然未能抓住任何特定民族叙事的实质。拼凑补缀出这类身份的种种文化片断有着迥然不同的起源,它们本身从理论上讲不是中立的或可互换的。有鉴于此,历史学家就想弄清近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所曾利用的种种偶像,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早先时代权威的延续。对某些现今存在的民族来说,那些“早先时代”是由征服性帝国当政的世纪,其统治曾需要建构既因应杂多(multiple)、同时表达合法性符码的从属关系范畴。清帝国(1636-1912)就有一个如此运作的统治,作为其历史后果则是一份历史身份遗产,这份遗产不但对19世纪出现的民族、族群观念的具体特点而且对有关身份的基本观念,都发挥了显著的影响。有清一代,关于统治者的想法、关于被统治者的想法一直在交替变化。17世纪有关努尔哈赤(Nurgaci,1616-26年间在位)[1]与其辖下民众关系的表达,根本不同于对第一位清帝皇太极(Hung Taiji,1627-35,1636-43在位)臣属的观念。进入18世纪,尤其是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1736-95),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完成了又一轮转变。当征服机器停歇下来并接着植入民事管理的支柱,这种意识形态关系不但获得了新的复杂性,而且在教化野心勃勃的官员和不在政府彀中的文士方面取得了新的立足点。作为初步介绍,上述变化的实质或许可以粗略概括为如下范式:努尔哈赤所创大汗统治下的某种主奴关系的象征符码(这些术语经若干考虑和解释后,将用在本书第二、三章中),被修订为17世纪下半叶清帝统治下某种高度分化的文化、道德身份体系。进入18世纪,帝国统治要对境内各色人群均有体现的重担,成为对普世化统治的历史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建筑的、个人的等各类表征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对无远弗届的统治愈益抽象的朝廷表达要求对其宇内进行划界,关于身份的标准由此必然就会嵌入这种意识形态。对仅有一般兴趣的读者而言,上述说法看似不证自明。但对专家而言,它则可能是疏阔而成问题的。随之而来的事情对每位钻研清史及其涵盖的诸多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是见仁见智的:人人都试图在某关键之处偏离通常的叙述。不过,在清史领域中,若干基本要点仍得到一致接受。帝国被认为是17世纪早期由满人建立、控制或打上特定政治与文化烙印的。在“满人”这一名称得到制度化确立之前,清的前朝金(通常称作后金)的主体人口是“女真人”,从800年到1636年间的大半时期,“女真人”这一名称屡屡见之于汉文中。女真人1635年正式变为满人。除了女真人/满人之外,清廷还征调了一些蒙古人,并在1644年攻下明都北京,征服了中国。在此之前,清还将许多汉人以“汉军旗人”身份编入清的军事组织八旗中。八旗领导了1644年对北京的袭击,并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巩固了清对中原和华南的控制。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的清统治者,其中尤其是睿智长寿的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重造了朝廷,使其与悠久的中国价值和谐一致,由此赋予它单独通过征服不可能获得的稳定性与合法性。18世纪,清达到它政治控制、经济权力、军事扩张的顶峰——这一时期,它在政治上控制了满洲、蒙古、中国属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estan)、西藏和中国*等广大地区、以及那些在廷觐体系(有时也称“朝贡体系”)中承认清的优势地位的国家;经济上,由于茶叶、瓷器、丝绸和其他物品的出口,清将欧洲锁定在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军事上,在镇压国内怀有异心的群体(不管是由“族群”还是由社会界定的)的同时,还在对东南亚作战。这一黄金时期以乾隆帝这位最“儒化”、最“著名”或可说是最伟大的清帝的统治为集中体现。在他1796年退位、1799年辞世之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它在先是欧美、后是日本的扩张、殖民和帝国主义行径下变得脆弱起来。本书偏离对清的起源和征服的这种惯常理解的最显著之处在于:“满人”、“蒙古人”和“中国人”(汉人)这类铁板一块的身份不被看作是新兴秩序的基础、来源或建筑砖石。在我看来,这些身份是1800年之前帝国集权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性产物。日益成长的帝国机构要对多种地方性统治意识形态进行抽象、删除或合并,这助长了对我们这里称为“构成成分”但惯常被具体化为“人群”,“族群”并一度叫做“种族”的那种东西在帝国出版、建筑、仪式和人之表征(personal representation)中的建构和传播。如果这些身份的先在性被转移为某种动机,那么通常叙事中的其他方面也就必须受到重新审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康熙一朝的特征(这种特征被表述为力图呈现出某种“汉化”或“儒家”面孔以克服汉人精英对满人统治者的反感)与乾隆时期的伟大上(这种伟大被充分理解作处于“中国”文化或某种中国式“世界秩序”的势力或影响的顶点)。与对清帝国各色人群通常的处理形成对照,本书指出当这些历史性身份被人们当作古已有之时,它们产生的过程恰恰是含混不清的。
自1983年以来,我对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帝王统治(即无涉文化)之于身份的理想化编纂的关系发表了若干一般性看法。[2]仍然有待尝试的是,对有关征服、帝国构想和树立身份标准三者同步进行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原因,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大致过程在研究18世纪中国的著作中多有表现(比如P.E Will的《中国十八世纪的官僚体系与饥荒》,孔飞力的《窃魂者》,另外还有许多著作)——这些著作认为政府精英对那些相对国家影响或管辖的大伞来说位置暧昧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现象很不耐烦。不过,我还逐渐意识到清帝国叙事下的次属情节在别的近代早期帝国那里有着类似物,这提醒我们注意19、20世纪人们认定的许多新鲜事物,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欧亚各帝国意识形态遗产的映像或亡灵。
不过,对与近代早期连续性的强调,不应被理解为笼统主张中世纪或古代的遥远现象是清早期帝国表达的源头。虽然我们将会注意到帝国辞令或仪式中的许多要素有其在时空上远离清代的前身,但这不应在任何意义上被看作是在解释这些要素在本研究所处理的历史时期的用途、潜能或意义。[3]同样,这里的讨论虽然经常注意到与其他近代早期帝国的类似之处,但本书无意成为一部比较性著作,也不企图对类似现象进行系统观察与解释。最后,我认为我的论断严格局限于清帝国意识形态(通过某些媒介所显现的)及其与身份观念的关系,而没有重新解释清史所有方面的意图。“身份”一词本身模糊不清,因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身份,有的与民族有关,有的与宗教有关,有的与性别有关,有的与阶级有关,不一而足。虽然对现代观察者来说这些身份或许像是彼此分离的现象,但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它们代表了彼此分离的历史过程(后一观点在18世纪纪录向清纳贡的各色人等的簿册中有充分体现,内中男女装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表现作身份识别的显著标志)。[4]另外,这些身份类别中的任何一种都不适合17、18世纪清帝国语境下的“身份”:首先,我们处理的身份是“民族”或“族群”身份的前身,它们自身并非显然就是民族的或族群的;[5]其次,如研究其他身份的史家曾经多次评论的那样,帝国时期行将结束之时,在公共话语中民族和族群形式的身份堵塞了人们所能假设的任何别的一类身份。有点反讽意味的是:本书其实围绕着那些它必定要质疑其真实性的身份范畴组织起来;历史论断除了以当前假设为起始并回溯式地讲述每一历程外别无选择。
还应注意别的局限。本书并没有对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的帝治(或统治)、对社会或更一般地说对清史做出多少论述。对要涵盖1800年前清统治期间的哪些时段必须进行的选择,加剧了我所面临的困难。本书对前人已经颇有论述的康熙(1661-1722)、雍正(1723-35)两朝处理简略,以便给之前之后的时代留出篇幅。[6]我在《孤儿战士》(Orphan Warriors)一书中已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身份形成的某些社会机制及意识形态机制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多做重复以便审视它们的源头。对许多主题的处理和对某些个人的叙述,也拆散在两章或多章中。这对本书内容要锚定在统治与身份这两极来说是必要的。我试图使得二者能在章节结构中相互辉映,因而某些叙述顺序是因整体论证的需要而安排的。我希望上述说明有助于澄清这种选择可能导致的任何混乱。读者也会发现本书对清代某些中心主题——比如八旗与驻防部队、[7]“朝贡体系”、[8]蒙古诸部的管理、[9]生活在清疆域内的许多穆斯林人群的历史、[10]东南部的各色人群[11]等等——做了删除或者不同常规的处理。幸运的是,因为别的著作对这些主题做过研究,我便有可能仅在它们触及我的主题时对之加以处理。
--------------------------------------------------------------------------------
[1] 这个名字经常写作Nurhaci或Nurhachi。Nurgaci和Hung Taiji这两个名字在满文文献中极为少见;但在同时代的汉文或韩文记载中却经常见到。这两个名字在17世纪早期非常知名,但出于礼节(如果礼节也包括精神方面的考虑在内)原因在帝国文档中没有记录。以满文书写的这两个名字,仅出现于“老”满文中——1632年改革后的满文对老满文不做区分的某些辅音与元音进行了区分,这意味着努尔哈赤这个名字还可能拼作“Nurgachi”、“Nurghachi”、“Nurhachi”或“Nur’achi”。虽然上述不同拼写在我看来都有道理,但我还是遵照约定俗成的拼法(Nurgaci)。在Hung Taiji一例中,在遵循汉语拼音方面同样有个选择问题,如此Hong Taiji 、Hongtaiji两种拼法都有道理。只是Huang Taiji的拼法,因是基于对该名的错误中文理解,却是不对的。
* 这里的“中国”当指曾为明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后文对中国的用法大多同此——以星号*标示的为译注,后文同。
[2] 见柯娇燕(Crossley),《两个世界中的佟家》(“The Tong in Two Worlds”);氏著,《<满洲源流考>与满族遗产的形成》(“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氏著,《清肇基神话概述》(“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Foundation Myth”);氏著,《孤儿战士》(Orphan Warriors);氏著,《中国的诸种统治:一篇评论》(“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 Review Article”);氏著,《满族人》(The Manchus,112-30)。
[3] 涉及“皇帝(emperor)”一词,这一点尤当受到注意。对该词的最早使用(imperator)——拥有绝对世俗权威及独一无二的超自然认可的某人——很可能见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27BC-14AD)。但这里在充分的相似与连续基础上援引该词并不是要说罗马皇帝是欧亚大陆东部帝治的源头,也不是要说无论罗马或中国建制的独特之处都是无关紧要的。
*奥古斯都(63BC-14AD),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凯撒的继承人,在位时扩充版图,改革政治,奖励文化艺术;原名“屋大维”,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的称号。
[4] 《皇清制贡图》,见第六章。性化过程与东方化过程间的关系是现代学术上的一个常见问题,早在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中对此就有论述。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更为相关的研究,见Rey Chow著《妇女与中国的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尤其3-33页);Millward, 《一个Uyghur穆斯林》(“A Uyghur Muslim”);冯客(Dikotter),《中国的性、文化与现代性》(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尤其8-13页);以及Dorothy Ko 在《身体作为行头:缠足在17世纪中国不断转变的意义》(“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8,no.4[1997年冬])中对性别与满人“族群特性”之重叠标识的研究。
[5] 我在这里处理的与构成成分建构相关的现象,在我看来并不等同于Dru Gladney在当代语境中称作“过度结构化的身份”的那种东西(虽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它是文化人类学中大量文献的主题,不过还是请见“Relational Alterity”,466-68),而似乎是先于它并激发了它。还可参见柯娇燕《思考近代早期中国的族群性》(“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以及本书后记。
[6] 关于康熙时期,参见史景迁(Spence),《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xi Emperor);氏著《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Kessler,《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K’ang-hi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关于雍正时期,参见Pei Huang《在起作用的专制》(Autocracy at Work)和吴秀良(Silas Wu)《通向权力》(Passage to Power);曾小萍(Zelin)的《地方官的银两》(The Magistrate’s Tael)和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的《君主与大臣》(Monarchs and Ministers)是研究雍正、乾隆两朝帝国行政的经典著作。另外,还有许多专门研究18世纪早期清廷决策的优秀作品。
[7] 现代研究的奠基之作是孟森的《八旗制度考》(1936),Ch’en Wen-shih、Okada Hidehiro、Liu Chia-chu等人对单个某旗或驻防部队做过重要研究。更一般性的研究见Sudo ,“Shincho ni okeru Manshu chubo no toku shusei ni kansuru ichi ko satsu”;Wu Wei-ping,《八旗的发展与衰落》(“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Banners”,宾西法尼亚大学1969年博士论文,成书时更名为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Banner Garrisons in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王钟翰编《满族史研究集》;邓《清代八旗子弟》;柯娇燕《孤儿战士》;以及Mark C. Elliott与Edward J. M. Rhoads即将发表的著作。
[8] Pelliot,“‘Le Sseu-yi-kouan et le Houei-t’ong-kouan’”,费正清(Fairbank)编《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Wills,《辣椒,枪炮与谈判》(Pepper, Guns,and Parleys);柯娇燕,《明清四夷馆角色中的结构与象征》(“Structure and Symbol in the Role of the Ming-Qing Foreign Translation Bureaus”);Chia,《清代早期的理藩院》(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何伟亚(Hevia),《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Howland,《中国文明的边界》(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尤其11-18页);Wills,《从Wang Chih到施琅的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尤其204-10页)
[9] 对蒙古社会史的最好简介是Fletcher的《蒙古人:生态与社会视角》(“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虽然该文关注的几乎只是从Chinggis 到Mongke的帝国时期。至于通史还可参考Morgan的《蒙古人》(The Mongols);Grousset的《草原上的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Jagchid和Hyer的《蒙古的文化与社会》(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有关更加靠后的帝国时期,见Allsen的《蒙古帝国主义》(Mongol Imperialism),Togan的《灵活性与局限》(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s)。有关清代的蒙古史,见Bawden的《蒙古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Bergholz的《草原的分割》(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Chia的《清朝早期的理藩院》,Fletcher的《清的亚洲内陆,c.1800》(“Ch’ing Inner Asia,c.1800”),柯娇燕的《制造蒙古人》(“Making Mongols”)。在中文里面,最清晰且全面的专著可能是赵云田的《清代蒙古政治制度》。
[10] 尤其见Rossabi的《穆斯林与中亚叛乱》(“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Fletcher的《清的亚洲内陆,C.1800》;Lipman的《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Gladney的《回民》(Muslim Chinese,尤其36-63页);Millward的《关外》(Beyond the Pass)。
[11] 有关背景可参见Herman的文章《帝国在西南》(“Empire in the South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