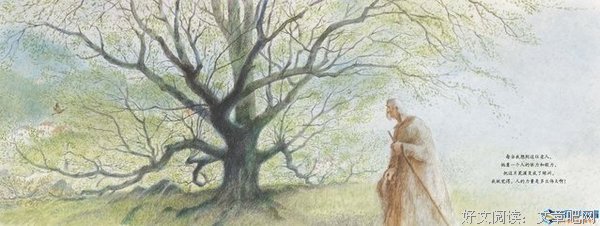叙事读后感100字
《叙事》是一本由毕飞宇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叙事》精选点评:
●叙事对文字的拿捏最细腻 青衣对人物的刻画最到位 雨天的棉花糖对价值的揭示最深刻
●文笔太好。
●叙事不合胃口看不下去,青衣不错,雨天里的棉花糖叙事和语言登峰造极。对于我这种读书持久性极差的人来说,能一次看完一部中篇不容易的,能在三天之内看两次也是不容易的。它的每一个字都足够吸引人。
●收录《叙事》、《青衣》、《雨天的棉花糖》三篇。说来惭愧,毕业一年了才发现自己一篇毕飞宇的小说都没读过,在书店闲逛的时候翻了翻这本书,结果停不下来直接一口气读完。《青衣》写得太好了,久久不能忘怀的是那句“我没有坚持。我就是嫦娥。”
●38叙事 6.我的身体热气腾腾,像刚剥了皮的兔子,在麻大妈的掌心渐次呈现出生命意义 20.人类的宇宙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家园方言,也就是地图上那一块固定色彩.世界就是沿着家乡方言向四周辐射的语言变异. 39.世界是逃不掉的,他永远是老样子,你躲来躲去还是要回到世界里去. 49.她转身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还弄出了不少画外音.她的口红笑起来,眼影部分有了适合于男人进攻的可能性.我开始赞美她的脖子,然后赞美她脖子的上面和下面.
●2015.12.8 /2016.2.17/……人类与历史,人类与宇宙
●妹纸推荐的 叙事是神作,用短句讲故事可以这么有趣。 青衣看着有点压抑。 雨天的棉花糖,看名字以为是美好治愈的,越看越沉重,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后来才反应过来,棉花糖被雨一淋不就塌了吗……原来两个美好的意向放到一起,也可能会变得残败惊悚。
●三个中篇的质量逐级下降,我觉得共同的缺点是炫技的意味太强,和《地球上的王家庄》那样的作品相距太远。
●毕飞宇绝对的文字大师,他的文风即严肃又浪漫,有很高的艺术性。 但我不喜欢他对于夫妻之间的描写。
●叙事的故事太清淡而主题太重,四星。青衣五星,因为纯粹的让人害怕的爱。雨后的棉花糖四星。
《叙事》读后感(一):毕飞宇《叙事》简评
《叙事》无论是在叙述技巧,语言还是思想内容方面都称得上是非常成熟的,在叙事上多重的时空转换和呼应,让故事一下子有了延展的时间维度带来的历史感,抗日战争、文革和当下,贯穿纠结于“我”的思绪里是关于身份与种族、文化与历史、时代与人性、婚姻与爱情、知识与政治等诸多主题的探索和思考,而穿插其中多处历史和神话人物的对话更是涉及宇宙探秘及生存等主题。可以看出毕飞宇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是有雄心的,当然也是成功的,在融入诸多主题的行文中没有生硬和浅泛之感,而是能够引起个人思考的。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篇佳作,而在引导人尝试文学创作方面而言也是一篇典范之作。 《青衣》让人想起很多其他作品,比如《黑天鹅》,以及《霸王别姬》。戏子历来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题材,他对舞台涉及的复杂多维的人性有一定的探索,在京剧艺术方面他没有更多的呈现,而是花了更多的笔墨描摹筱燕秋心理起伏变化,有人称其是“当代中国最会写女人心理”的男作家,可见其共情之深挚,笔力之卓绝。本文可以作为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写作的一个研究文本,探讨个体写作的独特性。 《雨天的棉花糖》写个体和时代尖锐的冲突,柔弱的少年红豆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的性格冲突在整个文革的时代背景下使得少年红豆一度自我怀疑和自我鄙薄,从而成为了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红豆参加越战后,对战争的恐惧则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而最终崩溃走向毁灭。而贯穿始终的悲戚哀婉的二胡曲调贯穿小说始终,既丰满了人物形象也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
《叙事》读后感(二):关于《叙事》
第一次读他的书。由于写不下,只好把本应写在短评里的内容暂且放到这里,算作拉长版的短评吧。
《叙事》
对婚姻、语言、海与陆地等等,解构得相当好。叙事在不同时空之间灵活跳跃,多条线索,试图构建起个人史/国族史并行的叙述,而且完成得不错。我唯一不喜欢的是奶奶那条线,无论是少女还是侵略者都写得如此刻板,一直觉得这种强暴故事特容易写,像是一种媚俗,人物也没有给我任何新的东西。在其他几条线中毕飞宇的机灵劲儿真让人羡慕,可这段历史的沉重恰好没给他抖机灵的机会。不过这篇很能看出他的野心,他的小说里总有鲜辣的讽刺和议论,要写得好非常之难,作者的聪明与自恋只有一线之隔。
《青衣》
佳作,写得平衡多了。猜测是先有筱燕秋,后有故事。依旧是极高的文化身份与老衰、不得已的现实身份的对撞,想起前些日子读的白先勇,戏剧真是极有生命力的主题。
《雨天的棉花糖》
主题很好,直指“战争荣耀”的虚无、战争对人的异化。结构和《叙事》一样交错呈现,人物的性别倒错也非常有魅力,可惜没深入写,这样一比就看出《假面自白》的力度了。与红豆的故事相比“我”的生活写得很是无聊,另,我也感觉到了部分读者看毕飞宇的“不舒服”,有些地方实在太轻佻。
对,看评论有些友邻说出了我的感觉,用力过猛,后面有点收不住了。
总体感觉读起来流畅聪明但余味不足,他是那种喜欢议论也写得好议论的人,感觉他写杂文/评论也该是很好看的。
《叙事》读后感(三):又一本流弊的毕飞宇小说
《叙事》:又是一本流弊的毕飞宇小说。
收录了毕飞宇的三篇小说:《叙事》、《青衣》和《雨天里的棉花糖》。两个多月以前,我在另一本毕飞宇的小说集《林红的假日》里读过了《青衣》,所以这次没再花时间重读,把重点放在了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小说上。
在小说《平原》的序中,我了解到毕飞宇被誉为"写中国女性写得最好的男作家",而如今,大大出我意料的是,毕飞宇小说中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也是顶厉害的,而且风格与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完全不同。
《叙事》:"日本人板本六郎在陆家大院里只做两件事:练习书法,强暴婉怡。他平平常常地这样做。陆家大院平平常常地这样接受。"
《青衣》:"筱燕秋边舞边唱,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丝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了液滴在往下淌。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了雪地上,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
对比以上这两个片段,在描写女性为主的小说《青衣》中,毕飞宇主要是以一种表面优美、内藏深意的笔法,通过别人眼里的液滴来表现筱燕秋身体的创伤,从而侧面渲染出一种凄美的女性之美;而在以男性为主的小说《叙事》中,则是一种赤裸裸的、单刀直入式的风格,直接点出"婉怡经常被强暴,而陆家大院视而不见"的悲惨,体现了一种男性化的简单粗暴之感。
毕飞宇关于男性的描写风格有些类似于余华,都是直接把最残酷的事情毫无遮拦的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给人一种残忍地无法继续阅读的感觉。 而在叙事风格上,《叙事》这篇小说也挺颇有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之感:通过三段时空的相互交错(奶奶婉怡遭日本人强暴、我和林康的爱情故事、正在海上的我的感受),构架一种三线同时进行的观感,有种电影分镜头的感受;而在讲述过程参杂的各种人物的内心旁白,在增加虚诞荒谬感的同时,又有种《百年孤独》开篇时跨越时空的纵深感,这让想到了胡适的一句话"任你一秒行三十万里的无线电,也比不上我心头的区区一念。"
至于第三篇小说《雨天里的棉花糖》,红豆的形象让我想到了那一个烟花般寂寞的男子——张国荣。有趣的事,在张国荣主演的一部电影,《纵横四海》中,女主的名字恰好也正是红豆。 只不过,电影里的女红豆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小说中的男红豆却以自杀为终……
《叙事》读后感(四):叙事:荒诞的梦魇
文学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东西:它不像有形的物质能带给你即时的享用快感,也不同于微妙的人际交往能充分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具备了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气质,蕴含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情绪。经由写作者与出版商,文学逐渐演变成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喜闻乐见的餐桌谈资。在这个由作者、出版者、阅读者建立起来的稳固的三角关系之中,阅读者的作用愈发显得不容忽视。一个挑剔的阅读者往往能够凭借想象力发掘出作者书中的弦外之音。
毕飞宇的小说《叙事》可谓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从语言的纷繁瑰丽到形式的别出新颖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小说以“那场雪从午后开始。”开篇,似乎是在向读者讲述一个老套而冗长的故事。事实上,《叙事》以10页左右的篇幅酝酿了整个故事的开端,即“我”的降生。村子里请来了“接生过的猪比接生过的人还多”的麻大妈亲自为我的母亲接生,结果“我”是寤生,这让全家人大为惶恐。在“我”握紧拳头紧闭双眼嚎啕大哭之后,麻大妈完成了我的“人之初”。渐渐成长起来的“我”养成了爱看地图的习惯,与妻子林康结婚后,夫妇二人也经常抱着地图妄想环游世界。在一次与家中三叔喝酒的过程中,三叔无意间透露了“我”扑朔迷离的身世,引发了一场“我”对于自己身世与家族的艰难寻根。
事实上,这场关于自我身份的寻找是一次“荒诞的梦魇”式的回溯,关于“我奶奶”的故事假定发生在奶奶十七岁时,那时日本人占领了村子,知道陆家的书法写的好,于是日本兵坂本六郎慕名而来,几次求字不得,渐渐的与“我奶奶”婉仪熟识,看着“我奶奶”唇红齿白含苞待放于是动了兽意。而“我奶奶”就这样生下了“我”的父亲。在这里,这一切的过程都是“我”臆想出来的,并没有历史的根据。然而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说,历史都是偶然性,那些所谓的历史规律都是史家通过逻辑推理证明出来的,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作者借由“我”之口,说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哲学观点。在探寻身份的过程中,“我”与妻子林康的关系也渐渐变得微妙,妻子辞去了出版社的公职,下海经商,与公司老板打的火热,“我”看不下去,正值妻子那时怀孕,“我”因此怀疑妻子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与妻子大吵一架。“我”感受到妻子的变化,心灰意懒,决意出外寻花问柳。先后找到了走钢丝的女艺人夏放和大学生王小凡,借她们俩排遣自己的欲望和寂寞,然而现实必须去面对,“我”终究要回过头来面对“我”自己的妻子,处理眼下最要紧的事。寻找“我奶奶”也成了心中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疙瘩。在踏上上海的土地之后,我吐的一塌糊涂,在忽明忽暗的路灯间隙,我突然泪流满面,泪眼模糊中,又想起了“我”的奶奶。
小说《叙事》运用多线交错的手法,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盘托出。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牵涉到抗战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也由童年的恍惚懵懂逐渐长成了一个学会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看问题的历史学者。在“我”的梦中,出现了爱因斯坦和老子对话的场景,我与斯大林的亲密交谈,这些段落,都是以梦境的形式反映,但却道出了作者内心的价值追求和哲学立场。
说到语言,《叙事》中的精彩描写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例如在描写“我”离家出走时,作者这样写道:“凌晨四点宁静而又淫荡,对日出充满引诱与挑逗。”;比如“我”与妻子一起研究地图时,“我”发出的感慨:“所有杳无人迹的地方都有我们想象的双飞翼,开满温馨的并蒂莲。”再比如“我”与三叔谈起“我”的历史,用了“历史在酒瓶里,和酒一样寂寞,历史无限残酷的从酒瓶里跳出来,带着泡沫与芬芳,令我猝不及防。”还有“我”面对与妻子情感的困境,叹道“头痛是我的天国走廊,它使我的思想沿着这种锐利的感觉拾级而上。”类似的词句数不胜数。这些语句的运用不乏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遣词造句的熟稔拿捏,可以说,整部《叙事》就是一场“荒诞不经的梦境”。在这场梦境的游历中,“我”逐渐认识到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意识到人最终无法与命定的运命抗衡,也在渴求知识和“情感猎奇”里悟出了宇宙和天地之间的奥秘。
毕飞宇在纷乱杂沓而又生猛有力的语言背后隐藏的不仅是他对于家族血脉的认同,而且蕴含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忧思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