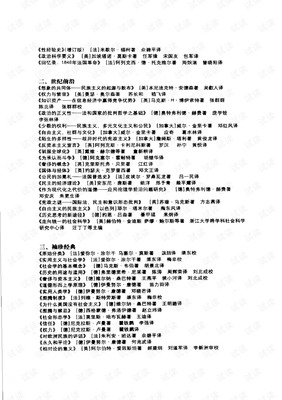从混沌到有序读后感锦集
《从混沌到有序》是一本由(比)普里戈金,(法)斯唐热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混沌到有序》精选点评:
●对我这种人文科学的学生来说过于不友好,中间很多术语和理论我都直接跳过了,专挑讲哲学的部分看了。大体简单粗暴理解了下,牛顿动力学——决定论——时间可逆,热力学——熵增——时间不可逆,通过涨落达到有序,平衡状态时的必然性与非平衡状态时的偶然性的相辅相成与阶层递进。认识从外部施加组织向内部的自组织性转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使得现代科学有了一个转向。
●大致内容:可逆-动力论;不可逆-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序从混沌中诞生。
●不是这个版本的,丢了,好可惜
●确定性消失在时间之矢中。。。翻译太差
●最终结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宇宙热寂说与进化论、时间之矢、熵垒。
●一直着迷着
●其实是一个世代之前的书。 科学哲学衍生而出的-形而上学。 用湍流有规模分布着的图形,来隐喻,混乱是可以发展为秩序的。
●20170518:存在到演化的普及版。有时间性的主体与从内部看无时间的客体的独立问题(也就是存在和演化),是不是可以包容在一个新的广泛理论中?如此,对于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或者复杂开放系统,混沌可能产生有序。
●一个有野心的人啊,让人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看不下去,逻辑混乱 好像什么东西都讲了 只觉得 眼花缭乱,头昏脑胀
《从混沌到有序》读后感(一):读此书,关注的重点不应在非平衡态热力学上
难得普里戈金当时如此受到我国人民的热捧,他的观点在学界还是算另类的。
其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无意识地掺杂进了意识形态。从最早牛顿试图用清晰简洁的数学公式解释万物之理,发展到上世纪对量子力学所展现的各种奇异状况持“闭嘴,只管计算!”态度的哥本哈根学派,到如今学界的热潮早已转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阐释与预测经济情况的Economics,某种实质,趋向,或者说能动性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这也许就是一种偏执吧。
《从混沌到有序》读后感(二):不确定性和秩序
此书属于那种不容易读的书,内容牵扯到许多专业知识,不过,有高中时代的物理,化学基础,再加上百度查询,基本上可以读懂,明白作者想说什么,想证明什么事情。
正如书中反复强调的,自然的系统是由不确定性和秩序组成的,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完全可以用经典力学或量子力学定律加以描述的系统。它们的行为是可逆的,但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绝大多数系统,包括所有的化学系统及所有的生物系统,在宏观层次上,都是时间定向的。
书中的思想非常丰富,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对于拓宽个人的知识体系有很大的帮助。
《从混沌到有序》读后感(三):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四块举世瞩目的丰碑之一
“耗”, 本来早就记录在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四块举世瞩目的丰碑之中: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海森堡等人的量子力学;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工业革命从发明蒸汽机到原子弹爆炸,“耗”, 早就倍增影响,一直威震全球!
人类认识“耗”,在1760年工业革命之后,近百年才在1850年发现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再过百年才在1969年发现耗散结构理论。经历了熵—热寂/进化之争—耗散结构,人类不仅认识到熵增与无序,熵与不可逆过程和紊乱度的联系。也认识到有序来自混沌,生命赖负熵为生。工业革命正是能量的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熵的革命—“耗” 的革命。
--余言述评:问谁能有几多“耗”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87/910687.aspx
《从混沌到有序》读后感(四):《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
《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844888/
有一首翻译的英文诗:“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
苏轼诗:“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成语:“差若毫厘,缪以千里。”
以上文字可用一个现代著名而热门的科学术语来概括:“蝴蝶效应”。
什么是“蝴蝶效应”?此一名词最早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源至研究非线性效应的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1】,它的原意指的是气象预报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初始值上很小的偏差,能导致结果偏离十万八千里!
例如,1998年,太平洋上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气象学家们便说:这是大气运动引起的“蝴蝶效应”。好比是美国纽约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就可能在大气中引发一系列的连锁事件,从而导致之后的某一天,中国上海将出现一场暴风雨!
也许如此比喻有些哗众取宠、言过其辞?但无论如何,它击中了结果对初始值可以无比敏感的这点要害和精髓,因此,如今,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使用它。
毫不起眼的小改变,可能酿成大灾难。名人一件芝麻大的小事,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可能被放大成一条面目全非的大新闻,有人也将此比喻为“蝴蝶效应”。
股票市场中,快速的计算机程控交易,通过互联网反馈调节,有时,会使得很小的一则坏消息被迅速传递和放大,以至于促使股市灾难性下跌,造成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五”这类一天的灾祸。更有甚者,一点很小的经济扰动,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时,股市的人们说:“这是蝴蝶效应”。
有人还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解释社会现象中的“蝴蝶效应”:如果希特勒在孩童之年就得一场大病而夭折了的话,还会在1933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对此我们很难给出答案,但是却可以肯定,起码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大不相同了。
蝴蝶效应一词还引发了众多文人作家无比的想象力,多次被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中。
然而,在这个原始的科学术语中,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科学奥秘呢?它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哪些?这些科学领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如何?其中活跃着哪些人物?他们为何造就了这个奇怪的术语?这儿所涉及的科学思想和概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有关系吗?这些概念在当今突飞猛进发展的高科技中有何应用?如何应用?
《从混沌到有序》读后感(五):你好,混沌(2)
一
我们用眼看,用耳听,用手触摸这个世界,看到的是影子,听到的是声响,触到的是感觉,我们根据这些有限的线索,来判断外在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外在世界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永远也不能直接知道,只有来自外界的一些信号。因为这个原因,笛卡尔说,能够判断真实存在的,只有这个能够对信号进行分析的东西,就是a thinking thing。一切外在,都可能是幻象,可能全是你想象出来的;也可能是一个超级存在给你虚拟出来的,无论是笛卡尔说的魔鬼,还是贝克莱说的上帝;即使我们不搞鬼神那一套,也或许会像康德那样发现,既然我们收集到的永远是“信号”,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表象的世界”,只能了解这个表象的世界,而对于真实的存在,对于“物自体”,永远都无法了解。他机智地用这个区分,来解决自然铁律下如何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但是探求真理仅靠机智是远远不够的。现当初卢梭为了解决如何创建一个理想国的问题,钻进了小树林想了七天,灵机一动想出来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general will”,就像是更高程度的蜜蜂、蚂蚁社会,或阿米巴群。结果呢?被柏林等人识破,发现他这个口称自由的人,背叛了自由,成了自由最危险的敌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默认存在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我们默认早上出发的路,傍晚的时候还通往自己的家;晚上睡觉时候的你如果是个姑娘,第二天早上起来不会变成个大汉。一般人从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原生智能出厂的默认设置。我们对于反常的问题才惊异,就像在心理学实验中,几个月大的孩子就开始对放在屏幕后面一个布娃娃打开发现有了两个而吃惊,但是对打开后还是一个的现象没有兴趣。所以哲学上早有传言,说日常司空见惯的问题才是哲学的真正主题。Sandel不是说,踏上哲学之旅,会让你所司空见惯的日常世界变得陌生。这就是对原生智能的修改。修改之后,一个人就会“异化”。比如说Steven Pinker,他在How the Mind Works中说,我们的基因给我们设定了生存和繁衍的人生目标,绝大部分人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从赚钱求名利,到生孩子传宗接代,这些实际上都是基因的目的。然后Pinker说,我就是不生,怎样?基因如果有意见,它们尽管跳楼去。我不知道基因是否坚强,又或者,基因也不是一些泥古不化的家伙,难道不是食,打出的只有泥,这输入法真的是相当文盲。否则,Pinker或许在暗夜里,会听到一些细声细气地呜咽?
二
由于我们实际上是在加工关于世界表现的信息,因此就有了一种所谓的“现象学”。现象学,实际上不止谈及现象,还涉及智能对现象的加工方式。实际上,一切学问,都得建立在这些“信号”上,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如此,任何科学家,都是一个小小的信息处理器。但是,显然科学选择了一套特别的路径,就是像Quine所说的那样,去掉主观内容,去掉个体性,留下来的就是可靠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还有一种途径,就是主观内容,就是个体性。Thomas Nagel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叫What it is like to be a bat,来论述说,科学研究恰恰是放弃了个体主观性,任何科学陈述,都会放弃个体的感觉或体验。就像Herman Weyl所说:
Scientists would be wrong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not the only approach to the phenomena of life; another way, that of understanding from within (interpretation), is open to us....Of myself, of my own acts of perception, thought, volition, feeling and doing, I have a direct knowledg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at represents the "parallel" cerebral processes in symbols. This inner awareness of myself is the bas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my fellowmen whom I meet and acknowledge as beings of my own kind, with whom I communicate sometimes so intimately as to share joy and sorrow with them.和Nagel一样,Weyl也说,我们通过这种独特的主观能力,来获得对别人体验的了解,如别人的痛苦、悲伤或喜悦。其核心还是John Searle在论及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区别时所强调的“感受”或“体验”能力。让我感到困难的是,我还没有想明白,这种感受能力是如何实现的。甚至还没有头绪。我有时候为自己智力不足感到焦虑和痛苦。可是也没得抱怨。
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呈现出来的表象。表象纷繁复杂,有时候让我们愉悦,有时候并不能让我们愉悦。我说艺术是一种对刺激的加工,是说我们的智能根据生存适应需要,对某些刺激会进行响应,或者产生愉快的感受,或者产生痛苦的感受,或者还有其他感受。这些刺激在艺术中被选取出来进行加工,呈现给观众,就是所谓的“美”。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艺术中的“美”,不仅包括美还包括崇高,甚至还包括丑,不仅能提供愉悦还能提供痛苦。所以艺术的“美”是一种广义的美。连Quentin Rarantino在将金棕榈给麦克摩尔的《华氏911》时都表示,好电影不一定要精致,也可以表达力量。有人看到精雕细刻的画面、绚丽夺目的色彩就以为电影高级,反而是一种审美能力低下的标志;这就像以画的得像不像来判断一幅画画得好不好一样。单一可能意味着贫瘠,而多样意味着存在可以探索的资源,所以我们喜欢丰富;但是我们喜欢秩序而不喜欢杂乱,所以我们喜欢规则的图案,喜欢对称。这些都被列入在传统上对美的定义里。这是智能的一种需求,我们无法利用混乱,但是能从规律中获益。现象虽然纷繁,我们却倾向于从中找到秩序。所以当牛顿作为上古大神一统自然(物理)科学,人们对牛顿的崇拜简直如滔滔江水。我如果没有记错,哈雷彗星那个哈雷也是个科学家,他称自己在牛顿面前感觉自己像个白痴。这就意味着,既然哈雷是个牛人,那么牛顿就变成了牛人的2次方。Pope甚至给牛顿写诗(墓志铭)说:最初,自然及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牛顿用他的智慧照亮黑暗。而自然向牛顿屈服,坦白自己的所有秘密。
如费曼所说,就像一盘复杂的棋局,仅仅来自简单的走子规则,我们所看到的纷繁表象,背后也只是一些基本的自然法则。启蒙时代的先驱们受这种乐观主义的驱动,曾经以为,科学能够很快获得关于整个自然的全部真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也能采用一套理性方案来建造一个和谐的理想国。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曾误以为,启蒙时代理想后来的破灭,尤其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导致在失去了上帝之后,科学和理性允诺的安全感也失效了,对理性的失望引发她们转而投靠非理性,发明了存在主义,或者一些奇怪的来自原生智能的产物,比如主张投入自然的怀抱,返回自然、想要天人合一,我记得被谁称作“返祖症”。但这里面有两个误解,首先,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进展使得人类当中的一些人失去了类似上帝这样的精神依靠,不是理性的破灭导致的。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种精神寄托,奥古斯丁需要,为了满足情感需求不惜驱逐理性自我欺骗;相比之下,托马斯·阿奎那就不需要,所以他保留了对信仰构成了威胁的理性。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推翻了神的信仰或其他宗教信仰,并且引出了宏大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而人是一种短暂的无根的存在,这才导致了帕斯卡的恐惧和投诚。至于萨特、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此处不多谈。另一个误解是,就像《高级迷信》中所说,很多人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就像民间科学家或其他外行人那样,往往采用原生智能来理解科学,所以他们会以为,“测不准”、“不完备”,表示科学宣告了自己的不可靠,所以他们觉得理性、科学的“可靠性”宣告破产。这甚至是滑稽的,因为他们看不到,“测不准”和“不完备”这两个定理就是可靠的。逻辑完全反转了直觉。我们直觉上判断不出这样的错误:“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概念自身是绝对的,所以是错的。所以明眼人都看到,相对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就像“建构论”是自相矛盾的那样(因为其理论按其自身的规定也是建构的)。启蒙时代的对理性的乐观,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一种心理安慰,满足人寻求确定和单一的精神需求。当世界重新回到不确定性、复杂性,那些情感脆弱、缺少安全感的人,会感觉失落、孤独、无依无靠甚至恐惧和颤栗,这是敏感脆弱者的哲学。
三
人类的知识是从无到有,从错误百出到逐渐发展出一些相对可靠的理论的过程。因此,知识实际上是逐步回答了我们关于自然的疑问。但是,我们的智能一开始就对世界有一种预设,而且我们的智能还会对世界自动发展出一种理论模型。不同的人有不同大小的模型,有的人的世界理论仅仅是自己所见,或者仅仅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所及,或者再扩展到天和地。在时间上,一般人的视角是从最近几日的事务,延伸到几个月,或某些事务跨了年,但是到了这里视野已经十分模糊。有些自助书籍会教人给自己设定五年十年计划,然后再分散为更短时间的目标,但是这种书也往往并不畅销。不仅是这种成功学不够吸引人,这么长时间跨度对于人的智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我们的眼睛是近视的,看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些都是原生智能的特点。当我们受了教育,或更准确说,一些人通过知识又安装了一些程序,就能够扩展我们对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模型,不仅看到天空和星星,还能看得清银河系以及更远的地方,甚至看得到大部分的宇宙,甚至还知道看不见的黑洞和暗物质,不仅能看得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还能看到自己祖辈,看得到人类的过去,甚至看得到地球的过去、宇宙的过去。当然,或许也能看得到未来。注意,一旦安装了这个app,你的整个思考方式可能就变了。当我们用原生智能看眼前的世界,我们会受利益计算的影响,热衷于美貌、财富、地位、名声和成功,看人大公司老板富翁大款、大权在握的官员、影视红星、天天在媒体出现的俊男靓女,本能地会喜欢、热捧,这是原生智能获利的策略。但是,如果拉长视野,我们会发现,这些价值在茫茫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根本不值一文。这些是基因用来推动人追求的价值,是用来实现基因繁衍目的,这样活着的人相当于是扮演了被基因打造的、为基因服务的工具。这样一种工具性存在毫无意义。
表象纷繁,而我们智力却有限,难免在面对这个世界时力不从心。普利高津和斯汤热说,最初研究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分解的过程,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还原的过程。但是,还原的过程不能解释全部的问题。就像罗维利在The Order of Time中所说,微观上一切都是相同的,就是量子事件。多伊奇在《真实世界的脉络》中特意提到原子、分子、有机体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则。那么全都还原到粒子上,我们恐怕就无法解释生命的存在。毕竟,如罗维利所说,如果我们放大到粒子层面,就不存在猫、高山,也不存在我们人类。如Gell-Mann所说,我们都是夸克组成的。你是一堆夸克,我是一堆夸克。那么,如果说,一堆夸克对另一堆夸克有了意思,这看上去就像是在开玩笑。现在还有个更难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每个夸克都是“死”的,怎么这一堆夸克组合在一起就“活”了呢。你身上每一个夸克都是死的,怎么你就是活的呢?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误解。不存在“活”,实际上你是死的,我也是死的。你可能会害怕。不要怕,有我这个死人陪着你。我是说,我们所说的“活”,实际上只是一种描述,就像我们用“光”,描述那个你我都见过都知道东西,我们用“黄色”,描述那样一个你我都见过都知道的东西,同样,我们说“活”,就是描述那样一种你我都知道都见过的“状态”。但是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活”。不然,我们就很难说“病毒”是不是活的,体内那些会进入入侵的病毒的白细胞是不是活的。你说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活”这个概念自身存在问题,就像人类学家很难定义“宗教”那样,因为有的宗教有神,有的宗教没神,没有一个清晰的设定。
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原生智能理解世界的方式,引入一种更精细、更准确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就像对混沌的理解,不能是日常意义上的那种混沌无序的观念。日常观念自身也是自相矛盾。比如说,在谈及熵时,常用的一个例子是把两种气体放在一起,刚开始两种气体分别在两个箱子里,是有序度最高,最终气体均匀混合,熵最大最无序,但是难道我们不会觉得,两种气体“均匀”混合也是一种有序吗?因此熵或许就只能表述为概率相关,而不是有序无序。所以,罗维利说,像普利高津和斯汤热这样认为生命是反熵,是在有序变无序定律下反向产生有序的现象,这种观点是错的。生命自身并非有序,而只是一种算法的产物,这种产物就是一种加工低熵的机器。因此,不应该说我们是消耗能量或能源,而是消耗低熵。否则,罗维利说,我们就该去沙漠里,因为那里能量最高。能量本身并不会消失,因为能量实际上是守恒的。我们需要的是低熵。普利高津和斯汤热的问题是:在熵增的宇宙中,怎么会产生(有序的)生命?罗维利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能把整个宇宙都看作一个单线系统,而应该看作宇宙当中有许多层面,或说许多子系统。仅仅在某些层面,比如我们所在的这个层面,宇宙过去处于一个低熵点。然后才有我们,产生了消耗低熵的生命。不仅我们和阿米巴、蜂与猫一样,是一种消耗低熵的结构,甚至我们人的一生,也是这样一种算法的产物。只不过,虽然我们是奴隶,从来不存在一个奴隶主罢了。普利高津说,生命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生物圈得以寄身的那些条件。多伊奇已经说了,他说基因里记录了对环境的一套反应信息。古典科学,甚至连基督教自身也认为,上帝造出来的宇宙是个自动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自动机的运行原理。当然,既然如此,那就不需要上帝,就像Laplace骄傲地说的那样。自动机不需要外部的推动,那么如果说生命是基因打造的自动机,同样也不需要一个主人。所以还是那句话,只需要一个程序员。程序自能能够驱动自动机运行。就像蚂蚁建窝,刚开始乱哄哄,很快,不同土块被不同数量蚂蚁搬过,留下不同量的化学标记,引导了蚂蚁对这些土块不同的对待,引发秩序。每个蚂蚁都是一个功能子,都执行一种简单的基本反应,比如“先搬留下记号最多的土块”。人类也一样,看不见的手不仅造出了你,甚至还引导你的整个的一生。只不过你不知道,还以为是自己在做主罢了。
人类知识历史的发展,就是一切学问研究都逐渐科学化。哲学,神学,玄学,巫术都是如此。科学和哲学的区分,或迷信,或神话,只不过是某些人类的认知,没有能够成熟为一种科学,也没有能够获取一种科学的理论。所有可靠的知识都来自科学,所有能产生可靠知识的都是科学。但是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的,利益是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尤其是在群体层面。所以即使在古希腊时代,那些探索知识的人,包括苏格拉底,也会被城邦控告亵渎神或传播、煽动不利于城邦团结的意识形态罪、败坏青年思想罪,而被流放或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被希腊人毒死的。尽管提起希腊,人们总是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而希腊民族是一个天才的民族。从来没有另一个文明、另一个民族获得如此的赞誉,新月沃地不行,中华文明也不行。宗教裁判所也判处了不少异端,还烧死了布鲁诺。这简直就是荒谬和愚蠢,他不过坚持自己的一种对世界的见解。但是人类就是这种本性,是利益驱动的本性,党同伐异,联合起来扩大自己势力消灭敌对势力。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本质。当然,这个本质是真的本质,是nature,不是essence,essence是精华,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其实不是本质,是存在先于精华。存在先于精华,这就是没有追求。应该说,存在就以精华的形式存在。是存在先于精华,这是萨特的误解,他和普利高津一样,预设了一种静态的存在,然后以为动态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但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纯粹静态的存在吗?并没有。所谓平衡态,也并不是静止的,也是变动不居的,就像均匀混合在一起的两种气体。萨特的理论是,自我永远是超越自我的,即明天的我是超出今天的我的。他这就是不能理解变化,不能把“自我”一开始就定义成一个变动的过程。海德格尔就比他明白,海德格尔说,自我不是一个自我,而是一个场。什么意思呢?就是威廉姆斯定义的“自我”:他的思想和他的身体,他的妻子儿女,他的财产和地位、他的人际关系等等。当然,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定义,因为他的定义竟然是针对一个“中年白人男性”。这就是海德格尔说的一个“人”,一个“我”。普利高津是说,平衡态是稳定的,惰性的,也是无趣的。但是远离平衡的系统,如果受来自外在的某种影响,可能会产生某种有趣的现象或说秩序,就像进化,趋向复杂、高级。我觉得普利高津也受了自己某种原生智能的误导,总是觉得生命是趋向有序和高级,但是觉得进化是趋向高级是一种对进化、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直觉上的误解。或许仅仅是存在多种attractors,当受到某种影响,就会出现attractors之间的跳跃。就像掷骰子,六个面是六种可能的结果,外力会引发显示不同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