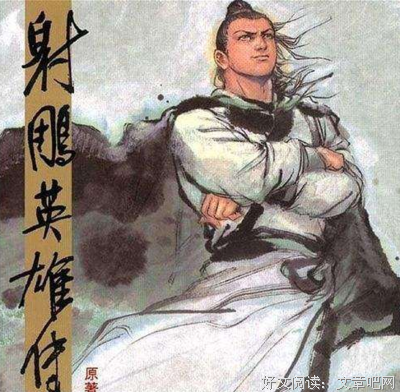儿女英雄传经典读后感有感
《儿女英雄传》是一本由文康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6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儿女英雄传》精选点评:
●20100203 哪里有英雄儿女
●以前当评书给外婆讲了。
●十三妹好看,安老爷不好看。
●真迂腐
●可以当个评书看看
●就是喜欢这种无脑的大团圆( ̄▽ ̄)
●我竟然能把它读完,orz。。。选一个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更低的星可选了。一句话书评:一个卢瑟wsn穷极无聊的疯狂yy
●从情节来说,真不咋地。
●不过是觉得出名才买来看看~~比较失望
●好好一个十三妹,愣是被文康给毁了!通篇的京油子味,越往后越读不下去,翻两页读都不影响进程,冗繁啰嗦,跟《红楼梦》的语言简直没法比。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后半部十三妹的转变,简直让人不忍直视!生生把个侠女给毁了!身世经历都差不多,文康比曹雪芹可真不是差了一截两截,越比较越看出《红楼梦》的好和不易!在古代,悲剧的结局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来的。
《儿女英雄传》读后感(一):地地道道的北京话
不说别的,文康那北京话够味儿,地地道道的。小说的情节一上来很吸引人,但自打安老爷安太太与儿子重逢,以后的就全是鸡肋了。要说一本小说能一以贯之的紧凑好看确实有难度,保不齐后面的内容就拖沓无聊起来,可是您猜安老爷安太太是第几回重逢的?第12回,全书可是有40回啊。按比例来算,应该是1.5颗星,四舍五入,两颗星。
《儿女英雄传》读后感(二):1/4的好书
在我看来,这本书顶多算是1/4的好书,好就好在前几章让人读得神清气爽,先是安老爷老来入仕,却因不谙官场规则,失官赔金,然后安公子带银上路,却被小人所觊,幸有侠女十三妹相助,从此才化险为夷。但从安老爷辞官去寻十三妹开始,小说便变味了,完全入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将一个本来至情至性的十三妹变成个低案举眉的良妇,时而又如探春理家一样的能干,完全变了个人,好不怄人,安家自从遇着十三妹后,便事事亨通,安公子得了金玉双美后,又中举、娶妾、升官,后半部完全是作者意淫之作。作者似乎还对《红楼梦》颇不服气,怪曹雪芹与贾府何仇,偏要令贾府家破人亡,实是庸人之见。
所可取者,乃这部小说语言活泼,为我读旧小说所仅见,大约作者为旗人,所受儒道之害不深,时而流露出“京油子”的调调,但是到了后面,到底也能看到孔孟之道的影响。
《儿女英雄传》读后感(三):直男的终极幻想
我国众多才子佳人小说,虽然一看就不靠谱,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小女孩儿,因为读了书认了字,对这世界有了一点与蒙昧时不同的看法,忍不住就想表达,就想寻找同路人:我是这样的,有没有人能看到我?有没有人能懂我?正好路过一男的,反正他宣称他懂,有了一点知识但完全没有见识的闺中少女能区分出这人是恰巧撞上还是处心积虑蹲守已久吗?能辨认出他是真懂还是假懂吗?不能的。那她们的沦陷几乎就是必然的。
无论情节怎么不合理,这种心理变化是真实的。人一旦意识到“我”是这样一个“我”,“我”眼中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就会向世界寻求共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男人也一样。只不过男人可以高山流水遇知音,过去女人不行,她们的社交被婚姻家庭与世界割裂,就算有一二闺中密友,一旦成家,就是咫尺天涯。她们能寻求共鸣的对象只有丈夫,那小说中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丈夫刚好就是一个知音。至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像《西厢记》和《莺莺传》。
所以虽然我们痛批这些才子佳人反逻辑反常识,仍然要赞美这些小说抓住了女性这刚发芽的自我意识。然后来看《儿女英雄传》。一个少女,江湖经验老到,连土匪窝的地窖子在哪安都一清二楚;武艺超群,还不是那种学院派的精熟,是既能单打独斗演练套路又能群攻中寻找契机各个击破,连杀十人脸不红心不跳的实战派;处事周全交游广阔,要救人连怎么护送怎么了结都预先打算明白,凭名号就能找到江湖朋友帮忙。这么一位江湖老油条,对上一个连低端骗局都分不清好孬、场面客气话都说不来、见了土匪就吓尿的年轻人,居然还要耳边一红以示娇羞,担忧男女大防以示贞洁。当然后来还添上大家闺秀娥皇女英等要素满足男主的虚荣心。可以说是工具性高到了极点,而自我意识低到了极点。就好像一个人工作了十年还相信“公司就是你家”这种鸡汤,就好像一个人游戏No.1还是觉得一个菜鸟好牛X。
难怪我小时候看不下去,现在更看不下去。
《儿女英雄传》读后感(四):新式侠女---十三妹
《兒女英雄傳》中十三妹身上的狹義之氣與傳統俠女形象表現出來的有所不同。女俠形象發展至十三妹,有追求獨立自由轉變為遵從禮教,集“俠女——賢婦”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與一身的十三妹是作者理想中的完美的“英雄兒女”的典範,雖然十三妹形象有俠女到賢婦的轉型歷來頗受爭議,但其對內的控制力和對外的開拓力也有其內在邏輯的合理性。十三妹這個人物的身體原型是由舊小說中各種人物模式重新組合疊加起來構建而成的,晚清這種融合公案小說、才子佳人、世情小說于一體的創造方式,預告著章回體小說在新的創造時期來臨前的掙扎與反抗,雖然無法阻止其必然衰落的歷史命運,但作者在理論指導下的自覺探索與有意識的追求是成功的。
燕北閒人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兒女英雄傳》中的十三妹,可謂古代小說中比較有影響力的“非典型性”俠女形象,成為後世小說作品裏深入人心的藝術形象之一,經常活躍在戲曲舞臺及說唱藝術裏。但因其不同于傳統俠女的性格特徵及命運轉換而引發了很多學者的爭議。
小說中的何玉鳳出身于世祖大家,自幼習得一身的武藝。後因其父被奸臣所害,她化名十三妹,攜母流落荒山,遂與江湖豪俠為伍,尋機為父報仇。書香門第出身的公子安驥和村女張金鳳被惡僧困在能仁寺,十三妹慷慨相救,撮合二人成婚,並贈金説明安公子救父。安家、張家等人為感謝十三妹大恩,乃苦勸十三妹也嫁給安驥,以使她能夠安身立命,過上富貴尊榮的生活。成為安家大奶奶的何玉鳳,將俠女的豪俠果決變作治家的精明與魄力,佐夫成名,最終“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從十三妹到何玉鳳,從俠女到賢婦,不只是人物從“英雄傳奇”中的“江湖”走向了“世情小說”裏的家庭空間,敍事模式明顯不同于唐人小說。十三妹的俠女形象主要新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強調俠女的女性化氣質
容貌與服飾是樹立女性外在形象的基本要素,也是考察俠女形象虛構性質的一個途徑。傳統俠女主要不是以悅目的容顏、善良的性情成為讀者欣賞的對象,她們往往是作為“非常之人”進入傳奇世界而成就一番“非常之舉”,因此敍事者為了取得神秘化的效果,似乎是有意淡化了俠女們的性別意識。而《兒女英雄傳》中卻特意凸顯十三妹的容貌,安驥第一次見十三妹的時候,“只見她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朱丹,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旁帶著兩個硬紅的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什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當然,作者強調人物的女性化氣質,不僅僅是通過十三妹的外貌及穿戴,還要一系列的小兒女的心理情態的凸顯,例如她對其他女性的生活方式和衣著打扮的好奇與羡慕。十三妹初見安太太時,通過她的眼睛,有一段對安太太衣襟首飾的細緻鋪張描寫,從中可以看出十三妹的女孩兒情態。“看了這番說話、行事、待人,才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兒,原來還有這等一個境界。她心裏頓覺甜苦寒暖,大不相同,益發和安太太親熱起來。”這種心理活動是尋常的女兒心思。其他一些特徵,如侍奉母親的孝心、對鄉鄰的溫和友善、喜歡為人謀劃的細緻以及女性巧於撮合他人婚姻的天性,都是她身上更本質的女性情感。
由此可見,其外在形象和情感方式異于唐人小說中對傳統俠女形象偏於中性化的敍事模式。細膩豐富的情感方式和心理層面的女性性別的內在特質。周作人認為世間固有十三妹這般矜才使氣的女子,小說不過是撲捉到了現實中的一種人物性格而已。
二 驚人的食量和氣力
讓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倒不是因十三妹是一個“ 絕色的年輕女子”,而是她驚人的食量、力大於身的勇力和雷厲風行的作風。江湖好漢的神勇氣力在十三妹身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提,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便一手提了石頭,挪動一雙小腳,上了臺階。那只手撩起了布簾,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眾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詫異”。特別是在能仁寺“雷轟電掣彈斃凶僧,冷月昏登萬殲餘寇”之後,“只有十三妹姑娘,風捲殘雲,吃了七個饅頭,還找補了四碗半飯,方才放下筷子”,據此我們不難看出十三妹身上也有《水滸傳》裏梁山好漢盡情地搏鬥廝殺之後狂吃海喝的痛快淋漓的身影。即使在和安公子成親的那天早上,她還吃了四個饅頭,八塊栗粉糕,兩碗混沌,兩碗半粥。
在宋元講史、小說話本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章回體小說,當然不會放過任何能夠博得眾彩的有趣噱頭話題,一如交代人物的能量來源以及生活細節上的趣味性等等。這種略帶搞笑的戲劇化敍事方式是對以往舊小說嚴肅而中規中矩的敍事方式的一次突破和調整。
三 融入世俗的現實生活
俠女十三妹被抹去神異化的玄幻色彩,著上了一層現實功力性的外衣。傳統劍俠小說都極力強調俠女超越凡俗的“異人”形象,身份神秘、情感冷淡為其寫作的統一內在相同點。《兒女英雄傳》中十三妹原名何玉鳳,本出身於世家大族,是有根可尋的大家小姐。她的一身的好功夫也是自幼習得,“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離山老母學來的”。“俠女”一詞是由“俠”和“女”兩個詞性構成,真正的俠女必然是在肯定“女性”這一性別符號的基礎之上才能完成理想中的狹義之舉。身為一個普通的女性,豪俠如十三妹,脫離了傳統小說中的神異化身體,這位俠女就必然要回歸到傳統女性的性別角色,找一個男性安身立命,依靠家庭生活。於是,唐宋劍俠小說中人際關係疏離、遊戲人間的生活態度、不受性別規範約束的俠女敍事模式被打破了。
婚後的何玉鳳“早把從前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卻事事克己、步步虛心的作起人家,講起世路來”。她對功名利祿的功力態度,是傳統劍俠女性,甚至世情小說中的普通女性所不具備的。《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郎,聆蘭言一心攻舊業”,何玉鳳望夫君成就功名,打造成功男性的野心當然無可厚非,而她這番言行舉止與傳統劍俠小說中的女性不同調,也和世情小說中女主人公隱忍恬淡的境界有著天壤之別。何玉鳳式的俠女是一個特殊時期的文學現象,而晚清小說創作中各類題材的合流趨勢,造成了各種人物模式疊加於一身的現象。
人物模式的多重疊加造成了人物性格邏輯的混亂感,以致使十三妹有嚴重的人格分裂症,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受到懷疑。孫楷第認為十三妹“前半則劍氣俠骨……及結婚後,……又平平極了,與流俗女子無以異,一人人格前後不協調如此,真是怪事。”身體構建中各種原型拼接疊加的痕跡難以圓融貼切,不免引起人們感官上的不快。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十三妹“當純屬作者臆造,緣欲使英雄兒女之概,備於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動絕異,矯揉之態,觸目皆是矣。”歷來受到很多文學大家的批評,即便如此,也並不能減少人們對十三妹的喜愛和對《兒女英雄傳》的追捧,這一點,從後世人們對《兒女英雄傳》的續書方面就不難看出。續書有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宏文書局石印本三十二回《續兒女英雄傳》;宣統間四卷四十回石印本《再續兒女英雄傳》,作者俱佚名;令據佚名《續兒女英雄傳序》稱此前已有續書。不僅如此,京劇劇碼也有“紅柳村”(“十三妹”)、“能仁寺”(“悅來店”)、“弓硯緣”(“青雲山”)等,至今仍在搬演。
作者塑造十三妹這樣一位俠女形象究竟有何與眾不同的意義呢?
作為晚清小說家,文康無力挽回即將解體的舊秩序,只有在想像中拯救衰落者,而何玉鳳就是這樣一位深具化腐朽為神奇之“魔力”的新式俠女,是從舊文學中擇優捏合出的人物,在她的身上堆積了舊小說中所有受人歡迎的人物模式。從作者的創造本意來分析,何玉鳳之所以成為前後脫節的“超人”,是有其必然性的。作品緣起首回“開宗明義閑評兒女英雄,引古證今演說人情物理”,開頭就以八句韻語作為全書綱領:俠烈英雄本色,溫柔兒女家風;兩般若說不同,除是癡人說夢。兒女無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憐兒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龍鳳。作者力圖在小說中把“天性”與“人情”統一,將“俠烈英雄本色”與“溫柔兒女家風”融合為一體,這種看似對立的兩端,巧妙地結合在作品主要人物十三妹一人身上,成為超越此前小說作品人物形象的一個集大成的新形象。
俠女多重身體的構建是晚清小說題材合流的結果。《兒女英雄傳》是公案小說、才子佳人和世情小說的混合體,其中人物並不以敘寫狹義為滿足,逼真呈現世俗生活場景和各式人物內心情感成為敍事的主要目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多套用傳統的模式,缺乏作家自己的創作個性”。何玉鳳式俠女的出現,正是舊小說無力塑造寫實性人物的表現。總之,俠女作為古代小說史上的一種獨特的人物類型,其演進的軌跡是從非寫實的虛構到寫實型的人物。在中國俠文化史上,女俠形象經歷了由豪俠、義俠到情俠的演變過程,女俠形象發展至十三妹,我們可以看出她身上的種種新變,也可以通過分析出其背後創作模式的集大成狀態和文學的發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