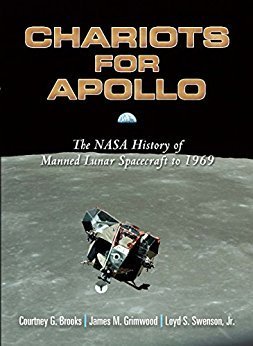《我的朋友阿波罗》读后感100字
《我的朋友阿波罗》是一本由[美] 西格丽德·努涅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朋友阿波罗》读后感(一):Apollo
我的朋友里可能有埃里克也可能有彼得,但从来没有过阿波罗,这个A开头的名字,希腊性的名字,去掉“poo”就会变成“All”的名字。 All,一切, 听起来尽在掌握的狂浪像是晃动过的可乐不知好歹,可十六岁,满身泡沫也能被原谅,世界鲜明,闪闪发光。 通常来讲生成这个图景的概率不低,或者很高,而你预计未来也将是如此。 可过了两年,你看到涂尔干写自杀的中介变量是社会疏离。又过了一年,你发现箫沆说知道可以选择自杀,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你看不见All了,你只能看到poo。 词语可以被拆解,话语当然也可以消失。 你是个作家,你不想写了,因为你的读者似乎已经无法看懂你印在纸上的话,而你又不愿意仅仅为他们选择了你而退让半分。 你是个情人,你的对象死了,他的三位夫人,你能对他和她们说什么,死人听不见你的话,而活着的人,你和她执手相看泪眼,你允诺收留了她不要的大丹犬,话语脱缰于缄默的方向。 你是失明的柬埔寨女人,别人问是怎么失明的,你答哭瞎的,但检查结果并不支持,它们讲一切正常。 你是性工作者,你主张自由的性交易,你抗辩自由的性行为有什么不对,可你又说如果有钱,谁愿意做这个,我要写。以文字替代性,你还是一名文字工作者。 你是接受心理治疗的女孩子,你的喉咙总是很痛,发声过于痛苦,风从喉间疾驰,只有哑喑的回响。 你是和丈夫一起寻求心理治疗的妻子,你们说同一种词,却无法沟通,你大吼“我说的是帮助,帮助”。 你是不再写作的未来之星,你是路过遛狗女人的甲乙丙丁,你是电影里说要回来现实里说太累的脱逃大师(累了所以要回来?回来了所以才累?),你是从大桥上一跃而下的雏妓,哪有白色的天使,只有碎掉的浪花。 哦,对了,你还是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现下失去主人的大丹犬,你低伏着,时而颤抖,发出像气垫床慢慢漏气的嘶声。 当话语走到了断头路,取而代之,行动便要搭梯。 你哭泣,用泪水。你做爱,用肉体。你用手,不停不停不停地写,不断不断不断地画。你扣开心理治疗师的门,某一刻,管他什么歇斯底里,你只想和他大打一架,用你刚晾干的他丢给你的衣服,捂住他的口舌。 一阶一阶,如果还是不行,那是不是只有,自杀。 或许也不是,你可以抱着那只大丹犬,他像人一样侧躺在你的床上,他有温暖的吐息和重量。 他不像腊肠,不会躺在小毯子上,不是你毛茸茸的一部分,他很老了,有两只剪的失败的耳朵,会听你朗读的耳朵。 语言会失效,外延的行动会失灵,理解在三分之二的时间会输掉。 可还有乐观估计的三分之一,悲观预判的万分之一,理解会赢,当它敞开全部为赌注,去祈祷一个不可能的奇迹。 求一个解。 人对狗的理解,狗对人的理解,人对人的理解。 去年的春天,我和短暂的失语狭路相逢,记住是失语,不是失声。在刚刚动完手术之后,她想说帮助,但她出口的是拥抱。当然还有更多不成语言的语言,我很熟悉,却听不懂的语言。 那个时候我想,究竟我和她,谁的语言,谁的举动,才是意义。 后来,我开始搭建我的梯子,它还没有完成,但我想它应该会带我看到一些什么。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你要说,你要听,你要看。
我会听,我在说,我将看。 在满溢阳光的午后,轻舔她的指尖。
《我的朋友阿波罗》读后感(二):不会自杀的朋友
在打开本书之前,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一部人狗情深的感人故事了,但读到第30页,书中的主角—阿波罗才第一次被提及,到第二章,阿波罗的真身才姗姗出场。
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动物与人”的小说。它甚至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我”在经历亲密导师“你”自杀身亡后,被“你”的现任妻子“三夫人”从悲伤中拉出来,拜托“我”收养“你”生前饲养的大丹犬阿波罗。不能接受它可能被处死的风险,“我”只好把阿波罗接回家,这只曾经流浪,后被导师收养的大型犬深沉安静,仿佛它在主人去世后一直沉默地哀悼着。“一回到家,他径直去了卧室,然后一头扑到床上。我满脑子想到的是:悲痛欲绝。” 阿波罗和它的新主人/朋友无法用语言交流,但两个悲伤的灵魂却在遇到彼此后逐渐得到救赎。
这本书的叙事像一封长信,失去至亲的“我”讲述着“你”走之后的种种经历和所思所想,亲切如带着一束花到墓地旁坐着聊天,一聊就是一天。从文学到哲学,从两性到心理治疗,再到“我”与阿波罗越来越融洽的相处,仿佛要把“你”走后的世界一一讲给“你”听。
书中对狗的描写很令我触动,不同于人类,“他们不自杀,他们不哭泣。但是他们可能而且真的会崩溃。他们可能而且真的会心碎。他们可能而且真的会丧魂失魄。” 刚来到“我”家的阿波罗有些冷漠乖戾,在“我”不在家时会焦虑到啃遍“我”的文稿,却在“我”念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给它听时,露出了不多见的笑容。就这样,“我”与阿波罗建立起了微妙的友谊。
阿波罗年岁已高,“我”总在担心,也许在不久后的某一天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送它去兽医院了。“我”甚至在想,怎么才能让它在家里安详地走呢。据说狗总能在死亡之前预知到自己的命运。后来的某一天,在海边的小房子门廊处,阿波罗在“我”的陪伴下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有两个真正的朋友,“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程,却见证了阿波罗的退场。
不得不说,在读完最后一个字,我还是欣慰于这样一个有温度且有偿还的告别。
这还是我养狗以来读的第一本与狗有关的书。很长时间以来当我看着自家的狗们,想着他们十年后可能就不在这里了,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人类的懦弱,从出生贯穿到死亡。但狗儿们不会有遗憾,也不会担忧明天以后的事情,它们只是看到你就喜欢你,看不到你就默默地伤心一会,然后把自己蜷成一个小球,进入梦乡。我经常矫情地想弄清楚它们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它们知道我们在爱它们吗?它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最终,我相信这都是人类的一厢情愿,是动物的存在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类,而不是反过来。就像本书作者转述的昆德拉的看法:“动物没有和我们一起被逐出伊甸园,它们留在了那里,不受肉体和灵魂分离这样复杂的问题的困扰,也正是通过我们对它们的爱和友谊,我们才能重新与伊甸园联系起来,尽管只是通过一根细线。”
最后发个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阿波罗》读后感(三):老友狗狗阿波罗
“你无法解释死亡。而且爱配得上更好的回报。”
女主人公“我”的写作导师自杀身亡。她相继和导师的三任夫人见面,了解一下导师生前的一些状况。三位夫人性格迥异。还沉浸在如同丧亲之痛般痛苦的她,跟夫人们聊起来,还持续怀念着那已经故去的导师:
(故事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而“你”指的都是那位导师。“他”则是后来接过来收养的阿波罗。)
⭐大夫人:
跟“我”是同一个班上的同学。“我”曾见证导师热烈追求大夫人。大夫人毕业后就找个人嫁了。这让导师痛不欲生。他们以往的爱,太炽热。然而,大夫人跟“我”说道,“如果我们没有相爱那该多好啊”。
⭐二夫人:
“我”并没有过多地和二夫人接触。她疯狂嫉妒着“我”和导师的亲密。他是她生活中的光和爱。“我”只能获得二夫人的怒目而视。
⭐三夫人:
优雅漂亮是她的专属形容。60岁的她依旧魅力不减。当年导师和三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周围的人哗然。三夫人当时是个寡妇,年龄跟导师几乎一样大。(这对于喜欢追求年轻貌美女子的导师的取向截然相反。)正是因为这段婚姻,导师一下子像是老了10岁。
她不惊讶导师的最后的死亡结局。她的祖父也是如此,饮弹自杀。她参加追思会,并没有失声痛哭,只是单纯像是来参加个活动那样,从容冷漠。
三夫人跟“我”说着话,礼貌而疏远。她拜托“我”收留那只导师从公园里收养回家的丑角大丹犬。那只狗本来叫迪诺,现在叫阿波罗。她好心引导“我”说,倘若我无法带阿波罗回家的话,阿波罗只好待着狗舍,日日夜夜吠叫,思念那死去的主人。
况且,在她的眼中,“我”是个很适合的人选:一个人生活,没有伴侣没有宠物没有孩子,在家工作,以及热爱动物。只是她没有设身处地想到,房东不允许“我”在房子里养狗。
——
“我”无法想象阿波罗日夜伤心吠叫,试着悄悄地把阿波罗带回家中。
阿波罗跟平常看到的狗狗不一样:不会对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跟别的狗狗也玩不来。他只喜欢蜷缩成很小一团,自己给自己怀抱。
不过,他极其收到周围的欢迎:狗狗们围向他。邻居们会主动跟“我”聊起他,想和他合照。他俨然成了附近邻居里的明星狗狗。
“我”平常在教授写作课。跟导师一样,我们认为写作是这辈子里最好的事情。“我”建议那些患有心因性症状(失语、失明和瘫痪)的女人写下日记,记录自己想说的话。她们有的一个字也不想写,拒绝透露自己的悲惨,有的却写得密密麻麻无法分辨。她们的苦楚需要出口。出口可能就是她们手中的笔记。
“我”想念着故去的导师“你”,想到导师的好色,像库切的《耻》当中的主人公戴维·卢里,想到都很喜欢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到处都是关于导师的回忆。“我”不大自知自己需要心理治疗。
朋友们都察觉“我”处在半疯癫状态,特别是听到导师的死讯之后。“我”常身处在某处却不知道怎么过去的,想做某事却忘了是什么,去上课却没带备课笔记,跑错时间和医生诊室。一切都处于失常状态。
阿波罗的到来似乎正在改变着“我”:“我”上课会盼着赶紧下课,好能和阿波罗一起到楼下散步;他曾咬烂过“我”的克瑙斯加德平装本;他如今会走过来“我”要读的书,头靠在“我”的腿上准备听“我”念书给他听。
“我”不确定阿波罗是否是治疗犬。治疗犬的目的是希望减轻人类可能经历的任何痛苦,给他们带来安慰、令他们振作。“我”也不确定是否把阿波罗当作一部分的“你”(导师)了。但是阿波罗的陪伴确实能让“我”重新拾回写作和读书的状态。
房东最后还是知道了我在房子里偷偷养狗。他无奈但无可奈何跟“我”说要不得带着狗狗搬离这里,要不把狗送给别人收养。“我”无法再次抛下阿波罗,愿意带着他流离失所,找别的住处。
“我”还没收养阿波罗之前,十分担忧自己能否担起养宠物的责任。以前养过的猫咪,最后都离“我”而去,“我”却无能为力。过往养宠物的痛苦令“我”犹豫不决。还好,“我”坚定了要和阿波罗一起生活下去,直到他老去,安详死去。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是,邻居们不反对阿波罗的存在,即便阿波罗流着有点臭味的哈喇子,他们也很喜欢他,愿意让他留下来。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可以晒着太阳昏昏欲睡下去了。
——
“我”想过另一个结局,一个“你”并没有死的结局。“我”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那里学到了,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变成小说中的人物。“我”把“你”放到小说里了。小说里的“你”比现实中好色一点。“我”也把腊肠狗换成了丑角大丹犬。好的,主角并不是“你”,而是那只狗狗,陪伴“我”走出没有你在的日子的狗狗,阿波罗。
“我”把自己对“你”的思念和缅怀都写在作品里了,在《我的朋友阿波罗》里了。
《我的朋友阿波罗》读后感(四):从一只主人离世的狗身上,她看到了女性的悲伤
文/ 管舒宁
1
20世纪8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很多柬埔寨裔女性因为同样的病症去看医生:她们看不见。这些女人都是战争难民。在逃离自己的家园之前,她们中很多遭到强奸、虐待或其他残暴对待。她们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在自己面前遭到杀害。一名女子说,一些士兵带走了她丈夫和三个孩子,从此她再也没见过他们,四年来她每日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她似乎不是唯一一个哭瞎眼睛的人。还有其他人出现了视力模糊或部分视力丧失的症状,她们看东西重影而且眼睛疼痛。总共150人。检查后医生发现她们的眼睛正常。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显示,她们的脑部也正常。如果这些女人所言属实——的确有一些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女人可能是在装病卖惨,她们想获得关注,或者是希望领取政府发给残障人士的福利金——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心理原因致盲。换句话说,由于被迫经历了太多恐怖的事情,而且再也无力承受更多,这些女人便设法熄灭了自己心中的那盏灯。西格丽德·努涅斯当西格丽德·努涅斯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她不会想到2018年的秋天,她因为这部开篇具有纪实风格、上来就给人捅刀子戳泪点的小说《我的朋友阿波罗》,获得了当年美国书业最高奖——国家图书奖。
获奖时她已经67岁了。用她这本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女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变得不显眼,然后——麻烦就解决了。
女人的麻烦是什么?西格丽德·努涅斯在《我的朋友阿波罗》里反复回答这个问题:
她不可能怀着与男人同样的情绪、采取同样的举止漫步街头。她会被盯视,被评价,被猥亵。她从小就被教育要时刻保持警惕:这家伙是不是走得太近了?那家伙是不是在跟踪她?那么,她如何才能放松情绪,来体验真正的闲荡漫步的欢愉呢?嗯,购物就好,哪怕是随意浏览橱窗。她会被一个写诗的男性导师要求接受面试,这样他就能根据容貌来决定录取与否。导师会引经据典,告诉她,教室是世界上最色情的地方。《大师与门徒》里不是说过吗:‘色情,无论隐秘的还是公开的,幻想的还是付诸行动的,都与教学交织在一起。这一基本事实已经被对性骚扰的关注冲淡了。她可能还不到14岁,她也许不是在美国,但一定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她待在一个棚屋里,长长的一列男人的队伍在屋外蜿蜒,他们有的在仰望天空,有的在看报纸,总之,那种百无聊赖的神情,让人很可能以为他们是在等公交车,或者在车管所等候上牌、罚款。但,他们是在等待屋里的女孩接客。这是一张真实的新闻照片。甚至,当年同苏珊·桑塔格一同外出时,就因为往手包里多塞了几个卫生棉条,努涅斯就招来一代知识偶像困惑的眼神:女人离不开手包已经够让桑塔格嘲讽了,出门几小时,哪用得上这么多棉条?
2
1976年,努涅斯25岁。她父亲是中国和巴拿马混血,母亲来自德国,一张1/4华人血统、青春无敌的脸孔,又有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硕士的加持,当年轻的努涅斯经友人推荐,以《纽约书评》助理编辑的身份,前去给正处于癌症术后恢复期的桑塔格做助手,这位散发着异域混血气息的女文青让桑塔格母子沦陷。
她帮桑塔格打字回信,同时和其子戴维·里夫谈恋爱。几个月之后,她就搬去和他们一起住了。她和偶像的儿子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图片苏珊·桑塔格与戴维·里夫母子没有人能想象苏珊·桑塔格当婆婆的样子,但这个穿着宽松衬衫牛仔裤,脚踩胡志明人字拖的女人是个天生的导师,她把对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教育视为一种道德义务,令她无穷快乐。桑塔格以自己的文化激情和思想激情来影响周围的人,这是出了名的。作为一个梦想着成为作家的女青年,努涅斯一直把遇上桑塔格、进入一代知识分子的私人生活视为人生的幸运之一。
虽然努涅斯和里夫最终没能在一起,但她没有浪费这段岁月。假如把早年与桑塔格的交集视作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的话,努涅斯将它化作了长线投资。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她关注移民文化、跨文化交流与冲突,创作与之相关的小说,对性别与种族歧视、战争创伤、人口贩卖这类话题,有着勇敢而深刻的思考。她回归校园,在多所大学执教创意写作课。
直到十多年前,努涅斯收到了一本名为《导师、缪斯和恶魔》的文集约稿,请30位作家谈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人。努涅斯首先想到的是她的本科老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但这位受人敬重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已被两个人选走。于是,她想到了自己没有正式拜过师,但比起其他导师来更大程度改变了她人生的桑塔格。
永远的苏珊7.5西格丽德·努涅斯 / 2012 / 上海译文出版社文章问世后,一家独立出版公司找上门来,于是,历史再度启封,她得以重新完整思考这段非同寻常、人人都会将其描述为“敏感话题”的友谊。桑塔格,这位超凡不群、被人用“偶像”来称呼的传奇人物,在去世7年后,有了一本立意独特、堪称迷你的传记——《永远的苏珊》(2011),一时轰动文坛。
“别那么循规蹈矩,谁说我们就得像别人一样生活?”这是桑塔格曾经对努涅斯说过的一句话。
3
桑塔格论摄影、写疾病,上天入地激扬文字求知若渴;而努涅斯似乎更关注地上的“六便士”——那些被压迫、受侮辱的女性,包括但不限于贫穷落后地区,都市女性逼仄的生存空间、无处释放的精神压抑,都是每天睁眼闭眼挥之不去的残酷存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减除甚至局部加剧了这些疾瘤。
她通过自己的第7部小说——《我的朋友阿波罗》——构想了一个特殊的创意写作机构,或曰“写作治疗坊”,用以疗愈那些无法言说、无法启齿、无法用时间来愈合的创伤:战争之伤、拐卖之伤、性虐之伤、家暴之伤,或者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暴力伤害。
但有人认为,主持这个创意写作机构的作家企图从这些受伤的灵魂中榨取灵感——要治疗焦虑,为什么不试试涂色游戏呢?与其让她们书写自我,不如把她们虚构成小说。
永远的莉莉亚 (2002)8.22002 / 瑞典 丹麦 / 犯罪 剧情 / 鲁卡斯·穆迪森 / 奥莎娜·阿金什那 Artyom Bogucharsky无知的人觉得这些姑娘、女人可以被塑造成生动有趣的人物,她们的伤痛也可以编成离奇的都市传说。但实际上,艺术不一定比生活更震撼。在《我的朋友阿波罗》里,摩尔多瓦的性工作者们观看了一部讲述苏联少女厄运、情节几乎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的瑞典电影《永远的莉莉亚》之后,神色平静地说:真实远比这个来得更残酷。
伊萨克·迪内森相信,只要把悲伤写进故事,任何悲伤都可以忍受。也许,《走出非洲》就是她自己的写作自助。
走出非洲8.8[丹麦] 伊萨克·迪内森 / 2019 /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创意写作机构里,这些女人书写着相似的名词:刀子、皮带、绳子、酒瓶、拳头、伤疤、淤青,还有血。另外一些是相似的动词:强迫、殴打、鞭抽、火烧、窒息、挨饿、尖叫……
4
但是,在《我的朋友阿波罗》里,即便是女主人公、写作治疗师本人,身为都市知识女性的她,也是需要被拯救者。
她的导师自杀身亡后,留下的一条丑角大丹犬“阿波罗”。她勉为其难地收养了这个“温柔的巨人”。在它身上,她惊讶地发现这种被誉为“犬类中的阿波罗”的巨型犬是最好的哀悼者,她所有看得见的伤口、看不见的恐惧,它全都能嗅到。
没人跟它解释过什么是“死亡”,也没有人告诉它,它的主人永远不会回来了。它不哭泣,也不自杀,但是它真的可能会崩溃。当这条身高7英尺的庞然大物尽力蜷缩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小、浑身哆嗦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义犬博比、忠犬八公是虚构的神话故事。
这条叫“阿波罗”的大丹犬,不乱溺,不“拆迁”,担心乘电梯惊到邻居,它甚至风度全无地跟着女主人公从六楼走下来;即便是小型犬作弄它,它也完美诠释了那句“把另半张脸送上去”的教诲;它甚至没有隐私,容忍路人对它便量、尿量的围观与猜想。
大丹犬,犬类中的阿波罗,以高贵温和著称女主人公想起英国作家阿克利的小说《我的小狗郁金香》。如果一个人最重要的关系是和狗的关系,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但是阿克利充分体验了人人渴望得到、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彼此无条件”的爱。他相信,与人在情感上交融,并试图永远取悦他们,让狗狗们长期处在焦虑和紧张中。狗和其他动物对疼痛的忍耐程度比人类高。
收养了阿波罗之后,有关人类这些不说话的朋友的遭遇不断从记忆中向女主人公袭来:
在亚洲某些国家,藏獒因为人的贪婪而被过度饲养,又因为狂热过去、食耗过大而被送入屠宰场,甚至因为等不及到目的地,就在拥挤的卡车里被折磨而死。这种凶猛如狮,又以忠诚护主著称的动物,在去屠宰场的路上也许还在想:现在谁来保护主人呢?
曾参加过一战的英国作家格雷福斯这样描写索姆河战役:死马和死骡子的数目令人震惊;人的尸体也就算了,把动物拽进这样的战争,似乎是不公正的。
从柏林奥运会转战太平洋战场的美国传奇飞行员赞佩里尼回忆起二战日本战俘营,最无法摆脱的记忆是一个看守折磨一只鸭子。
坚不可摧的二战老兵赞佩里尼:宽恕酷虐,但不能释怀一只被折磨的鸭子为什么有人认为动物一定比人类遭受更大的折磨?努涅斯在这部小说里写道,她相信:
你对动物的怜悯程度与该动物引起你对自己的怜悯程度有关。人,终其一生记着早年的时光,那时,我们一半是动物一般是人,无助、脆弱,还有无言的恐惧,对保护充满渴望。如果我们能大声喊出来,该多好。纯真时光是我们人类经历过但无法回去的东西,但动物终其一生都是这个状态。有人会把这种多愁善感称为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但等到哪天我们不再有能力去感受,对每个活着的人而言都将是可怕的一天,我们滑向暴力和野蛮的速度也会更快。至此,关于人类与他的朋友——动物之被压迫、被侮辱,被解救与被疗愈,努涅斯完成了一种互化。
由此——
“阻止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厌世者,是看到了狗对人类的爱。”
甚至——
“养一条狗代替丈夫,是否胜过一个狗一样的丈夫?”
但,更愿意——
“不想让它成为我的保镖,成为一杆枪,我要让它情绪冷静,成为我的‘快乐狗先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要把笔墨留给这个世界的那些受害者,那些经历了恐怖,却从没人倾听又最终被人遗忘的人。
努涅斯《我的朋友阿波罗》,用卑微故事,奏出最强音。
2018年11月,当努涅斯接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证书,她就与索尔·贝娄、福克纳、厄普代克等一长串闪耀的名字一起,被写进了美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她的导师桑塔格(小说《在美国》)获得这个奖相距18年,那年,桑塔格恰好也是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