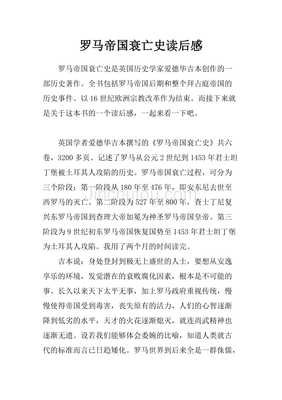植物与帝国读后感100字
《植物与帝国》是一本由隆达•施宾格著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358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2020-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一):植物与权利
植物本应是自然的财产,也是自由的存在,但是,人类在生活和历史中却为植物贴上了“占有”的“标签”,选择某些标签可能出于归类,而有些则反映出贴标者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倾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越俎代庖”地删除或忽视植物的“原住名”和“原住用途”,而为其冠以各种出于私人目的的名字。公平来说,这就是在侵犯植物的权利。
植物也有权利吗?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它们的所有特点应该被完整展现,而非被选择性地呈现、理解,更不应该被误读、误解,这是自然赋予它们的权利。然而,植物同许多生物一样,在人类的话语体系中无法发声,它们只能通过科学的公正偶尔“表达”自己,伸张权利。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隆达•施宾格的《植物与帝国》一书是为植物发声的渠道之一,通过调查原始细节和溯源,为我们尽力呈现植物学世界的本来面貌。
地理大发现时代也是生物大“发现”的时代,虽然那些存在于西方探索者视线之外的生物早就被当地人所识、所用,但是就和新大陆明明早已存在和有人类定居一样,被纳入西方文明系统之中才是西方世界认可的存在。具体到西方探索者“发现”植物的过程,西方人所为带着强烈的殖民和帝国色彩。
首先,驱动他们探寻和搜集非西方植物的动力少数才是出于对科学的好奇,而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力量,所以,在逐利的背景下,对植物的认知就难免简单粗暴——西方的植物“发现者”和收集者的首要目的是寻找“有用”的植物,而且于这些有用的植物中还着重关注商业方面的用途,缺乏对其全面认识;其次,对非西方植物的命名和分类则充满了“逐名”的做法,西方发现者们往往抛弃和忽略当地人对植物的称谓,而冠之以各种关系人的姓名,或者单纯出于自己的偏见而命名,被沿用的现代植物学命名方法——双名法,就带着明显的“留名”目的和不自觉的“傲慢”——双名法中不仅有创立者卡尔·林奈的姓氏“L”的永久印记,还给所有发现者“指明”了留名的途径和方法,而且从根本上说,双名法采用拉丁语系的做法就是帝国时代的特权痕迹,这让西方学者比亚洲等处于不同语系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植物学的研究中。
在西方价值和话语体系下,对植物世界的认知不仅产生了本土学者在学术系统中成为“故土陌生人”的尴尬,还造成了人类智力的浪费。植物原生地的原著民往往对其认识更深刻也更全面,但西方殖民者并不习惯让“野蛮人”左右自己的认知,以及进入自己的认知系统并且留名,不屑于从后者的世界里学习其祖祖辈辈通过实践得来的知识,因为若要如此,他们就不仅要学习“野蛮人”的语言和文明;即便他们愿意学习或者偶然习得,也更倾向于将自己作为冠冕堂皇的“发现者”,而那些教授者则被从西方人的荣誉中悄然抹去了,在《植物与帝国》中,施宾格提到,她在遍寻植物学命名的历史中发现,在苦木的学名(Picrasma quassioides (D. Don) Benn.)命名中,夸西(Quassi)是唯一得以留名的奴隶,而且这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西方化。
而且,即便是在西方的发现者中,偏见和歧视也一直存在。女性植物发现者的作用往往被学术界忽略,她们的发现和命名也容易被同行窃取和掩盖,即便是林奈也吝惜在学术著作中对女性博物学家和发现者的提及、引用,比如德国的博物学家玛丽亚·梅里安,她不仅是较早进行环球旅行和探索的女性,还在发现多种植物上功不可没,然而,林奈依然对其功绩依然惜字如金。实际上,甚至梅里安的环球旅行都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才得以实现,并且岌岌可危,因为在西方的迷信乃至当时的法律中,载有女性的船只常被厄运笼罩。很显然,女性植物学家的学术权利如同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利一样,都被侵犯了,她们在那些男性主导的时代比“野蛮的原住民”和奴隶的境遇和话语权略好,但也只是略好而已。
仔细阅读《植物与帝国》的读者可以发现,施宾格教授对女性、“新世界”的原始居民、奴隶等在帝国时代中的弱势群体有专门的关注和论述,为他们把被殖民、帝国、男权等霸权力量窃取豪夺的权利公布出来。施宾格教授不仅致力于扫除对植物的偏见,还植物以完整的权利,还恢复了在植物研究进程中被有意边缘化的人的权利。她的观察视角是纠正错误的重要举措,也是对植物学研究和科学史的重要补充。消除片面,还原全面,科学本应如此。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二):殖民地里的植物学家
能否为殖民地创造价值,是评价一切的标准。
1914年,“阿拉伯的劳伦斯”装作不经意间,在沙漠里邂逅了正在进行圣地旅行的两个美国人,他当然知道他们究竟为何而来:石油。
这不是帝国第一次派人前往海外探寻所需的资源,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自第一个殖民地建立之后,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地以各种名义向外输出,或是政府组织,或是贸易公司负责,又或是私人赞助,以期这些人为帝国的远征铺平道路,带着各种物品和知识回国效力。在回溯18世纪殖民扩张的这段历史时,《植物与帝国》一书里的主角,植物学家自然也是“帝国的代理人”之一。
这些这些植物学家(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博物学家)的初衷恰与帝国的需求不谋而合。一方面,他们以科学探险为名,实则寻求商业利益。作者隆达·施宾格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重点提及了斯隆、梅里安、梅农维尔、菲塞-奥布莱等多位植物学家,他们远赴他乡主要是为了寻找奎宁等新药物(斯隆)、丝绸(梅里安)、胭脂虫(梅农维尔),在当地找到标准药物的本地替代品(菲塞-奥布莱)。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庞大的帝国正需要植物学家的知识,为殖民者实现从食物到药物等多方面的自给自足。至于测绘当地河流水道等任务,也落到了这些人的肩上。“外来植物成为一种交换资本”——帝国殖民者与植物学家各取所需。
在研究生物勘探的过程中,身为女性主义科学史家的施宾格敏锐地注意到了一个令学界难堪的问题:在殖民地各种资源被疯狂攫取的同时,为何只有避孕药的相关知识没能传回欧洲,造福女性?在殖民地,奴隶承担了殖民者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双重压迫:劳动力和性工具;生而为奴,在绝望的处境中,奴隶用拒绝结婚生子作为反抗,堕胎药是他们仅剩的武器,堕胎成了一种政治反抗形式。而在西方强权国家,在殖民帝国崛起与扩张的大背景下,人口成了与土地、制造业、海外贸易并重的经济核心。无论是殖民地的繁荣,还是重商主义政府,都需要不断增加的人口,才能“扩大国家财富”。因此,无论是本国,还是殖民地,女性的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变成了一种繁殖工具,“一项国家财富”。施宾格因此认为,同样是帝国的需求,导致了金凤花等殖民地的堕胎药一直没能像金鸡纳树那样,进入欧洲医学体系。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施宾格谈到语言霸权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对新物种的命名中。在以拉丁语为标准用语的命名过程中,植物的用途、地理分布、文化意义和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发现者、政治人物的名字。卡尔·林奈的命名过程,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堪称欧洲精英在科学界里的再一次殖民;正如洪堡所言,“优先使用一种语言而不说另一种语言时……隐含着权力关系在里面”。
《植物与帝国》是一本非常扎实的史学著作,隆达·施宾格从无知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殖民地的生物勘探情况,选取了一种很容易被忽略掉的药物:堕胎药,回答了“为什么被忽略”的问题。在这背后,是帝国与植物学家的合作与博弈,更是殖民地的血泪抗争史。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三):植物旅行:后殖民视野下的博物学与性别
在西方科技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往往被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所遮蔽,植物在这种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更长期被轻视。在新近面世的译著《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中,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通过追溯和研究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
■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前不久,四川大学姜虹送我一本她新译的著作——《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并在扉页上亲绘了一幅金凤花与毛毛虫的钢笔画赠予我,十分惊艳,令我感动。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熟悉的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施宾格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西方解剖学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对女性主义科学元勘(feminist science studies)的目的、实践与意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让人印象深刻。她后来还主持了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提出了性别化创新(gendered innovation)概念,是一位在学术界和科技政策界都有影响力的学者。
鉴于姜虹的博物学和科学哲学背景,以及她之前对博物学女性的特殊关注,由她来翻译《植物与帝国》实在是非常合适。她所受的哲学和性别研究方面的训练,也使得她对该书的翻译十分精准到位。更难得的是,她的译文十分流畅,读起来很舒服。
从植物的角度揭示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发生在欧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植物旅行故事。
以往,关于17-18世纪西方科技史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中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关注那些伟大发现和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科技史画卷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在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中往往被遮蔽。女性主义学术注意考察科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关心历史上身处科学共同体边缘的女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及其价值。比较而言,植物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却长期被轻视了。
施宾格想要追溯和研究的便是植物的故事,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施宾格将目光聚焦到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来自宗主国的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每天都能观察到不同于欧洲的植物,了解到与这些植物相关的丰富知识,他们的任务便是对这些植物进行采集、调查、引种、分类、命名以及提供医药试验,尽可能地把它们纳入欧洲既有的知识框架和政治秩序之中,增加并巩固帝国的财富和利益。
这一过程不只是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同时也是商业贸易、奴隶交易、殖民扩张的现实故事。这些植物学探索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科学家或医生,还充当了帝国的代理人。无论是旅行博物学家、远航的植物学助手还是在欧洲足不出户的植物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18世纪庞大的全球植物交易网络中的积极分子,是欧洲“科学-殖民机器”的代言人。可以说,施宾格从植物的角度,揭示了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知识传播的利益博弈与金凤花的性别政治意涵
不仅如此,在西印度群岛上,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以及来自英、法、西班牙、荷兰等宗主国的殖民者在共同的时空中相遇,不同势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
生物勘探与生物偷盗并存,博物学家的故事充满了惊险刺激的男性英雄色彩。在所谓的“生物接触地带”,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之间充满了策略、猎取和抗争。语言障碍、侵略造成的敌对以及欧洲人自身的认知局限,导致植物知识的传播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知识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欧洲人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采集新的植物标本以满足经济上、医学上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本土的文化认知框架,这些殖民博物学家们很难去真正理解、认可并传播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理解自然世界的方式和他们所构建的自然秩序。
金凤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8世纪,美丽的金凤花开遍了欧洲的植物园,但它的流产功能既没有出现在各类药典中,也没有在医药实验中得以验证,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原因何在?施宾格认为正是17-18世纪欧洲的生育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造成了这种无知。虽然19世纪之前的欧洲,孕早期流产仍不违法,但也并不被赞许,只能秘密进行,人们因此很难就殖民地流产药物的使用与安全性问题做公开讨论。并且,这一时期欧洲的分娩实践逐渐从助产士让渡到男性产科医师手中,产科手术而非安全的流产药物成为欧洲医学共同体优先考虑的主题。再加上,当时的欧洲将确切的自然知识视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霸权地位的关键,人口众多是国家财富和王权荣耀乃至帝国的命脉。在此背景下,欧洲的植物探索者、贸易公司、科学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不可能有兴趣去传播殖民地的流产药物及其知识。换言之,欧洲的生育观念、性别文化、科学观念和政治经济导向共同造就了欧洲人对金凤花流产知识的无知,使得19世纪的大部分欧洲妇女逐渐失去了对生育的控制权。
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带来的系统性无知
不仅如此,系统性无知的出现还源于更深层次的认知结构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林奈在对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时将医药用途、生物地理分布和文化意义之类的信息与植物完全剥离,只留下抽象的拉丁文名称。他以著名的欧洲人尤其是植物学家的名字为全世界的植物命名,并在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霸权处于顶峰之际获得完全的认可,由此强化了科学由杰出个人创造的观念,刻画并巩固了欧洲精英男性植物学的光辉历史。其实质和结果如同施宾格所言,18世纪的植物命名法是帝国的一项工具,将植物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里。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欧洲命名体系随之发展起来,将世界原本多样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质统统吞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18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霸权与认知立场造成了它对其他本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无知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取得普遍性的地位,而造成了非西方世界对自身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或自我贬抑,最终不利于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四):植物的考察与帝国的凝视:博物学家如何“征服”世界的隐秘角落
在记述殖民地生物调查时,多将博物学史视作“剥削脂膏”的资源控御。不过,单从经济搜刮视野检视殖民地生物调查,无疑是以偏概全——殖民地生物调查,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工具化”资源攫取,它有着更多元的权力展示。
撰稿 | 邹赜韬
蒋竹山先生主编的“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最近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本书作者隆达·史宾格(Londa Schiebinger),是斯坦福大学科学史约翰·辛兹讲席教授。她聚焦“女性与科学”的《自然之体:现代科学形成中的性别问题》、《骷髅之战:“她”的科学史》等著述,在科技史、女性研究领域曾激起不小思想涟漪。此次译出的《植物与帝国》系2007年“旧作”,但其对于蒸蒸日上,却缺少“政治史”内涵的博物学“中国思考”而言,着实是可贵的“导引”文献。
《植物与帝国》,顺畅地将难计其数的博物学史“碎片”系于“权力”这一轴线上,既展示嘉木良药的“空间挪移”、“知识产出”(博物学之“果”),又力透史录纸背,清晰披露了西方博物学与其研究对象致密往来的互动之“姻”,最终落脚至博物学的“因”——博物学不单考索“植物”,它还是“帝国”的凝视。几百年间,博物学家迈出欧陆门槛,跨进一处又一处西方世界的“隐蔽角落”。不过,无论是何等“僻远”的角隅,博物学实践的权力本色始终不曾泯灭。若怀着对“权力”的好奇,与史宾格共同思考“植物与帝国”,我们对博物学“多识鸟兽草木”的“名词化”成见,或可得到一全面再造。
「是“殖民工具”,更是“帝国标志”」
博物学史在记述殖民地生物调查时,多将之视作“剥削脂膏”的资源控御。《植物与帝国》对此说持肯定意见。在评价17世纪巴黎皇家药用植物园时,史宾格认定,该植物园其实是法国为削减贵重商品贸易逆差而进行的“生物盗窃”,“将自然资源从边缘聚集到中心,对法国殖民地的物质和智力资源进行中央集权化管理”。不过,单从经济搜刮视野检视殖民地生物调查,无疑是以偏概全——殖民地生物调查,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工具化”资源攫取,它有着更多元的权力展示。就此,《植物与帝国》贡献了两方面精彩解析。
首先,《植物与帝国》呈现了欧洲博物学家在殖民地“奴役地”开展活动之事实:“文雅的欧洲绅士不习惯弄脏自己双手去干体力活,殖民者与本地人主仆关系的建立让欧洲人在热带地区过度依赖他们的向导。”政治科学对“殖民”有一条非常关键的定义:掠夺和奴役当地人。由此,欧洲博物学家在殖民地,基于主仆关系,驱使深谙地方资源的本地人为宗主国采集奇珍异草,实质上构成了持续的“帝国权力宣示”。
其次,《植物与帝国》复现了一类普遍存在于17、18世纪殖民地博物学活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殖民者“从被征服的欧洲人那里获取了大量知识,他们依靠这些知识才得以在热带生存”,而与此同时,“生物接触地带”(史宾格语)的欧洲人又难以含括“截然不同的新知识”,总在试图将自成体系的新大陆植物药强硬塞入“体液学说”作呆板理解。这重既“有求”又“有嫌”殖民地的矛盾心态,形象地表露了殖民地博物学活动的“帝国文化”——一切科学活动均被安置在权威与“层析”铸造的外壳内,其存在就是为了“确证帝国、宣威帝国、巩固帝国”。
此处荡开一笔。在《植物与帝国》着墨不多的18世纪中后期,博物调查最终由“野趣”彻底升格为帝国治理的有机组成。李猛博士提出:自约瑟夫·班克斯“掌舵”起,“科学探险活动与启迪民智、富国强兵的国家启蒙策略联系在一起”(《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第37页)。可见,《植物与帝国》所再现的“帝国标志”,在威权形象渲染之上,亦涵蕴着“帝国科学”走向“科学帝国”的权力符码。假使将《植物与帝国》叙述的若干“帝国表演”比作连续“地震”,辄其下“权力岩浆”最终推动的,是18世纪往后博物科学熔铸入殖民帝国的“板块漂移”。其间,“涓流”变“汪洋”的权力枢纽,值得我们继续玩味。
隆达·施宾格,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学史家,著有《奴隶的秘密疗法: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人、植物与医药》、《女性主义改变了科学吗?》、《自然之体:现代科学发展中的性别》、《心智无性别吗?现代科学起源中的女性》,其著作被译成德、日、韩、西等多种语言。「回归“地理中心”,忆起既有博物学史叙事的“边缘”」
近代博物学在殖民地的活动,是对“地理边缘”的发掘,是将资源、技术、文化“边缘”拉入“西方秩序”的向心过程。不过,在当时全球政治经济“地理中心”欧洲,也曾出现过一批意涵丰富的博物学“边缘”故事。《植物与帝国》就点亮了许多博物学发展史的欧洲“灰色”片段。这里择其尤为精彩者略作展示。
其一,纵使博物学成果多被包装成“某大师杰作”,但似乎在该学科发展史上,后世仰视的“大师”们只是“知识掮客”,“躬耕于野”者另有人在。《植物与帝国》道出了林奈的“算盘”:他培养并派驻海外的学生们“就像分散在全球的大使”,辛勤为业师搜罗各处珍奇异宝,让“博物学家们在欧洲的家中就可以远距离‘看到’这一切。”煌煌博物学成果,至少有一半出自“边缘”的“无名”学生?!其间权力运作,着实令人讶异。
其二,在近代博物学史上,也曾出现过“巾帼英雄”。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女性博物学家不单在开展研究时饱受性别歧视、禁锢,其顶着双重压力完成的研究成果,亦随时会被性别歧视从“功勋榜”上抹去。《植物与帝国》告诉我们:早至1689年,法国皇家海军就已明令禁止“女性除短暂造访外以任何形式登船”。但在1766到1769年环球探险队里,女子珍妮·巴雷特还是乔装成科默森的男仆,踏上了前往遥远异乡的博物学之旅。此次探险之旅,巴雷特自主采集了大批珍贵植物、昆虫、贝壳标本,同行船员对其收获啧啧赞叹。即便如此,在18世纪博物学结构性束缚之下,巴雷特依旧无法“正名”——保护其完成本次探险的科默森,曾提出以“巴雷特”冠名某种新见楝科植物,谁料“后来植物学家觉得她身份低微,将该属重新命名为杜楝属”。
其三,一如后世反复提及的“殖民地人体实验”,殖民地医生、博物学家在向欧洲输送“新药”时,也曾招徕贫苦患者,利用其救命心切的“弱点”试验毒理、药效尚不明朗的危险药剂。《植物与帝国》提到,维也纳的斯托克医生为测试毒堇的“抗癌”药效,在多位出身低微的乳腺癌老妇身上做人体试验。其中一位清寒的七十余岁水果小贩,在治疗无效去世时未得到后事料理,反而“被切下乳房,带到大学给教授们检查”。而面对凄惨离世老妇的身体标本,医学教授们非但丝毫没有表达任何哀悼,甚至还抱怨“(她的)意外死亡阻挠了实验的成功进展”。此情此景,今天看来,可谓触目惊心,却是那时站在“权力上风口”的欧洲博物学家、新药“发明家”所习以为常的。从这一视角品读,近代西方博物学发展,又何尝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阶级压迫血泪史”?
「帝国语言:“鸟兽草木之名”的权力意志」
在《植物与帝国》里,史宾格自金凤花名称演化提炼出“名字帝国主义”(onomastic imperialism)这一概念。她认为,“名字帝国主义”于18世纪取代了前一个百年间“融合多种文化的各种命名方式”——在“复杂政治”作用下,金凤花的“美洲本土名字”被选择性遗忘,朝着拉丁词汇“flos pavonis”独霸的方向愈行愈远。既往读到的博物学史著述,大多只紧盯“博物发现”,对“博物命名”及其权力机制言说有限。《植物与帝国》掐住语言“线头”,在“鸟兽草木之名”与“帝国”间穿引起一张意义网络。
在史宾格看来,“名字帝国主义”实践的起点未必“晦暗”,其基本目标是“将植物从本土文化语境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最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简言之,就是让“知识爆炸”时代的欧洲人通畅地理解、记忆异域知识。然而,“由多入一”的命名管理,很快便从名词技术蜕变为“帝国话语”,开始标榜基于“欧洲优越性”的“帝国权威”。
在《植物与帝国》中,有一生动案例:在林奈等人坚持下,作为“养胃滋补药”引入欧洲的苏里南苦木,最终以获释奴隶戈拉曼·戈塞命名。起初,戈塞的血统,无法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欧洲博物学的闪光符号——“没有人会考虑以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的名字命名植物,就算这种植物的用途好像是他发现的。”戈塞能跳脱歧视束缚,成为18世纪欧洲博物学历史的罕见“特例”,关键还在于专业之外——方方面面“入乡随俗,遵从欧洲方式”。而对另一激进猜想,史宾格含蓄地表达了认同:“与发现苦药同样重要的是,戈塞为荷兰殖民者的部队效力,帮他们镇压了自己民族的叛乱,最终才在欧洲的植物命名体系中获得了不朽的勋章。”
功勋卓然的“本土”博物发现者,必须接受“帝国代理人”审查,且假若其未曾“背叛”原族群去效忠入侵者、略带戏谑感地“成为欧洲人”,辄其名字只能被“帝国代理人”的不屑一顾所湮没。由此可见,18世纪左右欧洲博物学体系的“鸟兽草木之名”,从来不是单纯的知识信息——那是帝国威权怀着野心,刻划在知识“纪念碑”上的暴力痕迹。
《植物与帝国》以植物学为例,讲述了近代科技发展史的“无知学”本色——“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某些知识得到开发,另一些知识却被湮没。”人既是记忆的生灵,也是健忘的动物。我们常常站在“后来者”的高傲视角,冲动地赞美“我们传承(记住)了进步的科学”。然而,那些“被遗忘”科学、“被遗忘”发现者,真的全然是为“进化论”所淘汰吗?科学,也许永远存在盲区;但权力,每时每刻都在入侵着“隐蔽的角落”。
邹赜韬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原文标题为“权力不曾隐蔽的角落”。
<燕京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