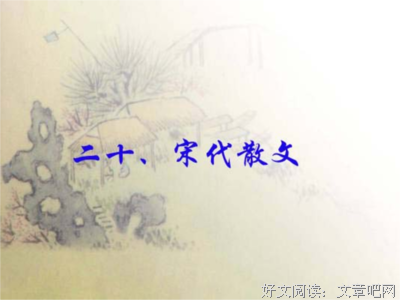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读后感锦集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是一本由朱刚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4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精选点评:
●对二苏事迹的考辨细致严谨,对二苏行止的回护我所不能及,至于苏辙梦荆公使“赧然有愧恨之色”事,书中解释甚圆融,疑读者不能尽知,愿稍增言之:原文“……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得饱满,余人皆不悦。已矣勿复言,人人好颜色。”可知苏辙并非针对荆公生前推行的新法,而是苏辙自述“文章自一家”,有感于徽宗朝万马齐喑,只有新学一枝独秀的场面。 然而书中对儒学史的阐述则未免有不周全之处,至于对唐宋变革论、士人地方化理论运用的批评已为人所发,不必多论。
●好看!优秀!
●珠玉联翩,高潮从头至尾,这本书再次证明吹zgbb是有充足理由的。我只在历时层面讲一点,朱老师从博论《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到这本书,接续了“文学-文化”的框架,确定“士大夫文学”作为考察古文运动的视阈,因而在具体个案的研究深入(对比两书有关杨亿的部分)基础上实现了高屋建瓴的把握。朱老师此书已经完成了把“文学”还给“文化”“社会”的重大工作,尤其是对引人注目但一直难以解释的古文运动“中熄”阶段做了非常好的处理。朱老师的文字功底极好,用语不“自我作古”,只是平实地展开,很好读。一句话:都给我读!对古代文学没兴趣也要读!
●很难看到这么精彩的文学史著作,非常有逻辑的argument,有观点,有论证,有视野,对于你国本土文学史学者来说简直是奢侈品。可惜最末一篇偷懒采自演讲,实在浮光掠影、简单重复;很多篇修改自论文(同样精彩)自然可以理解,但论著向心力也较弱,对于“政治化”和“学术化”的士大夫文学似还缺一章全面的论述,其实这也才是本书的实际论题~第二章概念辨析读得实在头疼…
●很好
●有些部分好像是凑字数的感觉。。。因为自己也写这一段的论文所以经常会会心一笑啊。与科举相关的部分有启发。
●一、从各部分研究综述来看,文学史界的整体问题意识比较滞后,对相关学科的理解很是肤廓,应该多去翻刊物。二、语境化的多元尝试,重看古文运动中被遮蔽的群体和文人身份带来的具体紧张,比较独到,但缺乏文学文本的分析,可以说非常不“文学”。三、结语潦草充数,和前文不相吻合,这不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所能容忍的事。四、一堆四库本看得我尬癌发作。五、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读其文而不知作者为谁也不成问题,其实我比较向往神交,评价一本书也尽可以糊名。
●很快翻了一遍,將文學史的研究放到了具體的歷史中,是真正的歷史的研究,寫得很好。之所以沒有仔細看,實在是因為最近事太多,只能匆匆瀏覽一遍了。說實話,現在確實也很少仔細看現代人的研究了,能吸引人且有價值者並不多,往往只需瀏覽一遍就够了。與此相應得是,原典的價值及可玩味處更多,但相比於對研究論著,我的原典修養卻相當不足,以後應該多看原典,以為補課。
●只是一涉義理的領域,就稚嫩粗疏了,不過在中文系應該算不錯了。
●极精彩。读此书,时而击节赞叹,时而会心一笑,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大都枯槁,如此有趣有味有料的可谓凤毛麟角。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读后感(一):笔记: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读后感(二):閒來翻書: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
“古文運動”之名提出以來,研究者輻輳,成果蔚為大觀,至今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然時至今日,如何跳出以往研究的桎梏,開拓思路,實為難而必爲之事。本書在詳細檢討研究史的基礎之上,不劃地為牢地限於“文學史”學科的研究範式,而將文學史置於思想史視野之中,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將“古文運動”界定在“士大夫文學”的範圍內,尤其強調的是古文作家的身份。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不同於唐以前的貴族士大夫,出身於科舉,失去了家族的依託,而以學問爲立身之本,士大夫的自我定位與認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最主要的特色乃是大多經由科舉而進入政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科舉是界定士大夫身份的社會體制,任何想要成為士大夫的讀書人都需要在科舉考試中顯示自己的能力。於是,文章的意義就不簡單的是一種“文學”寫作,而成為士大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本書主體部份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即分別從內在心態的轉變與外在制度的塑造兩方面討論宋代士大夫文學的特色。在後一方面,作者特別考察了宋代制科的進卷,發現了其中的內在結構,於是將其視爲獨立的著作,無疑是十分精到的見解。
對於“太學體”,以往研究皆從文體著眼,作者則獨具慧眼,結合嘉祐時期的太學學風、思想潮流,指出“太學體”實際上並不能在文章風格的“險怪”上簡單理解,而應注意繼歐公而起的後繼者在“性命之學”上對早期古文家的超越,注意作家的個性風貌及在時人眼中的形象。由此出發,作者勾勒出了另一條“怪文”的系譜,提醒研究者注意,自韓愈到歐陽修之間,五代宋初的隱士、慶曆之際學統四起的諸“先生”,是中唐古文運動的直接繼承者,也是韓、歐的中間環節;而且,正是由於其“險怪”,才使古文運動於在野之時顯示其活力而能不絕如縷。更進一步,由於這種“險怪”與學術思想相關聯,而北宋後期王安石一派的經義時文更居於主流地位,則險怪之古文與歐蘇平易流暢之古文之間,已經蘊含著後來道學與文學的所謂“歐蘇、周程之裂”的種子。這樣一條線索,發前人所未發,極具啓發性。
在作者的筆下,這樣的線索似乎是自韓愈而降,到了歐陽修的時代,在慶曆士大夫中才開始分裂的。從唐代“古文運動”之興起來看,已然具有不同的傾向。尤其是自韓愈而降,或學其平易處而深於性理如李翱,或得其奇崛而爲皇甫湜、衍而爲來無擇、爲孫樵、爲劉蛻。即在唐時之古文已蘊二派。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則指出,宋朝早期的“古文運動”“大都是皇甫湜一派,所以柳開穆修的文章,都不免偏於晦澀,而到宋祁爲尤甚。”而至歐陽修倡平易流觴之古文,“恐怕他學韓愈是從李翱入手,不從皇甫湜一派入手的緣故”。是宋世爲古文者亦分為兩派。尤有可論者,歐公之平易若自李翱入手,而李則較皇甫、孫、劉等偏於內在心性之探討,則宋之兩派,其趨向實與唐時相反。即作者所謂“險怪”之古文偏於道學,文風上近於唐之“詞勝理”者;平易之古文偏於“文學”,而近於唐之“理勝詞”者。其中之轉折、變異,不知更有何故?
又宋之古文,於三蘇雖已達於頂峰,奠定後世古文之基調,然世亦未盡從之。如鄭樵之文,《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滉漾恣肆,多類唐李觀、孫樵、劉蛻,在宋人爲別調”,則“險怪”之風亦自有其傳人。韓、李、歐、蘇自是大宗,而小宗亦不絕如縷。置於歷史之中,未可全不措意。在近年西昆體逐漸受到重視的局面下,“古文運動”的另一面也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2013年5月31日草成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读后感(三):新宋学还刚刚开始吧
新宋学研究的重镇本在复旦,尤其是经由王水照先生对陈寅恪的新宋学进行一番阐发之后,宋代文学研究也可以以“新宋学”这一观念为据,在文体研究的领域以外开拓一些空间。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宋代职官研究、理学的研究、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这几个方面,宋代文学研究都在逐渐涉及。《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这部书也是在这个大的方向下写作的。之前在一些学术期刊上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近年来的研究方向都倾向于北宋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时期。关键的问题,如宋代的太学、以王安石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为分界的宋代政治改革,都有所述及。复旦所出的六人文集是日本学者的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东英寿的研究(包括欧阳修的九十六封书简)也提供了一些便利和视角。只是日本学者对宋代的理解,初读之下感觉新鲜,但仔细一看,整体思路太过于“整齐”——也就是内藤湖南等人所谓的唐宋变革说和中国中世史的观点,这套理论对日本学者的影响太深入骨髓了,以致常给我这种读中国书的人一种隔膜之感。所以,中国学者自己书写的对宋代的理解,我还是非常期待的。而且读完之后,也可以说不算失望,虽然确实因为“内容”多而显得不够“整齐”,但对自己的历史的感知,很多方面直觉上的感觉甚至好过逻辑上的推论。
第一章《“古文运动”与“文以载道”》,第二章《“古文运动”与“新儒学”的进展》的结构和论述,应该说是整齐的。而且做为北宋“古文运动”的理论依据,这两章不能说不精彩。但是我在阅读之后,反而对第三章《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上):思想心态》和第五章《晚年苏辙与“古文运动”的终结》更感兴趣。这是因为这部书确实有很多闪光点,但在较为严密的总纲论述中,“唐宋变革论”基本上一直在统领文章思路,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又不得不落入到一贯的文体研究的习惯里。后者的习惯,我想可能是深藏在所有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思路里的,而且唐宋文学尤其有这个传统。所以无论在哪种习惯之下,论述的闪光点也会很快被惯性思维给遮蔽了。当然,比如在谈到太学体这个问题时,作者确实有跳出旧有批评史思维之处。“古文”这个说法会让人习惯性地把欧阳修反对的太学体理解成与古文相对立的一种文体。甚至会认为太学体就是受西昆体影响的。(电视剧《苏东坡》在讲述太学生“太学体”与三苏、曾巩等人的“古文”时,就想当然地把太学体理解成只会声律对偶。)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文体问题上,并没有像后世理解的那么绝对。“古文”这个名称笼罩下的宋代士大夫,基本上不可能不会写一些骈文。古文与骈文的对立在宋初(太祖太宗到真宗三朝)应该说确实存在,尤其是以南方籍贯的朝中词臣与北方在野的古文家的对立最为显著。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仁宗朝确实已经大为改变了。对“太学体”险怪文风的分析,也着力于分析太学生的行文方式与他们的论理倾向有关系。太学生的写作(主要二程为例)是在试图找到更深刻的表达思想的方式。把思想史的视角引入到文体研究中,就使欧阳修与太学生的对立从“文风”的不同标准转移到了两代人不同风起之间的对立。这一点确实对文学研究是有启发的。近几年对学术史、经学的关注,也使宋代文学研究和经学联系起来。这一点在书中也有体现。因为北宋所出的文章大家,在政坛上、文坛上确立地位的同时,也是需要在经术上有著作的。特别是在北宋中期学派鼎立的局面形成以后,老师著书,学生撰写、为师门吆喝的风气也是日益强烈。这些历史事实也确定了文学家不可能不与经学产生联系。尤其是古文作家,各个时期有影响的人物不但有对经书的阐发著作(或是后学所记载的语录),还往往是有讲学经历的。作者在描述北宋经学对文学的影响时,一直在把握从中晚唐到宋代的经学变化的谱系。“谱系”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在第一、第二章的文字中。尤其是注意到了春秋学在这条谱系上不一般的作用。并且,对宋代人来说,他们对尊王统这件事特别重视。凡是要论及道统的文章,其论理的依据往往都是来源于公羊学。唐代经学(春秋学)到宋代的发展谱系,大概就是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集传纂例》中的尊“夏道”、复尧舜到柳宗元的尊尧、舜、法先王再到韩愈的尊孔子,发展到宋初分成两路,一路好险怪、师法子书,一类尊经讲究大义。但宋代无论哪种古文思想,总体上都遵循尊王道、尊孔子的路径;尊孔尊经,这是从欧阳修、苏门弟子基本上遵循的路;法上古三代帝王,言尧舜而已,这是古文经学方面的王安石的路径。二者虽然具体做法不一样,但尊经方面主要是时代先后的问题。科举考试对学术和文学的影响也固然存在,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好为什么从唐代开始就已经确立了的考试内容,为什么在历史进程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相反这些经学观点的变化,一开始都是在无法通过考试进身的寒门士子中发生的。一旦有师事之心的人考上了进士,往往也会试图提携这些人。作者当从士大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所谓“士大夫”的形象的塑造,从中唐韩愈开始,确实有一些人是有意而为之的。宋代对这个问题也确实重视,寇准、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种士范的缘故,在党争中对这些大臣的私德批评也最为苛刻。
经学、科举、思想史、党争,这几个宋代文史研究中问题比较多的视角,作者在论述北宋“古文运动”时都运用了。也正是因为这几个视角涉及的北宋政治、文化的层面确实太多,而且互相都盘根错节,有些章节会更像是尚未完成的论文。同时,这几个视角也是传统宋史研究入门的途径。特别是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沿革。对欧阳修这个人物,作者的一个看法是欧苏弟子与周程之学二者的分裂,认为这是北宋初期的“文道合一”走向文道分裂的标志。这一点可能也是受到唐宋变革说的影响。近世史在学术史上的观点就表现为宋代是近代学术分科的时代。确实,宋代中期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而且往往是学派之间的对立。但是如果具体看当时学者著述,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不绝对。北宋出现的博学大家,往往都是史馆修撰。编修史书、丛书的经验,本身对塑造博学的士大夫尤为便利。道学一途,如果没有中期进士出身的古文家大力从民间推荐老师进入太学讲学,其实也不可能在京师中形成风气。两者之间,有相互成就的关系。固然,欧苏弟子讲道功夫不能称之为精微。但是,对论这一体例,他们也一样重视。其实所有浸淫在史官文化里的人不可能不重视论。对两宋之际的学者心态,如刘子健也写过文章描述,大体上也确实有所谓“转向内在”的变化。但是这种分殊应该更晚。总体来说,没有哪个时代像宋代这样重视文,遑论重视史。文学与道学,相对来说还是《宋史》那样的分类法,两方也许对如何表达想法、怎么想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绝对的割裂应该是不至于,也不可能的。
最喜欢的一章还是第五章,因为苏辙的《诗集传》的缘故。苏辙的议论很有趣,而在训释方面又很尊经。苏辙对经的态度比他的老师欧阳修还要尊重。他的议论又自成一套,史论方面是他擅长的。从文道合一的古文运动缘起,到苏辙晚年隐居,古文运动退场,中唐到北宋中期整个古文的脉络也就完成了。
题外话,对唐宋变革论这个提法,因为自己也在写论文,已经越来越感到这个说法对思维的限制其实非常严重。固然,唐宋之际是学术、文化、文学的分水岭,这个判断大体上无论日本还是国内已有的史学论述对此都没有太大异议。但唐宋变革论把整个中国历史切开变成两部分,其实也导致一个问题:在具体读材料读史料的过程里,会在这个思维的限制下有意识地不去顾及一些材料。“新宋学”这个提法,如果只是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之中阐发,恐怕还是很难深入进去。相对来说为什么反而是旧有的制度史研究反而能够将一个问题说得深,做得透,并且能够真正形成一套方法,可能也是因为有时候研究一个对象,介入了太多变化的因素和方法,反而是不能见全局的。所以在阅读过程中,也常常会有论述未能悉数展开的印象。试图跳出既有思维的局限的努力是看得见的。文学这个范围也确实太局限了。抛开了学术史谈文学,其实很吃力。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读后感(四):古文运动的“三位一体”
20世纪以来,对于唐宋“古文运动”的研究,可谓成就卓卓。在几乎“前人之述备矣”的形势下,朱刚老师《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仍能凭借其独到的视野与沉潜的研索,对“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王水照先生语)进行钩沉发覆,散发出丝毫不逊于前辈学者的理性之光。本书建立在朱刚老师博士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基础上,下分五章,从对固有研究范式的不满与批驳出发,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全面系统地勾画出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线索及士大夫文学的创作风貌。笔者不才,斗胆对此书加以评述,不当之处烦请师友指正。
一、内容评述
(一)、“古文运动”与“文以载道”
“古文运动”和其标榜的“文以载道”早已成为文学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知识界对“古文运动”之所以被称作“运动”的原因以及“文以载道”的理论内涵,前者不够重视,后者众说纷纭,均缺乏理性而富有逻辑的认识。抱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朱刚老师在全书开篇就从这两个问题入手加以探讨。第一节以研究史与问题点为导向,回顾了“古文运动”术语的提出和近代学科史视角下“中国文学史”对“古文运动”及其最初倡行者的认识与书写,并在正确认识“古文运动”背后的“人为性”基础上,对承担该“运动”的主体身份性质加以辨析,从而承接下一节中该身份群体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构建的话语系统,即“文以载道”。
此节虽是综述,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研究史回顾、文献爬梳、思想整合的层面,它指出“古文运动”术语的提出与20世纪思想、学术语境紧密关联,意识到 “进步史观”对研究“古文运动”的种种干扰,呼吁学者突破学科藩篱,正确把握“古文运动”复“古”的内涵,将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一并纳入考察范围内,在扬弃前说基础上为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
那么第二节便承接前文,厘清“道”的内涵。首先是辨析“载道”与“言志”的概念,书中采用了钱锺书先生的观点,破斥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然后指出唐宋人所论之“道”乃是作者主体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并非巩固为意识形态后上升至抽象伦理之道,进而追问:这样一种与主体的精神追求密不可分的“道”源于何处?指出“道”正发于一家之“学”,“载道”即“学”和“养”的结合。而当唐宋时代的文学家将自身所学与儒学传统有机结合时,新的理性思考应运而生,试图指导政治和文学,于是产生“旧儒学”向 “新儒学”的嬗变。全书剩余部分则围绕士大夫文学创作与“新儒学”创建和成熟的同步发展加以展开。
总的来说,这一章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对文学史、批评史家受制于时代语境、立足于单一学科所得出的片面观点加以批驳与甄别,同时不囿成说,自立新见,整体把握“文”“道”关系,赋予首章开宗明义、高屋建瓴的全局性意义。
(二)、“新儒学”与“古文运动”
第二章可以概括为“新儒学”的创建与成熟对士大夫文学的影响。共分四节,逻辑上围绕思想史的展开路径探讨“文学”作为其表达方式的多种面貌。
第一节聚焦中唐时期“新儒学”之肇始。围绕“尧舜之道”,考察了韩柳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化,特意强调“尧舜之道”最初是作为救国之利器而倡行,“原本含有明确的反对贵族经学之目的,与多数出身庶族的科举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相呼应”(页57),本质上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之上兴起的实用性学说,指出这一时期的争论始终停留在“道”的层面。
而在第二、三节中,随着科举士大夫登上历史舞台,庆历士风的振作使北宋“新儒学”的探讨呈现出别样风貌,话题突破了“道”的层面,而转向更深层次的“性”。此二节以“太学体”为案例,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文学史考察的窠臼,重新从思想史的层面探讨“太学体”的生成与接受,以及“险怪”文风在历史全貌中的复杂涵义。方法上,第二节抓住“太学体”的倡导者(石介)、排抑者(张方平、欧阳修)、受害者(刘几、程颐)、濡染者(朱长文)以及受益者(苏轼),由生平考证入手,对这些关键人物作了抽丝剥茧式的分析,从而站在“新儒学”立场重新审视了时人对“怪人”、“怪文”的界定,指出“异众之行”与“怪诡之词”互为表里的背后是“北宋思想文化向‘性命之理’的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页81)”,从历史进程的维度上肯定了一直以来在文学史中被贬抑的“太学体”的积极意义与学术价值。于是第三节紧承上节排抑“太学体”事件,继续从文学史的叙述之外,钩沉“古文运动”的另一条演变路线。通过追溯渊源,勾稽系谱,从而将景祐“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嘉祐“太学体”以及新学“经义”文续之一脉,藉此考察北宋“性命之学”的逐步推进。此节最有价值之处,是在研究方法上由学科回归到“人”,对历史过程中牵涉到的人物,作一综合性的考察。节中客观评价了欧阳修之于“古文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不追随文学史的宏观叙述,而是以全局性的眼光,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看到了身为高级士大夫的欧阳修对待新兴思潮的局限,认识到古文除了在继承欧阳修方向的历程上得以茁壮后,它的“另一翼”——即与“性命之学”息息相关的怪文同时得到长足发展,甚至在日后占据主流地位。这“两个方向”的提出无疑是有建设性的。
最后一节承接“两翼”分途,突破学科藩篱,对“周程、欧苏之裂”作出理性探讨。这一节考察了共同政治语境中作为文化主体的士大夫在思想史的视野下的分裂和对立,本节最后提出了新“道统”的概念。经层层铺垫,笔至此处,才真正揭示了“周程、欧苏之裂”的背后是“新儒学”与“古文”的分家。至此,“古文运动”、“文以载道”与“新儒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才在条分缕析中呈现出完整的面貌,其背后牵涉了政治、思想、文学的三重互动。
(三)、“士大夫身份”与“古文运动”
第三章依旧采取“由学科回到人”的研究方法,以“士人身份与文学”为研究面向,将宋代文学家还原成士大夫进行整体或个案研究,从思想心态角度观察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本章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四例个案、三组群体,立足于“科举士大夫的身份自觉”,考察这些“古文运动”的实际承担者的文学创作面貌。
前两节围绕神童科,按照历史研究的路数,对杨亿和晏殊的家世、从政、交往与在朝党争作了大致的考察。正如朱师自己所言,在考察杨亿时,本节“基本放弃了纯粹文学性的鉴赏”,力图将杨亿“还原成一个生活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士大夫加以探讨”(页139)。对杨亿政治生涯的追述,最终是为证明:日后在庆历时期形成的士大夫人格风范当时已初具雏形,强调杨亿或者说太平兴国五年进士集团在北宋士大夫文化演进的整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同为“神童”,下一节中对晏殊的考察则在史料之外,结合存世诗文,对晏殊的政治主张、思想动态、文学观念作出比较详细的论述。
第三节以欧阳修为中心,探究了“日常化”倾向与庆历士大夫“先忧后乐”人格之间的关系。关于“日常化”的讨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汤浅阳子,美国学者柯霖等人均已先后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朱刚老师又前人基础上联系京都学派“唐宋转型”学说,指出“日常化”倾向与唐宋之际社会转型,尤其是科举士大夫在历史上的崛起有关。具体到士大夫的创作实践时,此节先以宋初“白体”为靶,指出干政意识的缺乏致使宋初文人片面发展了白居易诗风,继而推出欧公,阐明其将科举士大夫救时行道、积极干政的身份自觉付之诗文,形成了同时继承“白体”干政精神与生活情操的“日常化”诗歌与平易流畅的文风。但本节的最后也指出,欧阳修所推崇的“日常性”,以及从“日常性”中延伸出的“至理”“人情”,并未影响新儒学的发展进程,在理性思维蓬勃发展的北宋,这样的认识注定是要被时代淘汰的。
第四节篇幅较短,主要针对“学记”文类,以政见相对的王安石与苏轼为例,考察了“执政”与“在野”两种士大夫文化模式。之所以选择“学记”,是因为学校,抑或说教育,乃勾连学术与政治之桥梁,与士大夫文化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由文类入手,再次抓住共同政治语境下的对立来作文章,足见作者深厚功力。
后三节篇幅较长,基本可以独立成篇。内容上选取了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表达、群体心态以及发展困境三个面向,将节与节黏连在一起。第五节通过考察北宋士大夫“非集会的同题写作现象”,勾画出同题写作由集会模式、非集会模式到面向公共领域自发性集体表达的演变路径,折射了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立场、文学好尚、情感共鸣等方面互相认同,并究其根本,指出该现象的成因在于士大夫政治上的群体意识向文学领域的投射。第六节结合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与刘子健“转向内在”说,探究北宋士大夫由“外王”转向“内圣”的原因和表现,最后回到具体的人,透过苏辙诗文中对人生态度的思考,考察北宋士大夫心态的“内向化”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第五部分,朱老师指出,尤其是北宋末期,现实环境的压迫致使士大夫已不仅仅满足于对“性”的探讨,更努力地将中立的“性”论改造成“性善”论,近一步地完成自我体认,满足心灵需求,不过这种“内省式”思考的过度发展也在南宋造成流弊。第七节综合前文所述,从士大夫群体身份性质与结构特征的变化,对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作了宏观的论述,继而考察这种变化对文学领域的影响。
总体而言,第三章内容丰富,体量庞大,围绕北宋士大夫思想心态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使研究兼具深度与广度。同时,这一章选取了多个研究面向,囊括了文学与制度、文学与党争,体现了学科交叉意识。
(四)、“贤良进卷”与“古文运动”
上一章将北宋文学视为科举士大夫的表达载体,这一章则是对该载体中的特殊一类加以细致考察。由于北宋中期士大夫阶层的迅速成长与科举制度的改革,策论成为表达思想政见的主阵地,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故本章选择将策论与科举制度相关联,聚焦“制科”中的“贤良进卷”,作出了专题性的考察。
第一节是对北宋贤良进卷的宏观论述。此节先略述北宋“制科”制度,罗列现存贤良进卷者及其进卷标题,对聂崇岐先生的整理进行补正,再将北宋一代尚可窥得全貌的贤良进卷(50篇)列为一表,直观呈现贤良进卷内部结构、层次,分析其性质,强调贤良进卷的整体性价值。接着,一一考察贤良进卷在哲学、历史、文学领域的创获,具体反映在贤良进卷与“新儒学”、新旧党争之关联,以及贤良进卷作为制度性写作,其独特的写作方式与鲜明的文体特征之于士大夫文学的意义。
第二、三、四节分别对苏轼、苏辙、李清臣和秦观的进卷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从选择的对象可见,新党旧党各有涉及,针对不同人物的生平经历、政治立场、学术态度、文学倾向,每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
二苏的贤良进卷面貌完整,结构互补,佳作名篇,俯拾即是,且兄弟二人传世文献与留存资料甚多,故对二苏《应诏集》的研究,主要从其整体性说起,探析进卷中呈现的篇目结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艺术特征等等。由于苏氏兄弟与庆历士大夫关系密切,又与将来的党争领袖“纠葛不清”,故此节第三部分专门基于嘉祐时期的学术与政治动向,指出二苏思想、政见师承欧阳修,重在调和复古伦理与世俗日常,这也使得基于“人情”的学术思想缺乏抽象而统一的理论总之,与王安石辈强调的最高原则和唯一路线相悖。
李清臣的贤良进卷是新党诸人文集佚失的今天有幸留存下来的沧海遗珠,其人也是“新党”中的另类——虽然支持变法,却不阿附“新学”,具有独立之思想。尽管他的后世影响不可与苏氏兄弟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其文竟获得了至少能与苏轼相提并论的地位。故对李清臣贤良进卷的考察,首先从其应“制科”与写作行卷的时间入手,再依进卷本身结构,对各分类下一系列策论作整体把握,指出其进卷具有以“王法”理论贯穿始末的特征,最后讨论李清臣进卷的写作艺术,结合具体文段分析,证明他并非谬得文名,并附录《全宋文》《全宋诗》所收李清臣诗文补正,为北宋“新党”文学作一难能可贵的补白。
秦观的进卷是以上三人中较为特殊的一例,由于他应“制科”而未售,其“应制”本身便是一件错综复杂、值得考察之事。故本节开头先考史实,正前人旧说之误,证明元祐三年贤良举士本身就是党争的表现,秦观应举之初便被烙上派系之争的鲜明色彩。正如书中所言,元祐年间旧党复起,意欲“更化”,恢复制科“无非是想为支持‘旧党’政策的人提供优越的仕进之途”(页317),所以,作为被扶持的对象,秦观也必须在进卷中输出与“旧党”立场相关的政见,为“旧党”利益服务。基于此,紧接着就按“党争”情况分类,详加论述秦观三十篇进策的政治内涵,对《进策》所表述的政见给予总体评价。最后乃观秦观进策之文学成就,为了勘察秦观进卷“五十篇皆用一格”之评语,朱师切观推求,不惜胪列除《序志》外四十九篇论、策论事立说之法,得出立论之法化单为多的规律。
此章较之前面章节,专题性大大提升,选取了北宋时期最符合表达需求的策论文体,将集中呈现士人政见、思想的“贤良进卷”作为士大夫文学标本进行考察,以观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典型性不言而喻。所选取的四组进卷,依进卷者身份、立场以及应制背景、经过的不同,或作整体考察,或按结构分析,研究内容涵盖哲学、史学、时政、文学多个领域,使贤良进卷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学术潮流、党派斗争与文学好尚。
(五)、苏辙与“古文运动”
作为思想运动,“古文运动”有着改造政治、改造文体的双重作用,它不以某个文学家的“成功”为标志,也不因某种思想被钦定为“国是”而宣告终结。最后一章,朱师创造性地提出以苏辙“国是”环境下的晚年创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终结”,并开启后“古文运动”时代的讨论,为这场延续三百年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了总结陈词。 以苏辙晚年创作为考察样本,其视角无疑是新颖的,“研究者往往只是碍于‘八大家’的盛名,在论述了苏洵、苏轼之后,不得已才附加上一条‘小小的尾巴’,以显示研究的全面与包容。”[1]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身份于一体的士人却没有得到与其历史地位、文化价值相匹配的关注与研究。此章第一节便针对散文领域,对苏辙散文基本风格作进一步考察。先从二苏对比入手,在共性基础上寻求差异,归纳出苏辙文风及其个性特征为“外柔内刚”,接着依照生平经历,细致考察外柔内刚风格在苏辙五十六岁之前每一时期散文创作中的体现,并指出随着写作环境发生的巨变,苏辙五十六岁之后的文风放弃了先前刻意经营的风格。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下文另辟一节,对苏辙晚年官阶、迁居汝南、独得优待、“不敢见客”、禅僧交往等问题进行考辨,为读者了解苏辙退居颖昌期间思想、创作的变化交代背景。第三节就苏辙晚年散文作一专论,
对苏辙散文中呈现出的独立性见解与平淡自然的风格提供了细致的解读。最后一节,伴随着苏辙离世,“古文运动”时代落下帷幕,但士大夫社会的分裂局面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深刻分歧依旧延续了下去,留给后继者一笔庞大但又泾渭分明的思想遗产。对前辈思想遗产的总结以余论形式为最后一章作出总结陈词,鉴于“新党”子弟可利用国家名义来做总结,故此节选取“旧党”子弟的总结性意见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分析吕本中政和三年帖的批评史意义,充分肯定其身为元祐后学所提供的宋代文学整体观——包括文学的基本范式与未来的文化导向,对吕本中政和三年帖的文化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
最后一章围绕苏辙最后十二年的创作实践,还原历史实情,揭示了苏辙散文之于北宋思想、学术史的重要意义,也“反映了作者对古文运动各阶段重新划分的新理念”(刘成国先生语)。最后以吕本中政和三年帖中提供的宋代文学整体观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总结,开启了后“古文运动”时代的讨论,颇耐人寻味。
二、优点及创新
(1)视野的扩大
本书的研究视域并不仅限文学,而是打通文史哲,从政治史、思想史宏观视角下把握“古文运动”的性质,认识到“作为文体改革的‘古文运动’,原本并不囿于‘文学史’的范围(页21)”、“古文运动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与政治紧密相联的思想运动(页95)”。由于过去的文学史、批评史叙述过于依赖“文学观念之演进”的思路,从而脱离历史语境,孤立地评判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产生的“古文运动”。故本书努力跳脱这一既定框架,舍弃了“纯文学”的定义,屡屡强调摆脱“文学史”信仰看待“古文运动”的必要性,进而从常见的文学史叙述之外,寻求“古文运动”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因素,将思想的流变、文学的演进重返历史语境中理解,把原本被割裂的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研究重新合并在一起,还原了“古制-古道-古文”三位一体的关系。正如第一章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说,学术研究的任何领域都应该重视自身规律的话,那么反过来,任何领域也都应该防止仅据自身规律解释历史的倾向。(页22)”文学发展或演进的背后既有政治环境的支撑,又有思想潮流的引导,参与文学发展与演进的主要人物之间,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对于研究者而言,应用联系的眼光考察历史、考察事物,而不拘泥于单一领域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也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2)方法论的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新儒学”与“古文”不可分割的状态,宋代思想史分裂与对立的情形以及文史哲领域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合,本书选择打破近代学制划分的学科藩篱,
由学科回到人,结合史学考证,将宋代文学家还原成士大夫进行整体或个案的研究。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颇有勇气。一方面,在文官政治的背景下,北宋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他们凭借自己在史学、哲学、文学、艺术领域的非凡造诣,共同将士大夫文化推向顶峰,形成了群星闪耀的格局,这意味着如何在空前庞大且优秀的士大夫队伍中选取典型案例进行考察,将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另一方面,北宋士大夫大多兼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学者于一体,这样的“通才”属性也加深了纵向上的研究难度。故第三章的处理颇为高明:先对杨亿、晏殊、欧阳修三人做了详切的个案研究,此三人正好呈一递接关系,可窥得士风崛起对士大夫创作实践的影响;再选取一组截然对立的士林楷模——王安石、苏轼的“学记”创作,考察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最后分别研究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群体心态和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分化问题,仍是有一内在的逻辑主线串联。
(3)“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后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2]本书正是依循这样的原则,在研究中不断还原历史语境,破除僵化的对立意识,不轻易肯定或否定历史进程中的某个人物或事件,而是设身处地地同情和理解古人及其思想,追寻历史现象背后的“合理性”因素。
如论及“怪文”时,朱师并不轻易置否:
“有关这些‘怪’文的史料,本身都带着否定的记录立场,如张方平笔下的‘变体’和‘太学新体’,在肯定欧阳修功绩的背景下被提及的‘太学体’,以及作为王安石‘罪证’之一的‘经义’文等等。因此,在个别看待时它们很容易一一被否定和忽略,但面对整个系谱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思考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追究其中可能包含的合理性因素。”(页87)
“古文运动的说法是近人在文学史领域提出的,它至少兼具思想运动的方面,如果那些写作怪文的人对思想史的进展起过积极作用,那么文学史也不防对“险怪”文风多一些同情,因为思想与文学至少在古文运动中是不可分割的。”(页95)
又如论及一向被后人冠以“西昆”诗人标签的杨亿时,朱师真诚地写道:
“同时,笔者也无意否定过去和现在的有关论述其华美富丽的写作风格的概括,不管它们出于赞扬或批评的立场。其实,只要把上面的追述与我们对‘西昆’诗人的固有印象结合起来,就不难想见,他在如此复杂、凶险,时时会令其心情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依然编织着美丽的辞章和繁富的典故,是一种多大的心力付出。”(页139)
这是一种多么浪漫的表述!此类“了解之同情”在书中比比皆是,既不枉屈古人,亦不抛却古人以伸己说,真正的同情,正应该是“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本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提醒广大研究者须时刻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不简单粗暴地将问题看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不站在后人的立场上评判先人之说,拒绝进步史观、历史目的论以及预设的目光,取而代之的是努力还原具体语境,怀有“温情与敬意”,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考量是非功过。
四、不足与结语
本书尽管论述严密、论证详实,或许因为是收纳旧作,重新编订,有些内容前后重复,不免啰嗦。第三章内容充实,体量庞大,覆盖面广,但结构比起其他章节相对松散,略显不足。 关于刘成国老师提出的问题[4],笔者比较赞同他对陶穀“依样画葫芦”为例的指正。 案《东轩笔录》,“依样画葫芦”之语最先出自太祖,颇有蔑视之意:
陶穀,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章足用,故尚寘于翰苑。穀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5]
邓小南先生《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指出,北宋建国之初,政治模式开始由“文吏型政治”向“文士型政治”过渡。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宋初依旧重视通技术与实务的文吏、贴己顺心的近臣而非道德学问型士大夫,“儒者调门渐高”不过是用以逆转唐末五代重文轻武政治语境的利器。太祖不取陶穀,致使其生发“年年依样画葫芦”的怨望,反映出北宋创业之君对陶穀一类儒士控御、利用而绝非倚信的态度。而且,就陶穀个人而言,他的品性风范也为太祖所鄙夷,出于个人喜好,太祖并不想对陶穀委以重任。《涑水记闻》卷一载: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6]
所以,考虑到北宋肇建的政治模式与创业之君个人取向等外在历史性因素,用陶穀之例指责宋初“官场惰性”与“软熟士风”或许是不太恰切的。然瑕不掩瑜,总体来看,朱刚老师《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牢牢抓住了“古文运动”文体改革与儒学革新的双重属性,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从士大夫阶层社会属性的转变中探讨“古文运动”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方法上拓宽研究视野,打通文史哲,破除学科泾渭,尊重历史现象背后的生发因素,怀着“了解之同情”进行客观评判。全书结构完整,体大思精,飞针走线,鞭辟入里,尤其是第四章,深入挖掘材料,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贤良进卷对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系统阐述,写作风格亦不乏个性色彩,会心之处,令人莞尔。在“士大夫文学”的研究领域,《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可谓作出了示范意义的开拓,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吾辈当深习之。
[1] 刘成国:篝灯时见语惊人——评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6月,第380-381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279页。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279-280页。
[4] 刘成国《篝灯时见语惊人——评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文指如下两点有待斟酌:第一,“太学体”新解部分尚存疑问;第二,存在社会属性决定论嫌疑。详见文章,此处不表。
[5] 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5页。
[6]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3页。
参考文献:
[1] 刘成国:篝灯时见语惊人——评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6月。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
[3]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9月。
[4]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9月。
[5] 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