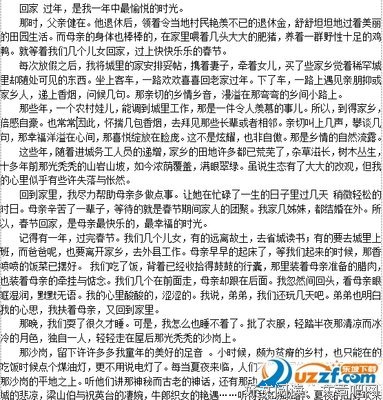《第五个孩子》的读后感大全
《第五个孩子》是一本由[英]多丽丝·莱辛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01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五个孩子》精选点评:
●面对黑暗力量时,人性的正面和负面?在一开始,我想怪胎野蛮恐惧,还是死了好,想法就像戴维和周围所有人。后来那个心理医生说,海蕊,是你的问题。我想大概是这样让我印象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心理貌似有点阴暗_(:з」∠)_
●班有毛病,他暴力,侏儒,但他不笨,他冷漠。海蕊歇斯底里地抚养他长大,她好累,只是文里行间,她好累。无人理解她。班又那么不通人性。她的第五个孩子,拖垮了她的一生。
●这个写作手法也太炫酷了,从开头到结尾一直是围绕人物叙述。我是无法理解有些女性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经历身体和精神双重巨大折磨的生育行为,并且这种生育是赌博性质的,毕竟无法提前预知胎儿是否患有多动症、唐氏综合征等各类足以打垮整个家庭的疾病。
●生活中总有一些责任会毁了原本的生活,然而没有具体的标准可以评判它,值不值得只有自己知道。
●在想,做重大决定时,恐怕多数人靠的还是思维与行动上的惯性。 "意义"是能寻找到的,还仅是被解释出的?
●你有本事再恶心点,继续写出令人恶心的结局,父母愚蠢,兄妹可怜,能看出什么,作为一个母亲能怎样杀了他?有时候佩服那些置于自己的孩子死的父母,他们不怕晚上睡不着觉?
●所有的温情在第四章戛然而止。作者太残忍,硬生生撕裂了一个家庭,扯碎了主人公梦寐以求的生活。不过,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呢?
●异类的到来导致家庭分崩离析。从维持表面和谐到逃离,亲人与亲人之间冷漠疏离,海蕊活在困惑犹豫中,孤独痛苦,就像她返祖的班。爱的丢失,人类集体异化。
●被嫌弃的班的一生,从边缘人的母亲的视角讲述他的成长。人类的繁殖真的匪夷所思。
●2020^06 冷峻到近乎恐怖的故事,窗外的紫丁香树投射在天花板上诱人阴影只是美好的憧憬,畸形孩子收容所长廊里的排灯也无法划破的黑暗才是生活的底色。
《第五个孩子》读后感(一):幸福家庭 幽暗人性
海蕊是个多产的母亲,她和丈夫戴维都热衷于“制造”生命。但在怀上第五个孩子后,海蕊尝到了苦头:
孩子在胎中给她无数罪受,幸好,生产顺利,只是容貌、个头与正常孩子迥异,她为之命名“班”;
班不受待见,因为他具有攻击性。亲戚不愿到访,兄弟姐妹敬而远之,就连丈夫戴维都嫌弃;所以海蕊同意将班送进一家特殊的医院。
可她毕竟是班的母亲,她无法想象班所受的非人待遇,因此,她将班再次接回家中,一点一点教化。她发现班对家人都很冷淡敌视,却喜欢和街头流氓混在一块。不得已,海蕊特地请那些街头小子帮忙照看班,自己还要花时间去弥补对其他孩子亏欠的爱。
班长大了,逐渐离开家,走上了社会,成为社会打压的一份子……
《第五个孩子》读后感(二):悲伤而非恐怖的故事
《星期日泰晤士报》认为Dorris这本书本“让人毛骨悚然,却也让人欲罢不能”。我十分赞同后一句,对于前一句却不能十足的同意。我也承认,这本书描写班的样貌和异于常人的行为时,那种平铺的,娓娓道来的描写让没有准备的读者感到恐惧,或许还有些许的厌恶。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像海蕊一样,希望班站在窗台上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去;亦或会做出和戴维一样的决定,把班扔进所谓的“疗养院”。
Dorris没有道明班如此异常的原因,没有将故事引向黑暗力量(恶魔、诅咒)。我却在想是什么造就了班的样貌、性格。或许是海蕊的情绪和对待还是胎儿时期的态度,从怀上班时夫妻俩的沮丧、海蕊面对胎动服用镇定药以此威胁腹中的胎儿、到班出生后一家人的嫌弃。或许班确实也是和普通的小孩子不一样:好动、脾气比较大、易怒,也或许有着医生也无法检查出来的疾病。但我们可以从班喜欢和约翰等人玩耍、待在一起可以觉察出,班其实渴望被接纳,渴望被爱。
那么是班的出生造成了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还是这个家促成了班异常的性格和行为?Dorris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结局,一个班最终的结局。但是,还好,班最终被特殊的群体所接纳了,即使家人要卖掉房子离开当地。或许结局会如海蕊设想的那样,但班可能是快乐的额,感觉到了归属感和爱。
《第五个孩子》读后感(三):“真的只是第五个孩子”
是不是人越活越复杂?想的越来越多,原本很简单纯粹的问题,总是会摊铺来看…… 海蕊和戴维的相识有点不可思议,对待婚姻对待孩子的态度倒是契合… 他们先后拥有了四名子女, 他们有着周围人觉得过大的房子, 他们有着与四个孩子生活并不等称的收入来源,幸好,他们的父母多少赞助了些, 他们热衷于搞家庭聚会,在一些节日里, 他们因此感到满足和兴奋, 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五个孩子——班! 他在娘胎里就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势大力沉、好动顽劣……而降生后,他带给周围人更多的大概是“毛骨悚然”的恐惧,双商远异于常人,暴力倾向严重,全家人大概只有海蕊能容得下班,即便其他人是班的父亲兄弟姐妹。 我能说我一度从文章中感受到的仅有母爱么(除了描写背景铺垫中感受到的虚荣)?毕竟,在海蕊艰难的抉择了将班送走后实在不忍心的又接了回来——这不是母爱又是什么?当然,我并没有感动,毕竟对于班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塑造,感情是无法撼动和拯救的!我强烈的认为理智应当替代感情,此刻! 但在文章的最后,一丝诡异的气氛,像是海蕊目送着班堕入深渊,却用着很平淡的文字……作为母亲,海蕊做了一切可为或者不必为的事情,付出了儿女四散、夫妻冷漠相对的代价……然而,这一切只为了看着他就这么走下去,不再去挽留挽回…… 这些,是在告诉我,当你已经倾尽全力之后,最好的表达就是目送他的远离么?这是爱?还是……无奈?我权当如此解读吧……放手,对于海蕊来说大概无悔无憾,也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诺奖得主的作品仅此而已?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简介里曾经提到过“以极其简洁流畅的叙述风格,写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第五个孩子》,探讨面临黑暗力量时,人性的正面与负面……作者用一个正常家庭如何对待异于常人的小孩,阐述邪恶的本质,直指人性幽微处,勾勒出共同的不安和惶惑”。 前半部分的评价我很赞同,的确简单流畅的日常叙述几乎可以让人一气呵成就读下去没有半点障碍;关于“黑暗力量”和“人性正面和负面”,我愿意将其解读为班的孕育、降生和成长,以及海蕊、戴维和四个孩子的不同态度(“毛骨悚然”的恐惧、没有任何犹疑的送走大概是一种幽暗的体现吧!);而关于“邪恶的本质”“不安…惶惑…”则有点摸不着头脑,非常欢迎读过此书的朋友进行探讨…… 之所以诺奖,到底是因为立意深刻?还是因为用简洁明了的描述,却直击人内心最深的本质以及情感?
《第五个孩子》读后感(四):可怜的班
在读《第五个孩子》之前,只读过两本莱辛的小说,无论主人公的境遇如何,字里行间都是极其压抑的氛围。但是《第五个孩子》不是,这个故事太可怕,直接像读者抛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甚至来不及去感受这种压抑,而是不停的去思索:怎么办?
海蕊和戴维都是自认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会在聚会上不约而同的同时走向彼此,然后结婚,买房子,不约而同的决定要生很多孩子,对家庭生活充满了期许。因为格格不入,所以孤独,因为孤独,所以相爱,因为孤独的相爱,所以对家庭的幸福如此珍重。
如果第五个孩子没有出生,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但是班来了,爱和恨交织下生出来的返祖儿,一个幸福家庭的破坏者,因为他的出生,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的亲戚们渐渐不再来了——异类是危险的,人和人之间小心维系的幸福是脆弱易碎的。孩子们纷纷选择寄宿学校离家而去,丈夫戴维和她渐行渐远,出于对班的恐惧,两个人不再继续性生活,甚至戴维搬出卧室,并将自己睡的房间称之为家——家应当是幸福的,可是这个家庭不再幸福,于是隔出自己的房间,一间房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家,以维持“家”的幸福。
海蕊无数次希望他在意外事故中死去,又无数次的救下了他。希望他死去,以继续家庭的幸福,救下他——这是一个母亲,这是自己的孩子。
莱辛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变着法儿写女性,写婚姻,这一篇也不例外。班出生之后,海蕊成了一个罪人,成了替罪羊,是她生下了这个孩子,是她坚持要养育教导好这个孩子,是她不顾反对去了疗养院,接回在那里等死的班,她被全家指责毁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每一次拯救班的时候,她都会想:戴维也会这么做的。但是,戴维真的会这么做吗?人和人之间是脆弱的,尽管这对夫妻很努力的去维系——这是一对很努力去追求幸福的夫妻,海蕊无法割舍下这个孩子,并因此无暇去顾及其他四个孩子,家庭的本质是抚育孩子,父系和母系在后代传承的问题上本质是不同的,既然孩子出现了问题,那么飞鸟各投林,分道扬镳不可挽回,家庭也支离破碎。生活本身就是充满了不确定,幸福触手可及,也转瞬即逝。
开篇就说到,海蕊和戴维是与这世界格格不入的人,而班,甚至无法称之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文中用“返祖”加以解释,这是一个异化的可怜人。异化是危险的,是家庭的累赘和耻辱。他努力学习社会的基本规则,哥哥看电视时学哥哥的模样去看,哥哥看电视时笑了也学哥哥的样子去笑,学别人的话称自己是“可怜的班”,或许他根本不明白“可怜的班”是什么意思。海蕊努力的去同化他,让他像一个“人样”,他也努力的去学习,但是基本无济于事,反而在下层人之间,在流氓地痞之间,在被他们嘲笑“傻子”等脏话之间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可怜的班至少活了下来,一次次被厌恶又不肯放弃的母亲救了下来,最终成了社会的边缘人。而在疗养院,那么多个可怜的异类孩子,在恐怖的房间里注射镇静剂等死,无声无息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好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些异类。
文明是脆弱的,感情是脆弱的,幸福是脆弱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份脆弱,面对异类,文明才会化作一股黏合又强大的力量,去摧毁这个异类。
至于莱辛留下的这个问题,我无解。不幸没法解决,只能背负。
《第五个孩子》读后感(五):异类的悲剧
有人把多丽丝·莱辛的《第五个孩子》称为“富有哲理的恐怖小说”。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说是恐怖小说,似乎也不至于如此。与其说这本书让人毛骨悚然,不如说这本书让人感到压抑。 本书开篇叙述了戴维与海蕊的相遇相识相爱,这一情节其实颇具戏剧性,走了一见钟情的套路。书中描写的戴维与海蕊似乎同为异类,他们在众人尽情狂欢时,只是静立一旁,好像自己只是一个理性的观众,正在观看一场滑稽表演。但同为“观众”的二人,隔着舞池中的茫茫人海,目光却产生了交汇。只这一眼,二人便擦出了爱的火花。在多丽丝的精心铺垫下,读者对于这二人的结合绝不会感到奇怪。戴维和海蕊,性格是如此契合,他们都不曾尝试也不屑于融入主流,这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此处其实也另含深意,一方面,戴维与海蕊的独特个性,让后来二人的生育观念脱离英国传统显得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班与其他四个孩子的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戴维与海蕊性格的一个折射。 结婚后的戴维与海蕊,认定家庭生活会是他们幸福的源泉。于是他们不顾双方家人的反对,坚持生育了四个孩子。戴维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拼命工作;海蕊则辞掉了原本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如戴维海蕊这样对生育有着强烈欲望的年轻人并不多,大部分年轻人的家庭观念都十分淡薄,他们更乐意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认为家庭反而会是自己的束缚和牵绊。但我们的戴维与海蕊,却拥有一套异于常人的三观:家庭重于一切。而这种观念的最大弊病或许就是对个人的压抑,当需要顾全整个家庭时,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便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必须为了整个家庭做出牺牲。从这个角度,书中的海蕊无疑是一个典例。 虽然戴维也多多少少为家庭奉献了许多,但笔者以为,多丽丝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实非常自然地着重突出了海蕊的牺牲。在构建好未来生活的蓝图后,海蕊毅然辞去了工作。对此她没有丝毫的犹豫,她似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再者,在生育这件事上,作为女方的海蕊本就承受着比男方更大的,来自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书中写到,每次怀孕,海蕊就会变得脾气暴躁。但事实上,二人对于生小孩这件事都是抱有极大热情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海蕊本身不排斥,不抗拒怀孕,一次次的怀孕的确给她带来了不少困扰。 将这种对个人的压抑再上升一个层次,基于海蕊的女性身份,女权的问题也慢慢浮现出来。暂且不谈书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单从多丽丝安排的双方家庭背景中便暴露出了问题。戴维的家境显然优越于海蕊的家境,戴维的父母甚至在诸多观念上都与海蕊的父母产生了所谓阶级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海蕊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压迫。更何况戴维的父母对于海蕊远不只是无形压迫,在班出生后,戴维的父亲一声令下要把班送到疗养院,海蕊起初并不同意,但在戴维与其父亲的强权压制下,海蕊最终选择了妥协。后来海蕊出于母亲的本能将班从疗养院接回来时,她更是受到了全家人的冷暴力,自己俨然成了家里的罪人。 除去海蕊,班其实才是本书的核心矛盾所在。班的出生好像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生下第四个孩子后,戴维和海蕊原本打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暂不做继续生育的工作,可是班却在这时不请自来了。班在海蕊肚子里时便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他在海蕊的肚子里拳打脚踢,让可怜的海蕊痛苦不已。以往戴维在这一时期都会对海蕊倍加关怀,但就因为班的到来不合时宜,戴维对海蕊的态度并不如从前。丈夫的冷漠和肚子里孩子的折磨,使得海蕊甚至产生流产的想法。这里似乎便提醒了读者,班尚未降临世间,就受到了家人乃至自己亲生母亲的不欢迎,成为了悲剧的开端。班后来的出生,也是打破了戴维和海蕊最后的一丝幻想。班的样貌十分不讨喜,甚至用丑陋来形容也不为过,最重要的是,班作为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孩子,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残暴与蛮横。他还躺在摇篮里时,便把试图逗他的三岁哥哥的手掰得骨折;等到再长大一些,他还勒死了一只宠物狗和宠物猫。班的性格古怪,他的眼神总是冷冷的,带着一种骇人的意味。 认清班的怪异后,家中的四个孩子开始疏远孤立班,班在的地方,他们都表现得谨慎小心,丝毫不透露出小孩的本性;班一离开,他们便好像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开始回归小孩子的状态,尽情玩耍。班似乎也渐渐发现了这一点,他也做了一些融入哥哥姐姐们的努力:在其他小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班也会跑到沙发上坐着,但他并不是看电视,而是仔细观察哥哥姐姐们的一举一动,然后模仿,努力让自己同他们一样。但班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人们一旦给某人戴上了一顶帽子,便绝不会轻易摘下。所以班索性恣意展示自己的不同,不再试图变得与其他孩子一样。这样,海蕊接下来为了改变班而费尽心思,便也成了无用功。于是海蕊作为母亲的天性被班的顽劣一天天磨着….. 作为母亲的海蕊尚且无法忍受班,家中其他人对班的厌恶之情可想而知。终于,戴维的父亲提出把班这个怪胎送到疗养院去。众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决定意味着彻底将班从家庭中驱逐出去,所以他们全部表示赞同。而此时,海蕊内心深处的母性也没能战胜戴维与其父亲的强硬。虽然后来班还是被心怀愧疚的海蕊接回了家,班的成长依旧全程灰色。海蕊为了让班待在家里的时间少一些,放任班去和约翰这样的社会青年鬼混,后来班与他的这些伙伴们的关系愈发亲密,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呢,自班出生后便失去了生气,到最后,家里只剩下精神近乎崩溃的海蕊与早出晚归的戴维。 多丽丝极力展现邪恶的本质,残酷揭露人性的复杂面向。仔细想来,人们的确擅长划分群体,圈定自己人与敌人。而这个区别的标准,则是共同点与不同点。无论社会或是个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判定事物的模板,只有跟这个模板相吻合了,才是同类,否则就是异类。异类们在现实中绝对不受待见,他们似乎只能在一次次失败的求和经历中慢慢接受自己的命运。《第五个孩子》里,传统意义上的亲情也显得不堪一击,这尤其使人感到压抑。如果说其他四个孩子对于班的抵触是因为不懂事,那么戴维对班自始至终的漠不关心则难以解释。因为班的出现,戴维甚至将怨恨转移到了海蕊的身上,对于班,他从未尽过哪怕一秒钟父亲的责任,事实上他也从未承认班是他的孩子。至于海蕊,她的情感取向在文中一直显得模糊暧昧,不能说她喜欢班,因为她实际上也是将班“抛到荒岛”的帮凶之一;不能说她完全憎恨班,毕竟她一直还是保有那么一些对班的母性光辉。或许海蕊是多丽丝留下的唯一不至于让人绝望的火苗吧,让我们不至于只看见人性中丑恶阴暗的一面。 《第五个孩子》实在是一个令人压抑的故事,但它也让读者在压抑的同时不得不陷入沉思:班可能的确是个怪胎,但新生婴儿的邪念,又从何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