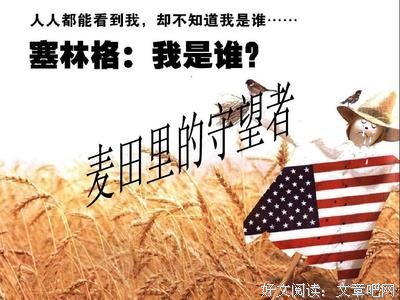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摘抄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由J. D. 塞林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一):谁的青春不迷惘?
这本由塞林格创作出版于1951年的作品自出版之日就大受青睐,一直到今天仍在被读者传颂。这本书究竟为什么这么火?剖析其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16岁的名叫霍尔顿的中学生因为考试成绩多次不合格被学校开除,然而又不敢回家,因此在纽约家门口流浪了三天的经历。在这几天里他见了很多人,有同学、旧友、妹妹、曾经的语文老师等等。但是他无法完全倾诉出自己的迷惘和痛苦,别人也没有办法彻底理解他。他酗酒、斗殴、找性工作者,眼看就要走上沉沦之路…… 那么霍尔顿为什么迷惘?因为他讨厌这个装模作样的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那么得虚伪,爱通过耍酷把妹的同学,爱炫技的钢琴师,世俗的上班族。他认为这个世界缺少一种纯真,像妹妹菲比那样的儿童的纯真,想说就说,想做就做的纯真。霍尔顿热爱文学,他跟很多文艺青年一样,都很适合用两个词来形容:多愁善感、愤世嫉俗。 谁的青春不迷惘?不消说霍尔顿,不消说塞林格,不消说二战后的美国青年,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的年轻人们不都是迷惘着走过来的吗?儿童时期的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随着年龄长大,感受力增强,我们才渐渐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如我们想象得那般美好。于是我们痛苦、挣扎,有些人由此走上了弯路,有些人甚至付出了惨痛代价,当然大多数人到最后选择了向现实低头。正如小说中霍尔顿的语文老师给他写下的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年轻时我们总想着怎样死,但是成年后我们却每一天都在考虑如何活下去。 塞林格的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真实。可能这种真实来自于他的切身体验。因为他也是在15岁的年纪就被父母送往一所寄宿制军事学校学习,跟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尔顿经历相似。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短,仅有三天,将其内容撑起的是大量意识流的描写。霍尔顿的愤懑不满以及单纯善良的心思全都被展现出来给读者观看。因此这部小说也不断引起青少年们的强烈共鸣,甚至引发了一些不好的事。本书甚至一度被某些地方列为禁书。比如枪杀约翰列侬的凶手曾说他的真实想法全都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中。当然这只是文学作品被曲解误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就像罗兰·巴特所提出的“作品诞生,作者已死”的观点。作者在创作完一部文学作品之后随即消失,剩下的剖析解读工作,全都是读者的权利了。 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脑子里总会串联起其他几部同样有关于青春疼痛的作品,比如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杜穆里埃的《我不会再次年轻》、约翰欧文的《放熊归山》甚至是欧文·威尔士的《猜火车》等等。而且有意思的是塞林格在成名后选择到乡间隐居,并且沉迷于东方哲学及禅宗,这一举动跟凯鲁亚克作品中的主人公非常相似。 我想阅读这部作品,对于一名像我一样的中年人来说,也许更多的只是对青春的一种缅怀吧。那些彷徨无措、暗无天日的时光已经远走,活在现实中的我们是否变得像霍尔顿厌恶的那样得虚伪了呢?但是虚伪与否,都是他人为我们定义的,只要我们朝着自己的价值和目标进取,坚定内心,我们就是最纯真的人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二):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
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
我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你
我们要是看到很多孩子
在麦田里做游戏
请微笑请对视
态度都浮在生活的措辞里
我们都活在彼此的文字
——罗伯特-彭斯
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可能是我的过客,也可能不是;我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你,可能是你的过客,也可能不是。但既然相遇了,一定会有那么点渊源,可能相互影响,也可能毫不相干,当然我还在我的麦田,你可能如一阵风,微微吹过我会弯弯腰,但风过了,我依然守望着我的麦田。
童年,成长,人生好像很多个轮回,虽然在数不清的方向上曾经一路狂奔,但是每一件事又悄悄回到了原点;虽然为好些人心花怒放或者黯然神伤,但是守在身边或者心里的还是一眼难忘的那个。说的俗一点,不忘初心也好,归来仍是少年也好,意思倒是不错,总之还是在固有的那个小世界里视死如归。做自己人生的主宰啊,“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要不然,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物欲横流也好,虚情假意也罢,世界就是如此般灯红酒绿蝇营狗苟。历史的洪流滚滚而过,我可否活的澄澈?人生的起伏茫茫无边,我能否步若清风?“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里注定会不时去寻找一些他们自身周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要么他们以为自身的周围无法提供,所以放弃了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寻找前,就放弃了。”你看,寻找自我的意义就在此,不去寻找,又怎么发现自我呢?
所以,“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的活下去。”这真的一点都不庸俗。
孩子的世界最纯净,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最残酷,哪有那么多的拐弯抹角隐喻讽刺,他只不过在按自己的理解探索人性的边界。我喜欢书里关于学校教育关于人性的判断,但是呢,孩子也许会接受也许会拒绝,他总会在寻找自我的过程里活出自己的样子。
塞林格已经仙逝啦,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霍尔顿已经70周年了,他却可以永远鲜活在书里。
“千万别跟别人说事儿,说了你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就像译林这本特殊的纪念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说其他我真的想起了好些人。
《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
罗伯特-彭斯
这里不是家
你却是生长根茎的影子
习惯把自己养在金黄的梦里
我在你的世界练习降落
不谈金钱权利和性
只开着一扇干净的窗户
折射低飞的阳光
我们成了假模假式中
两尾漏网的鱼
不能跳舞不能唱歌不能暴露
在这个季节
我们适合坐在锋芒的背后
幻想给世界灌输一点点酒精
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
我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你
我们要是看到很多孩子
在麦田里做游戏
请微笑请对视
态度都浮在生活的措辞里
我们都活在彼此的文字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三):霍尔顿,霍尔顿,你在守望谁?
对于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美国著名当代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是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个精神偶像,是写出《九故事》的天才作家,也是退居山林的先知、隐士。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塞林格。他将精神的一部分留给了那个孤独的、叛逆的、迷茫的,但内心深处却时刻守望朴实与真诚的少年霍尔顿……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名为霍尔顿,这个生于富裕家庭的16岁叛逆少年是很“不幸”的,他就读的贵族学校潘西是一所教学质量极高的学校,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不允许有差生的存在,当学生成绩多次不及格时,只能被开除处理,就如校长与老师口中的“比赛规则”一样。期末考试,霍尔顿多门不及格,于是校长跟他说,圣诞假期之后,你不用回来了。因此,霍尔顿决定提前离校,在纽约城里转悠两天后再回家。
霍尔顿是作为一个烟不离手、满口脏话的叛逆少年,很多时候,又会不经意流露出迷茫和脆弱。人格心理学上讲,12到18岁是一个很微妙的阶段。这个时期叫作“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霍尔顿就在经历着这一时期,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讨厌成人社会的虚伪,认为只有孩童的世界才是纯净无暇的。因此,他最害怕的,就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也会变得跟成年人一样虚伪。
因此,霍尔顿的眼里,幼时的玩伴、因病死去的弟弟和天真无邪的妹妹,才是最美好、最值得自己珍视的。在他孤独、空虚、迷茫、无助时,他也向外界寻求帮助,他找过历史老师,找过曾经的学长,还找过他一直都非常尊敬的英文老师。这些人,都对他说了很多很多,可他却一直不得要领,因为在他们面前,霍尔顿其实是无法彻底敞开心扉的。
书中写道,在经历了朋友之间的争吵,见证了男女之间随随便便的两性关系,看透了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假模假式之后,霍尔顿彻底对生活失望了。引发他绝望的一个事件是,约定好的花五元钱找一个ji女,他却因一时的怜悯之心,仅仅只是跟她聊了会天就被ji女伙同电梯工以暴力威胁敲诈了他。这令他对社会更加怨怼。霍尔顿的绝望在于:他以怜悯和善良之心觉得ji女生存不易,可她却心安理得反过来敲诈于他,并称他为“没用的废物”,这不仅让他难过,而且让他更加憎恶这个世界,所以他想逃离“”的生活。
后来,在一次次向外界寻求帮助皆碰壁后,霍尔顿决定搭车去西部,从此装聋作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于是,他向妹妹菲比捎了纸条,约她中午在博物馆门前见最后一面。
有一次,霍尔顿曾对菲比这么说:“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段话可以被认为是整部小说的精髓所在。因为,在麦田中尽情释放的孩子何尝不是少年霍尔顿真实的情感寄托?
然而,我们知道,麦子一般都生长在平原地区,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在悬崖边种麦子。因此,这种荒谬的组合无疑在暗示着霍尔顿所想象的成人世界与孩童世界的对立其实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并非真实存在。一向依赖霍尔顿的妹妹菲比拖了个小行李箱,带着仅有的一点积蓄应约前来,要和霍尔顿一起走。身为哥哥的霍尔顿出于种种顾虑自是拒绝,但又无法说服菲比,只得放弃离家的打算,答应妹妹自己会回家。
在这个悲伤的故事结尾处,霍尔顿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成为无法一名合格的守望者,还要由少不更事的妹妹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这部小说正如我们所见,它并非如以往的治愈类小说那样,对主人公锐意进取的决心大肆褒奖,而是对那个年代叛逆少年的颓废和挣扎心理,给予了最真挚的理解与包容。
如同小说《达摩流浪者》中的贾菲和雷蒙一样,霍尔顿同样是“垮掉的一代”。他的口头禅“假模假式”,就是他对虚伪、浮夸的成人世界的失望。塞林格亲身经历了美国二战前后的变化,通过塑造霍尔顿这样一个“不愿成长”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少年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四):“麦田里的守望者”意向溯源
1951年,塞林格出版了《麦田里的守望者》,2021年6月,译林出版社推出70周年纪念版,译者是孙仲旭。
一、麦田与塞林格、孙仲旭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在家中去世,享年91岁。 当天,37岁的孙仲旭和友人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最心爱的书,并在博客上引用了书中的一段话:“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新版P199)”
4年后的2014年8月28日,年仅41岁的孙仲旭因抑郁症去世,令读者唏嘘感叹。当年的《三联生活周刊》以《孙仲旭:再见,麦田》为题进行专题报道,文中提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孙仲旭译的第一本书,1999年开始翻译这本书后并没能立刻出版,孙仲旭每隔一两年就将它拿出来重新修订,电脑里存下了5个版本。“他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他的迷惘正是我的迷惘,他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孙仲旭这样描述自己情感上与主人公霍尔顿的共鸣。
二、麦田与70年纪念版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译林出版社的长销书,有施咸荣、孙仲旭两种译本,每种译本都多次出版,影响广泛。2020年7月,译林推出了 塞林格百年诞辰限量纪念版,选用孙仲旭译本,封面复刻了1951年初版的封面设计,红色奔马扑面而来,以“马踏纽约”的桀骜彰显叛逆的青春。
译林出版社2020年7月纪念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初版封面
译林此次推出的“出版70周年纪念版”仍选用孙仲旭译本,封面设计延续红黄色调,环封为红底黄字、内封为黄底红字,红色的青春搭配金色的麦田,给人强烈的视觉刺激。腰封在红黄底色之下,是头戴红色猎帽的霍尔顿黑衣背影,在麦田里走向前方,去看护麦田里做游戏的孩子。
出版社还提供了定制化制作,在腰封上印刷读者的名字,以“献给每一个勇敢而纯真的理想主义者”为题,赠送给部分读者。个性化设计让这个版本极具情调和收藏价值。
译林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70周年纪念”版
译林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70周年纪念”版
三、“麦田”溯源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太过经典和普及,笔者已说不出什么新意。借70周年纪念版出版之际,不妨把“麦田”意向的来源梳理一下,供同好参考。
在70周年纪念版中,有两处提到“麦田”。一是P133,霍尔顿在百老汇游荡,听到一个孩子唱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听到这句歌,主人公“感觉好了点,不是很沮丧了”。二是P201那段耳熟能详的话,孙仲旭是这样翻译的:“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人,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这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网上还能看到多种翻译,但意思都是不差的,道出了年少轻狂的霍尔顿隐藏在内心的理想化追求。
书中提到 ,“穿越麦田”源自罗伯特·彭斯的一首诗。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年1月25日—1796年7月21日)是苏格兰诗人,《友谊地久天长》的作者,1782年创作了《 走过麦田(Coming Through The Rye)》,里面写道: “如果一个他碰见一个她,走过麦田来,如果一个他吻了一个她,她何必哭起来?(王佐良译)” 这是一首具有乡村风格的爱情诗,16岁的霍尔顿误将原诗中的"if a body meet a body"理解为"if a body catch a body",他的脑海中浮动孩子们在悬崖边的麦田中游戏的情景,他告诉妹妹菲比,他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抓住玩儿疯了跑向悬崖的孩子。
菲比是霍尔顿的妹妹,也是他的拥趸。当菲比提出想跟他出走时,反倒阻止了霍尔顿的脚步。经历了纽约三天的流浪后,霍尔顿又回到了虚伪刻板的现实生活,青春的狂想曲也戛然而止,但余音绕梁久久不散,《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成了经典的意向,激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青春记忆。
那是一片心中的麦田,麦浪滚滚,有孩子在其中奔跑嬉戏。那是一个纯真的守望者,静静地站在那里,欣赏着孩子们的欢乐,并做好随时守护的准备。
这是一曲青春与理想的欢歌。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五):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叙事上的“狄更斯”情节及“追寻”和“逃避”
对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有时很难精确的去进行一种评价,既不像是简•奥斯丁再现了范妮•伯尼【1】的文学艺术,描写一种拥有敏感细腻的女性异类人物(当我们读到《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独自赶路前往宾利家宅时候,就已经可见一斑【2】),再则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否一个男性异类人物(达西先生【3】亦是如此)也一直存有疑问,只有我们思考到霍尔顿•考尔菲德是我们对于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自我投射后,这样的疑问几乎不攻而破,继而不值一提。其中作为起点的便是“诱惑”或者“引诱”,其次就是“信赖”和“反抗”(这是一组精妙的,勉为其难的反义词),最后就是对于心灵上亦或精神上的属灵,经过最后一步在“阅读”行为下的“文学”才会变为“追寻”和“逃避”(西方文学中的用来概括传统主题的老套且有用的词),所以,霍尔顿•考尔菲德的确可以是我们心中某种程度的分裂出来的自我个体,以及他们(代表了众多作品的主人公)中的对于“我”的理解。
塞林格一开始就用十分确定的语言戏讽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开端【4】,以及狄更斯式的个人自传因素的成长小说的老套成见。虽然,霍尔顿的本意只是利用《大卫•科波菲尔》来反讽一种成人化的高级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成人世界,这两者密不可分的程度就等同于霍尔顿话语中的粗言鄙语一样。更简单的理解便是,霍尔顿有可能反感的就是狄更斯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局被社会整体的接纳或者接纳整个社会。但是,霍尔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反狄更斯式”的小说人物,只是一种反“大卫科波菲尔”的大众神话(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也是如此);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反狄更斯情节,更多让《麦田里的守望者》接近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让霍尔顿•考尔菲德接近于那个“平凡的乡下小子”皮利普【5】的形象。小说家塞巴斯安•福克斯就很明确指出皮普(皮利普的又名)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一个成年化的皮普带着无情的自我批评的视角下讲述了自己的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可能怀疑整本书的开端的那个叙事者,就是一个成年化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只不过,这个成年化的霍尔顿也可能不存在,却可以使我们读者进入一个同情(褒义的情感反馈)霍尔顿的小说真空,对于皮普的理解也是如此。当我们能够理解皮普因势利和忘义而犯下的错误的时候,也能够想起霍尔顿•考尔菲德的“我喜欢看到人们偏离正道,这才叫有趣”的观点时,我会想起在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论及的“不服从”,让皮普变得更为幸福而幸运,可再现在霍尔顿•考尔菲德身上的时候,会让读者错觉的以为霍尔顿身上有一种超越所有社会分野的道德秩序感,只是显得更为失落和心灰意冷,让霍尔顿•考尔菲德变得更为消亡和迷失而充满了悲剧之痛的人物。
可惜,对于霍尔顿•考尔菲德,我更多的时候怀有褒义的同情,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对其生出一种贬义的厌恶。因为霍尔顿•考尔菲德缺乏一种英雄主义,只会让超越所有社会分野的道德秩序感显得更加软弱无力。霍尔顿的意志,有时像是一个成年人中儿童,有时又像是一个儿童中的成年人,来回转换之时变得飘忽不定,我们无法从霍尔顿的身上看不见“决不屈服绝不顺从的勇气”,只能看见“你这一辈子大概没见过比他更会撤谎的人”。【6】这无疑就是一种反讽,让霍尔顿•考尔菲德变成困惑型的小说人物。
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确实很容易让读者想象出来。反而,作为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前辈,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贝利更显得欢快愉悦得多却失真,两者的主题上如此的接近的程度上,更让霍尔顿显得失落和心灰意冷。霍尔顿的三天二夜在纽约街头的流浪行为无疑是对其个人的痛苦做出的终极报复,有时候就像是失控的哈克贝利,只不过霍尔顿的素描更像是漫画,一种狄更斯情节的再现,让读者面对霍夫顿的困惑时更为清晰的感受这种困惑。伴随霍尔顿的困惑的表现是撒谎,这种撒谎行为的特质就像是王尔德戏剧《认真的重要》所言“我的人生经验是,每当你撒谎,你便在各方面得当巩固。当你说真话,你便被遗弃在一个孤独而痛苦的位置,且没有人信你半句”的扩充版本,只是说真话和撒谎在霍尔顿这里都是一个孤独而痛苦的困惑。如果我们看一下快要接近于结尾的霍尔顿与妹妹菲比在旋转木马时相伴的段落,就会发现一种特殊的力量彰显出来:
我现在就在想,霍尔顿•考尔菲德的意志确实有一种温情,是转向死亡的消极的内驱力。塞林格为了稀释这种“允诺的结局”带来的浓重的消极,想象出了一种利用温馨色彩的特别意向(霍夫顿的某种希冀)——“麦田里的守望者”(即是书名):
麦穗的金黄色,金黄色次一级落日余晖的色泽,麦穗被风吹扬时的不停的“唰——唰——”声响,以及可能是永远竖立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实质是一个稻草人在悬崖永远在凝视的一种真相。确实,组成了一幅那般如此胜利的意向,虽然其中充满了某种挫折的虚无感觉。我同意哈姆莱特的“死亡终结一切”的观点,我迷惑的亲信霍尔顿的想象出来关于死亡的种种的幻想,在这里塞林格降低了深度,给予了霍尔登某种重获新生的规划,如同塞林格自己的归隐山林一样,霍尔顿的重获新生的规划也只不过是“西部边缘一个阳光明媚,景色美丽的地方去”,继而一种飘渺虚无的梦幻色彩变成了另一种颇为实用主义的拯救企图,这种企图就是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提倡的重回自然中去,在精神上重新净化,达到完美的境界。
可以说根本没有完全的失败,只有我们通过阅读霍尔顿•考尔菲德的自我,扩大了自己的自我,尽管其中充满了死亡意识。塞林格降低了作品文学上的深度,避免霍尔顿成为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人物(让他直面死亡),将故事变成了最后的勉强胜利的理由就是纯良的道德感。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微小的胜利。
【注释】
【1】范尼•伯尼:英国女小说家和书简作者,风俗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的《埃维莉娜》的作者。
【2】伊丽莎白独自赶路前往宾利家宅的情节可见《傲慢与偏见》第7章。
【3】达西先生是《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
【4】可参看《大卫•科波菲尔》的开头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的比较。
【5】皮利普:《远大前程》的主人公。
【6】引文见《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章,引用时改动其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