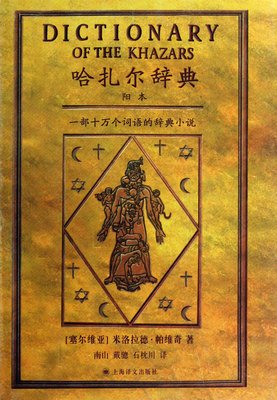《哈扎尔辞典》经典读后感10篇
《哈扎尔辞典》是一本由米洛拉德帕维奇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311图书,本书定价:18.80元,页数:1998-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一):哈扎尔辞典
哈扎尔辞典 米洛拉德帕维奇
辞典的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本身,通过一个个词条构筑起的关于哈扎尔的故事,又由于辞典词条的文字展现形式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读者的阐释空间更大,正如序中所言,读者强于作者,读者阅读千本小说,而作者只是创作一本小说。但米洛拉德帕维奇并不是纯粹追求形式的新颖,当然这种形式上的特殊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作者的文学观,现代小说从情节主题到表现载体表现形式的转变是对文学本体的思考结果。虽然觉得阴阳本之分的噱头的成分更多。
抛开形式,小说透过词条信息的罗列整合还是建构起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宗教视野下的哈扎尔史料。三种宗教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世界本质的解释有相似性,三种宗教在哈扎尔辞典里的地位并无高低。宇宙中最高层次的智慧并不比最小的动物的智慧更伟大。只不过前者由纯粹的物质构成,故能永恒,层次也更高,只有创造它的造物主能将其毁灭,而动物则由容易受到各种影响的物质组成的。智慧在它们身上感受热、冷及其他影响它们本质的一切东西。这段话更像是对哈扎尔辞典中的宗教观的阐释。无论是红书还是黄书亦或是绿书,将的看似无关的故事,其实是拆分的时空再加以梦,那些关于达乌勃马奴斯、勃朗科维奇、马苏迪和合罕、阿捷赫公主的词条贯穿了古今,地跨多处。喜欢哈扎尔辞典的原因,并不是米洛拉德帕维奇的技巧,我可能更喜欢那些依托于斯拉夫的民间故事加上神秘的卡巴拉产生的效果。
哈扎尔辞典是循环往复的,所以无穷无尽,就像阿捷赫公主能任意地变换脸孔一样,在文本留下的大量空白中,读者的智慧可以发挥到极致。一本书可以由阅读来加以医治或扼杀。书可以被改变、夸张或歪曲。书的阅读导线可以改变方向,你总会错过某样东西,你会在宇里行间失去只语片言,几张书页会在你的指间漏过,而另一些东西却像甘蓝在你眼前生长。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二):2016年11月4日
帕维奇灵气逼人,让我想到了马克尔斯,和该死的詹姆斯乔伊斯…这三个人其实都很“飘”。
其中马克尔斯的组织能力最强(最平易近人)。詹姆斯乔伊斯的表达能力其实最强,但是丫喜欢炫…尼玛的爱炫…最后就是帕维奇了,可能是得益于他的哲学家和诗人身份,如果要挖,他会是最有才的。但是正是因为他是个哲学家和诗人,所以他“小说家”的身份是不够纯粹的。
最后,帕维奇犯了一个和詹姆斯乔伊斯有点类似的错误:过分关注文本技巧,而把对内容的需求放在次级位置上了。但是对于小说来说,感染力和表达内容才是比较重要的。不过帕维奇错得有点可爱…和尼玛的詹姆斯乔伊斯不一样…靠…
另外,最近有点躁,所以这本书看不下去。当然,我怀疑我静心凝神的时候也看不下去…它的可读性有点糟糕,主要是太破碎了。以后有时间可以再挑战一下。
:但是这本小说的主要故事很性感。为了决定国教,而发生的一场关于三个宗教的辩论会,以及穿插在其中的神秘盗梦者文化。
《哈扎尔辞典》记录了一个曾经存在的由哈扎尔部族组成的王国的历史,讲述了一场发生在公元8或9世纪的哈扎尔大论辩,哈扎尔的首领 可汗做了一个梦,于是邀请了基督教,古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代表前来解梦,最终归顺了其中一个宗教。不久后亡国,一切都已湮灭成为了一个谜。《哈扎尔辞典》分为红书(基督教)绿书(伊斯兰教)黄书(犹太教)三部分史料,包含了错综交叉的历史和人物记录。
真相已经不确定,因此故事呈现多样的和模糊的发展,各种线索的交织,各个史料的各执一词且互有联系,使得读者只能将信将疑,却又不得不接受梦一般的历史来拼接成一段真实而完整的故事,阅读就像是做了一场奇幻的大梦,而梦醒来,你就经历了你的一生。
哈扎尔大论辩 861年左右 P63 P169
-------------------------------------------------------------
参加论辩的三个代表:1:基里尔--基督教 2:伊本•科勒--伊斯兰教 3:伊萨克•桑加里--犹太教
基里尔(康斯坦丁):希腊基督教代表,论辩者 P41
法拉比•伊本•科勒:伊斯兰教代表
伊萨克•桑加里:犹太代表 P243
-----------------------------------------------------------
研究《哈扎尔辞典》的三人及史料收集者:1.阿伯拉姆--基督教 2:马苏迪--伊斯兰教 3:合罕--犹太教 三者由 杰奥克季斯特•尼克尔斯基 收集而成,卖给了 达乌勃马奴斯.
阿伯拉姆•勃朗科维奇:(1651-1689)外交官,公使 P7
撒母耳•合罕:(库洛斯) (1660-1689) P180
马苏迪•尤素福:(17C-1689)乐师,释梦者
杰奥克季斯特•尼克尔斯基: 见补编资料
达乌勃马奴斯:(17C) 1691年将《辞典》三个版本合编而成 P210
--------------------------------------------------------------
《哈扎尔辞典》的三个研究学者:1:舒立茨博士--斯拉夫语 2:苏克博士--阿拉伯语 3:穆阿维亚--犹太语
以撒洛•苏克:(1930.3.15-1982.10.2)考古学者 P78
阿布•卡比亚•穆阿维亚:(1930-1982) P159
多罗塔•舒立茨:(1944-) P246
-----------------------------------------------------------------
论辩编年史的三位作者:1.梅福季-基督教 2:哈列维--犹太教 3:斯巴尼亚德--伊斯兰教
萨洛尼卡的梅福季:(815-885)基里尔之兄 P56
犹太•哈列维: 后由 犹太•伊本•杜蓬 翻译。
阿勒•拜克里•斯巴尼亚德:(11C)
--------------------------------------------------------------
《哈扎尔词典》的两个作者:阴本:阿捷赫 阳本:萨费尔
--------------------------------------------------------------
阿捷赫:哈扎尔公主 9世纪 P3 P177
可汗:哈扎尔首领 P48 P221
哈扎尔人:P51 P221 P158
捕梦人:哈扎尔教派 P40
阿丹•鲁阿尼:第三天神
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9C-11C)著名捕梦者,女修院院士 P158
------------------------------------------------------------
勃朗科维奇仆人:
尼康•谢瓦斯特:17C 撒旦化身 P68
安伟尔基•斯基拉:师爷,刀客
马苏迪•尤素福:乐师,释梦者
尼克尔斯基:
------------------------------------------------------------
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17C 乐师 P99
穆斯泰•别依•萨博里阿克17C 土耳其巴夏 P167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四):第二遍看完,书评还是很难写啊
难写的原因自然在于,某跟文学的相性一向不算好。当年英国文学课因为期中期末都是论文,所以有旁门左道可走,结果也不错,等到回答主观题的美国文学课考试,立刻就现原型了。
勉强来写的话,首先,第一遍看到绿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几年前的fate/stay night: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终于完满落幕,然后,时光倒转至一切的开端,某个时刻突然你多了一个选项可选,于是故事就此不同。虽然主线依然,但很多新的真相纷纷出现,甚至可能颠覆一开始的认知。接下来,故事第二次落幕后,时光再次倒转。第三次故事的结局,才是真正完美的结束。(当然啦,后来还出了资料片,这资料片的汉化是个大坑)
而这部书更为纷杂:分三次把三个分支的无数拼图块抛洒下来,一个拼图块虽然可能是由这个分支的其它块生出来,所以属于这个分支,但填补的却是另一个分支的空白;又有很多图案要三者放在一起才有意义。如此纠缠迂回,最终的图像却始终只在三片色彩下若隐若现。就如书中的一根树枝三个分叉的比喻(不完全一样,但类似的比喻多次出现),三个分叉都源于同一枝干,有相似却又各自不同,乃至冲突,而且三者加起来也不等于根源,中间还有很多空隙。这感觉实在很奇妙。
我唯一的不满是,这幅华丽到诡异的图像,指向性却不甚明白,如同一个迷宫作者设计了入口而没设计出口(我觉得阴本独有文字的后半段正好用来形容这种感受)。这样的细节更是数不胜数(所以看到最后那段关于民主的论述总觉得有点违和)。当然,这大约是我的偏见,所以我跟文学相性不太好。
,绿书里介绍哈扎尔这个民族和国家时列出了它的汉文写法:苦撒。而据说,“历史上确实有哈扎尔这个国家,它还是一度横跨亚欧大陆的强国。这个民族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突厥帝国崩溃后出现,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说法,其衰落是在公元10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时期”。不知这话靠谱靠谱,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还应该有一本书,来自某国的典籍记录?说不定还比这三本更完整?不过,唐宋时期的信仰是……貌似某国就少有统一的信仰嘛……嗯,美学上是个缺陷,还是算了。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五):一本辞典,一首殇
一
“哈扎尔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民族,由于翻译不同,百度百科上可以检索到的是“可萨人”。然而可萨人建立的可萨汗国就像草原上的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并未留下太多的文字史料,于是给了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充分发挥的空间。
我承认辞典是一种比较枯燥的文字,豆瓣网上也看到有不少人对这本书发出了负面的声音:
“没看完,看不完,不是我那杯茶”;
“ 读了五十页就弃书了,实在把握不住它想说什么“。
这些人可能忘了在《哈扎尔辞典》的扉页上写的这么一句话:
”在此躺着的这位读者永远也不会打开这本书,因为他已长眠于此。“
我是先看过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看这本同样现实、同样魔幻的《哈扎尔辞典》就感觉适应多了。一杯清茶,一盏明灯,一个悠闲的寒假,正好消磨掉这本慢书。
关于书的情节我不想说太多,各式溢美之辞也早已被用滥了,我只是希望分享一种读完全书后恍然大悟的感觉。那些读不下去的人想必是被本辞典错综复杂的词条和旁征博引的众多史料绕得晕晕乎乎。但当你即将放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此书的作者可能正在某处得意地奸笑呢?三个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对于哈扎尔人信仰的论辩,捕梦人与魔鬼的千年斗争,光怪陆离的民族风俗……只有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闯出作者用想象力设下的迷宫,得到他留下的宝藏。
二
听来的一个故事:
有个外国人,在上海工作生活很多年了,别人一直不知道他的国籍。有一天人家问他,“你哪个国家来的?”那哥们十分忧郁地说了一句:“我的国家曾经叫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对于曾经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解体了,之后爆发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本书的作者米洛拉德•帕维奇生于1929年,逝于2009年,正是前南斯拉夫籍塞尔维亚人。尽管初版是在1984年,但米洛拉德身处小国林立、鱼龙混杂、曾经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又怎能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无动于衷呢?所以我总以为,作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内心是十分悲痛的。哪怕他已经以一种最最枯燥的文学形式——辞典来掩饰,可那份悲痛还是像潮水般从字里行间涌出,把我淹没。
这些曾经在中亚草原上驰骋的哈扎尔人最终被其它文明同化,隐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个民族兴起过,然后又悄然衰落,不知所踪。
《哈扎尔辞典》洋洋洒洒二十万言,又何尝不是作者在为自己的民族作殇呢?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六):获得永生的两种方法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最后一页,我感谢了朋友K,我钟爱的几乎所有作家都是他最先介绍给我的。他最早介绍给我的作品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时候我们都是高中生,一共六个人,坐通宵火车跑去北京参加一个电视台的智力竞猜比赛,他就是在那列火车上向我们推荐《尤利西斯》的。我从北京一回上海就去学校门口的盗版摊买了本《尤利西斯》,字非常小。那之后K渐渐地成为了我的某种导师,我随着K的兴趣读到了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赫拉巴尔等等当时还比较小众现在已经非常普及的名字。因为K的偏爱,我开始认为一本书最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隐去的话,然后是书之外的话,然后是题献和感谢。书的正文不值一提。他第一次跟我提起列奥•施特劳斯的学说时,我甚至以为这位哲学家是他依照自己的趣味编出来的人物。
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K在香港工作,最近某个周末回上海,买到了我的书,他说,“因为时间关系只看了书的最后一页。”
过几天,K又说,生命中最健康的东西是虚荣。他说他再推荐一个作家给我吧,米洛拉德•帕维奇。他说看完《哈扎尔辞典》,他明白了自己最喜欢的虚构风格是介于帕维奇和博尔赫斯之间。
--------------------------------
我在去往马丘比丘的通宵巴士上读完了K推荐的《哈扎尔辞典》,这本书显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博尔赫斯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可以说,《哈扎尔辞典》具体实施了《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里的构想。
这让我想到好多年前,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刚出现,我刚读完了K推荐的牛逼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便想在百度百科里面靠建立和篡改词条来编造一个像特隆一样的虚拟王国。维基的审定制度比较严格,而百度的词条简直可以随心所欲的修改。我最早编造的是一种已经灭绝的蕨类植物,然后开始编造一部并不存在的电影的剧情简介。我野心勃勃,没过几天,已经为我的虚构百科全书搭了一个架子,多少想象中的动物,多少不存在的都市,多少消逝的民间艺术,大师从未画过的画。我建立了一个自觉精巧的系统,如何从现实世界不着痕迹地过渡到虚拟世界,我小心翼翼地在虚构的词条中平衡虚构的和真实的词条。有一天,虚构过的词条太多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于是我开始不断更新一张表格,提醒自己哪些词条被自己动过虚构的刀子,省得我自己也再也分不清虚构和现实……
好多个星期之后,我自豪地向K展示自己的成果,一一指出那些顺利通过百度百科审查的虚构词条。K只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还要保存那张能让我区分虚构和现实的表格。K评论道, “隐藏一片叶子最好的地方是森林。”
K的话让我那几个星期的努力瞬间成了一个沾沾自喜的低级游戏。我停止制造虚构的百度词条。K让我意识到,只有一类人能成为有趣的虚构制造者:那些诚心抵达现实而浑然不知自己在制造虚构的人。在这一类作品中,我觉得最成功的例子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二成功的例子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我还非常推荐一位看似名不见经传却拥有诸多笔名的学者A. D. Harvey,他在抵达现实却制造虚构的路上走得更远,并依靠一种特殊方法过着好几个人生,他的事迹详见这一篇叫作《当狄更斯遇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http://www.the-tls.co.uk/tls/public/article1243205.ece 。
《哈扎尔辞典》在这一类作品中只能列第二等(但仍然非常优秀),因为它虚构得过于明显,对梦的运用过于直白。我能想到的改进方法是大幅增加本书阳本中的现实成分,甚至阳本可以是一本严肃的历史学术书,只有阴本中稍微有些虚构情节。A. D. Harvey肯定能对此提出更加高明的改进意见。
--------------------------------
怎样总结K这个人呢?还记得我们六个高中生通宵去北京是为了参加一个智力竞猜节目吗?(我刚刚很惊讶地发现,这个节目居然到现在还顽强地播着。)狂热喜欢《尤利西斯》的K和一个狂热喜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女孩子组成了一队,最终拿到了季冠军。
最近一两年的智力竞猜节目越来越不好,不但题目简单,而且要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的时候要听起来特别酷,特别自信,特别牛逼,否则电视台根本不会选你上节目。我更喜欢我和K参加过的那种老式的智力竞猜,没有自我介绍,大家穿校服,不化妆。
我爱赛林格写的关于格拉斯家族七个子女的所有故事,这七个孩子的共同点是在少年时都参加过一档智力竞猜节目,并依次得了冠军。这七个孩子的精神领袖显然是老大西摩•格拉斯。
每当我想起K,(我想起K的次数比我见到他的次数要多很多),我想起西摩•格拉斯,以及在我看来最完美的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好日子》。在K写作高产的几年,我阅读K的文章就像祖伊阅读大哥西摩的信。当时的K写四类文章,看球笔记;有趣的数学难题;结构精致的短篇小说;诗。幸好K大学毕业就停止了写作,别说是诗,甚至连看球笔记也不写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用担心他重蹈 西摩的结局。
--------------------------------
以下是K多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叫作《获得永生的两种方法(一)》:
在《斐多篇》的开头,柏拉图写下了他所有作品中最惊世骇俗的一句话。这则对话中斐多(后世对此人知之甚少)描述了苏格拉底之死,并探讨了永生的意义。在被问及死刑当天哪些人在场时,斐多列举了几个人之后,说:“柏拉图,我想,病了。”
马克思•布洛德曾经指出,这是柏拉图在所有对话录中唯一一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宣告自己不在场。[1] 这句话短促但力量巨大,迫使我们去接受(至少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如果柏拉图不在场,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苏格拉底的言行——在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时间里的一切言行——都不过是柏拉图事后的想像。即便柏拉图当时确实在场,他也一定在后来十几年中的某个瞬间感受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指示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让他推卸了记录第一手资料的责任,并获得了创造的自由。(这种设置多重叙事人以降低故事可信度的做法后来屡见不鲜,包括柏拉图本人的《会饮篇》。)我们读到的苏格拉底,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种秘密的延伸。苏格拉底是否有过如此光辉动人的场面已不重要,他的学生柏拉图仅仅通过无名之辈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就剥夺了苏格拉底的真实存在。始终是旁观者的柏拉图,就这样牵引自己鲜活的理想进入了死者那光芒万丈的躯体——穿过真实与虚拟的界限——传承万世。
[1]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柏拉图一共三次提到过自己,另外两次出现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但仅仅是为了表明另一个人与他的亲属关系。然而关于马克思•布洛德,我们有更多话要说。事实上,很多人相信,作为弗兰兹•卡夫卡的好友与遗嘱执行人,布洛德不但违背了卡夫卡死后不出版作品的遗愿,而且凭自己的意志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我们今天读到的卡夫卡,只是布洛德在死者身上的永生。
--------------------------------
多年前那个去往北京的通宵火车,我们六个高中生都没有睡觉,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真正通宵不眠。一个男生在疯狂地宣传《达芬奇密码》有多厉害,一个女生在疯狂地宣传《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有多厉害,而大家的宣传热情都抵不过K对《尤利西斯》的狂热,他让我们参观他那本厚厚的《尤利西斯》,在大家筋疲力尽又难以入睡的几个小时用动人的声音(他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主持人)朗诵萧乾所译的那些鲜有标点的长句子。对了,在那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还有一个男生在不断练习几种魔术把戏。在半睡半醒之中,我觉得这列火车将不断开下去,这个男生将最终无师自通地学会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而K能一直用漂亮的男中音读完《尤利西斯》的最后一个词。
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周末,正逢久旱的北京发射九十几枚高射炮来人工降雨,于是整个周末排水系统不好的北京城都淹了。我和我的智力竞赛队友,一个我已经认识十年的女孩子,被邀请去参观清华园。邀请我们的是一个学神,刚刚大三。什么叫学神呢,就是我和这个女孩子从小都搞理科竞赛,虽然学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是我们俩是读着他编写的竞赛书长大的,他还负责出过好几年全国联赛的考题。那个晚上,雨大得像要把马孔多镇淹没,清华园的水漫到了膝盖上面,伞没有用,于是我们都没撑伞。游园的一个多小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学神从头到尾没有说什么话,一直在用力唱张信哲的歌。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他们正在相爱。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七):评论哈扎尔辞典
1692年,宗教裁判所下令销毁达乌勃马奴斯版的辞典时,只有这两本躲过劫难,得以幸免。这样一来,那些胆大妄为的人或异教徒若读了这部禁书,定遭死亡之凶。谁若打开此书便会立刻全身瘫痪,胸口像被针尖刺中一般(更多精彩日志尽在空间日志大全网:www.njhylight.com,空间日志转载网:www.doii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