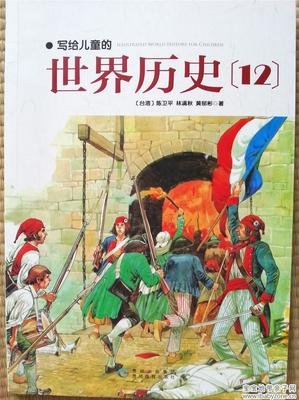《世界史的誕生》读后感10篇
《世界史的誕生》是一本由岡田英弘著作,廣場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 330,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治通鉴》的中华思想
162-163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帝国,从突厥汗国到回鹘汗国,一直对隋唐时代的中国造成威胁。从西元九三六年中国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帝国以来,在五代、宋朝时代,游牧民族站在了有利的地位。西元?年的澶州和议更确定了契丹帝国对宋朝的优势。
这个形式让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原本的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而住在皇帝统治的城市之中,使用皇帝制定的汉子的人是中国人,与出身的种族无关,而且甚至没有“中国人”这个用语。秦朝的人称“秦人”,汉朝的人称“汉人”,三国时代的人分称“魏人”、“吴人”、“蜀人”,晋朝的人则称“晋人”。这些全部代表了属于皇帝的人,没有种族的观念。
后来发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西元三一六年晋朝灭亡,皇帝制度一度消灭。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一直被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统治,中国人成了被统治的阶级。隋朝和唐朝都是鲜卑人的王朝,进入五代之后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又是突厥人的王朝。终于到了宋朝,中国人好不容易在睽违六百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收到高粱河的败战与澶州和议的屈辱,被迫承认同是游牧帝国的契丹帝国的优势。
六百年来在非汉人统治之下的汉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受损,而这个情势更带给他们严重的打击。“中国人”在此才终于有了种族的观念,他们开始主张,武力上面也许不如“夷狄”,但文化上面远甚于“夷狄”。这个主张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但这个主张却是与事实相反。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统治阶级都比被统治阶级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当然文化水准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就算在中国,统治阶级的“夷狄”,他们的文化水准也都胜过被统治阶级的“中国人”。中华思想是中国人病态劣等意识下的产物,而试图借由历史将这个思想正当化,以证明中国人优越性的史书正是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记载西元前四零三年(战国时代初期)至西元九五九年(宋太祖即位前一年)的历史。在司马光的年代,一个“天下”(世界)有两个皇帝并列,分别是契丹皇帝和宋朝皇帝。这以司马迁《史记》的架构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违背了“正统”的观念。《资治通鉴》的架构反映出了宋人超越了现实的情势,把历史理想化,希望能够挽回中国的名誉。
就像司马光的时代一样,南北朝时代也是两个皇帝并列的时代。唐朝的史观平等对待南朝和北朝,承认南北朝皇帝的正统。然而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在标明年代的时候,从头到尾使用的都不是在中国中心地建国的北朝年号,而是使用江南边境亡命政权南朝的年号。年号代表的是皇帝对时间的支配权,因此,《资治通鉴》的写法代表把鲜卑人的北朝视为契丹,且认为北朝的皇帝是假皇帝,拒绝承认北朝的正统。相反地,南朝虽然衰弱,但由于与宋朝一样都是汉人的王朝,因此男潮的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承认南朝的正统。《资治通鉴》将周朝以来的正统,经过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直接与宋朝接轨。这种写法是在强调只有汉人王朝的宋朝皇帝才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权力。在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对抗契丹帝国的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出自尊心受损的汉人为挽回自尊所做出的努力。
相对于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这个世界做出定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规范了汉人的种族观念。正统的观念与中华思想结合的结果,让之后的中国人愈来愈看不清中国的现实。
《世界史的誕生》读后感(二):第一章 一二零六年的天命-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17
历史是文化
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与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的世界。
首先最重要的是,历史与人类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没有人类的地方不可能有历史。“人类出现之前的地球史”、“银河系形成之前的宇宙史”等,这些是将地球或宇宙比拟成人类,将如果是人类可以当作历史的东西,以比喻的方式称作“历史”,这样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历史。
18
另一个重点在于,历史与时间和空间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广大世界的这里、那里,或是之前、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将这些事情整理并排序的便是历史,这一点无论是谁都无法反驳。
21-22
与对于时间的感觉相同,与历史密不可分的是文化要素,也就是记录。写下在自己眼中的世界,希望在当时的状态不复存在的未来时间里,这些记录可以唤起一些记忆。这属于高度文化,孕育自然,与自然同化一同生活的人类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想出要留下记录这件事。另外,为了留下记录,必须要有不输给测量时间的高度技术。创造文字、学习文字、活用文字,这些当然也是文化的一种,但在没有文字的地方,在木头上刻纹,在绳子上打结、记忆数字等也都是记录的文化。
《世界史的誕生》读后感(三):第三章 皇帝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司马迁的《史记》
58
日语的“历史”一词虽然用汉字书写,但这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的词彙。现代中文的“历史”一词其实是借用日语而来。日语的“历史”是在明治时期所创造的新词彙,用来当作英语“history”的翻译语。西元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的日清战争之后,在日本学习的清朝留学生将“历史”一词带回了中国。
62
到底什么是“帝”?
63
在“帝”字下面加一个“口”便是“敵”、“嫡”、“適”等字的偏旁。“帝”的发音原本也与这些字相同。从此可以判断,“帝”原本的意思是指“配偶”。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世界)之前,每个城市国家都有各自的地母神作为守护神。地母神是天神的妻子,产下了城市国家皇家的始祖。地母神的“配偶”天神,也就是“帝”。
69-70
实际上,夏、殷、周也称不上是一个王朝,只不过是在多数城市国家当中属于军事武力稍强的国家罢了。
当中的周朝建立“封建”制度。乍看之下,好像是统一天下,天子将国土分封给诸侯。然而,“封建”原本的意思是武装移民从母城市出走,在心的土地上建立子城市。“封建”下的子城市从母城市中独立,经营独自的政治生活,不受母城市的支配。从被周朝分封在山东的鲁国纪录《春秋》中可以看出,《春秋》将西元前七七二年至西元前四八一年的纪元以从鲁隐公到鲁哀公位置的历代鲁侯在位年数表示,而非以周王在位位基准,这就是最好的证据。由此可见,中国世界(天下)尚未成立,国家也尚未统一。
《世界史的誕生》读后感(四):書寫世界史的另一種可能
頃讀岡田英弘教授的舊作《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由於我沒有日文原版,所以把手邊的中譯本與蒙譯本對照著讀。感覺蒙譯本的譯筆比中譯本來得可靠一些。日文原版於1992年,經過了21年後才被譯介到中文學界。資訊略嫌陳舊。但仍可當岡田史學管窺看。雖然我不盡同意岡田教授對地中海型與中國型歷史的本質化詮釋(前者是以變化為主題的對決歷史觀,後者是不承認變化的正統歷史觀),不過第七章「從東洋史與西洋史到世界史」倒是有些不錯的討論火花。岡田教授認為傳統日本史學界的日本史、東洋史與西洋史三大分支,由於缺乏共同的分期標準,因此無法從中為新的世界史發展出一個適當的研究架構。例如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中將皇帝專制視為是中國走向近世的指標之一,但是在西方專制主義主要發展僅僅限於法國,並非整個西方都有同樣的發展,因此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指標。而一種從內陸歐亞視角所出發的世界史有潛力成為未來世界史學界的典範。
中文本譯文與編輯由於專業所限或手民之誤,因此出現了一些瑕疵:例如松贊干布誤植為松贊幹布(第141頁),塔塔兒部誤植為烏古部(第168頁),阿音札魯特應位於巴勒斯坦,譯文誤作巴基斯坦(第175頁)等等。但瑕不掩瑜。看得出來譯者應該是下了不小功夫去查找這些人名、地名與術語。站在鼓勵的立場上,有興趣的朋友還是可以找來讀讀的。
建議可以和杉山正明的《顛覆世界史的蒙古》(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21534/)一書對照著讀,會發現兩者有互相發明之處。
《世界史的誕生》读后感(五):一種寫世界史的方法
本書是廣場的蒙古史系列的最新作,岡田英弘坦白說一開始筆者並不認識,正如杉山氏筆者也是透過有它們的翻譯引進才得以知曉。日本研究遊牧民族史的有一種跟傳統中國不同的史觀,這對我而言是很特別的。
岡田氏在本書提出的觀點是“蒙古帝國的存在創造出了世界史的可能”,怎麼說呢?它主張,最初的世界史是由兩大“有歷史”的文明所構成,也就是希臘的希羅多德與中國的司馬遷,這兩個人分別撰寫了史學的先河:《歷史》跟《史記》,並建立起其世界觀。
在希臘,跟波斯帝國的對抗中塑造出來的是一種東西對抗,“正邪”之爭的視角,守護自由世界與專制奴役的戰爭,這成了日後「歐洲與亞洲不可避免的對立,而前者必然戰勝後者」的宿命論。
在中國,司馬遷建構出一個以皇帝制度為中心,掌握對“時間”的控制,撰寫“正史”,建立一種正統的框架,並在兩千年來一直運行其中。
這兩個文明各自書寫自己的歷史,並認為這就是“世界”。而把這一切串聯起來的,就是曾經征服了歐陸的蒙古帝國。只有在他們統治的時代,歷史學家撰寫史書時,才會開始把視野擴展到整個大陸,這才是世界史的真正開端。以此為契機,現代史家要開始撰寫一部真正的世界史,也是必須捨棄掉原本由這兩大文明所創立出的各自框架,找出一個能夠貫通一切的論述,才可能達成。
坦白說,岡田氏的觀點雖然對筆者而言很“新穎”,他在書中固然跟衫山氏一樣強調遊牧民族在歷史上的作用,但總讓人覺得有點牽強。固然,在所謂的“歷史的連續性”中,任何事件的發生必然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把事情都解釋成蒙古帝國的遺產,想來很多讀者都會覺得有點彆扭跟難以適應。畢竟這種主觀性的說法,好像把整個的一切都說成了是蒙古“刻意”為之的結果,會有這樣的感覺也不難理解。
不過,岡田氏的世界史撰寫的觀點,放在今天追求“全球史”的建構中,當然也是一種觀點,而且考慮到作者撰寫本書的時間點,這算是一種先驅。
順便一提,廣場這次請來的譯者相當的優秀,本書的翻譯相當流暢,筆者閱讀過程中並沒有感覺任何不順之處,此外,這次也都沒有糾到錯字,也是值得一提。
==========
這兩天回老家,把架上的柯嬌嬿的《書寫大歷史》(什麼是全球史)拿來翻幾章,除了看到推文中版友推的那本Abu-Lughod的書的簡介外,也讓筆者一直隱約覺得哪裡不妥的地方清晰了起來。
岡田氏對於日本歷史研究的批評是中肯的,這也是在對於過去整體史學研究都適用的論點。但他說要以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做為起點來建構世界史(全球史),是不是也太侷限於舊大陸,而忽視掉那些被他稱之為“沒有歷史”的文明。雖然岡田氏的本意應該是指“這是一種方法”,不過我覺得是過份強調了。
大概就這樣。
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一书,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虽着眼宏观,又不乏细腻处的丰富文献资料,不可不谓是一本经典之作。此书有两个主题:一是阐明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是两个拥有不同历史观的文明,并都对人类历史观和世界观造成了深远影响;二是提出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本书是对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探索,同时也是在从新的视角来诠释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
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是文化,而文化从本源上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区域性、民族性的烙印。但经过漫长时间的多形式的交流和融合,如今的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普遍价值,如平等、自由、民主、和平等。日益变化发展中的现实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从此看,本书的问世,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需求。
远在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用武力征服了广袤的亚欧大地,把大陆东西更加紧密的连接了起来。虽然面对浩瀚的人类历史,蒙古帝国犹如昙花一现,但它确实进一步打通了文明之间交往的障碍,促进了文明间的相互认知,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由此,可以说,目前我们对蒙古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仍需要深入的挖掘和探索。这方面,冈田英弘是个先行者。
既然是对世界史观的新建构,就更应该注意:在努力消除东西界限时,还需尊重区域界限的现实存在。如何做到两者的均衡,值得我们去继续注力。
《世界史的誕生》读后感(七):第二章 对立的历史——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对立的历史观
41-42
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借波斯学者之名提出的看法将世界划分成欧洲与亚洲,主张欧洲与亚洲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断地对立与抗争。这样的额看法成了地中海世界首部历史书的基础论调,“欧洲与亚洲的敌对关系”,这样的历史观成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这样地位的历史观贯穿西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现代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论调。由于这样的论调过于普遍,反而让西欧人、日本人或事其他国家的国民不自觉世界笼罩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然而,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与所创造出的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引发了许多不幸的事件,从今以后恐怕也将会是其他许多悲剧的主因。
44
从《历史》一书的大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罗多德的“研究”对象并非希腊人的世界,而是横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他想要描述的是对与几乎支配全世界的强大波斯帝国,甚至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一线曙光,最后奇迹似地获得胜利。
由于希罗多德的著书是地中海文明所孕育出的最初的历史,很不幸地确立了“亚洲与欧洲的对立是历史的主题。而对于亚洲,欧洲的胜利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种看法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持续影响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人对于亚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