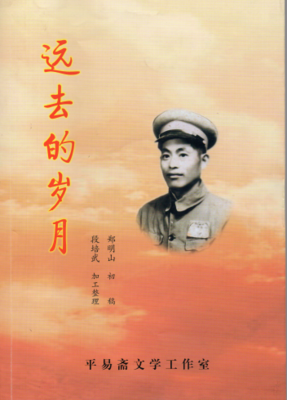《心的岁月》经典读后感10篇
《心的岁月》是一本由[德]保罗•策兰(Paul Celan) / [奥]英格褒•巴赫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心的岁月》读后感(一):來自罌粟花園的聲響
策蘭與巴赫曼的愛情從頭至尾始終是聚少離多,兩人相互廝守的時間僅僅是彼此生命中不值一提的片刻;但正是這疾逝如閃電的片刻,卻成為彼此最冰冷及最炙熱的光明,凍傷卻又灼燒了他們的餘生。正如巴赫曼的信中所言,他們的愛情,甚至是他們彼此的人生軌跡,都是具有示範性的,誠然,在我看來卻是最哀傷亦最完美的希臘式悲劇示範,完美得如同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而這本《心的歲月》,則不單單是來自冥河的哀歌,也同樣是來自罌粟花園的聲響。
《花冠》是策蘭的名詩,也是他贈予巴赫曼眾多詩作的其中之一。這兩位二十多歲熱戀的青年詩人,以愛情在一間屋子裡奇蹟般地催發了無數盛放的罌粟:
「我的眼沉降于愛人的性器:
我們相互凝視,
我們講述彼此的晦暗,
我們相愛如罌粟與記憶,
我們睡著如貝殼盛的酒,
如月亮血光中的海。」
其後巴赫曼于給策蘭的回信中寫道:「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詩,是對一個瞬間的完美再現,那裡的一切都將成為大理石,直到永遠。」(第7封信)
那也許是在倚窗便能夠眺望到維也納市政公園的公寓:
「我們在窗前相擁而立,他們從街上注視著我們:
人們知道,是時候了!
是石頭勉強開出花朵,
心臟不安跳動的時候了。
是時間將成為時間的時候了。」
這一情景在二十餘年後巴赫曼小說《馬利納》(1971年于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中的《卡格朗公主的傳說》里又再一次重現了:
卡格朗公主在震驚中說道:「我們將站在窗前,讓我說完!那窗將開滿鮮花,而每個世紀都將會有一朵花在窗后枯萎,超過二十朵,那時我們將認出正確的地點,所有的花都將變得和這裡的一樣!」而當公主說完,異鄉人沉默了;他籌劃著他與她第一次的死亡,他不再為她唱驪歌。異鄉人在可怕的寂靜中,將第一根荊棘刺入了公主的心臟。公主渾身是血地從她的黑馬上墜下來,她在高燒中微笑著譫妄道:「我知道,我知道!」
可來自克拉根福特(巴赫曼的故鄉)的公主與異鄉人的重逢,卻已不再是初遇時的甜蜜,卻是別離與死亡的前奏。
在策蘭詩《在埃及》中,化作水、走入水中的「異鄉人」是巴赫曼,而這裡欲殺死公主,并決意自殺的「異鄉人」顯然是作為猶太人的策蘭。而那些鮮花,是猶太人的鮮花,也是盛開于時間之中的罌粟,如同魔法般在來往的年月中散發著致命的芳香,竟也最終見證他們的死亡。
正是這首《在埃及》確立了策蘭與巴赫曼的戀情;1948年6月策蘭將這首情詩寄給了巴赫曼:
你該在異鄉女子的眼眸里,尋你在水中認識的她們。
你該把她們從水中喚出來:路得!拿俄米!米利暗!
你該把她們妝扮,當你躺在異鄉女子旁。
你該以異鄉女子的雲鬢妝扮她們。
你該對路得及拿俄米及米利暗說:
看!我睡在她一旁!
你該把你旁邊的異鄉女子妝扮得最美。
你該用路得的拿俄米的米利暗的痛苦妝扮她。
你該對異鄉女子說:
看!我睡在她們一旁!
在這首清歌式的情詩中,除了作為「異鄉女子」走入詩中的巴赫曼,這些棲沉在水中的女子路德、拿俄米以及米利暗無一不是出自《聖經》中的猶太女子。拿俄米與路德是《出埃及記》與《路德記》中失去兒子的母親及失去丈夫的妻子;而米利暗則是因懷疑神蹟患上麻風的猶太女神官,是帶領猶太人渡紅海的摩西的長姐。詩中策蘭以甜蜜的宣言向巴赫曼示愛,可在愛情之外他仍舊揹負著沉重的民族的枷鎖。
巴赫曼也在兩人重逢的1957年,曾以《米利暗》一詩應和策蘭:
向我們允諾吧耶律哥,讓《詩篇》甦醒,
約旦之水自你手中流出
讓劊子手們驚懼地石化
一瞬變為你的第二片土地!
你感化每塊石心,創出奇跡
連石頭都奔湧出淚水。
并讓你用熱水洗禮自己。
我們仍只是異鄉人,直待更為異鄉。
詩中巴赫曼引《聖經》中的《詩篇》(Psalter)呼應策蘭。而耶律哥則是約旦河畔前往聖城耶路撒冷苦旅中的最後一站,巴赫曼同樣以約旦河之水呼應策蘭猶太女子之水。她還又一次使用「異鄉人」的意象,來表明并迴應她對策蘭的愛情。
雖然策蘭曾在巴赫曼的眼中找尋到了如水的猶太女子,甚至找尋到了灰髮的蘇拉密特。可在而後的年月里,策蘭卻仍將巴赫曼當做了「異鄉女子」,他最終都未能逾越過彼此身份的鴻溝。
在1957年兩人的戀情重燃之前,策蘭對巴赫曼的詩歌甚少關注,他認為比起作為以德語寫作的猶太人的自己,作為日耳曼人的巴赫曼的成功乃必然的結果;在1959年的戈爾剽竊事件中,處於惡劣精神狀態下的策蘭甚至竟然如驚弓之鳥般地寫信給巴赫曼與弗里希,指責他們為謀害者的共謀。可恰恰相反的是,巴赫曼從在維也納結識並與策蘭相愛之後,她一直在積極地證明策蘭的詩歌是納粹滅絕行動最好的證言。她多次為策蘭策劃朗讀會;將他的作品宣傳與推廣給出版社、甚至是她工作的電臺;在她的詩歌及小說中,幾乎處處可見策蘭詩文中的意象及隱喻;在戈爾事件中,她寫信給許多文學界的朋友要求他們聲援策蘭。可即使如此,策蘭仍然無法真正地讓巴赫曼走入他的黑暗,走入他的沉痛之中,他同時也忽略了,同樣作為詩人,作為戰後前納粹黨人的女兒巴赫曼也有著她自己的黑暗。(但我不願亦不忍苛責策蘭,取而代之的卻是哀慟與傷懷:集中營沒有立刻摧毀了他,卻這樣慢慢折磨拷問著他,最後還是將他拖入了黑暗的深淵。)
終於,在1961年,兩人關係已幾近冰凍的時刻,巴赫曼寫了一封總結她與策蘭關係的信,這也是我認為整本《心的歲月》中最為感人的信箋之一。她如此寫道:「我常常感到心酸,當我想到你的時候,有時我竟不原諒自己,因為自己竟然不曾為你寫下的那些詩——竟然指責我犯有謀害罪——而恨你。你越指責愛你的人犯有謀害罪,你是否就越沒有罪了呢?」她情意拳拳地寫道「你想要他們因為你的毀滅而良心不安,而我卻不能夠支持你的這種意願……」(第191封信)巴赫曼誠摯而深切的情誼與對策蘭的希望與失望交織在這封長信中,她甚至在信末希望策蘭想想一直默默支持他,從未抱怨過的妻子吉瑟爾。然而最終她也未能將這封信寄出,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她由於害怕策蘭因為這封信而受到傷害才沒將它寄給當時精神幾近崩潰的策蘭。結果她給策蘭寄出的最後一封信竟是當年聖誕的祝福,他們的生命并從此陰差陽錯。(巴赫曼並沒有從此放棄對策蘭的維護!1963年,由於出版社未將阿赫瑪托娃的詩歌交由策蘭翻譯,反而給了納粹黨歌的作者鮑曼,她憤而收回了該書在此出版社的出版權。)
自1961年之後,兩人便各自墮向了生命的低谷與地獄,期間策蘭兩次弒妻未遂,并數次嘗試自殺,不斷輾轉在各個精神病院療養,直至1970年4月悲劇的發生——而巴赫曼在與弗裡希分手后也陷入了困頓,也同樣斷續地在醫院接受治療。可她所經歷的沉痛勢必不比策蘭少!策蘭身死之後,策蘭遺孀吉瑟爾寫信給巴赫曼通知她他的死訊:
「保羅自己跳下了塞納河。他自己選擇了孤獨而無名的死亡。英格褒,我又能說什麼呢?我不能幫助他,我多麼希望能幫助他啊。厄里克(策蘭與吉瑟爾的兒子)下個月才滿15歲。」(第230封信)
便縱是巴赫曼也許已得知了這個消息,但這封死神誥命般的信函所帶來的摧毀性能量是可以預想的。孤獨而身處異鄉的巴赫曼,肉身或許還苦楚地支撐著,而精神卻已隨著策蘭,與猶太女子一同死逝而去,沉入水中。她在1973年逝世于寓所內由於菸頭未熄滅而導致的一場火災,而此前她已多次服用過量的鎮定劑。
無論故事的結尾是如何地讓人心碎,但我依舊還是想回到巴黎,回到曾印刻著他們最絢爛時刻的巴黎,回到那個傍晚點起煤氣燈的巴黎,在那裡,策蘭寫下了《旅途中》:
那個鐘點,當灰塵成了你的扈從,
你巴黎的屋子成了你雙手的祭壇,
那家農莊,一架馬車為你的心停駐。
當你啟程,你的發幾欲飄飛—— 那是禁止的。
留下并揮手道別的人,一無所知。
而巴赫曼則寫了美麗而滿懷憂傷的《巴黎》:
如果我們,因鄉愁恍惚
直至頭髮散落會將如何,
停在此處并問道:如果我們,
駐留了美景又將如何?
登上光明的車,
也醒來了,我們失落,
然而我們不在之處,是黑夜。
曾經激烈的死亡與傷害在漫長的時光中凝聚為微小的沙礫,但罌粟花季依然一年一度,豔麗無端地覆蓋了整座花園,靜默地被夏天吹開去,或者為墨黑的雪花遮蔽。斗轉星移,當鏡頭定格在一張越洋的明信片,或者一張舊照片上時,他們未曾講述完的愛情故事,像一句箴言,輕輕省省以藍墨水寫在了背後:
他是她凱爾滕柔情的慰藉與羅馬冷酷的幻滅;而她則是他維也納未竟的浪漫及巴黎無盡的鄉愁。
*又及:最後我想指出的是,《心的歲月》是兩位偉大詩人之間的書信來往,巴赫曼在其中佔着極大的比重。而譯者似乎則過分偏袒于策蘭,給我的感覺是幾乎未曾研究過,甚至未曾讀過巴赫曼的作品。
**記錄疑似錯譯
31處,《在埃及》一詩首句,原文為“Sei das Wasser”,應為祈使句,意思差不多是“be the water”。譯者譯為“那是水”。
143處,“Mirjam”簡單按音譯為米爾楊(這是一個男名!),應為專有人名,米利暗。
476處,策蘭詩題“Schwarze Flocke”;同一詞組出現在巴赫曼詩的中,譯者譯為黑色碎片。策蘭詩中明顯含有雪的意向,首句便有落雪的描寫,認為應譯為黑雪花。
巴赫曼詩中“beschneiten”(被雪覆蓋)譯作切割,疑為看成beschnitten(或beschneiden)。
477處,“Und ich gehör dir nicht zu.” 譯作我再也聽不到你,原意應為我不屬於你。 疑為看成zuhören。
我手頭所擁有的僅僅不過是一些兩人的詩歌,因而不得不懷疑全書的可靠性。
《心的岁月》读后感(二):不让人绝望的窃窃私语(侯磊/文)
也许是对欧美现代文人之间的八卦缺乏关注,我最先读的是巴赫曼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杂文、广播剧,记住的是她的小说,后来才读了保罗·策兰的诗。但直至拿到这本《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我才想起来,巴赫曼也是诗人,他们原来是没能最终在一起的一对儿。
保罗·策兰与巴赫曼的生命之中多有交集,他们都是出身于多语言、多民族混杂的地区,但都以德语作为主要语言来生活和写作,还都有一定的精神病史。策兰大巴赫曼六岁。他们在二十多岁时相遇,一起相恋十年,见面十二年,通信将近持续了二十年。在1970年,策兰一头扎进了塞纳河,而仅仅过了三年以后,巴赫曼不幸因为火灾去世。他们都是在五十岁以前英年早逝,把最为黄金的年龄、最好的作品、最真挚的情感都献给了对方。
翻阅这部诗加上注释能有500页以上的书信集,开始以为会多么难读。实际上并非如此,书信就是书信。它行云流水,诗意盎然,是两个诗人之间的窃窃私语,彼此在信中有自述、有抒情、有约会、有表白、有分手、有复合,大凡催讨稿费、策划出书、创作安排、打笔仗等文人们的生活剪影都面面俱到。巴赫曼写给策兰一般都是“亲爱的,亲爱的保罗”,策兰也多次回以“我最亲爱的”。他们之间会这么说话:“当然,你的沉默不同于我的沉默……如果把它们放在天平上,与你的遭遇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如此写了半天,都是两位诗人之间的窃窃私语,似乎读不出他们指的都是什么事情,而等到数行以后,才发现这样迷人的句子:“我曾经爱过你,至今依然如此,完全没有变,在一个平原,那里曾是"栗树的对岸"。”这才是他们之间所要表达的。
自从在22岁那年父母被送入集中营并最终被杀害在那里,以及自己也进了劳改营而侥幸活命开始,策兰的文字受了伤,直至他投入塞纳河以后还不肯愈合。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策兰恰恰这样野蛮地写了下去。听他自己朗诵的代表作《死亡赋格》,虽然不懂德语,但能听出其中渐进的节奏和音律之间如山的气势。他的诗远比文字所表现得要宏大的多。在没有国籍、没有财产、没有固定工作的情况下,策兰在巴黎永远是流亡的状态。虽然他很快在文坛上名声鹊起,却又遭受到前辈文人家眷有关“抄袭”的攻击。实际上策兰天生就是个无法治愈的病人,而与居住在奥地利的巴赫曼通信就成了治愈和上来透口气的方式。这种方式从他在劳改营中就开始了,是写信让他们不会绝望。
其实巴赫曼才是整部书信集的主角,全书中策兰写给她的有90封,而她写给策兰的达到了106封,在策兰逝世后还与策兰的妻子有25封通信。在通信过程中,她一直占据主动。巴赫曼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恋爱,她的文字充满了女性的敏感和神经质:“然而,如果你再也不能够,或者已游入了另一个海洋,那就用你的手拉起我,使我不致沉溺其中!”在通信中巴赫曼像个初入爱河的少女,而策兰还是像个诗人。他的信篇幅不长却有不经意间的雕琢,有的时候干脆就寄诗、送诗集、写贺年片。看来即便是在恋爱中,策兰也难以忘记自己的诗人身份。或者说,最好不要与男诗人谈恋爱,他们把最真挚的感情没有留给女人,而是都留给了诗歌。
保罗·策兰的诗集在大陆目前仅有两个版本,巴赫曼还没有单独的诗集,虽然他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大名鼎鼎,但对于他们的阅读和研究则刚刚开始。对诗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写东西拒绝平淡,不论写什么都是极其跳跃性的语言,仿佛每个词都想奋力从句子中跳出来。尤其是诗人的书信,更是凝结着他们不经意间跳动的乐章。如果有了对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的《三诗人书简》这样的阅读经验后,那么对由诗人兼翻译家芮虎、王家新一起翻译的策兰和巴赫曼的书信,则更会是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原载于7.12北京青年报)
《心的岁月》读后感(三):《心的岁月》
这两天我一直在海德格尔的精神世界里漫游,今天当我读完这本《海德格尔》,一下想起策兰和巴赫曼的书信集《心的岁月》,想起在那本书中读到过策兰对海德格尔评价,今天找出来重新阅读,才发现自己在这本书里曾经还写过那么多读书感想,当时由于自己懒惰,也没好好把这些感想整理出来。 策兰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就像王家新老师所说:“他们一个是里尔克之后最卓越的诗人,一个是举世公认的哲学大师;一个是父母双亲惨死于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一个则是曾对纳粹政权效忠并在战后一直保持沉默的‘老顽固’。”他俩之间的情感是非常矛盾和复杂。因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历史关系显然是策兰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实际上我读海德格尔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以前我无法读他的文字,在感情我就不接受海德格尔,就没兴趣去了解他,这有点像我根本无兴趣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前些日子读完《爱这个世界》后,却激起我了解海德格尔的兴趣。这完全是因为汉娜.阿伦特的之故,汉娜.阿伦特对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的感情是如何保持终生?他们俩的政治理念是那么不同,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又是反犹主义,并且海德格尔一直是她心中的“思考之王”……也可以说因为阿伦特对她老师的感情,让我对海德格尔产生了好奇。
《心的岁月》读后感(四):奥斯威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王家新/文)
“心的时间,梦者/为午夜密码/而站立……”这是策兰1957年写给巴赫曼的一首诗的开头部分。多年之后,“心的岁月”成了这两位诗人书信集德文版和中文版的书名。
□王家新(诗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保罗·策兰(1921-1970)和英格褒·巴赫曼(1926-1973)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然而,维也纳对策兰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后来的二十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语战后文学史上一个双星映照的时代。
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纳粹的恐怖喧嚣深怀厌恶和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她也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1952年,已在诗坛崭露头角的巴赫曼力荐策兰参加当年的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并在信中要策兰一定带上《死亡赋格》朗诵,对策兰的成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戈尔事件”中,也是巴赫曼率先站出来为策兰辩护。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1970年5月,当策兰在巴黎跳塞纳河的消息传来后,她随即在自己的小说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因为他已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强迫运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
因此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悲剧故事,它折射出战后犹太人和德国民族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集中了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最为纠结的历史、政治、道德和文学问题。这些书信也不仅仅是两位诗人人生、创作和爱情/朋友关系的记载,也同样是战后德语文学的重要见证和珍贵文献。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诗学后记”所言:它们“是1945年后的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书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作为奥斯威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最重要的出版社苏尔坎普在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后,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这部书信集(它收入两位诗人自1948年至1967年20年间的196件书信,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男友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的25封相互通信。根据出版惯例,这些书信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它很快成为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引起广泛注意和反响。它不仅为一般读者展现了这两位伟大诗人更为隐秘的一面,也为策兰、巴赫曼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就文字的深刻优美、扣人心弦而言,其中很多书信本身就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
我们是在2009年初开始翻译这部书信集的。这些书信,把我们重又带回到那“心的岁月”里,带回到对两位诗人的心灵之谜、命运之谜的探寻里。书信集的第一封即是策兰在维也纳期间为巴赫曼的22岁生日写下的一首诗《在埃及》:“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成为水!”它震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诗题“在埃及”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而流亡的沙漠与在异乡女人眼中感到的“水”,首先就构成了一种命定的对位关系,这就如同策兰接下来为巴赫曼写下的另一首名诗《花冠》中的“罂粟与记忆”(“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一样。为什么是罂粟?它艳丽,“有毒”,可提炼出鸦片,而鸦片是一种麻醉、镇痛物质。幸存者也想忘却,不被“奥斯威辛”的死亡幽灵纠缠。所以“罂粟与记忆”正好显示了幸存者那种既想通过爱情忘却、但又不得不去追忆的深刻困境。
【奥斯威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
那么,策兰对巴赫曼又意味着什么呢?书信集最后的“诗学后记”显露了一个密码,那就是巴赫曼早期名诗《延期支付的时间》中嵌入的一句“你不要回头张望”!仅此一句,将俄耳甫斯神话引入到她自己全部的生命中。因此德文原版的编注者称策兰与巴赫曼为“1945年后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
天才的歌手俄耳甫斯未能把自己负罪的爱人带出冥府,他自己最终也“身首异处”(只留下“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乔治·斯坦纳语),这就是命运!而从神话回到历史,从这个“1945年后”的再版故事中,我们听出的,则是“奥斯威辛”的持久回声——它在策兰、巴赫曼的生活、创作和两人关系中都留下了深重的痕迹:“紧压着我的死者,/都缄默不语。/无人怜爱我/向我摇晃灯盏!”(巴赫曼《流亡之歌》)“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策兰《翘起的嘴巴》)
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位诗人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在我看来,远远比文学史上一些类似的“佳话”要更深刻,更富有历史的含量,也更能对我们的心灵构成冲击。“一条弓弦/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策兰《里昂,弓箭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就不时地感到这根神秘的绷紧的“弓弦”。早期的通信是那样温柔,让我们沉浸在灵魂的倾诉声中(如巴赫曼早期致策兰的那些书信),而到了后来,爱情的复发不仅迸发出令人炫目的火花,也给他们各自带来了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策兰自己后来有了妻子和孩子);随着“戈尔事件”(伊凡·戈尔遗孀对策兰“剽窃”的指控)伴随着新一轮的反犹浪潮愈演愈烈,那一封封充满呼救、误解和指责的通信,也成了“历历可数的病痛”,那根不可见的“弓弦”也绷得更紧了!说实话,在译到巴赫曼致策兰的最后一封长信(未寄出)“我居然不恨你,那简直是不正常”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而策兰妻子吉赛尔1970年5月10日给巴赫曼去信报告策兰的噩耗:“保罗自己跳下了塞纳河。他自己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也使我久久地不能自已……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我不禁想起了阿多诺当年的论断。借用这个说法,在论及策兰与巴赫曼时,我们同样可以问“奥斯威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这部书信集给予了某种回答——它是肯定性的,但又是否定性的,是否定性的,但又是肯定性的!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使我体会到命运的黑暗,心灵的挣扎和无助,以及痛苦对生命的窒息。这一切,更使我感到一种生命的光辉,爱和牺牲永恒的意义。
http://site.douban.com/110384/widget/notes/283957/note/288440533/
《心的岁月》读后感(五):更久远的黑暗,更复杂的爱情
美国作家约翰•巴思曾在他的小说《烟草经纪人》里这样赞美诗人:
“是谁比诗人更需要神灵一般的天赋?诗人有画家般的眼睛,音乐家般的耳朵,哲学家般的心灵,律师般的雄辩;他仿佛神祗,看得见事物的奥秘灵魂,看得见它们形式下面的本质,它们最秘密的关联。他仿佛上帝,洞察善与恶的源泉,洞察凶手心灵里那圣徒的种芽,修女心中那淫荡的蛆虫。”
诗人们自然该享受这样的赞誉,但一切是有代价的,因为他们有异常敏感的心灵,他们无法过庸常的生活,庸常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简直生不如死。如果有人开列一个古今中外死于自杀的诗人的清单,那将是骇人的。
1970年4月的一天,著名诗人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飞身一跃,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年仅49岁,给死于自杀的诗人的清单了又添加了一个名字。策兰之死是犹太人之死、幸存者之死、诗人之死,策兰死时二战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但死亡的种子其实在他的早年就已经种下,他的死一直可以追朔到他“更久远的黑暗”,而他与巴赫曼的爱情,因为其深重的苦难,远不止爱情那么简单,或者说是更复杂的爱情。多年后,人们把他与奥地利女诗人英格褒·巴赫曼的通信结集为《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出版,试图追寻这两位诗人的心路历程,破解早早埋在策兰心灵深处的死亡秘密。
在《心的岁月》所附的《诗歌的信件秘密》中,两位巴赫曼的研究专家这样说:“在信件里,两个都保留着各自一次的‘声音’与‘沉默’,只是比诗歌中的信件秘密更没有保护,更带有放弃的意味,也更加矛盾和具有戏剧性,因为在这里是两个死亡的‘灵物’以自己独特的出身和历史在共同而分别寻找自己的道路。”这可谓是对策兰与巴赫曼信件最精确的解读。
1948年春天,策兰与巴赫曼在维也纳相识,很快陷入热恋之中,巴赫曼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策兰给她的心灵带来的悸动:“他极具魅力,却对我产生了热恋,这给我枯燥乏味的写论文的日子无疑增添了些刺激。”巴赫曼的激情也很快被点燃,在随后的她与策兰的信件中这种激情一再地得以展示,“你,美丽和忧郁,分割我飞逝的日子”、“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却是非常幸福的,即使在非常糟糕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对方最可恶的敌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思想总在找你,不止是作为我最亲爱的人,而也是作为同样的一个失落者,我们都需要一个地方保住自己。”而策兰也不乏激情的表白:“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是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
都就像大多数陷入热恋中的男女一样,在经历了最初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之后,他们也相互指责和埋怨起来,“你创造了那些我必须承受的混乱的元素,它们很无情,就像我过去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你使我遭受的伤害远比我过去对你的伤害大得多”、“你想要他们因为给你毁灭而良心不安,我却不能够支持你的这种意愿”,“你曾经对我说,你把我看得非常轻,同样真实的是,你同样对待我比对待所有别的人都更沉重。”,“我真的想着她(指策兰的妻子),并为她的伟大而坚强感到钦佩,而你却缺乏这些……她的自我牺牲,她的美丽的骄傲和忍耐对来说比你的诉苦更重要。”但即使在最怨恨的日子里,巴赫曼都企图打造一条船,把策兰从绝望中带回来。
策兰仿佛一个落水者,虽然巴赫曼向他伸出了那只并不有力的手,但他还是慢慢沉了下去,直到被彻底淹没。抛开他们两人的诗人身份,他们两个的相识、相恋到最终分开,其实与普通的男女并无不同,但一旦与他们各自的宿命纠结在一起,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生命则更充满了悲剧性。由于他们两个经历与身份的巨大不同,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会有结局,也注定了他们虽然都彼此想相互拯救,都一切都是徒劳,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他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多次提及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不堪苦难的记忆,好不容易活过了艰难的岁月,却在和平时期选择了自杀,多年以后,他本人也走向了这条道路,而保罗·策兰,他可以说从未被拯救,一直被淹没。他的父母二战时惨死于集中营,他本人在战争初期在柏林亲眼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在战争中做过纳粹的苦功中,颠沛流离,侥幸得以活命,但死亡的阴影在他的心里驱之不散,成为他日后的诗歌永恒的主题,而《死亡赋格》正是其代表作,他在与巴赫曼的通信中称《死亡赋格》是“一篇墓志铭和一座坟墓”。像策兰的诗歌一样,巴赫曼的诗歌里其实也充满了死亡意识,她的《黑色的言说》其实也是一篇墓志铭和一座坟墓,只不过这篇墓志铭和这座坟墓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我再也听不到你/我们都在抱怨/然而如俄耳甫斯我知道/生命站在死亡的一边/你永远闭上了眼睛/使我通体变蓝。”
在策兰死后不久,巴赫曼在她的小说《马利纳》的手稿中特别加了这样的句子“我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死于河里,他曾经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在她的《致读者的诗歌》中,她这样写道:“如果你死去,我就要跟随你,你将转身朝向你,即使我受到被石头砸死的威胁,我将鸣响……并将让石头开出花来。”
策兰死去三年多一点,1973年9月,巴赫曼在罗马寓所死于一次火灾。
===
刊于2013年12月4日《都市快报》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kb/html/2013-12/04/content_1629917.htm
《心的岁月》读后感(六):《心的岁月》:“我的思想总是在找你”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分离,才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书信文学。而分离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思念,还有无数沉重与黑暗的岁月。当你面对面看着对方,即使没有任何言语,也胜过千言万语。如果分离,就算通过信件无穷无尽地诉说,也总会有阴影慢慢从心底滋生。对两位诗人而言,分离成就了思念的寄托,思念成为了诗歌的情感;而对于恋人而言,分离只会制造裂痕,无数美丽的误会,直至悲剧的发生。
《心的岁月》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与奥地利诗人英格褒•巴赫曼来往的书信集,一本名符其实的分离之书。分离对诗歌是幸运的,对恋爱中的诗人却是不幸的。1948年5月,策兰与巴赫曼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其时,策兰二十七岁,巴赫曼二十二岁,前者是一位年轻的流亡诗人,后者还是一名在维也纳大学读哲学博士的学生。也许更为重要的裂痕源自记忆与身份的差异性:策兰是一位背负着大屠杀记忆的幸存者,犹太诗人,而出生于奥地利的巴赫曼,她的父亲参加过纳粹军队,她终生都背负着这种耻辱与罪责。但在爱情到来的时候,一切都被忽略了,两位诗人之间的相爱多了很多心灵的诗意,却对他们之间巨大的鸿沟视而不见。“我可以比别人更能理解你的诗歌,因为我们曾经在里面相遇”。巴赫曼写给策兰的信中这样诉说,“我常常想念你,沉湎于你的诗歌,并在里面与你对话……男人们以各种方式围绕着我,对我却没有什么意义:你、美丽和忧郁,分割了我飞逝的日子。”爱情没有任何逻辑性,爱情唯一的逻辑就是飞蛾扑火,巴赫曼主动示爱的时候,很少留意到这个“陌生而黝黑的”年轻人为何总是沉默,就好像背负着整个世界的苦难。
策兰一家是生活在切尔诺维兹的犹太人,1921年他出生不久,这个地方归属了罗马尼亚。他的父母身上都有可怕的经历,先是苏军占领,之后是1940年和1941年的德军占领,然后是强迫劳动。1942年罗马尼亚开始清理不受欢迎的犹太人,一天晚上,策兰因为去参加朋友的聚会躲过了灾难,他的父母被关进了劳改营,被驱逐到德国人占领的乌克兰,死于残酷的疾病与枪决。在他的父母驱逐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策兰也被迫加入了劳改营,直到两年后的1944年年初才安然回到家中。1945年,诗人策兰背负着苦难与记忆,孤身一人开始流亡生涯,先是到了布加勒斯特,1947年年底到达了维也纳。
策兰在维也纳写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写给巴赫曼的。巴赫曼在1971年的小说《马琳娜》中虚构了一位来自东方的陌生人故事。他有着乌黑温柔的眼睛,穿一件披风,声音动听。在这个故事中,巴赫曼从策兰的诗歌中吸取了很多灵感,引用了很多句子,尤其是策兰的名篇《花冠》:“我们相互望着/我们叙说黑暗的事/我们相爱如罂粟和记忆/我们睡了像酒在螺壳里/像海,在月亮的血色光芒里。”罂粟花成为了爱情的象征,但罂粟花的迷狂与沉醉,也给他们的爱情注入了一丝不祥。在巴赫曼的生日,策兰送了一束罂粟花。在1949年6月24日的信中,巴赫曼说:“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然而,我这里却不是‘时候’。我饥渴着什么,却又得不到,这里的一切都浅薄而陈腐,困倦而陈旧,无论新旧都是如此。”此时,策兰远在巴黎,巴赫曼在维也纳,他们分隔两地。
在巴赫曼的那篇小说中,公主问来自东方的陌生人:“你一定要回到你的族人身边去吗?”陌生人回答:“我的民族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历史更悠久,这个民族已经播撒在风中。”这是一个流亡者的选择,尽管有巴赫曼在维也纳,他的第一本诗集《骨灰瓮之沙》出版在即,考虑到艰苦的生活环境,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策兰还是决定离开维也纳前往巴黎:“我并没有在那里住很久,因为并没有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不知道巴赫曼看到这句话会是什么滋味。爱情不能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全部证明,她无法了解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心中有多大的精神创伤,爱情不能治愈他的伤痛。他全部的生活都好像一只惊弓之鸟,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巴黎为他的流亡提供了一个更好精神栖息地。他的法语流利,他早年曾经就生活在这里,当然,最重要的与那些心目中的诗人波德莱尔、维尔伦、韩波、超现实主义者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是一种逃离孤独的心态。
1948年7月,策兰达到巴黎,开始了另外一段艰难困苦,孤独难熬的岁月。他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诗人放弃写作,“即便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写诗所用的语言是德语。”在巴黎用德语写作意味着没有读者。在这里,他以工人、口译者和翻译的不同身份挣扎着,他还教人学德语和法语,同时自己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和德国文学。在最初的这段日子里,他几乎没有写诗,保持了沉默。在1949年8月20日的信中,策兰对巴赫曼产生了忧虑:“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的沉默也许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至少从这部书信集《心的岁月》中,我们所得到的印象,策兰在这段感情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他的爱意多少有些冷淡,懒得回应,不是巴赫曼想要得太多,而是策兰能给的太少。爱情总会有失衡与沉默的那一刻,在分离这么久之后,每当他们两人有矛盾的时刻,策兰就会觉得很受伤,因为他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这个男人总是受害者一方,巴赫曼总是成为那个小心翼翼修补他的精神创伤的理疗师。巴赫曼意识到在他们的感情当中充斥了更多其他的东西,策兰受到的伤害,他总会敏感地怀疑自己的爱人。在策兰要回送给巴赫曼戒指后,巴赫曼一针见血地说:“你使用了一个失望,这个失望是别人给你的,你却用它来使大家毁掉。”也许是遥远的困苦生活摧毁了他们坚守爱情的信心,策兰一度对巴赫曼保持了沉默,分隔两地的爱情遭遇到了危机。而巴赫曼一直苦苦哀求他。在1951年11月的信中,巴赫曼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察觉出,我只是向你,而没有向别人,将自己的信念寄托在‘别人’身上,我的思想总是在找你。不止是作为我最亲爱的人,而也是作为同样的一个失落者,我们都需要一个地方来保护自己。”极力想挽回爱情的巴赫曼并不知道,正是在这个月初,策兰认识了法国富裕贵族家庭出身的版画家吉赛尔•德•勒斯特兰,他们于1952年底结婚。巴赫曼孤身一人,在远方,沉默,孤独,陷入抑郁,生活混乱。
这本书信集《心的岁月》,名字取自1957年10月20日策兰的一封信,此前的一个星期,他们两人刚刚恢复了中断许久的联系,爱情在友谊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这一次主动者是策兰,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了这份爱情对他多重要似的,他写了很多诗给巴赫曼,想重新点燃他们的爱情:“告诉我,你是否还想着我?”但这样的爱情太沉重了,巴赫曼不免遭受良心与道德的谴责,对策兰与吉赛尔的婚姻也是一个负担。1958年,巴赫曼遇到了瑞士作家马克思•弗里希,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策兰感觉到了她的变化,发现她陷入了新的爱情,并为她的幸福祝福。他们的感情重新回到了理性的轨道,内心的冲动与激情被掩藏在平常的言语之中,幻化成一首首迷人的诗歌。
1961年9月,巴赫曼因为策兰对她的误会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总结他们这些年复杂难描的情感关系,其中提到说:“我曾经对你说,你把我看得很轻,同样真实的是,你同时对待我又比对待所有别的人都更沉重。”撇开诗人这层神秘的面纱,这不过是一段再普通不过的爱情故事,最爱的人往往伤害最深,因为知道对方爱你,愈加肆无忌惮,恨不得把全心全意的信任与爱透支干净,还口口声声你伤了我的心。正如巴赫曼一直要求的那样:现在你必须原谅我——这不公平。可是爱情中哪有公平可言呢?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诗人,无论你写出什么样的诗歌,成为了爱情的俘虏,也会臣服于再普通不过的情感。也许与普通人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爱情能够留下许多文字与诗歌的见证。而我们这些普通人爱情,在时光中发酵,沉淀成岁月的晶体,在记忆中闪闪发亮。
思郁
2013-8-30书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德】保罗•策兰 【奥】英格褒•巴赫曼著,芮虎 王家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for《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