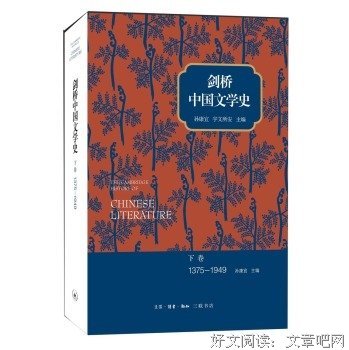《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读后感精选10篇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是一本由[美] 宇文所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页数:7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读后感(一):劍橋版「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英文參考書目
English reference attached to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studies on literature during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D.581-960)
equenced by the alphabet of the authors's name
Recommended by Stephen Owen & Xiaofei Tian
Doulist: http://book.douban.com/doulist/3510586/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读后感(二):那些意料外的文学史事
虽然从没系统接触过中国文学史,但我一直知道有这么一套书的存在,只闻其名而不知内容,通读上卷之后,有一种站在西方视角整体看待中国文学史的感受。
“整体性”是这套书编写时的一个目的,再一个就是强调文学作品不断被后世编订、完善,是变动的、受历史影响的过程,这些书写文学史的想法确实能让读者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有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章从早期写至西汉,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起初不太适应书中西方学者用偏西化的术语来形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但读进去之后,观览中国文脉,渐有“洞若观火”的明晰。最深的印象,是文中强调现在我们读到的那些汉前典籍,是经过西汉编订者的选择、编写的,编订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选择或舍弃了些什么主题,都会对典籍的传播、湮灭、保存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作品的年代和作者是不确切的,内容也在经历历时长久的、不断的完善……忽然明白,今天的孩子能大致读下来那些时间古远的文章、诗词歌赋,是很神奇的事情,而那些作品也许并不是原貌,后人将它们编写梳理得适当,才能不断被流传。
文学作品的题材流变是复杂的,朝代的突然更迭并不能斩断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所以书中不强调以朝代划分文学史,也不刻意沿用一贯以作者为文学史主体的写法,这样就保持了“整体感”,看得出文学在历史背景下的大体走向。比如四言诗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是庄正典雅的代表,赋产生后一直深受几个朝代写作者喜爱,诗即便在宋朝也是绝对主流,写词反而会受到鄙视……我们熟知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体裁划分,是极其简单便于记忆的说法,真实情况是具体而细微的。
整个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跟书籍形式的变化也有重大关系,印刷术出现前书籍是稀有物品,不便保存和流传,能拥有大量书籍的都是特权人士,他们又有闲,创作出文学作品也是当然的,但他们不凡的出身注定跟政治环境是连为一体的,皇室成员、高官、名门士族的身份会让他们深陷政治漩涡,很多人的命运、结局都让人唏嘘不已。南朝的萧梁,整个皇室都是文学爱好者,文学的昌荣盛极一时,但王朝毁于祸乱,从皇帝到皇子大都死于非命,爱好文学的梁元帝萧绎将十多万卷藏书毁于一炬,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毁灭典籍事件。
让人若有所思的,还有文中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质疑,因为此后文化传承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儒学反而有受益之处;苏轼感慨印刷术繁盛后人们读书不再像对待手抄本那样珍视,也让人想到现今对纸质读物没落的慨叹;东晋宫廷音乐的发展与几十年间因政治原因被不断俘虏、赠送而颠沛流离于各国的120个北方乐师有很大关系;日本、海外对唐代寒山诗的推崇极盛但国内却很少提及,也是让人讶异的文化事件……
除却文学史思想上的创新,从这本书里还能意外发现有意思的事。东晋到唐初,是作为一个章节写的,作者田晓菲详细描述南朝的萧梁王朝,让我对这段没怎么注意过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读至一半,突然发觉这个作者的名字仿佛在哪里见过,以前课本上《十三岁的际遇》的作者好像也是这个名字?一查,竟然就是她本人,她一路飞速发展的经历使她在35岁就成了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而她的老公,竟是本套书的主编宇文所安,她读哈佛时的导师——这真是一个能让人燃起八卦之心的故事啊。
此外,西方学者的用词套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上竟有种“反差萌”,一些特别的语句让人耳目一新到喷饭,比如战国末年的神话叙事热衷“天际旅行”,司马迁编《史记》“来超越自己家族的生物终结”,热爱发明的张衡被同僚批评他将太多的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科技”,在后来帝国管理者眼中刘歆是个“讨厌鬼”,谢灵运的山水诗被时人追捧,是因读者迷恋“来自远方的报告文学”……哈哈哈,读罢先大笑三声以示同情,作者真的不是故意的?
也许是文化差别原因或自己学识不足所致,整本书读起来略感生涩,但读完后是一种很扎实充沛的感受,这套书是面对西方大众的通读本,革新一下视角,转换一下思路,看到的都是新奇有趣的:原来,中国文学史还可以是这种模样。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读后感(三):閒來翻書: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1375年之前)
儘管書剛出的時候就知道是個刪節版,但還是沒有忍住買了下來。剛買的書是最有興趣讀的,間隔久了容易“審美疲勞”,所以也就儘快開始看了。
是書所謂“文學”,並不僅限於以往人們所認為的具有藝術性的文字,而幾乎包含了所有以漢語言文字書寫的文本——愈早期愈是如此。作者從甲骨文、金文寫起,除一般人們所理解的文學作品外,涉及《易》、《書》等經典、戰國諸子、史書、筆記、書信等等。涵蓋範圍之廣,遠超我個人的閱讀體驗。既然各種文字都被納入到“中國文學史”的寫作之中,也就涉及一個何謂“文學”的問題。編者在《導言》中寫道:“一部新的文學史,是一詞重新檢視各種範疇的機會。”他的意思並不在反思“文學”概念本身,而是在提出“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時的一種自覺意識。但在此過程中,他實際上將文學視作人們藉以表達其認同與定位的“工具”。也就是說,人們通過文字來表達自我,對個人與群體在宇宙——時間的歷史與歷史中的空間——的位置進行思考;反過來,文字之中都貫注著作者的理性與情感追求。如此說來,一切有形的文字乃至無形的口頭言說都屬於“文學”。更進一步,就特定的文字形態與其所以形成之國家民族而論,不同文字形態的“文學史”在範疇上是不同的,也是無法統一的。在對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學史進行研究的時候,是需要進行不同的處理的。
當然,這種擴大化的“文學”概念也引發另一個問題,即如何界定文學史與其他對歷史上遺存下來的文字進行的研究如史學史、哲學史等的區別。比如《史記》,在文學史、史學史乃至思想史、哲學史的不同“學科”內,其研究方式與視角究竟是否有所不同?其根本之區別又何在?如果說“文學史”更注重表達的形式與特色的話,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內在關聯實際上又無法使之成爲純粹的“文學史”。我這兩年讀的“文學史”著作如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李舜華師《明代章回小說的興起》,便總能不自覺地引發到對於史學史等問題的思考上去。這是我個人的胡想,抑或表明在對“文學史”進行反思的同時,也需要就“學術研究”之劃分領域提出質疑?
由於作者放大了“文學史”的視野,本書在多數時候都沒有孤立地討論文學的變遷,而放在更爲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這也就是編者所尤其強調的“文學文化史”。這是比較可喜的地方。儘管很多時候並無法兼顧到,有時甚至相當薄弱,但整體上畢竟是在此方向上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
上文中提及了“文本”一詞。在我看來,該詞包含了一種“意識性”,即這種文本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它們本來的完整的樣貌,而是經過了某種加工整理,甚至是某種有意識的選擇的結果。比如:柯馬丁提醒我們,先秦文獻大多經過了漢代學者、尤其是劉向、劉歆等人的整理和編輯,不考慮到他們進行整理時對於文本分類的性質、範圍等的認識與處理,就很難接近先秦文獻尤其是戰國論說文的原貌。田曉菲指出,六七世紀的選集和類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勾勒的唐前詩文的圖景,像《文選》和《玉台新詠》都按照編者自己的口味和標準進行整理,並由此建構一個可以將自身置於其中的文學史敘事。宇文所安也提到,“我們對於唐代文學的理解取決於幸存下來的作品,取決於反映了特定時代和特定個人的興趣的保存行為,取決於物質世界裡面發生的意外事件”。這樣的一種基本立場,使得他們在描繪一個時代的整體圖景時往往採取審慎的態度——我們所認識的只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我們所理解的未必是歷史的全部真相。當然,這種對待材料的態度在歷史學研究中是比較基本的,但在文學史、哲學史領域,似乎并沒有引起國內學界的廣泛重視(其實在歷史學界也有相當多的人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既然名之爲“史”,對於遺存下來的文獻就不能不考慮到其撰述、流傳等過程中本身所蘊涵的意義,而不能僅僅視作絕對客觀的認知“客體”。
由於成於眾手,各章風格不同,側重點也各異,此原也難免。然而,一方面,前後討論頗有重複之處,尤其是由二人分撰的第六章;另一方面,在我看來,各章的水平也不盡一致。對我來說,第一章和第三章寫得較好,我的收穫最大;第四章的寫得最差,敘述淩亂,沒有明確的系統;第五章過於偏重對詩詞的討論,其實對於宋代的“古文”著墨太少。而更爲重要的一點是,我沒有在全書中看出貫穿歷史的“文學史”脈絡。作爲一部通史,並不能讓我對中國文學的演變歷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更多的是點的擴充。當然,歷史上是否確實有所謂的一條線索本身即是值得懷疑的,但就我個人來說,至少需要發現一道軌跡,不然是不會滿足的。
2013年10月28-29日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读后感(四):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李白部分除了“抹黑”并没有第二个字
一、《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四章文化唐朝
1 宇文所安说:李白则不只是一个外省人。
宇文所安心目中李白这个乡巴佬的反例城市人王维:王维出身于唐代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在青少年时代,他常常出入诸王府第。
王维出身于唐代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吗?《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中》河东王氏:王维王缙兄弟的父亲王处廉是汾州司马,祖父王胄是协律郎,曾祖父王知节是扬州司马,高祖父王儒贤是赵州司马。
唐朝协律郎是正八品上,上一级从七品下有官职叫“下县令”,可知王维的祖父充其量是个副处级。至于其他一堆各州司马,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副县市级,很可能还是个闲职。唐朝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祖上四代混得也忒惨了点?第二点,李白是宇文所安口中的“外省人”,《旧唐书·王维列传》:“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难道“汾州”“蒲州”的山西人相对于唐朝都城长安不是“外省人”而是“本省人”?最后一点,《旧唐书·王缙列传》:“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报,则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看看王维的弟弟王缙干的好事,“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唐朝的大好江山就败在他手里,著名佛教徒王维难道不应该对此负有坏榜样的责任吗?
2 宇文所安说:李白则不只是一个外省人。很多学者怀疑他的祖先至少有部分非汉族血统。
请问宇文所安这是什么逻辑?有学者怀疑李白的种族,岂止部分非汉族,简直可能就是胡人,但是如何呢?宇文所安前面所说的李白外省人是一个事实,后面所说的李白血统却仅是一个假设,这样就能形成李白既是外省人又可能起码部分非汉人的逻辑链吗?有人怀疑,也有人反驳,为什么一定要采信对李白不利的说法?只能证明宇文所安为了黑李白,在尽其所能的选择性使用有利证据。事实上唐朝并没有省,更谈不上台湾流行的外省人;唐朝也不存在今天汉族这个概念,而是仍然处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之中。宇文所安身为美国人却以民族主义作为叙事的语境,无非就是寻找一切机会打击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自信心。这种打着中国文学史旗号却大谈猛扯名人八卦,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歪书不可能还有半点学术价值可言。
3 宇文所安说:他在四川乡间长大。
汉典乡间:远离文化中心或与它没有什么接触的农村地区;乡野偏僻的地方。李白在四川远离文化中心的乡野偏僻农村地区长大吗?范传正《唐故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请看清楚,“侨为郡人”、“以逋其邑”,有郡又有邑,刚好宇文所安推崇的王维有一首《汉江临眺》的名诗,其中两句说“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郡邑:指汉水两岸的城镇。宇文所安试图把李白从外省人到非汉人再抹黑成乡巴佬,请问这位美国人能拿出同等重量级的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敢瞎说一气还好意思出书,难道真的是“厚黑二字得一可三分天下”的绝招又使出来了?
4 宇文所安说:他在四川乡间长大,虽然曾在诗里自称少年时代很强横,但他显然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
“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出自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李白诗全集》TXT注:此诗一本作“我昔北门厄,摧如一枝蒿。有虎挟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来组织,呵吓相煎熬。”显然“我昔斗鸡徒”并不是李白自述曾经是个“斗鸡徒”,反而“鸡徒”以及“五陵豪”都是李白的对立面。
“杀人都市中”,出自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少年学剑术……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是乐府诗的一个题目,曹植以《结客篇》仅有的两句“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出了个题目,之后有南北朝的鲍照、庾信,隋朝的孔绍安,唐朝的虞世南、卢照邻等,包括李白都以此题为诗,所以“杀人都市中”并非李白自述。
“杀人如剪草”,出自李白《白马篇》,又是乐府诗的一个题目,在李白之前的曹植,以及南北朝的鲍照、沈约都写过《白马篇》。
“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出自李白《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但是诗词名句网和《李白全集》电子书都没有这两句,《李白诗全集》TXT注:“一本此下有‘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四句”,“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怎么看都不像是李白自述的口吻,所以被视之为不可靠的异文。注:“脱”又作“托”,异文又有异字,双重不可靠。
“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出自李白《书情题蔡舍人雄》,意思是“猛犬唁唁狂吠,枉杀忠良,使多少灵魂含冤而无比愤怒。”并不是李白自述杀人。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出自李白《与韩荆州书》,学剑而已。
崔宗之《赠李十二白》“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防身兵器不能作为李白杀人的证据。
最后只有出自魏颢《李翰林集序》的“少任侠,手刃数人”。汉典任侠: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尚气节有担当而乐于助人。汉典强横:骄横跋扈;强硬蛮横;蛮不讲理。把李白锄强扶弱的好人好事,歪曲成了李白蛮不讲理,宇文所安你是不是嘴巴长歪了,嘴巴歪是面瘫的症状之一,建议在美国唐人街找个老中医推拿一下。
5 宇文所安说:他十分博学,却未受过修辞训练;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任何形式训练和控制的痕迹,而这种形式训练和控制可谓王维的第二天性。
[唐]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李太白》:(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彰明逸事》: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褵褷,已有雏凤态。
李白蜀中作集中尚存5首,一首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首七绝《峨眉山月歌》,皆格律合式,郁贤皓先生评前一首云:此诗“为现存李白最早诗篇之一。全诗信手拈来,无斧凿痕,而平仄粘对都合律诗规则,中间两联尤属工对,足见诗人早年于律诗曾下过功夫。前人或谓李白不善律诗,岂其然乎?”
[元]方回《瀛奎律髓》:太白负不羁之才,乐府大篇,翕忽变化,而律诗工夫缜密如此,与杜审言、宋之问相伯仲。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明]刘世教《合刻李杜分体全集序》:自三百篇后,学士大夫称诗之盛,前无逾汉,而后宜莫唐。若开元、天宝间陇西、襄阳二先生出,遂穷诗律之能事,观于是止矣。
[明]刘鉴《合刻李杜分体全集序》:夫诗有古近律绝,体莫备于唐代,而妙莫兼于两公。
[明]李维桢《合刻李杜分体全集序》:夫诗至唐而体备,体至李、杜而众长备,而李、杜所以得之成体者,则本三百篇。
[明]高棅《唐诗品汇》: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气象雄逸。五言排律,开元后作者为盛,声律之备,独王右军、李翰林为多。
[明]胡应麟《诗薮》:读盛唐排律,延清摩诘等作,真如入万花春谷,光景烂熳,令人应接不暇,赏玩忘归。太白轻爽雄丽,如明堂黼黻,冠盖辉煌,武库甲兵,旌旗飞动。少陵变幻闳深,如陟昆仑,泛溟渤,千峰罗列,万汇汪洋。
安徽大学汤华泉《李白近体格律论析》:李白五律、七律、五绝、七绝292首完全符合格律形式的作品有176首,占60%。其合律比例各体又有所不同,五律127首,合律76首,近63%,七律8首,合律2首,25%,五绝73首,合律53首,占72%多,七绝84首,合律46首,近55%。以上所列百分比说明李白近体格律声病确实比较多,占了40%,这是一;二,但又不能说李白不太会或不善做近体律绝,毕竟有60%合式,特别是在一些庄重的场合哪怕是即席口占,“文不加点”,也能做到于格律“毫发无遗憾”,比如他做的应制进呈诗22首全部合律。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读后感(五):一点读书感受
9月9日开始,9月28日结束,历时19天。读完这两本大书,既有一种长嘘一口气的轻松感,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惆怅感。浩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厚重力量冲击着我的心智。感谢联合作者们沉静宽广的历史观,细致缜密的考证,连带着中华民族的政治历史变迁都重新梳理了一遍。
正如作者在文学史中点评巴金,“其在写作事业中并非技艺超群,他的文字充满无法自控的热情,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和说教”。 这段点评大概是不少初涉写作领域人士的通病,我也不能出其左右。不能用广阔而精准的文字表达情感才会出现情感大于文字的失控感,不能用绵延而简素的文字通过情节传达思想才会流于说教的弊病,不能将日常的生活和玄妙精深的人生根本含义有效地结合才需要借助戏剧化的情节寻找佐证。
如果说最初阅读此书的意愿是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华文学的发展史,了解历史长河中的文人命运变迁,那么通读结束之后,最深的感受竟然是自身的浅薄和浮躁。
无论是近代定义文学是政治的附庸,还是古典时代文化作为士人修身养性的根基,我都处在遥望千里远山的位置。
文学有何意义?这要问生命有何意义。张爱玲推崇生命的意义存在于“不相干”的琐碎东西中:时尚、饮食、音乐、跳舞、绘画、室内装潢-城市的一切声色味道。如今的社会生活将这一观念贯彻得可谓淋漓尽致。人民无不殚精竭虑丰富自己的物质,尽享太平时代的享乐生活。
在这一切中我觉得虚空而无趣。可是意图退出这样时代怪圈的自己,又能何去何从。
文学,文字于我,是一种情趣,自以为高尚的情趣,只是它和“时尚、饮食、音乐…”等那一切的情趣比起来,难道有根本的区别吗?
和ZL谈起人生意义是在促进人类更美好地生活中发挥一点光和热,可是,你能说,人们现在的情绪不是美好的么?明朝的《金瓶梅》开了情色文学的先河,连汪曾祺在《做饭》里都言说,明代之前不见札记里记录补品饮食的记录,可能是因为在明代之前,并无纵欲之习惯,也无大补之必要。可深思即是谬论,人民大众不曾在公众场所讨论,传说,并不代表背地里没有行为,没有需要。不然,何来的几千年人类之繁衍生息,三妻四妾,勾栏情话也并不只是摆设。
乔治.奥威尔自述到,当他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他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此即我心。文字没有效用,即是虫蛀之洞。政治之类的狭隘事物不是我心之所向,却不知道彷徨而往何处。
人对生命有热情,须有一些盲目的信仰,为之热切,为之一心向前不徘徊反复。
不算是书评,一点感受。且行且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