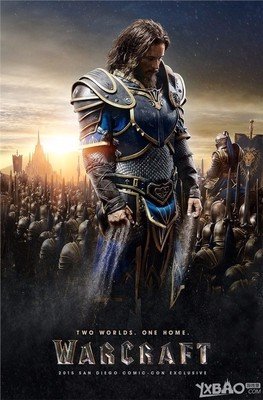《最后的山神》影评精选10篇
《最后的山神》是一部由孙增田执导,孟金福 / 丁桂琴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山神》影评(一):借问信仰何处寻
借问信仰何处寻
——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
《最后的山神》记录了大兴安岭上中国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孟金福一年多的狩猎生活,用极具真实性和生活化的镜头展示了奄奄一息的鄂伦春文化,发人深省。
导演使用线性叙事方法,通过解说词和画面表现,突出了冬——春——冬的时间顺序,使纪录片更为客观真实。孟金福作为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在山林中出生长大,纵然政府帮助鄂伦春人走出山林定居,但他和妻子还是习惯在山林中生活,选择走回山林。山林中的孟金福夫妇与定居地的同辈乃至子孙后代们,俨然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孟金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依然坚守着鄂伦春人固有的生活方式,而定居地的人们慢慢地丧失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信仰,逐渐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同化,终究走上忘本之路。本片引人深思——先辈们一直坚守着的信仰何以不能被后人所接受、所传承?人们在现代化的科技文明与古老的民族文明信仰的冲击之中到底该何去何从?失去信仰的蒙受现代科技恩惠的人,究竟可喜还是可悲?
“定居像一道线,划破了鄂伦春人的过去与现在。”“孟金福的山林是有神灵的,郭宝林的山林就是山林。”孟金福始终相信神灵,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迷信,但本片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信仰。本片开篇的场景便是孟金福在树上造山神像,孟金福拜山神时,导演采用了固定的长镜头,将原本没有占地较小的山神像置于前景,使山神像看起来格外的壮大宏伟、庄严肃穆,而让原本体型较大的孟金福看起来格外的渺小,通过画面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来表现孟金福对山神的信仰与敬畏之至,形象、具体。之后山神像遭人砍伐破坏,孟金福瘫坐在山神像后,导演依旧采用了这种镜头,使孟金福在信仰被人破坏后的悲哀、无助更为突出,接着导演又对孟金福进行剪影式的特写,配以呜咽般的笛声,将这种悲哀无助表现到极致,使人情不自禁地心生叹惋。
本片运用的解说词恰如其分,对画面内容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他更不肯学着用套索夹子去捕猎。他认为那样不分老幼的猎杀,山神是不会高兴。”“孟金福小心地握着刀尖,使刀刃正好划破树皮而不伤得太深,一年以后这棵树还能长出新皮。”几句解说词表面上很简单,然而更深层次地凸显出了这个山神信仰者因着对山神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懂得如何节制地生存、如何有原则地生活,他与外界文化交流并不多,并且那时可持续发展也并未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这种无形的意识天然地存在于他的信仰之中,无须他人宣传、无须政府强调,这是信仰者的自主选择,绝非外在人事物的强制。
“神走了,不会来了。”孟金福老母亲对儿子表演萨满跳神极为不快,她作为孟金福的长辈,已然失去了先辈们留下的信仰,更何况她的后代们呢?鄂伦春族的后代离山林越来越远、离山神越来越远、离信仰与鄂伦春文明越来越远。鄂伦春的意思是生活在山岭上的人,而随着孟金福老先生的离世,真正地鄂伦春人大概也像这最后的萨满一般消亡了罢。
本片最后用了远景——全景——远景切换的镜头,表现孟金福骑着马在雪地上前行,背景的笛声空灵而悠长,孟金福渐渐远去,笛声最终淡去,鄂伦春最后的信仰也缓缓与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告别。
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能够追寻并且坚守自己的信仰,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最后的山神》影评(二):都是为了生活
《最后的山神》是一部记录片,这部纪录片中,导演随孟金福来到森林中,用朴实的镜头以及简单的叙述,讲述了最后的萨满孟金福的故事。
该片最突出的就是对动作细节的运用。片中的细节刻画出鄂伦春人的传统习俗和质朴民情。夏天来了,孟金福拿着刀,对着镜子刮胡子,因为他想让自己好看些,才能配得上这美丽的季节。这是多么简单的想法,仅仅因为对季节的尊重。孟金福出去打猎,乘坐自制的桦皮船,去“捡场”。出发之前,老伴儿拿着柳条打他一下,寄托简单的想法:不要空手而归。这是老辈流传下来的习俗。“捡场”其实就在在河边守候,晚上动物来喝水的时候狩猎。可以说鄂伦春人是聪明的,在森林的生活中,他们积累出了经验,总结出了方法。尽管这次孟金满一个猎物也没等到,但是他们相信在祭拜山神之后,山神会保佑他们的。鄂伦春人在对待山林中的一切都是不伤害的,片中还记录了孟金福制作新桦皮船的片段,在树皮水分最足时,孟金福拿着刀尖,不深不浅的刺入树皮刨出一层,而不至于伤的太深,来年白桦树又能重新长出新皮来。取下树皮之后,用樟子松做船骨架,不用一颗铁钉,在朋友的帮助下,一天就能做好。又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孟金福咧开嘴憨憨的笑了。
这部纪录片淡入淡出,但是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刻画出人物内心的想法,比如孟金福在空手而归时的落寞;看到刻有山神的树遭到砍伐就如同砍在自己身上的悲痛;完成新桦皮船的开心。这一切都是质朴的,没有多少画面剪辑,用简简单单的跟镜头完成。同时,孟金福与老伴简单的爱情,在整个片子中也是一个暗的索引,为了生活。
《最后的山神》影评(三):何为信仰?
孟金福的抢很老了,老到很难找到 同型号的子弹,但他却不愿换成自动步枪,因为他觉得那样体现不出一个猎人的本事。
他不用套索和夹子,他认为,那样不分老幼的猎杀,山神是会不高兴的。
一棵雕有山神的松树被砍伐了,孟金福觉得就像自己被砍伐了。
定居像一道线,划开了鄂伦春人的过去和现在。
以上摘自《最后的山神》的旁白,是我在观影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几句话。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接触过很多的少数民族,不过悲哀的是,由于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的民族对他们而言仅仅只是写在身份证上的一个符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可言。对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而言,祖先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他们无心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去做进一步的了解,而他们民族的信仰,更是少有人知。
我参观过一个关于鄂伦春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十分惊叹于他们手工技艺的精湛,尤其被桦树皮船的精致折服。鄂伦春人生活在大山里,大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依靠,更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敬畏山神,并认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山神慷慨的赐予,他们在享受物质的同时也更加虔诚。可以说,因为大山,因为山神,鄂伦春人永远是心怀感激的。而这种感恩之心,往往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所缺失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单纯的信仰很愚昧,因为它把收获归功于上天而非个人的努力,但是想想看,谁的一生不是源于自然最后又归于自然呢?
随着政府帮助鄂伦春人定居,这种对山的信仰逐渐少了,对新一代的鄂伦春人而言,大山仅仅是大山了。
有人觉得这是悲哀,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人为之欢呼,觉得他们这是向现代文明的靠拢与回归。而在我看来,一切的一切无论对错,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还保留这心灵的纯真与美好。信仰有也罢无也罢,只要他们觉得幸福,一切都好,毕竟,信仰的存在时为了依靠于宽恕,进而让人觉得幸福。
写在后面:好久没有写影评了,有点乱,请多包涵。 ^_^
《最后的山神》影评(四):民族的消亡
在过去千百年的岁月里,萨满鼓声曾不时地回荡在兴安岭的山谷中。今天,恐怕是最后一次响起了……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每年都有一些少数民族在无声地消失。他们大都接受了“文明”的洗礼,使得他们的民族被“边缘化”直至消亡。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认为你既然落后就必然要消亡,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民族消亡的原因时,就会发现,少数民族的生存问题,主要是由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而他们的传统文化不能有效适应而引起的。所以,少数民族的消亡并不仅仅由于他们自己的落后,还由于其它民族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改变了甚至侵占了小民族生存的环境和地域。
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民族——鄂伦春族。纪录片表面记录孟金福夫妇的丛林生活,实则记录的是鄂伦春族逐渐消失过程。
“定居像一道线,划破了鄂伦春人的过去与现在。” 建国后,国家给予鄂伦春以特殊照顾,拨出大批资金,于1953年开始建筑新房,逐步实现了定居。政府的“优惠政策”保住了鄂伦春族的人口却深深地伤害到了本族的文化。影片中郭福林就是最好的事例。郭宝林夫妇是定居后出生长大的第一代鄂伦春人。受过学校教育,有固定工作。现在郭宝林是乡政府干部,妻子是教员,女儿在读中学。他们的生活道路与上一代已完全不同。在孟金福心里,森林是神圣的。而在郭福林眼中,森林就是森林。郭福林代表的是新一代的鄂伦春人,是拉动族人往“文明”方向走的人。不言而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无形之中扼杀了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
“眼看着树林越来越稀,野兽越来越少,孟金福常感到山神正在离他远去。感到一种无可依托的孤独。”一天,孟金福发现一棵刻着山神的树木被砍掉了,面对着残余的树桩久久不愿离去,夕阳穿过他们之间的空隙,留下了带不走的黑暗与孤独。那以后的很多日子,孟金福再也没有出去狩猎和捕鱼。现代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被动现代化”。可我们在建设文明社会,发展全球化经济的同时,并没有想过我们的举动已经伤害到了其他动物,破坏了大自然应有的样子。
“又一位鄂伦春人去世了。死去一位老人就意味着鄂伦春人又远离了山林一步。” 如今,还懂得鄂伦春族传统的人已经不多了,影片中也提到了,像孟金福一样会制作桦皮船的人不多了,会制作的人也只剩下了几位老年人。可想而知,他们逝去后,鄂伦春族的传统文化将会由此断裂。在这个提倡传承优秀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时代,我们有没有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影片最后,孟金福在忽明忽暗的篝火前跳起了萨满舞,中断四十年后,这位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又敲响了他的萨满鼓……
《最后的山神》影评(五):最后的萨满人,最后的山林人,最后的精神
《最后的山神》记录了鄂伦春族最后一个萨满对山林的特殊情感,表面上纪录片中只是记录了孟金福夫妇在山林中的日常生活,但是从中却反应了一个民族的没落。从而影射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在遭受着各种文化的冲击,总有一些文化会被淡化,原始的生活方式在走向没落。
对于原始森林的情感,也在伴随着文明的演变而渐渐发生变化,大概只有老一辈人会因为最朴素的原始意识的丧失而黯然神伤了。解说词中有这么一句话“在孟金福(老一辈)的眼里,山林是有灵魂的;而在郭保林(年轻人)的眼里,山林就是山林。”通过这种细节上面的对比,可以反映出两代人在思想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影片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层层展开描绘,结构严谨,叙事清晰,情节真实感人。影片着重塑造了孟金福的言行及形象意识,在人物的刻画上,着重表现他的淳朴与善良,表现出他富有原始气息的生活方式。
孟金福作为鄂伦春最后一位萨满,他的行为中必然带有很多原始宗教崇拜的痕迹,他把大自然的万物都看作是神来崇拜。每到正月十五,他都会敬拜月神,渴望幸福和猎运的兴旺,此时月亮的特写,这是孟金福虔诚的祈祷,火堆上方升起浓浓的烟,月亮笼罩在烟雾之中,这是一种朦胧的美,同时让在人们眼中最熟悉不过的月亮也多了分神秘的色彩。让受众也开始渐渐感觉到神灵的存在。孟金福每到一片山林,总会找一棵高大的树画上一尊山神像,他认为只有这样,山林和自己才能沐浴在神灵的庇护下,这是心灵的一种寄托,更是他精神的寄托。他每次进山打猎都要请求山神赐予他猎物,如果打猎有所收获,他也会认为这是山神的施舍,便要虔诚地给山神进贡祭品。他还会往山神嘴里塞食物,没有祭品时就给山神点根烟,这些细节都是人物性格的外化。
山林的数目越来越少,山林里的猎物也越来越少,鄂伦春人的生活也越来越难。郭宝春是新一代鄂伦春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孟金福一代完全不同,他们 一家虽然也和孟金福一起回到山林,但情感却不同。正是解说词中所说“在孟金福的眼里,山林是有灵魂的。而在郭保林的眼里,山林,只是山林。”在孟金福眼里,山林是有灵魂的,确实如此,从他的一举一动,对生命的热爱,对山林的热爱也展现的非常明显了,文明已经在一步步远离他们,远离了像郭宝春这样住在山下集体住宅的人。
还有影片最后的那个镜头,在编导的要求下,孟金福跳起了萨满的的大神,一轮巨大的落日前,孟金福的黑色剪影出现,落日预示着结束,这是萨满的结束,也是古老鄂伦春文化的结束。
最后的山神又可以理解为最后的萨满人,更可以理解为最后的山林人,同时也还可以解释为最后的精神。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原始生活已经过得越来越难,环境的破坏让这样一片树林失去了生机,猎物也越来越少。
《最后的山神》影评(六):最后的山神
逝去渐近线上的鄂伦春文明印记
——评《最后的山神》
定居像一道线,划开了鄂伦春人的过去和现在。
《最后的山神》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孟金福夫妇山林生活的故事,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而且从中没有很是强调他的生活是怎样,但是却让观众走进山民的内心世界。影片中从画面上的使用,人物的细节刻画以及音乐的转场上都使其笼罩着一层静穆的悲哀,一股遗老的味道。这味道是鄂伦春文化消弭的残香
该片在画面上传递着鄂伦春文明残存的血脉中以林为灵的意念。
影片中,进山拜神时,孟金福双手合一,头微微抬起,然后打开双手,头朝地上磕.画面用一个全景,固定的长镜头,把一个这位最后的萨满刻画得栩栩如生.此时的山林中只有偶尔的几声鸟鸣.寂静的环境渲染着庄严、肃穆的氛围.正反衬着孟金福的信仰,他的信仰是庄严的、肃穆的,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而在人们砍掉了画了山神的那棵树时,画面用一个中景看到孟金福跪在只剩下树根的树前将头埋下,画面中前景是半截的树根,而背景才是孟金福蜷缩的身影,两者相互映衬,“山神”与他感同身受,孟金福流露出淡淡的悲伤。还有的是跳神的时候,画面用全景镜头充分占山人物的形体动作以及人和环境的关系,黄昏时,夕阳落下,金黄的色调,巨大的太阳,舞动的剪影,让逆光的充分运用,使画面弥漫着一股遗老的味道,这究竟是倒数第几次跳神了。不同镜头的承转变换存于画面之中,辅助画面内容,让这座山林染上了鄂伦春的灵性的虔诚
该片在人物上的细节刻画出鄂伦春文明的新旧的冲撞。
孟金福作为鄂伦春最后一位萨满,他的行为中必然带着很多鄂伦春人特有的气息,世间万物皆为神灵。每次进山都会拜山神祈求得到猎物,并且认为这是山神的施舍,打猎失败时也会给跟烟山神,这些都折射出鄂伦春人的内心世界。他善良,不用夹子和套索打猎,因为他知道分老幼的猎杀;他自信,不用先进点的枪,因为这不能展示他的技术;他质朴,看见画有山神的树被砍掉时没有过多的言语,因为觉得就像自己被砍伐了。如果仅仅描写孟金福或许还没有一种遗老的味道。那么从描写郭宝林时,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只能看到山林就是山林,而老一辈则是看到山林是有灵魂的,可是孟金福母亲也说过一句话"神走了,不会来了。"那么究竟是两代人的思想差异呢?还是什么? 所有人都不再相信神灵的庇护,也没有人能理解孟金福这个最后的萨满的悲哀。谁也不能,就连同为鄂伦春人的他们也不能。每一处细节都是新鲜的,但文明的进行却不会停下脚步,新与旧,变与换,永远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都只是进程中的一列单行火车,知所往却不知何去。
该片在音乐独特和出了鄂伦春神性文明印记的哀婉之声。
一段段似悠扬似忧愁的音乐与画面形成声画同步,山林中的景色,白白的雪地,湛蓝的天空,渐隐渐入,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情景,正是山神所代表的的食物,而画面与音乐相互配合使情绪的拉长。山神究竟还在不在?时代的必然变迁,即使孤独,也无力反抗。
纪录片《最后的山神》通过画面上的使用,人物的细节刻画以及音乐的转场使达到情感上的共鸣.画面不会说话,细节不会动听,音乐不会表情,而他们三个却编讲了鄂伦春文明的印记,展现了这一古老文明的血脉痕迹,整理出这一古老文明进程中的一段历程,所以以文明的角度这注定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且令人神思的故事。(
《最后的山神》影评(七):最后的萨满 最后的信仰
这部纪录片以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孟金福的故事。孟金福老人虽然已经在政府的帮助下可以在山林外较好的条件中生活,但纯朴虔诚的依然在夏天上山林生活,狩猎捕鱼,在拜祭山神后接受山神的馈赠。 全片以朴实的视听语言展现了孟金福朴实的山林生活。除了平静低沉的旁白外,影片还收录了现场的许多自然音响,如虫鸣鸟叫,孟金福划船的水声。仿佛把观众带入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山林世界。同时影片多处运用了“淡”与“化”的剪辑方式,与舒缓的影片节奏相符合,光线与色彩也丝毫不加修饰,将最自然最古老的大兴安岭的山林深处的日升日落、昼去又返展现给观众。本片也运用了多处特写,从孟金福蹲碱厂支猎枪到孟金福砍树做小艇再到孟金福发现猎物走远沟壑纵横的脸上失落的神情。每一处特写无意不是在为导演想表达是主题服务。其中印象最深的要属孟金福做小艇,六十七岁的他灵活得如同灵长类动物般爬上树,小心砍下树皮(旁白此时强调不会砍太深,让白桦树能长出新皮提现了孟金福对山神的虔诚,同时也与片尾刻有山神的树被砍形成对比),以那双灵巧的如同枯树枝的手刮下厚度合适的木片,此时旁白讲道像这种技艺只有鄂伦春族的老年人会,已濒临失传。这条暗线又与本片主题消逝的信仰相和。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年代,机器取代太多传统技艺,但是机器只能从“形”上造出物品,而不能像孟金福老人那样制作出饱含对山神信仰的“意”的物品。就像在这个物欲纵横的社会,在资本的侵入下,人们拥有了富裕的物质生活,但精神上却是如同荒漠一般贫瘠,他们得到了很多,失去了更多。 我窃以为影片另一个重要的点是每一代的生活方式与对山林态度的对比。片末孟金福为制作组表演萨满舞(那荧荧的圣光之火与较暗的背景形成对比,表现了山神在孟金福们心中的神圣),而孟金福的母亲却对此感到不快,认为“表演”萨满舞是对神的不敬,“神走了,不会再来了”。而作为比孟金福还年轻一代的郭红波虽然有时还在山林中但是已经走入现代社会的他心中,山林就是山林与孟金福心中有山神的山林是截然不同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里山林的距离越来越远,对物质的向往也渐渐取代了对山神的虔诚。就像村里一位老人过世后,旁白所说的“远离山林一步”。 我脑海中依旧记得14分钟的时候孟金福划船时那个逆光的画面,晨辉洒落在孟金福不那么伟岸的肩膀上,有些许落寞,也有些许悲哀,那瘦小的身躯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却背负着最沉重的责任,他的虔诚使他的身躯又伟岸了起来,此时此刻,他是山神最最虔诚的信徒。 然而刻有山神的树还是被无良伐木人砍掉,他心中一定没有山神的位置,他入梦时也一定不会感到罪恶与不安。 影片快结束时,孟金福在被雪覆盖的山林中骑着白马,渐渐远去,依旧那么落寞。这便是信仰的消失,在外来社会的面前,那重若泰山的信仰又显得太轻太轻,我们只能在它没有完全消逝前,记录下来,记录下原始山林里至纯至真的情感。
《最后的山神》影评(八):山林再也不是家
世世代代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身处野外,既有种舒服自在(山林就是家,随处可点篝火睡觉,不愿住回定居地),也有种敬畏(山林是衣食父母:山神、和狼图腾里的腾格里)。不像城里人去到野外,既感到不适/畏惧,又肆意掠取。 鄂伦春族人的狩猎生活注定会消失,比他们多的多的掠取自然的人,会让他们无法生活。
这些人的生活,乍看上去,是很脏很辛苦。就像“赶马帮的女人”一样,但是他们都是认真的生活,夏天到了刮胡子,给老婆带去冬日里的绿芽,做一艘漂亮的桦皮船。。(赶马帮的女人到了市集上先去洗去鞋子上的泥)。
山神树被砍,他好像自己被砍了,他再也没有出去狩猎和捕鱼。这个时候用的都是剪影,画面是黑压压的。(为什么不用同期声,讨厌旁白)
孟金福的山林是有神灵的,郭保林的山林就是山林。听到孟金福学动物叫,郭保林的女儿笑疯了,这一代人离山林更远了。(你以后想干嘛?我想和你们一样拍电视,拍山里的小动物。)——山林再也不是家。
《最后的山神》影评(九):06年写的
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中,形成了56个民族,在56朵绚丽的花朵中,导演选取了鄂伦春族,作为影片的主角。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中,有孟金福的一家。
在初夏的来临之际,孟金福手持一把钝刀,紧拉唇上的皮肉,用刀一点一点地刮弄胡子,而妻子在笑。他们老了,只是想再变年轻点,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纪录片中,解说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并不是单一的游走于画面之外,而是为画面做一个补充解释的作用。在这部纪录片中,却常用潜台词,暗含一个为主题服务的寓意,而在这时,就不只是单一的画外音解说,而是有字幕的穿插。画面里,常常会出现孟金福坐在雪地静静地狩猎,或者是划动小船仓促心急地寻找猎物,即使拜了山神,即使被妻子用柳条打了,他还是空手而归。在充满疑惑中。解说词是这样说的:现在,动物越来越少了,可是真的只是动物越来越少了吗?孟金福用小船打猎却空手而回,此时他打算再做一条船——“船老了,人也老了。”孟金福做好了船,空空一人枯坐再那棵断腰死去的松,什么也没说——“又一棵圆木松被砍伐了,好像自己被砍伐了一样的感觉。”孟金福在祭拜一位死去的老人——“死了一个老人,代表,有远离了山神一步……”孟金福开始在夕阳降落的夜晚,作为最后一个跳萨满舞的人,舞动。可是她的母亲无奈了——“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些话语,引领着故事的一点一滴,那些话语,暗示了鄂伦春族的秘密——古老民族的传承是艰辛的,正如老了,砍伐了,心痛了,也无法阻止现代文明的脚步。正如再下一背的心中,只有树林。却没有山神。
解说令故事完整,而画面才让故事生动。在刻画外界景物上,特别注重色彩的唯美,情绪也随之波动。白的雪,惨白着,还有白树,在那样单薄的季节,孟金福们在狩猎;黄色夕阳使真个树林黄了,孟金福们却还没有扳动他们手中的枪。红的火把、绿的夏,那是欢乐轻松的微笑。而在刻画人物上,手法就多起来了,常常会出现逆光的运用,凸显出一个深刻的轮廓。在拜山神,拿枪行走,或划动船桨。那种轮廓,勾勒出古老的鄂伦春族的生息。在他们住的篷里,透过篷顶射入一束圆白亮透的侧光,人依偎在这柔美的光下,连火也要变得温柔,、再配上篷的土黄色,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导演在很多画面处理上的唯美,也许也正是表明它与现实强烈的冲撞吧!
最后,在运用音乐、景物转场方面是非常巧妙独特的。每次转场,都会运用一个长镜头,加上一段似悠扬似忧愁的音乐。更显情绪的拉长。画面上则是树、月亮、太阳的反复重叠,那些,却恰巧是村民崇拜的山神代表的事物。在这样微不足道的转场之间,也深刻蕴含点明主题的思想。
孟金福们孤独了,音乐转入高潮,他们的山神走远了,他们不会埋怨什么。只是时代的必然变迁,即使孤独,也无力反抗。让他们顺应历史的潮流吧!
就让山神走远!
《最后的山神》影评(十):神走了
神 走 了 ——浅析纪录片《最后的山神》 世界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曾说过:“纪录片的本质作用就是纪录”。1992年,由孙曾田导演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纪录了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孟金福的日常生活以及鄂伦春族世世代代所守护的山林。无论是色彩的烘托、声音的渲染,还是镜头的配合、人物的真实情感中都寄托了导演对鄂伦春人那种真诚的信仰的赞美。 通过对色彩的运用和捕捉塑造了人物的形象。描绘冬天山林的景象时,通常是泛黄的冷色调,那种阴暗陈旧的颜色,尽显着山林的落后与萧条。枯黄的树枝上压着皑皑的白雪,冷涩,枯寂,苍凉一一裸呈在全景的镜头之下。片中为数不多的彩色是孟金福他的马的尾巴上的那一抹红色,梦金福跪在地上为马系上红绳,对于他们来说,马是上天给他们的恩赐,是神,对马的跪拜就是对神的跪拜。而红色既是传统文明的象征也是梦金福这类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该片在音乐上的独特之处表现出了鄂伦春族对神性文明印记的哀婉之声。一段段或悠扬或忧愁的音乐与画面形成声画同步,山林中的景色,白白的雪地,湛蓝的天空,渐隐渐入,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情景,正是山神对人们的馈赠。当镜头对准夏季,大片的绿色映入眼帘,此时的音乐不仅仅只是婉转悠扬,而是多了一份清新脱俗,在不经意间带给观众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 本片的视听语言独具特色,片中多次出现的长镜头,把这位最后的萨满刻画得栩栩如生.此时的山林中只有偶尔的几声鸟鸣。寂静的环境渲染着庄严、肃穆的氛围,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观众的心灵得到解脱,灵魂得到释放。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景别变化,但起承转合间导演也是煞费苦心。孟金福划船一段,从脸部特写到中近景再到远景,推拉过程包括其中,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纪实性还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身临其境,切身处地的融入纪录片中。 没有现代生活的灯红酒绿,保留原始社会的纯真本质,孟金福仍然坚定的雕刻着他的山神,如同雕刻他的信仰。此时特写下的他的脸,却折射出岁月的芳华,和对生活的坚定。而观众们要做的就是反思自己,留住内心深处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