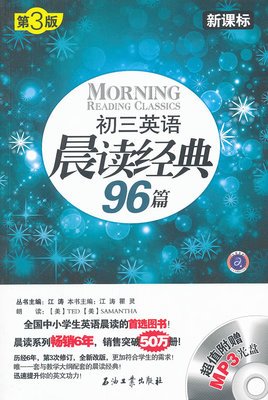最后一场雪经典读后感10篇
《最后一场雪》是一本由[法] 于贝尔·曼加莱利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一):如何直面死的灰暗,如何获得生的勇气
关于鸢和我
“我不知道一只鸢听了收音机放出来的东西后,是否还能将自己被捕捉之前的所见、所感长期保留在记忆之中。我担心的是,听了迪卡索听的那些爱情歌曲、鸢儿会忘记悬崖峭壁,忘记原野上空的翱翔。”
我一遍一遍地给父亲讲述捕鸢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猎人和鸢搏斗的过程。
“我”所在的家庭是灰色的,生病的父亲是灰色的,总是外出的母亲是灰色的,自己那份可有可无的工作,甚至工作的对象都是一群即将走进坟墓的老人也是灰色的。在“我”身边,这一片灰色的阴影笼罩下,没有生命力可言,直到我看到了鸢,“从那天起,我便渴望拥有这只鸢,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曾如此渴望拥有什么东西。”这只曾经翱翔在悬崖峭壁、茫茫原野上空的鸢,也许是让“我”感受“生”的一股源泉。
面对父亲的衰弱,我惶恐、不安、悲伤,我害怕面对父亲的死,甚至直到父亲真的死了,他也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幻想着自己去亲吻父亲的床架,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我宁愿看着空空荡荡的天空也不愿意看着父亲的脸。直到父亲死的那一刻,他都没有勇气去面对,纵使他希望在鸢的身上获得,可是还是没有成功。父亲留给我的只剩一双鞋了,我把它擦亮,纵使不愿意面对灰暗,终究还是要穿上鞋,重新上路的。
关于父亲和母亲
父亲喜欢听我讲述鸢的故事,他听了一遍又一遍,在黑暗中听我讲述,父亲会为猎人最后捕鸢成功高兴,要是猎人捕猎失败,他也会高兴,因为鸢英勇善战。父亲会全神贯注地看着鸟笼并沉醉其中。
父亲是一个缺少勇气的父亲,他会因为妻子偷偷出门开照明灯的声音感觉到是一种折磨,而他却从来没有勇气给自己的妻子抗议过。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带来的痛苦和失眠。他不愿意面对妻子的不忠,而只能沉溺在虚构的故事里。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是鸢是真实存在的,放在窗前的鸢,让我编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看着鸢把一盘的顶级肉吃完,父亲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份活力。虽然很微弱,可是他还是会惊叹,“天啊,孩子你看,它全吃光了。”
母亲本来应该担当着一个家庭中重要的角色的,可是,我的母亲却游离于这个家庭之外,一边暗暗地为自己的离场哭泣,一边又踏着楼梯间的照明灯的光远去,我在母亲的身边中得不到半点的温暖,父亲在妻子那里也得不到半点的安慰。也许,“鸢”从某个意义来说,是这个家庭中“母亲”角色的替代品,至少也是一个精神的替代品。
关于两窝小猫和一只狗
第一次溺死小猫后“我”和门房伯格曼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都故意比往常说更多的话,因为两人都无法面对那份挥之不去的阴郁时间。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无法忘记这些小猫的幽魂。作者用了极大的篇幅以及极其详尽的细节去描写我是如何完成处置那只老狗的任务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杀害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寻找的过程,这是我面对死亡的一个冗长的仪式,这是一个我接受新生的同样冗长的仪式。无论是死亡还是新生,总会伴随着各种不得不面对的状况,比如疲累、比如饥饿、比如摔倒、比如失禁。
虽然,看完了这本书,虽然,敲下了那么多的字,最终,我也是个无法直面死亡的人。唉。
《最后一场雪》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也很薄,116页,5W字,但就是这些不多的文字,让人合上书页时有放不下的纠心。那些沉潜的意象依然恍恍地浸润着,一种如鲠在喉的难受。说实话,我有点怕读这个故事,尤其是在父亲生病的当口,很怕,我真的无法没法直面死亡。就像小说中的“他”,懦弱、逃避、承受并幻想。尽管强打精神不得不面对各种不能不面对的状况,尽管忽视、麻痹、刻意冷落自己失落、沮丧、难过的情绪,可在作者看似无技巧的平实安静地讲述里,这些仍如影随行,咕咚咚地冒着泡,快要让人覆灭。
这个简单而安静的故事既是那样的隐忍、忧伤、内敛和深沉,难以言说的失亲之哀、失亲之痛都让人动容。我的心仿佛也在这些温柔含蓄的眷恋里碎掉了。
父亲病厄缠身,家里生活拮据,只有父亲微薄的救济金。“他”没有固定工作,只能以陪养老院的老人散步的工作赚些零用钱。回家后,视父亲精神的好坏,给父亲断断续续地讲最爱听的猎人捕猎鸢的故事。为了在父亲的病床前摆上一只鸢,他处理了弃猫崽,处理了老狗,也买到了鸢。他强忍内心充满的罪恶感,强忍舍弃生命的不安,必须“每夜打开水龙头,关起时故意不旋紧,听水滴声睡去”。 有鸢的陪伴,父亲很开心,甚至温柔地对他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安慰,但此时冬天最后一场大雪扑面而来。
被放大的等待死亡的过程,被压抑在心无法言说的情感,还有那些残酷与绝望下试图带来希望的动作,以及间或不小心擦碰出来的声音,或者虚弱的星点言语里,无比放大了亲人将逝的伤感。小说从来没有做一点骗情的处理,也没有任何传达强烈情绪的字眼,安静得如同一场无声电影,让我们似乎在仅有的那些晃动破碎的画面勉力拼合着却无可奈何地被感染着。这里的感伤,就像表面平静的河流之下暗流狂涌,稍不留神,失去抵抗,便被倾覆。
作者于贝尔-曼加莱利 Hubert Mingarelli,1956年生于法国洛林省,80年代后期才走上写作之路。《一 条寂静的绿川》(1999),以及《最后一场雪》(,2000)是于贝尔-曼加莱利奠定法国文坛地位的重要作品。2003年出版的《四个士兵》一举夺下当年的梅迪西文学大奖,被誉为“海明威式作品”的重要之作。期待作者更多作品。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三):生命的冬季
用一上午的时光读完这本书。虽然此刻窗外炎炎夏日,却仿佛和作者一起走进那个冬天,那最后的一场雪。是因为那两窝在水桶里挣扎的小猫?还是在郊外雪地里迷失方向的老狗?是那个隐忍着自己痛苦默默哭泣的母亲?还是那个在鸢地陪伴下安静离开地父亲?我竟觉得内心在隐隐作痛。
作者不象在向我们讲故事,而是在描述自己的各种感官。各种感官将我们带进那个故事,仿佛让我们也亲历一般。只能隐忍却无法掩饰的对死去的猫和迷失的狗罪恶感,不需要言表却一点点在文字中彰显的父子之爱,都在各种微观和细节中被放大,又在安静中微妙的一点点流入内心。
那读了无数遍的关于鸢的故事并没有叙述出来,关于每夜母亲外出的原因也没有阐明,仿佛还有好多情节和故事都被藏在了背后。但当我们想象着那飘雪的窗前有一只鸢在眨眼,当我们和作者一起走过那长长的铁轨,翻过那漫长的山坡,当我们陪作者一起聆听那安抚心灵的水管的滴水声,我们内心觉得丰盈充实而有痛感。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走进那个生命的冬天,感受着生命消失的平静和躁动,感受着某种罪恶,某种爱。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四):每一件礼物命运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
如果给你一百块,让你杀死一个人,你做吗?
如果给你一万块,让你杀死一个人,做吗?
如果是十万块呢?或者一百万?
如果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猫或者一条狗,你又会如何选?
如果有一个东西你特别想要,时时刻刻心心念念,每天都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能够有一天能够有钱买下它带它回家,可是有一天,如果不马上买下它,它就要不属于你了,但你还没有攒够足够的钱,你没有时间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上面的选择,你又怎么选?
如果这件东西你不想要,而是你深爱的人要的呢?
不要试图考验人性,要知道有的时候你的坚守仅仅是价码没到你的底线。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五):静静地看着你
“能给我讲一遍捕鸢人的故事吗?”父亲轻声对我说。
读完这本书后,获得的感动尤为奇特。像一枚慢慢浸出酸甜的青梅,而且味道越来越浓。最后浓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只叫你流下晶莹的泪,而且啊,那泪,真的像冬天时一样,似乎转瞬就会冻住。
这是一个颇具真实感的故事。静静的流淌开来。虽不免裹挟着现实残酷锋利的刀子,但情感的温厚更是拥抱了所有。
“我”想拥有一只鸢,整天都想着它,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得到它。甚至忘记过去的美好,将松鼠从记忆里抹去。带着故人的同伴走向遥远的荒野。“我”每天都要去确认那只鸢,就算隔着盖住笼子的布也要听到它的声响才放心。天冷了,“我”担心它会被冻着。这期间我一直讲着捕鸢人的故事,那故事是那样合理,精彩,听众就是父亲。
“父亲”对“我”的爱可以看出多少?那就像一望无际的星空,广博且绚烂。他保持着微笑,而“我”也“看到他的牙齿仍在,就觉得安心”。
我现在很少与父母面对面静下心来交谈,哪怕是说一下最近的琐事也觉得没有必要。很少注视着他们的脸庞,也就看不见他们眼眸里闪过的失落以及惊喜。但我总能感觉到一件时,就是他们在衰老。死亡的恐慌没有迫近感。但是当死神真正站在你面前时,你已经没有哪怕支离的言语,没能力与死神争论甚至哀求。无力的见着他们静静闭上双眼,涌上的是否只有懊悔?
我们为青春而一意孤行,父母静静地看着,静静的倾听。他们就算不明白内容也会点头称赞我们的高傲的“演讲”。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房舍,黄昏的光撒满木质的桌,玻璃板下黑白的照片里有那样一群人笑得是那样灿烂,而父母依旧是微笑地拿起一本往期的书刊,一个人,或是两个人相对着,读起书来。
是否牵着他们的手一起散步?是我领着他们,而不是他们拽着我们向前。
是否选上一块松软的炖肉送进他们的碗里?就算不亲手将饭菜喂给他们。
答案不能等待自己公布的那一刻。若不提前解出来,缺少的可能远不止那数字的减少。
我在这之前读过很多日本的小说,细节当然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也是我乐意看见的,细节嘛,多少会充盈人物的性格。看完日本的小说会觉得他们是好的,但好到哪种程度就难说了,因为你脑子里被细节的线条塞满,有时候,说这遮住了真情也不为过,或是说,这种情已经太强烈了,像繁复规整的工程图,故事的味道不会变多,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磨掉最初令人的惊诧。
法国的作品却是大不一样的。最近还读过一本叫做《恋人》的法国作家写的短篇,和《最后一场雪》一样像梵高的《星空》一样,像真正的艺术品,能让人去品,而且越品越有味道。
那《最后一场雪》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混杂着的浓烈的酒,最后仍是甜。
“我”是任性的。但“我”始终还是父亲的孩子。父亲与我倾听鸢在笼子里发出的声响,然后静静入睡。然后我静静的看着他,就像他过去看着孩时的我一样。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六):这是一个安静的故事
这是一个安静的故事。
父亲缠绵病榻,家里依靠父亲每月领取微薄的救济金,以及“我”在敬老院的工作——陪老人们散步赚取小费而维持生活。
每天,“我”按时出门去工作,陪愿意散步的老人在公园里绕圈,时尔听老人讲一个过往的故事;没工作或天气不佳时,在伯格曼先生的小屋喝上两杯咖啡,安静地望着窗外的长椅。离开敬老院后,去佩西亚街看那只鸢,,静静地待在它旁边,寻思着何时买下它,如何安置它。接着回家,把当天工作的酬劳交一半给母亲,再去陪父亲讲话,重复地讲那个凭空编造的捕鸢故事。
一切仿佛宁静得如窗外门前厚厚的积雪。只有每天晚上母亲形迹可疑的外出,和那一声定时照明灯的开关响声,像梗在“我”和父亲心中、梦中的刺。
为了凑够买鸢的钱,“我”接了两单敬老院以外的工作:“处理”两窝被主人放弃的猫崽。当“我”用一桶热水把那些猫崽溺杀后,它们就化成了半粉半黑的幽灵,开始缠绕在“我”的心里,脑海里,“我”和伯格曼再也不能安心平静地好好喝咖啡了。
入冬后,天气恶化,散步的工作停滞了,“我”攒钱的计划受挫。就在这时,有人委托处理一条主人去世了的老狗,价格很有吸引力,“我”终究撇开煎熬同意了。于是,我带着那条老狗,往火车站方向去了。沿着铁道的方向,路过长满落叶松林的山丘,穿过桥梁,往荒无人烟的方向静静走着。只在为了甩脱狗的奔跑中听闻一些喘息。在见到雪地里狗留下的转弯痕迹时见到一点疼痛。在丢飞狗绳时见到一丝惊惧。
终于,“我”还是买了鸢,在它行将冻死前。“我”重新整理了鸟笼,与父亲细心地喂养鸢,一起欣赏它在美丽的光影中进食,一起静听它发出的所有声响,一起回味那个精心编造的故事。只是“我”必须听着水龙头的水滴声入睡,梦中一直重回那片荒野雪地,也不敢再去敬老院面对老人,遂职了工作。
“我”终于告诉母亲,请她晚上出门时不要打开定时照明灯,教她如何扶着楼梯木质扶手,在幽暗中静悄悄地一步一步往下。一步步仿似踩在心上。却像那厨房里安静的哭泣,无声。
最后,父亲还是死了。
中午的阳光很明亮,鸢儿安静地待着。“我”静静地给靴子擦鞋油。
这是一个安静的故事。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七):《安靜地流眼淚的辦法》
quot;而我,我比她更轻声地哭起来。我知道如何安静地哭泣。"
—— 《最后一场雪》
最近在书店给放于书架前端,法国小说《最后一场雪》。捏在手可以薄薄卷成半圈的厚度,里面像给柔风搂着的草原一样舒畅风格的翻译,外面淡忌廉蓝色的漂亮的封面,好像是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在书店买下的那一型书。我想大家选购书的原则大概也是如此,不是吗?
结果大概因为书的厚度确实算是“薄”的那类,读后不少也在嚷着“故事情感婉折絮逝、静谧回味如饴”之类的赞叹。好像普遍因为书的厚度不足所以对故事没多大信心似的样子。
然而,没有错这确切是写来柔淡婉薄、却酿溢满心絮的一部薄小说。就像主角经常说的那样:懂得安静地流眼泪的办法。
于贝尔·曼加莱利(Hubert Mingarelli),1956年生,法国作家。17岁时离开校园,曾任海员、亦曾到近法国边境的城市Grenoble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骤眼看似乎是不太受所谓正规社会接受的那一型人。话说回来,似乎这类型的人都倾向当上作家,譬如说《麦田捕手》的沙林杰,抑或经常嚷住这个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读《最后一场雪》时我也幻想Hubert Mingarelli是个这样的人。
会这样想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最后一场雪》的主角也是个想法仔细,而且思绪绕着自己团团转的小孩。可以轻易记住椅子给挪前的位置,能够听出从水滴是从水龙头抑或从湿裤子叩下来的分别。套用《挪威的森林》里小林绿的话:就像在混凝土墙仔细涂抹上水泥一样的细腻程度。简单地说,就是个想法比较奇怪的小孩。
原因没有提及,不过小孩一开始便没上学校,却每天到老人院守候着:假若有老人想要到楼下花园散步,便挽陪住他们舒踱着,以换取老人们给的小费。赚取的钱一半还要使于家用,所以可以想像绝对不是富裕的家庭。家中还有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父亲。不知怎的母亲每晚也会外出,外出时候公寓楼梯照明灯的哑呜每次总会让房间里的父亲颤熬不已。
这样的小孩一开始就要在冬天里买一只鸢。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所谓鸢,并不是小说封面那款看来像MUJI刻板一样艺术性的简洁漂亮的宠物家禽,而是我们通常说成做麻鹰的野生的兽。一只给困在旧货店鸟笼内的鸢。就连店东也不耐烦似地嚷着“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想着要买下那只鸢”。当然小孩并没足够的钱买下来,再多的老人想要散步也绝对不会变足够。
前面说过,主角是个绕着自己团团转、想法比较奇怪的小孩。跟他处过来的只有老人院里同样沉默的门房先生,里面偶尔找他散步的随时死去的老人们,以及长期卧病在床的父亲,仅此而已。就连小孩母亲也给写成若即若离的样子。于是孩子一边每晚给父亲编造猎鸢者与鸢搏击的故事,一边不断渴望想要买下那只鸢。而且可以想像卧病在床、每晚听儿子编说故事、煎熬忍耐着妻子每晚外出的父亲,也固然同样会是个封闭的人。小孩说过,觉得这个世界里唯一真正了解他的人就是他父亲,原因也就是这个。
quot;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泪流不止,而且知道如何安静地哭泣。
但是这一次,我的眼前没有出现鸢儿展翅翱翔的景象。
我只是泪流满脸,实实在在置身于所在的房间。"
——《最后一场雪》
首先是门房先生的姐姐挽来的一箱小猫,他姐姐过来想他处理掉。门房没忍心,于是请小孩杀掉它们,酬劳归小孩。后来是另一箱小猫。再后来是老人院里一位逝世妇人养过的狗。
于是,他终于可以买下那只鸢。
然后他与父亲每天愉快地在房间看着笼里的鸢啃掉顶级的鲜肉。
如果说小孩与父亲也是绕着自己团团转的封闭的人,那么,母亲每晚外出,不论她在干些什么,也隐喻着她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正因为这个,卧病在床的父亲惧怕着公寓楼梯照明灯的哑呜。也因为这个,小孩对母亲的感觉不如对父亲的爱。因为他们俩本来就是同类型的人。然后是鸢的莅临。俩父子每天仪式性地观赏着笼里的鸢儿,鸢的莅临为他们从团团转的缠结里找到了出口。父亲由鸢戳破出房间,大概捣凿回到年青时代的湖区铁道里;小孩也因让着鸢儿在自己脑袋翱翔圈颤,任由思绪在舒服的松林里展翅踱回。看来非常美好的结局。
除却鸢儿本身。俩父子解脱自由,前提是:一直被关在笼里的鸢。
正如小孩在严冬里将垂怜即将冻死的鸢从旧货店买回来,前提是:让两箱小猫跟一只狗纷纷消褪死去。
某程度上,这是一部关乎生与死、封闭与开脱的小说。而且若从这样的角度看来,故事假若能够停留在孩子每晚给父亲编说着猎鸢者与鸢搏击的故事,好像会变得更美好。不是吗?
这或许是他们,那些绕着自己团团转、想法比较奇怪的人之所以都倾向当上作家的原因。他们懂得安静地流眼泪的办法。
文 / 朱洛謙
刊于北京晨报 2013.6.2
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3-06/02/content_228377.htm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八):安静地哭泣
在我看来,这是篇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小说。第一视角的叙述,如诗般寂寥的口吻,总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擅长安静哭泣的少年。
“我”很喜欢鸢,鸢如同一道和煦的阳光射进了“我”原本灰白色的生活。当每天包括闲暇时喝咖啡都如此程序化的养老院工作结束之后,安静的陪上鸢一会儿,便是唯一的调剂品。对“我”而言,鸢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也因为鸢的出现而多了几分神采,哪怕只为一个虚构的捕鸢故事。“我”如同一位卓越的演讲家,变着花样为父亲讲述这个故事,然而,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到底还是鸢自己,至此,我已无法断定“我”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父亲而得到鸢。
得到鸢的过程是痛苦的,哪怕有一个看似充分的理由:不买下它,便会被冻死。在“我”三度替人杀死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之后,所有理由所有回忆都消失了,只剩下自己跪在雪地里,安静地哭泣。人往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什么,但是却从来不敢去直视。如同“我”,把阳光给了父亲,自己的阳光却没有了,只有无边的寂寞和在国道上翻飞的狗绳。
鸢终于还是带回来了,父亲的生机似乎又多了几分,每每地喂食,便成了如今父子之间最为完美的时刻,此刻,杀戮、死亡、孤独、痛苦似乎也都消失殆尽。“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父亲温情且又决绝的如是说道,父爱如山,我亦如山般爱父亲,我所想要的鸢,亦随着父亲飘然而去。
书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母亲,虽描写不多,但我们从那淡淡几行里可以体会到她作为母亲作为妻子作为未来的一家之主所承受的痛苦,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夜里出去究竟做了什么,但我们知道即便有如此多的痛苦在这个瘦弱女人身上,她依然只是静静地哭泣。
即使时值炎炎六月,深入骨髓的寒意,还是从书中的雪地向我袭来。人生中有太多的情不得已,难以抉择的痛苦让我们肝肠寸断,难以承受的压力让我们生不如死,而对于这死寂的世间,纵有无限的感伤,亦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对于这些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与重,我们唯一可做的便是学会安静地哭泣。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九):为什么要买一只鸢,而不是一个收音机
为什么要买一只鸢,而不是一个收音机
文/六回
“我”是谁?我以为这个“我”是一个女孩,她在路边看到一只鸢(读yuan,第一声),她想买下。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买一只鸢,而不是一个收音机。
她告诉她父亲关于想买鸢的事情,且经常重复得讲述一个她编造的一个捕鸢的故事,直到在病床的父亲睡去。
每天,她都会去一家养老院陪老人聊天和散步赚取小费,贴补家用。为了买这只日思夜想的鸢,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她杀了两只猫,她还处理了一条狗。
直到买到了那只鸢,直到她和躺在床上的父亲一起看着鸢进食,直到父亲在病床上闭上了双眼去世。小说就结束了。
《最后一场雪》是一本小书,116页,5万多字。
看到快结束时,我才知道这个“我”是一个男的。其实在书的腰封上就写着“令人动容的父子情感之作”。这个腰封,我根本就没注意到。
它真如腰封所写嘛?
肯定是对的,对于很多读者来说。
对于我来说,不止如此。它在写的是一个充满心事忧郁又很简单朴实的年轻人,写一个在病床上等待死亡的父亲,写一个形象模糊经常夜晚出行的母亲。它主要在写这个“我”,这个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的人。这个极其细腻、敏感且有点倔强的人。我被这个简单纯朴又有点怪的家庭静悄悄得就吸引了进去。
《最后一场雪》在写一个深情的故事,它不仅是父子情,黄昏在作者的描述中都是深情的,还有那大雪和一盏灯等等。
“夜幕降临的时候,父亲醒来了。我稍等了一会儿,才打开床头灯。我看到他还是神情疲惫。我起身去厨房端出碟子,然后放进鸟笼里给鸢儿吃。我回到椅子上坐着,我们父子俩默默无语地看着鸢儿在如此美丽的光影下进食。但是其后我们两人没有一起去听鸢儿打理羽毛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父亲又睡了。我把所有的灯都熄灭,包括房间和走廊的。”
我之所以以为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女孩,那是被这个“我”的细腻和温柔骗了。
另外,小说中描述的是买一只鸢,而不是一个收音机。也定下了这篇小说的想象空间和基调,也让我一直好奇得看下去,为什么是一只鸢。答案似乎就是或者仅仅是小说开头写的“我从来不曾如此渴望拥有什么东西”那般想拥有而已。他仅仅是想买一只鸢,其他都是其次的。
《最后一场雪》或许可以写得更长一些,写到8万字或者更长。
但作者没这么干,作为读者也已经够满足了。
它这样的篇幅是恰当和刚刚好的。从“我想买下那只鸢的那年,是多雪的一年”开始,到“我就像是一个在凝视着一双新靴子的人”结尾。多处的留白设置,反而让整个小说更有想象空间。父子情在儿子如愿以偿得买到鸢的前后呈现得日常且温情、动人。
《最后一场雪》可以称得上一部佳作,称得上是小说的教科书之一。
它的作者叫于贝尔·曼加莱利,法国梅迪西文学大奖得主,1956年生于法国洛林省,《最后一场雪》是于贝尔·曼加莱利奠定法国文坛地位的重要作品。
(刊于成都《明日快1周》2013.6)
《最后一场雪》读后感(十):没闲心就别看了
我看到的其实是n个故事:
我与鸢的故事
我与老爸老妈的故事
我与煮咖啡人的故事
我与猫猫狗狗的故事
我与敬老院的故事
这些故事之间有些奇妙的联系,但修为不够的我也说不出奇妙在哪。总之,它们就是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一起了。
如果把它当普通故事看,会觉得其叙事方式让人头疼。比如我是谁,我爸什么病,我妈为什么出去文章一概不提。当哲理文看,又觉得难以理解。
------------
果然不该因为名字封面和书皮上那“令人动容的xxxx”就冲动的买下它。
暂且不论这句话就是个噱头,跟冰冰加盟钢铁侠一样误导我颇多,这种调调实在不适合我这种喜欢囫囵吞枣的人食用。
全然不能理解其用30页描写抛弃一只狗的用意,也不明白那只鸢的象征意义。结果是,到最后也不知道它想要表达什么,是永生的孤独,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矛盾,还是对死亡的畏惧?
一言以蔽之,这文我读的憋死了。
故奉劝修养不够,时间不够,闲心不够的人还是不要看了。
唯一句话印象深刻:我走到鸟笼边,蹲了下来。夕阳西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