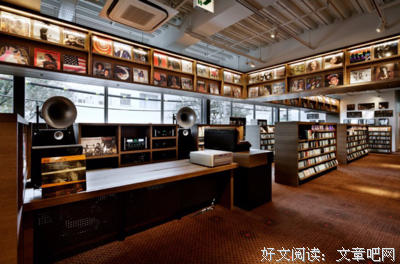《世界杂货店》读后感锦集
《世界杂货店》是一本由[美]罗伯特·谢克里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杂货店》读后感(二):《世界杂货店》—— 一场迷弟发起的总动员
《世界杂货店》出版于2012年,是美国科幻大师罗伯特·谢克里的短篇科幻选集,也是纽约书评“重现经典”书系中的一部。该书系的主编和每本书的策划编辑都是业界著名书评家,《世界杂货店》作为当年唯一一本科幻类作品,入选这个书系,也代表了主流文学批评界对谢克里的推崇和赞誉。
本书的主编之一,美国国家书评奖得主、麦克阿瑟奖得主乔纳森·勒瑟姆可谓美国跨文化界的扛把子,在书评、乐评、创作、出版、科幻领域各有建树,人脉广泛。
勒瑟姆做编辑纯属玩票,而且是迷弟性质的玩票。他只给两位作家做过选集:菲利普·迪克以及罗伯特·谢克里。在这本《世界杂货店·罗伯特谢克里科幻小说选》中,除了篇目选择,勒瑟姆还参与了序言的写作。在序言中他偶像滤镜全开,称赞“谢克里的故事一经过目,便从此再也挥之不去。”并以之与冯古内特、卡尔维诺等比肩,且“他令人难忘的佳作绝非寥寥二三,也不止八九篇或十数篇。”此外,勒瑟姆还因为不满“谢克里的事业发展和艺术成就仍然发生在科幻领域之内”而集结了主流文学界亲友团,各种周刊、日报、邮报、时报一拥而上,声势浩大地探讨谢克里的文学价值,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有了这样一位迷弟KOL,一时间谢克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也不乏读者,且讨论度甚高。实际上,对于罗伯特·谢克里,中国读者也同样不陌生。谢克里的作品短小精悍、想象力奇绝兼轻松幽默,风格独树一帜,几乎没有欣赏门槛,在十几年前刚被引入中国,就立即成为了中国科幻迷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他的《到地球取经》《欢迎仪式》《幽灵5号》《浪漫服务公司》,如今依然有读者愿意提及并津津乐道。
《世界杂货店》共收录26篇作品,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谢克里的创作巅峰期为核心,集结了谢克里最好、知名度最高,以及勒瑟姆最偏爱的作品,可以说是是近20年里谢克里分量最重的一本选集。除了一些中国读者熟悉的篇目,还有一多半国内第一次翻译引进的作品,比如,曾发表在《花花公子》上的《有无感觉》(Can you feel anything when i do this? )《世界杂货店》(The Store of the worlds )《从洋葱到胡萝卜》(Cordle to onion to carrot)等等,这些在当年卖出过5000美元天价的超一流小说。
这26篇作品,每一篇都将是一张带你进入奇异想象世界的车票,如果你在碎片时间,希望读一篇机智诙谐,魅力十足,而有具有启发意义的佳作,就来翻翻本书吧。
最后,附上勒瑟姆亲友团大作一览:
来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周刊总动员(待翻译)谢克里的文字犹如涂着蜂蜜的圆溜溜的洋葱,观之滑稽,入口甘甜,后味辛辣,最后不知不觉间,却已潸然泪下。犹记得2016年底,一个阴云低垂却仍有阳光照耀的冬日,在网上一篇介绍经典科幻名家的短文中,我看见了罗伯特·谢克里老先生的大名;第二天,我便有幸接到邀约,翻译他的这部精选佳作集,倒也算颇为奇妙的经历。一瞥日历,此时距这位曾以幽默短篇小说而名满天下的科幻巨擘去世已满十一年了。
罗伯特·谢克里生于1928年大萧条前夕的纽约,1946年高中毕业后,曾一路搭车旅行去加州。一路上,他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园艺师、椒盐饼干销售员、酒吧服务员、送奶工、仓库管理员等等。后来谢克里参军服役,归来之后,他就读于故乡纽约大学,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就如同某些“无名穷小子一路逆袭”的励志鸡汤故事一样,谢克里起初以普通小说试水文坛,此后却凭借奇趣的科幻短篇光速崛起,不到三十岁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幻作家,甚至与弗雷德里克·布朗、雷·布拉德伯里并称一时之杰,名登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巨匠之列;甚至也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极高评价,称他的小说与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讽刺文风一脉相承。
在翻译谢克里的作品之前,我对老先生了解有限,只知他以幽默闻名;而此时掩卷回顾,虽不敢妄下断语,但也深感老先生可谓集多产、多趣味、多情、多面等诸多特色于一身。
谢克里的多产是广为人知的。仅以他本名署名的作品,便有四百多篇短篇科幻小说和十五部长篇科幻小说,而他的实际产量则远远不止于此。在创造力处于巅峰的那些年,他如火山喷发一般,短短数年间,竟为各种杂志创作了一百多部短篇,以至于编辑为了避免他的名字在同一期杂志上重复次数过多,不得不让他使用多个笔名。
多趣味自然不必说。谢克里本就以幽默文风扬名天下,此前引入国内的多篇经典之作也颇以诙谐闻名。翻译谢克里的短篇可谓一种享受。随着一段段文字从笔端流出,一幕幕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也在幻想中轮番上演,若能搬上银幕的话,想必喜剧效果极佳。如《从洋葱到胡萝卜》一文中,原本唯唯诺诺的主人公在法国餐厅里冲冠一怒、在凯旋门下高奏凯歌;《如你所是》中,外星酋长被人类体味熏晕、饱受折磨;还有《专家》中,倒霉军官去海边欢喜度假,却惨遭外星人绑架,无不令人莞尔。谢克里的幽默无需过多修饰,浑然天成,仿佛速写一般,寥寥数语,人物便栩栩如生,鲜活的场景也跃然纸上。
说到多情,谢克里一生罗曼史不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欧洲度假胜地伊比萨岛邂逅了他的第三任妻子阿比·舒尔曼,并迅速结为连理。而在《从洋葱到胡萝卜》中,男主人公驾车横越欧洲,来到英国,在伦敦塔下与女神偶遇,很快坠入爱河,二人并肩同游,最终在新泽西州小镇携手终老。不知这个故事是否也有几分谢克里本人经历的写照?
至于多面,则是此时回首的感受。当我终于在电脑上敲入最后一个字,抬起头,重新望向窗外的人间烟火时,除了众所周知的滑稽诙谐,我不知该用哪些词句,才能最贴切地形容这部选集中呈现的多种风格。是《天堂二号》中对人类未来在大饥荒中以克隆人为食的灰暗诡谲,还是《会计》里巫师世家的叛逆传人偏偏想成为一个会计的俏皮轻快?是《风起卡雷拉》中对想象中外星世界刻画的细致入微,还是《可否一聊?》中洋洋洒洒以杜撰的语言交流时的煞有介事?是《陷落人海》中描写故乡布鲁克林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的黑色幽默,还是《温暖》中关于存在与虚无的理性思辨?
何况谢克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呢:当整个宇宙如一泓静水,水边安歇着一个才出生就已老了的人,独自面对漫漫永夜,与他相伴的唯有一台只会说五十个词的机器人,以及一个子虚乌有的女孩玛莎,直至最后,被长夜吞没。全文短短两千字,如一首孤寂入骨的悲凉长诗。
或许我可以借用《从洋葱到胡萝卜》的篇名吧——谢克里的文字犹如涂着蜂蜜的圆溜溜的洋葱,观之滑稽,入口甘甜,后味辛辣,最后不知不觉间,却已潸然泪下。
《世界杂货店》读后感(四):谢克里的一副科幻猛药:《世界杂货店》
罗伯特·谢克里是一位药力十足的作家,但所需的剂量却往往很少。区区十页或者十五页,他就能写出一篇最好的小说。他狡黠,如同冯内古特。他尖锐,如约瑟夫·海勒。他荒诞,如同卡尔维诺。他能使你目瞪口呆,能让你捧腹大笑,也许还能令你受益匪浅。但记住:谢克里的药力绝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你会感到持续的药效。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相反,一本书的作者往往比读者先失去兴趣。如果你运气好,谢克里也会见好就收,但他不是,他总是意犹未尽——故事写得好好的,突然话锋一转,让你措手不及,接着他便扬长而去。长话短说,谢克里是一位短跑选手,不是马拉松选手,但即便他心不在焉,他也依然在比赛。
所以你最好还是从这位科幻大师的短篇开始读起——尤其是那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往后的作品,那时的谢克里似乎拥有魔法和取之不尽的想象力,总能恰如其分地将一个故事带向结局。幸运的是,乔纳森·勒瑟姆和亚历克斯·阿布拉莫维奇帮我们筛选了这位作者的海量短篇,并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集结成册,就有了这本《世界杂货店:罗伯特·谢克里科幻小说集》。这几乎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集子了,它能帮助你理解为什么谢克里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就获得如此大的声誉。没有人“像谢克里那样巧妙地运用星际小说来承载诙谐和讽刺,颠倒众生,精巧机灵,令人着迷”,著名的评论家安东尼·布彻在1956年这样说到。在1960年,金斯莱·艾米斯认为谢克里是战后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称他为“科幻圈的头号牛虻”。布莱恩·奥尔迪斯后来将他比作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伏尔泰。
在艾米斯为他站台背书之际,谢克里那些最好的作品其实尚未写出来。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讽刺风格简直是给六十年代末的玩世不恭思潮量身定制。他本可以一跃成为一名反文化英雄,但他的对话风格和人物塑造仍然桎梏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方法和套路中。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和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宰场》中那种超越时代的感觉没有体现在他身上。他没有完成自身的跃迁,而是在一直重复自己。
但我们还是回到那些五十年代中期的优秀小说,大部分都发表在《银河》杂志上,并享受一把最好的谢克里吧。《第七个猎物》(1953)是其中名气最响的一篇,并被改编成了一部著名电影,由马塞罗·马斯楚安尼和乌苏拉·安德斯主演。尽管谢克里在后来的作品里尝试复制这样的风格和成功,但它们都无法超越这篇仅有十五页的杀人竞赛小说。我是先看的电影后读的小说,然后我就很震惊于谢克里用如此风轻云淡的笔触写出一个残酷至极的故事。
即便最后没死,谢克里小说里的主人公也都是一群糊里糊涂的倒霉蛋,一步步发现自己陷入了棘手的境地。在《世界杂货店》中,很多都是关于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故事,谢克里最擅长的就是讲那些好心办坏事的故事。在1953年发表与《银河》的《守望鸟》中,一项新技术可以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对其予以识别和阻止。故事本身充满趣味,笔调活泼,但其蕴含的智慧足以引发一场关于暴力本质和如何区分暴力的严肃探讨。在《去地球取经》(1956)和《爱情的语言》(1957)中,他在爱情主题上呈现了同样尖锐辛辣的反转。再一次,谢克里将主题升华于纯粹的逃避主义之上,向世人展示他能如此地发人深省——但又不会牺牲任何从容与幽默。这两篇故事刚好在十五页之内,似乎作者在这个长度能释放最佳药效。
书中的其他故事则更接近科幻小说的路数。关于星际战争(《形态》)、时间旅行(《双重赔偿》)、第一次接触(《如你所是》)、太空殖民(《土著人问题》)和异度空间透视(《保护》)这些主题,谢克里写出了种类繁多的故事。但是他最稳的主题,比如在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大脑切换》和《长生不老公司》中,则是人类意识以及它如何脱离原本的生物有机体而生存。你也许甚至会说,谢克里痴迷于灵魂的本质——有时候他的作品会带上一丝滑稽的神学色彩。但总的而言,谢克里在写作中强调荒诞而不是超验。本书中最好的三篇故事就从同样的起点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温暖》中的男子把脑海中的声音过于当真,结果自己变成这个声音;《宿醉》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冒险式假期,参与者根本无法确定到底有没有发生;《世界杂货店》则描绘了一个末日后的世界,人们可以拿财物换取另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体验,但是只限于在脑海里。
本书中创作时间较晚、篇幅较长的故事则揭示了谢克里在才华方面的局限——有些令人遗憾,但他仍然展示出他无可置疑的讽刺和社评功力。《陷落人海》创作于1968年,试图重现十五年前那篇《第七个猎物》中的生命力,同样是暴力和爱情背景的危险竞赛。但即便只有二十一页,这个故事也稍显臃肿,情节展开缓慢,人物动机几乎难以理解。在其他稍晚创作的故事里,比如《从洋葱到胡萝卜》和《人类行径》,谢克里则继承了他同时期那些长篇小说的缺陷——他只是将事件串联起来,希望读者能够忘记空白的过渡和未知的结局。
但是《世界杂货店》一书的编辑们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点。一眼看去,读者往往很奇怪为什么这本谢克里短篇集如此着重1953到1957这短短五年时间——确实,书中超过一半的作品都属于这个创作高峰期。毕竟,谢克里的写作生涯足有超过半个世纪,那为什么只关注这五年呢?是因为在氢弹发明到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这期间,谢克里在短篇科幻小说领域一枝独秀,并能将深奥的科学概念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确实值得表扬,一下子将标准拉到如此之高——而且令人难过的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基本只有他一人。
《世界杂货店》读后感(五):科幻幽默大师——罗伯特·谢克里
老相声里有这么句词儿:演员的肚——杂货铺。意思就是说相声演员肚子里的东西要多,得什么事儿都得知道点儿,什么都得懂点儿,那这相声才能说的好,说的精彩。
其实科幻小说作家肚子里的东西恐怕得更多,写的小说才够精彩。罗伯特·谢克里显然肚子里东西就不少,这不是嘛,就写了一部拥有着形形色色世界的杂货店。
这本《世界杂货店》是罗伯特·谢克里最新的中文版小说集。之前科幻世界大师系列出过两本,这次八光分的版本共收录了二十六篇,有12篇是第一次出中文版的新小说,而另外14篇虽然是以前有过中文版了,但这次也经过了重新翻译或是修订。其中有5篇是孙维梓先生翻译的旧作,翻到书末译者介绍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科幻翻译家孙维梓先生已经在2014年去世了。
要说起短篇科幻小说,恐怕但凡是科幻作家都写过,各个科幻大师都有不少短篇小说作品。要说没写过短篇的嘛——那恐怕掰着手指头都能数的过来,而且恐怕还是玩票业余写过那么一两部科幻小说的人。所以短篇科幻小说在科幻界不新鲜,写短篇科幻小说的作家就更不新鲜了。
但是,说道以短篇科幻见长的,甚至是以短篇科幻为主业的科幻作家,而且还写得生龙活虎惊世骇俗的,那全世界掰着手指头恐怕也就俩人。一个是日本的星新一,一个就是美国的罗伯特·谢克里。这二位可以说是短篇科幻双雄,不单数量惊人(星新一举行过一千零一夜庆祝活动,就是庆祝他发表第1001部小说,而他的总创作量绝不止于此。),质量更是惊人,哪怕说篇篇都精彩好像也不怎么过分。
比方说他的“大猎杀”类型小说,据说是开创了真人猎杀真人这种故事形式的先河。简单点说就是电视台制作节目,让一个人扮演猎手,另一个人扮演猎物,进行实打实的猎杀行动。杀死猎物是猎手获胜,杀死猎人是猎物获胜,获胜者自然获得重奖,而失败者就是实实在在的死。
很残酷,很冷血,很惨无人道,也很刺激。
于是催生了后来者无数的效仿之作,从小说到影视不一而足。好莱坞就拍摄过不少这类电影,有烂片,有经典,最经典的恐怕算是施瓦辛格的《过关斩将》。近些年最经典的恐怕就是《饥饿游戏》了。都是这个路子。
诚然,谢克里的短篇小说有浪漫的,忧郁的,惊悚的,恐怖的,怅惘的,神秘主义的,但绝大多数短篇科幻小说都透着幽默诙谐的色彩,且不管是冷幽默还是黑色幽默,反正都是幽默就对了。
要不然我用相声开头呢,就是因为这两者异曲同工啊。
说道幽默,想当年喜剧演员陈佩斯有过一番感悟。80年代到90年代,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可说一时无二,当时他也做过不少喜剧幽默的探索。90年代,他说起这番探索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很让他自豪的事情,他领悟到了一个幽默的真谛,就是尴尬。在情节当中制造尴尬,这种尴尬就会产生幽默。
陈佩斯感觉这是他的一大发现,感觉十分骄傲,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卓别林的一些书,卓别林总结喜剧表演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尴尬”。陈佩斯一看到此,感觉心潮澎湃,因为他居然跟大师暗和了。
所以看得出,制造幽默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尴尬”。这是自古以来幽默工作者共同的认识。小品如此,电影如此,相声如此,科幻小说也是如此。
而罗伯特·谢克里自然是个中高手。
以我最喜欢的“大风”来说说这种尴尬。就是《风起卡雷拉》。
人类到了一个整天刮大风的星球去搞开发。为了开发资源赚钱嘛,什么样的地方都得去。可这地方整天都刮大风,十几级的大风都是常事儿。地球人要在这儿生活,必须用厚钢板做成房子,房子周围还要用老粗的钢柱竖起一片钢铁丛林,以防被风吹来的石头砸坏房子。
人是别想出去溜达的,大风得把肺吹爆了。要想出去,得坐到十几吨的车子里才行,最大马力逆风行驶也是龟速。 然而这种大风环境里还有当地生物,他们是习惯在大风里的,他们的呼吸系统必须要靠着大风吹才能呼吸,要是风小了,就得窒息过去。地球人自然要跟当地人和谐相处才行。
这天风稍微大了点,他们的车子基本就报废了,他们的房子就要被吹飞了,各种保护设施也基本废了,反正是没法活了。打前站的地球人肯定不能忍这种环境啊,想着早点走,可是接应的飞船还得过大半年才能来,所以只能忍着。
可就这时候,他们发现当地人开始逃荒了,全家老小总动员抛家舍业去山里逃难。 地球人就想知道他们为啥跑。当地人说,当地的风季即将到来,他们要到山里避避风,不然没法活。
地球人咋办?
这就把尴尬的气氛制造起来了。让人物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里,只能按着环境行事,但是当环境跟人发生了极端的冲突,就产生了尴尬的境地。看到这里总会让人忍俊不禁。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啊,要不然全世界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那么少呢?绝对比科幻大师还要少的多得多。谢克里就是制造这种尴尬境地的高手。
比如《守望鸟》里所向无敌的机器鸟,《土著人问题》里被强行当作外星人的地球人,等等。甚至偷窥心理的《人类行径》,大猎杀类型的《第七个猎物》也能制造出这种尴尬情节,造出些黑色幽默来。而《可否一聊》里除了主角儿处于无奈境地的那种幽默,对于外星语言的分析更是绝了,绝不次于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
一般来说幽默故事是最难写的,可偏偏谢克里几乎篇篇都能带着幽默,你说绝不绝。
当然,谢克里的小说也不单单是幽默,有些故事还有点菲利普·迪克故事的影子。比如《温暖》《世界杂货店》等,营造出的迷幻气氛不次于菲利普·迪克。
那么问题来了,谢克里是怎么做到如此高产又高质量的呢?
答案也许可以从迈克·雷斯尼克讲的谢克里趣闻轶事里找到答案。谢克里告诉雷斯尼克,说他每天要写五千单词,如果没灵感写不出来咋办呢?谢克里有个绝招,就是把他自己的名字“罗伯特·谢克里”在打字机上敲2500遍,这不就凑够5000单词了嘛。
谢克里真是这么干的。一般来说,等他敲了八九百遍之后,他的脑子里就会跳出来个小人儿,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真***要把剩下的3300个单词都敲出来吗?有这功夫还不如写个故事换钱呐。”于是他就只好写个故事。据他自己说,这招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