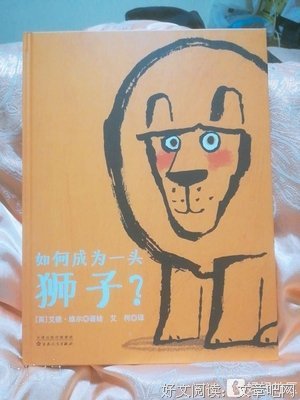审美的脑读后感锦集
《审美的脑》是一本由Anjan Chatterjee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8.00,页数:2016-9-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还挺有意思的。第一部分生物本能的美其实是进化学说的内容,相对来说没什么新知识点。到第二部分讲快乐,就涉及到了刺激的产生,行为经济学等更新的知识,到第三部分讲艺术,虽然理论很散乱,但对我来说算看到了一些很好玩的知识点。
●还挺有趣的
●心理科学和脑科学不多,大多在做简单统计和猜测,没确切的研究出因果关系,只是#从猜想中来,到也许中去#,令人丧气。如果是家庭报这种科普专栏汇总,还差不多;如果是专门写的论文,就,太!差!了!
●前几章读得我超激动的,是5星好评的那种感觉,后来就流于纯粹平铺的叙述,糊弄着读完了…… 对演化心理学和神经美学的结合也不是很到位 不过作者是个很厉害的大佬啊……
●21世纪颅相学+粗糙可怕的生物还原主义+20年前的认知科学+根本不懂美学 的伪科学杂烩
●7.7。多是一些猜想,但常有启发性。
●審美體驗是不涉及利益的興趣;對面孔美和風景美的追求幫助人類祖先生存;藝術的水深,深,很深,杜尚的便池不算啥,皮耶羅·曼佐尼的shit還拍出過12.4萬歐元…… 不必為生存掙扎,就能更關注藝術……
●以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为经纬度,以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美学、经济学、史学、医学等理论材料为基石解构艺术审美系统。吊诡之处在于所铺陈的背景知识与信息体系是单维度的,而本质上人体对艺术审美的感知能力却超越了脑的载体是多维度的。作者针对“盲人摸象”的寓言提出一个有趣的设想:艺术哲学家或许亦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触及到艺术的不同方面,全面了解各种理论,便将得出关于艺术的完整观点。但这个寓言只在我们不是盲的条件下才可成立。但我们极有可能是盲的,一如我们可能对于艺术一无所知,那么想象中的大象客观上有可能并不存在。我们进行拆解分析的只是我们的脑体结构之外的丰盈幻觉。私人较为认同康德“不涉及利益的兴趣”这一审美概念,即喜欢与想要的二元论,认同与艺术对象保持一定心里距离的审美态度。
●欣赏艺术就像跟朋友在一起消磨时光,或像是过性生活,享受美食,能满足人类基本的需求。
●第一部分看得简直要生气了。后两部分有学到新东西,不然打两分最多了。
《审美的脑》读后感(一):科普,心智,美是什么
审美是一种深刻的自我体验,既然是自我体验,作者认为也一定存在着某些可研究的机制。
在开头,作者也谈到,不一部分人文学家不赞同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美学,而作者认为审美体验一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心智。
首先,作者谈到什么是美?毫无疑问,审美是一种主观体验,但这种主观体验与感受,情境,意义有关。比如什么面孔是美的?婴儿脸是公认美的,很多卡通形象如米老鼠的设计就是基于婴儿脸;男人认为女性什么面孔是美的,主要是基于外貌所传达的年轻,雌激素,生育能力,性格等判断;而女性判断男性美,更深层的原因也是基于生存的判定;让人感受美好的大自然,也是适宜居住,繁衍的条件。
第二部分,作者谈到了快乐,快乐是一种自我奖赏,食物、水、性是首要的奖赏;金钱和艺术是第二级奖赏。这部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喜欢和想要的区别。喜欢是我们体验到这件东西,产生美感、愉悦的感觉,比如小老鼠吃到美味食物后会产生愉悦的表情;而想要是一种欲望,可能我们并不真的喜欢。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产品设计还是要尽量贴近人们的欲望,而不仅仅是让购买者长生喜欢。
在第三部分,作者提到审美与快乐有关,不太认同,有些艺术品也许我们并不喜欢,也不能引发我们产生美好的体验,但不能说它不是艺术。
书中引用了很多研究的案例,可信度、科普价值较高。我觉得研究可以看,可以用,但不能完全就视为真理,研究是片面的、割裂的,真正想要拥有美的体验,觉知最重要,没在书中发现类似的观点。
《审美的脑》读后感(二):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
一本关于美学的重要著作,将大脑与统计科学联系了起来,启发甚多。
19面孔美的三参数为:平均性averageness,对称性symmetry,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
平均性指的是优生学中的特征,并不是平板的脸,而是经过统计计算出来的如鼻的厚薄度、眼间距等。(宋案:参考BBC纪录片《人脸的奥秘》)
对称性是用同卵双胞胎证实的,用左右侧五官之间的距离来衡量的。
性二态指雌激素、睾酮给人带来的女性化、男性化的特征。现在鹿晗之类的,在性二态方面相当均衡。直男是不受欢迎的。雌激素给人以婴儿的印象,迪士尼动画的形象也利用了这一点。宋案:其实直接译成性征就完了。
22排卵转移假说(ovulatory shift hypothesis)是说年轻女人觉得男人是否具有吸引力,取决于他们想要短期还是长期的性伴侣。如果是短期的,他们会偏好男子气概强的。
averageness,还用在了第四章《身体美》中,比如克拉克、米开朗基罗认可的美的比例。25页男人、女人都喜欢身体呈对称性的。在美国高个子侯选人总能胜出。连女人选精子,都偏爱个高的。古罗马女人用驴奶洗澡,将此作为一种化学焕肤的方法。
26古罗马男人穿胸铠,主要是凸显胸部的宽度。今天男健美运动员的胸腰比可达到2:1。
27男人喜欢苗条的,还是丰满的女人与经济有关。经济不景气时,偏好尺寸大的。经济繁荣时,娃娃脸更受欢迎。
79食物可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快乐。玛雅人很早就用可可粉、水、蜂蜜、红辣椒制作巧克力,让林奈赞美为上帝的食物。其中花生四烯乙醇胺的英文是anandamide是用佛弟子阿难命名的。
87人的性欲得到满足时,眶额叶皮层外侧的神经活动会增强。会使人的伏隔核兴奋。相反,钱带来的刺激是抽象的。
我认为,书末尾部分对艺术的解释是不成功的。
《审美的脑》读后感(三):快乐的进化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是:神经科学是硬件,心理学是运行其上的操作系统。研究心理学是因为想知道为什么人会做出那样的行为,而研究神经科学则是想进一步知道其底层的逻辑。比如人在发现自己出错的时候反而会扭曲甚至自我欺骗,这种行为的心理学上的解释是认知失调和合理化。但是为什么人会有合理化倾向,大脑究竟做了什么?有没有办法避免它?这些就需要求助于底层硬件即神经科学了。
这本书要用神经科学来解释美。神经科学可以直接解释的是快乐。两种快乐感,一种是喜欢另一种是欲望,分别由阿片受体/大麻素和多巴胺传递。那快乐怎么和美建立联系呢?
快乐首先是源于演化,它对生存有用的。因为快乐驱动的多巴胺会开启大脑的奖赏回路,这个奖赏系统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它激发行动,帮助学习,让人得以在各种环境下生存。比如我们的祖先在食物匮乏的时候,正是吃了糖和脂肪得到的快乐启动的奖赏回路,让人不断地摄取这种营养物来维持生存。同样,我们的祖先看到对称的人脸,茂密的草原,以及数字的思考中感到快乐,因为这些让他们繁育后代,狩猎食物,计划生产。因此这些美的东西是奖赏,是有适应性有用性的。而我们继承了他们体验美时感到的快乐,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是美的。
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欣赏艺术在更重要的层次上是“不涉及利益的兴趣”。虽然审美是普遍的,但也是极其个人的和经验式的。我们很难相信在美术馆欣赏塞尚的画是一种对生存有用的策略。同时艺术和本能完全无关的观点也不那么令人信服,毕竟几乎所有人在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都会深受震动。所以这本书在讨论了艺术本能论和艺术是演化副产品这两个对立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艺术不是适应性的表达,而是对局部条件的一种灵敏的反应”。艺术的起源可能是源于人的本能,但是它的繁荣恰恰在于它脱离了本能可以自由发展,这样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脱离了审美的,更加“意义”维度上,更加“不涉及利益“的抽象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等。
关于艺术,在另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家史蒂夫·平克的《心智探奇》里,他认为在生物学意义上,艺术是不适应的。绝大部分艺术并不能“在演化的环境中增加基因的复制”。艺术在他看来更多是一种让精英们拿来炫耀和区分身份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晦涩难懂的原因。
关于快乐,《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里提到康德的观点。他说人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因为它给你直接的好处;第二种快乐,是你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快乐,这是道德上的快乐;第三种快乐,是它既没有给你好处,也不涉及道德,但它让你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灵上的快乐。比如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这种快乐才叫美,才叫艺术。当然康德的第一种快乐的好处已经不全都是演化意义上的好处了,更多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功利性的好处。他把艺术归为第三种快乐,是纯粹的心灵上的快乐。这种快乐似乎是脱离了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解释的那种本能的,为了生存的快乐,而是一种心灵世界的“快乐”,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肉体,没有肉体的生存之忧。
所以,视角从神经科学来到艺术,我们也就从脑抵达了心灵。进化选择了现在的脑,我们只能接受糖和脂肪带来的肥胖煎熬。但心灵却是无比自由的世界,在这里,艺术畅游无阻。
《审美的脑》读后感(四):《审美的脑》:新锐,有启发
这本书的内容虽然不深,但最好了解一点神经科学的基础(比如《心思大开》和《生物心理学》)后再看,不然可能有点难读,演化心理学倒是懂不懂都无所谓,书里解释得非常详细。有点像九九乘法表,虽然依然是初级数学,但不先学会加减法的话理解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
书里很多观点还只是作者的推测,因为神经美学是个新学科,现有的许多理论都存在争议,作者做了一些整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来说我是比较赞同的,看了有很大启发。
(这本书可能是作者单独文章的整合,经常出现不同章节内反复解释个别知识的现象,不过应该算小问题吧,反正也不贵)
因为书里也科普了演化心理学的知识,所以前三分之一的内容比较基础,从中期开始出现了大量非常新锐的观点,分享几个笔记:
1.Roguelike的生理基础: 比起每次都会得到奖赏,时断时续 不可预测的奖赏会让我们更频繁地重复某些行为。 2. 骗氪重要手段: 先用庞杂的系统或信息把玩家拖疲劳,玩家就容易在烦躁和智熄中冲动消费。 3. 喜欢和想要是两回事,简单来说重复玩喜欢的游戏边际效益递减。当玩家顶着递减的效益,还想靠游戏时数硬刚空虚感时,就出现了成瘾的迹象。 4. 有一个说法是,与其说艺术家利用视觉属性描绘现实世界,不如说他们探索的是视觉系统本身的特性。美学方面,我前两天写过一篇手札:先想象一位贤妻良母杀人犯,然后看看《The Aesthetic Brain(审美的脑)》里这段话:“……第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单身,那么维也纳是个好地方,那里有活跃的社交活动,很容易让你碰到另一半。 第二种说法则强调维也纳是一个大城市,像大部分大城市一样,维也纳也有犯罪活动。 听到第一种说法的学生,盯着有性吸引力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看的时间比没有的长。听到第二种说法的,盯着有吸引力的女人面孔的时间不变,但是有吸引力的男人面孔不再引起他们的注意。 因为街头暴力更多与男人有关,在危险的大城市这种情境下,男人作为潜在危险的角色比作为潜在性伴侣的角色更为突出。” 试图用演化来解释审美的想法很有意思,这个例子也确实有些道理,而且,审美的演化预设是既可以正着用,也可以反着用的。 比如在《Hotline Miami(迈阿密热线)》中,主角是个穿着夹克衫、气质冷酷的男人,可以说跟这个充斥着暴力美学的游戏非常契合了,玩家玩起来时多少会有些“就是这个味道啊”的王道感觉。 但假如一款暴力游戏的主角,变成了一个矫捷高挑的冷酷女人呢?或者一个看上去还挺柔弱的小妹妹?或者一个就算溅了满脸血还神情温柔甚至带点仙气的大姐姐?有没有“啊……这样也好带感”的感觉?反着用,大多就是俗称的反差美感了。 演化心理学在其中的作用之一,就是给我们一份经过科学验证的王道感官模板。翻出我刚塞进箱子里打算封印的《演化心理学》,再举个例子: 1. 男性对年轻的女性有偏好,这个非常直观,因为年轻女性的繁殖能力更强。试想一位年近50岁的孕妇。 2. 有调查表明年轻女子的发质普遍比年长女子要好,发质跟女性健康状况存在正相关,现在想想这位孕妇有着一头亮丽的秀发。 3. 现在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是,“女性化”的面孔通常意味着高水平的雌性激素和卵巢激素,而女性化通常指的是:“嘴唇饱满、眼睛大、颚骨薄、下巴小、颧骨高、嘴巴和颚骨的距离短。”那么,现在这位孕妇抿着薄唇,因为视力问题眯着带着皱纹的双眼,颧骨扁塌,棱角分明的下颚勾出一个略方的下巴。 好了,如果这是一位跟年轻的真命天子陷入热恋的保守女性,她的眼神可能是焦虑中又透着破釜沉舟的决意的;如果这是一位命途多舛的……比如“嫁给了大山”的女性,她可能是绝望而麻木的,也可能是神情中仍带着愤怒和隐忍、并因为即将逃离而隐含生机的。 再联系一下发质,小青年可能就是第一眼看见了她这保养得当的长发而爱上了这位深知如何自爱的成熟女性;又或者,年近50还能怀孕的躯体和悉心打理的长发,就是这位被贩卖到山里的女子一直没有放弃逃生计划的暗示。 不管“她”究竟是何人,这样一个违背演化预设的角色,相比于那些符合预设的王道角色,往往更轻易就能负担矛盾的冲击力。
《审美的脑》读后感(五):美与艺术:演化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李文倩
关于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美”和“艺术”这两个概念似乎都是绕不开的。事实上,以往的美学研究,有相当多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而展开的。由此,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美学的问题,恐怕仍然难以绕开这两个概念。
人们在不同的理论预设或概念框架中追问或讨论美与艺术的问题。在西方传统中,哲人们追问美与艺术的本质,力图在流变的、多样的现象之中把握不变的一。这样一种形而上的追问,在传统的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哲人们提出各自的理论或学说,努力与他人争论或辩驳,种种讨论加深了我们对美与艺术的理解,但始终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统一的、普遍有效的理论。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到了18世纪中叶,我们今天所普遍认为的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美学,被认为是认识论的一部分,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与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相对。作为认识论的美学,可被视为整体科学事业的一部分。认识论的基础是主客二分,事实上,也只有摆脱了那种日常的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感知方式,科学认识才是可能的。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人们对美与艺术尤其是美的本质问题有很多争论,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
英国哲学家达米特认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形而上学,到了17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向,即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这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从以上的简单讨论中,我们也可看到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亦分别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框架内得以被讨论。
到了20世纪,达米特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又一次大的转向,即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由此被一些人视为第一哲学。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美”与“艺术”的概念得到了相当多的讨论。一些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派的哲学家认为,“美”与“艺术”的概念是无法定义的,由此,任何试图寻求“美”与“艺术”本质的做法,都不过是徒劳。照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哲学家们所能做的,是将“美”与“艺术”这样的大概念,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它们本来的、日常的、复杂多样的用法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治疗性的,它不建构任何美学或艺术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颇具冲击力,但他对哲学之任务的规定,却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既不等同于科学,也不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建构理论,哲学则不然。在这样的理解中,科学是积极有为的,而哲学则不免消极。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或美学的消极理解,存在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即有可能会取消哲学或美学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学者们试图在更积极的意义上从事美学研究,并为此提出了种种“纲领”或方案。但对于这样一些“纲领”或方案,人们尽管争论颇多,却始终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判据。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笔者认为,如果真要考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学与科学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形而上学力图在多之中寻求一、在变化之中寻找不变的东西,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有其一致性。形而上学孕育了近代科学。认识论是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形而上学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美学与科学的关系都相当密切。甚至可以说,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一直在试图用广义科学的方式来解决美学问题,尽管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哲学的语言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使哲学与科学分离了。这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罗素、奎因等哲学家并不接受。
基于以上简单回顾,笔者认为美学研究的前途之一在于与科学结盟。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里的“科学”。在古希腊,科学是与形而上学混杂在一起的,并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近代认识论的科学“基础”,是以数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为范型的。美学研究的历史表明,建基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种种美学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传统美学到了今天,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境况中,美国学者安简·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在《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一书中提出,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美与艺术的问题,或许能让我们获得一些不同以往的新鲜见解。
如果我们将演化论视为一种理论基础或方法论,那么它与形而上学是非常不同的:演化论是经验的,而形而上学是非经验的。演化论也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但在演化心理学看来,“自然就像塑造我们的身体一样塑造了我们的脑(心智)。”这即是说,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与客体相对的模糊的认知主体,大脑作为具有认知功能的器官,本身就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美学研究需要关注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而不是继续沉浸在主客关系的“思辨”之中。
安简·查特吉的上述方法论提议,也并不是绝对新鲜的。在19世纪末,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兴起,费希纳就曾提出,美学研究需要经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自上而下”的美学到“自下而上”的美学。所谓“自上而下”的美学,即形而上学框架内的美学。而所谓“自下而上”的美学,则强调从经验出发,尤其是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形而上学虽然孕育了科学,但也包含了许多非科学的东西。
在费希纳的倡导之下,人们曾将美学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心理学的进步,但心理学后来的发展,似乎并未完全满足人们的预期。维特根斯坦本人积极关注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但他同时也认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能解决美学问题。因为美学问题在科学之外。我们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安简·查特吉今天所作的尝试性工作,可被视为费希纳所倡导的方法的一个当代继续和发展。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即来简单看一下安简·查特吉如何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美与艺术的相关问题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人们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之内讨论美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安简·查特吉说:“美不是仅仅存在于客观世界或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的心智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思考、体验、行动,是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形成的。对美的体验是我们的心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的脑经过演化,认为某些对象具有普遍的美。”
这就是说,在演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内,美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当然也不是主客观“统一”的。因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分,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我们的大脑或心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一些东西具有“普遍的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是主观的。
长期以来,我们受康德美学的影响,认为美是无用的、超越功利的。美学也被认为是无用之学。但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美实际上是有用的,有利于个体健康及种族繁衍的。安简·查特吉说:“美的演化逻辑是:有吸引力的特征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这些特征是相对比较好的健康指标。”达尔文说,美的东西必定是健康的,即是从同一个角度而言。
美的选择与生殖活动相连,这鲜明地体现在人类男性与女性的相互选择中。安简·查特吉说:“男人偏好的女性特征是年轻、生育能力强,同时又带有些许性成熟感。”女性则普遍偏好“身体对称”的“高个子男人”,认为这样的男性更具吸引力。
演化心理学也有助于解释一些与艺术有关的问题。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说:“科学有望能够解释艺术家、艺术天才,甚至艺术,并且它将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艺术来研究人类行为。”
关于艺术的起源,以往人们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诸如巫术说、宗教说、游戏说以及劳动说等。在演化心理学的视野中,“艺术的起源在于:趾高气扬的男性互相竞争,创造出没有实用价值的装饰物,试图向女性观赏者证明自己的作品比其他人的更壮观、更优秀。”艺术的有用与无用,或可在此获得恰当的理解。一方面,艺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不能吃也不能喝,在多数情况下仅具有装饰作用。另一方面,艺术又是有用的,它有助于制作者向异性炫耀自己的杰出才能,从而赢得更多交配的机会。
“艺术的萌芽源于本能”,但艺术却不是一种本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说艺术不是一种“本能”,即是说从事艺术活动并不是人类天生的必须,它不同于吃饭、喝水、性交等活动。斯蒂芬·平克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语言能力是人先天所具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类而言,语言似乎比艺术更为根本。
艺术更多是文化的产物,“只有在历史文化背景中才能被理解。”这表明我们对于艺术的研究,既需要积极吸收科学的成果,又应该继续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安简·查特吉在积极倡导科学美学的同时,也指明了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科学美学能考察知识对审美体验的一般性影响,但不能考察与个别艺术品相关的特定的知识与多层意义。”的确,科学处理的是一般性、规律性的东西,它提出种种理论假说并寻求验证,而对于个别的、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分析,则仍然有待于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安简·查特吉还提醒道,“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描述性神经美学。”因为“描述性神经美学”的许多说法,目前还停留在科学假说的层面上,并未获得足够多的证实,因此建基于其上的知识并不足够牢固。
在这篇短评的最后,笔者还想强调一下在中国积极倡导科学(主要是演化心理学)美学的必要性。正如徐英瑾在《对于一种达尔文式的新人文—社会科学的展望》中所分析的,由于在相当多的中国大学中,美学被设置在“中文系”,而“这样的专业是疏远于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的纯人文主义者的大本营,其所擅长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的隔膜程度,可能要远甚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隔膜程度。”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专业设置,极有可能已经结构性地限制了一些学科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