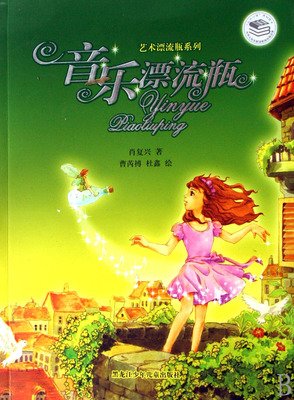酒吧长谈读后感100字
《酒吧长谈》是一本由[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201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酒吧长谈》精选点评:
●叙事线索的分配和选择太重要了,稍微做不好就让人困惑,打乱节奏,导致故事本该具备的“复杂的精确性”下降
●一组组对话之间插入回想、叙述以及画面之间的呼应,离间了线性时间发展的单调,抽离出立体情景的每一个棱角,无中生有般刻画出了包裹棱角的悬念—另一情景中与之相补充的棱角或者凹槽。如分光棱镜般将画面投射出的光按视角的不同成像为五彩斑斓的故事要素信息光谱!如果对那段卡魏德时期对社会的反思能再深刻点,以及后面再有相应的回响评论的话,个人会更满足点—可能圣地亚哥的最后的勇气也只是回想而不是反思,这个任务是丢给读者的!!!
●小说读出了电影画面感,第一次读完拉美长篇。
●首次见识到这种别出心裁的小说结构,很好的睡前读物,故事温柔,习惯了这段时间的陪伴,越往后越不舍得,真正的有一种小说人物因读者生因读者死的感觉,放下书他们都死去了,不想他们死,就只有一直读它。
●身份看似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一群人,在动荡不安的大社会背景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倒霉,那么别人就会让你倒霉。天真勇敢却又犹豫不决的圣地亚哥,伪善狡诈的费尔民,残暴变态的卡约,以及没有底线麻木不仁的安布罗休。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变换着角色,最终都无一例外的堕入深渊。 略萨太棒了!多线进行的叙述却丝毫不会惹人厌烦!管他什么主义,小说就应该这样富有吸引力!
●荡气回肠。第一段就让人确信这是传世之作,却在七百多页后依然让人屏住呼吸。秘鲁是什么时候倒霉的?你是什么时候倒霉的?个人与家国命运在历史中、在结构里相互纠缠,越陷越深,就像酒吧里用对话串起这一切的两个角色,在谎言和欲望中无法自拔,最终小人物与大时代一齐坠入深渊。揭露丑恶与罪行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目不暇接,推着读者飞奔向前,仿佛体验着同归于尽前的绝望速度,愈发黑暗。合上书才想起,谜底早在第一段就已揭晓,可依然无人幸免。记不得哪位大师说过,喜剧里才有偶然性,只存在必然性的故事注定是悲剧。《酒吧长谈》就是这样一部形式与内容双双完美的悲剧。
●结构现实主义的巅峰,完美的小说
●天使下地狱,魔鬼上天堂。 恶棍进朝堂,好人无处寻。 打手,混账,同性恋,妓院,酒吧,恶棍。 富翁,总统,将军,内阁,司机, 嘲讽,玩弄,欺瞒,哄骗。 秘鲁,你是从何时开始倒霉的 小萨,你是从出生就一直倒霉 秘鲁的孤独,何人知晓 略萨的同情,无人知晓 酒吧里的灯火熹微,长谈,仍将继续下去, 不出意外,酒吧长谈,将是我一生中读到的最为肮脏,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小说 一本真正可以阅读一生的经典 一首真正可以了解拉美的悲歌 值得力荐,值得细读,值得反思。
●文学是一团火,要烧掉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的人生经历中奥德利亚的八年,对话波的形式层层推进,妓女、佣人,打手,商人,部长,大时代下的不可控人生。
●这本书在写法上的问题很大。语言上的拉杂,啰嗦无法忍受。看似写实,实际上仍是幻想,毫无节制的幻想。犹如无根之木。
《酒吧长谈》读后感(一):五光十色的秘鲁
刚开始读的时候,有一种七零八落的感觉,作者似乎是将一面完整的镜子彻底打碎或是已经按着时间写完了整个作品,再将其打碎随意拼凑而成。而越读越发现虽然布局看似凌乱,但作者是按着某一种规律或共性组成一个个段落章节,读到最后发现依然是一面完整的镜子而并非碎片。
《酒吧长谈》读后感(二):毁灭与重生
在一个动荡不安、权力至上的社会里,个人命运的摇摆和信仰的崩塌,是最为揪心的命题了。圣地亚哥的命运集中了毁灭的痛苦和重生的自由。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秘鲁,处处是满溢的放纵与刺激,是随处的担忧与恐惧,是迷茫与无解。圣地亚哥的出身让他本可以走任何一条路,但当他一窥人心险恶、虚假面目后,他发现,他想选择的,是那个社会最为奢侈的真实平凡,简单快乐。这当然是一种奢望,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家人认为他的快乐是放任自己“堕落”到底层人群中,集权和恐怖主义政府又让他的社会价值变得虚假和一文不值。失去了一切信仰的支撑,他选择毁灭从前的自己,不再信仰。他失去了一切,拥有了一点点真实自由的自己。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圣地亚哥和几位同学的故事。他们起初生机勃勃,活力四射,他们一起阅读禁书,讨论政治和哲学,希望加入某些组织去为这个社会改变一点什么。然而圣地亚哥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大家聚集起来只是为了消磨无聊,谈恋爱罢了。因为确切地说,他们没有任何信仰,他们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一切活动都只不过是为了假装看上去他们有信仰。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政府的目的就是让青年人没有信仰,失去追求,大学成为政府听命者的培养机构,媒体成为政府的口舌。这个年代的青年,早早便消逝了。
《酒吧长谈》读后感(三):如果你想通过一部书纵览拉美文学或者结构主义文学,那目前我会选择推荐略萨的《酒吧长谈》
这部作品全景纵览式地展现了秘鲁奥德利亚军人政府独裁前后大小人物的生存钩沉;然而,这部小说却以一次十余年后两个落魄小人物偶遇式的酒吧谈话为勾连和贯穿,把那几年来的诡谲多变与彼此交往串通,在五十余万字的篇幅里,切片式的场景和对话无缝而和谐的切换、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察视角、涟漪一样的中心事件开花逐渐荡漾延展、不同时空背景间事件的迅速切换和整合、设置悬念直至最后的解构、事件句与句/段与段乃至章与章之间的倒叙,在略萨笔下熟练地应用着。此书分四部多章节,每部以一个中心展开,串联起不同人丰富的命运起伏,连缀勾合,丰富地展现出军事独裁背景下不同人的境遇、选择和结局,令人咋舌。
略萨尤其熟练地利用丰富的对话(译者的评价成为“对话波”、“涟漪”)之间的逻辑关系切换展开情节,对话内外都被其清晰而准确地整合于结构之中而不让读者产生误解,虽偶感龃龉但如果细细纵览(前提是对人物名和基本的情节相对熟悉)仍然很容易把握,酒吧长谈的内容和多个情境之下的混合逐渐荡漾和展开情节,译者统计最多有十八组对话进行混合——若是呈现在荧幕上怕是观众早已昏头转向,但对于认真的读者而言,略萨会贴心地组织好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让读者比较容易就抓住一些关键内容。甚至相比语言和结构的绚丽,背景反而显得弱了一些,要知道这可是生动的拉美军事独裁背景。
最后来说一下人物和内容感想吧。略萨再一次展现出个人在时代背景下无力的奋斗,所谓“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个妥协和摇摆的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丧失了命运的主导权;曾任内政部部长的贝尔穆德斯是个独裁者的白手套,政治上强力手腕,生活上声色犬马;圣地亚哥父亲费尔民作为大资本家,在人际关系上总显得令人同情,但在政治和私生活上却道貌岸然;贝尔穆德斯的前司机作为政治人物可怜的打手和利用者,残暴却可悲,对自己的悲剧麻木不仁。至于诸多小人物则苦涩不堪,尤其是女性角色各有各的悲戚,令人感喟。
此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云云在此不再赘述,总之这本万生相的作品绝对是上乘的读物,只需要认真读,一定会有震撼人心的感受!
《酒吧长谈》读后感(四):读《酒吧长谈》
很久没有写字了,但读完这么长一部作品,如果不写点什么,总觉得很对不起自己。
《酒吧长谈》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品。它那五十一万字的体量,逾七百业的厚度,以及顶着现实结构主义小说家名头的创作者略萨,无不使我对它久久的敬而远之。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当下定决心翻开第一页以后,我居然只用了一个周末就读完了两百多页。而当一个多礼拜之后的深夜合上全书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心里竟是满满的怅然若失:大教堂咖啡馆里的长谈就这样结束了吗?
说这是一本相当易读的书可能并不准确,但是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略萨确实在这本书中编织出了一种奇妙的结构,紧凑、直接而充满力量,它如旋涡般迫事回旋,又如飞轮般迫人向前。除了开头部分—小萨与安布罗修的重逢前后—压抑着午后催眠阳光中酒精浸泡过的昏昏沉沉,故事以略显单调的线条为后面的章节埋下无数的伏笔—其他部分全都是多线并进,一如奔出的赛马在不同的赛道上你追我赶。
这种结构在同一章里表现为许多人同时出现,许多事同时发生,许多话同时回响。略萨如同一个高明的电影导演,游刃有余的调度切换着镜头,让阅读者的眼前有时如罗生门,有时如平行宇宙,有时如多棱镜。究竟什么是谎言,什么只是可能性,什么又是事物不同的立面,全凭读者自己记忆的串联和思考去辨别。
另一方面,当我们跨越章节来感受这种结构,略萨的笔法则颇像立体主义的绘画。以“缪斯”为例:从她第一次出现开始,她的背景、她的故事、她的个性就基本都被作者用速写的线条勾勒得清清楚楚了,到她第二次出现则甚至连最后的悲惨结局也被描摹得分毫不差了。但作者所要表达的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于是,紧接着,略萨像毕加索一样,把所有打碎的细节通过安布罗修,通过凯妲,通过阿玛莉亚,通过小萨的叙述、观察、情绪、思考等等在书中不同章节一点点糅合叠加进去。这些不断加强和补充的细节把你一次次形成的对故事的理解与再理解又一层层覆盖与掰开来:你的注意力开始被集中到一个个单个的个体上,然后又被分散到一段段喧嚣的事件中,再然后则又一次次被拉回到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归属上。最终,这些片段、细节、线索终于可以随着终章的到来在完整的画面上被沉淀与安定下来。此时,在这幅被一次次涂抹、分割,然后又重新组合的画面上,缪斯、凯妲、安布罗修、阿玛莉亚、父亲、臭卡约、小萨,以及前前后后几百个人物都不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时光的刀锋在时间的化石断面上切出的脉络清晰独一无二的花纹。这把刀在化石上横着切下去,我们看到的是从乔洛人到大资本家,从反抗者到政客的社会众生。这把刀纵着切下去,我们看到的则是历史的潜伏、酝酿、爆发、高潮来临直至归于沉寂和衰败的熵值的递增。
因此,我读《酒吧长谈》,非常不愿意作出与“阶级”或“革命”层面有关的解读。恰恰相反,我宁愿相信书中那一句反复出现几十次的“小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就已经多少有了点“祥林嫂”般的同情和无奈。而小萨,甚至很可能比祥林嫂还要更糟糕一点,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倒霉的,哪怕连肤浅的错觉也没有。所以,我的理解—略萨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他的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是宏大社会下关于“人”的作品—它让我们关心人的孤独,人的失败,人的汲汲无功。你看我们的主人公小萨:他在人生的大河里顺流而下,无论是读书考试、参与政治,还是找寻工作或者投身爱情,他从来没有自己真正思考、选择、搏斗过什么。河水流到他脚下是什么方向,他就闭上眼跳上船漂到哪里去。而当他唯一一次试图自己轻轻划水选择离家出走,结果就被冲到了不同的河道中。但是,在那里他则继续安于“新”的“随波逐流”,令人费解的再也没有做出哪怕一点点尝试,换一条“河流”,或者回到原来的“河流”里。
也许,他以为他的这一次自我选择足够给与他在后来再也没有见到的同学们中的“尊严”。也许,他信仰他从此独立的生活就是“理想”的实现。也许,他以为他这样做可以对自己父亲所犯的不齿“错误”做出惩罚。也许,他以为这是他对自己“爱情”的坚持。但是,这一切在书中都毫无意义。他最终还是念念不忘重回圣马可读法律—那偏偏是他早年执拗放弃而父亲反复劝说的。他每天都在赊账中昏昏厄厄,连他的妻子都怨恨他不和家人和解带来的拮据难堪—此时,他所捍卫的爱情如同是空中楼阁。而他酒醉后面对安布罗修的激烈反应则更是把他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流露无遗—这么多年来,受惩罚的更多是他自己吧。他真的什么也无法改变,唯一改变的只是父亲曾经的“瘦儿子”日益无法遮挡的肚子,还有再也回不来的父亲和那些小说开头的平静时光—哪怕只是假象下的平静。而这是件多么令人伤心的事情!
无法抗争的孤独和徒劳无功的努力,又何止是小萨一个人。利马的观花埠几十年后经历数次革命、政变、发展,依然还是那个只属于上流人的观花埠。安布罗修一层不变的家乡依旧封闭、停滞,只让归来的游子留下垂垂老矣的眼泪。凯妲终究回到自己最开始的出发点,面对的仍然是令人厌烦的罗伯托。堂卡约从山区到利马,再到国外,最后回到利马,依然还是冷漠、自私,但却富有。政府经过政变,独裁,再政变,再独裁,最后回到民选,却仍然还是沙上的城堡,人人都在得过且过中被窒息得昏昏欲睡。
所有一切折腾,都只归于午后酒吧里四小时长谈后的几分唏嘘而已。这一切,又能比《百年孤独》里最终被雨水卷走的村子好多少呢?
小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
问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长谈》读后感(五):小萨,不愿成功亦不愿成仁的知识分子,只剩倒霉可选
略萨的《酒吧长谈》担得起一句气象万千。
此书旨在描绘奥德里亚军政府八年独裁期间秘鲁社会的广阔图景,通过资本家的公子圣地亚哥(又名小萨)和底层黑人安布罗修的一场酒吧长谈,勾连起不同阶层数十人的命运走向。
描写某一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群像作品在文坛中自不少见,而《酒吧长谈》又以其绚丽多姿的文学技巧独树一帜,读者为人物命运共情唏嘘的同时,还需要为弄明白作者在玩什么把戏耗费精力哦对不起是在推理和解谜的过程中增益了游戏的快感。
事实上,一旦厘清了书中冗长的人名,掌握了作者独创的几种编码规则以后,再读后文便如拨云见日。略萨在《酒吧长谈》中使用的结构技巧主要分为“双管法”和“对话波”两种。
“双管法”与电视剪辑中的双线并行相似,只不过更加自由肆意,有时两线的交点仅仅是一个概念,有时为表现事件的多因一果,略萨竟将3-4段对话平行铺开。
“对话波”则可以类比为从对话中荡漾出的涟漪。全文有一条主对话线,即贯穿全文的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在大教堂酒吧中的长谈、两条副对话线,即费尔民-安布罗修的对话(在最后一个章节之前,我们未能理解这一对话发生的场景与原因),以及圣地亚哥-卡里托斯的对话,用以带出圣地亚哥大学期间信仰破灭的心路历程。从这些寥寥几句、似是而非、有所隐瞒的对话中,穿插派生的是说话者回想的故事真相,事实在说与不说之间又形成一重张力。
作者对于事实的捏合方式为小说带来了悬疑特质,读者所追踪的不是线性的进展,而是在不断辨认新的图块,弥补这一幅立体拼图中的缺失,有时我们看见不同的人物故事,却不知人物间关系;有时我们只知道事情的结果,却不知过程,有时是知道了事实,却不知原因。缪斯的死、安布罗修与费尔民的关系作为核心的拼图,被巧妙地留在最后几个章节揭开,在解谜部分,作者回归线性叙事,使得故事在高潮处如飞流直下般通畅。
略萨在此书中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文学技巧,我们却不能忘记其主旨着眼于现实关照,是军权、政权、神权更替下动荡的社会和苦难的人民。《酒吧长谈》的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奥德里亚政权核心卡约·贝尔穆德斯以及大资产阶级费尔民为代表顶层人物。略萨对于政治的看法是负面的,他在竞选失败以后曾说:“ 谁介入政治,谁就和魔鬼签了契约 。”在《酒吧长谈》中卡约·贝尔穆德斯正是“魔鬼的化身”,他在青年时期便与卖牛奶的罗莎私奔,得到从政机会后便毅然将罗莎抛弃,再不涉足家乡,足见其果决又冷酷的特质。尔后凭借强硬、狡诈的手段迅速获得总统信任,一边圈养妓女,满足自己观看女同性恋的癖好。在应对联合党人发动的政变时,卡约一边听着与会者的高论,脑海里掠过的却是缪斯房间里旖旎的风景,略萨对于当政者的看法都在其中了。
译者孙家孟先生在译后序中称圣地亚哥的父亲费尔民·萨瓦拉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者”,我却认为略萨对他仍怀有善意和同情,他与圣地亚哥的父子关系、和安布罗修的“情人关系”亦成为全书中最令我动容的段落。作为能左右政局的大资本家,他应当享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最为之骄傲的瘦儿子与他离心,尽管他已经谅解和尊重了圣地亚哥的所有信仰和选择,日夜期盼他回家,圣地亚哥却仍然摆出“划清界限”的架势,对作为资本家的父亲和他“肮脏的钱财”敬而远之。作为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他在政坛上尔虞我诈、步步为营,却只能把自己的脆弱和欲望压抑起来,留给一个出身低贱的司机。他苦苦哀求安布罗修,“让我露露我的真相吧,让我做个婊子吧”,可若是安布罗修真的能“兴奋起来”,费尔民又会被耻感吞没。无论是对儿子还是情夫,他都像一个绅士一样尊重,卑微地祈求对方一点情感上的赐予。
第二类是以安布罗修、阿玛丽亚、缪斯为代表的底层社会。略萨致力于呈现独裁政权对于人们学习、工作、爱情、梦想和志向全方位的污染,以安布罗修为代表的这些人,则承担了最多政权带来的苦难,他们是大人物们呼之即来,又可以信手碾死的生物。因为警局的拷打,阿玛丽亚失去了第一个丈夫;安布罗修的父亲特里福尔修只想谋生,却在一场他并不理解的政治集会中,因为“被雇佣来拥护政府”而被殴打致死;妓女缪斯因为依附上层人物而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又因为卡约的失势而落魄,最终因为掌握大人物的秘辛被杀。在他们的身上有愚昧、贪利,也有阿玛丽亚淳朴善良,缪斯那样的至性重情。
最后一类是以圣地亚哥、卡利托斯为代表的知识青年,诺贝尔文学奖给略萨的授奖原因是:“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那个反抗失败的个体是圣地亚哥,也是略萨自己: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不愿做个“阔少爷”,于是考上了具有不妥协精神的圣马可大学,用一种浪漫的方式发现了社会的偏见和不平等,希望用同样浪漫的政治途径改变穷人的处境。
然而当圣地亚哥(或是略萨本人)参与其中的时候,他发现政治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党派选择,而无论面对暴虐的军政权,代表中下层利益的阿普拉党,还是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的gcd,他都无法摒弃自己的怀疑,即使时他最为认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排他性、扼杀想象和自由的宣传手法亦不能让他全盘接受。比起更多追随金钱享乐而随波逐流的人,知识分子圣地亚哥是用思想和原则指导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在入党时第一次退缩了。第二次学生运动被捕后,他彻底放弃了政治,因为懦弱或是厌倦。
每一个理想破灭,改换人生选择的节点,圣地亚哥都要如此拷问自己一番:小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你是从这时开始倒霉的吗?是发现理想和爱情一起破灭的时候?是堂费尔民把他从警察局捞出来,发现自己无法割断与家人联系的时候?是他选择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时候?还是得知关于父亲的真相的时候?圣地亚哥太清楚自己不想做什么,却对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毫无头绪,他拒绝像奇斯帕斯和蒂蒂一样参与罪恶的社会再生产,也撤离了同学们为某个信仰卖命的队伍,圣地亚哥的“倒霉”,实则是他拒绝了成功的道路,也拒绝了成仁的机会,只在规避两者的道路上顺流而下,浑浑噩噩,圣地亚哥投身报业,正如略萨转而在文学中寻求拯救社会的出路,毕竟文学是自由的、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影响深远的,远离实践而又不需要提出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