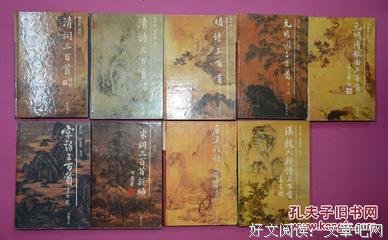《元明散曲三百首》读后感精选
《元明散曲三百首》是一本由浦江清 选注 / 蒙木 编订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19-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明散曲三百首》读后感(一):散曲中的美
散曲中的美
我想大部分人还是同我一样对“唐诗宋词”比较熟悉,也能随口吟诵几首诗词,或者创作几首,暂且不去管诗词的优劣,随性而喜。对散曲估计就比较陌生了。因为我对中国戏曲的接触几乎为零。的确汗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我只是皮毛。
马致远的小令《秋思》成为写秋的鼻祖是名副其实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画面感极强,唱起来回味悠长,音乐的魅力是无穷大的。一旦音乐响起,人的情绪立刻被带入那悠长的境界里。品析诗词曲,离不可音乐。元明散曲,带着乐感去读,能读出无数的美妙。
《元明散曲》是浦江清先生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为西南联大下一学期“曲选”课编选的教材。一看到这是一本大学教材,心里立刻生出敬意。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如何能编出适合教学的教材?的确如此,蒲先生的研究领域涵盖文学、历史、考古、民俗等诸多方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
蒲江清先生说:“后代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以诗歌为最好的文学。”而曲为诗之一种。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一旦深入研究,一定能发现其中很多规律,散曲与戏剧的联系,元杂剧与戏曲的联系,散曲与诗词的联系等,明代曲作家中,蒲先生人物汤显祖是“最杰出的剧作家”,但仍归因于元曲。他强调散曲作为曲体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忽视的。本册书选元代小令一百九十二首,套数五套;明代小令五十一首,套数四套。元代散曲数量占优,足以说明元曲的成就。蒲先生认为:元曲的成就如果合并戏曲与散曲来论是超过宋词的成就的,而与唐诗的成就可以相提并论的。
散曲题材广泛,是风流潇洒的,反正统思想。绝对没有酸腐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反之以道家的出世维多。多名士作风。读读蒲先生选取的这些散曲,他选择了很多优秀的作者,如张可久、马致远、乔吉、关汉卿、徐再思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各具特色,读起来回味余长。
当你有了对诗词的研究,再去品读散曲,那么一定会让你在诗词曲的世界里感受文字的美妙的。
中国古典文学随着大语文时代的到来,越加浮上水面。读者熟知的中国传统文学体裁有诗有词、小说等,但是对散曲大伙相对陌生些。可能是因为散曲鲜少被选编到中小学语文教材里,所以读者们极少从孩童时就近距离接触散曲,因而对它了解得不多。
那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散曲。摆渡一段:
“散曲,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之一。和唐诗宋词同为一代之文学。又称为“乐府”或“今乐府”。由宋词俗化而来,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中国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后来随着散曲格律化和去市民化,失去了个性鲜明的鲜活市民文化血液,变得与宋词几乎无异,随之衰败,未能像唐诗宋词一样繁荣延续及后世。”这里也说明了为什么散曲没有繁荣延续及后世。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组成的一部分,它的影响依然巨大,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由浦江清先生编订的这本《元明散曲三百首》如“唐诗宋词三百首”一般,有着非凡的意义,可让读者、尤其是爱好散曲的读者来说,可以较为系统地通读主要散曲,而对散曲不熟悉的朋友,也能通过此书清晰地了解散曲。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先生致力于文史考证,治学严谨。从该书的序,也算是导读中就能看到后人对他的褒赞。浦江清先生的《元明散曲选》有三卷,分卷一元小令、卷二明小令、卷三套数,不过在《元明散曲三百首》中还编订了卷四补选元明散曲五十首。
在该书中,浦江清先生整理收集的散曲,按时代进行归分,选注元明时期各大曲家的代表作品,并为每位曲家做小传,让读者迅速了解曲家生平。继而呈现散曲原文,再增补注释,注释中讲解精僻,为读者决疑析难,且在注释中有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的说明更能让人信服,而且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按所选诸作,再深入探究。
书中附有浦江清先生《元明散曲选》的手迹,字迹清秀,圈点夹注,细致无比。这样的读本是学界泰斗凝聚的研究心得,对当今和后世的读者来说都是珍宝,清晰整理解读,让读者在书中读到散曲的率真自然,也感受到浦老的率直自然。
浦老选文倾向于古雅,元小令里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也是大众熟悉的少数散曲之一,但是我们总是将它和词混为一谈,如今看来,是我错了。这首小令里“枯藤老树昏鸦”,让人立马眼前浮现这情景,有点凄凉,曹明善的小令《庆东原·江头即事》里也写了“老树昏鸦”,异曲同工。写出了秋日的萧瑟,悲秋的情怀,这些曲唱出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元明散曲三百首》读后感(三):散曲之美
曲是继诗、词之后而兴起的一种重要文学体裁。文学体裁的兴盛都是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就像昆曲兴盛于明朝,继之以京剧一样,唐诗于唐代独领风骚,而词在宋代大行其道,而在元明之际,则有散曲。可是词为诗余,而曲为词余。尽管散曲读来清新可喜,却似乎不得国人偏爱,仿佛大家更津津乐道于唐诗与宋词,对于散曲却兴趣缺乏。在这部《元明散曲三百首》中,我们似乎能够一窥散曲风貌。
浦江清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素以学识渊博著称。他的兴趣广泛博采众长,对于中西方文学均有深厚的造诣,而曲学则是他更为擅长的领域。浦先生不仅懂散曲,也常常看剧、唱曲,并参与到创作中去,他曾是俞平伯创办的谷音社成员,在课堂上讲到古典戏曲,往往要唱上一段。这本《元明散曲三百首》是他1942至1943为西南联大曲选课编选的教材,并装订成线装手抄本,据浦汉明先生说:“父亲为付印而抄录的各类文学作品很多,如此装帧的却仅此一册,足见他对这一选本的珍爱。”开篇选取的就是浦江清先生的手迹《秋兴》,点评恳切,字迹清秀,令人心向往之。
这本选本中分为四卷,分别是元小令,明小令,套数,补选元明散曲五十首。其中元代小令一百九十二首,套数五套;明代小令五十一首,套数四套,既可看出元代散曲的繁盛,也能看出作者的偏好。选取的作者既有我们所熟悉的张可久、马致远、关汉卿、冯梦龙、雎景臣、张养浩、白朴等,也有一些不甚熟悉的作者如回族人阿里西瑛、蒙古人阿鲁威等,使人对于元明散曲有着更全面的印象。
在篇首作者《元代的散曲》中,对于小令与套数有着详尽的解释,单支常见的为小令,同一宫调的许多曲子成为一套名为套数,套数根据内容需要,可长可短,短的只有三支曲子,长的可达一二十支,从形式上看,散曲是形式更为灵活的艺术形式,内容也多是清新自然,鲜活生动,题材广泛。
在选取上,作者侧重于“真”与“雅”,以关汉卿为例,选取的多为相思题材,语句秀雅清丽,马致远的《秋兴》,读来字字珠玑齿颊留香,而作者的评点亦是简约精到,文采斐然,读评点亦有陶然之感,并可看出作者对于散曲之美的审美标准。对于关汉卿的散套评价是“衬字极少”,马致远的秋兴则是“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这也是作者对于中华新文学的期许,学贯中西的浦江清先生推重传统文化,却也重视新诗的写作,浦江清先生是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能够发展出新体韵文的期待,期待元明散曲能够在中华文化中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关于阅读这件小事儿
《元明散曲三百首》读后感(四):元明散曲真率自然的活力
上学的时候,《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都没少翻,可的确没怎么看过《元曲三百首》,同学们也大抵如此。在唐诗宋词的光芒之下,散曲的确容易被忽视。
但必须承认,《天净沙·秋思》用白描手法营造出的苍凉意境,给内心带来的触动,绝不亚于唐诗宋词中的佳作,关汉卿那句“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也成了同学之间日常打趣的高频词。
相对诗词而言,散曲贴近民众生活,语言口语化,少了些文绉绉的高雅辞藻和深奥用典,通俗易懂、更灵活自然,得了一股活泼劲儿,又保持了几分朴质古雅,不会过俗而无趣,拥有如野草般的顽强生命力,自有其不同于诗词的魅力。浦江清先生欣赏的正是散曲真率自然的特质。
浦江清曾在西南联大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中讲授过元明散曲,选注了元明时代散曲的一部分代表作,为每位曲家做了小传,并细心地为散曲作品做了校勘、注释、讲解。《元明散曲三百首》中包含了浦江清这份《元明散曲选》的讲义资料,并由编者增选了五十首作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简教授在《“古雅”与“真”的选择标准以及对新诗的期待——读浦江清先生的<元明散曲选>》中,分析了浦江清先生对元曲的理解和喜爱,认为浦先生对作品的选择,可以体现出他偏重“真”和“古雅”的审美标准,“显然,那些真率自然,既能白描,又具备古雅之原质的散曲作品,才是浦先生推崇的作品”。
浦江清先生赞赏王国维对文学作品的“古雅”和“真”的追求,他同样看重文学作品的“古雅”和“真”。他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把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原始、黄金和衰败三个阶段,认为原始时期真而率、黄金时期真而工,衰败时期工而不真,可见他对“真”的重视。
浦江清先生所选的作品,也的确是符合“古雅”和“真”的筛选标准的,古雅质朴,保持了民间语言的原质活力,通俗又不缺少美感,不过于雅也不过于俗。所以,闲来翻翻这本《元明散曲三百首》,很轻松享受。
书中所选元曲作品对感情的表达,非常生动自然,胜在真挚。
写思念之情,“信沉了鱼,书绝了雁,盼雕鞍万水千山”化用典故,俗而不烂,“寒雁儿呀呀的天外,怎生不捎带个字儿来”则更显出殷勤期盼之情和小儿女般的嗔怪,感情饱满。
写山野生活的闲情逸致,“山村小过活,老砚闲工课、疏篱外,玉梅三四朵”,心境恬淡平和,洒脱简朴,又有情致。
写景,“长天落霞,方池睡鸭,老树昏鸦。几句杜陵诗,一幅王维画”,白描手法,简单几句勾勒,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意境不绝。
写现实问题,“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同样从民众的角度,用贴近生活的事物来反馈深层次的问题,语言轻松浅白,又能抓住深刻问题,以小见大。
这本《元明散曲三百首》所选篇目,都是这样真率自然的好作品,适合陶冶性情、休闲阅读。
2020.08.14雾凇
《元明散曲三百首》读后感(五):一人有一人之诗文选
1952年,年仅53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他的许多著作,因为在他生前尚未定稿,故去后又赶上时代激荡,所以一直未能出版。近年来,浦江清先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稿》等终于得以陆续整理出版,这不仅是对浦江清先生的纪念,更有助于古代文学领域的学术发展。
去年,我曾细读过《中国文学史稿》,认为这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史。从成书上说,《中国文学史稿》首先是浦江清先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积廿载授课之功而成的讲稿,是为了教学目的而撰写的教材。但认真读完,从性质上说,则能体会到这套《中国文学史稿》实质上是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
最近,浦江清先生的又一本课堂授课教材被整理出来。与《中国文学史稿》的厚重相比,这本《元明散曲三百首》(蒙木编订,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主要内容是浦江清从元明时期三十三位曲家作品里选了二百五十余首,除了选曲,还为每位曲家做了小传,为每篇作品做了校勘和简要的注释,部分作品还有较为详细的讲解。据浦江清先生后人浦汉明所说,这本书“是浦江清先生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为西南联大下一学期的‘曲选’课编选的教材。后来装订成册,加上蓝色的封面封底和白色衬里,成为一册线装手抄本。(浦江清先生)为付印而抄录的各类文学作品很多,如此装帧的却仅此一册,足见他对这一选本的珍爱。”
把这本小册子定义为“选本”,其性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只是单纯上课使用的“选本”,那么性质应该归类为“教材”,而教材需要客观、全面、四平八稳;而如果是更具匠心的“选本”,则需要体现选家的文学旨趣、审美维度。二者不能简单等同。事实上,“选本”尽管可以作为现代大学课堂的授课材料,但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学史”概念形成之前,或者说近代之前,古人当然不会去写一部“文学史”,最多在一些学案、学术笔记、选本序言等涉及一点。所以,在古代,“诗文选”几乎成了体现编选者文学和美学意图的主要载体。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一部优秀的“选本”,不仅能够满足授课的需要,还应该延续古代“诗文选”的传统,达到实用性和选家个性两者的统一。
在国内,几乎每一个大学的古代文学老师手里都会有一些讲稿、作品选,倘若来自于教师的私人严选,得益于小班授课的特殊环境,这种讲稿、选本就能够被赋予个性,其中不一定有何种惊奇的观点,但往往最能体现教师的美学观念和文学观念。浦江清先生这本尘封五十年的作品一朝“解封”,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审美气息,个人趣味十分容易识别,体现了浦江清先生鲜明的美学趣味。
最明显的就是“古雅”的标准。这一点,本书由李简教授撰写的《序言》已经言之极深。所谓“古雅”,指的是不要太过俚俗,也不必刻意俚俗,仍然具有中国古典诗学脉络下的清、正、雅、醇等特色的作品。所以,承李简教授指出,浦江清舍弃了一般教材的对元曲所必选的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那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尽管人所共知,但显然并不符合浦江清“古雅”的标准。
但是,“古雅”并不意味着“文人气”,浦江清在选曲时,也体现了明显的对“文人气”的不够欣赏。所谓“文人气”,就是俚俗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刻意将元曲向“载道”去靠拢,或是过多使用文人化的语言。散曲是唱在口唇、演在手足的流行歌曲,在今天的昆曲等戏曲里仍然能够得见其流风余韵。所以,散曲比起已经雅化的诗、词,妙就妙在灵动活泼,语言通俗。那么,“古雅”的标准就不能突破这一点,突破了就过犹不及,就显得“文人化”,就等于杀死了散曲最本质的情调。
其实,“古雅”与“文人化”之间的界限很难把握,既要“古雅”,又要摒弃“文人化”,就要在矛盾之中寻找平衡。从《元明散曲三百首》的选曲来看,浦江清先生基本上实现了自己这一较为独特美学品味的展示。
而究其原因,现在来看除了浦江清先生的美学主张之外,应主要与他本人的个人兴趣有关。浦江清先生早年就因热爱听曲、精于唱曲而闻名,据说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散曲,还常常在大学课堂上亲自演唱。据《曲学大家北大授课 俞平伯主持谷音社》(《北京晚报》2017年6月8日)一文可知,1934年6月俞平伯与曲友浦江清、汪健君、陈盛可等人发起成立了“谷音社”,俞平伯为谷音社社长,吴梅任导师,“实际承担教曲重任者为曲师陈延甫”,这是一个清华大学的组织。谷音社在1937年因为日寇入侵而停止活动,但南渡的一些社员旋在西南联大重新开张,成立“昆明三大学昆曲研究会”,范围显然扩大了。而浦江清先生从谷音社到昆曲研究会,始终都是重要成员。
唱曲若此,听曲就不必说了,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里记录了许多听曲的事情。盖因当时能够上演且火爆的戏曲,许多都是民间创作与文人润色的产物,唱词既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雅化,又因为舞台和听众的需要而避免过多的文人化。想来,浦江清对元散曲的审美选择,与他对曲子的酷爱是分不开的。
一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授课笔记,被整理后竟然演变为私家选本,这种蜕变既有原作者的贡献,也可以称为时间的馈赠吧。同样属于时间馈赠的,是收录了《元明散曲三百首》的这套“名典名选”丛书的其他几本书籍,特别是李云程的《古文笔法百篇》、胡怀琛的《言文对照古文笔法百篇》、余诚的《古文释义》这三本,已经绝版多年,坊间十分罕见。关于古文的鉴赏和写作入门,如今人人熟知《古文观止》,而忽略了《古文观止》作为一个选本只能代表选家的个人审美趣味,这显然不利于读者审美视野的拓展。所以,再版的这三册古文选本及讲解,与《元明散曲三百首》一样,也能在实用之余,增加一些更具个性的鉴赏品味。
一代有一代之“诗文选”,着眼于时代的“诗文选”,主要价值在于实用;当时光流逝,这种实用性渐渐褪去,就会出现一人有一人之“诗文选”的现象,着眼于私人的“诗文选”,主要价值在于审美趣味。这种变迁,恰恰体现了文学史的一种魅力。
刊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