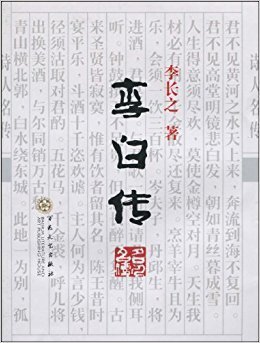《读诗的艺术》经典读后感有感
《读诗的艺术》是一本由[美] 哈罗德·布鲁姆 等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40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2010-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读,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很多观点和我理解的诗歌距离越来越远。书中的论述对象主要是英美诗歌,只是代表诗歌的一个方向,我还是亲近德语诗啊。
●有一些篇目不是很喜欢,虽然每篇选文之于作者年代流派都各有统领意义,但总的来说,我更喜欢赫伯特那篇《阿特拉斯》
●讲真,我读得很艰难……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涉猎的诗歌范围实在狭小,读来才这么费劲。书是本好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难得的还能读懂一点的书。#此为何梗,识得不识得?# 顺便传一个OCR的pdf。/s/1N1oYnVtlm7MA2uAB9a563g
●这本书对我而言如此乏味。只有第77页能读。其他也就是拉金和马克.斯特兰德本身是有趣的。去***英语世界!去***英语世界里的诗歌!
●如果要给天才取一个名字的话,那应该是Kenneth Burke,当时读英文版还没完全通,现在明白了很多细节,和伯克相比起来布鲁姆简直就是小儿科了。"行动–场景"比率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提喻,在批评中非常有效,不过伯克这一理论应该也是来自于施皮策的"戏剧比率",从行动场景比率引入上帝与善的古老论争,再回到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资产阶级对"主观"的强调,最后附着于爱与死(死亡与新身份的获得–资产阶级工商业发展的浪漫主义–个人身份感结构的转换)在意象上的非否定与非断裂:不同于语言学上的a或者b(或a不是b)意象使用时我们只能说a和b或a带有b(a-b)所以从意象角度讲,戒律不能被简单视为禁止,可能是潜在的挑动,比如"你不可以那样"可以被想象式地转化为"假如那样会怎样",济慈诗中的永生与死亡是彼此挂钩的。
本书能够让人:深刻地了解外国人是如何评价一个诗人,如何咬文嚼字,如何通过人类特有的激情来赋予诗歌生命的,详细地了解有关近代欧美诗人的生活八卦乃至性嗜好。在中文字海里找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词语与句式,找到许多睿智幽默的文学段子.......有助于我们今后阅读、写作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我们今后如何说一个好笑的笑话....
《读诗的艺术》读后感(二):读后感
好书一本,可算工具书,可重读。
而且关于诗,我还算幸运,小时候有过原初的诗的经验。想起初中很喜欢看一杂志好像就叫诗,很小的一本,很厚,特别破,被很多人翻过很多遍的样子,都是一些现代诗歌,那时候感觉很新,后来好像把图书馆所有能借到的都读了一遍,这样一来也到毕业了。
到了高中选择了理科,开始避免和文学的过度接触,仿佛想要看看世界另一面的样子,所谓理性的,纯粹的,判断的,逻辑的科学世界。现在想来,那段思考对我也很重要,可能真的是一种天生对平衡的追求,当感觉自身偏向某一边就会自动调整。那时候也蛮专注的,就想选修天文,解剖,自然等课,偏偏不去选什么音乐,陶艺,电影课。还假模假样看看什么霍金什么虫洞啥的,还在每周的电影放映夜和同学下国际象棋,在一切有关文艺的活动中力求出脱为一个纯粹理性思考者。虽然有些刻意,但是此番刻意也是自然随心的决定。
我觉得,诗和音乐都是真理性的,我不会说一幅画或者一部小说是智慧本身,但是诗和音乐总是带有一种别样的超脱和难以把握,这种空间和自由或许就是黑格尔说的不断进化的启发和认识。与此同时,我又莫名奇妙想要再读康德了。
《读诗的艺术》读后感(三):几个简单的读后感
1.写得好的诗人一旦关心诗歌批评,那他的诗歌批评的敏锐和洞察几乎一定高于批评家,不仅因为他对诗有更好的直觉,还因为愚蠢的学院教育没有伤害过他。这本批评集里最好的五篇批评是赫伯特讲阿特拉斯、威尔伯讲霍斯曼、奥登讲阿什伯利、沃尔科特讲拉金(我最喜欢的一篇)、希尼讲克莱尔。马克斯特兰德是比较水的。布鲁姆、伊格尔顿和另外一些以批评为业的作者,则很明显的不那么懂诗,起码不懂一个诗人真正是怎样写出好诗,怎样成为经常写出好诗的诗人。批评家的品位是二手的,他们更容易被虚张的“大师迹象”迷惑,而好诗人心里没有不可动摇的大师(除了自己),只有完成一首好诗的劳动和劳动收获的诗。
2.英语(英文)是一种低级的诗歌语言,又难听又难看,即使是蹩脚的汉语翻译,阅读体验居然都比原文令人愉快。象形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诗歌最珍贵的礼物,中国诗歌的灵魂也在于音形义的完美融合。可惜的是,汉语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疯狂地蹂躏与践踏,政治话语、翻译腔和冗赘的顺滑垃圾话,写作者们煞费苦心地经营浪费遗产的文学阿堵物。英语(英文)因为它乏味的客观性丢失了诗意,赢得了世界,中国要在失去世界的同时模仿它也失去诗意吗。在写诗方面,莎士比亚距离杜甫太远。英文诗歌天生的二维(没有象形)让它劣于汉诗,英文世界的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音韵在汉诗音律面前也低级得刺耳。中国诗人即使想认外来和尚,最好也不要选英语文学。即使认定了外来和尚,也一定要珍惜我们的象形。
3.不说一丁点废话的文章是难得的,而看起来没说一丁点废话一直有板有眼讲理论的文章很可能全是废话,比如开篇第一篇,还有勃克写济慈的那篇。理论家殴打诗歌,把诗歌打死了,他们就好研究了。王敖的序言写得挺不错,但正因为那是篇和诗歌关系不大的序言。
胡了了
2019.5.14
《读诗的艺术》读后感(四):如何分享诗的秘密
如何阅读现代诗,常常是普通读者的难题。在中国,由于有一个古典诗的传统,困难似乎就加倍了。人们更希望从诗中求得情感的慰藉,而不是知觉的惊异,而这却是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诗最主要的美学原则之一。
王敖的译文集《读诗的艺术》召唤的,也许首先是那些和他一样熟悉和喜爱欧美现代诗歌的读者,但它也为这种普通读者的困惑准备了钥匙。书中文章多数是关于欧美重要诗人的批评文字,有些出自学者手笔,如大名鼎鼎的诗歌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和海伦•文德勒,有的则属诗人的现身说法,如诺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对英国当代诗人菲利普•拉金的评论。它们无法充当“现代诗阅读鉴赏ABC”之类教程,但对阅读现代诗所需要的耐心、修养和“艺术”,却提供了一些远为生动的范例。
曾任美国桂冠诗人的理查德•威尔伯《围绕霍斯曼的一首诗》一文就是一个好例。这篇演讲对一首八行诗所作的精细入微而又引人入胜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地向我们演示了,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怎样使用技巧去获得对一首诗可靠的理解。一首诗的意义远不止于它的主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的音响、速度、词藻、文学典故和传统惯例,而理解这些都需要圆通的技巧。
威尔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一味地把责任都推在读者这一边,他进一步论证,这种圆通的技巧,尤其在用典的层面,也正是对诗人技艺的考验——读者固然不应把一首诗看作诗人对公众的直接发言,以“又好又流行”作为检验诗的标准也有失偏颇,但一个优秀的诗人在使用典故时,仍应努力达到因承有迹而化用无形。
不过,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做到圆通都诚非易事。就拿威尔伯的解读来说,他对这首诗中某一句的索解,哈罗德•布鲁姆就不同意,认为另有出典。两相对照,你会发现布鲁姆的推断也许更确切,也更圆通一些。布鲁姆是一个极佳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一个诗歌读者可以走多远。《读诗的艺术》中所收的他的同名文章,与其说是要告诉人们如何读诗,毋宁说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读者”的夫子自道。在他看来,读诗这门“艺术”的核心是评判诗歌的优劣,进而确认哪些作品属于伟大的诗歌。
小说家库切也是这样一位可敬的读者,此书选入他的一则长篇书评,对诗人布罗茨基在其诗学随笔中阐扬的某种语言形而上学观念表达了极其机敏的质疑,而他在这篇文章中显示出的睿智,从他对策兰、里尔克等大诗人的评论来看,至少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对诗歌的阅读。他的例子也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作为读者的信心:即使你不写诗,你仍然可能和诗人一样分享诗的秘密。
在当代诗人和读者的自我教育中,现代欧美诗歌批评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那些杰出的诗作,《读诗的艺术》佳文荟萃,就我阅读所及,堪称近年来这方面最具分量的一本书。它的翻译质量也保证了这一点,译文准确流畅,对其中引诗的翻译处理用心尤深。美国诗人哈特•克兰的组诗《航行》被哈罗德•布罗姆视为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向称难译,此书也专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译本,其间甘苦,大概也只有和译者一样的爱诗人才能约略体会吧。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0-11-6,发表时略有删节
《读诗的艺术》读后感(五):读诗
苏琦处借来的书,开始也并没有太高的期望,大概最近又有点蛮劲,所以拿来看了,整个过程是舒畅的,无比惬意,除了布鲁姆的头一篇和论阿什伯利的部分有点小滞涩,基本上是踩着音符愉悦地走下去的。
最近读的都是哲学和诗歌,大概都对于自己,都不是讨好的粗重玩意,匆匆扫过,有印象的少,没印象的多,但拾起散文来,就相信自己读书的感觉还依然生机勃勃。这是自古希腊哲学史以来,最适宜的一本。
关于当代诗和外国诗,一直是读者或者作者都头疼的事,想想自己虽然也写了许久,但总是觉得不得其门而入,要靠别人的评论才能读懂,不免让自负的读书者感到泄气——有时甚至看了评论还是感觉游离在某首诗外。而自己来说,不懂的东西总是显得怯生生的,甚至也影响了写的冲动和欲望。有时候甚至看看二十五六七生机勃勃乃至不朽的诗人,真不免汗颜。
印象深的是《在北大读诗》里臧棣第一篇对张枣的《边缘》的解读,记得当时自己先硬生生看了两遍而不明其意。但是看了臧棣的解读后真真觉得这首诗是好的,至少让自己明白了有些诗歌毕竟还是挑读者的。如果我们对于当代诗人不信任,或者认为对于艾略特的庞然大物本身给我们预设了障碍,但在这本书中,一首叶芝的诗清楚地告诉我们私人的典故是多么自私地抛弃了读者。
对于小说来说,越生涩艰僻,越庞然大物,反而地位越高,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因而声誉卓著,但这是建立在大部分小说都可以读下去的基础上的。相似的情景是;大家恨不得诗歌大都是《当你老了》《面朝大海》或者佛罗斯特和拉金的诗歌,当然你也可以造出荒原,但不要那么多,读读者愿意去智力探索,但不是每首都探索,这是专家干的事。
说到晦涩的诗歌大致不免几种,用典或者结构的颠覆,两者结合,或者作者自己也不明白要表达什么的狗屁。用典就解读出典,这是较易的,用典繁多就让人望而生畏,由其不在某种文化氛围中就不容易转出来。结构的繁复也很有趣,比如《边缘》或者王敖解读臧棣的《蝶恋花》,还有余怒的。结构的诗歌一旦讲破了,也就开然了。至于狗屁诗,我们到不必理它,有时候我们想那么这到底是一首狗屁诗还是一首好诗,作为一个纯读者来说,简单的办法是,读那些死人的诗,多个名气大的诗人肯定的死人的诗。典故多而结构复杂又长的诗歌,最是要了读者的命。然而作者来说,这样才能构建他的大厦或基石,所以这是矛盾的一对。
布鲁姆的读诗的艺术很有趣,细到词语的力量,但我想这是诗歌的长久祭奠,是后来诗歌散发的蕴力,根本的还是在用典或者写作者对于前辈诗中的领悟和贯彻。时间、毁灭、永恒,这种感觉的冲击的延续和变化。后来者借前者的诗来发力,当然有发好发坏和相当的。诗歌的生命在他的河流中散发出光的波链,而非孤独的星一盏。但如艾略特的理论全靠这些但是有点意思,试问一个作者能全面把握这条宽阔的河流吗?可能作者也是自以为的把握了其中的部分主流和力量。而在河底河外说不定还有不同的传统。说实话,布鲁姆所评论的哈兰的这首诗没看出多大意思,我承认我不懂。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也是明悟了的,虽然忘记了在哪看过好多解读,但这首只要想出它的情景就能衍生出丰富的画面和意义外延,所以说索解到是研究者而非读者干的事了。真或者美,无关紧要。
霍斯曼的这首到是有趣,这首既有典故,又不靠典故,我觉得没有典故我也能完全理解这首诗(因为短?),但有了典故似乎更有趣,但也没增加太多的诗歌力量,但能把前人挖出来比一比还是很有趣的,就像莎士比亚的那首夏日女人和斯宾塞的沙滩上,两首对比是多么有趣。
阿特拉斯能否成为被确立为一个经典的哲学意象,我想作者本人就开了一个好头,从神话的内涵和趣味性来看,肯定将来会有一个类似西西弗斯这样的故事出现,或者戏剧也不错,普罗米修斯能侃侃而谈,阿特拉斯到不能大放厥词吗?找几个听众就是个不错的等待戈多,或者椅子。这需要一个新的加缪或者尤涅斯库来完成。西西弗斯不是到加缪手中才大放异彩吗?这狡诈的西西弗斯在加缪手中显出孤独而深度的乐观。显出无与伦比的哲学深度和存在感。
伊格尔顿所写的艾略特一点也没印象了。或者对于研究艾略特本人到是用处更大些。
奥登是令人喜欢的,明晰而意义深刻的诗,晦涩而繁复的诗,俏皮话的散文,见解深刻而不偏颇的独到眼光,让人又完全的信任感。奥登是那种透彻的人,他不会犯下类似庞德的错误,而且对于生活和艺术都有着透彻和完善的世界观的人。切斯特顿并不了解,就当看了看奥登是如何做这盘菜,而并不管他的口味吧,但我记得读以上两篇的时候是相当轻松而愉悦的,至于内容却完全记不起来了。
奥登的名人轻体诗薄薄的一本,看的一点没头绪,英语也稍看一点,但还是没看明白,有人说桑克翻译的太烂了。哈哈。轻体诗是什么?或者在诗歌没有典故和技巧之时,他就是纯彻的交谈,是对于自然的领悟。甚至我们能否说,莎士比亚是轻体诗?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喜欢我自以为是的轻体诗,不长,有趣,有智力,有深度,不用却在诗歌外寻找典故,它考验的是对文字的感觉度、深度而非记忆力。但有时候看看自己回想自己,却全然不是这一类。而且这一类貌似总是冒着被容易看懂然后丢弃一旁的危险。
库切和布罗茨基两者都不够了解,但毕竟该找到《小于一》来看看。内容现在也想不来了。
德勒兹的评价到是让我窥视到他的民主性,至于美国的碎片的外部链接到是个很有趣的理论。德勒兹对于碎片的着迷是否过度的了?我觉得这要是到惠特曼和海明威的耳朵里肯定不屑一顾,摆摆手粗鲁地推开了。
在晦涩的诗歌之外,是否有另一条河流,是否能够产生伟大的诗。这是毋庸置疑的,许多诗歌,许多短的诗歌,许多明晰而含义隽永的诗是存在的。中国的诗歌其实积淀成文化内涵的不也是那些明白的诗吗?拉金是个有趣的人,被沃尔科特更是写的活灵活现,这个中产中产阶级的老男人,处处透露出机智、玩世不恭和丝丝的悲天悯人。拉金活的轻松,相比佛罗斯特可能更具常态性,他对于名声或现实都有着放松的心态,也没有说非要处于山尖的欲望和必要。
约翰克莱尔怎么看怎么让人想起荷尔德林,当然,中国还有海子拿来可以牵强地比一下。克莱尔的前期和后期显出差别来,前期是一个比梭罗更人性的兰波,后期是一个类似荷尔德林的彻悟。希尼更喜欢前者,文德勒把后者也提起来。艺术的道路上不乏克莱尔这样的人,他们仿佛不懂得世俗的圈套,一撞就把自己撞飞了,他们任性、自私,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而难以处落在乱世糟糟中,这些倒霉蛋们在鲁迅或者陀氏的眼中估计就是个玩笑。然而他们是纯粹的,由其在诗歌这一行上,短暂的深入的研究,能让他们产生飞翔的本领。哲学这玩意适合那些命运要长久一些的人。约翰克莱尔无疑还会被更多地人的颂扬,就像人们对兰波的念念不忘。同样,想起海子,我也有这种感觉。
关于阿什伯利,没什么好说的,奥登的不信任?貌似没太看出来,文德勒的解读到是有趣而繁琐的多。阿什伯利似乎进入了一种诗歌的游戏中,摆置而成的意义。
后面关于奥登和奥威尔的争论相当有趣,我觉得奥登第一次在奥威尔这儿吃了鳖,一口大大的浓痰,一个佛罗斯特所谓的不应该的出丑。在奥登写西班牙人时,无论如何他的眼光肯定比不上奥威尔深刻——这1984的大师。奥登既有些真诚,又有些委屈,但第一次可能让奥登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一个轻率的错误。或许他不去谈论战争或者严肃的问题,不会引起奥威尔这样的大师的嫉恨的,就像民国时,如果不是限于当时社会那样的状况,鲁迅也不会对胡林顾梁他们有那么的尖刻。奥登后来妥协改了自己的诗,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不容易,同时,这并不影响我对于奥登和奥维尔的欣赏,反而更多了。印象里奥登有首诗是不让选的,不知道是不是这首,查了查,没查到。
斯特兰德的是几个小寓言,读的倒有趣。
最后奥登关于希腊的叙述,由于最近啃完柏拉图的缘故,但有种平等亲切的谈话的意味。古希腊能成为欧洲的源泉,间隔了那么久,我觉得外国的典故和文化成为中国的倒也不难,关键是有多大的群体去接受这种文化。当前诗歌的策略,是什么?致力清晰而明白、寓意深刻的,中外都不乏这样的,我觉得这是相当好的一途,韩东的诗歌有些这样的意味。或者构造神奇的结构,不靠典故和传统,边缘是这样一类。或者化用典故,外国的现在有了,貌似从现代诗开源就有,用好了吗?但中国的传统典故呢,似乎当代从来没有用好过,在海子那里吐露出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