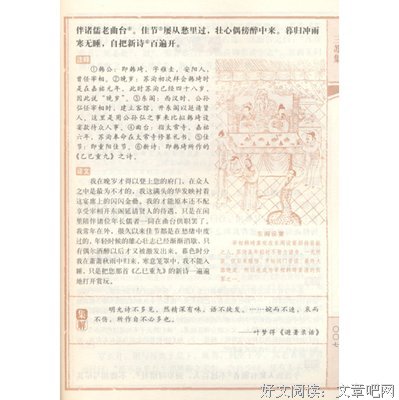《“五四”九十周年祭》的读后感大全
《“五四”九十周年祭》是一本由杨念群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四”九十周年祭》精选点评:
●社会角度观察“观念”的历史。
●硕论资料。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指出学界多从思想史进路研究五四运动的缺陷在于缩压了其意义空间,无形中使此一运动部分失色,故而需要从社会史这一进路对其进行研究,以彰其全貌。其次,作者分别剖析了“国家”与“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在近代史上的悲欢离合,最后导出以毛和新民学会为首的缺乏社会资本的边缘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全书尤其最后一章颇有启发,能用西方前沿理论(如哈贝马斯和布迪厄之著作)来分析五四让人眼前一亮,不过感觉仍可进一步扩充内容,莫非是为赶上九十周年庆而匆忙完稿所致。
●既然肯定说不清楚也说不了,干脆就别说
●不过尔尔
●较为细致的分析,包括社会思潮和前后运动的结合,对经过大陆“五四”历史教育的人来说又是一种较为丰满的重构。
●好吧,其实我觉得蛮奇怪的。。。
●没有干货。
《“五四”九十周年祭》读后感(一):这样的书才是时代的骄子
RT,
作者君是个聪明人,谁不知道54是当今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背靠皇上狠批痛批草民和他们的祖先,那是稳赢的是不是啊。
还有原来“苏化”不是西化啊,俄国19世纪以来不算“西方”,那算东方?玛嗯什么的呢?也不算西化?潜台词还是承认自己对现状有点不好意思吧。
《“五四”九十周年祭》读后感(二):“国家-文化-社会”的两个问题
社会史,更具体地说“社会改造”运动史,确实是补足五四作为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最重要面向。杨先生这点说得非常清楚。是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本书进行到三、四部分,把五四整个运动的路径“归约”(暂且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成“国家-文化-社会”的模式,似乎是有很大问题的。看完书,目前能想到的至少有两个问题:
2.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杨先生的基本论述是:五四的政治论争渐次被化约为文化问题,即以文化衡量政治。并认为五四人的立场——一面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姿态否定过往政治,一面又要重构中华文化以求新的政治——是矛盾的。但是,即便事情真是这样(批判旧传统、重构新文化),文化归约路线怎么就矛盾了呢?在“冲击-反应”的模式里,文化归约路线既坚持中国必须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一员加入政治游戏,又希望从文化资源中寻找新政治。如果是这样,那么九十年后的五四新鲜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有两个核心问题:1. 文化是否小于政治(小于也就是杨先生说的“归约”的意思);2.讨论文化的政治前提是什么?
简单说,陈独秀等《新青年》人之不谈政治,是不承认民初政治的政治单位和政治构想,亦即不认为中国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获得救赎。这比起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内部的“冲击-反应”模式,革命得多。所以,在这里文化决定/影响政治,并非重点。或者说,文化-政治的“矛盾”已经解决了。文化,其实不能被归约成归约政治的概念;新文化,其实一直与政治相关联。
《“五四”九十周年祭》读后感(三):再识“五四”
写就一本学术著作从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大约是醉心学术至一定境界的人的共识。就一般读者而言,若剔除学术著作中复杂的论据和繁琐的论证过程,仅观其结论,通常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觉得作者所阐述的虽则眼花缭乱,但不过是些“日常之理”,属于为学者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二是觉得作者所说的虽则奇思妙想,却是些“与己无关”之事,属于为学者的“自言自语”。于是,无论怎么看,学术著作于普通读者,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无聊之作,阅读这些著作只是虚费脑力,还不如多看些于己密切相关的业务书籍,或厚黑、心理等教人“练达人情”之书。
然而我要说,读学术书,似无现实裨益,却叫人对诸如“我是谁、我在哪里、我的来路与前程……”等此类玄学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为一个人在世之生存“奠基”。读历史类的学术著作是一条很好的途径,通过网上某场讲座知晓了杨念群其人,感兴趣的原因极简单,只因此人为民国奇士杨度曾孙,于是一时兴起花了5天时间,断断续续将其所著《“五四”九十周年祭》(以下简称《“五四”》一书)看完,虽然阅读过程也不乏跳读、浏览等各种不用心,但也自我宽慰,对我这等非历史专业人士而言,此等著作获其皮毛亦当有益。阅读期间,顺便听了杨先生的一场题为《从思想史、感觉史到隐喻史》的讲座录音,对杨先生在《“五四”》一书的写作脉络也有了更为深切的把握。
论及“五四”,着眼点大抵离不开“新文化”三字。受传统教科书教化,“新文化运动”几成“五四”同义词,其好处是考试有了标准答案;坏处却是模糊了“五四”本来具有的多面性,使“五四”成为一段悬浮于其他历史之上的真空。杨念群教授正是从思想史角度入手,以“中心-边缘”的更替作为理论阐述的框架,细细分析了“五四”运动内部隐含的话题转换和代际更迭。
其书读完,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问题,有了自己新的看法,虽非专业研究者,但多些观点,总可对看清事实多些帮助。
《“五四”九十周年祭》读后感(四):思想的盛宴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朦胧的想法,那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境况跟1919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多些像鲁迅一样的思想战士。可是想法的产生更多的是由感而发,况且是在对“五四”粗浅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系统的思考和逻辑的论证。
恰逢“五四”90周年,看了这本杨念群先生写的《“五四”九十周年祭》,这本书不能说全然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至少让我对“五四”有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认识,为今后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建立了一个指导框架。另外书中阐述的一些问题、现象和观点对当代中国确有借鉴之处,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和反思。
第一遍读,由于书中很多概念、观点要么是第一次接触,要么是虽然以前听说过,但从未真正理解,所以是边读边琢磨,往往是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缺乏作者整体思路的把握,感觉有些杂乱。所幸细枝末节的消化为第二遍理解全书的整体思路打下了基础。
书中的具体内容不想多说,在此我只想谈两点跟当代中国相关的论题或者是对今人颇有启发的论断。
二.对于民主、国家和社会的启发性解读
面对清末民初的危局,书中提到的很多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都在探索中国社会的前进道路,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观点,有些虽不合时宜,但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或对后来人有所启示。
例如,1.4节中就这样写道:在“社会”变成了“五四”讨论主题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社会革命”必须依靠介入日常生活的崭新行动方略才能最终完成。将“社会革命”设想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过程,一个“全体之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差别不仅是目的上的差别,而且是方法上的差别;政治革命是少数政党精英操控下的行动,“社会革命”则是大多数人的革命即平民革命。
那日,我坐在北京三味书屋通往二层茶室楼梯的木地板上听着一位学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讲座,当中提及他首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最后是一位个人主义者,然后便详细阐述为什么是三个“者”的原因,碍于理论知识的不足,直到从书屋出来亦未领悟内中深意。今日读罢此书,虽谈不上豁然开朗,但也算得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五四”九十周年祭》读后感(五):“为什么用祭,因为我觉得五四的精神已经死了”
(导)每年的这个时候,无数的人开始借“五四”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90年来,对于“五四”的各种解释,已经扑朔迷离。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关于“五四”又有多少种误读?在历史学家杨念群看来,认识“五四”首先要从破除“五四八股”开始。
2009年5月8日,《晨报周刊》对话湖南籍学者杨念群。
(主)“为什么用祭,因为我觉得五四的精神已经死了”
文|袁复生
“今年出版的‘五四’著作,也许只有我这本值得一读。”至于其他关于“五四”的书,大多无非就是边角余料,名人逸事,皆无足观。听到杨念群毫不犹豫地说出的这句话,我心里第一涌现的,就是他的先人杨度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作为杨度的曾孙,他却解读出了曾祖“遮掩其(湖南)缺乏文化气息所带来的历史隐痛”。曾写过《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他,则认为很多的“区域文化”,其实就是地方主义,没什么意思。
他父亲和祖父,都是学化工的,因为杨度曾提倡“科学救国”。虽然他“一直不太想谈家族的,觉得这都是虚构出来”,但到了他这里,自己成了“文科脑,理科不行”。杨度对于他,也许“潜移默化”,除了学术,可能还有性格基因。
()现在很多人谈爱国,什么爱国,就是粗口吧,就是一种暴力,就是《中国不高兴》
晨报周刊:好像上海有媒体采访你时,用的标题是“五四是一个终结”,“终结”这个词汇是否能准确地表达你的观点吗?
杨念群:为什么用祭,因为祭是一个非常悲观悲剧的东西。我就很明确说,五四的精神已经死了,从各方面死了,不存在了。五四之后已经90年了,但我们在其精神上,没有任何的进展,五四本身是辉煌的,但五四之后所有的成为悲剧。一代人的梦想,彻底地被打碎了,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鸡蛋碰石头,我们永远站在鸡蛋的那一边。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只会谈消费,哪有什么学生能真正地以天下为己任,对政治感兴趣,去参与政治,承担起国家的使命感,没有了。现在很多人谈爱国,什么爱国,就是粗口吧,就是一种暴力,就是《中国不高兴》,那就是一帮想赚钱的人在破口大骂。复生,或者凤凰涅磐,不知何年何月。
晨报周刊:我们之前心里总有一个等号,五四=科学+民主,但你在新作里,似乎并不是按这个简单的公式来归纳的?
杨念群:重新归纳的话,“五四”最重要的精神价值,第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第二是自由,对个人价值的崇尚。第三是对社会的关注,对基层民众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这实际上是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层面,再到对更广大的社会进行改造的层面。
晨报周刊: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在大众之间形成了共识。但“费小姐”从上世纪80年代被林毓生等学者提出来并放置首要的位置之后,但一直在大众脑海中还是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
杨念群:原因当然有很多,我觉得个人的表达或实践跟民主其实密切相关的。这个自由一定要有一个平台的,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民主进程。民主是为自由创造条件的基本平台和保障,只有这个进程加快,“费小姐”才会浮上台面。
()文革极端反传统,但它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政治逻辑的结果,这和“五四”有鲜明的区别
晨报周刊:看了你列举的那些“五四八股”,感觉都是绝对化的说法。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归纳、总结,但这和符号化、标签化之间,怎么平衡?
晨报周刊:谈到文革,就不得不谈毛推动的上山下乡,包括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你说毛是想打通知识和社会的流动性关系,这与毛在五四时期的经历和思想有关系吗?
杨念群:当然有关系,追溯得比较远了,谈到了湖湘的传统,其中有一点就是践履,他们认为文化首先要行动,是否有用。为什么湖湘出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特别注重效果。康梁和江浙也不行,都是书呆子在耍。此外,行动的平台,必须在社会层面,你要与社会处于接近状态,才能抓住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问题。但他为什么很失败呢,因为他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一下子把几百万的知识青年放到农村,用这个反哺农村,农村实用的东西又和知识结合,但我觉得这是对知识一种特别幼稚的理解,以为混两年就好,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在这点,我觉得毛恰恰没什么践履性,没实际的效果,他原来在政治上的东西很有效果,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就太一厢情愿了。我理解他最初的思维点,他想重新建立起城乡的人才循环,虽然他这种做法很荒唐。
()湖南不是靠文化起家的,不是靠一个根深蒂固或者辉煌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的,它的人才在近代以政治层面出现
这条路呢,很多研究者就觉得比较陈旧,是党史的路子。但从实际来看,这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方向,尽管从得失来看,我不一定完全肯定它就是对,别人也许会说你这是抬轿子,这种政治叙述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也不能故意回避官方叙事,完全接受台湾那种自由主义叙事。
晨报周刊:谈到湖南和近代的湖湘文化,很多人都会谈到你曾祖杨度,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但你的分析,却让人暗自心惊,你说“杨度潜意识里仍认同于‘湖南’是文化贫乏之地的传统概念,它不过只是在意识表层以湖南作为‘政治单位’的发达兴盛来遮掩其缺乏文化气息所带来的历史隐痛”,那是不是说,湖湘文化其实挺“没文化”的?
现在搞湖湘文化,都要在找它的源头,从宋代啊,明代啊,弄出一堆人来,搞出一个线索来。但说白了,当时的湖南,就是一个文化沙漠吧,从整体的出文人学者的几率是非常小,数量和密度也非常小。它不是靠文化起家的,不是靠一个根深蒂固或者辉煌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的,它的人才在近代以政治层面出现,它有特定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条件,当然也并不是说湖南人不好或怎么样,它的特色就反映在这方面,它不是出学术大家的地方,但确实是出政治人才的地方。我们说的群体,也是近代传统,近代传统和古代传统没关系,各种机遇和资源被利用起来了,有些人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对新一代的培养又有影响。
[配稿]
()“五四”八股图
文|杨念群
八股一:“五四”被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文革”中神像被砸,老师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祸。
我的回答是:历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唯成分论”、“血统论”,岂不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兴国学的一个理由,遗老遗少纷纷借攻“五四”出气,以批鲁迅为时髦,遍地以“返祖现象”为荣,奇观妙境一时无两。
我的回答是:堕落到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八股四:“五四”是“个人解放”的尝试,如果“个人”得不到自由,就说明“五四”完全失败,毫无意义。
我的回答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骨子里的东西;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但仍以为,“个人”自由学的像不像确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五四”唯一的价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是学术积累的大成,却与政治无关。
我的回答是:这是故意躲避意识形态解释的借口,情有可原却于理不合,偏离了历史的本相。学术文艺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
以上是我今年“五四”赶集的联络图,凡欲知我罪我者,请凭此图。
图说: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杨念群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定价:18.00元
杨念群,湖南人,长期从事清史研究,却有浓厚的“五四”情结,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等,兼任《新史学》丛刊学术召集人。 供图|杨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