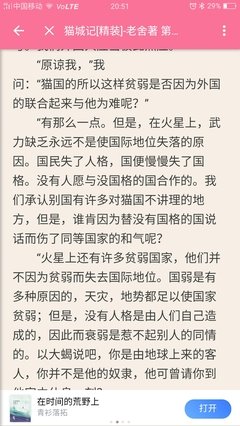《噩梦巷》读后感摘抄
《噩梦巷》是一本由[美]威廉·林赛·格雷沙姆著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噩梦巷》精选点评:
●作者像是边喝酒边写出这样的文字,处处散落着痛苦和绝望,无论什么时间点都没有脱离出童年和马戏团,所有的故事都是童年所得与马戏团之中发生的一切的重演,所以说,在巷道中无论奔跑多久,都不过是大雨击打在身上之前尽力所做的逃离。
●翻译差
●用塔罗牌做章节名很独特。塔罗牌的解释,心理咨询,梦境的各种意向解读,混在一起读得很有意思。斯坦其实一直没有逃出来,他一直在噩梦巷里,不过不再清醒了。
●关于冷读术的黑色讽刺故事,时不时让我想起《超感警探》(我爱这剧)和《别对我说谎》。
●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斯坦,莫莉的结局还好就好。
●人来到世上,不过是盲目摸索的虫蚁。他知道饥渴的滋味,他害怕噪声,害怕坠落。他的一生都在逃离——逃离饥渴,逃离命运的雷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呼啸的时间中坠落,坠落,落向黑暗的深渊……
●结局让我悚然。
●这部小说实在是太疯狂了,令人头昏脑涨,作者没有往死里摁可怜的莫莉,她终究有了一个好下场;但是看完可恶的斯坦的跌宕的一生,却不免怜悯起他了。这本小说的疯言疯语里有着对于人性透彻的理解——恐惧是支配、控制他人的要诀。不得不说,掌握人性、学会读心是多么可怕。但愿每个人都能从噩梦巷里出来,找到光
●学习了些有关塔罗牌的知识
●因为作者是狮子座所以带着好感读的
《噩梦巷》读后感(一):人生也只是一条巷子
读完之后我一直在想,男主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田地。他聪颖,能设计出那么精巧的蒙骗手段绝不简单;他有野心,不甘于呆在马戏团;他又英俊潇洒巧舌如簧。实话说,拥有了这些特质的人,想要成功实在是很简单的事呀。
作者把一切归结于他的童年,怨恨父亲,倾慕母亲。似乎从一开始他的命运就写好了。他只是一步一步在完成自己的“使命”。
窥见人性规律的他,开始蔑视人性。出人头地的念头占据着他的内心,他开始暴躁,开始想要更多。骗局越来越大,他越来越不满足。
恰逢其时,他遇到了他的“知己”。一个披着“心理医生”外衣的美女骗子。他俩合伙干了所谓的最后一票。当然,这票失手了,男主的所有积蓄也被女骗子骗走。
站在人生的开端时,男主信誓旦旦绝对不会成为野人,然而在多年苦心经营之后,他不偏不倚地成为了他最不想成为的人,甚至泯灭了所有的自尊人性。这真是天大的讽刺。男主最开始的设定,致使他所有的选择都可预见。正如他所言,“从他的脸上,我可以知道他的一切信息”。人生在这儿,变成了一条巷子,从起点,就可预见终点。
:故事悲观,然而事实的舞台指不定更为悲观。私以为,相比于骗局被破,坠入深渊,男主功成名就,一生繁荣才有可能发生。毕竟,以他的设定,骗局成功才是意料之中。
《噩梦巷》读后感(二):逃不开的宿命
对这本书的背景什么的了解不多,只说自己的理解。
有意思,就连首尾呼应这样的老梗用在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可能是对斯坦的一生描写的太过生动形象,从父母离婚离家出走的少年,到在戏团做事的青年,再到无限风光的通灵牧师,最后竟然落得开头自己可怜的那个“怪物”。
斯坦很可怜,可恨吗?我不是当事人,没有资格评判。但是我很喜欢斯坦。他聪明至极,高大帅气,他有自己的追求,摆脱了家庭去追梦,可是从哪里出了岔子呢?是吉娜的勾引。彼时的斯坦真的很纯粹,无论是外表还是心理,喜欢就想要。可是他得到了那个本子,人生轨迹从此拐弯。拐弯也不一定不是同一个终点,每个人人这一辈子也只活这一次,尝试而已。
斯坦做错了,他不该选择莫莉,生病以后也不该去选择莉莉丝。这两位女性一个极端弱势一个极端强势,只有吉娜那样的女人,才是真正适合斯坦的,她可以劝得动斯坦,又不至于欺骗斯坦。不过斯坦也配不上她。除了莉莉丝,这才是个真正的巫师,心肠是顶级的毒。
我的阅读理解太差,抓不住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应该是对现实的批判?其实只是讲述斯坦的一生也好呀,不一定需要多深刻的意义,只要自己理解到点什么就好了。
“这里没什么好害怕的。他一生都在这里,在暗巷里奔跑,无所谓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样的,不过是一条小巷,一点光明。”
嗨,好像我们的人生。
《噩梦巷》读后感(三):愚者的丧失
世界以它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自己,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圈。
这条蛇头尾相接,开始了另一个循环。
斯坦小时候经常做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沿着一条暗巷跑啊跑,两侧无人的建筑阴森可怕。巷子尽头有光,但身后有什么在紧跟着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接着,他醒了,浑身颤抖,最后也没有抵达那道光。
这条噩梦巷,成了斯坦命运的束缚。
在很多年后,斯坦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和小伎俩,收获了大批信徒,只差一点就能抵达那道光。
然后他又亲手把它灭掉。
第一张牌,愚者,指的是那个怪人。
但同时也是他的命运。
他出生在一个混蛋家庭,亲眼看着老妈和另一个男人,在他们的“秘密基地”里鬼混。老爸是个暴力狂,亲手打死了斯坦最爱的狗狗,吉普。
斯坦既恨妈妈,又恨爸爸。
但是斯坦同时也非常深爱妈妈。
他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不把他也带走。
就像莉莉丝分析的那样,斯坦有弑父的欲望,也有和母亲交媾的欲望。
在月亮牌里,他完成了对父亲的复仇。
他告诉父亲,自己还是走了神学的路,但不是他期待的那样,而是他自创的天堂来信派。
他告诉父亲,他听见了吉普的呼喊。他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他要把地狱的仇恨带回来,折磨垂垂老矣的父亲。
至于欲望,无论是吉娜,莫莉,还是莉莉丝,一旦对上女人,斯坦似乎总是吃亏。
看到斯坦把储蓄都交给莉莉丝的时候,我气得想摇他肩膀,叫他清醒一点。
即使他评估过莉莉丝的为人和智商,对他的骗局有利,把全部钱都交给她的这个行为,还是有点上头。
事实上他不爱莫莉,不爱吉娜,更没有爱上莉莉丝。
他的心里只有自己,为了实现目的,什么都可以付出。
那种极其强大的自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的理智,把他推上了命运之轮。
二十二张牌,二十二种命运,谁都无法避免相同的阴暗面。
《噩梦巷》读后感(四):代 序
文/尼克·托齐斯
读过这篇序言的人中,可能有不少人已经读过《噩梦巷》了。但是,我希望没读过的人也来体验一下这部杰出的小说。我非常羡慕后一类人,而且为免剧透,我也不会讲太多细节。从头读到尾,情节会越来越妙,越来越奇。不过,借用埃兹拉·庞德的一句话:“蜻蜓点水总无害处。”
本书初版于1946年,成书于1938年末至1939年初,是威廉·林赛·格雷沙姆在瓦伦西亚创作的。当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结束,他志愿为之战斗的共和国一方落败,而他正在等待归国。闲来无事,他就跟一个叫约瑟夫·丹尼尔·哈利戴的人喝酒聊天,结果对方讲了一个把他吓坏了的故事:当地有一个四处游荡的酒鬼,这人很邪门,只要给他酒喝,让他把鸡头和蛇头生咬下来,他也干。格雷沙姆当时才29岁。他后来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邪门酒鬼的故事纠缠着我。最后,为了摆脱它,我不得不把它写成一部小说。大概情节就是这样。它给读者带来的惊吓,似乎毫不亚于当年我听到时受到的惊吓。”
根据他的自述,从西班牙归国前夕,格雷沙姆的状态就已经不太好了。他遁入精神分析之中,而他为了摆脱内心的恶魔,还试过许多其他的方法。
在创作《噩梦巷》期间,格雷沙姆的兴趣从精神分析转向塔罗牌,从弗洛伊德转向写作期间接触到的俄国神秘主义者P.D.邬斯宾斯基(1878—1947)。
要是格雷沙姆早点知道弗洛伊德1921年9月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中央委员会大会上提交的论文,那该有多好啊!弗洛伊德在文中称:“单纯摒弃所谓的‘神秘事实’(occultfacts)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我们已知的动物和人类心理力量之外,它们似乎是精神力量的真实存在的支柱,它们揭示了我们迄今为止还不相信的心理官能。”在那个时候,弗洛伊德与邬斯宾斯基就可能已经在格雷沙姆的“噩梦巷”中并肩而行了。
本书是用塔罗牌串联起来的。一套塔罗牌由22张王牌(其中21张有数字)和56张小牌组成(分为四种花色:权杖、圣杯、剑、金币)。塔罗牌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一直用于赌博和占卜。占卜时主要用王牌,也叫大阿卡那牌,《噩梦巷》的各章标题便来源于此。第一张王牌是不标数字的“愚者”,最后一张是“世界”。格雷沙姆开篇题为“愚者”,但之后就没有严格按照牌序进行,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倒吊人”。
《噩梦巷》中既有犀利的心理分析元素,也有许多在作者和书中角色看来无异于骗人把戏的装神弄鬼,塔罗牌则穿插其间,奇妙地给出开示和预言。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虽然在创作《噩梦巷》期间,格雷沙姆正接受心理治疗,但他却描写了一位文学史上最邪恶的心理分析学家,从名字里就能看出来:莉莉丝·李特尔。
他后来说,六年的心理治疗既挽救了他,又辜负了他。“我当时状况就不太好,神经症留下了后遗症。我做了多年的心理分析和编辑工作,在小屋子里见过无数小孩子,最后还是靠酒精才把焦虑压了下去。”他说:“我发现酒不能断;我已经成为一个生理上的酒精成瘾者了。酗酒到了这个程度,弗洛伊德也无能为力。”
醉酒的人写下的东西没什么阅读的价值,但是《噩梦巷》中酒醉狂欢的痕迹真可谓无所不在。在这部小说里,酒精的存在感太强了,几乎要到书里开口说话了——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样。谵妄就像内心里的蛇一样,刺痛着作者,也啃噬着文字。威廉·华兹华斯有一句格言,诗歌是“宁静中拾起的情感”;而格雷沙姆则将自己的小说称为“种种恐惧”。
当然了,早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金银岛》(1883)中第一次写下这种意义上的“种种恐惧”之前,这个词就在酒鬼和烟鬼的口中传开了,至今依然。
格雷沙姆的语言是出类拔萃的。冷峻,阴郁,钢铁一般的文风臻于完美,对话和内心独白中的俚语也是同样。不动声色,自然而准确。
小说面世后不久,《纽约时报》书评版里对他有过一段简介:“格雷沙姆感兴趣的是隐秘的人物,他们的诡计和隐语在作者笔下信手拈来。有一天,一位莱因哈特出版公司的高管说过,普通的守法公民读到格雷沙姆的书一定会被吓坏的。”
“怪人”(geek,词源是geck,意思是傻瓜或头脑简单的人,至少见于16世纪初至19世纪)这个词原本不常见,现在主要指的是在巡回戏团里生咬鸡头或蛇头的“野蛮人”;是因格雷沙姆的《噩梦巷》闻名才为大众所知的。1947年,流行音乐组合纳京高三人组(Nat“King”ColeTrio)推出了一张唱片,题目就叫“怪人”。
“妥妥的,跟铅管似的”(Lead-pipecinch)是cinch这个词的“升级版”,意思是板上钉钉的事,用法可追溯至19世纪,之后一段时间也颇流行。纳尔逊·艾格林1949年的小说《金臂人》(TheManwiththeGoldenArm)和1949年《纽约时报》的一篇金融报告中都用到了这个词。
在《噩梦巷》中,格雷沙姆似乎还首创了一些生动的俚语。表示一种节目的geek或许是其中之一。据目前发现,最早在该意义上使用geek一词的,是在1946年8月31日Billboard巡回戏团板块的一份招聘广告上,当时《噩梦巷》已经出版了。广告上写着“不含怪人或女性演员表演”,发布方是“霍华德兄弟戏团”。(Billboard巡回戏团板块中,涉及“怪人”的招聘广告至少延续到1960年。1957年6月17日,约翰联合戏团发布了一份广告,言辞很直接:“诚聘怪人。要求懂蛇性。”)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冷读”(coldreading)第一次见诸正规出版物是在《噩梦巷》;令人难忘的“鬼骗子”(spookracket)也是一样。(我们一见到这些俚语就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格雷沙姆从来不会费力去专门解释。)
不久,朱利安·J.普利斯高尔就在1946年出了一本小说,题目叫《死人不会说话》(TheDeadDoNotTalk),里面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了这两个短语。《噩梦巷》出版几个月后,国会图书馆就收录了《死人不会说话》,编号排在格雷沙姆的小说后面。次年,C.L.鲍尔德自费出版了一本螺旋装订的灵修小册子,书名叫《性灵概要》(MainlyMental),开篇就用了“冷读”这个词。而“鬼骗子”则似乎一直隐于幕后,少人问津,和词义倒也颇为相符。
“冷读”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四章“世界”,其中包含着全书的一个转折点:主角斯坦在翻阅去世多年的心灵主义者彼得的一本旧笔记,从中读到了两句话:“发现恐惧之物,一切难逃掌中”和“恐惧是通往人类本性的钥匙”。
斯坦“越过纸页,看着炫目的壁纸,洞穿了世界。愚者是由恐惧造就的。他害怕清醒过来,面对可怕的事物。但是,是什么让他酗酒呢?是恐惧。发现他们在恐惧什么,然后回击他们。这就是要诀”。
在“世界”中,这就是斯坦和格雷沙姆所屈从的语言观。斯坦来到松林密布的偏僻南方,那里有一个占卜师,她做征服魔法草药(JohntheConquerorRoot)挣的钱,比算命结束时兜售的星座卡片还要多:
言辞让他着迷。他的耳朵捕捉到了节律,他注意到了生动的俗语,然后采撷存入自己的语言库。他发现了老艺人口中奇特的、慢吞吞的语言背后的理据。一种南方人听起来是南方话,西部人听起来是西部话的语言。它带着土腥味,慢吞吞的背后是敏捷的大脑。它是一种给人安慰的、俚俗的、乡土的语言。
这就是《噩梦巷》的语言,许多“城里人”评论家觉得它令人惊愕而野蛮。格雷沙姆带着邪气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既是从星空俯瞰大地,也要自沟渠仰望繁星。
威廉·林赛·格雷沙姆将要把我们带进噩梦巷,那里不是道德败坏之所,因为那里没有崇高道德存在的空间。
格雷沙姆的这部小说描述了许多形象:信仰的愚蠢与玩弄信仰的狡诈;酗酒与把人毁掉的谵妄;没有缘由,突如其来便让死亡降临的无常命运。它不是一部讲述罪与罚的故事,若是这样来看便是误读。罪在《噩梦巷》中无处不在,而罚却似乎是生命之所固有。
“这是一条从头到尾都漆黑的巷子,”斯坦在《噩梦巷》中对自己说道,“从儿时起,斯坦就在做一个梦。他沿着一条暗巷跑啊跑,两侧无人的建筑阴森可怕。巷子尽头有光,但身后有什么在紧跟着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他醒了,浑身颤抖,最后也没有抵达那道光。”斯坦反思了自己的印记,所有人的印记:“他们也有自己的噩梦巷。”没错,正如斯坦——也就是格雷沙姆——在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恐惧是通往人类本性的钥匙。
斯坦和格雷沙姆实际上是同一的。惠顿学院瓦德中心收藏了一封奇怪的信。信已经很破旧了,是正走向人生终点的格雷沙姆于1959年写的。他写道:“斯坦就是作者本人。”
《噩梦巷》于1946年9月出版,为他赢得了赞扬与成功,也有人咒骂,甚至还被打成过禁书。面世三十年之间,每一版都经受了审查和删改。这里仅举一例。原文是“满身花柳的交际花,屁眼欠干的银行家”,读者看到的却是“服用药品的交际花,眼神扑朔的银行家”。
不过十年出头的光景,这本小说就被人们遗忘了。又过了十六个秋天,1962年9月,格雷沙姆的尸体被找到了。自杀,在时代广场旁边一家酒店的房间里。他几周前刚过完五十三岁生日。他身边的名片上写着:
无地址 无电话
没人要
没有钱 已退休
巷子、奔跑、遥不可及的光,一切都结束了——最起码,写下《噩梦巷》的人已经安息了。那么,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