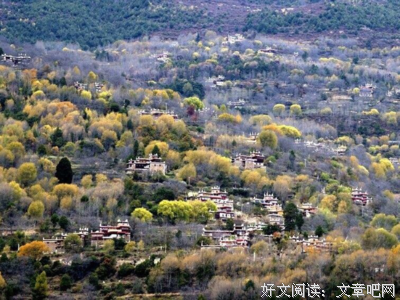《最后的晚餐》读后感1000字
《最后的晚餐》是一本由沈昌文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元,页数:1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晚餐》精选点评:
●失之琐碎……
●20130311购买。
●与《读书》有关的往事。
●得有多丰富的阅历多沉稳的心才能有笔下这份从容
●出版文化的作业
●书与吃,一个老顽童
●大开眼界 沈老打开了我未知的编辑领域的大门,知道了一些文学界的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读他们的书,和美食大门 看了他的书才知道吃也是可以如此讲究的
●小品文,就像过粥的小菜一样
●图书馆阅读
●以前的知識分子那股認真勁真是感動我。沈老很幽默,還挺時髦的,連洪晃的“凹造”都出來了。哈!
《最后的晚餐》读后感(一):生动多情的沈老头
本书与前所看过的作者的《书商的旧梦》一书意旨相近,趣味相同,折射出一个生动多情的沈公。
《最后的晚餐》读后感(二):阁楼人语——评《最后的晚餐》
作为读书的编辑,我是知道沈老的大名的,但是对于他的文字,只读过一篇关于的采访,说起话来挺风趣的一个老先生,始终没有读过他的文字。最近买了一批书,就有沈昌文的《最后的晚宴》。也算是对久闻其名的一个补偿了。
对于这个书名,他的解释是对于那些故去朋友的追思,但是鉴古可以知今。也就是说,这些文字后面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在其中的。比如,老先生一直对于启蒙,抱持着温温敬意,而这些敬意都化作了对于那些以故老先生们的追思上了。对于年轻后现代,老先生也不怯于放两支暗箭,刺痛一下现代的学术新贵们。就是大佬与今日新贵,这种微言大义,在二十世纪依旧拥有市场。
另一个吸引我的主题,在于沈昌文曾经说过,现代的文字缺乏readable,没法看全是一些概念,让人无从置喙。这个批评,不止沈先生其实还是很到位,这年月的文字越来越不耐看,越来越没有味道。其实出版界也从这个批评中,找到了获利的机会,于是乎大量出版那些文字过得去的好文章——民国学术的著作,不止一个出版社,是整个出版界都在这么轰轰烈烈地干。
而沈昌文先生自己的文章呢,说真的,也没有做到他所谓的readable,至少认为还没有,虽然都像是拉家常,但是总有一种拉虎皮做大旗的感觉,不知道这本书中,就如同跟名人合影一样,然后说出一套话来,虽然都是小事,却处处感觉到微言,做到好看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文字,也不喜欢这种文风。
其实,沈先生的看法,是有他的道理,至少对于学术界文字的批评,我是完全同意的。至少到现在,文字的数量增多的情况下,也看不到现在的文章比过去高到什么地方,更多的是感觉到文字兑水和掺杂了太多的杂质。反正,可看的文字与出版的文字相比,其实完全是反比。如果说,沈先生在这本游戏之作中有什么留下回味的,其实也就是那些谈吃的文字,以食会友,吃饭聊天都可以写文章,这也是一种境界,但是现在从哪里找这些可以吃饭聊天的朋友呢?
《最后的晚餐》读后感(三):腹中有料气自闲
沈昌文先生,沈公,笔下真是干净极了。说着老辈出版人、文化人的旧事,腹有实料,自信满满,不用哗众取宠的笔法,只须娓娓道来,我辈即如品甘饴。本是风趣的人,越是自然率性,越是怡人,常常让我忍不住暗笑。比如说这句“投桃报李,君子之风。尽管你的桃恁大,我的李恁小。”
中国文化命脉千年不断,到了清末民初,又受西风东渐之影响,数代学人,左牵右引,学贯中西,奇才蜂出,一个全新格局,已露尖尖角。只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这条新的血脉基本断了,到了今天,仍然没有开禁的迹象。随着老一代纷纷故去,学问的传承越来越难,精神的脊梁更是很难续接了。纵是沈公,都不敢称他请人吃的饭局叫“晚餐”了。
2:费老退位后提出组织些老人进行“思想操练”,结果“出于种种原因”,仅一次就不得不停顿下来。(哈哈,种种原因,对于我们资深中国人来说,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7:汪道涵不仅谙于文事,而且开口就是洋文和古文,指名道姓要看某某英文书和中文老书。谈得高兴时大讲莎士比亚,某剧某剧,某某人物,倒背如流。对配方哲学观念也极熟悉。(中共老一辈高官,不少是受“旧时代”教育出来的,可称渊博风流,与台港交锋,不落下风。我虽然无意臧否,但估计现今陈君,就未必有如此水准。)
67:三四十年代里,据说出版家多为文化人。以前是有了文化声望再当出版社领导,现在是当了领导再争取文化声望。中国很多事喜欢倒着来做。
44:记陈翰伯的十一条编辑意见,那真是字字见血,酣畅淋漓。(决定后附)沈公说“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其实不然,现在还流行着呢。我看陈翰伯后面的文字,也是清晰倔强得可以。有机会真要找来系统一读。
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一、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
二、不要穿靴、戴帽。
说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须说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须说上“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贡献力量”。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而是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全文中去。
五、制作大小标题要下点工夫。不要用“友谊传千里”、“千里传友情”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七、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
八、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处。此类注释可以和有关经典作家的注释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个署名,真名、笔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令人讨厌的谐音式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组”。不要用“××××编写组”。
十、行文中说“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还可以。但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一类空话。
十一、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最后的晚餐》读后感(四):2011年9月15日:沈昌文的《最后的晚餐》
虽然9月8日写了一篇《八十岁的沈昌文大叔》,但他的文章我是从未读过的。前几天沈昌文作客孔夫子旧书网,签售新书《八十溯往》,那次我错过了,有些后悔。好在最近从朋友处弄到了一册沈昌文的《最后的晚餐》,算是一种弥补。
这册07年出版的精装小书,装帧风格与现在常见的散文出版物差不多——我指的是今年五月在孔网在线发售的止庵的《比竹小品》和谢其章的《书呆温梦录》。后二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开本大小、封面设计、甚至书的厚薄都和这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的《最后的晚餐》非常一致。三本书放一块,看上去就像是同一系列的丛书。这大概是近年出版界的一种风尚。
不过从书的内容来看,《最后的晚餐》和《比竹小品》《书呆温梦录》等“书话”相比,有它自己的特点:不是讲和书有关的事,而是讲和书有关的人的事——此为书的前半部;后半部的内容则是“食话”,主题和饮食有关。简单地说,这就是一册有两类主题的散文合集。书名也有些奇怪,让我感到某种不好的意味。翻开“题记”,看到作者是这样解释的:
“兴趣点低”是借用“笑点低”、“泪点低”一类的说法,指的是很容易被勾起对某种事物的兴趣,很容易一时兴起,想去尝试某某,或者学习掌握某某。
比如当我读到沈昌文这本书中的《陈原的几句外国话》,文中写到他当年和三联老编辑陈原共事时,常常会听到说几句世界语,像“An korau venos printempo……(春天还会来的……)”之类;而沈昌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曾在夜校里学过世界语,于是也能回敬一句“Multaj belaj printempoj!(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尽管我曾自认为自己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至今连英语也用得半生不熟,而德语、日语也都在拼读字母和假名的阶段浅尝辄止。但我仍然因为沈昌文的这段文字产生了想学世界语的兴趣。
因为据我的联想,世界语是为了更容易掌握和交流而人工创造的一种语言,既然如此,那么掌握它的发音、拼写和语法就应该比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要容易得多。
查了查百度百科,了解到世界语是在1887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创立的,目前能流利使用的人数大概在十万到两百万人(这个估计范围的跨度真够大的)。而奇异的是,现在世界上还有约1000人是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他们的父母想必是世界语的坚定拥护者吧。
对世界语的兴趣还没有减退,我又读到了这篇文章的下面一段:
看!除了会世界语,陈原还会德语,还能在中风住院后用德语说出维特根施坦的名言!沈昌文虽自称德语不好,但他们那代人曾经为了学习马恩的语言而自学过德语!而且,他还能把俄文版的《逻辑哲学论》“翻读一过”!我刚刚为自己只会德语字母的拼读而惭愧,现在就发现,沈昌文随便列举的Sachverhalt,Tatsache两个词已经超出了我拼读的能力之外!
读到这里,我的心情用网络体来说,真是——“各种不甘心”!
暂时抑制住想去掌握世界语某国语某某国语的冲动,继续往后翻书。
在《最后的晚餐》的饮食篇里,我读到了《带着臭豆腐去旅行》。文中提到的臭豆腐不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而是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沈昌文引用了当代以写饮食文化而知名的沈宏非的一段话:“南臭热烈豪迈,排山倒海,臭而烘烘;北臭则阴柔低荡,销魂蚀骨,臭也绵绵。”这里的“北臭”,指的就是王致和臭豆腐。沈昌文继续介绍沈宏非提供的臭豆腐吃法:油炸窝头片后,抹上臭豆腐,那味道是“刚柔并济,冰火相拥,悲喜交集的香臭大团圆”。沈昌文对沈宏非谈论臭豆腐的文章表示非常满意:“居北京而又想过‘臭’瘾者,不可不一读沈作。”
沈作我没有太想读,倒是跃跃欲试地想去超市买一瓶王致和臭豆腐。对于王致和这个品牌,我只买过大块腐乳等比较正常的种类,且印象一般。王致和牌下的臭豆腐,卖相丑陋,跟南方的臭豆腐相比,是名同实异的两种东西,我从未起过购买的念头。
而现在,王致和臭豆腐似乎长出了招呼我诱惑我的小手,让我又向往又忐忑:真想也买一瓶来试试,看看被两位名人推崇的“悲喜交集”究竟是何种感受;不过,真要让我鼓起勇气夹起来吃,估计还得先把沈昌文的这篇《带着臭豆腐去旅行》翻开,放在瓶边作为佐菜才行。
书给人的阅读感受分两种,一种本身就是丰盛大餐,可以让人心无旁骛地饱食一顿;另一种则相当于下饭的咸菜腐乳,让人吃过之后胃口大增,有了吃更多其他食物的欲望。
沈昌文的文章就是这种下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