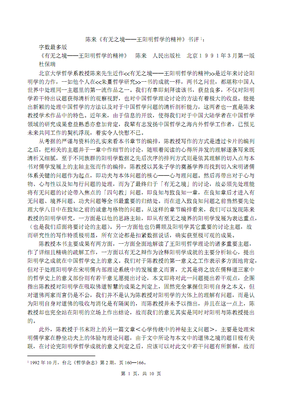《有无之境》读后感摘抄
《有无之境》是一本由陈来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无之境》精选点评:
●我要找到的就是一套适用于中国思想的概念体系,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问题以及用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概念。我觉得陈来的这本书很好。为了不流于僵化,我们还要知道这样的概念系统意味着什么,参照余英时的书我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易读 流暢 基本信息够 可以提示很多问题
●高山仰止
●不思天人之境,不问鬼神之学。
●陈老师通过扎实透彻的论述,解释了王学中很多疑问和争议,对入门者很有启发
●陈老师自己最喜欢的著作。
●好像就学到了一个词叫“乡愿”
●重新精读了第二遍,越发感觉陈来老师的用心。也加深了我对阳明心学的理解。陈来老师什么时候出一本老庄的书就好了……
●暂不评分,没有看懂,也没有看进去
●晚明的思想自阳明始,一扫数百年理学禁锢。陈来老师于褒贬之中,育教于无形。
《有无之境》读后感(一):存天理 灭人欲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很奇怪为什么偏巧是美式文化更多的体现了"天理"——“合理性”,而中式却多被"人欲"——“门槛表象”左右。这大约就是老子所谓的,既然有,则不必谈,谈者都是现下没有的吧。
好比:天下有德,则不必求德.天下自治,则圣人无为。
《有无之境》读后感(二):。。。。。。。。
陈来这书也就是一个资料汇编(当然这样说或许太刻薄了,中哲史的研究没有几本不是如此的),写论文的时候摆在手边作为分类查看是不错的。另外对湛甘泉等的交涉之考证也是不错的,包括早年格竹子的时代考证。总体来说陈先生就是擅长考据的,朱熹书信编年考证在日本也是被承认的。不过,除此以外么。。。。。。
没事喜欢扯几句西学的东西,例如祁克果之类,当然他的“高徒”彭国翔更喜欢玩这套,评价么。。。
另外,说到底,有无之境的这个说法,我很早以前就有质疑了,这里就不便多说了
《有无之境》读后感(三):至善者心之本体?
今天读《有无之境》,里面提到阳明的“至善者心之本体”,不能解释我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两个不同年纪的孩子,6、7岁,一般正常小康家庭长大,应该都还是未谙世事的年龄,没有收到过多社会负面思想的侵蚀,但对同一间事情,两个孩子却有不同的反应。家里来客人,坐客厅休息,大人到厨房烧水沏茶去了,客人逗两个孩子,指着桌上的一盒巧克力说,“这个给我吃好不好啊,你们舍不舍得啊?”其中一个孩子说“好啊,你吃吧。这个巧克力已经过期了,过期了东西就是要给别人吃的。”另一个孩子说“你别吃,这个坏了,不能吃了。”我觉得这两个孩子的反应,都应该是本能的反应,应该是透露人性的两种不同的本质,人性之初应该是有善恶之分的。那么阳明所说的“善者心之本体”究竟还对吗?
《有无之境》读后感(四):《有无之境》你让我情何以堪?
在一位朋友的书评下的追评,直接贴过来了;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看待这本书,原来还有高人;
说下我的看法:
除了是一本资料汇编和爱莫名其妙引用不知所云的西学哲语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首先,陈来自己没搞明白心学要讲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原因如下:
老把心学放在伦理和道德范畴来讲,若心学的范畴真是只限制在伦理和道德的范畴,那阳明到现在早被忘到爪哇岛去啦。
听说陈来还写过关于朱熹和理学的书,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他 ,没事就别写阳明了,这个实在不适合他。
二、好多东西就是汆到一起,比如37页讲:“心即理说的矛盾”,只提出问题,扯了一大堆蛋,最后连一点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结尾结的真叫一个烂尾楼,还引用康德,你读懂心学了吗,就来写,意之所在便是物,因此,阳明心学是最最唯物主义的学说,这点都读不懂还来写心学,侮辱心学。
三、这本书让我看并无推广心学的目的,如果有的话,用语绝不会如此晦涩难懂,还老是引用老外的话,难不成我看个心学既要去读通四书五经,还得再弄通,黑格尔,康德书里的哲学概念吗?
四、书名取的有问题,什么叫有无之境?阳明心学跟有无之境有半分钱关系吗?
叫知行合一或者良知与致良知,也比这个名字强。
五、全书从目录看根本是无条理,根据《如何阅读一本书》的方法,看一本书的目录结构,就知道作者写此书的时候,用了多少心力。如果真是想着让人能通过看此书学到一些心学的修炼方法,为什么不先写工夫这一章?绪言竟然以有我无我这种佛教的用语开头,我也真是醉啦。
六、除了陈来,还有其他一些为了赚钱目的,胡乱汆书,对于不会选书又爱看点儿书的朋友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花钱不说,还浪费宝贵的时间,规劝此类人士别误人子弟了,自己修炼好再来写书好吗?不然睡觉会做噩梦的。哦,还会死全家。
七、目前来看这本书45块买亏啦。以后买书还得慎重。
over!
《有无之境》读后感(五):三条目次序问题,不解。
原书P167:
“当然,这并不表明阳明格物说完全没有困难了。在致良知思想形成之后,根据阳明哲学的逻辑,首先应致良知,以辨明意念的善恶;然后诚其好善恶恶之意;最后即事即物实落为善去恶之事。这个顺序,即致知诚意格物,与《大学》本文的“格物致知诚意”的工夫次序有所不合。所以后来罗钦顺指出,若据致良知说,“审如是言,则《大学》则当言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当云知致而后物格,不当云格物而后知至耳”(《困知记》附录)。这说明,从经典学的立场来看,阳明哲学终究还有一些内在的难题没有解决。”
这是《第六章:诚意与格物》最后一节的最后一段话。作者梳理了阳明的“格物说”之后,在末尾提出了格物说的一点缺陷。不过却让我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作者认为按照王阳明在致良知思想形成之后的逻辑去理解《大学》八条目,则与《大学》本文的文本次序有所颠倒了,并附以罗钦顺致阳明书里的评论为例证。另根据作者在本节所述,阳明讨论格物说的主要材料有两个:一是嘉靖六年(1527,阳明死前一年)口述的《大学问》,一是《传习录》下一段讨论《大学》首章的较长的文字。两段文字皆录于本节正文内,通过比较阅读可以看出,《大学问》的学理阐述显然更加完整。
又,根据《第七章:良知与致良知》转引潜德洪等所纂《年谱》,阳明的致良知说肇始于正德十六年(1521),则《大学问》所作之年代,显然远在阳明致良知说形成以后。也就是说,《大学问》所体现的较为完整的阳明格物说观点,应被默认为是在阳明良知说业已成型的情况下。二者如有矛盾,则理应由其学说内部加以考释。
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三条目的逻辑次序问题)是否果真成立呢?
兹录《大学问》论格致诚正修:
问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亲民之说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
答曰:“此正详言明德、亲民、 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
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 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①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
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②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 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
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③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书》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 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④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谦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
按,作者名为引“《大学问》论格致诚正修”,其实却为摘引,比如上文所录【④】的内容便被省略了。不过实际上,即便不看【④】的内容,仅就其余所见,特别是【①】、【②】、【③】三个判断句,也可以清晰地看出阳明所论之功夫次序,实际上与《大学》原文中的格物致知诚意并无区别。按照阳明此处的说法,心体无不善,然意之所发则有善有恶,而欲“正”此“意”,则需“致吾心之良知”,而欲落实“致良知”,则必在“格物”。这是逆推。
正推的逻辑,则尽在于【④】。值得注意的是,【④】虽以“良知”起首,却并非以“致良知”起首。良知固是人人生而有之之物,然却有所“亏缺障蔽”,故必先格“意之所在之物”,“无有乎不尽”后,方可谓“致良知”。良知既致,才有所谓意诚,才有所谓心正。如果再将阳明四句教考量进去:“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则四句教与《大学问》,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读完这一章,十分不解作者何以认为阳明在致良知思想形成之后,对三条目的次序看法与《大学》本文有所不同。
此外,作者引用的罗钦顺的批评,今考罗钦顺《困知记》,罗氏此书系针对阳明与人论学书中“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一段文字所作之批评。按,罗氏所引阳明论学文字,系出于嘉靖四年(1525)阳明与顾璘之书,书中相关文字如下所录: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假而果在于亲之身,而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与?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于吾身之良知与?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见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不言而喻矣。”
由此可见,阳明此处所论之关键乃在于心/理不可一析为二。其之所以援引致知格物说,也不过是为了通过“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与“格物——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这两种落到实处的功夫来证明“良知”(心体/心之良知)即是理而已。书中固然存在致知格物这样一种次序,然而阳明本意并非探讨这两种功夫,因此这种字面的次序,似不应如罗钦顺及陈来教授所理解的那样具有实在的次序。
又及,罗钦顺与阳明书下注云:“初作此书,将以复阳明往年讲学之约,书未及寄,而阳明下世矣。”可见是书当作于嘉靖七年(1528)阳明谢世前不久。而阳明系统阐释格致诚正修的《大学问》成于嘉靖六年,或与罗氏此书相隔甚近,故此罗氏作此书时,因尚未及见阳明《大学问》而对条目次序问题有所误解,亦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