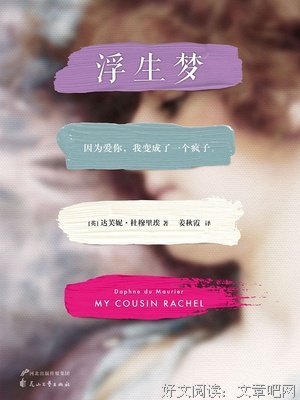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1000字
《浮生二十一章》是一本由任晓雯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1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浮生二十一章》精选点评:
●好是好,但总觉得故事不够饱满,就是个写作大纲。没稳住,出书早了,可惜。推荐阅读,由第一故事改写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35万字和2000字故事怎么比呢?任晓雯至少有两点好:1. 从非虚构向虚构跨越的度,拿捏的好,像海明威。2.语言生动简洁,明清笔记语言汲取得好,沪语运用得当。青年作家里的好作家。
●2019—49 好看,就是短了点,里面好几个人物都能变成长篇,这样就更好了!看了这几十个人,更加明白,每一个个体在ta的一生中能够选择怎样的生活,有怎样的命运,决定于ta所处的年代。
●文字利落,市井生活
●众生皆苦
●15年就在读库上接触过,想来这才出版。以前是学生,也认同那些岁月挤压之下的苦难是低眉顺眼难言的苦楚,可等你也大了也读了也工作也做着,多少事情,无非就是碰着了。 一茬算一茬的。
●活灵活现啊
●意犹未尽
●二十一个人物,二十一个故事,一百多页,也就是每隔三五页要重新进入情节,读起来不算轻松
●故事精简到有点浪费的感觉~
●素描群像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一):谁不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行呢
读完全书就去吃饭了,吃完再回想本书,只想感慨一句,在时代面前所有人不过是被驱赶着往前走。
书里的人面目模糊,只化成了一个个符号,代表着某一个时代里的某一批人,这批人普普通通就像你我,却因为时代的特殊被赋予了一些悲情色彩。没什么戏剧化的转折,也没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大风大浪,正是因为都是些平常的、琐碎的事情,才更让人悲哀。
悲剧是崇高的,可小人物的悲哀如何崇高呢。
只是生错了时代罢了。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二):与温情无关的书,以漠然旁观刺痛人心
第一次读任晓雯的文字,才发现夹杂一些浅白的文言和上海方言,写起小人物的故事来是这样恰当的。她很冷静,很多小说作家喜欢夹杂评论,她写故事一句评论都没有,好像失去了口齿,只剩下眼睛。她冷漠无情又恰到好处的文笔真让人钦佩。
二十一个故事,大都像张爱玲的《金锁记》,很多个曹七巧,很多个长安、长白。也像贾樟柯拍的《山河故人》。夫妻疏离,亲子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读下来,竟没有一个让人觉得稍有安慰的故事,没有一个可以拎出来称得上“好人”的角色。如果这是本虚构小说,我一定要说作者心理阴暗,这么多人物,怎能没有一个好些的?但序里写,这是根据采访内容写下的小说,这些名姓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这些故事里的人生,都是真实的人生。不觉汗涔。dollar、上海户口、回城,美梦浇灌下,地里始终长不出好麦子。这是一本与温情无关的书,以漠然旁观刺痛人心;这是一场浮世绘,数点小人物的沉浮,浸渍大时代的悲凉。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三):关于“浮世”与“人生”的某些形式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9-7-8
《浮生二十一章》里的作品在结集之前就陆续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这和它的传播方式有关。作者任晓雯自述道:“2013年,《南方周末》朱又可先生建议: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由此,书中的这21个短篇故事最初是以专栏的形式流传于坊间的,它们相似的题材,结构和言说方式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字数上也有严格限定;但同时,它们又是“故事性”的文字,呈现极强的原创色彩和形式上的革新。如何兼顾小说的文体特征和专栏的传播方式,并在两相结合之下突出作品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主旨上的深度,特别是作者选择的还是“人物素描”这样一个相当古典的创作视角。这种种要求,无疑对文本的生成都构成了相当难度。
笔者首先关注的自然是小说的篇幅问题,根据以往普遍的知识,小说的篇幅长短往往决定了作者处理题材的方法,这是出于对写作形式的基本考虑。从古希腊时期的史诗、悲剧延续至今,文学作品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认知,要么建立在时间的维度之上,即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段里呈现出这个人物的生命形态;要么建立在空间的维度之上,即强调在某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展现人物的内在冲突。前者是史诗的写法,发展到十八世纪以降的欧洲小说,便是狄更斯式的“成长小说”;后者则为悲剧的写法,强调的是人生的某个,或几个横截面,以此为“标本”,起到的是“透视”人生的作用。史诗和悲剧从形式上引导了作家理解写作对象,处理素材的方式,随着小说的兴起,形式特征也同样影响了篇幅的规制。比如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就认为中篇小说是一种新兴的艺术文类,是“人类命运的无穷长诗中的一个插曲”,是“分解成许多部分的长篇小说”,是人类命运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章”。别林斯基自然是基于俄罗斯文学的演变发展现状得出这个观点的,但仍然可以看到,他所理解的“中篇小说”从形式上讲与古希腊悲剧的互通之处。
但到了任晓雯这里,她似乎有意将这种立足于文学史的体式分野打通起来,从而完成一个文本实验。那么问题来了,两千字的篇幅如何得以承载“浮生”这个极为重大而普遍的人生命题?单从“生”这个字的意思去理解,要体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传统的处理方法无外乎依靠足够的细节来提供相对可靠的叙事,这里的“可靠”与否取决于对现实人生的模拟程度的高低。然而这种方法对“浮生”系列来说显然是不可行的,于是任晓雯从“浮生”中拿出一则素材,掉转头去写了四十余万字的一个大长篇《好人宋没用》。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以人物为中心,并且进行了充分展开和挖掘的长篇作品,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它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拿《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作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处理相似的材料时,两千字和四十万字的区别体现在哪里?一个文本实验的完成究竟需要牵动哪些语言与形式的“零部件”?在这里,不妨可以先谈谈“浮生”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效果,它带给读者最为直接的感受,乃是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它触动的是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文化记忆,源自于每个人对所经历的时代的认知经验。它唤起的是读者自身的某些经历及见闻,并且借助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体验来与作品中的人物达成共鸣。系列里的每一个作品都用一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者谓之“立传”。翻看目录,会发现这些名字都极为普通,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经常会取的名字。甚至,当完整看完这本书后,这些名字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变得模模糊糊。袁根弟是一个有着深重西洋情节的上海底层女性。杨敏安是当代屡试不第的“范进”,周彩凤和余鹏飞作为外乡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向往带着深深的自卑与压抑。这些人物,就其本身的经历而言实在是太“典型”了,而作者也并没有回避这种典型。因为要在这样的篇幅内让一个人物迅速地站稳脚跟,将他作典型化的处理是最为稳妥,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而这,便也已经是在暗示读者,不要将人物的境遇本身看得太重,因为这些境遇一旦呼应了具体的时代内容,就如同棋子找到了安置它的棋盘,有着明确的对应性和必然性。任晓雯对她的文本实验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乃是借助真实的社会环境来推动人物的发展,将个体的命运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内。所以在“浮生”系列中,作者对历史的处理方法式更需要关注的,而这种方法也同样考验着一位写作者的建构能力,即如何在不交代大环境大事件的情况下,仅凭借对细节的呈现来把握历史的脉络。也即是说,当写作必须回到历史发生现场的时候,写作者应该如何挑选,拾掇起历史尘埃中的碎片,将它们还原成作为进行时而存在的具体语境的某个部分,并且在一个立足于虚构的文本中产生实在的叙事动力。任晓雯的方法首先是,对“物”进行最实在的考据和体认。藏匿在长袍子口袋里的“道勒”,阴丹士林布制成的高领旗袍,“江北大世界”,《申论高分预测试卷》,当这些“物”作为开启人主体意识的一把钥匙而存在时,它们被赋予了无限描述与言说的可能性。甚至,物的存在暗示了主体的生成,并将作为符号赋予主体被阐释和理解的可能性,它的标识功帮助也我们更迅速地理解了主体与时代的黏连是如何成为一种必然,一种宿命。
此外,由于任晓雯特殊的地域背景,语言她成为抵达细节真实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对上海籍的作家来说,写上海事却绕开上海方言总是别扭的,何况沪语本身已被赋予了太强烈的戏剧性,被先入为主地植入到人的某些思维惯性中去了。前有韩邦庆的《海上花》,今有金宇澄的《繁花》,问题只是如何妥当地处理方言的强大标识力,使其不至于脱离文本的整体感而成为徒然抢镜的无用摆设。“浮生”的好处在于方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调节叙述语流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它没有抛弃作为语言的“本职”,但它又多少暗示了时代背景的特殊,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沪语方言在任晓雯的调教下给人极为舒适的感受,不但没有阻碍到叙事语言的一气呵成,也同样没有将某些文化惯性强行代入到文本之中。由此,对历史细部的加强及对语言真实感的运用极大弥补了事件铺设上的不足,叙事的扎实不再只能建构在情节的设置上,而是以一种物我合一,言行相辅相成的状态穿梭在文本之中。
然而出于主题学的需要,作者仍然无法回避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碰撞与磨合,“时代感”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脱离了人的时代本身可能成立,反而更要求人物实行他原本应该具备的功能,为时代注入充足的空气。我注意到在“浮生”中,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是:志气。虽然作者将他的人物定义为“无名者”,并且始终用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去看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但历史的必然性同时是一把利刃,它迅速而武断地割除了附着在个体身上的那些极为粘稠暧昧的欲望与渴求,让他们不断地迷惘、受伤,而这才是贯穿“浮生”的全部主题。如果说“生”的本质是鲜活的、沉重的、具体的、挣扎的,那么“浮”的状态则将“生”抽离出了它的具体形式,赋予其漂泊不定,且无法自制的特征。就如《曹亚平》中的这个主人公,他所做的一切都高不过命运,其实是政策加诸于他的苦难。他的人生的全部内容从表面上看与他本人的志气是无关的,他只是作为一系列政策的见证人和执行者而存在;但事实上,志气又像鬼魅一般与他如影随形。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下,展现在文本中的曹亚平和“浮生”里的其他所有人物一样,是冷的,好像没有可以自我支配的感情。但这恰恰是出于一种对可期待的,可理想的感情的盼望,也就是志气,在维持着这些人物的近乎悲凉的冷。任晓雯始终否认“浮生”是非虚构的作品(虽然她承认使用了一些非虚构写作的方法),也许正是出于对这弥散文本中的“冷”的激情的维护。事实上,所有的书写都不可能是全然“非虚构”的,在语言的层面上,非虚构是一个伪概念,因为语言是具备创造力的,它终究是向着“生”的。
写在后面:编辑发来《北京青年报》的样刊版面,我一看,此文仍然被归入“青阅读”版块,心中百感交集。去年年末,收到原来一直合作的编辑尚晓岚老师的消息,说“青阅读”栏目要取消了,心中十分遗憾。没想更糟的是才过了不到半年,又收到尚老师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心中大恸,一时竟不知该用什么语言表达。没想到时过境迁,兜兜转转,“青阅读”现在归到“北青艺评”下由编辑罗皓菱老师一并管理刊发,我也算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此文刊出时对题目和部分内容做了调整,特此说明。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四):《浮生二十一章》:就算有毛病,也是了解大变局前上海人的好文本
《浮生二十一章》的作者任晓雯在其为自己的作品撰写的题为《为无名者立传》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表达:"后期写作的《浮生》,不再标注年代,该用细节暗示。百年来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每个平常人家。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从序言开始阅读《浮生二十一章》时,读到这样的表述我还暗自赞叹过:好啊,用爱国布、用降低了领口的旗袍、柯湘头、布拉吉等等各个时代显而易见的风物特征来标识每一个故事的时代背景,要比用年月日这样直白的表述,要聪明了许多。等到被一个个故事绕晕了它们的发生时间后,我开始质疑作者为求文本的高级而采用的表达方式:你指望《浮生二十一章》的读者事先都知道爱国布、降低了领口的旗袍、柯湘头、布拉吉等等风物分别代言什么年代,是不是风险太大?假如读者被这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挡在了《浮生二十一章》的门外,文本再高级又有什么意义呢?
初读序言时被打动,还有一处表述:"续写《浮生》后,糅入了文言和沪语。我试图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语言就应该是与故事中人物生活的年代如影随形,况且,《浮生二十一章》中最早的故事也不过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所以,就算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夹带进了古语——对,说古语而非文言更加确切——对读者而言构不成阅读障碍。倒是那些沪语,真的通用性不够。首篇《袁跟弟》倒数第二段开头,作者如此写来:"袁跟弟让他别叫。弗听。袁跟弟搦了鸡毛掸,敲一通桌子。"句子中,"弗听",是沪语,不容置疑。但"弗听"的前一句"袁跟弟让他别叫",却是标准的普通话。就这么如此切近地杂糅官方语言和沪语,难道没有"一脚高一脚低"的不舒适感吗?况且,沪语本身也有区域差别。我小的时候,徐汇区说的是徐汇区的上海话,杨浦区说的是杨浦区的上海话,复旦有复旦的上海话,华师大是华师大的上海话,比如,"削香莴笋"这个动作,我家说"XIE香莴笋",我家隔壁,却说成了"XUE香莴笋",所以,"袁跟弟搦了鸡毛掸"中的动词,更多的上海人家会用"捏"这个动词。倒也没有高下之别,只是想说,将沪语书面化,实在太难,所以,我们读《浮生二十一章》的过程,就语言层面而言,常有小石子飞进鞋里的异物感。
尽管如此,非上海人要了解上海人,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是一本极好的文学口袋书。此处的"口袋书"不存在上地铁前买一本,到站后刚好读完顺手丢弃的意思。书的装帧虽然雅致,又配上了精致的线条人物画,只因开本选择正好塞得进口袋,所以我称之为口袋书,还有一层意思是,每一故事两千字的盘算,辛苦了作者——每篇局限在两千字,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迈阿密和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但便宜了读者。用读一篇微信上鸡汤文的时间就能认识一位经由任晓雯的精心打造几成一种上海人典型的故事,就阅读营养而言,真是太划算了。二十一章之一的《高秋妹》的插图《余鹏飞》这个故事的成色比较新,说的是从外地来上海读大学的江北人(苏北人)余鹏飞,上学期间认识了一个上海姑娘姚悦亭,糯米团子脸、戴着黑色胶框眼镜的姚悦亭长得虽不好看,但是上海姑娘呀,所以,余鹏飞春节回老家只告诉了大姐一个人,即刻全村都知道余鹏飞搞了个上海女朋友。见父亲不接纳,余鹏飞还安慰:"姚悦亭很朴素的,脾气也好,不像上海人"呵呵,不像上海人。半年以后,为让余鹏飞放心,姚悦亭随男朋友回老家,"走至茅厕,姚悦亭揭了帘子,见里头一大坑,秽物层层叠高,黄的黑的,软的硬的,粗的细的,几欲潽出来。白蛆犹如浪沫子一般,慢吞吞翻进涌出。她啊呀捏住鼻头,又跑又跺脚",可村里人嘲讽她资产阶级小姐要甩到乡下人时,姚悦亭脸上满是泪嘴里却犟着:"瞎讲……"我觉得,《余鹏飞》可以对付一大波不利于上海姑娘的网上风评。二十一章,二十一个故事,虽不能涵盖今日上海之人物风情,却是一次概述,很有意思。只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读者,总觉得有几个故事总有不尽兴之嫌。不,计较的不是篇幅,而是有些篇什的点睛一笔点到之处不够中心。再读序言找原因,原来,二十一章有些是通过书面材料虚构的。那就是了。要面子的上海人轻易不肯吐露生活的苦衷,被汇编如类似《口述小三线建设》和《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这类书籍的材料,口述者说了多少真心话,实在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