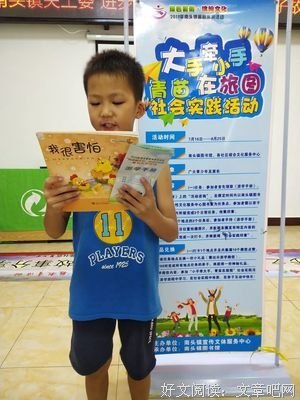我信仰阅读经典读后感有感
《我信仰阅读》是一本由[美] 罗伯特·戈特利布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信仰阅读》读后感(一):戈特利布:改变美国文学的编辑 | 《卫报》
本文译自《卫报》(The Guardian ),作者 Michelle Dean,发表于27 Sep 2016。侵删。
作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经典作品的幕后推手,戈特利布有理由吹嘘。但在他新出版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中,他更愿意淡化编辑的角色。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在采访中,他把自己作品的功劳归结于他的编辑。采访结束后,海勒接到一个情绪激动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他的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戈特利布让海勒把这部分内容删了。"我当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不应该让读者知道编辑的干预,"戈特利布在他的新回忆录《我信仰阅读》中说,“他们有权利感觉到他们所读的东西是直接从作者那里来的。"
戈特利布的书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对于一个所谓的传奇人物——他对我笑着说,他的女儿取笑他经常被人这样称呼——来说,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然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开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入主克瑙夫出版社,再到短暂但令人难忘的《纽约客》主编任期,戈特利布的编辑之笔触及了20世纪大多数重要美国作家的手稿——甚至还有几位英国作家。不过,他尽可能地藏在幕后。"我很少接受采访。"当我在他位于纽约东区书香四溢的别墅里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只接受这一次采访,因为他需要帮助出版商销售他的书。
《我信仰阅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本给书呆子看的书。毕竟普通的读书人大多看不见戈特利布获得成就的那个世界。大多数人不会注意书上的出版社印记。大多数作家比海勒更自负,不会在采访中谈论编辑对最终版本的作品的贡献。
而大多数编辑也和戈特利布一样,认为出版界的事情最好还是留在出版界。"这一点很无聊,但这是一份服务性工作,"戈特利布告诉我,"你是个服务人员。"
我指出,戈特利布明确服务的对象之一是文字。除了海勒之外,即使把他经手的作者列成一份简短的名单,也像是一份名人名册,如果在不怎么赚钱的图书界也可以这样说的话。托妮·莫里森,杰克·里奇勒,埃德娜·奥布莱恩,雷·布拉德伯里,辛西娅·奥齐克,多丽丝·莱辛,约翰·勒卡雷,迈克尔·克莱顿,罗伯特·卡洛,凯瑟琳·赫本和比尔·克林顿。《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地惊雷》,当然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些都是经典之作,如果没有他,这些书可能永远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这些年来,这让他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你看20世纪的美国写作,不可能不碰到他的名字。
戈特利布对这一观察算是点了点头,但继续坚持认为,对他来说,自己的成就从来不值得庆祝。"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了一个名字,"他摆摆手说。"我本可以遍地开花,我想,但真是浪费时间。"
我个人很理解为什么戈特利布的那么多作者都对他如此虔诚。他说话很温柔,但并不害羞。当他有意见的时候,他就会明确地表达出来。例如,谈到图书编辑工作的缓慢,这个过程有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是 "真正的犯罪",编辑们经常让作家们等待。他说:"我只是觉得这很卑鄙。"他是认真的。
他告诉我,编辑的基本素质是同理心。"你不应该接那些你不能共情的书。"在我们谈话的开头,他说,"如果试图把一本书变成不是它本来面目的另一样东西,而不是使它在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这样就会造成麻烦。" 在编辑过程中,最灾难性的事情就是编辑坚持要把书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作家来说,在这种关系中,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戈特利布说,"而且他们对发生的事情非常敏感,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告诉我,他知道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认识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并且知道这么多他们的八卦轶事,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在这本薄薄的书里。他写到,在一次出版午餐会上认识了诺拉·艾芙隆,那时候她是一个自由记者,领了一个愚蠢的采访任务。"她来到办公室(吃常规三明治),几分钟之内,我就看出她和我一样,对这个愚蠢的话题感到尴尬,"他写道,"在一个小时内,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成为朋友。"
其他更厉害的熟人也十分有爱。关于他与多丽丝·莱辛的第一次见面,他写道:"她没有尝试去吸引人,我也不会傻到去尝试吸引她。"但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在工作中她毫无架子。"他坚持这样评价托妮·莫里森。"我的许多工作伙伴都被认为非常难搞,极其复杂。"但他从未遇到过真正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他和作者没有过分歧。当他还是年轻编辑时编辑了罗伯特·卡洛的《权力掮客》。卡罗原稿的长度达到了100万字(普通非虚构作品一般10万字左右)。戈特利布说,他花了一年时间才将其删减下来。
另一种编辑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夸耀这一成就。但戈特利布不会。"他比我更加觉得我的工作很重要。"戈特利布在谈到卡洛时说,他们经常一起并肩作战地写作。
"他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编辑,尽管他喜欢这样想,我也喜欢这样想。因为在这一点上,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补充道。
《我信仰阅读》读后感(二):罗伯特·戈特利布带你走进出版的黄金时代 | 《华盛顿邮报》
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作者 Michael Dirda,发表于September 14, 2016。侵删。
在我的办公桌上,一个装满铅笔的咖啡杯旁,我放着一个领扣,上面写着:“生活?当然,我有生活。一个充满了书的生活。”而对此,你不会找到一个比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更能概括这句话的例子了。
在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六十载的生涯中,戈特利布出版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书,包括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托妮·莫里森的《宠儿》,约翰·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罗伯特·卡洛的多卷本约翰逊(即林登)生平,劳伦·白考尔、比尔·克林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自传。
戈特利布1931年出生于纽约市,是一位律师和教师的独生子,他说道:“从我的生命伊始,文字对我而言就比真实的生活更为真实,并且更加有趣。”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最喜欢的是亚瑟·兰塞姆的《燕子号和亚马逊号》系列,反复把每卷都读了50来遍。成长到青少年时期时,他是收藏家式的完美主义者。“阅读一个作者的仅仅一些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夏天,我会按照时间顺序把一个作家扫一遍,今年是康拉德,下一年是凯瑟。”他在7天之内就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读完了。他是个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书呆子,不喜欢待在户外,喜爱舞蹈和戏剧但害怕乘飞机。用他第一任妻子父亲的话来说,“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就会把他带出去然后把他像一只病猫一样淹死。”
戈特利布在莱昂内尔·特里林和马克·范·德伦的鼎盛时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英国剑桥大学待了几年。回国后,他就开始找工作——而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已婚人士并且有一个孩子,尽管他看上去依然是16岁的样子(直到30岁去买酒的时候还被要求出示证件)。经过了一连串的乌龙事件,最终戈特利布被杰克·古德曼,也就是西蒙-舒斯特的负责人,雇佣为了助理编辑。当古德曼在47岁去世时,公司陷入到了混乱之中,而戈特利布——通过实力和交友天赋——逐渐成为了公司的首席编辑。
在西蒙-舒斯特工作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以及在克瑙夫工作的1968年到1987年间,戈特利布同时喜欢“高级的通俗小说”和高级的商业非虚构作品。无论是怎样的题材,他只出版最好的书,并且那些他自身抱有热情的书。他有一次将出版人的角色定位为“本质上是将自己的热情传递出去的行为,”并且他自己的热情也是多样的,从Rona Jaffe性与都市的经典之作《最好的一切》到Michael Crichton的科幻恐怖小说The Andromeda Strain。
而戈特利布的天主教品位并没有延伸到创新或实验性的小说上,诸如威廉·加迪斯的《大小亨》,他写道,“这对我来说,似乎比小说更有建树。”有时,他也承认他通常正确的判断也会让他失望:他提到,他拒绝了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孤独的鸽子》和约翰·肯尼迪·图尔的《傻瓜联盟》,这两部作品在日后都获得了普利策奖。
戈特利布在序言中强调,“我们更倾向于记住一个人的成功。”也许是这样,然而这种心理暗示不可避免地使《我信仰阅读》倾向于讲那些成功的事情:在这本书中,那些风靡事件接踵而至,畅销书的绚烂缤纷地置列其中。然而,在戈特利布每年编辑的20到30本书中,难道就没有那些他深深珍视,但却没有找到读者,甚至即使到现在也值得重新被发掘的作品嘛?这些闪亮的失败,这些特立独行的小众经典,这些由那些可靠的中层作家写出的优秀的、坚实的作品——这些都是对于健康的文学文化来说必不可少的,并且能够得知这样的作品是一件好事。话虽如此,戈特利布确实认为Something Happened是约瑟夫·海勒最好的小说。
这位近乎传奇的编辑,尽管他宣称自己是个书呆子,但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作为一个真正的嗜读者是什么样的。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中,戈特利布总结道,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总是“在一个关系融洽、思路接近、目标一致的小团队里”。不仅如此,他将众多的作者和同事视为自己的家人,和他一起度假,一起吃感恩节晚餐。因此戈特利布总是会写如此这般句子:“在将近50年间,我们依然是亲密的朋友和相互依赖的同事”以及“我和她一起继续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她去世我都一直是爱她的。”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真挚的感情,但这样的关系确实也对于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话说回来,戈特利布坦言罗尔德·达尔是个麻烦的合作对象,并大胆地描述了出版界的天后布兰奇·克瑙夫“身材瘦小,看上去就像是从达豪集中营出来就直接去了伊丽莎白·雅顿的化妆品柜台。难怪大家都怕她。”他还注意到,凯瑟琳·赫本和苏珊·桑塔格有着“同样不顾一切的决心,同样的优越感,同样不许别人挡道的昂首阔步”。
1987年,戈特利布离开了克瑙夫,执掌《纽约客》,他在《纽约客》待了5年(直到被光彩照人的蒂娜·布朗取代)掌管期间,他聘请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雷姆尼克,在适当的时候接任为《纽约客》的编辑。自1992年起,戈特利布再次为克瑙夫非全职工作,通常是编辑一些老朋友的手稿或者是比尔·克林顿这样的大人物的自传(其中有几页是他写的)。同样重要的是,他重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真正的记者,评论舞蹈表演,编辑爵士乐评选集,以及出版了一本绝妙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的10个孩子的作品。
尽管我有一些吹毛求疵,但《我信仰阅读》将会被那些对近60年来的出版世界感兴趣的人狂热地阅读。毕竟,自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地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比罗伯特·戈特利布更令人敬佩地编辑。他的生活,他也会承认,是充满特权的和令人嫉妒的,这其实只是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书籍的另一种说法。
《我信仰阅读》读后感(三):“出版人本身,就是文学丰碑的组成部分。”
这是美国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也是一名普通的编辑的人生之路。他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的朋友圈,你可以看到约瑟夫·海勒、苏珊·桑塔格、约翰·列侬、鲍勃·迪伦、萨尔曼·拉什迪、鲍勃·卡洛、芭芭拉·塔奇曼、川久保玲、比尔·克林顿……他的生活,注定要跻身闪耀的人类群星,令所有旁观者艳羡;他也是平凡的,因为,即便出道于大名鼎鼎的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加盟全球顶级的兰登书屋-克瑙夫出版社,接管如日中天的《纽约客》,他依然是一个要与作者聊项目、与稿件较劲、与合作商谈条件的普通编辑,每天面对的都是策划、审校、营销、推广、发行等琐碎的工作。
作为一名内容行业的从业者,戈特利布是明星,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他在时代和潮流中的际遇,也一去不复返。但在这部充满个人体验的回忆录里,仍然能读出他作为编辑的闪光之处:广阔的视野、无处不在的创意、对价值观的坚守,以及对阅读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回忆录的译者彭伦,也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人、文学经纪人和编辑。作者和译者的搭配称得上是珠联璧合,这使得作品的中文版在可读性、还原度和专业性方面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
这是一部传奇出版人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美国当代出版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跨度六十年的美国文化史。
——董风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
读这本中信·大方的《我信仰阅读》是种很特殊的体验。我终于发现,原来做出版的人,自恋程度和对出版的激情是绝对成正比的。或者说,由二者混合产生的惊人策划力,一定会带来巨大的成就产出:不仅是一部部的畅销书,更是一次次验证一个编辑对作者与作品无比自信的判断力。而这些成功案例,又会进一步激发编辑的自恋与激情,让他有更坚定的信心策划出下一部成功的出版物。
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就是典型代表。从大学毕业后偶然机遇进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做编辑助理,到三十六岁接掌克瑙夫出版社,他这本回忆录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絮叨着上述循环。一部又一部的畅销名作和鼎鼎大名的作者高密度出现在他近乎流水账似的的文字里,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枯燥。可能,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同行从业者准备的。我们就是读者,都在做着类似的事,吐着一样的槽,为同样的理由兴奋或沮丧。
至于那些不理解为啥不挣钱还要做编辑这件工作的人而言,这本书就是一整本废话。只有你真正做过编辑,体验过编辑的乐与怒,才能理解为挣钱做书其实是最无趣的事之一。当你把做书这件事看作自己想做、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到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时,很多附带的利益和伤害都会随之而来,不想要都不行。这其实就是人生,也是拿任何一种工作作为终身事业的宿命与结局。
——韩志(未读创始人、CEO)
出版人判断力法则。
——周公度(大星文化总编辑)
一个做了一辈子书的好编辑,他自己的书,却并不是什么编辑圣经。他参与塑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却也谈不上成为一代编辑的偶像。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做书的人珍视,戈特利布说,出版就是把热情传递给大众的过程,编辑要谨记为作者做好服务——这都是些老派的价值观,正确,却并不总是被坚守,也因此需要时不时被拿出来再说一次。不过,真正令这本书吸引人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位好编辑在做书过程之中,和作者达成的情谊,那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让这本书有了温度,也让我相信,他真正参与的那些书,无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还是能够长存于文学史的经典,也必然是有温度的书。
所以,阅读是一种信仰,而做书,是一种关系。
——涂涂(乐府文化创始人)
作为出版人,戈特利布够传奇的。作为编辑出身的出版人,更是值得我们这些编辑学习,如果还有足够的自我期许。戈特利布谈得很诚恳,很谦逊。他从自己的阅读史娓娓道来,“简·奥斯汀把我钉在了墙上”,“我第一次真正把阅读的体验与内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我发现了某种道德指南针”,这一节收尾的话很有力量,道出了阅读的塑造力。戈特利布与阅读的故事就此开始,自我阅读,成就他人阅读,循环往复,意义生成。这大概就是从事编辑行当最有诱惑与成就感的事。像戈特利布这样参与塑造当代文学出版史、阅读市场的出版人,他们的故事(与作者,与书,与时代潮流)值得分享,他们本身就是文学丰碑的组成部分。
——魏东(“文学纪念碑”丛书主编)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的人生终究还是难免被物化,像罗伯特·戈特利布,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张“书单”。这本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编辑”的回忆录,与其说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贯穿始终的是一个人的人生,不如说是这个人一辈子都读了什么书,戈特利布真是用生命在诠释什么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人生书家”。在越来越多人放下甚至放弃读书的今天,听戈特利布说“我信仰阅读”,除了感动,还有一些吾道不孤的喜悦与苍凉。
——刘忆斯(《深港书评》周刊主编)
本书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的文学出版人需要一个,就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功力:书稿的鉴别能力。缺了这个,一切皆无。这个能力是年幼时潜意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成年后意识不断下沉为潜意识堆积的结果。对每一本具体的文学书稿而言,不要迷信集体选题论证会的判断和思维,要相信对语言、结构、想象的感觉和直觉。
——佘江涛(江苏凤凰传媒总经理)
年轻时曾经14个小时读完《战争与和平》,7天读完7卷《追忆逝水年华》······传奇出版人戈特利布首先是一位如饥似渴的嗜读者,这保证了他在后来的出版生涯中持续终生的激情(“我工作的激情是为书,为出版,为人”),在他看来,“所谓出版行为,本质上就是把个人激情传递给大众的行为”。他对西方正典文学及高品质类型文学的极大量阅读,塑造了他非常令人信服的文学品味,以及对文学中新动向与新感性的敏锐感知力和高超判断力。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整个1960年代最好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如果不是戈特利布跟踪数年的协助打磨(包括具体的叙事结构),它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它甚至也不会叫《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取的名字是Catch 18,但当时有位超级畅销书作家即将出版的新书叫Mila 18,可以想见,这对于尚不知名的海勒的Catch 18来说,会意味着什么,而换成数字22,正是来自戈特利布神示般的灵感)。
在戈特利布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位引领行业方向的出版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业务素质与工作方法,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出版机构未来许多年的强大书目,以及可以介入文学史到什么样的程度。
——杨全强(上河卓远总编辑)
罗伯特·戈特利布的精彩回忆录告诉我们,卓越的出版人首先信仰阅读,是热情的阅读者。更有趣的是,这部回忆录不仅写了他所经历的辉煌的出版案例,还详细描述了他作为美国著名出版人的三次跳槽经过。
——曹元勇(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
《我信仰阅读》读后感(四):罗伯特·戈特利布的编辑艺术|《巴黎评论》
译按:
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犹太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传奇编辑,曾就职于西蒙-舒斯特、克瑙夫两大出版社,后执掌《纽约客》。他的品位不拘一格,很难对与他合作过的作家,或是他编辑过的数百本书做出概括性的评价。过去五十年中,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书籍都由他经手,如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托妮·莫里森《宠儿》、约翰·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等。他的作者不仅涵盖多丽丝·莱辛、约翰·契弗等文学大师,还有约翰·勒卡雷、迈克尔·克莱顿等畅销书作者,以及凯瑟琳·赫本、比尔·克林顿这样的社会名流,这些书经过他的手无不大卖。
戈特利布也是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所采访过的第一位编辑,就他的作者们对他的评价给予了一些回应,戈特利布始终认为编辑工作不仅仅是和文字打交道,更是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将自己对一部作品和一位作者的热情传递出去的事业。尽管他的作者有时会抱怨戈特利布,但都一致对他的编辑工作表示赞许和感谢。
本文编译自《巴黎评论》对他的采访,有部分删节。
原载于The Paris Review No.132 Fall 1994
Interviewed by Larissa MacFarquhar
戈特利布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大而不那么鲁莽的伍迪·艾伦,我们的采访在他位于东四十八街的联排别墅的起居室中进行,他的家距离第五十街的克瑙夫办公室有两个街区,距离西四十三街的《纽约客》杂志社有半英里。他的起居室可以俯瞰海龟湾花园——一个相当正式的私人公园。从窗口,戈特利布指出对面是凯瑟琳·赫本的房子(她是他在克瑙夫的作者)。本篇中的受访者是戈特利布亲自推荐的。他们的评论和戈特利布的回应在事后合并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直接对话。
约瑟夫·海勒
当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出事了》时,当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我和他们谈到了鲍勃(译注: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作为编辑对我的价值。出采访报道的那天,鲍勃给我打电话说,他认为谈论编辑和编辑的贡献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公众更喜欢认为书中的一切都来自于作者。这倒是真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再谈论过编辑的贡献。
罗伯特·戈特利布
当然,如果有人在采访中说我的好话,我当然觉得很开心。但事实上,这种美化编辑的行为,我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不是一件有益的事。编辑与一本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无形的关系。比如说,读《简爱》的人最不想知道的是,编辑曾说服勃朗特,认为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应该被大火吞噬。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编辑干预案例一直困扰着我——狄更斯的朋友建议他更改《远大前程》的结尾,我不想知道这些!作为一个评论家,当然,作为一个文学史家,我很感兴趣,但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很不安。没有人应该知道我跟海勒说了什么,以及海勒有多感激我。这对读者是不友好的,是不合适的。
......
戈特利布与约瑟夫·海勒正在工作中多丽丝·莱辛
鲍勃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编辑,是因为他读过所有的书,浸润在最好的言论和思想之中,并且在评判作者的作品时,把这样的经验拿来用。大家可能会认为这种经验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或许,从前人们可以认为一个严肃出版社的编辑读过很多书,可以进行比较。但如今,在出版社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
戈特利布
很多平时没有想到过的事情都会影响阅读体验。比如说,你安排书的结构——你是把它分成几章还是让它不间断地继续下去,是不是要给各个章节起标题等等这些问题。几年前,我编辑了一部精彩的小说,后来成为一部成功的电影,《莉莉斯》,作者是J.R.萨拉曼卡(J. R. Salamanca)。这是一本充满力量和有影响的书,主导和引发整本书的是那个叫莉莉斯的人物,但她在前六十页或者八十页根本没有出现。我不记得原来的书名是什么了,但我建议作者把书名改成莉莉斯,因为这样一来,在所有开篇莉莉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读者就会对她充满期待。所以只是改了一个标题,就塑造了一种张力,否则就不会有这种张力。
多丽丝·莱辛和戈特利布在家约翰·勒卡雷
鲍勃会告诉我,他是如何理解一个故事的,在哪里他也许略微失望;在哪里的满足感不是他所期望的,或者类似的东西——还是非常松散的建议。他会对我说,我要在这些书页上画一条波浪线;对我来说,它们太过抒情,太过有自我意识,太过夸张。而我会说,好吧,我暂时不同意,因为我爱上了我写的每一个字,但我会把它们再翻出来,舔舐我的伤口,再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或者他会说,在这里你不需要一段优美的描述......对我来说这真的很痛苦。通常情况下,他对我的角色没有任何异议,虽然他一直觉得我对女性的描写比对男性的描写要弱,我觉得这是事实。偶尔我会说我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让这件事暂时悬置,直到我承认他是对的。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接受鲍勃的建议。在所有的大事上,他总是对的。
戈特利布
有一段时间,我在编辑两个写间谍小说写的最好的作家的作品,约翰·勒卡雷和莱恩·迪顿,我发觉你找不到比这两个人更完美的对立。勒卡雷对编辑的建议无比敏感,因为他的耳朵是如此之好,也因为他的想象力是如此之丰富——他会接受最细微的暗示,然后带着三十页无与伦比的新文稿回来。另一方面,迪顿——他是完全愿意的,对建议的渴望也是不能再强烈了——他是那种一旦一句话写在纸上,就会变成现实的作家,任何善意的劝说或努力都无法改变。所以你可以对他说,莱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说,是什么?什么问题?你就说,在第37页,这个人物被杀了,但在第118页,他又出现在一个聚会上。哦,我的天呐,莱恩说,这太糟糕了,但别担心,我会解决它的。然后当你拿回手稿,翻到37页,他就会改成“他差点被杀死了”。
托妮·莫里森
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不会把鲍勃放在心上,如果那样的话对我来说很不好。他不是一个理想的读者,但他是一个好编辑。
戈特利布
作家们想要的第一件事——这听上去很基础,但你会惊讶于它在出版界是多么的“不基础”——就是快速回应。一旦他们完成了新的手稿,并把它放在了你的邮箱里,他们就处在一种心理上和情绪上的悬置的状态,直到他们从编辑那儿听到了消息,对于动物来说让他们待宰是非常残忍的。我很幸运,因为我恰好是一个阅读速度非常快的读者,所以我几乎总是能在一夜之间读完一份新的稿件。此外,当我收到与我合作的作家的稿子时,我就会被好奇心吞噬,想知道他或她写了什么。但不管是不是简单,第一项工作就是迅速而诚实的回应,当然,要有技巧。
......
莫里森
在写我的前两本书《最蓝的眼睛》和《秀拉》时,我有一个新作家的焦虑,想要确保每一句话都是完全正确的。有时候,这会产生一种珍贵的、宝石般的品质——一种紧凑感,这是我在《秀拉》中特别想要的。后来我写完《秀拉》,在写第三本《所罗门之歌》的时候,鲍勃对我说,你可以放松一点、敞开一点。你的写作不一定要那么含蓄,可以放宽一点。我不确定这是他的原话,但我知道,这番话的后果是,我确实放松了,开始向各种可能性敞开。正是因为我能够对这些可能性敞开心扉,所以我开始想一些事情,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按照我脑海中这个没有肚脐眼的女人的这个奇怪的概念或形象或画面去做,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通常情况下,我都会把这样的想法当成是鲁莽的。就像他说的那样,要放肆想象。
戈特利布
我还记得在托妮开始写《所罗门之歌》时与她的讨论,因为虽然我们总是对她的手稿做一些边缘性的修饰工作,但显然像她这样有能力、有辨识度的作家在文章上并不需要很多帮助。我认为我为托妮服务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她——帮她自由地做自己。我给她的唯一的真正帮助是非编辑性的。我鼓励她停止编辑工作,全职写作,这是我知道她想做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我对她的经济状况做了保证——但我真正要说的是,你不是一个兼职写作的编辑,你是一个作家——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一直都很理解对方——两个编辑,两个爱读书的人,而且年龄完全一样。
......
托妮·莫里森、她儿子斯雷德和戈特利布在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罗伯特·卡洛
我的脾气不好,虽然鲍勃会否认,但他也脾气不好。当我们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急得跳脚,需要离开房间去冷静一下。当然,他比起我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当我们在克瑙夫工作时,他可以离开,到别人的办公室去处理一些事务,但我除了上厕所,没有地方可去。我记得我经常会去厕所。哦,他的语气!如果你听过他的语气!它让我如此生气,我必须试着淹没它们。我尽量不听他说的侮辱性话语,因为我说过,我的脾气很不好。
戈特利布
鲍勃·卡洛和我总是互相叫嚣着推进工作,因为对他来说,每一篇稿子都是那么的辛苦,那么的努力,那么的执着专注,每一件事都是同等的重要。对这样的作家,你的工作就是要能对他说,你可能在这些事情上都做得同样出色,但这个比那个更有分量,你必须放弃一些。有时在热烈的讨论中,这在作家看来就像是一种攻击。而这是没有帮助的,尽管有时它可以是有效果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编辑,你和每个作家的关系都是不同的。对一些作家,你要说一些你不能对别人说的话,要么是因为他们会生气,要么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破坏性太大。你不能只用一种方式,在某种本能的层面上,你不仅要对作家的文字做出反应,还要对作家的不同气质做出反应。这对一些编辑来说可能很难,我没有觉得很难,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取悦别人。比如我和海勒,就从来没有过不好的时候,因为他是完美的疏导。当你和他一起编辑手稿的时候,你们可以把手稿看成是两个外科医生在检查一具被摊在桌子上的尸体。你只需要把它切开,处理掉有问题的器官,然后再缝合起来。海勒是完全客观的,他有这样的头脑,即使在完成一本书后,也会立即进行思考。
......
罗伯特·卡洛和戈特利布我的动力是想把事情做好,把好的事情做得更好,这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我想我很幸运,我找到了一个有益的出口。......我曾经问自己,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好?我真的不明白。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因为我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功,却做了这么少的事情。后来我意识到,你不一定要成为天才才能做编辑。你不必有远大的志向才能成为一个出版人。你只需要有能力、勤奋、有活力、理智、充满善意。这些不应该是难得的品质,也不应该得到很多荣誉,因为你要么天生就有,要么就没有。这就是运气。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工作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你并没有发展出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天赋。
但是出版业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现在很多编辑都不做文稿编辑了。现在有的编辑基本上是做交易的,他们有助理编辑或副编辑为他们做实际的编辑工作。我在这一行成长的时候,哪怕这个编辑就是出版社的负责人,也往往是要亲自做编辑工作的,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会帮他们。现在则要分裂得多,出版行业也变得复杂得多,激烈得多,狂热得多。
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我所回望的黄金时代是被克瑙夫等人视为“懒汉的时代”,而战前的出版业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你无法判断时代潮流是否真的变坏了,还是你根本就落伍了,不再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