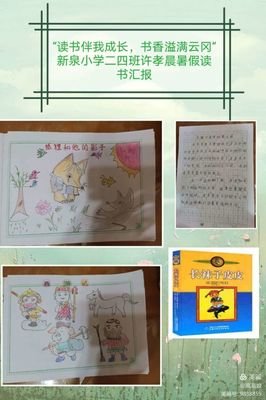庚子故事集读后感精选
《庚子故事集》是一本由弋舟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1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庚子故事集》读后感(一):轻盈、柔软、圆融
能否坦诚的面对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有的修行。
最近和朋友在讨论,我们得接受生活中我们力不能及的部分,承认自己有不足、会失败。这样人生会轻松许多。这不是消极,而是不得不有的坦诚。在《核桃树下的金银花》中,这个近二百斤的胖子就承认了自己的力不能及,坦诚的面对自己,在此基础上做出努力,找到了于劳作中蕴含的责任与义务自重的美德。能否坦诚的面对自己,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修行。
庚子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在这段特殊的经历中,我们内心变得更柔软更圆融。
这一年是弋舟的本命年,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而他的故事也难免带上此时此境的印记。《掩面时分》中,写到因为被关在家中,外出也得戴上口罩,许多的东西被遮住了,世界仿佛停滞,而许多之前没有理顺的事情,终于有了理顺的时间。故事里人在这个特殊时期,对生活进行了理顺,学会了容忍自己和理解世界。而我们,在这掩面时分,也可以琢磨一些原本无解的问题。无论是故事里的人还是故事外的我们,都变得更加柔软和圆融。
弋舟的故事语言温柔灵动,给人的感觉轻盈舒适。在特殊时期或某些艰难时刻,会在这些故事里读到些许盼望和慰藉。
《庚子故事集》读后感(二):时间经过2020年
庚子年,是弋舟的本命年。多思,乃有所得。名为《庚子故事集》,包括五个短篇。
五个短篇都在结尾标明了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写于2019年7月,最近的一篇写于2020年5月,每次搁笔之时,弋舟会否吁口长气呢?一些时间被封存,另一些时间将开启。
评论家吴晓东说过,时间意识是现代小说的自觉意识,作家没有自己的时间感受和体验,想要成为卓越的小说家是不可能的。《庚子故事集》自始至终流动着弋舟的时间意识。
疫情改变了2020年的人际相处模式,口罩成了所有人须臾不可离身的防护。《掩面时分》,戴上口罩的姜来显得很轻松,就像一半的不轻松被遮住了,在世界停顿下来的当口,那些悬而未决的往事也有了清理的机会。弋舟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起自己写作的缘由:“诚恳其实是一个无能者对于自己的解放。”这句话可作《羊群过境》注脚,在这个特定时段,众生如羔羊,那些久疏的情感也要依靠“诚恳”重新梳理,达成与家庭、与世界的和解。
《庚子故事集》有诚恳,经过审视的诚恳。作者若有所思,作品引人深省。
《人类的算法》,写于2020年2月,这个故事与后面那两个具有庚子年时间特质的故事不同,它更多地沉浸于私人体验。人物被放置于沉湎回忆的私密场景,她逐渐明了,现代人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大数据”这样的技术手段缔造的,爱的契机,只是恰好推送的附近的“ID”。我们真正的生活,如我们感觉到的那样的现实,它同我们以为的现实差别如此之大,最终被公开和阐明的生活,就是文学所揭示的内容。
与时间紧密关联的,是空间。五个短篇都在结尾注明了写作地点:香都东岸。我猜想,这是弋舟的寓所。大约是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意味浓厚的城市社区。“城市”历来是现代小说的书写对象。弋舟写了《鼠辈》。在这篇小说的语境,“鼠辈”并非用来骂人,它指向的是那些隐遁在迷宫一般的空间,无法追寻的人和事。小说一再引出历史学家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作为线索,暗示《鼠辈》想要表达的主题,在于城市变动而消失的过去。
较之对被讲述时间与空间的探索,并通过它对叙事人物亲历事件的探索,弋舟的小说创作更关注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核桃树下金银花》是整部集子最好的一篇,是杰作。主角被设定为一个快递员,一个193斤的胖子,一个因为模糊地址四处无着的倒霉鬼。这部小说在时间上,可分作两半,前面是“遇见”,后面是“归返”。在后面部分,主角不再从事快递工作,成了家族企业的少东家,一个他自嘲的“公子哥儿”。某一天,他回到这个城市,寻找当初帮助他的胖姑娘,然而,时移世易,时间不会为谁停留。
听上去很像烂俗的言情套路,但它实际上是反套路的,是超越生活层面的心灵的飞升。精简、机智与凝练是公认的好的短篇小说的标准,《核桃树下金银花》以其出色的完成度而出类拔萃。偶然并置的人和时间的流动彼此共振,它们好像自动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主角离开之后,久久无法忘怀。他的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回来,才能重启。与此对应,“玉林街”,或者每个城市可能都有的人民路、解放路等,“路”之前往往还被冠以东南西北或者一二三四,但凡缺少一个锚点,人们就会迷失在喧闹都市的荒凉之地。
假设这部小说是言情的,它所说的,也不是男女之情,而是更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情。是被抛掷的、边缘化的、原子化的个体,与无法捉摸的、庞大的虚化的集体力量的抗衡。所以是新手快递员,他要穿越陌生的疆域;所以是胖子,他要蔑视肉身的桎梏。这是现代奥德赛的城市寓言,寻觅精神的家园。我甚至认为,那个胖姑娘,只是他臆想的、分裂的一个人格,他需要以她建构起另一种现实的真实,寻找那个丢失的自己。
在时间洪流的孤岛上,他在写作,在城市空间的缝隙里,他们在流离。在顿悟的时刻,我们是否能以超越时空的静思展开对2020年的这场阅读呢?
《庚子故事集》读后感(三):在凝固中盼望,在彷徨中寻找安定
转眼今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时间的节奏,在不平凡的年份里显得尤为快速。像是做了很长的一场梦,突袭的疫情改变了一切,连回归庸常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代自序中“钟声响起”的“钟声”,象征着世界如常运行中由无数的社会角色构建成的一种秩序。庚子年,面对失控的一切,人们将如何重建新的内心秩序?
读完《庚子故事集》或许也无法确切解答这个问题,但是能体会到在遭遇困境的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的情绪,没有所谓的出口和结果,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在“凝固中盼望”。
核桃树下的金银花
一直自诩失败者的男胖子,每每心情颓丧时,只能坐在唯一认得的核桃树下哭泣。他的体重在一百七十三斤至一百九十三斤之间浮动,状态好的时候振作起来减重,能降到一百七十三斤,状态差的时候自暴自弃,又飙升至一百九十三斤。他的快乐和悲伤,如同肉体重量的变化,隐藏在这区区二十斤的摆幅之中。终有一天,男胖子参悟了自己的人生,不再纠结于体重的变化,“不过区区二十斤”,生命的意义本不应受限于体重,而体现在精神的重量上。
在四月的玉林街,男胖子骑着三轮车,不停地寻找着,并不是为了把货要送到目的地,“寻找”本身就是他出走的意义所在。在“寻找”途中,邂逅了另一个“我”,这个“我”安抚了我,让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失败的胖子。这另一个“我”让男胖子发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就算是与主流审美相左的胖子,也可以活得舒坦、自在,她的存在就像路边核桃树下开满的金银花,一个风向标,在精神上指引着男胖子,让他在失落时不至于沉沦。
当男胖子摆脱了失败者的自我定义,在人生边上行走得游刃有余的时候,他回想起十几年前记忆中的女胖子,那个翻版的“我”。几经周转打听得知,她已经在汶川地震中丧生。然而她和“核桃树下的金银花”,已经带领男胖子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她一起“寻找”着什么的那种状态,就是男胖子与女胖子的自我探索、自我和解之旅。
人类的算法
人类的算法:数字150代表了人类认知能力被允许承载的极限,只有在这个极限之内,人才能以一种富有社会效益的方式记忆和回应他人,因此,这个定律是人类社交野心的制动器,人际关系不断增多,只能导致超载,而超载,就意味着翻车。——罗宾·邓巴在茫茫的人群中,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突然有了巧遇,你的取景框里出现了他,对方又恰好看到照片,就这样以一种浪漫的方式,走入了彼此的人生轨迹中。寂寞的两个人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总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嫁给我吧”,没得到任何回音之后,第二天之后两人中断了联系。她小心翼翼地留存了他的胡茬,辞了职,回到了三口之家的生活中,而他给她微博私信了“我结婚了”之后就移除了对她的关注,变回149的总数,给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限腾出一个余额”。
无法说清,你与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一个选择,一个行为,加上点巧合,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境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诸多巧妙缘分,缘来缘去,顺势而为。在人际关系之中,你掬在手中悉心呵护的情谊,也许在对方的场域里只是一个交往的可选数额而已。不执着于关系,不依赖于关系,能少受点伤。
我们一直在满怀期待地等待梦醒,同时也在学着适应偏离轨道的生活,试图在不确定中抓住一些固守的事物来安放惶惶不可终日的自我。读读《庚子故事集》,也许会少些彷徨,感觉更安定些。
《庚子故事集》读后感(四):专访|弋舟《庚子故事集》:文学介入现实,需要诚实
本文原载于2020年9月16日澎湃·文化课
作家弋舟今年疫情爆发时,弋舟待在西安。他整日宅家,几近封门。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或许不算太过难熬,但铺天盖地的消息也足以叫他坐立难安。
就在那段非常时期,他总听见窗外有钟声响起。这钟声来得古怪,声源不明,每天只在午后两点和傍晚六点这两个时刻准时现身。
“你开始怀疑,没准儿,许多时刻,你那所谓的理性,也只不过是自以为是。”
“腿真的是被关住了。耳朵貌似依旧自由。但你早就明白,这人间,从来都有着对于耳朵的囚禁。更多的时刻,人还会充耳不闻,自我拘囿在听觉的牢笼里。”
“往日,你并不觉得有一座大钟在你生活中的存在,就像你并不察觉这世界是在如钟表一般地运行着,无数个你无视的人,人构成的组织,齿轮一般的咬合转动,才支撑起了你轻慢的生活。”
……
他将自己内心的波澜写进一篇《钟声响起》。而钟声究竟来自哪里,它为何不响够二十四下,是弋舟至今想要解开的谜底。
9月,弋舟“献给这个本命年”的小说集《庚子故事集》由中信·大方推出,这篇《钟声响起》作为代自序也被收录其中。《庚子故事集》主要由五个故事组成,有人说,这是一本2020庚子年的记忆保留之书。
今年9月,《庚子故事集》由中信·大方出版。但它并不是一份简单的记录。对弋舟而言,“怀疑”或许最能形容他在这段日子里的个人状态。他怀疑自己,也怀疑写作,“语言,字词,是我工作的基本材料。那段时间,这些基本材料被动摇了。那些既往被我们用来描述世界、说明自身的语言,突然间变得不那么准确和好用了。我甚至对‘隐喻’这个曾经津津乐道的词都怀有生理性的厌恶。就像一个面包师突然不再信任面粉和奶油,这很要命。”
在这样的怀疑之下,《庚子故事集》“非常难写”。按弋舟的话说,“此刻,我们活得有多难,我写得就有多难。”
尽管新作不到十万字,但它依然为今年的现实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固化的场景与正反分明的人物之外为我们了解与想象这个庚子年提供了更多微光。它起码提醒我们,人类的痛苦并非只来自健康,人类的孤独并非只源于隔离;它也提醒我们,在医护之外还有很多人正默默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生活秩序,在口罩之下还有很多隐忍不发或难以言说的心事与秘密,在疫情之外人类还有很多“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以及孤独与爱。
近日,弋舟就新作《庚子故事集》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庚子故事集》内页澎湃新闻:因为疫情,你的生活与写作节奏有了哪些改变?到今天为止,你觉得自己的节奏恢复了吗?
弋舟:显著的事实是,上半年的节奏的确是被打乱了,也真的是让我领教了何为失措。时间似乎倒也充裕了,但仅仅充裕的时间,原来并不足以令我们活得从容与写得从容。除了物理的时间,原来,我们更加受制于内心的时间。这种“内心的时间”,兼有空间的性质,它是立体的,时而一望无垠,时而空前逼仄,我们因之空茫或者窒息。
时至今日,一切似乎是有所“恢复”了,但我知道,这种“恢复”感,更有可能源自我们渐渐“习惯”了。时光之下,有些事物,大约是再也无法恢复了。
澎湃新闻:疫情发生以来,你因为什么有过最难受的时刻?在那些艰难的时刻,你想起过你的小说人物吗?
弋舟:写完《掩面时分》的那个晚上,手机上看到一组剪辑的视频,镜头里是流浪在高速公路上的长途车司机,阳台上鼓盆的女子,追着殡仪车哭喊亲人的女儿……那一刻真的是痛苦万分,积压已久的情绪几难自控,我哭得满脸泪水。我想,这应该是人类普遍的情绪,在一场整体性的灾难面前,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切己”的由头,人类本身的苦难,就足以令我们痛彻心扉。这组视频配有音乐,是那首《只要平凡》。于是,我把这句歌词也加进了小说里: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这样的情绪,不过短短半年时间,现在都已觉得有些遥远。我们是多么容易遗忘。回答你这个问题,令我重温了这样的情绪,我发现,它是如此的宝贵。
那些日子里,一个人关在家,是有自己小说中曾经写过的人物在脑子里浮现,但我很难一一指认他们,只觉得他们也在这尘世,一同受罪。
《庚子故事集》内页澎湃新闻:《庚子故事集》的《代自序》给了我很多触动。它定稿在今年的2月10日——国内“抗疫”依然十分艰难的时候。“午后2点的钟声”在你的生活中真的存在吗?按你的说法,它完全是“现在进行时”中的情绪。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想到它会是新集子的“代自序”吗?于你而言,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弋舟:它真的存在。我自己一度都怀疑是否有了幻听。为了佐证,我专门在那个时刻站在窗前录了音,连续录了几天,让它确凿地成为了一个“真”的存在。然而如今它却没有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重新沸腾的市声湮没了它?是自己再度粗糙的内心屏蔽了它?还是真的有那么一个人间的机构,只在特定的日子里敲响钟声?这是一个重大的谜面,我一定会专门去寻找一下答案。
这篇文章也是应刊物的约稿而写的,彼时,文学似乎也仅仅能做到这些。当时完全没有计划让它成为一本集子的“代自序”,我没有这样的习惯,出版的书从未有过序言。但是,当《庚子故事集》决定结集时,我发现用这篇文章来做序言真的是恰切。它就是“现在进行时”的,与这本集子的“现在进行时”高度吻合,甚至也和小说一样,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构成某种我需要的混淆。而且,更重要的也许是,不把它收进来,我害怕自己无可救药的遗忘,害怕它也像那准点鸣响的钟声一样,消失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恢复”之后。
澎湃新闻:从《核桃树下金银花》里的那个下午,到《代自序》里的“钟声响起”,再到你和贺嘉钰对谈时说:“我们不属于空间,我们属于时间”……我的感觉是,“时间”在这个新集子里无处不在。
你曾说小说家是时间的捕手,“时间观”约等于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性”。我想问,疫情对你的“时间观”造成了哪些影响?
弋舟:这些对于“时间”的指认,我现在依然毫不动摇。如果说,现在我的“时间观”有了怎样的改变,那只能是——我更加地顺服在了它的脚下。最初,我们信任一个“十四天的周期”,屈指一天天地数算,就这样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数算了下来,直至“恢复”,直至麻木,直至生命中失去一个又一个“十四天”,直至坚固的成为涣散,有过的化为乌有……可是,有几个人清晰地觉察到了,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一个春天,失去了一个夏天,失去了一个庚子年。失去了时间,我们就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
澎湃新闻:说到时间,比起阿拉伯数字,以中国的天干地支来纪年更有一种周而复始的意味。你在2016年写下《丙申故事集》,又在2017年写下《丁酉故事集》。很多作家对“写当下”会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对你来说,坚持写“故事集”系列,难在哪里?你会接着写《辛丑故事集》《壬寅故事集》吗?
弋舟:“当下”与“即时性”,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象。我们也习惯于认为,自己更好的表现,更佳的创作状态,都悬挂在不久之后的他日。于是,今日留给“感受”,他日留给“加工”,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但是你看,那“今日”的钟声瞬息便被湮没,被外部世界湮没,也被我们的善忘所湮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及时地提起笔来?
提起笔来,结果当然有粗糙的风险,有被证伪的可能,但至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愿意忠诚于自己的局限,我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暴露出怎样的状态,我没有必要“装得像托尔斯泰一般优秀”。就像这本集子说到的:我活得有多难,我写得就有多难。
至于继续写《辛丑故事集》《壬寅故事集》,目前来看,应该是会的。我不敢确定,但我期望我能够写下去。
澎湃新闻:《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其实写于2019年,你为什么想到也把它们放进《庚子故事集》?
弋舟:这的确是一个改变。依例,《庚子故事集》要放在明年结集出版的,并且,也只应该收录庚子年写下的故事,但这一年改变的岂止是一本小书的出版节奏?一切都被打乱了,那么,为什么就不跟随着整个时代的步伐一起颠簸?这也是这本集子“现代进行时”的一个体现,我就是想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留下属于自己的特殊痕迹。
集子里破例的事儿多了,我破例给自己的书加了篇“代自序”,甚至,还有一篇没写,就破例和嘉钰做了整体性的对话用来做“代后记”。前面的两篇收进来,也正好是一个时光的接续吧,从中你会发现,原来,尽管天翻地覆,但人的内心却并未断崖式地被改造,我们依然在那些“基础性”的困惑之中打滚。于是,在庚子年出版,也就可以叫《庚子故事集》了。
澎湃新闻:我想这本新集子和刘晓东系列一样,依然在写“时代中的人”,只是因为2020的非常事件,让这个“时代”尤其具体,意有所指,但它的落脚点还是人。
你在集子里有一句话——“我终于看到了我。”它让人想到了认识核桃树的“我”、因为旧物翻检过去的“我”,走到天台边缘往下一望的“我”……这里的“我”似乎可以是弋舟,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人,这里既有普世的况味,也有温暖的力量。如果要你自己用三个词去形容《庚子故事集》,你会用什么?
弋舟:露底。等待。熬着。
“露底”在于这本集子我完全没有想要“表现”的冲动,也没有“再上一个台阶”之类的妄想,不过是如实地兑现出此刻我既有的能力,喏,我活得有多难,我写得就有多难。“等待”的意思在和嘉钰的对话中有过阐释了,《等光来》,一如篇名,这是温柔的盼望,也是一个人应有的自尊。“熬着”就不用多说了,小说中的人们都在熬着,你我都在熬着。但这“熬着”,我视之为力量,是一场生命的盛宴。
澎湃新闻:无论是《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还是写于2020年春节之后的《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羊群过境》,它们都有关“人的困境”。这个主题也是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一以贯之下来的。
疫情当然也是人类的困境,但只是“之一”。在没有隔离的日子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依然有隔阂;在能够自由出入的日子里,人依然会懒惰、懈怠、难以专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掩面时分》里写到一句:“世界何曾太平过。不戴口罩的日子里,每个人不是照样深陷在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里。”我觉得这个表达很真实——“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面对这样的人类困境,你认为文学有哪些能与不能?
弋舟:对此你已经描述得很充分了,文学“所能”,也无外乎忠实的、准确的、富有艺术性地将其捕捉下来,这些“能”,在我看来也许恰恰是文学的“不能”。那些自以为文学无所不能的人,就让他们奔放地去“能”好了,那些自称“从未对文学绝望过”的人,恭喜他们,他们从未理解过,文学之“无能”与绝望,亦是人的根本性困境。他们感受不到人的困境,欢天喜地地追名逐利也好。
澎湃新闻:有关“疫情时期的文学”,线上线下、纸媒网媒都有很多对谈、讨论,也有很多打着现实主义名号的写作,但似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有效性也在下降。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在你看来,文学应该如何与现实生活重建关联?
弋舟:这样的难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也开不出什么药方,只能说:如果文学真的能够有效地介入现实生活,我所认为的唯一前提便是——诚实。你不能一面赞美英雄,一面对于自己的自私毫无羞耻,不能一面天花乱坠地表达着文学理想,一面提笔就是表演。自私其实没那么不堪,是你得直面自己的私欲,表演也可被理解,但是你一边表演要一边懂得害羞。